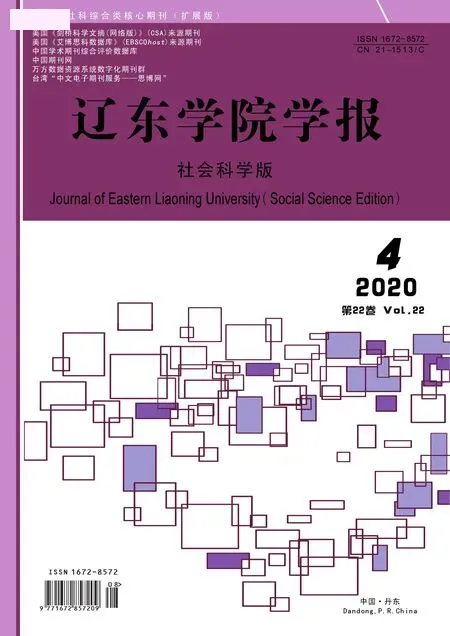《汉魏名文乘》的成书及其汉赋观
——明代书坊对汉赋传播与普及的贡献
2020-07-20曹祎黎
曹祎黎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明代是继宋代以后,中国古代印刷业的又一个大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汉赋接受的重要时期。由于明代——尤其是晚明市民经济和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以商业出版为主要业务的书坊焕发出蓬勃生机,形成了北京、南京、建阳、常州、苏州、湖州等多个书坊聚集地。其图书的生产和销售,不仅为书坊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也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重要途径。本文试以《汉魏名文乘》一书为例,探究明代汉赋接受过程中商业出版途径所起到的作用及其意义。
一、 《汉魏名文乘》成书考
福建建宁地区自宋代起就是著名的印刷出版中心。至明代,建宁府下属建阳县的出版业更是盛况空前,屡见史册。《嘉靖建阳县志》有载:“书籍出麻沙、崇化两坊,昔号图书之府,麻沙书坊毁于元季,惟崇化存焉。”[1]1成书于弘治年间的《八闽通志》对此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建阳县麻沙、崇化二坊,旧俱产书,号为图书之府。麻沙书坊元季毁,今书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书坊所刻者也。”[2]534除了刊刻之外,建阳县崇化里还有专门进行书籍交易的集市:“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3]1据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一书,可以统计出从明太祖洪武年间至明思宗崇祯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开设的书坊中可考的有253家,其中建阳67家,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仅比位于南直隶的金陵略少。而杜信孚的《明代版刻综述》则著录有明代书坊四百余家[4]1,那么按照概率推断,明代建阳书坊的数量应为百家上下。
明代建阳书坊的发展,主要以家族经营的模式展开。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所述,明代建宁地区迄今可考的书坊堂号有84个,绝大部分都在建阳县,且主要集中在余氏、刘氏、熊氏、杨氏等出版世家的名下,其中余氏书坊最多,共有20家[5]267-269。建阳余氏从宋代起就是著名的出版世家,清代叶德辉《书林清话》载:
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且当时官刻书亦多由其刊印。……余氏刻书为当时推重,宜其流传之书,为收藏家所宝贵矣。[6]46-47
明代万历年间,余氏书坊和建阳刻书业一起发展至巅峰,成为建阳刻书行业中最大的家族,“双峰堂”“萃庆堂”等余氏书坊名号常见于明代坊刻本图书之中。
《汉魏名文乘》的编者余元熹、张运泰便是晚明时期书林余氏的成员。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书林余氏重修宗谱》有载,余元熹乃建阳书林余氏第三十七代、萃庆堂主人余泗泉之孙,字延稚;又据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所考,张运泰,字来倩,乃明末古潭(今湖南长沙)人,就业于建阳书坊[7]298。他们二人合作刊刻的图书现存只有《汉魏名文乘》一部,见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8]1。
《汉魏名文乘》,又名《汉魏六十家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二人皆闽中书贾也。所录凡六十家,盖杂采何堂《汉魏丛书》、张溥《百三家集》二书合并而成。”[9]1765据此可知,本书是由余元熹、张运泰二人,将西汉初年至曹魏正始年间著名作家之重要作品和著作,或全录或节选的编成别集,而后又将这六十部别集纂成一部总集。全书以赵晔的《吴越春秋》为始,以嵇康的《嵇中散集》为终,是一部以作家为单位的汉魏诗文总集。
《汉魏名文乘》全书版式不甚一致,张运泰所作序言部分四行十字,四周单边,无鱼尾,版心刻篇名及页码;余元熹用以代序的《文始篇》及张运泰所作《汉魏名文乘选例》皆六行十四字,四周单边,无鱼尾,版心刻篇名及页码;正文部分九行二十五字,双行小字同,四周单边,无栏线,无鱼尾,版心刻书名、卷数及页码。全书大致以作者年代先后为次序,别集之内不分卷数,亦不分文体,文中有圈点,文末有总评。
关于此书编定的时间,书中没有标明,只《汉魏名文乘选例》之后有张运泰的落款,题曰“壬午孟夏日”;又有张运泰在所选桓宽《盐铁论》的题辞后落款云“嘉靖癸丑闰三月朔旦”。按嘉靖元年(1522年)即为壬午,嘉靖癸丑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从这两个日期似可直接推断本书是于嘉靖元年至嘉靖三十二年间陆续编纂刊刻而成。但该书所录东汉王充《论衡》的题辞落款却为“黄道周石斋氏识”。黄道周乃晚明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政治家,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因抗清被俘,壮烈殉国。《明史》黄道周本传有载:
(黄道周)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玑》及《太函经》,学者穷年不能通其说,而道周用以推验治乱。殁后,家人得其小册,自谓终于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来也。[10]6601
由此可知黄道周终年六十二岁,则推其生年应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再由陈旭东先生考证,余元熹之祖余泗泉为万历时人,卒年应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泰昌元年(1620年)之间[11]。结合以上信息,则署名为余元熹、张运泰的《汉魏名文乘》似无可能刻于嘉靖年间。嘉靖之后的“壬午”之年有万历十年(1582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和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但万历十五年时黄道周年方两岁,不可能为本书题辞;而纵观此书中“玄”字都未避康熙皇帝玄烨之讳,因此也不可能刻于清康熙年间。余元熹之祖余泗泉的生年与黄道周有所重合,有可能与同为福建人的黄道周交游往来。结合以上线索,比较合理的推断应当是本书始编于嘉靖后期,但直到崇祯十五年左右才由余泗泉之孙余元熹编撰刊刻完成。
二、《汉魏名文乘》的编选思想及体例
作为一部杂选众家、诸体兼备的文学总集,《汉魏名文乘》有自己的编选思想。
该书卷首有张运泰序一篇,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其一是文学的社会地位问题。张运泰在序言的开篇便指出了文学对国家、社会的重要作用,所谓“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必以文”,作为一名文人“欲报国恩,惟有文章”。接下来,张运泰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汉魏文章的喜爱和推崇:
记束发学古文,辞慕汉魏人文之盛,怕以储书弗广,莫能纵涉为恨。……念汉兴值燔书之余,文体丕茂,绝学则推陆贾、董仲舒,绝才则推贾谊,以至刘安之辩博,司马相如之瑰丽,扬雄之奇倔,篇章骚赋溢于秘府,迄今诵习不衰。中兴以还,著述寝炽,若桓宽、荀悦、蔡邕、刘邵诸子虽稍尚整缛,咸以作者名世。降而至于魏代,一门之横襟掞藻,七子之搦管流葩,亦依稀与龙门《史记》,扶风《汉书》相雄长。[8]2-3
这段话从学术、修辞、文风这三个角度对汉魏的重要作家予以简要点评和概括,字里行间流露出张运泰对西汉文学的尊崇。东汉文章已较西汉为弱,魏代文章则更是等而次之。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张运泰有自己的看法——“世数迁转使然”。这说明张运泰认识到了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作品的发展是与时代变化紧密联系着的。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文学作品都天然的与其所处的时代发生着或显或隐的联系,也表达着对其所处时代的认识。在这样的文学发展观之下,作为两汉“一代之文学”的赋理所当然地会因其对两汉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成为本书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
余元熹在其代序《文始篇》中呼应了张运泰的观点。余元熹认为研究和阅读文学作品,首先要做的是“溯其始”,每种文体都有其源头和典型代表,论及赋体文学时,他说:
赋则古诗之流也,《汉书》曰:“不歌而颂曰赋。”《左传》言:“郑庄公入而赋大隧之中。”荀卿、宋玉之徒演为别体,而敷布其事。[8]9
余元熹的论述完全继承了班固的观点。随后,余元熹进一步强调了文采的重要性,所谓:
《典》曰“慎徽之”,《礼》曰“秩之”,《乐》曰“谐之”,《帝载》曰“缉熙之”,虽无意于文自不容于不文也。[8]6
三代圣贤所作神圣严肃之经典虽不以辞藻称胜但也不能毫无文学色彩。这样的要求亦使余元熹在编辑本书时不得不认真关注那些以恢宏富丽、辞采飞扬而著称的汉赋。
该书除了上述两篇序文之外,还有张运泰所作《汉魏名文乘选例》一篇,张氏在其中再次强调了汉魏文学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对于汉赋,张运泰以邹阳、枚乘、扬雄、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为代表作家。不过就本书正文所选的汉赋来看,张运泰和余元熹两人既没有对这些代表作家的作品照单全收,也没有对未在此提及的作家作品置若罔闻。这也正符合了其自陈的编选思想:
世之辑选,多取习传,岂知英雄之心灵各辟,古今无不翻案之文人,亦无不开必先之风气。读之而精其理,博之而求其归,褰裳以就,予胡恤焉。[8]11
“古今无不翻案之文人”一句,鲜明地表现出一种晚明社会所特有的破除陈旧腐套、反拨传统观念的时代气息。
《汉魏名文乘》对每篇选文都做了圈点,批评则以文后总评为主,对于文字、音韵、名物、典故的注释极少。其总评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从它书抄出的杨慎、张溥、陈仁锡、陈继儒等明代名人之论,二是余、张二人自己的见解。每篇选文文末的评点只有一条,因此无法就同一篇目将余、张二人的评点与其所引名人评语对读比较,是为本书的一个缺憾。纵观本书体例,每位作家别集之下首列独立成书的著作,如贾谊之《新书》、董仲舒之《春秋繁露》等,次列颂、书、诗、策等单篇作品;若该作家入选的作品中没有独立成书的著作,则将这些单篇作品以文集形式列于总目录之中,如《张平子集》《蔡中郎集》等。但无论哪种情况,赋全部被列于每部别集的最后,这很有别于以《文选》为代表的赋列首位的文集编纂传统。包括赋在内的单篇作品在全书总目录中都并无体现,如扬雄之作在总目录中只有“《法言》”一项,别集前的题辞也只论《法言》而不及辞赋,只有别集目录中才显示有他的辞赋作品。这一做法应该来自《汉魏丛书》的编纂方式。
三、《汉魏名文乘》所录汉赋篇目及其评点
《汉魏名文乘》全书共选两汉赋16家45篇,分别为:贾谊《旱云赋》《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董仲舒《士不遇赋》、东方朔《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上林赋》《子虚赋》《长门赋》《大人赋》《美人赋》《哀二世赋》、王褒《洞箫赋》、刘歆《遂初赋》《甘泉宫赋》、扬雄《解嘲》《解难》《太玄赋》《逐贫赋》《长杨赋》《羽猎赋》《河东赋》《甘泉赋》《反骚》、冯衍《显志赋》、班彪《北征赋》、班固《答宾戏》、班昭《东征赋》、崔骃《达旨》《七依》《西征赋》《反都赋》、马融《长笛赋》、张衡《应闲》《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思玄赋》、王逸《荔枝赋》、蔡邕《释诲》《遂行赋》《协和婚赋》《青衣赋》。
通过观察这些作者和篇目可知,张、余二人所选的汉赋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从入选作品的时代上来看,虽然编者反复强调自己对于西汉文学的推崇,但本书所选赋作却以东汉为主。这样的选择是符合两汉辞赋创作和留存状况的。现存汉赋作连残篇、断句和存目在内一共三百余篇,其中产生于西汉的作品仅六十余篇。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优中选优,又要不落俗套,无疑是一个极难完成的任务。因此本书所选的西汉赋作均是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基本可以体现西汉赋作的整体风貌。
其次,从本书所关注的汉赋作家作品上来看,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这“汉赋四大家”的作品全部有入选,最多如扬雄共有九篇,最少如班固只有一篇。张运泰在选例中列举的两汉六位赋家中尚有邹阳、枚乘,但这两人却没有作品入选。张、余二人这样的编纂方式,应是以各位作家的存世作品数量是否足够编为一集为考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张、余二人独特的汉赋审美。本书既称“名文”,那么对于所选作品便当以“名”为重要衡量标准之一。邹阳的赋作现存《几赋》和《酒赋》两篇,均为小赋,影响有限,本书不录可以理解;枚乘的《七发》也未能入选,考虑到余、张二人将崔骃的《七依》列于书中,可知《七发》的落选并非出于辨体的需要。这应该能够证明张运泰在《选例》中所说“英雄之心灵各辟,古今无不翻案之文人”并非虚言。
在这一编选方针下,《汉魏名文乘》对王逸之赋的关注值得注意。王逸本不以辞赋名世,其辞赋作品现存只有三篇,分别为《九思》《机赋》和《荔枝赋》,后二者为残篇,历来不甚受重视。明代只有八部文学总集收录了他的赋作,而收有《荔枝赋》的更只有包括《汉魏名文乘》在内的五部。可见张、余二人所选的确颇有“心灵各辟”而欲为王氏扬名翻案之意。
其三,张、余二人所作赋评也时有独出机杼之处。如张运泰评贾谊《惜誓》曰:
贾长沙一腔热血,全副经纶,《惜誓》一篇则悲壮激宕,不能自已。盖以灵均之香泽雕玉露之芳馨也。[8]129
点出了《惜誓》一文在贾谊全部赋作中与众不同的风格特点;又张运泰评《羽猎赋》曰:
昔人谓子云赋在班、马伯仲之间,以其博伟雄丽,缛组之中自有生气也。乃如文无生气,即累牍连篇,总压人目。[8]560
“有生气”三字可谓一语中的,点出了《羽猎赋》的精神所在,使《羽猎赋》的巨丽蓬勃之美如在眼前;另外,余元熹评崔骃《反都赋》云:
人心所向,天命攸归,帝王所兴,向有天数,在德不在险,良非窾郤。[8]64
《反都赋》的立意与《东都赋》一样,都是论述洛阳作为东汉帝都的合理性,其中有“客有陈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陈祸败之机,不在险也”之句。余元熹此言从字面上来看,不过是重复了崔骃的观点,但崔骃作此论时,东汉初建,方兴未艾;而余元熹作此评时,大明已是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余元熹在此言之外,或许更有一些感于时事的沉郁之情。另外,余、张二人作为书商却直接参与到对汉赋文本的评点当中,这在此前及同时期的同类型汉赋选中是仅见的一例,值得注意。
四、《汉魏名文乘》所选汉赋篇目与同时期其他汉赋选的异同
参与市场竞争、尽可能获取利润是坊刻本图书最重要的使命,不论书坊刊刻何种书籍,其最终目的都是营利。营利性是坊刻本与其他刻本、抄本的本质区别。张运泰、余元熹二人在编纂出版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时,首先考虑的一定不仅仅是文本本身的价值,而应是作品的市场号召力,以求其能够最大限度地打开市场、获取利润。因此本书在篇目选择上与同一时期文人所编的汉赋选存在很大差异。
我们可以将本书所选汉赋篇目和与那些和它篇幅相当、时代相近的晚明其他重要文学总集在选录篇目上稍作比较(表1)。

表1 《汉魏名文乘》与其他汉赋选所录汉赋篇目对照表
表中所列陈仁锡所编《奇赏斋古文汇编》、张燮所编《七十二家集》和张溥所编《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均为晚明重要的文学总集,亦均为杂选众体之作。《汉魏名文乘》所录的45篇赋作中,与《奇赏斋古文汇编》重合15篇,与《七十二家集》重合34篇,与《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重合43篇。检视四书在汉赋选篇上的异同,可以发现《汉魏名文乘》一书的编选特点。《汉魏名文乘》与《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在篇目上重复最多,其原因在于后者本就是前者重要的文献来源,这一观点早已由四库馆臣提出,现通过篇目对比可证其确。《汉魏名文乘》与《七十二家集》相比,其篇目差异主要体现在刘歆、班彪、班昭、崔骃、马融、王逸、蔡邕等人的赋作上;与《古文奇赏汇编》相比,《汉魏名文乘》在选篇上的独特之处更多,既有对于同一作者不同赋作的扬弃,如贾谊《旱云赋》《吊屈原赋》、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崔骃《反都赋》等;也有对同一作者的不同态度,如《奇赏斋古文汇编》对董仲舒、东方朔、蔡邕、王逸之赋的摒弃。从其他三书未录的篇目来看,这些赋作的并非因为辨体因素而被摒弃,因此这只能说明张、余二人的汉赋审美和编选思想确与其他三书不尽相同。尤其是与《奇赏斋古文汇编》相比,《汉魏名文乘》“求全”的意图更加明显。
张、余二人之所以选他人所不选,除了说明其自身反传统的编纂思路之外,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其所选汉赋在晚明作为文化产品进行流通之时所具有的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和影响力。《汉魏名文乘》对于所选篇目并没有进行详尽高妙的注解,也没有进行长篇累牍的点评,只是在篇末以总评稍加解说。这一做法除因余元熹和张运泰个人学术水平有限之外,更是为了适应普通读者的阅读水平和阅读兴趣。这一做法使《汉魏名文乘》与其他三部文学总集在内容、风格和体例上有所区别,从而扬长避短,各为所需。
五、《汉魏名文乘》对晚明汉赋接受与普及的作用
虽然张运泰在《汉魏名文乘》的序中,将此书的编纂过程和选篇列体的标准描述得十分精审,所谓:
上者探其旨,次者衡其篇,又次者考其辞。其篇之长者,固取气势结构;其长而节录之者,亦取简重,不妨芟蔓。[8]4-5
但此书在编纂和刊刻中也没能避免建阳坊刻本图书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一为篇名舛误,如扬雄《反离骚》目录作《反骚》而正文作《反离》,崔骃《大将军西征赋》目录仅作《西征赋》等;其二为版式不统一,如每部别集题序署名或在文首或在文末,全书序、选例、目录、正文的版式和字迹也不尽相同;其三是印刷粗疏、字迹漫漶。至于评语署名托伪名家,内容改头换面之类的问题更是时有出现。不过从促进本时期汉赋接受的角度来说,该书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汉赋的接受过程始于它产生的当时,司马迁在《史记》中便对其进行了大量记述,后经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的相继收录而获得了最初的文献积累;至南北朝时期萧统《文选》和刘勰《文心雕龙》的相继面世形成了中国古代汉赋接受的第一个高潮;唐、宋时期,汉赋的传播和接受主要依靠类书的收录以及“《文选》学”的兴起和发展;元代,科举的因素开始作用于汉赋的接受历程,祝尧的《古赋辨体》应运而生。到了明代,影响汉赋接受的因素更加多样,在文学评注的兴盛、文学思潮的尊崇、文学创作的追摹、文学选本的勃兴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汉赋接受达到了第二个高潮。而以上四个因素的社会背景是明代出版印刷行业的高速发展和市民生活的极大丰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就直接影响到了汉赋作品传播、接受的广度,其中像余元熹这样的书坊主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坊刻本图书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其生产内容与社会需求的关系也较其他类型的刻本更为密切。虽然各个书坊的主要出版内容不尽相同,但一切出版内容以市场为中心、以满足社会各阶级的不同需要为目标则是其共同的生存基础。与其他行业的生产活动不同,书坊的生产活动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它会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而反过来,社会文化的风气也会作用于书坊的生产活动。
《汉魏名文乘》的编选和刊刻正能说明这一点。作为一部生产于建阳书坊的文学总集,它明显的具有建阳坊刻本所普遍存在的优点和缺点,这说明它所面对的主要消费对象不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精英知识分子,而更多的是那些以一般性阅读为目的的普通读者,因此它在篇目编选和注释评点这两方面都必须符合目标消费人群的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汉魏名文乘》的刊刻出版以及其中所选的16位汉赋作家45篇汉赋作品有赖于建阳地区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和余氏家族在晚明商业出版领域的重要地位,无疑会对当时当地的汉赋消费起到带动作用,既扩大了这些汉赋作品的传播范围,也促进了这些汉赋作品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尤其是那些在同时期文人所编的文学总集中未收的汉赋作品,恰因本书对其的青睐而获得了更大的传播和接受空间,也获得了成为经典的更多可能。
由于现存的由书商独立编选刊刻的明代汉赋选仅见《汉魏名文乘》一部,我们难以得知明代商业出版背景下诞生的其他汉赋选的编选情况;并且《汉魏名文乘》的发行量及其发行范围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因此也难以知晓其影响力的具体大小。然而从《汉魏名文乘》这样一个例子管中窥豹,不难想见同时期的其他书坊也一定会刊刻出版有各类汉赋选。这些以营利为目的、充满商业特点的汉赋选构成了明代汉赋接受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汉魏名文乘》一书出身于行业竞争激烈、图书质量参差不齐的建阳书坊,却在经过编者筛选之后录入多篇汉赋,更有书商亲自参与评点,这说明晚明汉赋传播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台阁士林,在普通文人甚至普通百姓中间,它也被广泛地需求着,是当时重要的文学审美对象。可以说,以《汉魏名文乘》为代表的坊刻本汉赋选从汉赋文献的保存和汉赋文献的传播两方面对晚明汉赋接受及其普及起到了自己独特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