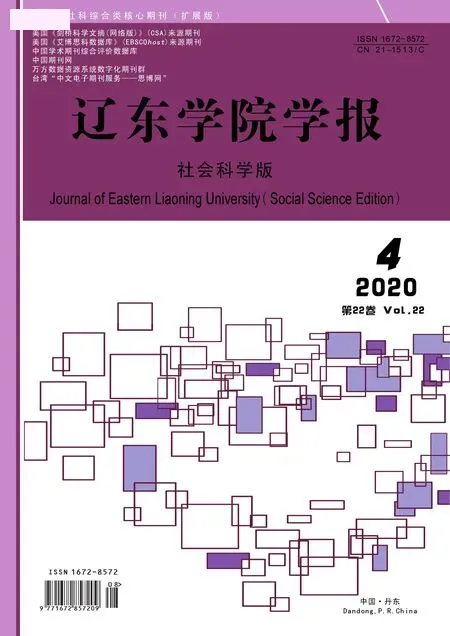20世纪韩国世态小说的叙事与美学转向
——从《川边风景》到《无名花》
2020-03-03何元航朱明爱
何元航,朱明爱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济南 250100)
一、韩国世态小说创作概述
世态小说是指对某个特定时期的民间风俗或社会生活的单个或多个侧面进行描写的小说体裁,亦称市井小说或风俗小说[1]。该类作品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的细致考察反映社会发展的轨迹和面貌,将看似琐碎的人情冷暖与众生百态在文学作品的世界中重新建构,使之成为社会一角的缩影。韩国文学史中有关“世态小说”的定义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文学评论家崔载曙对《川边风景》的评论,他表示:“《川边风景》描绘的是隐匿在都市一角里的世态人情。”[2]此后,世态小说凭借以小见大的视角及细致入微的笔调成为韩国文学领域的新兴创作模式。
作为韩国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朴泰远(1909—1986)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都十分独特,他善于通过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描写,借助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表现生活本身内在的巨大力量和丰富内涵。在他看来,文学本身具有独立性和艺术性,对功利主义文学不屑一顾。《川边风景》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首尔市民的生活状况,记录了韩国的现代化过程及当时的世态风俗,揭示了现代都市的本质特征,被称为“韩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梁贵子在1987年以短篇小说集《远美洞的人们》成为令人瞩目的天才小说家,并作为继朴泰远《川边风景》后又一部优秀的世态小说而获得20世纪80年代短篇文学精髓的高度评价[3]。她的另一部世态小说《无名花》获得1992年李箱文学奖大奖。作为新兴创作手法的主人公小说,《无名花》将作家的自我省察与独白纳入对20世纪80年代世态描写的过程之中,以独有的观察视角和细腻的语言结构将市民的情感与社会的变化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文学评论家洪正善说:“梁贵子是20世纪80年代小说界诞生的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中的一位,她尽可能地向我们展现生活中的真实和具体。”[4]
学界将《川边风景》纳入世态文学这一研究范围始于林和的评论。他把该作品归于“世态小说”,指出作品既没有塑造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也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缺乏思想性”,是“非长篇的长篇”[5]。这之后虽然有相关研究将其纳入“都市小说”的范围,但依旧没有脱离世态小说的研究范围,基本上是围绕人物建构和叙事类型这两个角度展开论述。梁贵子被称为世态文学的集大成者[6],其作品也被纳入相关视域进行考察。《无名花》作为令人瞩目的获奖佳作,学界的研究视角包括对话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等,但尚未从世态文学的研究框架下对其进行详细的阐述,在文学批评和艺术审美的领域留下了较大空间。
世态文学的产生从其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具体社会现实因素的再现,其中包含着作品所反映的创作主体意识。也正因为韩国世态小说与韩国近代以来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因此透过世态小说可以完成对社会发展格局与面貌的一次审视,在此过程中可以剖析创作主体的社会思维和主观审美。本文以朴泰远的《川边风景》和梁贵子的《无名花》为研究对象,从叙事类型和审美方向的差异入手,纵向比较不同时期韩国世态小说的特征,以期有助于韩国20世纪文学作品的批评与审美研究。
二、韩国世态小说的叙事转向
《川边风景》和《无名花》成文于不同时期,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两部世态小说在叙事类型方面存在着不少差异。
(一)叙事空间:由静态都市到动态旅程
朴泰远出生于1910年的韩国首尔,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化进程不断深化,韩国城市化进程也被迫加速,客观上给韩国的经济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朴泰远儿时的成长环境恰好位于首尔的繁华地带,药店、酒吧、酒店、理发店等现代商铺云集。横亘首尔的清溪川,在地理位置上为当时殖民地时期的首尔划开了界线。在《川边风景》小说中所描写的清溪川边的都市空间,便是以此为背景展开叙述。清溪川所划分的南北,区分了日本人和韩国人不同的生活面貌,但小说中构建的现代化迹象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都市化政策的反映。和信商会、韩青大厦等鳞次栉比的现代式建筑为这里在表面上勾画了现代都市风貌,在历史的进程中衍化为传统和现代相互交融的地区。不论是小说《川边风景》中人物活动的现实空间,还是对20世纪30年代首尔地区的写实表达,作为日本统治下殖民地空间的缩影,都市在朴泰远的叙事模式里有着典型的象征意义。
与《川边风景》中选择“都市”这一静态空间不同的是,小说《无名花》中以“归信寺”为目的地构建了往返程的动态的旅行空间。梁贵子在文中先是表明在归信寺的巧遇才使得这篇小说的诞生成为可能,后又说明出门旅行是为了寻找写作灵感,随之就是整个旅行过程形成小说结构:去程─—归信寺相遇——归程。小说旨在构建一个情景交融的叙事空间,通过旅程中的所见所感,作家将自身经历中存在的悲痛用细腻的语言进行描述,使其最终化成一股力量,而文中所表达的美感也依照旅行空间与个人情感的交替得以增强。在作家的成长经历中,梁贵子毕业于国学专业,后又在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这些经历使她在有意无意中接受了美学的熏陶,并将其大胆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在她的小说中,人物的情感往往伴随着适当的情与景的配合,以景物煽情,借景物寄情,增强了小说的美感。”正因为作家在空间布局上不拘于单一的静态考察,使得该小说的叙事结构更加多元化。
由此看来,韩国世态小说中所构建的空间想象并不相同,其中“世态”的概念随着创作主体的改变而发生迁移。透过《川边风景》和《无名花》两部小说的叙事空间转变,可以看出小说建构的背景依托作家的成长时代,同时也与作家的生活背景、个人体验和文化感知息息相关。
(二)叙事视角:由主观全知到客观平视
在建构小说人物体系时,朴泰远采取的是一种富有主观性的全知叙述视角,使得作家的主体精神得到了充分发挥。在小说《川边风景》中,采取全知视角使得作者能够掌握作品中每个角色的行为认知与心理动态,通过俯视的角度实现对世态人物的观察与记录。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实现了自身的人物化,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则成了作者所构建的价值体系的总和。在小说中出现的“闵老爷”内心所展示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在作者的笔下一览无遗,这便是作者将人物内心活动旁白化,使得人物的形象得以丰满、立体[7]。同时,《川边风景》中的人物塑造并非将某个典型人物作为主人公进行着重描写,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分布在社会各行各业,不同阶层之间的众生相在作者笔下公平地呈现出来。作品中描述了七十多个人物,全知叙述视角使得作者与作品人物往往合而为一,通过客观观察与主体叙述相结合,使得每一个角色都能全面地展示个体的形象特征。
《无名花》被称为作家主人公小说,在内容上突出了小说的创作过程,同时兼具对现实生活细腻具体地描写,采取的既不是男性作家惯用的俯视视角,也不是传统作家对于女性的仰视视角,而是令自己置身于作品中,用平视的、客观的角度去描绘生活的本来面目,通过作者内心独白这一独特的叙述方式展现自身的生活状态。在作家与丈夫作别前往旅途时有过一段心理描写便是很好的例证。这段心理描写中,丈夫的平静令作家羡慕,他的平静与作家为小说灵感的苦恼相对比,更令作家觉得委屈、不公平,甚至后悔全部的写作人生。平静本身不是一种难得的状态,但是在作者的主人公位置上却显得非常遥远。正如1992年李箱文学奖授奖词中所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原本对小说创作的意义最为敏感且卓越的作家反而陷入迷途。《无名花》既具有自传体小说的亲近感,又具有旅游小说的安定感,采用告白式写作,以作家主人公小说的方式如实地描绘出现实的困境,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韩国文学创作的新特征。
两部作品在叙事视角上的差异可以反映韩国文学在不同时期的时代映照。20世纪30年代的韩国社会存在差异性和多元性,在殖民地话语体系下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而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则呈现出同一性和离心性,后工业社会强调物化的意识体系同经济效用性的消费时代相辅相成,但往往使个人情感诉求得不到充分表达,以至于作者渴望内心的“平静”。
(三)主体表达:由现实批判到个人回归
《川边风景》从小人物的众生百态着手建构一种真实的社会风貌,在勾勒人物形象的同时,将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性格特征纳入民族道德情怀的评价体系之中,不同的人物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能够迅速捕捉作者的价值传递。在顺东这一人物的形象塑造中,作者将其“勤劳”“节俭”“诚实”等人物特征进行强化,同时以“三峰”作为对比,突出作者的价值导向。现实主义的作品往往立足于动态的社会发展。在他的笔下,阶级的划分并非由资产多少而决定,相反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相应的生活姿态决定了他们的堕落或进步。而作者心中的评价标准自然是传统伦理道德所赋予的价值观。正如林和指出的“精神的风俗,人性的世态”一样,他在这部作品中所体现的情怀实际上是对传统伦理与道德仁义的呼唤,在刻画中产阶级的虚伪与丑陋时,也将解决问题的方向引导至民族文化的优秀内涵当中。
在《无名花》一文中,梁贵子将个人的态度和观念融入作品当中,在情感的处理和把握上比较模糊,虽然有别于朴泰远深刻而直接的价值引导,但通过对细节的主观处理和客观烘托之后,作品内容反而显得更为朴实、真诚,在情感的表达上更是是入木三分。靠根维系的无名的秋之花朵、被风干了的屋檐下的风磬、寺院后山上自然生长的古老柿树,皆给人一种寂静安然、古老质朴的安详神秘之感。然而,回忆和想象都是为了衬托真实的世态风景。在回忆与现实的对照下,被剥得精光的、一裸到底的屋顶才是现实状况,长着幽静的花被沙堆覆盖才是真实情景。作者在想象和现实之间综合自身的感受,通过自述的方式将目之所及的鲜明图景呈现出来。
世态小说的叙事对象决定小说传递的价值指涉,不论是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生存对比,还是主观想象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实感差异,从一定程度上说,世态小说所反映的主体表达都是在时代价值体系的映照之下完成的。梁贵子也曾经说过:“所谓小说,就是对人类理解的方式;而人类本身就是小说。”[8]《川边风景》和《无名花》分别植根于韩国社会的不同时期,其中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也有所不同,却暗合着从殖民地时期到后产业时期韩国社会发展的现实。
三、韩国世态小说的美学指向
韩国世态小说与其他文学作品相比而言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即便如此,在近六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以《川边风景》为代表的作品和以《无名花》为代表的作品之间也产生了不同的美学指向。
《川边风景》反映的世俗是以狭义的世俗为基准,而《无名花》中反映的世俗与世态生活是以广义的世俗为基础。朴泰远在建构都市空间时,着重叙述的对象不局限于某一个个体,而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将社会群体囊括在内。《川边风景》中虽然人物形象和风格有所不同,但人物关系还算平等。但是梁贵子的作品将这种社会群体进行分解并重构,即对环境氛围进行细节描绘,对小说人物进行立体性塑造,以主人公金钟九的日常生活为主线进行细节刻画,以恰如其分的情景交融呈现世俗生活。这样一来,小说中所体现的世俗特征看似有所“离地”,但在理想与精神层面却得到无限放大,作者并非仅从物质主义的角度去书写,而是强调在包括理想和精神世界里的广义的世俗生活中实现世态格局的建构与完善。
如果说世态小说是将过去围绕历史、战争和英雄人物进行宏观创作的作品类型进行的一次微观处理,那么20世纪80年代世态小说则是对20世纪30年代世态小说空间的再一次缩小,由客观物质生活移向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状态。《川边风景》所塑造的都市空间的典型环境与《无名花》中所构建的社会环境的多样性实则是由宏观叙事往微观发展的一个重要策略。“典型”之所以存在,那就是因为具有代表性,虽然都市空间在韩国20世纪30年代有特殊存在意义,但不同社会的发展经历相同阶段时会产生共鸣,而梁贵子笔下的社会环境随着作家的心理活动不但发生变化,甚至在“回忆”过程中也与过去印象中的形象存在细微差别,创新了刻画世态的方式与方法。
《川边风景》的创作主要围绕社会群像的刻画,但《无名花》却以自身的实感为基础来映照社会的面貌。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作家的内心独白和自我省察如实描绘出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的困境,二是从其丰富细腻的现实认识呈现作者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与失意。朴泰远通过人物描写表明了对社会现象的态度,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十分具有戏剧色彩,在文中勾勒了阶级有序、善恶分明的世俗面貌。在梁贵子笔下,现实生活里处处都是从回忆中感知的深刻体验,哪怕是看到“连翘丛中的狗洞”都夹带着自身的实感。在《无名花》的刻画中,作者以通过自己不断反思与省察从而在社会中保持冷静的“旁观者”姿态,面对社会给予自身的压力,作者将其视作灵魂的逆向考验,在反思个体的同时类推社会的困境。
从这一对比中可以看出,作家主体意识的扩大是世态小说发生转向的重要特征之一。强调“主体意识”的意义在于,意识中有“我”,作品中才能表现好非“我”。作者主体意识的缺失必然带来作品主心骨的缺失——即审美追求的不足。立足20世纪80年代韩国社会背景可以看出,随着产业社会后期的来临,强调个人主义和物质至上的价值体系和经济效用性的消费时代相辅相成[9]。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作家文人数量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文学的格局变得有所不同。如此一来,小说家的待遇相对萎缩,作品生产却日益丰盛,小说家所面临的压力愈来愈大,这种压力与不安使小说家在创作道路上陷入困境与彷徨。以作家为叙述者诚恳地吐露小说创作的困难,可以称为文学创作领域一次全新的尝试。
《川边风景》的价值指涉立足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原始道德品性的复兴,在作者笔下的七十多个不同的人物,面对生活的挑战,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姿态去应对,有的顺应现实,有的积极抗争,有的则只能延续着不幸的生活。文学即人学,在与自己生活相近的“镜子”式的现实作品面前,对人性本身的自我批判也更为强烈。而《无名花》更加重视作为个人内心与生活日常的回归,以及对本能、爱情等细节的深切关注。20世纪80年代韩国文学将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在文学作品中不断放大,相比历史人物与社会事件的宏观叙述,底层人民内心的细腻、郁闷与彷徨则被更多地展现出来。《无名花》中对文学创作困境与迷途的告白,以及对金钟九潇洒自由的生活姿态的描绘,都属于对当时文学创作环境缺乏稳定性的如实呈现。这里的世俗性不是与阳春白雪相对的下里巴人,世态小说也不是高雅文学的对立面。对世俗生活加以关注,把细碎的平凡人物和生活图景呈现在小说中,可以令读者更直观地审视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平凡以及世俗中的幸福。
究其原因,不难想到韩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所经历信息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与革新,导致韩国文学的创作同样受到了商业化冲击,在文学思潮领域接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文学创作面临着多元选择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作为外来文化的一个分支,在当代市场消费话语的联手下,突破过去较为单一的宏大正史的压抑,将人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中释放出来[10]。它既为20世纪80年代小说提供了个人化的视界,也促进了文学观念的更新。同时,它也将文学置于一个大众化、无深度的尴尬境地。
四、结论
综上所述,以《川边风景》和《无名花》为代表的韩国世态小说的创作大部分是围绕某一社会时期人们的总体生活状态,包括政治、宗教、阶级矛盾等多个领域产生的不同现象。作者通过对作品中不同人物生活细节的描写和不同心理状态的刻画来反映社会整体,是一种微观式和集成式并存的表达方式。小说人物的形象塑造或思考方式大部分是由小说背景下的经济或物质条件所决定,小说中所存在或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则真实地反映出隐藏在社会群像中的个体差异。作品中往往由现象回归至对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反思,是一种由小见大、由表及里的传递模式。两部小说选取特定的社会存在来构建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学空间,在对具体矛盾的整理和表达中在原有社会模式下找寻合理的解决路径,小说所反映的只是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失序,往往通过放大失序来完成秩序的重建,是一种由反叛世俗到回归世俗的逻辑范式。
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作品《川边风景》和20世纪80年代作品《无名花》的分析,不难看出,韩国世态小说呈现出独有的人文蕴涵与美学风貌和小人物叙事的书写格局。从历史、战争素材为主的宏观叙事走向市井社会生活视角下的微观白描,世态小说所展示的是浓汁厚味的市井风情。如主人公小说一类的作品中通过强烈的自我表现带有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更加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与独特的艺术风格。淡化故事情节,笔触多涉及人文景观,诸如风土人情、文化氛围、艺术时尚等等,小说非情节化的过程已悄然发轫。审美不仅限于“美”,对“丑”“平庸”“悲”“喜”等世态的真实描写日益深化,同时追求平谈自然的美学风貌,逐渐扫尽语言文字上的烟火与铅华,使美感更为真实、贴切。
总体来讲,世态文学是以社会生活为创作素材,而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特征,所产生的主流审美限制了主流文学的创作方向。在这种判断之下,通过突出被工具意识压迫的无意识的角度,从内部展现具有颠覆形态的文学表达,韩国文学解构式创作也变得丰富多彩。韩国社会生活变化丰富,是世态文学创作的沃土。研究和评价相关作品时要立足时代背景和创作主体,把握作品中蕴含的社会多样性和情感灵活性。随着韩国世态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渐渐获得更多关注,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