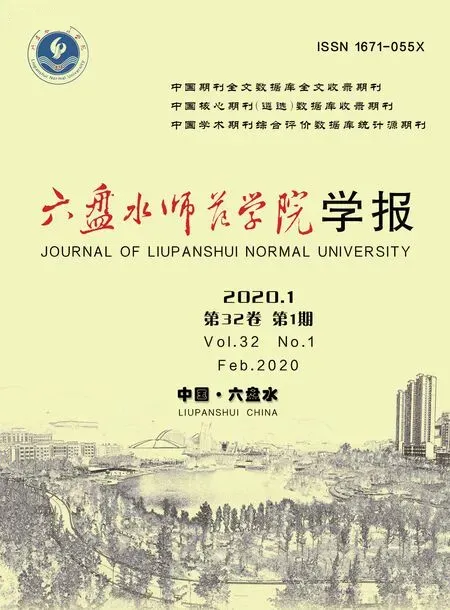记忆之魅与人性觉醒
——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2020-03-02陈沙沙
陈沙沙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有研究者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奠基是从对过去,尤其是十年‘文革'中所推行的极‘左'的文艺政策、文艺观念的凌厉批评起步的。在时代倡导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新时期文学担当了先锋角色。”[1]20世纪80年代初,控诉与反思是文学主要的话语方式。但铁凝没有加入这一合唱,《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以清新幽默的笔调叙述了后革命时代一个女中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故事。但细读文本,又能在这种轻松中品出作者掺杂的一些“文革”记忆,在涓涓生活中传递出的对时代的凄楚感受,而这些记忆又多被研究者悬置。本文从这些被悬置的“文革”记忆出发,探寻铁凝对于时代独特的反思方式。
一、纽扣的“束缚”——“文革”记忆的纠缠
作家的神经往往最先感应到时代的变化,新时期文学充当了时代“先锋”角色,在政治的拨乱反正之前,以美学的方式对“文革”给个人、国家和社会造成的伤痛进行揭露与批判,反思“文革”也就成了当时文学的主潮。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发端,一大批“伤痕”“反思”小说涌入文坛。如方之的《内奸》,通过田玉堂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在与各色共产党人的对照中,揭示了“内奸”这一角色的复杂的内涵;戴厚英的《人啊,人!》,则立足对“文革”时期人性的拷问,呼唤对人的尊重。整体来看,书写“文革”所造成的苦难是这些小说的共同指向。不同于当时立足于政治而言说政治的叙事,《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另辟蹊径。小说没有直接面对“文革”的惨痛,而是以平易市的中学生安然评“三好学生”为线索,在安然一家的日常生活中展开叙事。安然明显不同于《班主任》中深受“左”倾思想毒害的谢惠敏,不同于《醒来吧,弟弟》中对真理失去信仰的“弟弟”,安然是一个活泼可爱、自主而有个性的女孩,在她身上有着一抹时代难有的青春亮色,是新时期一个极富时代色彩的形象。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充盈着安然一家鸡零狗碎的琐事,反复出现的“文革”记忆主要是借助姐姐安静的回忆予以碎片化展现。小说从日常的角度切入政治对普通人的影响,“文革”记忆就像带有纽扣的衣服束缚着人们的身体,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小说中的妈妈在“文革”之前是那样美丽,对生活充满热情、富于幻想,还会写些“缺乏逻辑”的诗歌。在“文革”开始时,妈妈“积极投入运动”,不辞劳苦地满大街贴大标语,渴望被划入“红五类”的行列。“文革”后,妈妈既失去了青春,又被原单位抛弃,对生活总是充满了怨恨情绪。妈妈本想在政治上追求进步,最终却成了被政治所抛弃的“弃妇”,时代扭曲了妈妈的心理,使亲人走向了“敌对”,她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作者从她那烦躁和暴怒的情绪中,很准确、很富有特征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给她带来的深刻影响,这影响甚至使她与自己的女儿之间都失去了起码的信任和理解。”[2]生活中的任何小事都会触碰到妈妈敏感的“政治神经”,她在得知安然私下与男同学外出游玩后,将之界定为“思想复杂”。仅凭异性交往就对他们的思想性质做出评判,夸大异性交往的严重性,这表现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恐惧。西美尔认为现代人因为城市空间和文化疏离而患有精神“畏触症”[3],但妈妈的交往恐惧,却是极左时代人与人之间因为政治带来的冷漠与对立所留下的心理疾患。
安然的班主任韦婉在新时期依然作出“我高攀着民族灵魂的火箭”“用自己的痴情,遥望那布满宇宙的红旗”的“甩膀子诗”。时代变了,但韦婉依然停留在“文革”的氛围之中,自觉保持一种“文革”时代的步调,想象以“连自我衣着都不顾的‘忘我'精神”去为教育“献身”。韦婉还穿着不合时宜的老式大背心,像坚持“防患于未然”的消防员,像侦探一样密切关注学生的各种变化,心里时刻绷紧的还是那根阶级斗争的弦。于是,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就成了问题少女的表征,对于学生时尚的衣着服饰与正常的异性交往如临“大敌”,始终保持着敏感的政治神经,结果是把学生中的一切问题都视为政治问题。“极左”政治的时代已经逐渐远去,但那些惯常的记忆依然纠缠在心,走不出日常生活政治化的阴影。时代吹来了新气息,但妈妈与韦婉依然用“文革”时期的革命伦理来打量人与人的正常关系,人际关系依然是不自由的,仍然遭到革命伦理评判,“人道伦理”并没有恢复。有研究者指出:“‘人道伦理'之实现与遭受伤害往往首先体现在最为基本的人际关系中,一大批‘伤痕'、‘反思'小说均表现了‘革命伦理'对于人际关系的伤害,并且试图以‘人道伦理'来取代‘革命伦理'从而建立新的人际关系。”[4]在这里,铁凝对妨碍新时期人际交往的革命伦理的批判,其意义还在于通过日常生活的层面,揭示历史对现实的铭刻。在一次访谈中,铁凝说:“安然的特立独行正反衬出了社会集体的麻木,反衬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还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反衬了过去的黑暗与禁锢仍在人们的身上留下的后遗症。”[5]没有纽扣预示着一种解放,同时也暗示着另一种无形的禁锢:一种革命伦理对人的观念和生活的控制,“文革”历史给人们心理造成了创伤。“文革”对亲历者的伤害,提醒人们实现由革命伦理向新时期人的解放、人性自由的精神进阶的艰难。对历史沉疴、无意识深处幽灵的展示,这正是小说意味深长的地方。
虽然新时期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文革”历史留在人们心里的阴霾还很难在短时间内去除。平易市有了新的时代气息,三十年前这座古城是灰蒙蒙的,现在的青年已经穿上宽脚裤,青年农民也带着迈克镜,街边的膨香酥代替了烤红薯。但商店还是很少,新店的门窗依然是黄配蓝,且新旧混杂。吊诡的是,商店橱窗里的塑料模特“在气温高达三十六度的季节,他们还未换下厚呢大衣,二人蓬头垢面,脸色焦黄,目光呆滞,躲在半开半闭的葱绿窗帘里,无可奈何地向街上行人摊着两手”,商店里的玻璃橱窗目的在于展示商品,在视觉上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但平易市橱窗里的模特却在夏季还穿着冬衣,人们似乎还停留在过去的时光里。小城人的生活表明“人们的精神世界还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反衬出了过去的黑暗禁锢在人们身上留下的后遗症”[5]。平易市新旧掺杂,也是整个时代的缩影,新的东西虽然已经莅临,但心灵深处的“过去”并没有真正消逝。陈旧的过去依然左右着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就像商店里的橱窗,夏季的模特还穿着冬衣,虽然突兀怪异,但人们见惯不惊,自然也就习以为常了。过去的“文革”记忆犹如鬼魅,处处遁形,但又无处不在,它会时不时走出来对生活指手画脚。
二、罅隙之光——多重规约下的成长
在五四文学中,个人化的叙事比较明显。随着后来的革命文学,尤其是到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个人化叙事逐渐让位于集体宏大叙事。“文革”结束之后,个人化叙事依然受到政治话语的挤压,“伤痕”“反思”文学中展现的主要是被政治化了的日常生活。铁凝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选择现实日常生活,通过对日常生活之于人的合理性展开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肯定日常琐碎生活的价值意义。这对当时主导文坛的宏大叙事观念和经典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无疑是一种突破,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活的原生态处理和强调日常生活的审美经验,其实铁凝已经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做了成功的尝试”[6]。小说以“后革命时代”一个中学生的成长揭示“文革”记忆对现实生活的纠缠,以中学生的成长环境展示出社会的多重规约,从小说的立意与表现角度上看,具有开拓意义。
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等多方面的影响,在他们的身上能看到很多家庭观念、学校教育和社会规范的影子,有了一定自主观念和独立思维的中学生则可以成为时代的面影和镜子。从他们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成长和他的思想是如何被社会接纳或规训的。因而铁凝选取的中学生这一形象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新时期的“伤痕”小说中也有以中学生为中心人物的,如《班主任》《伤痕》中的谢惠敏和王晓华,但她们已经被政治化了,作者通过她们表达的更多的是政治因素,而中学生的心理、生理特征和情感世界很少得到展现。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中学生形象“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对安然生理、心理特征、性格的描绘和情感世界的呈现,让读者“感染到了某些时代情绪”[7]。小说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个维度呈现安然的日常生活,安然作为一个未成年学生,不管其思维如何独立,她的成长还是需要父母、老师等人的正确引导,安然的家庭、学校和社会不仅对安然的成长起着引导的作用,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规约。
家庭在文学中多被塑造成幸福的港湾,总是萦绕着温馨的气氛,但在安然的家里,家不仅是避风港,也是家庭矛盾的漩涡。妈妈和爸爸经常吵架,姐妹俩经常给父母劝架。妈妈脾气不好,也不甚关心家人,父亲对子女也较为冷淡。安然谈论父母的婚姻时说道:“在他们身上我看不见……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爱情。”[8]92整个家庭的气氛算不上特别“和美”。青春期的安然活泼可爱、有个性,她顶喜欢佐罗的下巴,最近也爱照镜子了,还喜欢和男同学刘冬虎一起学英语,安然的情感在懵懂中发芽。当妈妈发现安然与男同学一起学习英语、外出划船后大发雷霆,本是正常的人际交往,但妈妈却质问安然:“你了解现在的孩子吗?复杂着哪!”“复杂”二字给安然的男女同学关系定了性,他们眼中的“复杂”意味着腐朽与堕落。“文革”历史的负担通过母亲的教育向安然传递,特殊年代的特殊观念通过家庭教育仍然束缚着新时代的安然。“五四”启蒙文学中重在对“人”的提倡和重视,这个“人”指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个性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当时的文学写作来看,这一启蒙话语关注的并不是‘人'的个性,而只是要把‘人'从旧有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9]。即这时期的人的解放注重的是把人从“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想中解放出来。母亲作为“红外围”难以实现对安然的正确引导,安然的出现正表明了作者对日常生活中隐含的政治批判。
教师作为学校的知识主体在思想品德和学习上对学生起着引导作用。班主任韦婉提醒安静,安然现在打扮起来了,在学校穿没有纽扣、后面带一条拉链的红衬衫,并总和男同学刘冬虎在一起。“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在班主任韦婉眼中成了问题的表征。作为学校知识主体和教育主体的韦婉并未与时俱进,依然处在“极左”话语的梦魇下,培养着守规矩、受其“驯服”的“好学生”祝文娟,依然用过去的规则对学生进行评价,力图用过去年代的观念“塑造”学生。成绩并不是评“三好学生”的唯一因素,品德和群众关系同样重要。对学生个人品德的鉴定则来自班主任韦婉,也就是班主任韦婉的权力。因为安然在课堂上指出老师的错误,在作文中写出同学的缺点,在评选的关键时刻还穿上了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安然的勇敢、诚实、个性在韦婉的教育中遭到瓦解,安然自然落了选。“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成了评价一个人品德的重要标杆,纽扣本是订在衣服上面防止暴露身体而包裹自己的,可以拒绝诱惑隔绝欲望,“没有纽扣”给人以无限的遐想,“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充满着诱惑,刺激着人们的想象空间。在穿狗舌头领的时代,“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张扬着安然的个性。有个性的安然遭到教育主体的拒绝。这不仅表明了学校给有个性的人设置的无形的规范,而且反映着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同时,“小说触及了学校的教育目标、价值观念、行为标准等,具有直接的社会意义”[6]。
安然还是一个中学生,她的生活空间主要是家庭和学校,尚未进入社会。“在小说中,安然的家庭和学校不是孤立的,透过它们反映了具有复杂因素的社会环境,这主要是通过其他人物的刻画表现出来的。”[10]安然作为成长中的学生,在社会上尚未扮演某种固定的角色。而她的父亲、姐姐、老师等人都拥有特定的社会角色。父亲在省画院搞专业创作,但他的画既“起不到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也无法获取现实利益,只能孤芳自赏。韦婉作为学校的知识主体不仅给学生传授知识,还运用有限的权力为自己谋求额外的利益。如安静为了安然评“三好学生”给韦婉带来的利益,帮韦婉发表又红又专而文学性差的“甩膀子诗”,给韦婉送电影票。韦婉凭借自己的身份和权力心安理得地收受这一切,二人在无形中达成了某种利益关系。诗歌刊物本是纯文学杂志,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要求。编辑安静为一己之私,不惜违背原则刊发了韦婉的诗。韦婉的那首诗传播的并不是艺术,而是暗地交媾的利益。安然评“三好学生”这件小事却拉扯多人,人们都在为自己谋求利益,最终勾连成社会中无形的利益链条。个人利益最小化的年代已经渐行渐远,新的时代社会正在转型,价值观念也在改变,安然身上的正义、诚实、勇气、创新的品质在新时期的日常规范中遭到瓦解,看不见的社会中的利益网络正日益规范着安然的个人成长。
安然的确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抹光亮,但个性独立的安然的成长势必面临着与社会的冲突。她的成长受到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三重规约,并在规约下艰难地成长。父母身上的“文革”记忆仍然缓缓地向安然渗透,学校的育人规范制约着安然的个性,价值转型下的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塑造”人。铁凝通过中学生安然的成长环境呈现的“文革”历史的负担,学校教育的规约以及社会中无形的束缚,不仅表现了社会价值转型的现实语境,也展现了个人的成长与社会规范的冲突,无疑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
三、“扔掉”纽扣——人性解放的期待
“我妹妹是个女孩儿”“她是个地道的女孩儿”。叙述者在文中多次强调安然的性别,故一些研究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及其母亲表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强烈、明朗,将这篇小说置于铁凝整个女性主义创作的过渡阶段[11]。安然作为一个有强烈性别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女孩儿,表现的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对自我身份的内在确认。但小说中的妈妈,自我的女性意识是模糊的。在“文革”前后,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好,总吵架,而母亲不为爸爸缝纽扣、熨衣服并非是反抗家庭束缚、男权压迫的表现,更可能是性格所致。联系时代背景来看,对安然性别身份的强调真正传达的是性别觉醒中蕴含的人性象征意义。
安然性格活泼,平时大大咧咧,一副“男孩子的秉性”,最近也注意自己的容貌,爱照镜子了,还喜欢穿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并大胆说出“我真漂亮”,并且申诉到“我早就知道你们都拿我当男孩子看,其实我是个女的,女的!”“男孩子秉性”的安然关注自己的性别并声明自己的女孩身份,实际上是在寻求性别认同。而且安然凭借着女孩的细腻、敏感,以独特的艺术感悟对爸爸那幅只画了一半且没有名字的风景画赏析,将落叶飘向大地解读为自然对大地母亲的回归,将其起名为“吻”。安然没有将“吻”字局限于男女恋情,而是丰富和拓展了“吻”字的内涵和深度,将其理解为一种赤子之心和对于母体的皈依。安然摆脱了革命时代对感情过于单一性的理解,张扬了感知世界的主动性和创造性。80年代的新人文话语,以高扬个体的“主体性”,强调主体身份为主要特征,性别意识也是主体的重要内涵。铁凝在文中对于安然女性身份的反复强调正是对特殊时代“男女都一样”的政治话语的挑战,女性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因而小说中的姐姐安静才会想起“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那个以被人称‘铁姑娘'‘假小子'为荣的年代,那些不男不女的装束,那些不男不女的发型。虽然我没有朝着‘铁姑娘'、‘假小子'的目标打扮,可也很少注意自己是男是女”[8]106。在那个时代,女性是被作为和男性同等的劳动力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看待的,政治掩盖了性别差异,人被同质化为劳动者,甚至物化为劳动力的存在。人的丰富性受到政治的规训,如果过于注意个体容貌或强调性别身份,就有可能成为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甚至被视为小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意识。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人的阶级性、革命性或反动性进行了全面、明确的定位分析,不同阶级在政治上有着严格的区分。在“文革”时期,政治性和阶级性被“极左”分子进行极端化演绎,人与人的关系被革命化、阶级化。正常的人际关系被简化为“革命”“同志”等关系。这种简化的结果,不仅抹杀了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也无情地掩盖了性别的差异,实质上是对人的本质化处理及人性的异化。在特定的时代,女性和男性一样获得了全方位的政治和社会权利,成为与男性同等的国家主体,但在文化表述层面上,女性是以“男女都一样”的形态出现,女性实际上是“无性别”的存在,是政治催生的“第二性”。进入80年代,当代中国人文思想界的主导潮流是对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主流思想的文化批判,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话语的批判。因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人性解放在此又一次浮出历史地表。于是,“在80年代的中国,作为对‘阶级话语'的反拨,性别成为标识人性的主要认知方式”[12]。人性的解放通过性别的重申,表现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自由和个性的承认。这才是铁凝会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强调安然女性身份的原因。
同时,安然的成长环境勾连着“过去”与“现在”,通过日常生活的具体语境,言说新时期善良纯真的人性人情,以及人情人性在记忆纠缠中苏醒的艰难与酸楚,从侧面进逼文学中的意识形态话语。革命时期人与人之间分阶级、论同志,不谈感情,“爱”“想念”“喜欢”这一类表达私密感情的语词无形中遭到封杀,个人日常生活的一切都充满罪恶。小说中的安静谈了一个男朋友,但父母因其离异还带有一个女儿便不同意他们交往,最后“在安然的再三催促之下”,“我还是去了省城”,安然支持并鼓励“我”勇敢地追求爱情。红色代表着热情和欲望,没有纽扣则意味着对束缚的挣脱,“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具有独特的意味。安静给妹妹买了这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是安静内心的觉醒。安然很喜欢姐姐送的红衬衫,在重要时刻都穿着,象征性地表达了姐妹俩对个性释放和生活的期待。在这里表明,后“文革”时代的人们终于有了选择生活的权力,人不再是权力的附属物,更不是革命模子的产物,“红衬衫”折射的是人欲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小说中对安然性别身份的再三强调,实际上是对“极左”政治话语的反拨,是对抹杀性别身份时代的反思。虽然铁凝“不是一个社会寓言的书写者”,《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也并非铁凝对于整个社会文化和精神的寓言,但它却处处透露出铁凝对于人性与合理欲望解放的期待。
四、结语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通过日常生活中丝丝缕缕地透露着的“文革”记忆的纠缠,从日常生活层面对“文革”进行反思。家庭教育对“文革”历史负担的承载,学校教育对诚实、勇气、个性的拒绝以及无形的社会利益网络的束缚共同构成了安然成长过程中面临的规约。小说对安然的性别意识的强调实际上表达的是人性的觉醒,对世俗欲望及日常生活之于人的合理性的肯定,反映了作者对人性解放的期待,由此实现对“极左”政治对人性的压抑和文学宏大叙事的反拨。而如何在新历史的“去革命”中实现精神“进阶”,是小说留给读者意味深长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