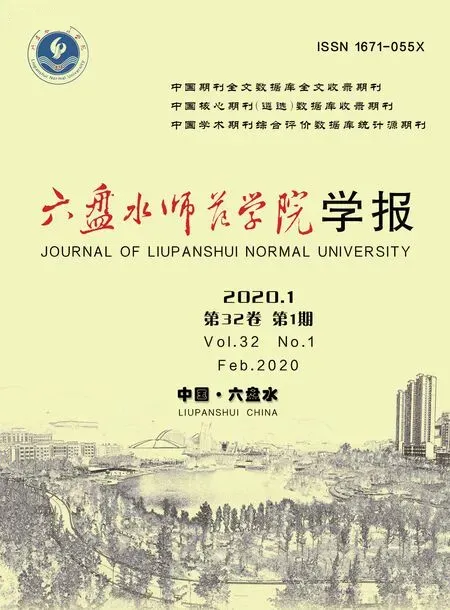论卢照邻的后期文学创作
2020-03-02周伟
周伟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对卢照邻潦倒多磨的身世以及敢于独创的文学才能的认同,使得卢照邻在后世留下了不灭的身名,并在“四杰”的并称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纵观其一生的文学创作,可以将诗人三十一岁时遭遇邓王薨的变故这一时间节点作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本文即围绕诗人的后期文学创作进行论述。
一、题材选择:政治贬谪与身世漂泊的人生书写
走出宫廷,接触市井勾栏与江山塞漠并将所见所感形诸物咏,为“四杰”乃至初唐的诗歌带来了一股鲜活的生机,也为“四杰”奠定了崇高的文学史地位。闻一多先生曾在《唐诗杂论》中专立一节“宫体诗的自赎”[1],其中对“四杰”诗歌题材的变化和视野的扩大作了细致论述,正是在深入地看到了初唐(尤其是“四杰”)诗歌的这一写作特点而得出的精辟见解。而以“四杰”为代表的初唐诗人们,他们走出宫廷接触到更广大丰富的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正是政治贬谪带来的结果。宇文所安曾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王勃、卢照邻的四川之逐,到宋之问、沈佺期的南荒之贬,再到王维在八世纪二十年代中叶的谪宦,贬逐诗为培养个人诗所做的贡献超出了其他任何题材的诗,正是这类个人诗发展成为盛唐优秀个人抒情诗。”[2]7贬谪无疑对于诗人具有强大的感发魅力。
卢照邻的一生动荡潦倒,尤以后期羁留蜀中对其诗文创作影响最大。据李云逸附录于《卢照邻集校注》后的《卢照邻年谱》[3]482-510可知,卢照邻大概在十八岁时与赏识其才华的邓王元裕相识,此后一直依靠邓王元裕入仕,之后在二十三岁时奉邓王使命入蜀,返回后跟随邓王辗转各地,直到诗人三十一岁时邓王去世,诗人又得到新都尉这样一介微职,随后就是长达七年左右的居蜀生涯,一直到三十七岁方彻底去蜀北归。此期间诗人不仅遭遇政治依靠邓王元裕的去世,还遭遇了牢狱之灾。再后来,在去蜀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诗人又分别遭遇了风疾、父忧、瘫痪等痛苦和磨难,且一直未再入仕,以隐居学道求医的潦倒姿态结束了其晚年生活,终于在不堪病痛折磨、不愿连累亲友的巨大心理压力下自沉颍水,享年在四十七八岁左右。
诗人自邓王谢世后,仕途越发潦倒蹇舛,文学创作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看到,诗人书写自己沉沦不偶、漂泊无据的诗篇开始大量地出现了,而前期那种华而不实的应酬之作明显地消歇了。这是诗人的创作开始走向自由的一个突出征兆。正是根据此,我们才将诗人在三十一岁时遭遇邓王谢世、羁旅蜀中这一时间节点作为其文学创作的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的。
由《年谱》我们能看出,卢照邻的创作高潮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时段都处在其文学创作的后期。前一个时段是蜀中的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后一个时段是晚年的文学创作,以骚、赋为主,《五悲》《释疾文》即作于此阶段。另外,这两个创作高峰又分别对应诗人的两段最潦倒穷愁的人生阶段,前一阶段是诗人遭遇人生理想受挫、长期沉沦下僚,并且遭遇小人奸谄而身陷囹圄的艰难穷愁时期,后一阶段则是诗人面临痼疾的折磨,备尝人生艰辛,甚至产生生命的信仰危机的潦倒时期。这样明显的对应关系体现出来一种明显的文学召唤结构:身世的遭遇对文学创作的召唤。正是这样的召唤,使得卢照邻的文学写作在其人生历程中体现出来明显的分层结构,而每层又明显地展现出不同的风貌和内涵;明显地感知到,不同的风貌和内涵又恰是对各自所属的那段潦倒身世的回应。
《卢照邻年谱》在“唐高宗永徽三年壬子(652)”下谓:“卢照邻十八岁。当于本年前后入长安,出入王侯公卿之门。”[3]487这段时光在卢照邻的一生中恐怕算是唯一一段色彩鲜丽的了。此后他的人生,将面临一重又一重的磨难和困苦。其实,若仔细考察卢照邻在邓王麾下的一系列活动,我们会发现,他实实在在仅仅是一个王爷身边的文学侍从。自弱冠的年华与邓王结下深厚的“布衣之交”[3]479,卢照邻在邓王身边做了大概五年的典籖、王府书记等卑职[3]483,而后长达七年左右跟随邓王镇守各州县的时间里,卢照邻充当了邓王的使者等身份。从麟德二年(665)邓王薨后诗人仅被赋予新都尉这样一介微职来看,诗人待在邓王身边的十多年时间里并没有获得多少政治资本,唯一为诗人赢得的,倒是其在当时文坛上的杰出声誉。
仕途上既缺少了靠山,诗人便只好守着新都尉这样一份卑职,直到咸亨元年(670)秩满方离去。去官之后诗人度过了一段“放旷诗酒,婆娑蜀中”[3]497的浪荡生涯。这段时间卢照邻与另外一位当时已声名鹊起的青年诗人王勃以及邵大震会面,共同登上玄武山赋诗。这次三人登高所赋的同题之作《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分别如下:
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卢照邻)[3]165
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王勃)[3]165
九月九日望遥空,秋水秋天生夕风。寒雁一向南飞远,游人几度菊花丛?(邵大震)[3]166
三首诗的叹息漂泊、寄思家乡的情感与高山秋空一道化为清远之物,明澈伤感,又带有感伤生命流逝的味道,于清空中注入复杂情感,读来极有韵味。
蜀中的游历为诗人卢照邻博得了盛炙的诗名,与卢照邻同时的文士张鷟甚至称王、杨、卢、骆的并称正是从蜀中的诗酒人生开始的:“(卢照邻)后为益州新都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4]141联系贺知章、李白等因京中豪饮的事迹而获“饮中八仙”的美誉,我们应该可以粗略地看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好恶,因此逆推过来,恐怕王、杨、卢、骆四人的蜀中诗酒生涯正是为他们赢得“四杰”称号的肇因。虽然现在学界对“饮中八仙”的具体人属问题尚无定论,但此八人大概并非同时饮于长安城中而获此称号的,而应该是由于共同在京城有过的豪饮声名促成这一并称的,那么同样,“四杰”的并称也该是如此。居蜀期间,诗人写作了大量反映自己沉沦下僚、迹如飘蓬的诗篇,如《赠益府群官》《失群雁》《相如琴台》《元日述怀》等。这些直接书写自身真实经验的诗篇,才能够获得令后世于“千载之下,为之动容”的感发魅力。
在婆娑蜀中度过大概两年的放荡生涯后,诗人北归返家洛阳,后又赴长安,随后渐染风疾,此疾缠绕其后半生,并越形转笃,终因信仰破灭、不堪折磨而沉水以终。正是这样的晚年经历,促使了诗人在文学创作中加入了大量的对人生和历史的追问与探讨。在《驯鸢》《病梨》《五悲》《释疾》等文章中,都对人生中遇与不遇、穷与达、悲与喜,以及历史的盛衰轮转等问题做了深入思考。
卢照邻后期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引起了后代人们的普遍共鸣。张燮在《幽忧子集题词》中写道:“古今文士奇穷,未有如卢升之之甚者。夫其仕宦不达,则亦已矣,沉疴永痼,无复聊赖,至自投鱼腹中,古来膏肓无此死法也。……若夫《驯鸢》《病梨》之赋,《五悲》《释疾》之文,笔端尚存,曷禁输写?乃持议者,讶其不能义命自安,亦太甚矣。因梓升之集,而详揭之。”[5]既梳理了卢照邻潦倒一生的可悲可叹处,又将自己整理刊梓其文集的缘由做了说明,对诗人的才华给予了肯定。
二、不羁之气,风骚之意:漂泊与病痛中的抒情之音
在漂泊不偶的人生中,诗人练就了一股不羁之气,后来又在病痛穷愁的压迫下,在诗文中充实了另一股早已存在的风骚之意。所谓的“不羁”,是指一种敢于表达自我真率性情的抒情勇气,其特点在于不写或少写空洞的题材事物、敢于突破传统的雅致内容。而所谓的“风骚”,即是指这种表达出来的直率性情以及贯穿在其中的敢怒敢怨、敢爱敢恨的意气。
初唐诗人们深知当时文坛重形式轻内容之弊,因此他们用充分的抒情性写作来革除这一弊病,以期找到一种足够满意的文学形态来书写人生和现实。从这一点来说,政治生涯上的诸多磨难以及人生信仰上的诸般挫折确实为他们的这一写作模式带来了巨大的资源。
来比较一下卢照邻笔下的应景酬唱诗和他由蜀中奔赴长安时写下的一首纪行诗:
三月曲水宴得樽字
风烟彭泽里,山水仲长园。由来弃铜墨,本自重琴樽。高情邈不嗣,雅道今复存。有美光时彦,养德坐山樊。门开芳杜径,室距桃花源?公子黄金勒,仙人紫气轩。长怀去城市,高咏狎兰荪。连沙飞白鹭,孤屿啸玄猿。日影岩前落,云花江上翻。兴阑车马散,林塘夕鸟喧。[3]50-51
早度分水岭
丁年游蜀道,斑鬓向长安。徒费周王粟,空弹汉吏冠。马蹄穿欲尽,貂裘敝转寒。层冰横九折,积石凌七盘。重谿既下漱,峻峰亦上干。陇头闻戍鼓,岭外咽飞湍。瑟瑟松风急,苍苍山月圆。传语后来者,斯路诚独难。[3]48
前一首诗仅仅按照社交惯例吟咏了宴席周边的人事物,表达了对于主人淡泊情趣和隐逸生活的羡慕以及对于主人的感谢,其余的并无更多的趣味。我们不妨将其与这场宴会的另一位与会者王勃的同题作相比较:
三月曲水宴得烟字
彭泽官初去,河阳赋始传。田园归旧国,诗酒间长筵。列室窥丹洞,分楼瞰紫烟。萦回亘津渡,出没控郊鄽。凤琴调上客,龙辔俨群仙。松石偏宜古,藤萝不记年。重帘交密树,复磴拥危泉。抗石晞南岭,乘沙渺北川。傅岩来筑处,磻溪入钓前。日斜真趣远,幽思梦凉蝉。[6]60
卢诗的开头以陶渊明和仲长统的典故歌咏了宴会主人的隐逸高致,王诗的开头亦用陶渊明和写作《闲居赋》的潘岳的典故歌咏了主人的高情远致。接着二诗都以描写主人风姿以及把宴会场景想象成为道家神仙环境的方式,进一步歌咏这位隐逸主人的雅致生活。最后则落实到现实风物上面,描写了傍晚时分舒和的夕阳景象,以平和舒雅收束全篇,符合社交传统。可以说,两位诗人在构思这两首诗时按照的并非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是一种弥漫于社交之中的书写惯例;促使诗歌得以生成的并非诗人的表达欲求,而是应景酬答。
那么反观《早度分水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很大的不同:诗中出现了诗人自己,弥漫着诗人充沛的感情。诗人在诗中道出了内心对漂泊游历、仕途人生、报国无门的诸多感想,内涵复杂而生动,为诗歌注入了深刻的情感和丰赡的血液。诗人不再趋附于外在的事物,而是从属于自己的内心,他的所见所感不是为外物所同化,而是同化了外物。
书写羁旅他乡、人世感怀以及生活物兴的诗篇,在诗人涉足蜀中奔波于各地之时得到了丰富和深化。《奉使益州至长安发钟阳驿》中感慨着为生活奔波的辛酸:“联翩事羁靮,辛苦劳疲恙。”又想到自己死去的妻子,不禁情不能堪、气不能平:“谁念复刍狗?山河独偏丧。”[3]53《山行寄刘李二参军》写仕途之难,声音最悲苦:“狂歌欲叹凤,失路反占龟。”[3]135拥有孔子那样的治国才能,却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蹉跎中寻求占卜的回答来安慰自己,其悲伤之情可想而知。诗人在总章二年(669)突遇横事而下狱,这一冤屈始终耿介于诗人怀中。在《赠李荣道士》中,诗人一面表达对方“敷诚归上帝,应诏佐明君”的优渥身份,一面哀叹自己“独有南冠客,耿耿泣离群”[3]46的冤苦身世。这样的政治遭遇使诗人在晚年回忆起来时犹胆战心惊:“虞人负缴来相及,齐客虚弓忽见伤。”[3]71感伤于自己的孤危处境,愤怒于小人的诋毁暗伤。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卢照邻的诗中明显地开始流露出了一种壮大的情思和气魄。《哭金部韦郎中》云:“岁时宾径断,朝暮雀罗张。书留魏主阁,魂掩汉家床。徒令永平帝,千载罢撞郎。”[3]151此诗不止于悼念故人,更包涵了世态炎凉的感怀、人生无常的凄苦、人才流逝的感伤、衷心许国的赤诚。诗中贯穿着的感情是太丰富太厚重了,以至于将祭悼的情思扩张到了无限的历史和人生之中,产生出一种壮大的情感张势。诗人去官后游宦长安一带作有《送幽州陈参军赴任寄呈乡曲父老》,云:
蓟北三千里,关西二十年。冯唐犹在汉,乐毅不归燕。人同黄鹤远,乡共白云连。郭隗池台边,昭王樽酒前。故人当已老,旧壑几成田?红颜如昨日,衰鬓似秋天。西蜀桥应毁,东周石尚全。灞池水犹绿,榆关月早圆。塞云初上雁,庭树欲销蝉。送君之旧国,挥泪独潸然。[3]149-150
全诗既包含了诗人当下所处的送别场景,又包含了诗人穷困潦倒之一生的诸般感慨喟叹。送别之地与友人将往之地之间,是横亘在漫长地界上的三千里烟尘原莽;带动思绪运转起来的是二十年的漂泊生涯;化成苦泪滴洒出来的是壮志难酬、岁月荒芜、物是人非、命运无常、离别哀思等一系列人生大恸;矗立在诗中的是诗人自己以及消散在历史烟尘中古往今来的诸多明主贤才。这些复杂不可一概的熙熙攘攘事物共同炼造成一杯苦酒,包含了历史上所有贤人穷士的遗憾和悲愁,使得这些无处倾诉、只能留给人们抱恨而终的微妙情感得以从历史和人生的深处发泄出来。总之,这首诗所包蕴的情感是太激壮太宏阔了。
到诗人的晚年,由于遭受痼疾的折磨,卢照邻对功名、人生以及历史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写作了《五悲》《释疾文》等名篇。《五悲》分别是《悲才难》《悲穷通》《悲昔游》《悲今日》《悲人生》,是对自己一生经验的系统总结,先论述了怀才难施之悲,次论述了穷通不可自决之悲,再论述了过往不可逆追之悲,又论述了今日不可挽留之悲,最后论述了人生之轻不可承受之悲。《释疾文》是诗人在经受了“羸卧不起,行已十年”的病痛磨折之后,病体稍舒之时所写的,整体上是为表达自己对“赋命如此,几何可凭”[3]239的生命虚无观的认识和体会。其中《粤若》篇效屈原《离骚》,回顾了自己仕途不遇、潦倒不堪的一生经历,诗人最后慨叹道:“东郊绝此麒麟笔,西山秘此凤凰柯。死去死去兮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3]261揭示了人生难遇乃世间常态这一历史真相。《悲乎》篇效江淹《恨赋》,指出吞悲饮恨乃人生常态。《命曰》篇揭露了生命的虚无痛苦真相,并试图以道家成仙思想对其予以超越。总之,卢照邻晚年的书写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这一突破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对抒情性写作的运用和开拓。
在当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宫廷诗风笼罩之下,卢照邻以其直书个人困顿生活以及真率感情的抒情性写作,给自己的诗歌带来了壮大的骨气和风致。后人对此颇多美誉之辞。如同时代人张鷟说:“卢生之文,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4]141其所谓“时人莫能评其得失”,正确切地反映出了卢照邻诗文内涵丰富、风格多样、体式多变、情感复杂的特点。明人帅机在《二京篇序》中评价卢、骆的歌行诸篇时,甚至持与《诗经》相媲美:“昔卢照邻有《长安古意》,骆宾王有《帝京篇》,并精新妩媚,曲终奏雅,盖‘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如不怒',二篇有焉。脍炙人口,有由然矣。”[7]
卢照邻正是从自身的实感体验出发进行文学创作,才与当时的革新者们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当时重形式轻内容的不良风气,这也就是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所说的主要由初唐“四杰”的文学创作反映出来的“唐文学繁荣到来之前的第二次思想准备工作”[8]28。如上所述,这一点在其后期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卢照邻的这一历史贡献得到了当时与后世的广泛认同。在当时有杨炯的大力推崇,其在《王勃集序》中有一段文字对唐高宗时期宫廷文学的弊端作了声讨,并对当时的文学改革运动做了这样的总结:“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薛令功朝右文宗,讬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9]274这里所批判的“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文学风气显然不止于龙朔初载,更是对整个过去的六朝隋代以及唐初的靡艳精细文风的批判。而既欲对当时的文学风气进行改革,改革者们便不得不直接对当时的宫廷文学展开攻击。杨炯在序中提到了当时文学改革运动的两大主将,一个是当时的文坛盟主薛元超,另一个就是卢照邻。杨炯的这篇序最明显地反映出了卢照邻在当时所受到的肯定。在后世,如胡应麟一方面强调“王、杨、卢、骆以词胜”[10]189,一方面也不得不指出:“先是,唐起梁陈衰运,后诗文纤弱委靡、体日益下。宾王首与勃等一振之,虽未能骤革六朝余习,而诗律精严、文辞雄放,滔滔混混、横绝无前,唐三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者为之前导也。”[11]再如近代的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独辟一章“宫体诗的自赎”用以说明“四杰”等初唐诗人对宫体诗旧弊的变革和扫除,当代也有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专辟一章“卢照邻:宫廷诗的衰退”来专门介绍卢照邻对传统宫廷诗的超越。
可见,无论是在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中,还是在后人的文学史观构建中,卢照邻的文学创作都得到了充分肯定,同时其文学史地位也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结语
在整个初唐文学中,卢照邻有着很不同于俗流的一面,尽管他也写作“上官体”那类诗歌,但他更富有成就的诗歌则是那类表现他在漂泊生涯、困顿人生,以及缠绵病榻中的痛苦和思索,这类诗歌充分反映了其沉浮于时势、挣扎于生命夹缝中的心理现实,将其精神风貌尽情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这一类书写在其后期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突出的展现。正因如此,其后期所创作的诗文在感染力上焕发出了巨大的张势和丰沛的活力,包含了深刻的人生感悟和情感蕴涵。正是诗人这种希冀表达更广大人生和世界的创作要求,使得诗人得以将自己的艰难经历转化为写作资源,创作出不固守时代旧习、多所独创的优秀篇章,从而为初唐文学的革新之路带来一股巨大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