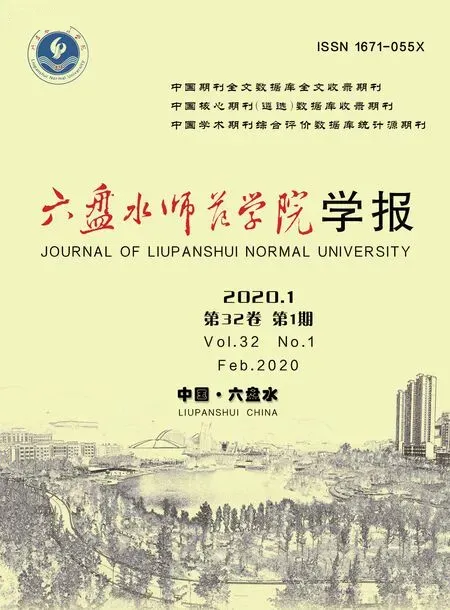生命边界的突围
——评王刚的小说创作
2020-03-02费虹
费虹
(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贵州六盘水553001)
王刚是近年来写作势头正健的作家,从2014年开始,在不长的时间内,已在《短篇小说》《民族文学》《厦门文学》《北方作家》《草地》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这样勤奋而成果丰硕的创作状态,使王刚成为贵州六盘水本土作家中的后起之秀,令人瞩目。读王刚的小说,能深刻地感知一种充溢在情节和人物内心诉求之间的强烈冲突,以及人物对自己生存的狭小逼仄生存空间和卑微的生命状态的奋力突围。同时,还能认识到王刚对自我生存状态和写作状态的不断突围和不断创新,立足于艺术的真实,在求变求新中使自己的创作不断走向新的高度。
一、人物:在人生愿望与现实之间奔突
王刚是土生土长的贵州六盘水花嘎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成长历程和返乡工作的经历都决定着他的创作冲动必然源自这方土地,这里乡民的生活和乡村学校的教学生涯给他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创作源泉。立足于这片土地的风土民情和沧桑变化,王刚在作品中着力展现其中的生活情态和本相,探索社会环境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人物在人生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左奔右突,结局则或抵达生命舒张的极致,或沉沦至灵魂消遁的深渊。在人物悲欢苦乐的人生遭际中,将一个乡镇从过去的宁静稳态走向嘈杂喧哗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一)在逼仄的生存空间中挣扎
王刚的小说大多以花嘎乡为描写范围,表现了这一方水土的山川风物、世道人心,将目光聚焦于底层小人物寻常而艰辛的生活境况,表现他们的人生梦想和悲欢苦乐。社会底层既是市场经济大潮推涌之下贫富两极分化的现实呈现,也是社会权利和生存状态失衡的一种重要表征,是20世纪90年代已降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聚焦点。描写社会底层生活困境和人生百态的小说如迟子建的《盲人报摊》《踏着月光的行板》、史铁生的《命若琴弦》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底层这样一个庞大而被忽略的社会群落,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底层生活的苦难和绝望终因作者营造的温情氛围而被冲淡。相较之下,王刚小说的底层叙事则更为暗淡,充溢着深深的悲悯和忧伤。
深陷危机的困兽之斗。《那夜灯火朦胧》中生性要强的马二为了两个孩子的教育,到深圳打工,没过半年却弄残了腿,只好回乡务农,他让老婆张翠花在城里租房带孩子读书,自己在村里不辞辛劳种地喂猪,节衣缩食将钱汇到城里供孩子们读书。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村里有传言,张翠花到KTV 当了小姐,于是怒气冲冲的马二带上板斧来到城里,核查妻子的行迹,如果传言属实,就决定用板斧结束老婆的性命。马二果然在KTV 包房见到了陪客人喝酒的老婆,而在板斧即将落下的瞬间得知妻子为了生活不得不去歌厅陪酒的事实,望着骨瘦如柴、疲惫睡去的老婆,此时的马二只剩下无奈与疼惜。《红鱼》中的马鸣曾经是一名老实巴交的乡村代课教师,妻子红草被鱼贩子阿郎勾引拐骗去后,又被抛弃,无路可走的红草沦为娼妓,最终患艾滋病悲惨地死去。屈辱悲愤的马鸣发奋致富,若干年后回乡找到阿郎报了仇。《标签》也是讲述复仇的故事。这三篇小说都以寻仇和复仇的叙事,再现了农村或城市底层的社会状态。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方面可看出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普遍缺乏基本的法制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小人物在生存空间被极度挤压、做人的尊严底线被严重挑战时被迫采取的一种极端自卫方式,是深陷生存危机的小人物令人叹惋的困兽之斗。从以上作品中可体会到乡民在卑微而难堪的生活际遇中的痛苦挣扎,也可了解到乡村在现代化渗入过程中原有的封闭格局被打破,新的格局还未建立的骚动不安的社会状况。
绝望中的呐喊。《蚂蚁的悲伤》这篇小说2017年发表于《东渡》第3期,正像篇名一样,它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为还给母亲治病欠下的高利贷,瘦小的农民安子来到矿上当了一名挖煤工。老实懦弱的安子很快成为镇上黑恶势力猎取的对象,他们给安子设了一个骗婚的圈套,在煤矿塌方时设计阻止安子逃出,导致安子被塌方的煤层活活砸死。在他死后,他的妻子白凤与其他合伙人皆大欢喜地瓜分他用生命换来的赔偿费。安子是一个胆小勤劳、与世无争的年轻人,他视为保护神的朋友胡财和看似贤惠的妻子对他的暗算,与安子的单纯善良形成鲜明的对照,使读者看到工业化社会金钱对人性的严重腐蚀,看到矿工如蝼蚁般卑微的生存境遇。
《师娘子》2018年发表于《民族文学》。美丽聪慧的小米深深爱着癞子老师,无奈父母却用她换亲嫁给了矮小丑陋的陶大安,婚后的小米遭受到非人的折磨和无尽的羞辱。为了摆脱困境,她拜师娘(读音niānɡ)子盛婆为师,也成了一名人人敬而远之的神婆师娘子。小米虽然沦落到生活的最底层,遭受到人世间最屈辱的不幸,但是她始终没有屈从于命运,没有被命运彻底打垮,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在最卑微的尘埃中顽强地站立,以一种畸变的方式支撑着自己和家庭,履行着一个母亲所应尽的责任,将两个女儿抚养长大后,平静从容地度过自己的晚年。
笔者认为这是王刚最好的作品。这个凄恻而略显诡谲的故事,充满悲剧的力量而又不乏理性和克制。小米悲惨的一生和顽强的生命状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在这篇小说中,再现了王刚对生命的理解和对女性命运的独特诠释。从前者来说,他呈现了小米这样一个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在极度的苦难中的两次突围,一次是为了打掉腹中胎儿进而摆脱悲惨的遭遇而成为师娘子,这是一次不得已的畸变;另一次是即使遭到其他师娘子的嫉恨暗算仍然拼命保住这一份给人算命消灾的谋生技能,因为只有它才能给她带来经济保障和不可侵犯的地位,只有它才能为她实现将一对女儿送到县城接受教育的愿望,而在将女儿培养成才的历程中,她实现了对自己灵魂的救赎。小说最为悲壮最为酸楚的情节是她为了寻找丢失的签册,冒着危险返回失火的天门村主家,被天门人和其他师娘子围住群殴和羞辱的时刻,这一场面的震撼程度,令人想起《天龙八部》乔峰血战聚贤庄的无助与悲怆。从后者即对女性的认识来说,这篇小说无疑渗透着某种程度的对女性的呐喊与歌赞。王刚在谈到这篇小说时说:“我始终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的存在是一代代农村妇女用血肉奠定的。每次回到老家,我看着那些或拄着拐杖,或踽踽独行,或拖着小孩,或靠在墙下晒太阳的老妇,不由心生敬畏。千万不要小看她们,她们是某个家庭的纽带,是某群人的灵魂。只要她们在,这个家庭就不会散,哪怕儿女飞多远,也会不时回到乡村,共享全家团圆的天伦之乐。她们就是一棵棵大树,把根深深扎进地下,站在乡村的土地上。”在小说中,小米历尽辛酸,也似乎变成一个异类(师娘子),但仍不失其善良的天性,即使对待曾经虐待过她的婆婆和侮辱过她的公公,她也给他们养老送了终。而置身在最危险的境地,她也没有忘记母亲的责任。婚后的小米决绝地割断了与癞子老师杨德邦的联系,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却始终珍藏着18岁时的爱情,这是支持她度过漫漫长夜的重要力量。
对女性命运的表现,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重要母题。女性普遍具有温暖的人性和深沉的母爱,有着超出想象的坚韧与顽强,而她们却长期处于被掠夺被损害的地位,所以她们的人生就会衍生出无穷无尽的悲欢苦乐。因此可以这么说,从女性的生存状态和人格的是否独立,可以考察社会的文明进步状况。无疑,阅读这篇文章,能感受到作者王刚那来自岁月深处的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深刻思索和对女性生命强度的热切歌赞,以及对农村贫穷落后背景下进一步恶化的男权社会和蛮荒风俗的审视与批判。
(二)源于道义和责任的坚守与担当
王刚的大多数小说有着较浓厚的阴郁感和沉重感,而《黑狗张》《1988年的春天》《生死碑》等作品却充溢着温暖的底色和神圣的力量,呈现了来自底层民间的正气与道义。《1988年的春天》和《黑狗张》都是描写乡村教师的作品。《1988年的春天》中的王老师是一个家庭负担重的民办教师,他除了教书,还常常要承担村里的摊派任务,在要么停课去修路,要么继续上课但要交一笔代工费给村里的抉择中,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他最终选择了卖牛卖树交代工费。《黑狗张》是一篇充满诗意与感伤的作品。师范毕业的张朵和男友李天明是花嘎村小学仅有的两名教师。刚分来不久,李天明就因挡不住外面世界的诱惑离开了花嘎村,离开了张朵。为了孩子们能继续读书,张朵留了下来,一个人独自支撑着一所学校,支撑着孩子们走向未来的希望。为了避免孩子们过桥时滑落到河中,每天晨昏张朵都带着她的黑狗在竹竿桥头接送学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王刚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了家乡花嘎中学当老师,在这里一干就是8年,这段经历给他的人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自然也就成为他的创作最重要的源泉。王刚塑造了许多乡村教师的形象,其中,有坚守乡村三尺讲台,为打造农村孩子的未来耗尽青春与心力的老牛、张朵老师和陶老师,有为了孩子们的未来甘愿自己卖牛卖树交代工费的王老师,也有为了得到所爱的姑娘不惜残害情敌的“我”,沉迷于网络的网虫以及生活堕落、道德沦丧的教师败类“苍蝇”。从这些人物身上,大致可以了解到乡村教师这一比较复杂的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农村基础教育的艰难境况。
以上这两篇小说都反映了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但王刚却通过小说中人物的突围表现了一种可贵的精神力量。王刚的父亲是一名兢兢业业的民办教师,《1988年的春天》是以他父亲为原型塑造的艺术形象。这篇小说围绕王老师面临要么停课修路要么上课交钱的艰难选择展开描写。乡长对待王老师是公事公办的冷漠和高高在上的鄙视,村长则更是赤裸裸的趁火打劫,但是纯真的师生情谊和教师的使命感却让我们看到了人世间还有真善美存在。几十个孩子穿着雨胶鞋,扛着铁锹一定要跟着王老师去修路,他们巴望着早点修好路,老师就可以早点回来教他们,面对着孩子们幼稚却毫不动摇的举动,王老师最后毅然决定卖掉自家的水牛和树木来上缴代工费,以此换得给同学们继续上课的权利。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民办教师处境的尴尬卑微和生活的贫困艰难,也看到了他们中的不少人视教育为神圣,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去成就孩子们的未来的高尚的精神世界。
《黑狗张》中张朵老师的前男友李天明十多年后再次来到花嘎村,希望与张朵重修旧好并带她到深圳,但张朵再次做出了选择,继续留在花嘎村,留在孩子们身边,留在她爱的马啸身边。美丽的乡村女教师张朵在农村小学坚守十多年,这种源于道义和责任的担当,正是一种对个人生存价值的超越。这篇小说弥漫着一种忧伤的诗意和淡淡的孤独感,结尾浪漫的描写,为小说增添了令人回味的温情和韵味。
《生死碑》无疑是一篇独具风格的作品。这篇反映抗洪救灾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豪气与力量。面对肆虐的洪水,龙王村几乎所有青壮年男丁奔走在堤坝上,打桩,结绳,挖土,装沙,扛沙包,封堵,不舍昼夜地加固堤坝,守护着龙王村的安全。这篇小说一扫其他小说阴郁凝重的气息,充盈着激情澎湃的阳刚之气和战天斗地、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正能量。小说个性突出的人物塑造、夺人心魄的场面描写和主旨明确的主题提炼证明了王刚能很好地驾驭这一类题材。
二、作家:在生存与叙事中不断蜕变
王刚是一个起步较晚但创作成果较为丰硕的作家。从他创作的成绩与势头来看,呈现着不重复自我、不断超越的态势,而这种勤奋且勇于探索的创作状态,让我们对他的未来有着更多的期待。
(一)不甘于平庸的突围
王刚在六盘水市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喜欢写作,在校刊《春梦》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曾梦想将来做一名作家。1999年毕业后分配到水城县花嘎中学做了一名语文教师。花嘎乡地处偏远,过去交通通讯闭塞,生活单调,亲友同事们多热衷于喝酒玩牌打麻将,爱好文学的同道者少之又少,渐渐地,曾经的作家梦被现实消磨殆尽,王刚学会了喝酒,在爬山玩水中打发着时光。“就这样,我变得实际起来,让自己随波逐流,不再谈什么追求,也不再想什么理想。只有一点,我恪守父亲对我的教导,切不可误人子弟,所以,当我回首那段时光时,唯一问心无愧的是,我还算一位称职的教师。”王刚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这样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手机和电脑等现代资讯工具将外面的世界与花嘎乡连接了起来,一批优秀大学生进入到花嘎中学,社会的变化和年轻人的才能使王刚体会到了落伍的危机感,这一切唤醒了他不甘平庸的进取心,于是他开始发奋学习,相继取得了专科和本科文凭,并凭借着这些积累,2007年顺利考入六盘水市第八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高中语文作文教学激发了王刚的创作灵感,使他在事隔多年后再次拿起笔,开启了他的创作之路。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危机感和有准备的人,看似机遇的偶然青睐,实则都是因果相循、水到渠成。王刚人生的蜕变,正是一次内心自我超越的诉求对平庸的生存状态的突围,而他创作的起步又是源于内在诉求对深埋于心的作家梦的唤醒。
(二)王刚小说创作的自我更新和超越
2014年王刚开始创作小说,在其不长的创作生涯中,已推出多篇优秀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的质量呈现出节节攀升的态势。
《黑狗张》——良好的创作起点。《黑狗张》于2016年在《厦门文学》第7期发表,这是王刚发表在公开刊物上的第一篇小说。《黑狗张》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细腻而准确,环境描写与情节叙述之间的衔接十分自然,人物塑造个性鲜明而又含蓄有致,行文形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感伤基调,不失为一篇立意较高、艺术感觉良好的作品。
《蚂蚁的悲伤》——平稳上升的可喜局面。《蚂蚁的悲伤》《那夜灯火朦胧》《侯三》《生死碑》都发表于2017年,这四篇小说题材迥异,但整体水平接近,有较高的思想格调,艺术性也较强,尤其是《蚂蚁的悲伤》这一篇。主人公安子在矿难中死去后,变成了一只蚂蚁,他万分挂念妻子白凤,担心她的安危,变成蚂蚁的他,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白凤,却发现他深爱着的这个女人正与其他两个男人在喜气洋洋地瓜分他的抚恤赔偿费。小说最后部分的描写,运用了表现主义手法,安子的灵魂变成了蚂蚁,以蚂蚁的渺小和孤立无助象征安子地位的卑微和遭遇的悲惨。这篇小说所描绘的生存环境对人的精神的异化,使读者不自主地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表现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要求突破对人的行为的描写而揭示其内在的灵魂……表现主义者将人物类型化、抽象化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出一类人的本质。”[1]对表现主义手法的适当采用,使小说的触角深入到哲学的层面,对社会和人性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审视。在叙事中作者十分自然地实现了从现实主义向表现主义的转换,过度相当流畅,了无痕迹,从中可体认到王刚在使用不同表现手法时已能做到驾轻就熟。
《师娘子》——显现实力的新高度。发表于2018年的《红鱼》和《师娘子》,进一步印证了王刚小说创作成熟度的持续进步。《红鱼》用胡彪(阿郎)和钟教授(马鸣)对话的方式展开叙述,这两个人明面上的身份和实际身份之间的差异构成二重对话关系,从而展开比较复杂的情节和心理描写。这种叙事角度的转换无疑构成了一种挑战,以至于在其中的一个段落,胡彪与阿郎的称谓有些混乱,但总体来说,悬念的设置、故事的推进、人物的性格逻辑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小说捕捉人物的感觉敏锐而细腻,语言圆润洗练,景色描写也见功力。
中篇小说《师娘子》,无论是其主题开掘的深度、人物悲剧命运的典型性还是表现手法的独特性、结构的巧妙和语言的艺术感染力等方面都达到了王刚创作的一个高峰,前两个部分已在前面进行了论述,下面着重分析后三个部分。
第一,在表现手法方面,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巧妙地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使得小说的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和谐统一。“古老的神话、民间传说与巫术中奇幻、怪诞的成分,激起作家们的想象”[2],小说故事背景为贵州西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作家根据题材表现和人物身份的需要,摘取了民族民间文化中的走阴、驱鬼、消灾祛病等神秘符号,将之生动地穿插在情节中,使之既体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神秘文化,使小说具有强烈的异质文化色彩,同时也使小说呈现着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张力。
第二,在结构方面,小说采用倒叙的方法,开头即大肆渲染师娘子的神秘诡异且大多数形貌丑陋,而陶三娘却是一个美貌的师娘子,从而将读者带入小说特定的氛围之中,并形成悬念。在随后的叙事中,追溯少女时代的小米(陶三娘)与乡村教师杨德邦的爱情,在对他们爱情的描写中,聚焦于爱的信物——小米纳的一双绣有“桃花”和“德邦”字样的鞋垫。小米被迫与陶大安结婚后不久,命运急转直下。小说将描写的重心放到了小米婚后的悲惨遭遇和她成为师娘子的经历及此后的作为上,这一部分凸显了小米命运的不能自主但成为师娘子之后却能掌控自己命运的极度荒谬感。陶三娘到天门村驱鬼却遭到他人陷害,在此,情节的推进达到高潮。多年后老去的陶三娘已不再算命,她的女儿准备将她接到城里,在收拾行囊时,翻到了陶三娘珍藏在箱底的那只绣着“德邦”字样的鞋垫。这一细节的安排,从结构来说,形成了前后情节的呼应,从对人物塑造来说,则深化了小米的思想情感,给小说增添了余音绕梁、咀嚼回味的神韵。
第三,在语言方面,《师娘子》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捕捉准确而独到,对感觉的描绘尤为灵动细腻。人物语言较之过去的作品更为个性化,逻辑关系更为严密,留下了更多令人回味的余地。环境描写与人物塑造、情节推进之间更为水乳交融,描写更加凝练。
《师娘子》在思想艺术性方面均达到了较高水准,显示了王刚的创作实力。这篇小说所到达的思想艺术高度,使我们相信在今后的时间里王刚将会给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作品。
三、对王刚小说创作的几点意见
作为六盘水市具有较大影响的青年作家,王刚的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十分希望贵州西部这片不算肥沃的文学土地上,能涌现出在贵州乃至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实力雄厚的作家,因此,在此也提出几点意见以供参考:
(一)精神品质是照亮晦暗人生照亮文学作品的一注光芒
王刚小说的底层叙事常常着眼于现代文明冲击之下无序状态的乡村以及乡民在窘困中左奔右突的生存境况。《蚂蚁的悲伤》《红鱼》《大雪夜》《那夜灯火朦胧》《老付的月光》《猴人》等均关涉这类题材,这些作品对乡民在原有生活格局被打破、被迫到城镇谋生的生存困境进行了细致描绘,对社会复杂面影的勾画和对人性的探索均有一定力度。乡民们既脱离了原有的乡村社会背景,又难以融入城镇主流社会,只能沦落为城镇边缘人。生存的窘困艰难和精神世界的卑微不安,使他们陷入双重的困境,人物苦楚无告而又缺乏精神寄托的叙事使小说流露出一定程度的哀伤消沉情绪。
底层叙事是对社会底层的人们生存状态进行呈现的创作领域和创作态度。底层人民家庭经济的困顿,生活环境的恶劣,人生际遇的多舛,社会地位的卑微,这一切诉诸文学作品,往往容易获得充满悲悯与感伤的情感冲击力和美学价值,进而进入社会学层面的道德审问。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新写实小说钟情于这类题材,也将底层叙事写到了极致。新写实小说创作的困境也恰恰证明了如果作家仅仅满足于揭示生活的苦难和本相,而缺乏对人的本质也即精神品质的提炼的话,文本则很难进入对人性深层次的探索和表现,也很难展开对人类命运和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开掘,从而难以获得更高远的创作视野和格局。
放眼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创作,有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创作者提供有益的启示。陕西作家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都以乡村青年的奋斗作为书写焦点,这两部小说既有对高加林、孙少安和孙少平等农家子弟贫困的生活情状的揭示,更着眼于对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不屈服命运的坚强意志的深入描绘,使小说始终萦绕着崇高而强大的悲剧力量,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被这种力量所感染所牵引,从而获得意味悠长而又无可名状的人生启示和审美愉悦感。以小说《傩面》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贵州作家肖江虹直面乡村文明的衰微,在《百鸟朝凤》《傩面》等小说中,从容、厚重、古老的乡村文化在价值观巨变的物质化时代显得如此老迈落伍,却又如此遗世独立,无论是视唢呐如生命的焦师傅还是奉傩面如神明的刻匠秦安顺,他们都以一种圣洁的情怀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绝世技艺,守护着一方乡亲视为至宝的精神领地,尽管世道人心沧桑变化,尽管乡土文明难以为继,他们仍然是那一方土地上顶天立地的精气所在。笔者认为,肖江虹的小说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不仅因为他善于讲故事,也不仅在于他描绘出了贵州山川风物固有的韵味,更在于他基于对贵州山乡文化的谙熟与深沉的爱,而传递出的大山深处的贵州乡村独有的质朴古拙、深沉执拗的精神气质,这些东西氤氲而成了他的小说独特的神韵与精气神。
以上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他们没有忘记作家反映真实、直面人生、为百姓鼓与呼的责任和良知,是他们的创作在世俗的肉身之中徜徉却始终不放弃对灵魂的逼视和追问。王刚的小说为“小人物”代言,有着深厚的故土情结,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切入点。对照他的小说,对乡民艰辛处境的描绘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对人性的开掘亦有一定深度,但作家更多地着眼于人物的生存境况的描绘和道德评判,对文化根源的追问和哲学思考则较为欠缺;从小说基调来看,悲悯感伤有余,而理性思辨不足。除《师娘子》《黑狗张》以外,大部分小说的基调较为灰暗阴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悲剧力量。
(二)应慎重对待“死亡”的描写
读王刚的小说,会让我们有一种想象,感到作者一定是一位有着忧郁气质的作家。他的多篇作品萦绕着阴郁甚至阴晦的气息,造成这种风格的原因除了上文分析的对底层小人物灰暗的人生状态的关注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作者醉心于描写死亡。如《标签》《蚂蚁的悲伤》《红鱼》《大雪夜》等结局都是死亡,《那夜灯火朦胧》中虽然马二的斧头没有砍下去,但他别着斧头去寻找妻子的过程就笼罩着死亡的气息。死亡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如果不断地想到描写死亡,也许就要对死亡的情节设置持慎重态度。在小说中,会让人感到很多人都是怒气冲冲或是蓄谋已久的,这种杀气腾腾的状态常常会使小说对人物思想情感的展现难以进入更深层面的剖析状态,也可能会使小说难以抵达它应达到的思想高度。相比较而言,《师娘子》以一种救赎的态度去面对苦难,那种隐忍与顽强、拯救与蜕变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所获得的悲剧力量也许正是它走进读者内心深处的重要原因。
(三)以瑕疵为鉴
总体来说,王刚的大部分小说情节发展和人物思想情感变化的内在逻辑比较严密,描写也较细腻。但有的小说也存在着一些小瑕疵,在此罗列出来,目的是引起作者的注意,在今后的创作中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从而使小说的构思更趋合理。
如《黑狗张》对年轻时的张朵没有与李天明一道离开花嘎小学一节的情节描写,没有更细腻地展现张朵的心理活动,对她选择留下这一举动深层的思想动因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存在着思想情感逻辑不够清晰、说服力不足的问题;《标签》在细节设置上存在一定硬伤,如胖子当众下跪向薛玉献花,两人在酒店门口拥吻的描写显得有些造作失真,描写也显得有些粗砺;《乡村教师的爱情》系列小说(含《老牛》《桃花》《苍蝇》《网虫》四篇短篇小说)落入“讲故事”的窠臼,主题挖掘缺乏深度,故事叙述、人物描写流于粗浅;《师娘子》中小米婚后的称谓叫陶三娘,这个称谓有些奇怪,因为小说中并未交代陶大安排行老三,他就只有一个妹妹,小米在娘家也只有一个哥哥,因此这个称谓不符合中国家庭伦理的称谓习惯。
(四)应留给创作更多积累和打磨的时间
王刚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还能够创作出有较高质量的作品,其中必定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勤奋与努力。笔者有幸看到王刚2018年和2019年密集的写作计划,在钦佩之余也有着某些担心,一是担心高强度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写作和教学既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是否会造成身体的过度劳累?二是从文学创作的状态来看,创作是对生活观察、体验、思考、提炼的审美创造,其中既有对创作灵感及时快速的捕捉,也有充满理性地对文本耗时耗力的反复酝酿和修改,这种沉淀和磋磨是文学作品成为精品的重要保障。所谓“文章不厌百回改”,《红楼梦》的写作也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王刚也说过,《师娘子》写得很下功夫,反复改过多次,才有了更好的质量。当然,以王刚创作的强劲精力和良好的艺术感觉,始终保持高产优质的创作状态不是没有可能,但仍建议王刚适当放慢写作的脚步,这样才能有更多时间对作品进行精心打磨,从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小说。
四、结语
王刚说:“小人物的世界也很精彩,再卑微的地方也能开出花朵。”立足于为小人物写生,使王刚的小说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写小人物的悲欢苦乐,写他们在艰难狭窄的生存空间中生命的挣扎和突围,这既是基于王刚人生经历的自然取向,也是他自觉选择的情感皈依。在生活的道路上不断掘进,人生的风景便会不断涌入心中,积淀成创作的丰厚土壤。文学创作需要才能和禀赋,也需要勤奋和探索。以生活作为土壤,以勤奋作为犁铧,以才华和梦想作为阳光雨露,我们相信,王刚一定会创造出一片生机勃勃璀璨夺目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