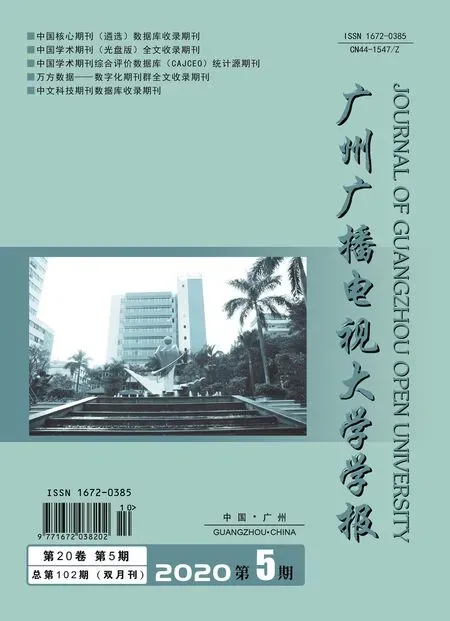“大地之子”海子笔下的“土地意象群”
2020-03-02张猛
张 猛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诗中,“土地”是深受诗人们爱戴的意象,诗人们对于土地的深情好像无论如何都诉说不完,它变成了一个经典的意象,流传于一代又一代诗人的诗歌中。不同历史时期,诗人们赋予“土地”不同的象征内涵。从20世纪20年代新诗运动发起后,诗人们就离不开“土地”意象,闻一多以《太阳吟》等诗作怀念祖国的故土;到20世纪中期蒋光慈又在《我要回到上海去》中写出了自己渴盼“旧地重游”的心愿。这一阶段的诗人们对土地的书写始终是联系着游子之心和国家时局的变化。从上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诗歌会的蒲风曾以《茫茫夜》和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集中表达农民的命运和土地上的现实;再到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以一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凝聚着对祖国、对土地最深沉的爱,表达出一个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对满目疮痍的大地的深情表白。
诗人们争先恐后地大声喊出对土地、对祖国的情感,土地成了他们表达政治阶级立场的工具,成为了具有社会性的意象。而海子却与他们不同,海子对于土地的情感是私人化的,是儿子对于母亲的喃喃细语,是不需要别人懂得的情感,它们细碎地潜藏在海子的诗篇之中。
一、大地之子
传承千年的农耕文明让中国人从骨子里就对养育我们的土地饱含深情。在农民看来,土地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是上苍给予世人的希望,是庄家人的命根。在诗人看来,大地是受苦受难的地母,是任劳任怨的奉献者,是无限灵感的源泉。海子,作为一个从安徽渣湾村走出来的少年天才,从他开始创作诗歌起,他就承载着农民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的身上便流着对土地的双倍情感。那海子和大地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海子在《生日颂》中深切的表达了他与土地的关系,“土地的不幸是我们全体的不幸/我们生在其中 长在其中 最终魂归其中”[1],他从土地中来,最后又回归土地,能深切的感受到大地的每一寸波动和颤抖;他是大地血脉中的一部分,是大地之子!
作为大地之子,他生于斯。天才之所以称之为天才是因为他们能看见普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看到的奥秘。普通人看不到的,海子看到了。他在《活在珍贵的人间》中写到“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2]。将自己看成“黑土块”无疑是海子的独创,是天才式的想象。而且他还强调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这里海子在暗示虽然他是来自土地、来自农村,但是他的灵魂是彻底干净纯洁的,没有受到尘世风俗的玷污,他是骄傲的。他看清了生存的本质:自己是从土地那里汲取营养而存活的,他的一切都来自土地的馈赠,所以他把自己想象成是由黑土块构成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黑色的颗粒,是干干净净的土地之精华。
作为大地之子,他长于斯。海子的童年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人民一切的生活来源都是土地,粮食是他们视若珍宝的东西,是一切安全感的来源。海子在《自画像》中写到“镜子是摆在桌子上的/一只碗/我的脸/是碗中的土豆/嘿,从地里长出了/这些温暖的骨头”[3]。这里海子竟然将自己的脸看做是碗里的土豆,碗中出现土豆这样的场景应该在海子童年生活中是经常存在的画面,所以当海子照镜子的时候,他可以自然地联想到碗中的土豆。脸应该是一个人最珍视的器官了,尤其是在这么一个“看脸的时代”,海子将脸比做土豆,可见其对土豆的珍视。那“这些温暖的骨头”是指什么呢,是指海子的脸,还是指土豆?从语义指向角度分析,“碗中的土豆”是大主语,“我的脸”是小主语,“从地里长出了,这些温暖的骨头”是谓语短语。在这句诗中存在一种情况,即大主语和谓语短语中的某一成分有复指关系。这也就是说碗中的土豆是从地里长出的温暖的骨头,这样的说法是指土豆是土地的产物,土地的一部分,是土地的骨头;它给人们带来温饱,使人们感到温暖,所以是从地里长出的温暖的骨头。从诗歌情感角度分析,诗人的脸是从地里长出的温暖的骨头,也就是说诗人是被土地所养育而长大成人的,所以说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温暖的骨头。由此可见,这是一首很简短的小诗,虽小但却不简单,海子的诗大多都是如此。
作为大地之子,他最后魂归于斯。海子是似鲁迅、张爱玲般的天才,一出手就是大作品,艺术水平相当之高。在他公开出版的第一首诗《亚洲铜》中就直接表明他对于土地的浓郁而深厚的羁旅情怀及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亚洲铜 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会死在这里/你是唯一一块埋人的地方”[4]。这里的“你”仅仅指亚洲铜吗?当然不是。铜是人体所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是一种存在于地壳和海洋中的金属,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海子以“铜”充当连接人类和土地之间的媒介,以“亚洲铜”这一恢弘的意象指代苍茫土地,无论是从声韵角度还是诗歌境界层次都是相当地恰当。这里的“祖父、父亲、我”可以具体指海子的祖辈、父辈及自己,也可以是指抽象层次上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最后都归于土地。这可以说明,在海子诗歌创作的伊始,他就对自己的归宿有清醒的认识:土地是唯一埋人的地方,他最终将魂归大地,回到土地母亲的怀抱之中,完成生命的轮回。
二、“土地意象群”
虽然海子是“大地之子”,但是他对大地的深爱与歌颂并不是直白露骨的,而是隐晦深情的。因为爱得太深沉,所以从不轻易张口。正如相爱多年的老夫妻从来不轻易说爱,但爱却弥漫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而海子对于大地的深情亦是如此,是散落在他的诸多诗篇之中的。
西川曾评论道:“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每一个诵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5]。海子成为大地之声的代言人,他将泥土的光明与黑暗、温情与严酷化作自己生命的本质,化为出类拔萃、简约流畅又铿锵有力的诗歌语言。他在诗歌中常常通过土地、麦地、泥土、粮食等诸多带有大地气息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替大地发声。这些意象也就构成了海子诗歌中的“土地意象群”。
1986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年。这一年,海子完成了期待已久的旅行,游历了青藏高原、青海、敦煌和内蒙古等地后,陷入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中。这一年,初恋女友和海子分手,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思和绝望中,正如他在日记里写的:“两年来的情感和烦闷的枷锁,在这两个星期(尤其是前一个星期)以充分显露的死神的面貌出现,我差一点自杀了”[6]。自此,他记忆中的美好已经无法抵御现实的孤独和无奈,海子的诗歌风格开始出现了转变,很多意象开始带有浓重的死亡气息。与前期相比较,许多美好的意象出现了颠覆性涵义。
(一)“麦地”的多重象征
在海子众多诗篇中,除了以麦地为主题的《麦地》《熟了麦子》《五月的麦地》《麦地与诗人》《麦地(或遥远)》之外,很多诗中也出现了“麦子”的意象,如:《四姐妹》中出现了“这是绝望的麦子”,《死亡之诗》中“请在麦地之中”等。由此可见“麦地”是海子“土地意象群”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重要意象,但不同诗中麦地的象征意义却差别很大。在前后期诗作中,麦地的象征意象甚至出现相矛盾的现象。
1.前期象征着生存的希望
在海子前期诗歌中,他通过麦地表现出浓厚的乡土情结。麦地成为了远在他乡的游子思念故乡的媒介。记忆中的村庄和麦地被无限放大的温情所包围,一切都呈现出勃勃的生机,麦地在这一时期通常象征着生存的希望和生命的活力。
海子在《麦地》中写道“月亮下/连夜种麦的父亲”、“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妻子们兴奋地/不停用白围裙/擦手”[7],这里海子通过写种麦和收麦时一家人的农忙场景来分享麦地带给农民的沉甸甸的喜悦,隐晦地写出虽然农耕繁重,但农民们却甘之如饴。“麦浪——/天堂的桌子/摆在田野上/一块麦地”,这里把麦地看做是天堂的桌子。在庄稼人看来,秋天麦地能丰收,来年全家就能吃饱穿暖,日子就有盼头,就有活下去的希望。这首诗的结尾写道“一同梦到了城市外面的麦地/白杨树围住的/健康的麦地/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妻子”。诗到结尾,海子才点明,身处城市的他在怀念故乡的农忙场景,梦到城市外边的麦地是健康的麦地和麦子。这里的健康的麦地不仅仅是指麦地,还指相对于城市而言的未被玷污的农村,健康的麦子也暗指存在于农村人骨子里的向上的生命力和至善的人性。整首诗都交织着丰收的喜悦和默默的温情,它们在深秋的夜里发酵弥漫,穿越时间历久弥新,让海子每每回忆起来都饱含喜悦。
2.后期象征着痛苦和绝望
在海子后期诗歌中,麦地的象征意义也就跟随着诗人的心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期,麦地更多的代表着痛苦和绝望。
海子在《麦地与诗人》中写道“在青麦地上跑着/雪和太阳的光芒/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8]。为什么诗人会无力偿还呢?“天地生养万物,人为大地之子,特别蒙受眷顾。天地对人类似有某种愿望,且有善良的期许。这一点,敏感的诗人首先领悟到了,所以才萌生出‘无力偿还’天地情义的愧疚感。”[9]这种想偿还却又无可奈何的无力感使诗人倍感痛苦,这种痛苦是麦地带来的。这个时候的麦地带给诗人的是压迫感,是如鲠在喉之痛。诗人在诗的结尾绝望地喊出“麦地啊,人类的痛苦/是他放射的诗歌和光芒”,诗人把自己的痛苦升华为璀璨的诗歌,以此来唤醒尚处在蒙昧之中的人类,企图用个人的觉醒来唤醒全人类的觉醒。无处宣泄的诗人只能把痛苦上升到精神层次,以此来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
日常生活中,人们接受麦地和太阳光芒的恩惠都认为是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海子不这样认为,他感到无力偿还并把压抑在喉的苦闷宣泄而出。这就打破了读者正常的阅读体验,造成了诗歌陌生化的效果,形成了阅读期待,使海子的诗歌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这样的诗在海子的创作中不是少数,如:《四姐妹》中“四姐妹抱着这一颗/一颗空气中的麦子/抱着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明天的粮食与灰烬/这是绝望的麦子”[10],这里麦子象征着绝望的海子,是海子幻想自己死后四姐妹来为他扫墓。
(二)土地与人类的矛盾
“土地”是海子“土地意象群”的中心意象,但是在海子的抒情短诗中却只有《歌:阳光打在地上》《土地·忧郁·死亡》这两篇是以“土地”为题的诗,其余的都是零散的存在于他的诸多诗篇之中。这确实如前文所说,海子不轻易吐露他对土地的情感,但是海子对土地的深情却是深切存在的。他在《太阳·七部书》中创作了一篇《太阳·土地篇》,就足以见他对土地的深切情感。“土地篇”不像《太阳·七部书》中其他篇章只有残稿或者只有存目。它是《太阳·七部诗》的“顶峰”,“是独立完整的、有对称性及和谐构造的;是七部书里最完整、最有涵括力的一部”[11]。这足以说明海子对于“土地”意象的重视。
以“1986年”为重要转折,海子前期的作品中诗人是和土地保持着亲密关系的;但是后期的作品中,他对于土地显示出矛盾的情感。海子的矛盾情感源自于人类和土地的矛盾的不可调节,海子夹在其中,左右为难。
1.土地的母性与人类的劣根性
海子在《黑夜的献诗》中写到:“丰收之后荒凉的土地/人们取走了一年的收成/取走了粮食骑走了马/留在地里的人,埋得很深”[12],丰收节是人们一年最重视的节日之一,通常会举办一系列传统的祭祀活动来庆祝丰收,人们沉浸在拥有粮食的喜悦中。丰收是大地孕育了一年的结果,是大地的生殖和奉献;然而人们在粗鲁地取走了粮食之后,连马匹和牲口都带走了,留给土地的只是无尽的荒凉和空旷,满目疮痍。人们偶尔想起来的、会留给土地的,就只有死去之人的尸体,埋得很深很深的尸体。这些是谁的尸体呢?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这是海子式的天才们的尸体,这些天才看见了土地的无私奉献,看见了人类的贪婪索取,他们饱含愤怒和忧伤,高声呼喊:对于土地的恩情,我们无力偿还。然而没有人理解他们的愤怒和忧伤,人们只是把他们看作疯子,把他们留在了很深很深的土地里。正如海子在《太阳·土地篇》的第六章“王”中写道:“大地躺卧而平坦 如一个故乡/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其中只包含愤怒、忧伤和天才”。
面对这样的现实,这让海子感受到的是无法拒绝的真实存在与内心情感之间的尖锐矛盾。作为大地之子,他看到土地的无私奉献,感受到了土地的痛苦和哀嚎,他深感羞愧,但是他却没有能力阻挡人类的贪婪,无力偿还土地的恩情。大地提供给人类的是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只能化作一抔黄土归于大地,将自己生命的光和热归于大地。海子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无法认可人类这种“一边依赖索取、一边伤害毁灭”的行为,他也深知人类和土地的矛盾无法调和。这种尖锐且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海子痛苦的根源。因此,海子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的土地意象都夹杂着痛苦的气息。
2.土地象征着扭曲的欲望和淳朴的呼唤
人类和土地之间的复杂关系除了给海子带来不可避免的精神痛苦,还让海子沉浸在对人性中扭曲欲望的质疑和渴望淳朴人性的回归之中。
诗人之所以能成为诗人,正是因为他们的目光能穿透时间的屏障看透生命的本质,伟大的诗歌也必须是超越“表面化”和“世俗经验”的诗歌。1987年的海子就看到了当代社会中必将出现的乱象,因此他诗中的大地意象里透出因工业文明而造成的精神的困惑与迷离,表现出对人性中扭曲欲望的质疑和对至善淳朴人性的呼唤。海子在《诗学:一份提纲》中提到:“在这一首诗(土地)里,我要说的是,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的漂泊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代替品——那就是欲望,肤浅的欲望。大地本身恢宏的生命力只能用欲望来代替和指称,可见我们已经丧失了多少东西”,他清楚地认识到现代人的欲望来自土地的丧失,欲望是大地恢宏生命力的变异。
1986—1988年期间海子创作的长诗《太阳·土地篇》里的第三章“土地固有的欲望和死亡”中提到:“土 从中心放射 延伸到我们披挂的外壳/土地的死亡力 迫害我 形成我的诗歌/土的荒凉和沉寂”[13]。这里诗人面临的是来自土地的双重迫害,即土地的欲望和土地的死亡力,这种重压使诗人成为大地的喉咙,发出对淳朴人性的呼唤的诗歌。大地为何要借诗人发声呢?还是以迫害的形式?诗歌在接下来娓娓道出了原因:“土把羊羔抱到宰羊羔的村庄/这时羊羔忽然吐出无罪的话语/‘土地,故乡景色中的那个肮脏的天使/在故乡的山岩对穷人传授犯罪和诗’”[14]。“土地”借羊羔之口给“肮脏的天使”顶下了罪名,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之上对农民传授犯罪。那在“土地”的眼中“肮脏的天使”是指谁?“犯罪”又是什么呢?当工业文明入侵农耕文明,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作为农耕的土地开始被机器、工厂、污水所蚕食,农耕用地面积日趋减少,人类记忆中的故乡在消失,转而变成规划有序的城镇。土地被钢筋水泥所取代,所以现代化的工业文明被“土地”称为“罪恶”。那些带来工业文明的人就是“土地”口中“肮脏的天使”。工业文明起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它在带给农村高速发展的经济和现代化的生活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工业污染,所以这里称为“肮脏的天使”。人类知道工业化的弊端,却依然坚持工业化的快速步伐,说明了人类的欲望战胜了淳朴的人性。正是因为如此,“土地,这位母亲/以诗歌的雄辩和血的名义吃下了儿子”,它要借诗人之口,以诗歌的名义控诉人类的破坏和欲望,呼唤至善淳朴的人性和记忆中的故乡。
海德格尔说过:“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海子以他天才式的创作完成了自己的天职。因为他是大地之子,土地就是他的故乡。他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归于斯。他笔下的抒情短诗中的“土地意象群”饱含着对大地的深情告白,他创造的长诗《太阳·土地篇》完成了土地的呐喊,他可以安心的返乡了。
天才总是过早地耗光了生命的光和热,因为他们的创作都是血与泪的结晶。海子通过天才式的想象、至真至纯的情感、不落窠臼的比喻以及凝练简洁的语言,融汇中西经典,把中国诗歌推向了一座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诗歌神话。诗人陈东东曾盛赞海子:“他不仅对现在、将来,而且对过去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虽然天才的海子在25岁时就溘然长逝,但他却可以通过诗歌突破时间的壁障,自由地穿梭于时间,在自己建筑的诗歌神话之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