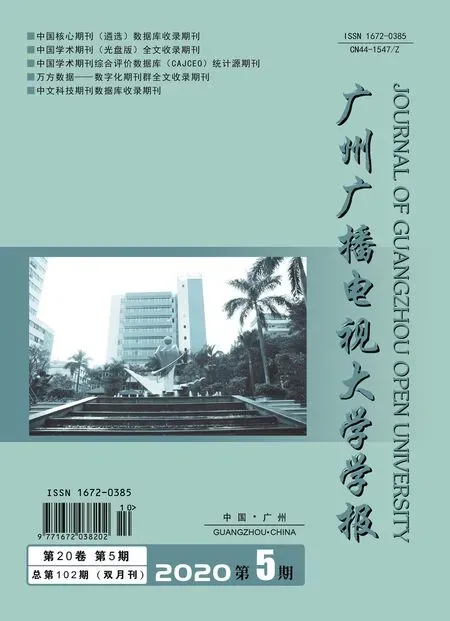“语言的画师”:论绘画性对艾青诗歌的渗透
——以艾青早期的诗歌为考察中心(1932—1942年)
2020-03-02丘思琴
丘思琴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艾青自小喜欢美术和手工,中学后考入杭州市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师从孙熙福;后留学法国,在巴黎接受现代西方绘画艺术教育。留法回国后一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曾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这一艺术学习经历和绘画创作实践开拓并丰富了他的艺术审美能力,为其诗歌带来别样的特质和韵味。“画家和诗人/有共同的眼睛/通过灵魂的窗户/向世界寻求意境”,[1]由于深知艺术形式之间的联系,从绘画界转入诗歌界的艾青非常注重诗歌的画面美和视觉美。他认为“绘画应该是彩色的诗;诗应该是文字的绘画”,[2]视“新鲜”“色调”“光彩”“形象”等为诗歌艺术的生命力所在。
吕荧曾指出,艾青“在体现诗的生命的基本因素的创造上,在‘新鲜,色调,光彩,形象’的手法上,已经获得了完满的成就”;[3]黎央说,艾青写诗“像印象派在作画”;[4]美国学者罗伯特·弗兰德称艾青为“语言的画师”。[5]显然,学界早已注意到艾青早期的绘画背景与他后来诗歌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大多仅限于只言片语,或是只关注“色彩”在其诗歌中的运用及其表现出来的美学特征,而较为全面研究艾青诗歌中的绘画因素、绘画性的文章仍是凤毛麟角。吴非在90年代曾提出“绘画性对文学的占有”这一概念,[6]指文学作品中艺术语言向现代绘画色彩美学的认同和趋近,认为色彩“在小说的情感——形式结构中常被作为第一性、复盖性或渗透性、凝聚性的神秘因素”,启示着某一精神内涵。本文则借用这一概念,研究绘画性,包括光影捕捉、线条刻画、整体构图、色彩运用等对艾青诗歌的渗透,企图更加细致地解析其诗歌美学特征。
纵观艾青的创作历程,从1932年发表《会合》为开端,①到1942年整整十年间,他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并由此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显示了他对资本主义罪恶性的揭露和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忧。而1942年进入延安后,他的诗风为之一变,诗中的绘画色彩也日渐淡薄。因此,为论述方便,笔者以1942年为界将其作品粗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本文仅讨论其前期的诗作,即1932—1942年间的作品。
一、光线捕捉——明暗对比的画面描绘
不论是年轻还是年老时,艾青对光总是葆有一份执着和偏爱。他在诸多作品中都对光进行了精彩的刻画和描绘,仅就其1932年发表的6首诗作来看,其中便有4首写到“光”,由此可见“光”在艾青心中和笔下的重要性。艾青对自然界、对事物拥有敏锐的观察和感受能力,他说过,“诗人应该有和镜子一样迅速而确定的感觉能力”。[7]他对光和色极其敏感,善于捕捉光线,尤其擅长刻画光线与光线间的缝隙,善于表现在不同光线的碰撞下营造出的那种喷涌的力的美。
1932年,在离法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时,艾青写下了一首短诗《阳光在远处》,②表现出年轻的他对于“光”的特殊迷恋与思考:
阳光在沙漠的远处,
船在暗云遮着的河上驰去,
暗的风,
暗的沙土,
暗的
旅客的心啊。
——阳光嘻笑地
射在沙漠的远处。
阳光本该是洒落在整个大地的,但诗的第一句却说,“阳光在沙漠的远处”,温暖的、明亮的阳光喷泻在主人公的远处,在画面的尽头。紧接着第二句“船在暗云遮着的河上驰去”,可见首句的“阳光”是作为一个背景式的远景描绘,而主人公、其所在的船及其周边景物则是一个特写的近景描绘,也是诗人着墨最多之处。“暗云”“暗的风”“暗的沙土”“暗的旅客的心”,几个紧凑的短句以一种复沓的节奏和回旋的韵律出现,解构了前面“阳光”所构成的暖色调,使冷色调占据了画面的主体部分。在这里,“光”的明暗对比是其重要的结构因素和意义因素。整首诗呈现出一个由大片暗部和小片亮部组成的画面,看似沉重、压抑,但是,应该注意到诗人在首尾两句都强调“射”在沙漠远处的“阳光”——这一富有动感的、充满力量的、可以射穿阴霾的阳光。在明与暗之间,并非是一条隔绝线,而是企图冲破“暗”的一切的明亮的太阳光,它向整片暗部延伸、渗透。由此,明与暗相互对比、又相互交织,分明寓意着诗人在归国途中对未来、对前途的不确定性感到忧虑,而又仍然向往光明、追求热烈的心境。
同样,作于1932年的《那边》,对“光”的描绘更具隐喻性:“黑的河流,黑的天/在黑与黑之间/疏的,密的/无千万的灯光。”在诗人眼中的并非是万家灯火的温暖景象,而是黑压压的天幕下几点“疏的、密的”寥落的零星灯光。在这首诗中,诗人不再用“暗的”来形容景物,而是以“黑的”代之,呈现出完全死寂的、凝重的效果,因为他知道这是“永远在挣扎的人间”。然而,在一片“黑与黑之间”,诗人仍然抓住丝丝缕缕的“灯光”。实际上,此时黑色的环境退而为背景,这微弱的光在铺满黑色的夜里更加凸显,在暗色的反衬下“无千万的光”倒成了画面中的主体。正如世间的人一样,尽管困苦,但仍在黑夜中寻找光,仍“挣扎”向上,其中体现的生命哲学可谓力透纸背。艾青的另一首《黎明》(1937年),以相似的笔法传达着同样的道理:“希望在铁黑的天与地之间会裂出一丝白线”。不过在这首诗中,光即“白线”显现出更多力的美。在《那边》中,光是静止的,整幅画面也是静态的;而在《黎明》中,光则是动态的,是在“铁黑的”天地间一瞬间“裂出”的,是经过力的搏斗、较量后冲出来的“一丝”光芒。这样,整首诗的语言便更具灵动感、更具铿锵之分量。
在艾青的诗中,不仅有明亮两种光线的对峙、较量,还有不同光线混合而成的不对称之美、和谐之美。如《黄昏》(1938年):“黄昏的林子是黑色而柔和的/林子里的池沼是闪着白光的”,这里的“黑色”不似前面两首诗作那般沉重,它因了“黄昏”这一特殊的时间背景而被柔和化。可以想象,此时的林子糅合了落日余晖时的柔美和黑夜来临前的深远,它有着静谧悠远、深不可测的暗处,但这里的“黑”不是毫无光泽的黑色,而是有着厚度和层次的黑色。这混合了夕阳的“柔和”的黑色配以池沼的点点闪亮的白光,就像一幅高贵典雅的水墨画。这里有黑白对比,有明亮对比,有软硬质地的对比,有动静的对比,呈现出光和物的和谐之美,因为这景象给诗人带来的是“田野的气息”,而他“永远是田野气息的爱好者”。
艾青在《光的赞歌》中写道,“艺术离开光就没有生命”。他一生中写下了很多涉及“光”或以“光”为主题的诗歌,主要出现的是“太阳/火”“夜”为代表“光明”和“黑暗”的两组意象群。据统计,艾青直接抒写太阳及其边缘类的诗占了其诗作的10%左右,[8]如《向太阳》《太阳》《火把》等即是“光明”的一类;而抒写“夜”的光的有《透明的夜》《监房的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在这些诗歌中,艾青往往在大片的暗调阴影中抓住一丝亮光,利用大面积的暗部凸显小范围的亮部,成功使得亮色系的光成为画面的中心,从而构造出一个色彩、明暗对比鲜明的画面,刻画出一个明与暗、冷与暖相碰撞、相交融的诗情世界。
二、工笔线条——“以线立形”的形象刻画
绘画属于结构艺术、造型艺术,而线条则是造型艺术的主要手段,“线条又是最高级的语汇,因为线条能表达画家精微的感觉和细腻的情感”。[9]艾青曾要求诗人诘问自己,“我有着‘我自己’的东西了吗?我有‘我的’颜色与线条以及构图吗?”[10]可见,绘画因素如色彩、线条、构图等已经被艾青有意识地纳入到自己的审美视野中,他的诗歌也因此富有独特的审美特征。艾青中学后接受孙熙福、林风眠的教育,后来曾几次提到自己喜欢齐白石的作品,可见他对中国传统绘画也深爱在心。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不仅是写形,更求形神兼备,因此,线条造型务必到位,要精致入微,既要画出形象特征,又要抓住神态特征。学界常言艾青受到西方印象派的影响,但在笔者看来,艾青的诗也未尝不透露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特质。他的诗,特别是描写物象、人物类的诗,便常常属意于画的构思,讲究线条造型,有时直接运用线条的概念来勾勒轮廓,进行构图。
与水墨写意画不同,工笔画更多地关注“细节”,力求形似。这一绘画技法往往使用“尽其精微”的手段,通过“取神得形,以线立形,以形达意”达到神态与形体的完美统一。在艾青的诗中,便有工笔画讲究“形”,注重线条刻画的特点,例如《手推车》(1938年):
在黄河流过的地域
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
手推车
以唯一的轮子
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
穿过寒冷与静寂
……
在冰雪凝冻的日子
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
手推车
以单独的轮子
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
穿过广阔与荒漠
……
在诗中,“河底”“天穹”“群山”“小村”“土层”“荒漠”等意象被诗人用干涩的笔触铺张开来,浅浅勾画成一幅远近交替的冷寂又辽阔的背景画;而手推车这个中心意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凸显出来。诗人没有对手推车进行细致地描绘,而是以“唯一的轮子”“单独的轮子”一笔勾勒出它的形象,以“独轮”这一典型特征显示其承载着的负担、凄惶、艰难和深重,可谓取一形而达到神似的效果。而后又从这只独轮联系、扩展到其发出的声音和留下的车辙。诗人抓住手推车声音沉重而又尖锐的特点,将它可感化、形象化——“使阴暗的天穹痉挛”这一动态描写使声音的尖锐、刺耳和给人带来的不适乃至恐惧跃然纸上。而对车辙的描写则体现了一定的力度。这条车辙是“深深的”“刻画”在土层上的,如烙印般深入土地内部,诗人用精细的线条勾勒将车辙的形态表现出来,使我们仿佛看到车辙在黄土地上的凹陷与凸起。在这首诗中,诗人将声、光、色、图等结合起来,用色彩渲染和构图线条勾画出在一片灰黄、苍凉的底色上,以“手推车”为象征物的北国人民的贫苦和悲哀。
当然,线条的运用在人物刻画上会取得更显著的效果。线条的勾画使得语言塑造人物的暗示力和雕塑感增强,使人物造型更加突出,使诗歌获得力感。例如,这首作于抗战爆发时期的《他起来了》(1937年):
他起来了——
从几十年的屈辱里
从敌人为他掘好的深坑旁边他的额上淋着血
他的胸上也淋着血
但他却笑着
——他从来不曾如此地笑过
他笑着
两眼前望且闪光
像在寻找
那给他倒地的一击的敌人
……
整首诗在艺术审美上呈现出一种巨型的雕塑感。诗的前三节从不同角度勾勒“他”的形象:第一节从空间的角度——在“深坑旁边”,整体上呈现“他”站起来的样态,第二、三节则是特写“他”身上的血以及神态表情。“敌人掘好的深坑旁”这一特定的空间环境赋予了“他”更多的意义,他不是单纯的物理意义上的“起来了”,更是与敌人搏斗,宁死不屈,挺立于天地间的精神上的“起来了”。在这样的时空下,他的整体轮廓被粗砺的线条定型下来,而后诗人着重刻画了战争给他留下的“血”,精细圈点出他额上、胸上淋着的血,还特别强调他从不曾有过的笑和坚定的目光,他的面部形态便逐渐清晰乃至深化。牛汉评论说,“《他起来了》是一尊巨大塑像,只能用庄严凝重如岩石的文字创作”,[11]全诗朴实无华,没有任何修饰语、色彩词汇,而所有的文字都是铁一般地厚重,血一般地凝重。“他”的形象就在这样庄严而凝重的语言中,在如同白描一般的线条粗浅勾画中雕刻出来。
还有在《补衣妇》(1938年)中“坐在路旁”,头巾上、衣服上都是沙土,“无声地给人补缀”的补衣妇,在《乞丐》(1938年)中伸着“永不缩回的”“乌黑的手”的乞丐,都给人一种雕塑般的凝定感,仿佛人物永远定格在画面中。艾青在抗战时期的作品尤能体现以线立形、用线造型、以形写神等艺术特点,或用线性词语几笔勾画,构造出画面的空间感,或用粗浅不一的笔触勾勒人物/事物轮廓,再细致描绘人物/事物的局部特点。应该注意到,艾青的这类诗较少使用柔和的线条,而是常常用硬挺、深邃的线条突出对象的某个外在特征,从而表现其精神特质。而这种线条的使用是与诗歌的精神内核相一致的——只有硬朗凝重的笔触才能刻画出中国大地以及这块土地上人们的苦难之久远和深重。
三、斑斓色彩——以“色”达意的诗歌意蕴
几乎所有诗人都在他们的诗作中运用过色彩词汇或者含有色彩的字眼,但像艾青那样自觉、有意识地将色彩元素融入诗歌的却不多。同样,出身于美术专业的闻一多,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倡导诗歌要有绘画美的诗人。他在诗中也运用带有色彩的词汇,例如,在《死水》中的“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绿酒”“白沫”等。但是,显然闻一多不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考虑色彩的运用,而更像是对中国传统诗歌意象的借用,从而营造出画面美。可以说,在中国新诗史上,还没有哪个诗人的绘画意识能比得上艾青,也没有哪个诗人对色彩的钟爱程度在艾青之上。色彩是艾青诗歌艺术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据统计,艾青一生创作的481首诗歌中,有240多首包含色彩词汇。[12]艾青用画家的眼睛写诗,非常讲究色彩的搭配和运用,充分发挥艺术视觉效果的审美功能,建构生动鲜明、色彩斑斓的画面。
也许得益于印象派艺术对于光和色的捕捉,艾青也非常注重感受色彩的瞬间变化。他不但善于描绘色彩斑驳的画面,同时也关注色彩的流动变化和色块之间的搭配效果。写于由巴黎到马赛路上的《当黎明穿上了白衣》(1932年)一诗,艾青便以色彩的不断流转和变化构筑出一幅色彩鲜明而丰富的画面:
紫蓝的林子与林子之间
由青灰的山坡到青灰的山坡,
绿的草原,
绿的草原,草原上流着
——新鲜的乳液似的烟……
啊,当黎明穿上了白衣的时候,
田野是多么新鲜!
看,
微黄的灯光,
正在电杆上颤栗它的最后的时间。
看!
这是一幅风景画,但它不是以物象的轮廓为中心的风景图,而是以色块组合为构成的色彩图。诗人敏锐地捕捉到黎明瞬间大自然丰富多彩的颜色,颇有几分莫奈《日出·印象》的感觉。莫奈的这幅画主要由淡紫、微红、橙黄和蓝灰等四个色调组成,除蓝灰外其它都属于暖色调,正契合“日出”这一主题。而艾青的这首诗由紫蓝、青灰、绿、乳白和微黄等几个色块组成,除微黄之外其它都是偏冷色调,表明太阳尚未升起的黎明时分略带清冷的感觉。可见二者对特定时间下环境中色彩的处理如出一辙。
尽管这首诗主要使用的是冷色调,但并不会给人以沉闷、凄清之感,反而呈现出清新、灵动,还带着一丝生气的特质。诗的前三句为我们铺展开一幅色彩纷呈的画面,紫蓝、青灰和绿色相互交织。“林子与林子之间”“由山坡到山坡”直至“绿的草原/绿的草原”,随着诗人视点的移动和物理空间的变换,这些色彩在反复中得到加强,在文本的意境中得到延展、交融。而草原上流着的“新鲜的乳液似的烟”不仅有颜色、有形状,还有了一种流动的质感,从而在前三个背景色中突出,成为画面的中心。颇为有趣的是,全诗唯一的一个暖色调——微黄,在这里却承担着某种反面的象征意义:尽管微弱的灯光能在夜间给人照明,但黎明代表着新生的力量,它的到来终将代替灯光的历史作用。这一冷暖色调的对比使得这首诗不再是简单的风景画,而是由富有美感上升到哲理层面,具有了社会现实意义和深度,加强了诗歌意境的延展。
对比色的运用也是艾青诗歌的一大特点。在绘画艺术中,对比色搭配是色相中的强对比,其效果鲜明、饱满,常用以表现随意、跳跃、强烈的主题。色环上遥相对应的颜色包容并举,能够产生光怪陆离又相得益彰的视觉效果。艾青就经常用黄与紫、橙与蓝的对比色来制造矛盾,表达情绪上的冲突,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堰河——我的保姆》(1933年):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
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
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
这几句中“黄”和“紫”的运用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骆寒超认为,“紫色是一种能给人以痛苦感觉的色彩,因为被人鞭笞后呈现出来的伤痕往往是紫色的……大堰河的‘灵魂’是受尽世人创伤的灵魂。”[13]他从现实层面来分析紫色在诗句中的运用,认为艾青通过紫色把握住了大堰河痛苦的本质,但笔者更倾向于从色彩学的角度来解读。黄和紫是一组对比色,黄色为前进色,而紫色是后退色,③但艾青反其道而行,用视觉上给人以近距离之感的黄色作为背景色,视觉上较远的紫色反作为主题色。黄色亮眼,属于中性偏暖色,紫色则比较暗沉,属于中性色。但在这里,大片的黄色反而能使原本暗淡的紫色更加聚焦,更加醒目,更加稳定,而且鲜亮明快的黄色更能衬托出紫色的高贵、神秘和感伤。这一色彩搭配和运用非常符合大堰河的形象气质和诗人所要传达的情绪。大堰河首先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农村妇女,她一生中历尽各种辛酸苦楚,她的生命早已蒙上灰黯阴郁的底色。但她又是艾青的乳母,给了他无限的母爱,因此对于艾青来说,她是美丽而高尚的,她的人格是高贵的。所以,用紫色——这个由红色和蓝色调合而成,融合了红色温暖和蓝色忧郁的色调来代表大堰河再合适不过了。
“很多作品是有显然的颜色的”,[14]艾青的诗歌,尤其是早期的诗歌,往往能给人以视觉冲击感,感受到色彩的巨大魅力,从而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张力。可见他有意识地捕捉事物的色彩,并注重各色块的拼接组合,善于借助某种色彩表现对象的精神特质,运用色相、色域的色彩对比关系来表达他的思想感情。
综上所述,绘画艺术对艾青诗歌的渗透较为充分,光影、线条、色调等成为其诗歌的生命力和张力所在。正因为有这些绘画因素的融入,才使得艾青诗歌在以“口语入诗”、追求形式自由的同时仍然能保持诗歌的语言美、画面美。在三四十年代“为艺术而艺术”和“一切艺术都是宣传”两种对立的文学思潮中找到平衡点,提出并亲自践行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主张,有力扭转了当时诗坛的这两种不良倾向。
注释:
① 实际上艾青最早的作品是1928年5月发表于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市第一中学)校刊《学蠡》上的《游痕》(二首)(署名蒋海澄),但因这两首诗是艾青中学时代的作品,故不纳入考察范围。
② 本文所引用的艾青诗歌均摘自《艾青诗全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后文不另作注释。
③前进色(Advancing Color):在置于同一平面的各种颜色中,显得比其它颜色更靠近眼睛的某些颜色中之任一种颜色,如黄色、红色等暖色。后退色(Receding Color):亦称“缩色”。和其它颜色在同一平面上,看上去离眼睛较远的几种颜色,如绿色、蓝色、紫色等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