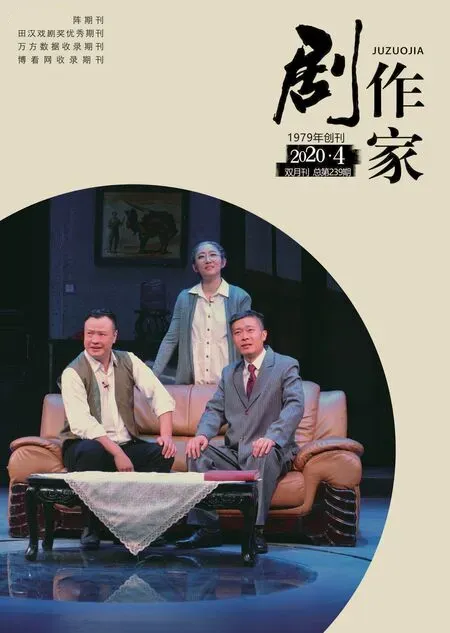传 统 与 创 新
——关于泗州戏作曲与演奏双修的思考
2020-03-02张峻峰
■ 张峻峰
安徽地方剧种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有徽剧、黄梅戏、庐剧、泗州戏,简称:徽黄庐泗。泗州戏是安徽省四大剧种之一,又名拉魂腔,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泗州戏的唱腔委婉动听,悠扬高亢,为淮河流域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
蚌埠市的安徽省泗州戏剧院是个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剧院。早在五十年代,院里主演李宝琴、霍桂霞等老一代艺术家们就誉满大江南北淮河两岸,曾代表安徽省三次进京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及中央多位领导人进行专场演出。
像演员一样,我把自己“归门归档”为泗州戏的柳琴(主胡)演奏。我少年从艺,跟随父亲学习柳琴演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父亲的严格训教,让我在柳琴演奏这圈子内暂露头角。进入剧院时几乎所有的泗州戏传统音乐都能烂熟于心,不但能娴熟地弹奏老一辈艺术家李宝琴、霍桂霞等的唱腔,而且分得清每位老艺术家的演唱特色与技巧。可以这样说,我是在泗州戏的传统音乐里泡大的。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我都是泗州戏音乐老传统的继承者和守卫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现实题材创作,要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泗州戏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是我们这一代泗州戏人的责任。安徽省这些年紧抓机遇,乘势而上,我们蚌埠也紧跟时代步伐大抓狠抓戏剧创作,特别是现代题材的戏剧创作。五年来,除小型戏曲外,剧院共排练演出了五本大戏。我这个本想一辈子当好柳琴伴奏演奏员的人误打误撞地走到作曲队伍里来,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创作剧目的作曲。
作曲与演奏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当,本人如今从一个传统的继承者、守卫者转身而变成作曲——改革者、创新者。
其实,传统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今天我们所认定的传统换个角度来说就是昨天的创新,昨天的创新就是我们今天的传统。由此可见,传统与创新是辩证的对立统一,是事物的一个发展过程。如果传统一成不变,没有创新的延长和弥补,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传统就会中止;而创新离开了传统这个根本,也必定会迷惑甚至变种,胎死腹中。我从一个泗州戏主弦伴奏到泗州戏的唱腔设计,在专业双修的历程中,始终把传统与创新的基点把握作为我的最高艺术追求。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要继承传统,要在创新的基础上继承;要跟进时代的步伐,要有创新,但一定要在传统的基因里创新,不变种。前些年有个笑话:有人拿一段唱腔给常香玉先生听,常香玉先生听完以后,一叠连声说了几个好听好听。就在大家如释重负之际,常香玉先生问道:这是哪个剧种的声腔。这一问,现场气氛的尴尬可想而知。常香玉是豫剧的开创者之一,是四海扬名的声腔大师,却听不出剧种特色,只说好听不知道剧种。这虽然说的是一段小笑话,但是这段笑话警醒我们的从业者,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不能不讲规矩地逾越传统与创新的辩证关系,生产出许多“四不像”的作品。
2015 年我们泗州戏剧院创作演出的泗州戏《绿皮火车》进京,首演于北京长安大戏院,参加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会演。泗州戏第一次进京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时隔六十年,泗州戏又一次进京,虽然是一次艺术活动,但更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任务。前几届都是黄梅戏,这一次我们泗州戏觅得战机,代表的是安徽省。我是全剧主弦又是作曲,心头的压力可想而知。人往往都是这样,没有退路时,压力就是动力。
为泗州戏《绿皮火车》作曲与给传统戏编曲不同。圈内人都知道,虽然说泗州戏有着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泗州戏不像京剧那样的博大精深、自成体系。泗州戏在一百年之前还是个说唱形式,连正规的乐队伴奏都没有形成,更谈不上什么作曲了。再说,后来渐渐形成了本戏,也是小打小闹。直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泗州戏才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即使到今天我们传统戏的故事都是单线条的,唱词也都是套路,方便流动演出,演出时做套路放水词,不是七字句头就是十字句头。而《绿皮火车》的剧本结构显然是现代产物了,首先在文本结构上就不同于传统戏,它是双线结构,十分讲究烘托场面场景,人物性格、人物情绪,有着大段大段唱腔,还有不少对唱、群唱、合唱及边舞边唱。这些在传统戏中是不曾有过的。最令我头痛的是编剧写的唱词多是不规则的长短句,上句下句不一样,有的上句五个字,下句十几个字;有的上句十几个字,下句四五个字。按照传统的泗州戏音乐曲牌根本就套不上去,想去与编剧交流沟通要编剧对唱词进行改动,编剧找出一万个理由婉言拒绝。在茫然与阵痛中我必须自创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是不忘传统,又必须让传统在此处有所突破,而突破的过程又必须坚守泗州戏的“移步不换形”,写出来的曲子不能让别人说好听是好听就是不像泗州戏。吃力不讨好事小,万一进京演出打不响,辜负了各级领导的信任,丢了泗州戏拉魂腔脸面,那真就是万死莫赎了。
我在创作中除最大量使用泗州戏的传统音乐曲牌之外,还将花鼓灯音乐当作一抹悦耳的色块用来加强淮河流域的文化特色。幕未打开,泗州戏的旋律融汇着花鼓灯的背景音乐一下就会把人带入淮河两岸,体会到那一方水土的风土人情。在创作中找到感觉,写出旋律,自己弹出来,再唱出来,一弹一唱,熟悉了自己写出来的旋律,加上自己的主弦弹奏与作曲家在钢琴上“试谱”,传统质感兼具,这样更方便我的反复修改,也可以说这是作曲与伴奏双修的互惠互利,真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现在想起来作曲与写文章是一样的道理,许多有建树的名家都说过好文章都是一遍一遍改出来的。通过泗州戏《绿皮火车》的创作,我对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反复地弹,反复地唱,广泛地征求编剧、导演、演员的意见,有时候编剧导演不在一起,我会用微信把自己试唱的录音发给他们,尽我所能做到极致。
《绿皮火车》所到之处,观众对音乐高度认同,纷纷赞誉泗州戏好听,是对我最大的慰藉。
《绿皮火车》最后获得了第五届少数民族会演银奖,网络评选入选最受欢迎的十大剧目之一,还获得了中国人口文化奖和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2019 年代表安徽省参加了在西安举办的第五届国际艺术节,并获得特别贡献奖。2019 年,本人由省文化厅推荐到北京参加了文旅部举办的“千人计划”培训班作曲班,进一步开拓了眼界。通过泗州戏《绿皮火车》的成功上演,我对泗州戏的作曲和伴奏提高了认识。戏曲要讲究一棵菜精神,个人技巧要服务于全剧这个大局。
从主弦伴奏到泗州戏作曲,从看着曲谱演奏到自己演奏自己创作的曲子,付出的心血不一般,心里的感觉也不一样。以前是作曲者写好乐谱,上面什么样的音符,什么旋律,我们只要看着指挥手势(节奏)伴奏,伴奏任务完成,收拾“家伙”回家。作曲就不一样了,最早进入主创班子,第一个要直接打交道的是编剧。拿到剧本不但要反复阅读,而且得反复斟酌研究,情景音乐描写、唱腔设计,先得在心里打成腹稿,再与编剧进行沟通,尤其是主要人物的音乐形象塑造、性格刻画等等。正如著名编剧汪曾祺先生所言,编剧的语言节奏决定于情绪的节奏。语言的节奏是外部的,情绪的节奏是内部的。二者同时生长,而又互相推动。情绪节奏和语言节奏应该一致,要做到表里如一,契合无间。作曲不懂编剧的良苦用心,必然会自作聪明删改剧本唱词,这是编剧与作曲之间的大忌。我在为《绿皮火车》一剧作曲时做到了每改文本一个字需与编剧进行沟通交流,凡编剧不同意修改的,就自我消化。
在个人技巧服务于全剧大局的创作流程中,必须做到成竹在胸。圈子内有一句行话,戏曲戏曲,没有曲子就没有戏,可见一部戏的成功,曲子(当然包含唱腔)是何等重要。
后来在泗州戏《夙愿》《淮水情》等大戏的创作中,由于有了《绿皮火车》的创作经验,便从容成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