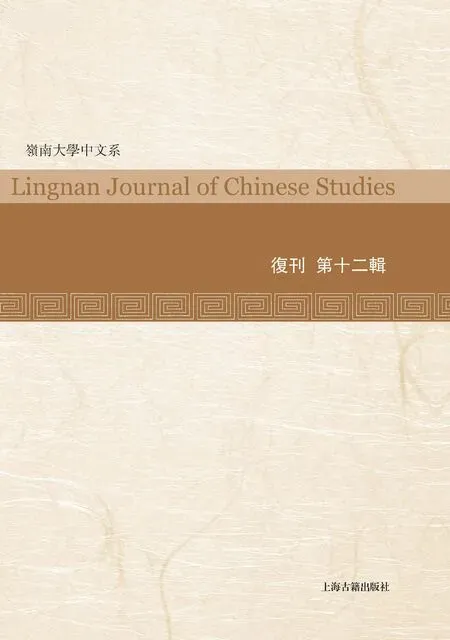長慶體、梅村體與“本事詩”
——略論中國詩體的叙事形態
2020-03-02張寅彭
張寅彭
一、引言:“叙述”與“叙事”之分疏
中國傳統詩學早在《毛序》總結《詩三百》的“六義”中,即有“賦”一義,其功能略與今人習用的“叙述”一詞相當。相較於“三用”中的其他二用“比”、“興”,尤其是興的複雜性,“賦”的鋪陳叙述手法似乎較為單純,從鄭玄注《周禮·大師》“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到朱熹《詩集傳》“敷陳其事而直言之”,歷來釋義穩定,“不譬喻者皆賦辭也”(孔穎達《正義》)。直至杜詩繼《詩經》出,元稹作《杜君墓係銘并序》,亦以“鋪陳始終,排比聲韻”為其最主要的藝術特徵,元相亦被許為少數第一代老杜真正的知音之一。“賦”之用可謂極於斯矣。
在中國詩學中,賦與並立相對的比、興,所謂“比喻”,所謂“發端”①“興”亦有比喻之義,如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興,引譬連類。”,它們作為表現手法,各司其職,並無軒輊。清人吴喬《圍爐詩話》曾據比興與賦褒貶唐、宋詩,其説甚辯,然《四庫總目》斥之云:“賦、比、興三體並行,源於《三百》,緣情觸景,各有所宜,未嘗聞興、比則必優,賦則必劣。”①《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806頁。清中葉詩學漸趨尚實,這是四庫館臣上述批評的大背景。但“叙述”(賦)的不可或缺,根本上還在於詩之元理方面的原因。
相較於賦與比、興的並列,歐西詩學有將“描寫”與“叙述”並立的看法:“叙述的對象是往事,描寫的對象是眼前見到的一切。”“叙述要分清主次,描寫則抹煞差别。”②[匈牙利]喬治·盧卡契:《叙述與描寫》,載《盧卡契文學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9、56頁。吾國詩篇的具體分析當然也可以運用這一對概念,但在詩學中,將叙述與描寫兩種功能合而為一,則是集中於“賦”一辭了。例如《葛覃》首章:“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朱熹《集傳》標為“賦”,解作當下的動態描寫似也不錯,但却是“追叙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③朱熹:《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頁。又陳奂《詩毛氏傳疏》謂是興,今不取。。老杜《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全首自是賦而非比興,從題目言,應是當下之“望”的描寫,但下半首則又轉為叙述矣。總之吾國詩的趣味並不在此種分别,“賦”叙述故事與描寫當下的兩種功能兼而有之。
“賦”具有時、空全方位適用的性質,這從“賦”的釋義也可得到證實。如上述鄭玄注:“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劉熙《釋名》:“敷布其義謂之賦。”劉勰《文心雕龍》:“鋪采摛文,體物寫志。”鍾嶸《詩品》:“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可以陳善惡、敷義、體物、寫志、書事、寓言,是一種基本的表現手法,適用甚廣,而“事”只是所叙對象之一耳。故“賦”的“叙述”功能,與包含表現對象的“叙事”,在外延上是並不周延的。
“賦”從《詩經》總結而來,出處堂皇。而“事”與詩的聯繫,《漢書·藝文志》“詩賦類”小序也已有“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正式的表述。至六朝文獻中的“事”義較紛歧,如《文心雕龍·事類》篇的“事”,乃指用事(用典);蕭統《文選序》“銘則序事清潤”,則非指詩體,諸如此類。唐後較常用於詩的是“本事”與“記事(紀事)”兩個概念,但也發展出了新的意涵。如“本事”成於唐人孟啟《本事詩》,“記事”成於歐陽修《詩話》,司馬光《續詩話》小序揭橥其性質云“記事一也”①《文選序》有“記事之史,繫年之書……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云云,此處之“記事”亦尚非指詩體。。南宋計有功又有《唐詩紀事》。前者所謂“觸事興咏,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本事詩序目》),詩雖由事起,但並不直陳於詩中,須另著文發揮説明,其側重由“詩”轉至“事”之究竟了。後者孔天胤《重刻唐詩紀事序》釋“紀事”,亦同此趣:
夫詩以道情,疇弗恒言之哉。然而必有事焉,則情之所繇起也,辭之所為綜也。故觀於其詩者,得事則可以識情,得情則可以達辭。……故君子曰:在事為詩。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夫謂詩為事,以史為詩,其義幠哉!②《唐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頁。故“紀事”亦猶“本事”之意,乃詩情之所缘起,而隱於辭外。當然從兩書所記的内容看,“本事”更直接關乎詩,“紀事”、詩話等所涉則稍泛,侧重在詩人、逸事,稍有不同。故《四庫總目》集部詩文評類小序標舉之五種體例,《本事詩》與詩話便是分列的。而若就其“事”旨言,則合併亦無妨。至於唐人詩間有運用“叙事”一詞的,如韋應物《張彭州前與緱氏馮少府各惠寄一篇多故未答張已云殁因追哀叙事兼遠簡馮生》、鄭谷《叙事感恩上狄右丞》等,題云“叙事”,但詩中所叙之“事”都非正式“事件”,題中的“叙事”不過是個一般之詞而已,尚非概念。
由此産生一個問題,即唐宋詩學的“事”觀,雖然强調“事”的重要性甚或在“情”前,但在詩内並不“直書其事”,反要借助詩話之類詩外説明纔能得其原委。比如王維《息夫人》詩的“事”寜王奪賣餅者妻,劉禹錫兩首“游玄都觀”詩的政治事件,都不在詩“内”直接寫出。此種“事在詩外”的趣味,竟與比興的“意在言外”殊途同歸。如此則“叙事詩”豈非也就無從談起了?現代論者於此一議題,頗有誤“叙述”為“叙事”者。不過即便如此,持此誤者也往往不能不遺憾地認識到,所叙一般只是“事”之片段、片刻而已,並不充分,距離“叙事”的典型程度,猶有一間之隔也。此類誤會甚多,觸目可見,此處不煩舉例。而揆諸詩史,也確實只有唐前之樂府詩及老杜、香山的“新樂府”之作,纔稍有人物、情節之類“叙事詩”的要素。而五、七言古之正體雖長於叙述,老杜以下更兼喜議論,嚴格説來都非“叙事”之體。律體為平仄、對仗、字數諸種規則所局限,就更不便於叙事了。
唐後諸體中,惟有七古歌行一體,其中的元、白“長慶體”,較為充分地具備了“叙事詩”的樣態,有完整的第三者的人物故事,如白居易的《長恨歌》;有客觀之場所可供情節之開展,如元稹的《連昌宫詞》、鄭嵎的《津陽門詩》。至清代又發展出“梅村體”一脈相繼,纔稱得上是所謂詩人自覺的“叙事詩”,纔在詩史站住了地位。其“叙事”之詩旨又與“韻調”、“辭藻”三位一體,融合而成中國叙事詩特有的審美趣味。兹試論如下。
二、元白“長慶體”較之“新樂府”更具叙事形態
中國標準意義上的叙事詩,曾在唐前驚鴻一瞥,出現過《焦仲卿妻》、《木蘭詩》等傑作①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一:“《焦仲卿妻》詩,六朝人所作也。《木蘭詩》,唐人所作也。樂府惟此二篇作叙事體,有始有卒。”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頁。。但這是樂府詩,文人之作則無之。唐前是五古高度發達的時期,所以彼時能產生出這樣的作品。(《木蘭詩》略雜七言數句及九言一句。)唐後七古開始成熟,五古長篇的“叙述”之風,以杜、韓等為代表,由“事”轉向了“議論”②參胡小石《李杜詩之比較》、《杜甫北征小箋》等文,載《胡小石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此也即是李滄溟名論“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之一義也。
五古的這一轉向應是七古發展後的自然之勢。七言句式,叙述更為酣暢自由,篇幅也更充分,自是叙事詩體的不二選擇。唐人的所謂“叙事詩”,歷來之關注集中於兩大對象,即老杜、樂天的“新樂府”之作與元、白的“長慶體”之作。但如果深究之,兩者“事”的表達方式及形態是大有區别的。蘇轍《詩病五事》曾比較老杜《哀江頭》“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而“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③載《欒城三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3頁。之不同,竊以為此即言中“新樂府”與“長慶體”叙事不同的實質,其失惟在“拙於紀事”之“拙”字上耳。所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即快速通過不停留於一地之謂;而“寸步不遺”者正相反,乃是持久地專注於對象之謂,如此則始有形成完整的人物形象、詳盡的事件情節之可能①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卷二老杜《哀王孫》引吴星叟(農祥)語云:“起用樂府體,昔賢所謂省叙事也。”似即指蘇轍此評,惟移《哀江頭》為《哀王孫》,義則通。。子由此語乃是揚雄“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的宋代翻版,都只説對了一半,其失在昧於文體區别之意識。但在歷來褒貶元白長慶體的衆多言辭中,此一語雖是貶辭,却又最搔着癢處,以今日之眼光視之,實是詩體進步的一種表現,子由之揚抑不免保守,以致南轅北轍了。
“新樂府”的旨趣,如元、白所言,主要在“先向歌詩求諷刺”②白居易《新樂府·采詩官》,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③元稹:《樂府古題序》,《元稹集》卷二三,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92頁。,而非叙事本身的趣味。縱觀郭茂倩《樂府詩集》末十一卷所收,除少數篇什容或有“叙事”的因子,如“桃源行”一題,以有陶潛《桃花源記》為藍本,故事稍完整;劉禹錫《泰娘歌》、白居易《上陽白髮人》、《縛戎人》等篇,人物經歷稍完整;(元稹同題之作便不同,而以議論為主。)杜甫《兵車行》、白居易《新豐折臂翁》、《賣炭翁》等篇,特寫場面具體完整,其他幾乎都談不上以“人”、“事”為主題者。而即使上述諸篇,也都還未及發展出“情節”來。此無他,蓋篇幅不甚大,叙述於對象未能至“寸步不遺”的程度也④新樂府體晚唐有一絶大之作品,即韋莊的《秦婦吟》。此詩長逹119韻,惟述一路聞見,中間雖有故事,而皆碎為片段,“四隣婦”云云,更顯為樂府寫法。韋莊宗杜,其集即名“浣花”,故與長慶體異趣。。此事必得待元、白“長慶體”登場,方纔獲得改觀。故將“新樂府”一體之旨趣總歸於“叙事”者,實屬誤會也。
新樂府的“諷世”與長慶體的“叙事”,乃是唐人七古歌行中兩大不同的類型,而元、白兩類之作兼擅,且俱為典型,俱是傑構,此點歷來論者衆多,早已獲文學史定評。而兩類在“叙事”方面的不同,則似尚有進一步辨析之必要。昔者陳寅恪先生論元、白之“新樂府”,曾析出元氏“一篇數意”與白氏“一篇一意”的區别,或可作為此一議題討論的起點。陳先生云:
關於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較,又有可得而論者,即元氏諸篇所詠,似有繁複與龐雜之病,而白氏每篇則各具事旨,不雜亦不複是也。陳先生並於各篇詳為比較之,如舉兩家《法曲》之作,謂微之此一首多意,樂天於是析“所言者為三題,即《七德舞》、《法曲》、《時世妝》三首,一題各言一事,意旨專而一,詞語明白,鄙意似勝微之所作”①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2頁。。陳先生並進而指出元氏後作之古題樂府,即學樂天此點而改正之,“無一首不只述一意,與樂天新樂府五十首相同,而與微之舊作新題樂府一題具數意者大不相似。此則微之受樂天之影響,而改進其作品無疑也”②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302頁。。
陳先生對元白新樂府的這一分析思路,在其辨析兩家同題之作《琵琶引》與《琵琶歌》的不同時,竟又一次運用之,並據以分出高下:樂天《琵琶引》“既專為此長安故倡女感今傷昔而作,又連綰己身遷謫失路之懐,直將混合作此詩之人與此詩所詠之人,二者為一體,真可謂能所雙亡,主賓俱化,專一而更專一,感慨復加感慨”。而微之《琵琶歌》“盛贊管兒之絶藝,復勉鐡山之精進,似以一題而兼二旨,雖二旨亦可相關,但終不免有一間之隔”云云③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47頁。。樂天《琵琶引》固是所謂“長慶體”的代表作之一,則“專一而更專一”的要求,被轉用至此體無疑。
尤有甚者,陳先生於《長恨歌》與《連昌宫詞》之比較場合,仍復隱然不脱此一思路,而得出更進一步之結論。如所周知,陳先生於《長恨歌》,有一極大之發現,即陳鴻傳白傅詩“為一不可分離之共同機構”。由於歌詩與傳文有此分合之關係,故所謂“史才”、“議論”之内容,便都可以從“詩”移諸“傳”中了。陳先生云:
白氏此歌乃與傳文為一體者,其真正之收結,即議論與夫作詩之緣起,乃見於陳氏傳文中。
白傅此歌遂至於能够專一於叙事,所謂“寸步不遺”者,其秘蓋在於此也。而元相之《連昌宫詞》適相反,其已無須傳文而自獨立了。陳先生復云:
至若元微之之《連昌宫詞》,則雖深受《長恨歌》之影響,然已更進一步,脱離具備衆體詩文合併之當日小説體裁,而成一新體,俾史才、詩筆、議論諸體皆匯集融貫於一詩之中,使之自成一獨立完整之機構矣。
其後卒至有如《連昌宫詞》一種,包括議論於詩中之文體,而為微之天才之所表現者也。①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4、5、11、44頁。
可見在所謂“長慶體”的場合,元、白二氏竟又一次重現了他們在“新樂府”之作中的不同,一“潔”而一“複”矣。在“新樂府”的場合,此“潔”是“一首一意”之謂;而在“長慶體”的場合,“潔”則是排除了“議論”之類成份後的純粹的“叙事”。陳先生進而云:
是以陳鴻作傳,為補《長恨歌》之所未詳,即補充史才、議論之部分,則不知此等部分為詩中所不應及、不必詳者。②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12頁。陳先生從文體的角度揭示出這一點,而與本文的論題亦復相通,即“事”被凸顯出來,成為主要之旨趣,“叙事”已不僅是技法,更上昇為詩旨了。《長恨歌》下半篇幅的“海上仙山”故事,最是此種叙事意識的産物,否則詩人恐怕是不會冒此“荒誕不經”之大不韙的。陳先生對此特大贊云:“在白歌陳傳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於人世,而不及於靈界。其暢述人天、生死、形魂、離合之關係,似以《長恨歌》及《傳》為創始。此故事既不限現實之人世,遂更延長而優美。然則增加太真死後天上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陳諸人,洵為富於天才之文士矣。”③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13頁。由是之故,《連昌宫詞》之納入史才、議論,雖是完成了詩篇内容的獨立,此點同樣也受到陳先生的稱贊,但加入的終是“詩中所不應及、不必詳者”。陳先生此評釜底抽薪,完全顛覆了傳統評價④如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五云:“《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宫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謨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二年間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8頁。,自是一個現代學術的立場。
《連昌宫詞》藝術上的獨創性,乃在於改從憑弔空間遺跡來講述這同一個故事,從而大大加深了故事的歷史滄桑感。在《長恨歌》的“女角”主題外,再增一“宫苑”主題,形成所謂“長慶體”並行的兩主題。稍後鄭嵎的《津陽門詩》即步其後塵,甚至歷千餘年,猶産生如王闓運《圓明園詞》、王國維《頤和園詞》等後勁之作,不絶如縷。雖然“每被老元偷格律”①白居易《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注》卷一六,第1053頁。,元相筆下的這位“宫邊老翁”,仍不無從樂天《琵琶行》的“長安倡女”竊得的嫌疑。
由於改以舊宫遺跡為主角,明皇貴妃故事的叙寫方式也隨之改變。全詩四十五韻,除去最末十三韻議論不論外,餘下三十二韻中,大抵用十一二韻叙寫當年盛衰過程。有“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闌干立”直寫兩位主人公,而力士、念奴、二十五郎(邠王李承寜)、李謨、岐王、薛王、楊氏諸姨等一干相應人物也悉數出場,筆力不俗。其餘二十餘韻皆寫宫苑凋敝之景况,合於“連昌宫”之題,然亦處處不離“上皇砌花”、“太真梳洗”之跡,烘托其事無遺。故全詩雖非如《長恨歌》之“寸步不遺”寫法,但也差可謂“叙述”不離“叙事”了。此種寫法,以今日之眼光衡量,是並不亞於老杜《哀江頭》“江頭宫殿鏁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之古典寫法的。至於數十年後鄭嵎之《津陽門詩》亦用宫苑為題,亦設一“旅邸主翁”話舊,篇幅更擴至一百韻,次第從明皇寵幸貴妃、安史作亂,亂後殘隳,一一道來,明皇内苑事實更形完整,更見具體,誠為“長慶體”叙事之又一鉅製。然就詩藝言,全詩不過按部就班、填砌舊聞而已,用心大不及元相,其結構、意境,不僅不如《連昌宫詞》,猶或不逮晚清民初人之《圓明園詞》、《頤和園詞》等作也②此用陳寅恪先生之評。參《元白詩箋證稿》,第73頁。。此體隨之也沉寂下來。
三、“本事詩”之新形態(上):明人之“長慶體”諸作
如上所述,“本事”之概念在唐人孟啟首創之時,“事”並不直接表現在詩中;而“叙事”之功能趣味則以元、白“長慶體”諸作最稱充分。“本事詩”後世雖有續作者,但大都或佚或殘,如五代處常子《續本事詩》、宋聶奉先《續廣本事詩》等,未能形成風氣。直至清初,此題纔又復興,如順治間有夏基《隱居放言詩話》、錢尚濠《買愁集》等,都以“本事”為旨,録詩輯話,大抵不脱孟啟初作之旨趣。康熙間有程羽文《詩本事》,自謂倣孟書,實非其旨,然亦可見當時熱衷此題之聲氣也①諸書均已收入拙輯《清詩話全編:順治康熙雍正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清初這一批著作中最可注意者,乃是徐釚的《本事詩》。徐釚(1636—1708),字電發,號拙存,又號虹亭、楓江漁夫,江南吴江人。康熙十八年舉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著有《南州草堂集》等,所輯《詞苑叢談》流傳甚廣。其《本事詩》有自序、略例及吴中立序,綜合可知,此書作於康熙十年六月至次年臘月。刊刻行世則稍遲,已在康熙四十三年,是由時任濟南太守的吴中立,遵王士禛之囑託而付梓的。徐釚是王士禛的早年弟子,據書前所載王士禛的三通信件,漁洋也曾參與了此書初期的編輯,提出過修改意見,有些版本的目録中頁標有“王士禛論定”字樣,即指此。原稿也一直留在漁洋的蠶尾山房中,久未獲梓,也是經漁洋督促纔得以問世的。漁洋並擬書成後撰一序,後未果②參《本事詩》自序、略例、吴中立序、王士禛書等。載《清詩話全編》,第1025—1030頁。。此一事例,似也可稍洗歷來對於漁洋不重白香山的誤會。
徐釚此書雖名“本事詩”③此書據略例、吴序、漁洋書劄,俱作“本事詩”。光緒徐氏刊本徐榦跋亦作“本事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排印本即據此本,然改題“續本事詩”,殊非其舊。,但與孟啟之旨已大不同,不再以發明詩中之事為旨,而是改以詩人為目,直選有事之詩,類如選本。入録之詩的本事也較孟書有所限定,即必須關乎婦人韻事,大抵只相當於孟書所列七類中的“情感”一類。此類情韻之事包括“宫掖内庭”、“香閨紅樓”、“寵姬愛妾”、“游仙諸女”、“青樓狹邪”、教坊樂工,乃至美少男(“歌童人寵”)各色人等,即連幽冥鬼域也無漏列。全書十二卷,所選時限始自明初,迄於清康熙初,分隸前、後集,前集六卷録明人,後集六卷録清初人,編選頗為整飭。這一斷限恰好呈現出“長慶體”在宋、元沉寂了較長一段時間之後,明代開始復甦,並進而過渡到清初“梅村體”的史實,亦即上文討論的“叙事詩”一脈的後繼發展也。
全書所選三百餘家,計明人二百零七家,清初人九十七家。所録之詩自然不盡七古歌行一體。經檢,作有此體的詩人凡七八十家,明人四十餘家,清人三十餘家,多帶有“長慶體”風味。其中稍嚴於體制者,明、清各十餘家,明人如高啟、孫蕡、李禎、瞿佑、韓邦靖、張獻翼、王稚登、王叔承、徐、吴兆、葉紹袁等人,清初如林雲鳳、杜濬、朱隗、俞南史、鄒祗謨、陳玉璂、董以寜、顧景星、毛先舒、汪懋麟、毛奇齡、陳維崧、吴兆騫等人,再加上“梅村體”本尊吴偉業,可見此體在清初即已漸盛於明人了。
唐人之七古歌行,明人詩學有詳盡之討論,大抵分出了老杜體與初唐體之不同,而以元、白“長慶體”上承初唐,歸為一體。(詳下)但宋元七古多承老杜一體,“長慶體”基本上無嗣響。明人七古歌行一體,也鮮有學初唐體或長慶體的。如前後七子的李、何、王、李,四家中自以李夢陽七古成就最高,然夢陽七古屬於老杜一路;李攀龍以七言近體勝,古體未足道,後人對此皆有定評。王世貞古體,後人推服其五言,如朱竹垞《明詩綜》録其《袁江流鈐山岡》一篇,沈歸愚《明詩别裁集》選其《將軍行》一首,而七言皆未為所賞。只有何景明略近初唐四子,如胡元瑞云:“獻吉專攻子美,仲默兼取盧、王,並自有旨。”①胡應麟:《詩藪》内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頁。將何與李對比言之。但這一般也是被視為缺點的,如許學夷即斷言何“歌行遠遜國朝諸子”②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一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頁。。此外明初高啟《青丘集》中七古之作不算少,也稍有得長慶體風味者,但“才調有餘,蹊徑未化”③《明詩别裁集》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頁。,也並不成熟。
明人七古歌行的創作情形,其學初唐體、長慶體的程度,自然需要一家一家翻檢明人别集,纔能最終確認,上述五家雖云大家,也不過是嘗鼎一臠而已。但徐釚《本事詩》前集六卷所録,卻頗令人意外地看到明人效法“長慶體”的熱情其實並非低迷。如孫蕡《驪山老妓行》,題下即注云:“補唐天寶遺事,戲效白樂天作。”小序復借客語云:“子詩淺易明白,恍惚樂天。”又如李禎《至正妓人行》,小序亦借妓言云:“此元、白遺音也。”效“長慶體”的意識是十分自覺的。其他如高啟《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夜飲丁二侃宅聽琵琶》、瞿佑《安樂坊歌》、韓邦靖《長安宫女行》、王稚登《聽查八十彈琵琶》等篇,或詠教坊、宫女,或聽琵琶而感,題目亦近樂天。張獻翼《再過會卿卜吴姬為屍仍設雙俑為侍令伶人奏琵琶而樂之》、徐《玉主行》、吴兆《秦淮女兒鬥草篇》、葉紹袁《午夢堂除夕紀夢詩》等篇,題稍溢出,然皆以數十韻詠婦人情事,叙事詳備,音調亦皆流轉,體屬“長慶”,當可無疑。
其中孫蕡《驪山老妓行》一首頗具代表性,明人對“長慶體”的興致,以及運用此體的嫺熟程度,此詩表現得淋漓盡致。所謂“驪山老妓”者,唐妓也。詩人用八十七韻的長篇,虚構了一個與之相逢的故事。此妓當年色、藝雙絶,開元時曾“隨龍侍君側”,又特地將其侍君的場所設在驪山,使之親歷了驪山盛衰悲歡的全過程,尤其著墨於悲劇過後舊宫廢園的衰敗,此即詩序“補唐天寶遺事”之謂,將《長恨歌》之佳人主題與《連昌宫詞》之宫苑主題合為一詩,可謂盡得後作之便利。然詩旨不免平庸,叙事完整之外,略以辭藻工麗見長。此妓獨擅“搊箏”,而嫌“琵琶橫笛徒聒耳”。詩中描寫其技高,奏畢“四座無言俱寂寥,餘音已斷猶縈繞”。又形容其聲“溶溶宛宛復悠悠,切切淒淒還窈窈”,這顯然改寫自樂天《琵琶行》“大弦嘈嘈”、“小弦切切”的句子。但與樂天“聲漸歇”後的“此時無聲勝有聲”不同,此處仍是有餘聲的。當然,若據沈德潛之説,樂天此句宋本原為“無聲復有聲”,則孫氏所寫又與之同趣了①沈德潛:“諸本‘此時無聲勝有聲’,既無聲矣,下二語如何接出?宋本‘無聲復有聲’,謂住而又彈也。古本可貴如此。”《唐詩别裁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4頁。歸愚此説,宋翔鳯首議之,見其《過庭録》卷一六“近人妄改元白詩”,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67頁。近人高步瀛與陳寅恪亦指其非,分别見《唐宋詩舉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10頁、《元白詩箋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6頁。然不妨可備一説也。。此詩結語:“不因水上琵琶語,那識江州司馬名。為爾臨風歌一曲,百年哀怨起秦箏。”續《長恨歌》之遺而效《琵琶行》之事,音調流轉,庶幾明人之“長慶體”傑構也②孫蕡才情冠於當時所謂嶺南“南園五先生”,徐釚引牧齋、竹垞語,以為即連吴中四傑亦應讓出一頭。。
李禎《至正妓人行》之題,亦從樂天《琵琶行》脱胎而來。全詩八十八韻,叙寫此元妓一生遭際甚完整,四韻一换,詞藻亦極博麗。此妓擅簫,詩中寫聲音不再用象聲詞,而改為叙述:“似啼似訴復似泣,若慕若怨兼若訣。”則演奏之樂聲歟?老妓傾述身世之肉聲歟?不復可辨矣。“分離或變成淒切,淒切愈加音愈咽。”前一個“淒切”講身世無疑,後頂針再一“淒切”,即轉到“音”上,既是樂音,亦可兼人聲,技法極有可觀處,較之《驪山老妓行》不遑多讓。此二詩可稱明人倣“長慶體”之雙璧也。
若就徐釚此書觀之,明人“長慶體”之作稍有創意者,當推徐之《玉主行》。此詩寫一生與一妓愛情不渝之故事,其妙幻亦如《長恨歌》在下半首,著重寫姬死後,生以“連城玉”刻一偶像,“中間自鏤芳卿字”,“鎮日重重牢繫臂”,“東西南北但隨身,旦夕何曾暫相棄”。此生後為歹人所害,竟由玉偶之力得以伸冤,種種曲折,全詩五十六韻之大半即寫此“片玉酬情”、“白璧伸恨”之離奇故事,辭藻清麗,亦合度。此外如韓邦靖的《長安宫女行》長達八十韻,篇幅可觀,然多用諷諫而非叙事的寫法,辭藻清直,不復穠麗,更像是一首樂府詩,稍欠長慶體之風味也。總而言之,“長慶體”之再次掀起高潮,進入新階段,明人尚非其時,此事須稍待吴偉業“梅村體”之登場了。
四、“本事詩”之新形態(下):清初“梅村體”之成功
徐釚此書之最具眼識者,在於後集用與前集相當的篇幅,頗具規模地集中輯録了清初詩人之“本事詩”。其成書之年恰是吴偉業的逝世之年(康熙十一年,1672),編者雖未明言為梅村體而作,然觀其《略例》第二條即云:“宫掖之作,如《長恨歌》、《連昌宫詞》之類,雖或寄慨興亡,然皆述内庭之事,余故間為采入。”末一條又云:“近時名賢,如牧齋、梅村諸先生而外,豈遂無紅粉青衫之感?”其輯旨儼然有一樂天、梅村在,則是不妨可以推斷的。所采梅村詩十五題三十首,數量居冠,所謂“梅村體”名作《永和宫詞》、《圓圓曲》、《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蕭史青門曲》、《臨淮老妓行》等,悉在其中。至此,上述明人之作的中間過渡屬性當可無疑,而清初各家則又是梅村此體之羽翼也。
梅村體上承初唐體與長慶體的性質,早在梅村身後不久,清人即已取得共識。乾隆中《四庫全書總目》發為“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為深;叙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韻協宫商,感均頑豔,一時尤稱絶調”云云①《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别集類,第1520頁。,遂成定評。所謂四傑之格律,最初是由何景明《明月篇序》提出,以與老杜七古之拗調區隔;(詳下)香山之叙述,上文也已藉寅恪先生之論,略作了分析。而梅村較兩者更進一步,所謂“情韻為深”、“風華為勝”,此又何謂也?其中“事”之成分佔何比重,形態表現為何,與現代“叙事”理論銜接之處何在,均需再作考察。
梅村七古之作現存九十四首①此據康熙吴氏原刻《梅村集》本,乾隆間程穆衡、靳榮藩、吴翌鳳諸箋注本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李學穎標點本據《梅村家藏稿》增補出七首。,詩旨詩格不一,大抵可分為如下幾類。一是旨在諷諫的新樂府之作,如《悲滕城》、《捉船行》、《蘆洲行》、《馬草行》、《茸城行》、《打冰詞》、《再觀打冰詞》、《雪中遇獵》、《銀泉山》、《松山哀》、《通元老人龍腹竹歌》、《海户曲》、《織婦詞》,倣古樂府的《堇山兒》等。即事而發為議論,未脱前人“新樂府”的格局。兩首“打冰”詞,事頗新穎。《松山哀》事關明社稷存亡,詞雖隱,而直指洪承疇心曲,“摧心肝”復“征夫樂”,誠為犀利;既寫下“十三萬兵同日死,渾河流血增奔湍”的慘狀,又就田畝荒蕪無人耕種發出“若使江山如此閑,不知何事爭强弱”的大哉問,至今猶振聾發聵,較老杜《哀江頭》等作絶無遜色。
二是酬贈懷人之作,此類甚多,如《東萊行》、《送志衍入蜀》、《送徐次桓歸胥江草堂》、《贈吴錦雯兼示同社諸子》、《畫中九友歌》、《贈文園公》、《退谷歌》、《壽總憲龔公芝麓》、《送沈繹堂太史之官大梁》、《贈馮訥生進士教授雲中》、《送舊總憲龔孝升以上林苑監出使廣東》、《曇陽觀訪文學博介石兼讀蒼雪師舊跡有感》、《贈陸生》、《吾谷行》、《悲歌行贈吴季子》、《畫蘭曲》、《送杜大于皇從婁東往武林兼簡曹司農秋岳范僉事正》、《高涼司馬行》、《送杜公弢武歸浦口》、《秋日錫山謁家伯成明府臨别酬贈》、《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贈穆大苑先》、《白燕吟》、《沈文長雨過福源寺》、《短歌》等。此類之作往往亦有事,但都是用上文指出的“叙述”手法帶過而已,“事”並非詩旨所在。如《送志衍入蜀》多述交往事,甚至有“我昔讀書君南樓,夜寒擁被譚九州”的早年之事,但下句即轉到“動足下牀有萬里,駑馬伏櫪非吾儔”的述志了。此種寫法非為叙事詩甚明。此兩類中又多有十韻上下的短古之作,如《悲滕城》、《捉船行》、《送徐次桓歸胥江草堂歌》、《沈文長雨過福源寺》、《短歌》等,以及《行路難》十八首、《遣悶》六首,篇幅既短小,則更非叙事之體矣。
三是題圖觀畫之作,如《清風使節圖》、《南生魯六真圖歌》、《項黃中家觀萬歲通天法帖》、《題志衍所畫山水》、《題崔青蚓洗象圖》、《觀王石谷山水圖歌》、《題蘇門高士圖贈孫徵君鍾元》、《魯謙菴使君以雲間山人陸天乙所畫虞山圖索歌》、《京江送遠圖歌》、《題劉伴阮凌煙閣圖》等。此題自老杜七古頻得佳作後,宋人如蘇、黃等皆愛用來談書論畫,明、清詩人一般也不例外。而梅村此題之作,多由書畫抒發人生情懷,於畫作本身反而著墨甚少,較老杜以來寫法有新發展。如《南生魯六真圖歌》一首,梅村有感於南氏命人為自己畫下的六幅生活圖,而作詩記之,“真”即日常生活之謂,最可見出此種新趣味①靳榮藩《吴詩集覽》引申鳧盟語,見已及此:“此等題雖老杜亦不能佳。蓋以牽率應酬,非所以抒寫性靈耳。梅村集中時或收此,然筆力恢然有餘,才餘於詩,詩餘於題,則忘其為應酬作矣。”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396册,第480頁。。今以非關叙事,暫不具論。
四是詠物之作,如《宣宗御用戧金蟋蟀盆歌》、《宫扇》、《田家鐵獅歌》等。梅村近體詠物甚多,七古不多作。另有一首《詠拙政園山茶花》實非詠花,乃記莊園,已入下一類。《蟋蟀盆歌》、《田家鐵獅歌》有諷意,旨近新樂府,然字面仍以賦物為主。惟《宫扇》詠“為講官時御賜”之物②程穆衡:《吴梅村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頁。,追懷君恩而純為賦物也。又有一首《汲古閣歌》,述毛晉藏書事,未可謂“詠書”,庶幾亦歸於此處。
五是家國時事之詠,即趙翼《甌北詩話》“所詠多有關於時事之大者”③《甌北詩話》卷九,載郭紹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3頁。之謂。如《殿上行》、《雒陽行》、《雁門尚書行》、《永和宫詞》、《琵琶行》、《鴛湖曲》、《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楚兩生行》、《臨淮老妓行》、《王郎曲》、《蕭史青門曲》、《雕橋莊歌》、《詠拙政園山茶花》、《圓圓曲》等,梅村七古之足以名世者,蓋在此一類,其當得“叙事詩”之義者,亦在此十數首爾。
此一類下,又可按寫人物與寫莊園分為兩題,略相當於前述長慶體的“佳人”與“宫苑”兩主題,惟人物女角外又增男角,私家莊園亦不同於皇家宫苑,而大幅開拓了社會面向,都可視為“梅村體”在題材方面的發展。
“梅村體”叙事以史實為勝,其人物故事都無《長恨歌》出入天上人間那種虚構,往往實寫其人一生經歷。如最為膾炙人口的《圓圓曲》,起首“衝冠一怒為紅顔”點題後,即從頭説起:“相見初經田竇家”,“一曲哀絃”訴向“白皙通侯”,復被“軍書抵死催”而“將人誤”,落入“蟻賊”之手,後又“壯士全師勝”,“蛾眉疋馬還”,終歸聚首。過程跌宕起伏,亦可謂愛情不渝。中間穿插横塘故郷、浣纱女伴,再繼續西向秦川的征程,構成迄止梅村寫作時圓圓的完整故事。《永和宫詞》叙述更為平順,從田貴妃入宫寫起,“夾道香塵迎麗華”,然後叙其入宫後的得寵及失歡,種種情事,直至“病不禁秋涙沾臆,裴回自絶君王膝”,亦是一生的故事。“永和宫”者,乃帝與妃失和復好之場所,梅村取以名篇,幾同於《長恨歌》之“長生殿”也①參程穆衡:《吴梅村詩集箋注》,第72頁。。惟通篇用典,與《圓圓曲》及另一篇《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的基本白描大不同。此或以貴妃身份與圓圓、玉京之差别,宜用典故代出之,以示莊重乎。梅村此一用心,不容不表出之,在藝術上也不能視為消極②昔王靜安《人間詞話》有“《長恨歌》所隷之事祗‘小玉雙成’四字,梅村歌行則非隷事不辦”云云,乃就一般原理言之。至於詩人高下,固以致日人鈴木虎雄“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則專以使事為工。然梅村自有雄氣駿骨,遇白描處尤有深味”一語為最穩當。。《臨淮老妓行》主要寫此妓昔日在甲申變後代主將“暗穿敌壘”探尋兩宫消息的俠義之舉,從“請為將軍走故都”至“翻身歸去遇南兵”,即寫此一段驚險之事。但也擬其自述身世,小名冬兒,與陳圓圓同為田遇春所畜伎,後歸山東總兵劉擇清。上述探營歸來後,又接以“退駐淮陰正拔營”,一路寫到劉氏的“豎降旛”、“過長淮”,而“長淮一去幾時還”,結局不堪已不問自明。“老婦今年頭總白”,也隨之走完一生。三詩以叙事之體,寫成三位女主人公各異的形象。《圓圓曲》末八、九韻,《永和宫詞》末十二韻為議論,蓋至此時,詩體早已獨立完全,無需再另作“傳”文了③《圓圓曲》有陸次雲後補之《傳》,頗多小説家言,轉以梅村詩為徵,以詩語“衝冠一怒為紅顔”代議論,完全顛倒了傳與詩的關繫。。然亦寫得艷麗,色彩與叙事幾近一體,而非議論慣常的“灰色”調。《臨淮老妓行》也是夾叙夾議作結。
《圓圓曲》、《永和宫詞》及《臨淮老妓行》此種叙寫女主角一生的體旨,後世多有倣效,最具影響力,姑可名之為“梅村體”叙事的“正體”。其他尚有寫群角、寫男主角等的不同。如《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與《蕭史青門曲》,非專寫一人,衆人什事,穿插銜接,叙寫實更不易。玉京琴曲中的衆候選嬪妃,既有“中山女”、“祁與阮”家女,還有“同伴沙董兩三人”等;“青門公主第”中的衆公主,樂安嫁鞏公(永固)、寧德嫁劉郎(有福),兩家甲申變後一殉節,一流落苟且於民間。中間還插寫了另一位公主“神廟榮昌主尚存”的結局,即神宗駙馬楊春元早卒而榮昌公主獨享永年。兩詩之人、事斑斕紛呈,極見謀篇技巧,是“梅村體”叙事的另一種路數格局。《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大抵循白樂天《琵琶引》的寫法,又與《楚兩生行》、《琵琶行》等同一旨趣,借藝人説世事,而皆有“我”置身其中,“事”的客觀性不盡徹底。
以男士為主角的數首,《雒陽行》詠李自成兵陷雒陽福王被殺事,《殿上行》詠楊士聰敢諫事,二詩略遜情韻;惟《雁門尚書行》記兵部尚書孫傳庭事,前半十八韻寫其代行陝督,與李自成軍潼關大戰敗亡的始末,聲氣悲壯,後半十九韻再詳其妻女殉節、諸子流離的戰後遭遇,以代議論,悲上加悲,叙事完足,可與女主角之《臨淮老妓行》媲美。《王郎曲》詠歌郎王稼(一作子玠),與《琵琶行》等説世事不同旨趣。後亦有嗣響,如陳維崧有《徐郎曲》,袁枚有《李郎歌》,樊增祥有《梅郎曲》,易順鼎有《賈郎曲》、《朱郎曲》、《萬古愁為歌郎梅蘭芳作》等,都是梅村此題的後勁之作。
上述人物主題諸詩,徐釚《本事詩》多有選録,“梅村體”的重心自在此一端。徐氏因其選旨所限而未及選入的詠私家莊園一題,實與“梅村體”關繫亦非淺。明季多事,繼而江山易代,吴氏南人,熟悉吴越一帶私人園林,目睹其興衰,不免賦詩興感紀實。如《鴛湖曲》詠嘉興城南之鴛鴦湖煙雨樓,主人吴昌時崇禎十六年在朝遭嫉被殺;《後東皋草堂歌》詠常熟縣北瞿式耜之東皋草堂,瞿氏擁立桂王,順治七年在廣西事敗被執就義;《詠拙政園山茶花》歷數明季以來此園主人之興替,尤惜憾於當前主人陳相國(之遴)之買園不歸。而《雕橋莊歌》詠梁夢龍之雕橋莊,則在北地直隸正定縣西,梅村因與其後人相識,感慨此園“後亂獨全”,“四海烽烟喬木在”。《九峯草堂歌》詠諸乾一松江九峰山下之草堂,也是難得的園在人在,蓋主人“取第後未仕”也,詩序指出此點,當非偶然。
梅村寫此題,多因與園主有舊,故感慨係之。其與一般懐人之作不同者,乃在每以七古體之長,著重寫莊園之淵源興亡始末,園景故跡被寫得極為充分,幾乎代為主角。私人園林本非皇家宫苑之比,但梅村諸作終得以“故地”之趣,而與《連昌宫詞》等的“故宫”之旨為近,差可入其範疇,其義蓋在於此。後同治末王闓運作《圓明園詞》,尚云倣《連昌》、《津陽》,而民國初王靜庵作《頤和園詞》,已自比於梅村體了。則梅村此題諸作,正可視為中間一環節也。
以上略分析了梅村體的叙事性質。梅村七古在承襲長慶體之餘,一個重要改變就是悉採實事,直接從社會原樣取材,不用虚構誇張,向新樂府之取材標準靠攏,同時也能保持其故事性,甚至更形生猛鮮活。這自然不必是梅村有意為之,而是所處的時代風雲激蕩使然。吾國詩學一般認為七古較五古體卑,元白長慶體的虚構性、故事性不够矜重,不及老杜新樂府的不避五言、議論叙事並用體格大方。如流傳甚廣的李白之語“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孟啟《本事詩·高逸》),上述蘇子由批評長慶體的叙事“寸步不遺”之説,最為直白。梅村體反其道而行之,大張七古叙事之功能,但又斷然“改採實事”,此舉大為改觀了長慶體叙事飄忽虚構的品質,是獲至後世詩學首肯的一大關鍵。從梅村體的成功可以看到,吾國叙事詩體的成立,主要在以叙事克服諷諫、議論而成為首旨首趣,但其背後仍然是以樂府采詩、興觀羣怨的詩教傳統作為支撑的。
五、“梅村體”叙事的風華情韻
上文疏理了從長慶體到梅村體的叙事性質,有别於新樂府等其他體的“叙述”或者僅有的“叙事因素”。如果進一步分析,吾國此種唐後發展起來的“文人叙事詩”體(相較於唐前樂府无名氏叙事詩而言),在用詞與押韻這些基本方面,也會由叙事之旨發展出新的特點,而與杜、韓、蘇、黃為代表的七古主流風格形成顯著的區隔。
七古體内部的這兩種風格區别,最初是由明人何景明指出的,他的《明月篇序》極敏鋭地從初唐四子與老杜的對比説起:
僕始讀杜子七言詩歌,愛其陳事切實,布辭沉著,鄙心竊效之,以為長篇聖於子美矣。既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為,而反復之,則知漢魏固承《三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辭固沉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鳩”,六義首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托諸夫婦以宣鬱而達情焉,其旨遠矣。由是觀之,子美之詩博涉世故,出於夫婦者常少。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此其調反在四子之下歟?①《何大復先生集》卷一四,嘉靖刻本。大復此論在清代獲至的支持,詳拙文《明清詩論中的唐歌行與梅村體七古》,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及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合編:《中國文學學報》第九期(2018年12月),第147—162頁。
指出初唐體“音節往往可歌”,有别於老杜的“調失流轉”;“托諸夫婦以宣鬱逹情”,有别於老杜的“博涉世故,出於夫婦者常少,而風人之義或缺”,這兩點即成為後來長慶體、梅村體所繼承的兩個主要藝術特點。音節的流轉與所謂“夫婦者”也即男女主角的具體設定,尤其成為梅村體的表徵。而老杜七古的所謂“啞調”,在清人學杜韓、學黃庭堅的詩人手上也有所變化,如錢載、鄭珍、陳三立等。又有學李太白、學楊誠齋而音節亦復流轉者,如袁枚、黃仲則、郭麐等,情形不一而足,共同形成了清人七古歌行創作繁盛的局面。
這裏主要談梅村體。梅村七古的音調如何流轉?趙翼曾揭其秘:“妙在轉韻,一轉韻則通首筋脈倍覺靈活”,“其秘訣實從《長慶集》得來”①《甌北詩話》卷九,載《清詩話續編》,第1283頁。。關於這一點,昔人又曾對比老杜七古甚少轉韻,往往一韻到底,而元、白歌行則一二韻即轉,“未免氣促”的兩極②方世舉:《蘭叢詩話》,載《清詩話續編》,第772頁。此是在音韻方面的揚杜抑白,實質與蘇子由同。汪師韓《詩學纂聞》曾駁方氏老杜七古不通韻之説,甚是。。梅村七古自然與元、白為近,大抵以二韻一轉為常式,或平或仄,形成全篇動蕩急迫的基本節奏,此非其短,而是合於其詩内容動輒涵括人物一生、家國大事的長時段性質。中間又不時穿插一韻與三四韻的轉换,或更急促,或稍作緩和,適應事件推進之進程,遂倍覺其出神入化矣。
具體來看,例如《永和宫詞》全首五十四韻,二韻一轉,凡二十六轉,極為整齊,是其典範之式。其中第三、四、七、八、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二十一、二十五轉是以鄰韻通押的方式完成的。再如《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全首三十五韻的前十五韻雖不規則,有五字句,有五七字句,有三句一韻,轉韻除二韻一轉外,又有一、三、四韻一轉者,極為錯綜;但後半之二十韻,却又二韻一轉,入其常式了。
而多數之作的轉韻,則是以二韻一轉建立基本節奏,再隨機插入一韻或數韻一轉的其他節奏,與上述兩首不同。以《圓圓曲》為例,起首六韻,二韻一换,先一平(上平删韻)一仄(去聲霰韻)交代完將軍陣前奪美人、報君親之讐這件亦壯亦艷之事,即再轉平韻(下平麻韻),快速進入兩人之初相識。下面再以三平韻(上聲紙韻)接,較舒緩地從頭道出圓圓“横塘水”、“采蓮人”之出身。隨即又轉為二韻(上平五微)、二韻(入聲十一陌)的常式,叙其離家而奪歸豪門。接下來以四韻,較充分地叙述兩人相識相悦到分離相思,用去聲遇韻,頗合此過程之苦澀基調。又接以三韻(上平十四寒)叙美人陷賊手。以下五韻皆一韻一轉,亟傳出陣前奪人的緊張激烈與美人驚魂啼妝的瞬息變化,而第五韻已走上秦川西征之塗了。人物故事至此叙完。下面回到“江鄉浣紗女伴”,與作對比,發苦樂毁譽之議論,夾叙夾議,是四韻(下平七陽)、三韻(去聲四寘與八霽通押)、三韻(下平八庚與九青通押)之轉,平仄平,可見詩人感慨之甚。最後“君不見”下,復歸二韻(入聲二沃)、二韻(下平十一尤)的常調,全詩結束。其他如《蕭史青門曲》、《臨淮老妓行》、《楚兩生行》、《王郎曲》等,大都如此,隨叙事之需要而轉韻,並不求一律。《臨淮老妓行》中間叙其自告奮勇,代主將穿越敌營入都城探舊主,從“錦帶輕衫嬌結束,城南挾彈貪馳逐”到“薰天貴勢倚椒房,不為君王收骨肉”九韻通押(入聲一屋二沃),全過程不换韻,返程“翻身歸去遇南兵,退駐淮陰正拔營”始轉韻,此例最可見出“梅村體”用韻服從叙事、韻調助叙事的特點。其“情韻”勝於初唐體、長慶體之處,端在此乎?
至於梅村七古擅以男女情事為主線,上文已作過分析。對此一特點,也是趙翼評得準確:“梅村詩本從香奩體入手,故一涉兒女閨房之事,輒千嬌百媚,妖艷動人”;其得失則是“有意處情文兼至,姿態横生;無意處雖鏤金錯采,終覺膩滯可厭”①《甌北詩話》卷九,第1290頁。。此言雖亦有微辭,然較晚清朱庭珍“入手不過一艷才”、“倘不身際滄桑,不過冬郎《香奩》之嗣音”②《筱園詩話》卷二,載《清詩話續編》,第2355、2389頁。的批評大為中肯。“香奩體”的尊卑本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以韓冬郎品行之堅貞而作成此體,其詩之情趣,若究其實,與國風、屈騷之香草美人並無二致,實不容小覷,此處暫不深論。而况梅村七古所取之男女情事,幾乎無一首不涉及家國之鉅變,與一般之兒女情長又非可同日而語,筱園竟以假設之辭詆之,不可謂厚道也。
若再回到徐釚《本事詩》來看此一問題,又可知梅村當時此道不孤。他體不論,七古長篇即有陳瑚《蘭陵美人歌》、俞南史《定定詞》、鄒祗謨《金屋歌》、陳玉璂《小虎詞》、董以寜《碧玉歌》、顧景星《楚宫老妓行》、《憶戊子夏客廣陵遇田九自云故貴妃異母季弟也潛述其事恨流傳失實追賦此篇》、汪楫《女羅篇為冒巢民蔡姬賦》、吴兆騫《白頭宫女行》、彭椅《舊院行為閻再彭題姜姬畫蘭作》、李良年《塞上嚴都尉署中觀女樂歌》等,姬妾歌妓、貴妃宫女,俱為主角;吴綺《韓繡行》之織婦,則是新的身份。其中尤其如《定定詞》、《金屋歌》、《小虎詞》、《碧玉歌》等,旨制最近梅村體。又有顧開雍《柳生歌》、汪懋麟《柳敬亭説書行》、毛奇齡《羅三行》,以及陳維崧之《徐郎曲》、《贈琵琶教師陸君揚》、《贈歌者袁郎》等,藝人男角,也都與梅村同題同趣。諸作或即倣梅村而作,也未可知。如顧景星《閲梅村王郎曲雜書絶句志感》十二首,内中即有“柳生凍餓王郎死,話到勾闌亦愴情”,“永和宫怨雒陽行,手語矜能卞玉京”等語①徐釚:《本事詩》卷一〇,載拙編《清詩話全編:順治康熙雍正期》,第1302—1303頁。,當時熟知梅村詩之情形,於此可見一斑。
康熙以後,直至清末民初,吾國叙事詩的創作,嚴格説來似仍只在“梅村體”的範疇内進行,乾嘉時期的楊芳燦、陳文述,晚清民初的樊增祥、楊圻,四家之七古都被明確視為“梅村體”的傳人。諸人以女性為主角的長篇,楊蓉裳有《鳯齡曲》、《香修曲》,陳雲伯有《龍幺妹》、《赤陵女子琵琶歌》,樊樊山有前後《彩雲曲》,楊雲史有《天山曲》、《長平公主曲》、《神女曲》等,都被公認歸為梅村體的傑作。與樊山並稱的易順鼎,其七古長篇也有傚梅村體者,如集中有《四月八日集榕山古歡閣傚梅村體賦長句紀之》一首,即明言之。上文曾舉其以歌郎為題者多篇,他還有一首《鮮靈芝曲》,以女戲子為主角,然言頗率意,則不足觀也。
梅村體的影響當然不止於此,若再廣泛搜集其他詩人集中的個别之作,如李慈銘《杏花香雪齋詩》有一首《包英姑歌》,錢仲聯《夢苕庵詩話》録有王甲榮、薛紹徽的“彩雲曲”等,加上“宫苑”主題的王闓運《圓明園詞》、王國維《頤和園詞》等鉅製,其影響之普遍性也是大抵可窺知的。
總之,七古本是舊體詩中最晚發展起來的兩體之一(另一體為七律),清代又是傳統社會的最後一個時期,梅村體横貫其時,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叙事詩的主型,其成就是令人歎為觀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