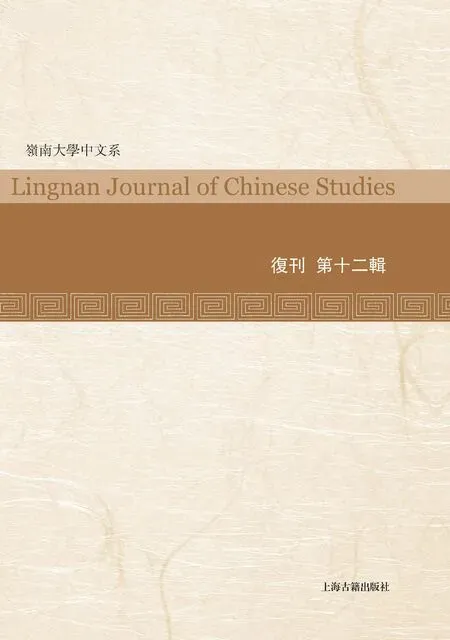論叙事與抒情的邊界
2020-12-30饒龍隼
饒龍隼
近世以來隨著抒情傳統與叙事傳統討論的深入,中國古代文學叙事與抒情的邊界問題日益凸顯。它們究竟有無邊界?若有邊界則在哪裏?其邊界是模糊的,還是截然清晰的?其邊界是一次劃定,還是歷史地生成的?這一系列問題,亟需得到解決。這些問題若獲解決,且能付諸學術實驗;則可為疏通中國文學抒叙傳統提供理論依據,也能夠更好地參與中國文學研究的國際對話,以校正充實陳世驤“中國文學抒情傳統”説,並證成中國文學叙事與抒情兩大傳統並行論。
一、叙事與抒情之同體共生
文字表達的方式多樣,叙事與抒情特其二義,此外還有議論與説明等,而前二者更適用於文學。從中國文學史的源頭上説,叙事與抒情發生孰先孰後,是個難以考索的問題,今日恐衹能任其茫昧。然據甲骨文和青銅文,及其相應的表達辭式,猶可探悉情、事性狀,並考察抒、叙之何如。甲骨文出現“事”字162處,衹出現“情”字1處;青銅文無“情”字,出現“事”字338處;甲骨文無“抒”“叙”字,《殷周金文集成》亦無之①甲骨文出現“事”字,分别見《合集》115處、《合補》41處、《花東》6處;甲骨文出現“情”字僅見於《合補》1處;青銅文以《殷周金文集成》為檢索標本。。這起碼説明,在殷周之際,抒與情、叙與事不可能成辭,抒情與叙事的概念無從談起。
然而這衹是一種器物文字上的表象,並不排除當時有抒情、叙事之行為。此中抒情、叙事的實際狀況與情形,可據从“心”字和“事”字來分析。

如較早的周武王時器保卣銘文:
乙卯,王令保及殷東或五侯,兄六品,蔑曆于保,易賓,用乍文父癸宗寶彝。遘于四方王大祀、于周,才二月既望。
又如較晚的周宣王時器虢宣公子白鼎銘文:
虢宣公子白乍鼎,用追享於皇且考,用祈眉壽,子孫永用□寶。①以上參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册),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330—331頁。
但也有學者指出個别特例,如西周前期作册嗌卣銘文:
乍册嗌乍父辛,氒名義曰:“子子孫寶。”不彔!嗌子,子延先盡死。亡子,子,引有孫!不敢憂。況彝,用乍大禦於氒且匕、父母、多申。母念哉!戈勿剥嗌鰥寡遺,石宗不刜。晁福林説:“《作册嗌卣》卻是一個例外,它既没有稱頌先祖之美,也没有走‘子子孫孫永寶’這樣的‘明著之後世’的路徑,而是彰顯個人的失子之痛、失子之憂。就此而言,若謂此篇銘文是後世悼亡文字的濫觴,並不過分。此篇銘文没有直接寫自己的苦痛心情,而是胸臆臨銘而發,感觸方現於筆端。”②晁福林:《〈作册嗌卣〉:風格獨特的周代彝銘》,載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4月29日第7版。據實而言,這番分析屬援後例前,明顯有誇大其詞嫌疑。銘文中確實述及嗌亡子之事,但並非抒寫器主的失子憂痛,而衹是向祖神陳述其情,並明確説“不敢憂”。所以,該銘雖然表達很特殊,但仍屬叙事而非抒情。

初 期 中 期 晚 期乍册 乍册尹、命尹内史、乍册内史、乍命内史 内史尹内史尹氏、尹氏友 尹氏史史史
但甲骨、青銅文所反映的情況,並不能説明叙事就早出於抒情。這是因為,龜甲獸骨和青銅鼎彝作為器物,其貞卜、祀典功能是第一屬性,其所銘刻的文字衹是附屬品,而不是獨立自足的文本形式。若將甲骨青銅器物與所銘刻文字一同觀察,就會發現其所含叙事與抒情是同體共生的。通常貞卜的對象是祖先或神靈,貞人和時王都滿懷虔敬之心情,在這通靈的占問與刻辭活動中,情感表達和事件陳述是並行的;同樣,鑄銘隱含的對象是祖先和後代,器主人既敬慕祖德又冀望後人,在其家族銘功紀德的鑄造活動中,情感表達和事件陳述也是並行的。
今所見保存較完整的甲骨卜辭,包含前辭、命辭、占辭、驗辭,各部分文辭不是連貫的,而是貞卜諸環節的記録。如:“(前辭)戊子卜。(命辭1)嘏貞:帝及四夕令雨?(命辭2)貞:帝弗其及今四夕雨?(占辭)王占曰:丁雨,不辛。(驗辭)旬丁酉,允雨。”③胡厚宣總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1982年版,第一四一三版。這四部分要連綴起來,纔能構成完整的叙事;而其連綴所依憑的就是貞卜程式,以及貫注其中的對上帝虔敬之情。故知其事與情是一體二分的,則叙事與抒情行為實屬共生。青銅器銘的情況與甲骨貞卜近同,而又有自身特點和後續發展變化。早期青銅器的銘文簡樸,字數偏少甚或僅為族徽,其叙事的意味不甚明顯,而銘功紀德的情意較強;以後銘文字數逐漸增多,所述祖德勳績亦更詳實,其叙事的功能日益凸顯出來,而與器主人的情意共為一體。
以上通過甲骨文與青銅文這類器物文字,分析殷周之際叙事與抒情同體共生現象。這個現象在遠古時期是普遍存在的,因而隱含了叙事與抒情共生之通例。以此推尋,遠古歌謡,例皆情、事兼含,抒情與叙事共體:
例1《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①趙煜:《吴越春秋》卷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463册,第60頁。傳説此為黃帝時的歌舞,舞蹈是模仿狩獵的場景,歌詞是呈現捕獵的過程,前者為激奮情緒之宣洩,後者為連續動作之描述。將這兩相配合起來分析,即為抒情與叙事之共生。
例2《葛天氏歌》:“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②吕不韋主撰,王利器注疏:《吕氏春秋注疏·仲夏紀·古樂》,成都:巴蜀書社2002版,第536—538頁。此為遠古葛天氏族祀神慶功的歌舞,儀式為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這八闋實為八個歌舞段落,逐一演述氏族生活的場景,包括養育百姓、圖騰崇拜、水土保護、五穀生產、敬奉天常、建立帝功、依順地德、統領萬物③吕不韋主撰,王利器注疏:《吕氏春秋注疏·仲夏紀·古樂》,第538頁。引畢沅校語:“舊本作‘總萬物之極’。校云:一作‘禽獸之極’。今案《初學記》卷十五、《史記·司馬相如傳》索引及《選》注皆作‘總禽獸之極’,今據改正。”畢氏所據諸校本均出自唐代,比東漢高誘的注本更晚產生。“禽獸”作“萬物”,或另有所本,可並存不廢,而於義無害。,這些實堪稱宏大叙事,而多種崇高情感寓焉。
例3《伊耆氏祭歌》:“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勿作,草木歸其宅。”④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郊特牲》,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第1454頁上。這是伊耆氏蠟祭歌舞,為祈求來年風調雨順,而模仿天神威嚇訓斥的語氣,命令水土昆蟲草木各安其事。此將叙事隱含在神威之中,而呈現快意又莊嚴的情氛。
例4《搶親歌》:“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⑤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賁》,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第38頁上。這是遠古氏族搶親習俗及場景的描繪,其野性衝動和歡快喜慶之情溢於言表。
例5《潛龍歌》:“潛龍勿用,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飛龍在天,亢龍有悔,見群龍無首。”①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乾》,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第13—15頁上。這是一首遠古歌謡,描述龍的潛飛過程;但它不是意脈聯貫的文辭表達,而分屬於筮占操持程式諸步驟。其步驟有四:(一)用枚蓍籌算,以確定占問事類所隨機配對的卦名《乾》;(二)查閲占卜書,以給《乾》卦的每一爻位和整卦配對謡辭;(三)依據卦象和《易》象對爻辭作出解説;(四)結合謡辭和《易》象來占斷吉凶禍福。在這頗為神秘的操持程式中,逐步灌注敬慎、剛健之志意;故神龍潛飛之事與君子自強之志,同演述於卜官的筮占諸步驟之中。
例6《佚女歌》:“燕燕往飛。”此為有娀氏二佚女所作歌,因其極簡樸而為北音之始。其創作情形為:“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諡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②吕不韋主撰,王利器注疏:《吕氏春秋注疏·季夏紀·音初》,第627—631頁。燕應該是某氏族的圖騰,蓋該氏族與有娀氏通婚,纔發生男女戀情,而產生這首戀歌。像這種演生於原始宗教之鳥圖騰崇拜中的愛情,其燕飛鳴逝之事與戀慕不舍之情是一體未分的,兩相共生,見於音初。
例7《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這是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卷一所録詩歌,大概是依據更晚出文籍所載《擊壤歌》諸本校訂的。該詩前四句為叙事,最末一句則屬議論。其實,在王充《論衡·感虚》等篇中,載録有《擊壤歌》更早版本:“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本叙事性增強,議論的意味減弱。若再往上追溯,則知該詩本無。《莊子·讓王》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乎,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後《淮南子·齊俗訓》亦因承之,衹是將主角善卷改為古童蒙民。由此可知,傳説堯盛平時期的擊壤歌,實為一種自娱的歌舞唱和,其文辭之有無、文本之歧異實不足深考,然其情緒的發洩與美善之追述必相伴生③以上參考饒龍隼:《擊壤歌小考》,載於《古典文學知識》2001年第2期,第64—70頁。。
例8《候人歌》:“候人兮猗。”此為塗山氏女所作歌,因其極簡樸而為南音之始。其創作情形為:“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①吕不韋主撰,王利器注疏:《吕氏春秋注疏·季夏紀·音初》,第616—619頁。“候人”既為極短之叙事,“兮猗”又是深情的發抒,兩相共生,亦出音初。
如上所示,原始宗教活動中的歌舞謡謳,其抒情與叙事是同體共生的;而作為原始宗教整合昇級版的祖神崇拜,及其制度化產物的甲骨貞卜、青銅鑄銘,其抒情與叙事也仍是同體共生的,故表徵為抒情與叙事之早期狀態。這狀態為叙事主要由文辭承擔,而抒情主要由器物或儀制承擔。總之,從遠古歌謡,到殷周甲金,例皆情、事並生,更兼抒、叙共體。
二、叙事與抒情之體制分化
中國本土的原始宗教諸形式,如天帝—高級神、巫術儀式、圖騰崇拜、萬物有靈、祖先崇拜、自然—星辰神話、祖神崇拜,及其作為制度化產物的甲骨貞卜、青銅鑄銘、《周易》占卜、禮樂儀制、《詩》篇演述等等②參見饒龍隼:《原始崇信及其表象》,載於《上古文學制度述考》,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90—92頁。,都是抒情與叙事的原始載體。這些原始載體之功能發揮,其有效時間是極為漫長的,上可追溯至遥遠的鴻蒙時代,下則臨届春秋晚期禮崩樂壞。但從周公旦制禮作樂,到孔子所遭禮崩樂壞,這些原始載體也經歷一個衰落失效的過程,就是在這過程中抒情與叙事發生體制分化。
這些原始載體的衰落,是個局部緩慢的過程:一方面,甲骨貞卜、青銅鑄銘、《周易》占卜、禮樂儀制、《詩》篇演述等還在流行,但同時它們的某些傳載功能、操持程式與寓意内涵在逐漸流失、消退或變改;另一面,言語這種新媒質的傳載功能在悄然生長,並逐步取代器物或儀制原來擔當的職能。由於早前叙事主要由文辭承擔,而抒情主要由器物或儀制承擔;所以言語傳載功能之增長,更明顯體現在抒發情志上。
這可從《詩》篇所載,來考察情志抒發狀況。大抵説,十五《國風》和《小雅》中的情志抒發頻繁,而《大雅》和三《頌》中的志意活動卻極少。這個分佈性狀表明兩點:(一)《詩》篇的情志抒發主要發生在志意活動場景,而明顯遠離朝政、宴饗、祭祀等公共典禮場合;(二)其志意活動不再依賴禮樂儀制,而是主要訴諸言語文辭之表達。此性狀既見於《詩》篇,也還表徵於《尚書》中。例如:
1.謔浪笑敖,中心是悼(《邶風·終風》);2.心之憂矣,我歌且謡(《魏風·園有桃》);3.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小雅·白駒》);4.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小雅·節南山》);5.心之憂矣,雲如之何(《小雅·小弁》);6.往來行言,心焉數之(《小雅·巧言》);7.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小雅·白華》);8.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商書·太甲下》);9.爾惟訓於朕志(《商書·説命下》);10.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周書·旅獒》);11.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於民(《周書·多方》)。例1至例7是《詩》篇中的語句,年代範圍為西周初以至春秋中期;而從其情感色彩看,大多是憂傷的思緒,蓋屬變風、變雅之類,應出自平王東遷前後。這些語例反映了西周晚期人們對志意與言語溝通的樸素認知,其主要特徵是志意與言語發生直接溝通而不需禮樂儀制傳載,志意是抒情主體的,言語也屬抒情主體,兩相均由抒情主體來操控,而達成二者的無間隔膠合。
以此認知進度來反觀更早《尚書》中的語例,就會發現《尚書》的志意與言語溝通更古樸。例8和例9中的言語和志意,明顯分屬施受兩種身份的人。施言者發出言語,來幹預受言者的志意;受言者懷有志意,來接受施言者的影響。此即造成這樣的一種狀態,志意與言語不是同出一人;故二者溝通是間接的,尚未達至直接之溝通。例8和例10中的志意與言語溝通還另有隱情,即志意與言語借助“道”的中介而發生關聯。這樣,不論志意與言語分屬兩人,還是統合在同一個人身上,它們均因“道”的間隔而發生間接溝通,卻無法達成直接溝通。至於例11“不肯慼言於民”,雖關夏政而所言在西周早期,時序上更接近《詩》篇中的語例,故其志意與言語溝通與《詩》同。由此可知,儘管《尚書》有疑偽成分,但其語例所顯示總體情態,仍然真實地反映了殷周之交人們對志意與言語溝通的認知,故《尚書》與《詩》篇的認知序列恰與上述示例順序相反,即在該時段人們對志意與言語溝通之認知,經歷一個由間接溝通趨嚮直接溝通的進程。若説志意與言語間接溝通,仍表明有器物儀制的痕跡;那麽志意與言語直接溝通,就使抒情脱離了器物儀制,以此引發兩相的體制分化,而與叙事同訴諸語言表達①參見饒龍隼:《前諸子時期言意關係的新變》,載於《上古文學制度述考》,第46—51頁。。
至此可以説,抒情與叙事之傳載體制及介面,已由器物儀制轉接為語言媒介。正是得力於語言媒介的逐步深入地參與,抒情與叙事的邊界纔因體制分化而彰顯。比如殷周青銅銘文,越往後其文字越多;並且隨著長篇銘文大量出現,不僅其叙事性獲得長足發展,而且其抒情因素也有所增長,終使器物的表情功能被弱化。尤其戰國中山王鼎,作為巨幅的青銅載體,竟然銘刻有六百多字長文,而使述事與寫情一體兼備。其文曰:“氏(是)以賜之氒命:‘隹(雖)有死罪,及參(三)(世),亡不若,以明其德,庸其工(功),老奔走不(聽)命,寡人懼其忽然不可得,憚憚,(恐)隕社稷之光;氏(是)以寡人許之,(毋)(慮)盧(從),皮(彼)有工(功)智旃,詒(台)死罪之有若,知為人臣之宜(誼)旃。烏虖!念之哉,後人其庸,庸之,毋忘爾邦。”②參見徐中舒:《殷周金文集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387頁。此一文例亦充分表明,青銅器之情、事共生,已由器物含情、銘文述事之一體二分,演變為銘文既述事又寫情之一體兼備;則其抒情與叙事之邊界,也就移置到語言媒介上。
與此類似的情形,也顯明在易象上。前引《潛龍歌》之文辭,是依託占卜操持程式的,其神龍潛飛之事與君子自強之志,實分屬於筮占的文辭與程式之中,雖一體二分,而以占為主。及至春秋晚期孔子研《易》時,占卜功能弱化而文辭功能增強。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所出帛書,其中的《要》篇有一段文字曰: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子贛曰:“……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尚書》多於(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贛曰:賜]“……夫子今不安其用而樂其辭,則是用倚於人也,而可乎?”……子贛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易》,我復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③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載於《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35頁。
孔子研習《周易》之取向,是“不安其用而樂其辭”。“安其用”即尚占,是指卜、筮、贊、數等要素;“樂其辭”即尚辭,是指遺言、辭、德義等要素。在尚占與尚辭之間,孔子顯然更重文辭。如此就出現了尚辭不尚占的趨勢,以至有偽託孔子“十翼”之創作,其文辭義理具有相對獨立性,而不再依賴占卜之操持程式。後《焦氏易林》即依循其文辭義理,推演編撰出四千零九十六首卦變辭。這些卦變辭均為四言詩,其中既有叙事又有抒情。如卦辭:“黃鳥悲鳴,愁不見星,困於鷙鸇,使我心驚。”①焦延壽:《焦氏易林》卷一《屯之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808册,第279頁。這是一首很純粹的抒情詩,其情思乃因《説卦》而來。依據焦延壽的“卦自為變”之占法,《屯》之《豐》可演為七個單元卦:《離》有“雉”象,可引申為鳥;《震》有“玄黃”之色,則“黃鳥”之象出。《兑》有“口舌”之象,《坎》有“憂愁”之義,則“悲鳴”之象可得。《坎》又為水,可引申為雲;《坤》有“陰”“夜”之象,合而為陰雲;《巽》為風,風吹陰雲掩蓋天空,則“不見星”之象出。《艮》有“黔喙之屬”,為黑嘴鳥類之象;《兑》又有“困境”之象,則“困於鷙鸇”之象生。《震》又有“決躁”之象,則可引申為“心驚”②參見陳良運:《焦氏易林詩學闡釋》,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349頁。。這樣僅在文辭義理上推演,就奇妙地生成一首抒情詩。像用這種方式創作的詩歌,實已脱離占卜程式之共體,而單純在語言媒介上,就可區分叙事、抒情。
其實上述情形,也可反過來看。語言媒介功能之逐步上昇,擠佔器物儀制的傳載空間,因使鑄銘或筮占承擔的抒情職能退化,而需更純粹的言語文辭形式來替代之。如在晚周詩教興廢和兩漢辭賦興盛的背景上,“賦”的功能變遷及體式生成就頗能説明之:
在《周禮·春官·大師》中,載有針對樂師瞽矇的六詩之教,即風、賦、比、興、雅、頌;同書《春官·大司樂》中,又有針對國子生員的樂語之教,即興、道、諷、誦、言、語。前者旨在培養能演述詩篇的音樂人才,後者旨在培養能行使專對的行政人才。在周代禮樂制度尚完好時,這兩類教職都屬史官系統,能並存不替而各司其責,共同承載禮樂言語行為。及平王東遷而天子衰微,更因春秋晚期禮崩樂壞;這種教學制度遭破壞,出現“詩亡”的局面,瞽矇采《詩》之官失散,新的《詩》篇不再產生③語出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離婁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第2727頁下。;已經整編好的《詩》篇雖留在官府,但其禮樂形式日漸流失而徒有文辭,成為“賦《詩》言志”的素材,用來修飾朝堂議政和外交辭令;後來孔門開設言語一科,並以《詩》篇作為教程,就是為應對這個變局,以教導弟子能適應之;至於孔子删定“《詩》三百”,則無奈衹能以文獻形式保存之。在這脱落儀制而徒有文辭的《詩》篇文獻中,原來詩樂演述中的抒情與叙事行為無所附麗;其情志的發抒與人事的記述,就須轉接到新的創作活動中。當時活躍的創作方式有兩種:一是作為士大夫素養的“登高能賦”①參見班固:《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二十四史》縮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755頁。,一是制度化的史官之“《春秋》作”。前者主打抒情,是溢出《詩》篇外的謳歌嘯詠②參見饒龍隼:《先秦諸子與中國文學》上編第一章謳歌嘯詠,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37—109頁。;後者主打叙事,是為春秋時期的列國史記。兩者内涵、語體和功用均不同,展示了抒情與叙事的首次分化。
像這樣轉接為新的創作形式,衹是“詩亡”後的一條出路;同時還開闢另一條出路,即用《詩》方式的變革。原來“六詩”之風、賦、比、興、雅、頌,本是禮制完好時詩樂演述的六道工序,各項目之間是逐步遞進的,共同承載抒情與叙事功能;但隨著《詩》篇以文獻形式被編定,其風、雅、頌作為詩歌類名得落實,而賦、比、興則因無法歸類而没有著落,這反映在《詩大序》中便為“六義”説。《詩大序》對“六義”説,衹解釋了風、雅、頌三項,而於賦、比、興不予解釋,因使此三項有流失的錯覺。
其實賦、比、興這三項並未流失,而是以説《詩》的方式繼續流行,今存《魯詩》殘篇、《毛詩》鄭注等文籍,多保留“賦也”、“比也”、“興也”解説語。如:
《關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禦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為先比而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氓》,淫婦為人所棄,鄘人述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賦也,三、四、五[章]皆興也,五章賦也,六章賦中有比也。③以上申培:《詩説》,程榮纂輯《漢魏叢書》本,明萬曆新安程氏刊本,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二三頁上—二四頁上。這從功能角度對賦、比、興作出解釋,而與風、雅、頌之詩歌體類分列開來;並歷經鄭衆、鄭玄、劉勰、鍾嶸的遞相沿襲,至唐初孔穎達《毛詩正義》而有三體三用説。更在此“三用”之中,賦與比、興進一步區分,賦通常指嚮叙事,比興多指嚮抒情。如:
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①鄭玄注,賈公彦疏:《周禮注疏·春官·大師》,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本,第796頁上。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②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之《詮賦》《比興》,第134、601頁。
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詠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③鍾嶸:《詩品·序》,載於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1頁。
鄭玄從政教功利解説賦、比、興,指明其鋪陳與比類、取喻之差别;劉勰從摛文寫志解説賦、比、興,指出其體物與附理、起情之不同;鍾嶸從言意關係解説賦、比、興,提出書寫事物與隱喻情志需相待。兩相辭采、對象和效用均不同,體現了抒情與叙事的二次分化。
三、叙事與抒情之各體消長
上述抒情與叙事的兩度分化,導致賦的叙事功能急劇增強。隨著賦的叙事功能增強,其所叙事容量也在增加;當叙事文字達到一定長度,就會提高其篇幅的獨立性;而文辭篇章一旦相對獨立,作為文體的賦就脱胎而出。如戰國晚期荀況所作《賦》,本是由五篇詠物短賦構成的,分别題詠禮、知、雲、蠶、箴,文末附有佹詩、小歌兩小部件。此五篇短賦用問答形式展開叙事,所謂“君子設辭,請測意之”云,頗類謎語競猜而又含諷喻意味,將《詩》的諷喻精神移入賦體。類似兼含諷喻意味的詠物賦,還有宋玉《風賦》、《釣賦》。是知賦雖“自詩出”,然已“分歧異派”①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詮賦》,第136頁。。同是發揮《詩》的諷喻精神,漢代楚辭批評諸家依經立義,將屈原所作《離騷》諸篇及後學追摹之作,強行納入辭賦範圍而有“屈原賦”之名目;又因主客問答是戰國策士的主流言語方式,而使服習縱橫家語的“陸賈賦”獨標一類;至於《客主賦》等十二種,大都是詠物寫事誇誕之作,因無法歸入前三個賦類,乃彙聚一起而稱為雜賦。
對此情形,班固評曰:“春秋之後,周道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儷閎衍之詞,没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②班固:《漢書·藝文志》,《二十四史》縮印本,第1756頁。同出於周代“六詩”演述賦的源頭,至漢代而分出詩人之賦和辭人之賦,賦體從此走向獨立,因而“與詩畫境”③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詮賦》,第134頁。。前者“麗以則”,後者“麗以淫”;“麗”即語言修飾,是為詩、賦所共有;“則”為遵守法度,“風諭”之義存焉;“淫”為逾越法度,“風諭”之義没焉;賦體既然“没其風諭之義”,便衹剩“侈儷閎衍之詞”了。這就是漢代大賦的體貌性狀,其辭氣之鋪張揚厲長於體物寫事,而相應地短於言志舒情,故與詩分任叙事與抒情。以後詩、賦分途演進,各成體類而邊界分明,以至有“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之斷制④六臣注:《文選》卷一七《文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頁。。
與賦體叙事性增強同步,詩的抒情性也逐漸凸顯。中國詩歌最早的源頭,當可追尋到遠古歌謡;然至晚周時期,則有三個近源。一是經删修的《詩》文本,即文獻形態的“詩三百”;二是士大夫“登高”所賦,即散見於載籍的謳歌嘯詠;三是楚地巫歌及文人擬作,即屈原師徒所創作的楚辭。這三宗詩歌資源都出自“詩亡”之後,是與《春秋》叙事並行的抒情之產物,其情感特質明顯,並獲得當下認知。
《詩》篇章句的情感特質,是在用《詩》場景發掘的。春秋時期斷章取義式的“賦《詩》言志”活動,是建立賦誦者與《詩》篇之間的情感對應關係;孔門創設“不學《詩》無以言”的言語教學科,是開啟《詩》興、觀、群、怨的情感教育功能①參見何晏等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第2525頁中。。這些情感認知不斷培養積累增聚,終至《毛詩序》中獲得理論表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大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第269—270頁。這是“詩言志”説最早的完整表述,標誌著中國詩歌抒情傳統正式確立。
春秋時人“登高能賦”,本為士大夫的素能修養。故班固追述云:“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别賢不肖而觀盛衰焉。”③班固:《漢書·藝文志》,《二十四史》縮印本,第1755—1756頁。不論是賦誦那些脱離樂舞體制的《詩》篇章句,還是像《大隧》、《狐裘》那樣的“詞自己作”,它們都是“睹物興情”,允能“原夫登高之旨”④以上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詮賦》,第136頁。。由此可知,散見於載籍的謳歌嘯詠,容涵士大夫的情感體認。
楚辭是屈原借用楚地民間祭祀歌曲形式而創作的,如《九歌》就是他根據舊曲《九歌》而翻作新聲,有所因襲,又有創新⑤王逸、朱熹都肯定《九歌》是屈原在沅、湘流域民間祭歌基礎上的創作,胡適《讀楚辭》、陸侃如《屈原評傳》則指出《九歌》為楚地宗教舞歌;聞一多《甚麽是九歌》則認為是楚國郊祀的樂章,周勳初《九歌新考》肯定《九歌》為屈原的創作。。屈原創作一系列作品,已有明確的抒情意識。如《惜誦》“惜誦以至愍兮,發憤以抒情”,《抽思》“兹曆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此創作風氣一旦開啟,宋玉《九辯》亦效曰:“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托志於素餐。”對此,劉勰既從宗經角度強調其“取熔《經》旨”,又從情辭表達方面肯定其“自鑄偉辭”:“《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絶豔,難與並能矣。”⑥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辨騷》,第47頁。
以上三宗對詩歌情感特質的認知,不僅終結了情志抒寫的自發狀態,而且凸顯了詩家對情感的節文作用,從而確立了抒情在詩歌中的主體性。早在孔門《詩》的教學中,孔子就告誡弟子“無邪”;“無邪”就是保守《詩》的性情之正,對鄭、衛之音不要往淫邪的方向去想①參見何晏等注,邢昺疏:《論語注疏·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第2461頁下。。嗣後,《荀子·勸學》:“《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毛詩序》:“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止”就是節止於某一點,這在語言表達上即為節文②參見荀況著,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儒效》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33—134頁。。若將節文轉釋為漢魏六朝時期更趨華美的言語修飾,則“詩緣情而綺靡”之“綺靡”就是對抒情的節文。這樣,一方面詩歌明顯具有情感特質,另一面詩家對抒情又有所節止。對此,劉勰總括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③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明詩》,第65頁。
若將大賦與詩歌對照而言,則其叙事與抒情各有消長。賦長於寫物叙事,而短於言志抒情;詩長於言志抒情,而短於寫物叙事。正如劉勰所言:“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④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情采》,第538頁。這就確立了叙事在賦中、抒情在詩中的主體性,從此叙事與抒情便成為大賦和詩歌各自的專長;以後雖因文體的變遷與交疊,叙事與抒情的成分各有消長,但總體上不超出這個基本格局,直到中國文學古典形態的終結。
如果説大賦與詩歌分任叙事與抒情,作為“詩亡”後的一種代償與分化,實現了集體創制向私人創作的轉换⑤參見饒龍隼:《先秦諸子與中國文學》,第53—62頁。;那麽“《春秋》作”局面的出現,作為周代職官制度化寫作之留守,則使史官的集體叙事職能不至失墜。當時各國都有史記之編撰,正如《孟子·離婁下》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事即指春秋爭霸之史事,其文則指對爭霸事之史述,這當然是一種歷史叙事,衹不過仍屬制度化寫作。對孟子的這個稱述,唐劉知幾有解釋曰:“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没無聞者,不可勝載。……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①劉知幾著,王惟儉訓故:《史通訓故》内篇卷一《六家·春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據明萬曆三十九年序刻本影印,第二五四頁下。
但隨著春秋晚期職官制度進一步廢壞,史官的史書撰述職能從官府下移民間,以至出現國史日漸曠缺,而私家競相著史的現象。劉知幾《史通》首篇《六家》論史家流别,其中的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均屬私家著史的範圍,表徵了史學發展趨勢。《春秋》乃孔子依魯國史記而作,《左氏春秋》傳説為左丘明所作,都是私家著史的代表作,傳載了史文叙事之功能。故劉知幾評曰: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説,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②劉知幾著,王惟儉訓故:《史通訓故》内篇卷一《六家·春秋家》,第二五四頁下。
儘管孔子修《春秋》,還能夠遵行舊法遺文;但其義例已有學派傾嚮,甚至加入了個人的意見。如他驚懼弑君、弑父之事頻發,乃在史文中寄託“微言大義”,稱“知我”“罪我”惟在《春秋》,這種自我認知當然有他的評判標準③以上參見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滕文公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第2714頁下。。《左氏春秋》之史述,主要是記事而兼記言,因其行文多有誇飾成分,而被史家奉為叙事典範。如劉知幾贊曰: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穫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叙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①劉知幾著,王惟儉訓故:《史通訓故》外篇卷一六《雜説上·左氏傳二條》,第三八五頁。
這顯然突破了史家實録規範,而流為後世小説之虚構誇誕。此體流蕩以至於戰國時期,出現仿史書之《戰國策》,其實衹是輯録縱橫家語,已入諸子著述的範圍了。至於《虞氏春秋》、《吕氏春秋》、《嚴氏春秋》之類,更衹是假“春秋”之名以著諸子學派一家一得之見;其著史的體例既失,叙事也就無所附麗。直待司馬遷之《史記》出,史文的叙事性纔得以振復。所謂:“《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②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史傳》,第284頁。“述”、“總”、“鋪”、“譜”,是《史記》行文之“古式”;而稱“得事序”,就是得叙事之體。
與史書叙事性昇降變改幾乎同步,諸子著述的叙事因素也有所增長。《漢書·藝文志》所載“諸子十家”,各與周代官制中的某類官守相對應③參見班固《漢書·藝文志》載:“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説家者流,蓋出於稗官”。《二十四史》縮印本,第1728—1745頁。,此即史稱諸子出自王官之説,實指示六藝為諸家所共資取。通觀子書傳世文本與出土文獻,其行文大體是主議論而兼叙事;至於議論中夾雜的叙事因素,則主要呈現為四種文辭片斷:一是人物事蹟,如孔、墨、商、韓之類;二是歷史掌故,如武王伐紂之類;三是寓言故事,如狐假虎威之類;四是神話傳説,如後羿射日之類。這些文辭片斷,或因感生瑞應,或因時代久遠,或因虚飾誇誕,或因洪荒蒙昧,叙事多有不經,均非史家實録,頗類後世小説。即如《文心雕龍·諸子》所云:“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屍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説,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洞虚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弊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兹,況諸子乎。”特别是班固將不能列入“可觀者九家”的衆書目,歸為“街談巷議、道聽塗説者之所造”的小説家,為後世各種小説體式的產生奠定了文獻分類基礎,也為小説確立了虚構誇誕和瑣屑叢雜的叙事特質。六朝的志怪、志異、志人等,唐代的傳奇、變文、詩話等,均為“小説家者流”的變體,彰顯非寫實文學的叙事特性。
總之,中國古典形態文學叙事與抒情之各體消長,是以“詩亡然後《春秋》作”為轉捩點的。這個過程頗為延緩漫長,其時間起點在春秋早期,而截止點在初盛唐時期,大約經歷了1 400年左右。其基本情形,略可描述為:“詩亡”之後,賦與比興分化,賦體文學產生,而與詩歌並行,前者主打叙事,後者主打抒情;“《春秋》作”後,先是史官集體著史,之後私家著史盛行,史文叙事特質變改,由實録漸趨於虚構,催生小説叙事之體。
四、叙事與抒情之功能互滲
劉勰曰:“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①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通變》,第519頁。“體”即文體,包含詩、賦、書、記、誄、史、傳奇、雜劇之類;“數”即文術,包含賦、比、興、抒情、叙事、議論、説明之類。所謂“名理相因”,所謂“有常之體”,若衡以上述叙事與抒情之各體消長,某種文體分任叙事或抒情既有定性;則其界限明確,不至模糊混亂。但語言會歷時變遷,如六朝之駢儷趨偶,唐宋以後的通俗化,作家亦有才性差異;因使“有常之體”也會演化,而不是封閉邊界、固定不變。然文體“有常”,是不變的;而文術“無方”,是可變的。故文變在“數”,而不會在“體”;又因“變文之數無方”,故文術之變有廣闊空間。依循這個文學通變原理,文體與文術是不同位的。叙事與抒情雖可由各體分任,但並不等同於“有常之體”;而是能夠超越特定文體的拘限,在不同文類之間實現功能互滲。
然而近世衡文,易忽略該原理。論者常好將文體與文術混合使用,而有抒情型和叙事型文學之分,抒情型文學大概指詩歌、散文等,叙事型文學大概指小説、戲曲等。抒情是文術,雖主要由詩歌等體分任,但其實並不專屬於詩歌;叙事也一樣,雖主要由小説等體分任,但其實並不專屬於小説。甚至還有一些特殊文學樣式,看似兩種文體的嫁接或糅合,如抒情小賦、人物詩傳、小品文,以及叙事詩、演劇詩、子弟詩等,這與其説是“有常之體”的變例,不如説是叙事與抒情的功能互滲。若説叙事與抒情之各體消長,是為著眼於文體的定性分析;那麽叙事與抒情之功能互滲,就是著眼於文術的定量分析。而對於一篇具體的文學作品來説,若既在體式上作抒、叙定性分析,又在功能上作抒、叙定量分析,那就能更好地探觸兩者的邊界。
至於如何進行抒、叙定量分析,則是一個有待探索的學術命題。比如,可否引入若干較為確定的指數,來創建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模型。其法為:(1)對作品的虚詞、實詞及詞類頻度進行分析統計,(2)對作品的表情字詞、語彙的頻度進行分析統計,(3)對作品的用典、用事和歷史掌故進行分析統計,(4)對作品的風格、趣味和鑒賞體驗進行分析統計,(5)對作品的時間單元、長度和波度進行分析統計,(6)對作品的空間寬度、密度和跨度進行分析統計,(7)對作品的事件長度、幅度和厚度進行分析統計,(8)對作品的人物數量、身份和行動進行分析統計,(9)對作品的名物、意象和場景事態進行分析統計,(10)對作品的直抒、含蓄等抒情方式進行分析統計,(11)對作品的順叙、倒叙等叙事方式進行分析統計,(12)對作品的上述各項或更多的指數進行綜合測評。但建立各項指數及相關理論模型,仍然要以大量的個案積累為基礎,並從個案中歸納普遍適用的條例,而這也是難以在短時間内奏效的。所以抒、叙的定量分析應該嘗試,目的是積累經驗而不必急於求成;當前較為可靠的且能行之有效的辦法,是對叙事、抒情之功能互滲作特徵描述。
通觀各體文學的語言文字表達,以及歷代文學叙事、抒情性狀,叙事與抒情之功能互滲,略有如下可描述的特徵:
(一)詩、賦(文)分任抒情與叙事,但在某些特定的體式或變體中,竟會出現反向功能增強的現象,使詩主叙事而賦(文)主抒情。例如,小賦之作,本以詠物為專能,卻兼擅舒情寫懷①,如張衡《思玄賦》、蔡邕《述行賦》、趙壹《刺世疾邪賦》等;寫人紀事,本是史傳的能事,卻成為詩的主題②,如嵇康《幽憤詩》、韓愈《落齒》等;樂府民歌,本為入樂之詠唱,卻有叙①賦至東漢時期,顯然分為兩支:其一支是大賦,已顯衰落不振跡象;另一支是小賦,頗有後來轉盛之勢。小賦在東漢初年出現,到東漢中期大為盛行,並逐漸取代大賦地位,開魏晉抒情小賦先聲。這類小賦多抒發個人情懷,訴説仕途失意的憤懣情緒,有時也抒寫幽思閑情逸致,甚或對社會政治進行批判。這些作品不再供奉帝王,不再宣言儒家正統思想,而多援引道家之言,情感意緒較為疏放。
②參見饒龍隼:《明代人物詩傳之叙事》,載於《文學評論》2017年第5期,第131—138頁。其文曰:“寫人紀事是歷代詩家常備題材,其作品產量宏富可謂數不勝數;進而兩相結合,或兼寫人和事,或因人紀事,或以事寫人,像這樣的詩歌取材,歷來亦被廣泛沿用。”事之巨製①《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是一篇成熟的叙事詩,其序曰:“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如漢樂府《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北朝民歌《木蘭辭》等;歌行排律,作為長篇的詩體,卻以叙事為擅場,如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長恨歌》等。杜詩“三吏三别”,史家稱之“詩史”;白氏《長恨歌》、《琵琶行》等詩作,有人物、場景、情節及心理等描寫。此類詩作或講述完整人生故事,或截取人生的若干時段和剖面;雖仍合詩之體要,卻有較強叙事性。
(二)詩歌與散文“並”於同一文本,而使抒情與叙事構成互文關係,詩的情思因文之叙事更顯凝練,文的事義因詩之抒情得到昇華。中國古典詩歌作品,詩題之下往往有序;而散文、辭賦作品,往往文末附有詩歌。一般常見的文本狀貌,是詩(文)“并”序;而較少見文“并”詩,更難得見詩“并”詩。前者,詩“并”序②詩序濫觴於漢,形成於魏,六朝以來繼續發展,至唐宋時蔚為大觀。,如曹植《贈白馬王彪并序》,由74字《序》和長篇正文構成;文“并”序,如左思《三都賦序》,由329字《序》和《蜀都賦》、《吴都賦》、《魏都賦》構成。後者,文“并”詩,則有陶淵明《桃花源記并詩》,由321字《記》和32行《詩》構成;唐宋以後還有一種情況,是在碑文之末系以銘詩,用韻語復述碑文内容,并附益諸多評贊之意。還有一些無序的長題詩,直接用長幅題名替代序,交代寫作背景或指涉詩本事,亦具有“并”序的叙事功能③漢魏六朝的詩題較簡古,唐宋以後詩題趨於繁複。有些詩作雖然無序,但詩題的文字很長;其長幅題名類同於序,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如王世貞《封户部大夫次泉李德潤先生其先自關中徙豪衛京師遂為京師人補博士弟子通經術有聲而不獲第有子今儀部君早達以其官封先生不色喜惟杜門讀書繕性而已儀部用直言獲譴先生不色憂旋被召遷今官迎先生養先生亦不色喜其夷然泊然者如故也弇州生聞之曰先生其有道者歟選部魏子曰子以先生有道者則子之言遍天下而乃嗇於有道者何也辭弗獲已為古風一章歌以壽之》,詩題名長達158字,裏面人物關係、生平事蹟、性格修養、創作緣起等項陳述甚詳。。
(三)有些邊緣文類散語、韻語夾雜,詩、詞、賦、散文等諸體兼備,既有詩歌諸體式連帶的抒情性,又有散文、小説連帶的叙事性。唐中期興起、適於説唱的變文,是一種散、韻結合的文學品類,用通俗語言宣講鋪叙佛教義旨,内容有佛經故事、民間傳説等。例如《孟姜女變文》,有叙事、歌詠、祭文;還如《伍子胥變文》,聲辭并茂、情事兼含。唐傳奇是在六朝志怪小説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至中晚唐時期受俗講變文的影響而廣為流行,吸引一批文學名家如元稹、白行簡等參與創作,甚至成為士子科舉應試前展露才情的“温卷”①參見宋趙彦衛《雲麓漫鈔》載:“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温卷,如《幽怪録》、《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傅根清點校,《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35頁。。例如元稹所撰名作《鶯鶯傳》,在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叙述中,為主人公代作《春詞》、《明月三五夜》等詩,還插入時人楊巨源、元稹對崔張愛情的詩贊,既用以抒寫人物心理、情感活動,又因以推動故事情節的深入展開。此種以韻語抒情嵌入散語叙事的手法,還在後世小説、戲曲中得到廣泛運用。如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於紀行中及時著録丘處機詩作;曹雪芹為《紅樓夢》裏的衆多角色擬作詩詞,用以推動故事情節發展和預示人物命運結局。
(四)在人物題詠和寫人紀事基礎上,產生明代人物詩傳這個新品種②參見饒龍隼:《明代人物詩傳之叙事》,載於《文學評論》2017年第5期,第131—138頁。,它不僅提供了新異的文學質素,還拓展了詩歌叙事功能與題材。從質素來看,它是詩體的人物傳記,而非傳統常規的人物題詠;從題材來看,它是專為某個人立傳,而非因人紀事或以事寫人。它有詩歌的基本特性,抒情言志並含蓄凝練;又有傳記的主要特徵,叙事寫實而詳略得體。這樣就會產生互文性意涵,亦即通常所説的話語間性。其話語間性的產生,有兩重理據與來源:(1)從文本内的互文性來看,它既有傳記的叙事特性,又具備詩歌的抒情特性,故為一種混合交融性狀。(2)從文類間的互文性來看,人物詩傳所含話語間性,乃緣於詩與傳記之遇合,而非簡單機械地疊加。正是得益於詩歌與傳記的歷史性遇合,分化了的抒情與叙事功能纔一體交融。
(五)為適應社會各階層的消費需求,元、明、清時期市民通俗文學繁榮,催生了一些特形的長篇叙事詩,因使滲入的叙事功能空前高漲。這些新出的特種形態的長篇叙事詩,有子弟書、演劇詩和女子絶命詩等③傳世的子弟書作品較多,其書編録整理頗具規模。傅惜華編《子弟書總目》,載録子弟書約有400多種;黃仕忠等編纂《子弟書全集》,共收録子弟書520種存目70多種。詠劇詩散見於總集、别集、選集及筆記、劄記、日記中,趙山林《歷代詠劇詩歌選注》選録了646篇歷代詠劇詩作。女性絶命詩盛行於清代,多由當代女性詩人創作。胡文楷著《歷代婦女著作考》,統計從漢至明,共計女詩人有361家,而“清代婦人之集,超軼前代,數逾三千”(參見《歷代婦女著作考·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頁)。如邵梅宜《薄命詞》、姚令則《絶命詞》、何桂枝《悲命詩》、杜小英《絶命詞十首并序》、黃淑華《題壁詩并序》等。。子弟書是清代流行的曲藝形式,因其為八旗子弟所演唱而得名;又因其表演形式主要為清唱,曲詞雅俗有致而又講究韻律,不僅具有俗文學的特質,同時兼具詩化藝術品質①比如啟功稱之為“創造性的新詩”,參見啟功:《創造性的新詩子弟書》,載於《啟功全集》第1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頁;趙景深以為是古今絶美的叙事詩,參見趙景深:《〈子弟書叢鈔〉序》,載於《曲藝叢談》,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頁。。詠劇詩是一種特殊題材的詩歌,早產生於唐代而興盛於元、明、清。元、明、清戲曲表演活動興盛,因使詠劇詩獲得蓬勃發展,並在文人創作中頗有地位,產生數量蔚為可觀的作品。它是以詩歌形式對戲劇的文本及表演、作家及演員、審美與傳播等進行詠歎點評,從中體現詩作者的觀劇體驗、審美情趣、價值取向、文化心理與思想觀念等内涵,行文夾叙夾議,兼有抒情諷頌。清代女性詩人空前劇增,她們創作了一類絶命詩,講述自己生平遭遇,有很強的自傳色彩,或為節殉命,或撫存悼亡,或回顧一生,或感念懷恨,行文情事兼備而盪氣迴腸,有很強的抒情性和叙事性。
基於上述各項考論,可得一個基本認知:叙事與抒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者之間並没有清晰可辨的邊界;但兩者也非始終混合一體,而會歷時變遷、流動變化,大略有同體共生、體制分化、各體消長與功能互滲等進程。今日討論叙事與抒情邊界之命題,固然是出於當下學術語境的需要;然而這並非一時權宜應急之舉,而是命題本身有深入研討價值。學界期待對中國文學的叙事與抒情質素作定性定量分析,但在目前條件下定性分析容或可行而定量分析實難落實;然則當下所能夠做到的,是對兩者進行特徵描述。總之,叙事與抒情並非靜止而截然二分,兩者邊界一直處於流動變化之中;因之要研討探觸其邊界,就需作動態與特徵描述,從中獲取切實有效的理論認知,進而構建中國文學抒、叙傳統。以此衡量陳世驤的“中國文學抒情傳統”説,可知它只是西方霸權學術語境下的應對之辭,而不可執其説來中國文學中按圖索驥,否認與抒情傳統交錯並行的叙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