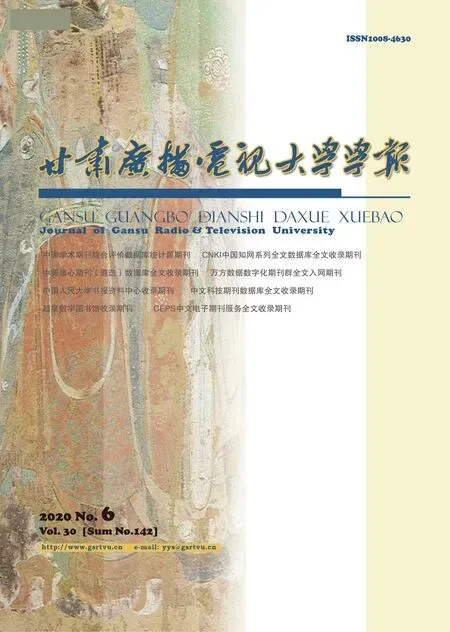从“融梗”嫌疑论电影改编权的边界
2020-03-02陈玲珺
陈玲珺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徐汇 200234)
一、“融梗”的理性之维
IP电影掀起的影视热潮折射出数字时代知识共享的福利之光[1],电影制片方同样也享受着高涨票房带来的成就感。近年来,IP热播影视作品因为版权纠纷引火上身,原著小说著作权保护问题随之备受瞩目。近日,源自小说《少年的你,如此美丽》改编的电影《少年的你》票房丰收,但因为颇具版权争议的原著而引发了一场轰动的IP电影抄袭与否的网络论战。电影《少年的你》与“融梗”这一具有戏谑意味的词语联系在一起,逐渐演变成网民对原著疑似抄袭的一派轰炸,改编电影也背负“连坐之名”。
可以肯定的是,对原著进行改编的电影剧本经过合法授权程序,电影成片也经历了电影摄制许可、备案审查等步骤,并且改编剧本来源——小说《少年的你,如此美丽》也经过版权登记。舆论冷却后发现,电影剧本的版权争议并不明显,使用“融梗”一词评价电影本身未免有失偏颇。“融梗”一词并非专业法律术语,甚至称不上正式的汉语用词,它是数字时代下国民知识产权观敏感性增强的产物。就侵权程度而言,“融梗”是对模仿行为的讥讽,贬义性比借鉴更重,但又够不上“抄袭”的标签[2]。电影剧本的复杂性使电影与小说相比能给观众带来更为直观的感受,但是强烈的感官刺激也模糊了受众对电影剧本与其他版权作品相似度的理性分析能力。“融梗”一词的出现,无不透露着观众对作品似有若无的联想和揣测心理,而电影剧本借助摄制与放映程序实现对原著的多维创作与重塑,使观众难以凭借确切的实体来证实脑海中忽而触动的“第六感”,只能借用戏谑之词表达自己内心的无奈或困惑。受到经验法则影响与知识储备的限制,人们容易将电影与原著版权问题等同视之,直接表现为倘若原著侵权那么改编电影也必然遭受诟病的推理逻辑。两者关系果然如此吗?对于电影改编权的行使还有诸多值得探讨的空间。
二、边界一:电影改编权与原著作权的关系
基于上文已经明确的前提,在原著本身版权问题遭受较多质疑时,基于原著的改编电影能否正本清源?面对第三人的著作权主张,应该如何权衡电影改编权、原著版权与之产生的利益瓜葛?首先要界定“电影侵权”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这是确定电影侵权主体与对象的前提。电影侵权包括以下三种侵权可能:电影剧本抄袭另一部或多部电影剧本、电影剧本抄袭小说、电影成片抄袭另一部或多部电影成片。而电影剧本与电影成片的区别是:电影剧本是文字作品,电影成片则是以多媒体形式展现的可以数字存储的组合作品。《少年的你》引发的争议焦点与电影成片并无直接关联,而应将争议点锚定于原著小说方与第三方之间的版权之争。电影剧本作为打通双方联系的介质,则是解构该争议点的关键。
(一)以信义为基础
电影改编权源于原著作者的授权,授权内容附着于电影改编授权合同,合同生效后即示被授权方取得将原著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权利。电影改编授权合同对许可方和被许可方的权利和义务集中体现在对原著小说版权衍生权的分配关系上。改编权属于著作权的财产权利,因此可以被转让,对于被许可方而言,一旦取得电影改编权,其运用该权利创作的电影剧本就被视为全新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被许可方视为电影剧本的版权所有者。由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许可类型存在差异,并非所有的电影改编授权合同都必然导致原著小说版权和电影剧本版权归属的完全隔离。许可方(甲方)和被许可方(乙方)对电影改编权享有的权利程度视授权合同内容而定。如果合同规定许可方实施专属使用许可,将电影改编权全部转移给被许可方,则许可方(原著作者)将失去对原著的改编权。如果合同约定许可方实施的是独占使用许可,那么许可方也可以享有电影改编权,除了电影改编权外,还可以对原著进行电影以外的其他变式。如果合同约定许可方实施普遍使用许可,那么许可方转移的改编权限度达到最小化,被许可方自由创作的权利则变得十分有限。可以看出,许可力度与被许可方行使电影改编权的自由限度成正比,合同双方对电影改编权的支配受到合同约定的限制,这是电影改编权信义原则的表现。但这绝非意味着行使电影改编权桎梏重重[3]。授权合同的双向保护重在强调授予被许可方突破原作框架体系的独创权利,这就保证电影改编作品既不因授权而完全脱离原著,也能够充分实现当事人双方处分权利、使用权利的意思自由。
(二)原著作权优位
原著小说许可方享有的人身权利具有不可转让性,因此即便做出了绝对转移改编权的决定,被许可人对新作品的创作范围也要受到原著人身权利尤其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限制。电影剧本对原著作出的删减和改动是不可避免的,著作权体现的是私权保护①,改编权作为著作权的一部分可以转让正是著作权私益性质的表现,原著作权人可以自由处分其财产权利[4]。依据民法规定,权利人转让权利时应当保证权利无瑕疵,这一规定也可以适用于著作权领域,目的是为了保证知识成果在传播过程中保持同质性。换句话说,同一传播链条上的权利个体都负有保证著作权及其衍生权利具备安全性的义务。电影改编权的出发点是原著版权,在承认电影改编作品具备独创性的同时,更不可轻视原著版权。随着改编作品的诞生,原著作品蕴含的知识成果也将得到延伸和传播,二者的承继关系不言自明。因此,著作权知识传播过程必须以原著的原初贡献为依托,在平衡原著作权与电影改编权的利益轻重时,应当遵循优先保护原著作权这一顺位。
(三)双重关系原则
著作权具有双重属性,电影版权可以拆分为人身权与电影摄制权、改编权及其他财产权。电影改编权不能简单地视为绝对权或相对权,其与原著作权的关系也不仅限于原权与衍生权的范畴。在内部关系上,电影改编权可以视为原著作权的繁衍,而在外部关系上,电影改编权与原著作权又是相互独立的。电影改编授权合同一旦生效,改编权从原著作权人转移至电影改编权人,电影改编权就此生根发芽,电影剧本将作为原作品受到保护②。从电影授权改编合同当事人关系来看,民法尊重双方地位平等和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即便电影改编权是原著版权的部分转移,但被许可方并不因授权关系而略逊一筹。电影剧本是寄生于原著之下的果实,原著版权正当性存疑时,果实也可能受其感染,而倘若果实成熟落地,“传染病源”即被阻断。因此电影剧本与原著不是一味的连带责任关系,是否连带还需要根据电影剧本的成熟度以及授权改编限度综合判断。
三、边界二:电影改编权与第三人著作权的关系
(一)平等尊重二次创作
电影改编权对应的客体是电影剧本,电影剧本是对小说原著的二次创作,因此尊重原著主旨和精神设定的必要性不言自明。忠实于原著并高于原著的电影剧本会同时为电影和小说双方版权主体带来收益。电影改编权与原著保护作品完整权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授权合同约定足够清晰且完善的情况下,双方相辅相成互利共赢的实现可能性更高。对电影改编权施以平等的尊重是二次创作的基础动力,改编作品与原著具有同等的权利③。改编权的独创性和自动性密不可分,自动性随着独创性工作的完成而产生,而作品的独创性又始终伴随作品版权始末。改编作品的双重性使其权利主体享有完整的版权支配权,这也同样是改编作品独创性的侧面反映[5]。改编权任何一个特性的缺失,改编作品将难以立足。从著作权法第10条第14项改编权的定义可知,独创性作为关键特质,其取得与否直接决定改编作品的未来。改编作品的独创性从实质和形式两方面得到彰显:在实质内容上,改编作品不仅不允许对原著歪曲和篡改,也不允许对第三人作品进行歪曲和篡改;在形式上,改编作品富有全新的表现形式或表达方式,能够给读者带来不同的感官体验[6]。遵循改编作品的独创性原则,既是电影剧本的萌芽之钥,也是电影剧本立足版权空间的关键要素。
(二)公法化的私权回归
电影《少年的你》反映的校园霸凌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电影剧本的公益价值值得被认可,但为了公共利益而偏废另一方私权也是不可取的。防止改编权无度扩张,一方面要做到对原作思想的充分肯定和尊重,另一方面要谨慎创作,避免侵犯第三人版权利益。电影改编权是著作权的组成部分,所以考量改编权边界应当结合著作权性质作为判断依据。当原著面临版权纠纷的考验时,电影改编作品往往难逃干系。电影剧本作为改编权产物,又会衍生出摄制权这种更为复杂的操作权利,电影剧本所反映的内容以摄制的方式被固定在载体之上,数字时代的传播效果将远远超出传统媒体的影响范围[7]。电影剧本内容被更直观和全面地反映在观众面前,最终的电影收益也会经过各个算式与比例精确分摊。一般而言,授权合同里不仅授予改编权,同时还包括摄制权转移,甚至全部著作权的财产权利的转移。脱离原著来考察电影剧本价值,无异于空中楼阁,而原著经过电影剧本的改编,产生的效益也可能远远超出原著带来的效益。原著版权与第三人著作版权都属于私权,两权平等而独立。综上,公权与私权、此私权与彼私权的较量是复杂的[8],作为原著影响力扩张的推动方,电影改编权方极有可能因自发的外部效应加剧对第三人私益边界的挤压,那么最终的结果是第三人版权独创性被大大削弱。应当意识到,依靠原著进行二次创作改编而成的电影剧本是对原著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但也有可能造成第三人利益的二次伤害。无论是原著还是电影剧本,在传播过程中,对第三人版权利益的尊重是必要的。
四、电影改编作品的侵权认定
授权合同不是侵权责任免除的挡箭牌,也不是为改编权滥用行为的避风港。在许多IP影视作品中,制片方和原著方是电影剧本的共同创作者,原著方参与电影剧本改编并参与利润分配,制片方对电影剧本改编来源的筛选和解读更为深入和透彻,因此制片方也承担着相应的原著版权审慎义务[9]。在这样的二重合作创作过程中,制片方和原著方签订的电影改编授权合同采用的是独占许可(排他授权)模式,双方对原作品与二次作品引发的版权纠纷都负担相应的责任。如果采用割裂双方义务范围来认定侵权责任,将不利于保护第三人版权利益。厘清电影改编权侵权要件,加强私权保护,是数字时代规范电影版权业发展的法治要求。在电影改编授权合同订立的情况下,电影剧本与原著之间是否存在版权争议的问题可以由当事人在违约救济或侵权救济方式中自由选择,争议解决不存在太大难度。而对于不存在合同关系的第三方而言,若要起诉电影改编作品只能寻求侵权救济路径,对受害方的举证要求也较高,因此,下文从第三方版权可能遭受电影改编权的角度出发,讨论电影改编作品的侵权要件。
(一)隔离原则
电影版权市场化充分,产品收益容易受到市场影响,电影剧本经过摄制和放映,利益相关者由编剧、电影制片公司扩展至院线方、发行公司、电影院方等企业或集团,发生版权纠纷时,梳理其中的因果关系也变得尤为复杂[10]。
1.跨域因素
隔离原则首先表现在改编权的地域性问题上,改编作品仅在本国享有著作权而对域外不发生效力,然而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外国版权在我国也应当得到同等待遇④。伯尔尼公约与trips协定中均对国际著作权作出了版权保护的规定,外国作者对其创作的外文作品及翻译作品在成员国应当享受同等待遇。授权改编电影《少年的你》被指责与日本作者东野圭吾代表作《嫌疑人×的献身》《白夜行》构成雷同,同时该代表作也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因此在判断改编的电影剧本是否能够阻却违法性时,仍然要秉承尊重的态度理性客观判断外国作品与本国作品的相似程度。电影方和原著方在签订电影合同时都应当负有高度的版权注意义务。影视改编授权合同范本提供了一种约定情形:原著方需要特别保证其提供的作品不存在侵权因素,电影方同样也要做出改编作品对保护原著作品完整性的承诺。至于电影方在改编作品过程中与第三人产生的纠纷,不应牵涉原著方。
2.原著侵权不必然导致改编电影侵权
原著版权、电影改编权、电影摄制权是三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原著版权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项,而电影改编权和电影摄制权分别是著作中财产权利的两项内容,而电影改编权和电影摄制权一般都属于电影改编授权合同的标的,两者不同点在于电影改编权客体是电影剧本,而电影摄制权客体是可以某种方式存储并放映的电影[11]。因此原著版权和电影改编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电影改编权人通过电影改编许可合同取得原著所有的财产权利,那么电影改编权人可以举证证明自己对原著侵权行为不知情而免责,比如根据原著方在合同中提供特别保证,电影改编方有理由相信原著版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如果原著侵权必然导致该改编电影侵权,势必会打压电影产业的发展,给电影从业人员积极性带来消极影响。
3.改编电影侵权不等于原著侵权
电影改编和电影改编权并不是对等概念。电影改编涉及的著作权利不仅有电影改编权还有电影摄制权、放映权等,其蕴含的权利范围要明显比电影改编权宽泛。因此,在讨论改编电影侵权时,不能一概而论为电影改编权侵权(“抄袭”),因为电影作品是综合而复杂的作品,参与主体多元化,组成内容包容性、整合性是十分明显的,因此改编电影侵权需要对侵权对象和侵权方式进行分类,由于本文讨论的核心在于电影改编权,因此由电影摄制权产生的侵权纠纷在此不论。(1)改编电影剧本侵犯第三人小说版权。电影剧本在吸收原著小说的基础上,未经第三人同意挪用或歪曲了第三人的小说内容,此时电影剧本构成对第三人小说版权的侵犯。(2)改编电影剧本侵犯原著版权。经过改编授权许可的电影改编权所有者违背了合同的约定,侵犯了原著作品的完整性,有违原著作者的创作初衷,此时改编电影剧本侵犯原著版权。(3)改编电影剧本侵犯第三人电影版权。这一种情况属于电影剧本“抄袭”电影剧本的表现。
4.主体识别
电影改编权对应的客体是电影剧本,因此电影改编权主体就是电影剧本的作者。其实不然,电影改编权主体准确地说应该是制片公司。因为电影剧本常常是由制片公司委托编剧编写,根据行业惯例,制片公司与编剧签订的委托合同中一般约定,编剧仅取得署名权和报酬权,电影剧本其余的财产权利一并归属于制片公司所有。这样的行业惯例给侵权主体认定带来不便。很显然,电影改编权的主体认定在实践中存在复杂性,根据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所有者一般是作者,作者依作品署名而判定。然而电影剧本版权的署名权和其他财产权利是分属不同主体的,编剧和制片公司分别享有电影剧本的署名权和电影改编权,这与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主体的一般规定相冲突⑤。电影剧本著作权主体就由单一主体变成了多数主体。而就电影改编权而言,编剧虽然是名义上的作者,但实际上改编行为受控于制片公司的委托,一旦改编结束,电影剧本的改编权就转移给制片公司所有,这就导致电影改编权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一旦发生电影剧本侵权纠纷,责任主体应当由编剧担当还是制片公司担当抑或二者共同担当,可以说是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空缺地带,所以在分析电影剧本版权主体时不可以作者一概而论。
(二)行为要件
电影改编权客体是电影剧本,当改编的电影剧本与第三人具有独创性的电影剧本“撞梗”时,法官需要从相似内容字数、占比、表达方式相似度等方面综合判断改编电影剧本是否构成抄袭。实质性相似与巧合撞梗的区别也有可能较为细微,当法官凭借经验无法判断时,专家证人的鉴定意见则显得尤为关键。我国司法实践适用的是传统的“接触+实质性相似”判断原则,只考虑作品的表达方式是否构成抄袭而不问作品思想是否雷同。如果电影内容本身和其他电影内容相似,构成抄袭无疑。如果电影思想与其他电影思想相似,实践中通常不予认定抄袭。如果电影情节、拍摄手法、镜头结构等相似,构成抄袭的可能性较大。如果电影思想主旨截然不同,但是人物情感关联、故事部分情节和其他电影相似,证据需要证明抄袭的相当性。电影改编权既体现了制片公司与原著方基于授权合同产生的约定权利义务关系,又反映了制片公司与编剧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制片公司享有的电影改编权并非法定权利,而是原著版权派生权利的转让以及编剧对电影剧本版权的部分让渡[12]。在合同关系之外,电影制片公司对电影剧本享有绝对排他的财产权利,与第三人创作的电影剧本版权并无而已。在界定电影改编权行使边界时,不能将电影改编权绝对地定义为绝对权或者相对权,而应当将电影改编权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并存的权利。在法官判断电影剧本改编是否逾越权利边界时,一方面,需要考察电影剧本是否超出了原著授权合同的授权意思,另一方面,电影剧本从整体上看如果具有独创性,可以形成对任何人的抗辩[13]。
(三)主观要件
主观要件是认定电影改编权侵犯第三人著作权的要件之一,包括主观恶意和主观过失两种程度。主观恶意表现为电影改编权人被许可对原著进行改编时,明知原著存在权利瑕疵或者已经存在较大舆论争议,仍然与原著方签订电影改编许可合同,或者电影改编权人擅自挪用、篡改第三人享有著作权的电影剧本或小说,混入自己的电影剧本中。主观过失表现为电影改编权人对原著权利瑕疵未尽到注意义务,或者在使用第三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内容时未尽到充分的请求和说明义务,从而构成电影剧本侵权。在判断电影改编权人的主观状态时,以其提供的授权合同中带有授权方特别保证条款作为阻却自身侵权责任的初步证据,还需要判断签订合同时改编权人是否存在主观过失情形,当然这一判断不可经过臆想而得,需要结合客观证据比如改编权人是否履行了对原著版权的审慎了解义务,以及是否存在签订时明知原著存在版权争议或纠纷仍然与之签订合同的行为等综合判定。当改编权人的审慎义务以及注意义务都履行完毕时,可以认定改编权人对原著侵权事实不知情,只要授权合同生效,即可善意取得电影改编权。
(四)结果要件
结果要件是从电影剧本造成的第三人或原著方客观损失数额认定其是否构成侵权的要件之一。由于著作权法没有详尽规定损失数额如何确定,导致侵权责任的确定具有实质障碍。同时,电影剧本版权归属者界定不明,侵权责任主体不明确,就会导致侵权所得或损失所得计算结果有着巨大的差异。编剧与制片公司的收入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如果原著方参与改编电影,则电影剧本版权者构成又更为复杂。受害第三人若要起诉,必须具备初步证据以及证明侵权方造成自身损失数额的证据,前者对于已完成版权登记的第三人而言并无障碍,而后者则需要第三人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并且电影票房收入仅仅是电影剧本产生的收入之一,电影剧本为制片公司、原著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带来的名誉是极为抽象的,被害方要量化这种侵权收入是最为困难的。因此,电影改编权侵权举证责任在分配上表现出不平衡性,正因为如此,被害方往往苦于举证压力而放弃诉讼维权。
五、结语
从电影改编权性质、侵权构成要件两大方面分析电影改编权行使边界,对深入认识电影改编权与原著版权、第三人版权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如何规范电影改编权运作、侵权责任分配,首先要从著作权公益与私益权衡方面进行考量,其次对电影改编权侵权要件的构成进行分析,形成较为具体的侵权认定步骤,初步探索电影改编权纠纷思维路径。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我国电影版权立法的完善措施,比如程序法方面,运用电子技术设定电影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计算公式,拟定将抽象损失转化成数额、等级或比例等可量化指标,完善诉前禁令、借鉴英美国家知识共享组织等专业协会制度,为版权者提供维权的公共服务。
注释:
①《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前言规定:“知识产权属私权。”
②《伯尔尼公约》第十四条之二第一款规定:“在不损害可能已经过改编或翻印的所有作品的版权的情况下,电影作品将作为原作品受到保护。电影作品版权所有者享有原作品作者的权利,包括前一条规定的权利。”
③《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翻译作品、改编作品、改编乐曲以及某件文学或艺术作品的其他改变应得到与原著同等的保护,而不损害原著作者的权利。”
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条规定:“每一成员给予其他成员国民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