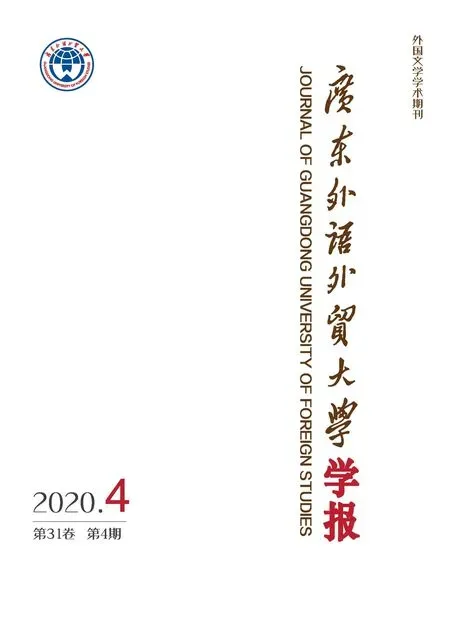德里达后期解构哲学的政治伦理之维
2020-03-02卜杭宾
卜杭宾
引 言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以拆解传统哲学理念而著称于世,广泛应用于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国内对于“解构主义”与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的认识基本达到了一定高度,尤其是《论文字学》(OfGrammatology, 1967)、《书写与差异》(WritingandDifference, 1978)等几部反映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的代表作相继有中译本出版,为国内了解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起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内对德里达的译介仍然集中在对其文学批评思想的宏观把握,对他以及西方当代解构主义思潮的评价过多、过泛。时至今日,国内外学界对德里达其人及其解构哲学依然褒贬不一。实际上,对德里达哲学思想内涵的深入挖掘除了要研究解构主义作为文学批评的最初思想资源之外,德里达后来的政治学转向也应该纳入这个前提下探讨(董迎春,2004:78)。
长期以来,解构主义“文本之外无一物”(il n’y a pas de hors-texte)的观点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封闭在文本内部、无关政治与伦理的虚无主义游戏。然而,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德里达陆续在《友谊政治学》(PoliticsofFriendship, 1997)、《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ofMarx, 1994)、《论世界主义与宽恕》(OnCosmopolitanismandForgiveness,2001)、《恐怖时代的哲学》(PhilosophyinaTimeofTerror,2003)等多部著作中将解构的锋芒直指全球化语境下的诸多时代议题,从高瞻远瞩的独特视角重新审视和批判诸如正义、宽恕、好客、友爱等传统政治学概念。德里达后期对政治的密切关注与他前期的解构思想一脉相承,他本人其实也从未否认过解构与政治的关系:“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是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德里达,1997:21)。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 1983)中多次提及德里达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德里达显然不想仅仅发展一种新的阅读方法:对于他来说,解构最终是一种政治实践,它试图摧毁特定思想体系及其背后的那一整个由种种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形成的系统借以维持自己势力的逻辑”(伊格尔顿,2007:145)。 因此,解构主义绝非纯粹的文本游戏,亦非藐视一切的虚无主义,而是将抽象的哲学思辨蕴于对新时代议题的创见,不断质疑社会政治体制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和文化观念。
在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量难民、移民与劳工涌入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排外舆论甚嚣尘上,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排外法令限制外来移民。当时的法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土的纯正,对外来者实行所谓“宽容的门槛”(threshold of tolerance),“超越了这个界限,要一个民族共同体欢迎任何更多的外国人、移民工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就不合时宜了”(博拉朵莉,2005:132)。一九九七年,法国政府颁布的新移民法对外来者采取更严苛的举措,例如提高军警特权、对扰乱治安的外来者取消居留权等。这些政治动向对德里达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而这与他个人的生平经历密不可分。一九三○年,德里达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受当时整个欧洲反犹氛围的影响,少年德里达常常遭到同学歧视。二战期间,维希政府上台后取消了阿尔及利亚犹太裔的法国公民权,德里达十二岁时被迫辍学。虽然德里达后来返回母国并定居巴黎,但他内心深处始终萦绕着局外人的孤寂之感,德里达对移民在主流社会遭受的排斥与无助感同身受,而全球化进程的新时代诉求也亟须对诸多传统政治、文化、社会议题进行重新阐释与理论建构,这些都为他后期引人注目的政治和伦理转向埋下了伏笔。德里达曾将解构哲学定义为“对不可能之物的某种体验”(Derrida,1992:328),他没有将研究视域禁锢在哲学抽象理论的象牙塔内,而是努力挖掘解构的深层内涵与社会现实和政治议题的内在契合点,因此解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浸润着政治伦理维度的存在经验和生命实践。德里达对“好客伦理”“避难之城”“将临的民主”的阐说,体现了他后期对全球化语境下社会困境和国际政治的洞见,以及他对未来世界政治图景的构想。德里达的解构哲学旨在消解一切封闭自洽的单向度建构,其内蕴的政治伦理责任和人道主义关怀观照个体与异质他者的共存空间,在一种不可能的情境中重构一种可能的生命形态。
好客伦理的吊诡
好客是所有社会礼尚往来的流风遗俗。希腊神话中的阿德蒙特斯虽罹丧妻之痛,仍盛情招待大力士赫尔克勒斯,赫尔克勒斯感激不尽,身赴冥府,救回友妻。《创世纪》中的亚伯拉罕欣然将三个陌生人(上帝和两位天使)请入自家帐篷,饭菜相待。时移境迁,全球化带来的跨国迁徙与人口流动,不断改变着各国的地理、社会与文化景观。如何在全新历史语境下秉承好客之道的应有之义,并将其贯穿于对他者的伦理省思与实践中,成了德里达解构哲学的重要议题之一。
《论好客》(DeL’Hospitalité)①一书透过对列维纳斯的“绝对好客”理论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的层层解构,鞭辟入里地剔析了好客伦理的本质意涵和内在悖论。列维纳斯试图打破同一性,借助他者批判并超越西方本体论的权力传统,寻求一种更能显豁出上帝的伦理意涵、超越存在本质的绝对他者。列维纳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第一哲学的本体论是一种权力哲学”(Levinas,1969:46),而他主张的好客之道是对大写的他者绝对无条件地开放接纳。德里达认为好客问题首先是外人的问题,而列维纳斯倡导“绝对好客”,“要求我开门迎客,不仅对(有名有姓、具有社会地位)的外人开放,也对绝对、未知、无名的他者开放,给他们提供住处,让他们进来,让他们抵达,并在我提供的住处出现,不求他者回报(订约),甚至不问来者名姓”(Derrida,2000:25)。在德里达看来,这种“绝对好客”容易导致主客身份的颠倒,甚至招致不可逆料的后果。由于法文 hospitalité的拉丁文字根hostis兼有主人和客人的双重含义,并与“敌对”(hostile)和“人质”(hostage)同源,德里达据此自创了hostipitalité(hostilité与hospitalité的混合)一词说明主客概念的模糊性与未定性。换言之,主人和客人都可能成为好客的主体,两者在不同条件下相互转换,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人质。因此,在具体的好客行为中,主人可以主动款待客人、为客人提供庇护,同时也有被客人挟制的风险。
德里达以罗得和俄狄浦斯为例,阐明这种关系颠倒的危害。在《圣经》中,索多玛城的暴民要求罗得交出客人,罗得为保客人安全,竟不惜用未嫁的女儿来交换。希腊悲剧《俄狄浦斯在克洛纳斯》中的俄狄浦斯临终前请求忒修斯为他保守葬身之所的秘密,忒修斯允诺照办,即使俄狄浦斯的女儿苦苦哀求,他依然守口如瓶。虽然忒修斯严格遵守“绝对好客”的法则,但也间接剥夺了俄狄浦斯的女儿悼念亡父的权利,最终“所有人都成了死者的人质,从客人开始,他与被嘱托给他的秘密牢牢联系,他必须遵守诺言,结果受制于法规,他甚至还来不及作出选择,这种法规就已落到他头上”(Derrida,2000:107-108)。德里达后来在访谈中多次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一直反对无条件的好客——单纯的好客和来者不拒的好客……无条件的好客是会招致有害结果的”(德里达、卢迪内斯库,2002:76)。列维纳斯提出的“绝对好客”对外人是不经任何质询的,且不附带任何法律、伦理、政治职责和义务,然而这种好客忽略了伦理活动中自我与绝对他者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其中隐匿的接待暴力,因为这些法则是根据家庭独裁者,即父亲、丈夫、老板和房主等“男性中心主义模式”(phallogocentric)制定的。例如,罗得牺牲女儿保全客人的举动本质上是一种性别暴力,而这种将好客法则盲目置于道德和伦理之上的接纳行为同样有道德沦丧之虞,更不可能实现列维纳斯所希冀的公平与正义。
与德里达对列维纳斯“绝对好客”理论的解构类似,德里达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同样持批判态度。在十七、十八世纪全球社会初具雏形的启蒙时代,康德提倡所有国家都应尊重外来者的访视权,并履行对外来者的伦理责任。他在著名的《永久和平论》(PerpetualPeace)一文中主张通过“被奠定在人类的义务之中”的“普遍的(道德-立法的)人类理性”(康德,2005:40),摆脱国家的自然状态,共同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最终迈向全人类的永久和平之路。康德(2005:24)呼吁一种“普遍的友好”,并将友好(好客)定义为“一个陌生者并不会由于自己来到另一个土地上而受到敌视的那种权利”。不过,康德(2005:24)也明确规定了享有此种权利的前提:“人们可以拒绝他,如果这样做不至于使他沦落的话;但是只要他在自己的土地上采取和平态度,就不能敌对他”。虽然列维纳斯和康德都崇尚“普遍好客”(universal hospitality),但是德里达认为康德式好客本质上仍是一种受制于法律的有条件好客。由此为思考起点,德里达透过解构哲学的辩证视域揭示了好客伦理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是无条件的好客法则,即让新来者宾至如归,对他倾囊款待,不问他的姓名,不求任何回报,不附加任何条件;另一方面,好客的诸种规则、权利和义务也是受限制、有条件的,这在康德、黑格尔等人界定的由家庭、公民社会和国家制定的规约中已经显露无遗。在德里达看来,这种由主人过滤和选择受访者的有条件好客一开始就裹挟着权力暴力或法律权力,而且只能通过公民法和国家法的终结才能实现(Derrida,2000:55)。尤其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信息爆炸的数据时代,电话、传真和网络等现代技术在改变好客条件的同时,也导致了国家机器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对私人领域进行各种监控,如电话截听和邮件拦截,而好客的权利也因此无从谈起。
德里达的“好客”论始终陷入一种伦理困境,在有条件与无条件之间徘徊不定,这种不确定性本质上是“绝对”与“相对”之间的永恒悖论,二者互相抵消并以法规的形式判定对方的不合法:绝对好客若不能成为有效、具体、可行的义务与法则,可能会流于乌托邦式的虚幻之物,而有条件的好客也必须以绝对好客为依归,否则容易腐化为一种有偿交涉或被迫接待。虽然德里达的初衷和原旨是努力探寻无条件好客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语境下的可能径路,但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德里达并未给出明确答复。从社会体制的实际情况考量,完全无障碍、无条件地开放国界几乎是一种不可能。不过,好客伦理仍然可以为政治实践提供某种参照与修正,也正因为有了对无条件好客的期待和构想,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摒弃偏见、尊重并悦纳异己,从而不断激活对自我的批判与超越。
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架构
德里达主张的好客蕴含了对他者无限的伦理责任,力主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他者,而这亦是世界主义的本质要义和基本内涵。德里达所关注的世界主义理念并不注重国家联盟,而是立足于好客伦理,孜孜探索一种不框限于国家主权架构的政治模式。一九九六年,德里达在国际作家大会②发表了题为《论世界主义》的演说,将解构哲学的政治伦理维度引入到对世界主义蓝图的摹绘和构想中。德里达一开始就诘问:“今天我们必须要问,我们是否还能合法区分城市(City)和国家(State)这两种大都会形式?”(Derrida,2001:3)“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一词中的polis,其实兼指国家与城市,因此以超越民族、语言和政治界限为宗旨的世界主义的运作载体可以是世界,也可以是城市,而我们似乎忘记了城市曾与国家占有同等重要地位。那么,我们可否寄望于国家政权结构所衍生出的世界主义理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无国籍人士与难民被主权国家拒之门外,连最基本的庇护权都无从保障,这充分暴露了以国家契约为基础的国际法的各种局限。以法国为例,尽管一九四六年的法国宪法和一九五一年的日内瓦协约都制定了相关庇护权法令,但是现实中难民的庇护权依然受到诸多钳制。究其根源,德里达认为主要是法国出于经济利益提供的政治庇护丝毫不考虑伦理和道德法则,而难民所遭受的迫害反而成为主权国家拒绝履行庇护义务的政治借口。与此同时,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利用新型远程科技,对外来者实施严密监控与管治,外来者的人权和庇护权未得到应有的尊重。
鉴于国家机器对个体基本权益的压制、侵害和践踏,德里达认为我们亟须一种迥然不同的政治运作模式,从而瓦解国家主权的单向度宰制。他建议拓展“庇护城市”的现有意涵,即不局限于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庇护,呼吁“一种新的好客宪章”或“避难之城的新世界政治架构”(a new cosmopolitics of the cities of refuge):
无论是普遍意义的外来者、移民、流亡者、遭驱逐者、无国籍人士或是流离失所的人……我们吁请这些新的避难之城重新调整国家的政治导向。我们吁请这些城市转变并革新城市与国家从属关系的形式,因为正在不断发展的欧洲或各种国际法律结构仍然由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规约所主导——一种无形的规约,或者至少是如此,然而现在这种规约岌岌可危、问题百出。(Derrida,2001:4)
德里达不无感慨地指出,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仍由主权国家意识形态主导和操控,康德式世界主义理想离我们还很遥远。德里达提出“避难之城”这种“类城邦”“类国家”的体制,正是将好客伦理纳入对难民问题的现实关怀,从而消解主权国家对世界主义理想构成的重重蔽障和阻碍。
德里达以“避难之城”的城市想象取代旧有的民族共同体观念,并尝试从历史的废墟中挖掘新型世界政治体系的参照坐标。实际上,在西方主权国家尚未成形前的确存在过一些自主独立的城邦,其中包括古希伯来传统和中世纪的避难之城。据旧约《民数记》记载,上帝要求摩西建立六座避难之城,还特别谕令他在约旦河东和迦南地各自分出三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都可以逃到那里。古希伯来传统中的“逃城”与今天“庇护之城”的理念颇为相似,不仅庇佑以色列人,还施恩于逃犯和外邦人,而在中世纪,一些拥有主权的城邦甚至可以单独制定好客法则,任何人无须说出姓名来历,完全来去自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但丁,他因卷入政治斗争被逐出故乡佛罗伦萨,最后避居终老于小城拉文那。在德里达看来,这些避难之城无条件地给予他者“住处、家庭、熟悉的栖身之所”(Derrida,2001:16-17),是对好客伦理本质意涵的切实践行。这些独立于国家主权之外的自由城市形态,正是德里达心目中一种能够打破国家主权魔咒的理想世界主义架构。
德里达以“避难之城”的好客体验为契机,转入对世界主义的深入剖析。世界主义的谱系可上溯至古希腊哲学。犬儒学派哲人狄奥格尼斯曾自称“我是世界公民”。斯多葛派也强调“每个人都居于两个社群,一个是我们出生地的社群,另一个是充满争论和理想的人类社群”,而世界公民的任务是“将所有圈子都导向中心,让全人类都成为同邦人”(Nussbaum,1997:9)。基督教的世界主义理想同样崇尚全人类的和谐平等,例如德里达援引的《以弗所书》中就勾勒了圣保罗向往的世界大同远景:“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Derrida,2001:17-18)。后世对世界主义的最著名阐说当属康德,他主张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所到之处都应享有同等权利,只有互相尊重包容,真正的世界和平才有可能实现:
他可能提出要求的,并不是任何作客权力(为此就需要有一项特殊的慈善契约,使他得以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同居伙伴),而是一种访问权力。这种权利是属于人人都有的,即由于共同占有地球表面的权利而可以参加社会,地球表面作为一个球面是不可能无限地驱散他们的,而是终于必须使他们彼此互相容忍;而且本来就没有任何人有更多的权利可以在地球上的一块地方生存。(康德,2005:24-25)
然而,德里达透过抽丝剥茧的解构式阅读,很快窥察到了康德式世界主义理念的两点局限。第一,在康德对世界主义的阐说中,外来者享有的不是一种长期居住权(right of residence),而是一种拜访权(right of visitation),而且获得长期居住权的前提是两国必须缔结了条约。第二,不论公私,有权自由行走于全世界的个体仍然依靠且受制于法律和国家警力。换言之,如果外来者违背了好客之道,所到国家随时可以诉诸法律和武力将他们制服或驱赶出境。康德式世界主义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德里达所批判的有条件好客,其对外来者居留的规定和限制也未能真正跳脱国家政权架构和既定法律的藩篱。
德里达对西方启蒙运动以降的世界主义思想表示质疑,不懈地探索“如何转化和改进法则,以及如何在历史空间中使这种改进成为可能”(Derrida,2001:22),并且在突破现行好客模式与国家政权束缚的基础上,将避难之城的现实体验视作批判思考的异度空间,呼唤“另一种世界主义理念”,亦即一种超越国家、甚至超越世界主义本身来重新界定政治本质内涵的全新世界政治架构,从而为“将临的民主”(democracy to come)奠定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源泉。
民主的弥撒亚性
纵观德里达好客伦理以及他对世界主义理念的重构,都在昭示解构哲学对同一性的拒绝以及对异质他者的包容,而这又与民主这一核心政治概念存在着紧密关联。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德里达在多部著述中提到“将临的民主”③,而这一关键概念也折射出解构哲学对人类共同体的殷切希望和民主观照。德里达在《友谊的政治》(ThePoliticsofFriendship, 1994)中倡导一种悦纳“无限异质性”的新民主政治,“思考和经历一种政治,一种友爱,一种正义——这种正义一开始就与它们的自然性、它们的同质性、它们可疑的原始场所决裂了。因此,在这种正义开始的地方,开端就(自我)分化和自我区分,通过标明一种‘原始’的异质性而开始;这种异质性已经到来,也可能仅仅在将来降临,将它们敞开”(德里达,2011:138-139)。这种民主政治概念保留了民主自我质询、批评和解构的无限权利,“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解构,没有解构就没有民主……民主是解构的自我规定之中的自动。这种规定和划界不仅以一种调节的观念和一种无限可完善性的名义进行,而且每一次都是在此时此地的独一无二的紧急状态之中进行的”(德里达,2011:139)。
在德里达看来,解构与民主的宗旨若合符节,两者本质上都不断追求与“无限他者”的共生互融,不断暴露封闭结构中的缺口与裂隙。因此,真正的民主永远处于无限增生与延异的“将临”或未来状态,绝非一种僵化不变的既定体制。正如德里达(2011:93-94)所说,“如果说,一方面若不通过专注于这个也许而中断确定性,任何决断(伦理的决断、法律的决断以及政治的决断)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另一方面同一种决断也必须悬置它的可能性条件——这个也许本身”。民主政治不是一种已告完成的在场状态,而是始终在决断与悬置中摆荡,由此孕育出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崭新的经验结构所展现的不确定性与灵活性,是“一种无宗教的弥赛亚主义,甚至是一种‘没有弥撒亚主义的弥撒亚性’(messianicity without messianism),是一种正义和民主的观念”(Derrida,1994:74)。德里达(2006:57-58)指出,“当我在《马克思的幽灵》里面强调弥撒亚性、并和弥撒亚主义相区别时,我是想说明弥撒亚性结构是种普遍的结构。只要你一开始与他者交谈,向未来开放,只要你有等待未来的现世经验,或者等待某人到来,这就是一种开放的经验。某人将到来,现在就要到来。正义与和平都必须与这种他者的到来、这种许诺相关联”。弥撒亚性召唤的是对未来期待的普遍性和不圆满性,一切都等待填充和扩展,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而弥撒亚主义则俨然以一种权威救赎的姿态应许诺言的兑现,企盼一种圆满的终结状态。因此,德里达强调不能简单地将弥撒亚性与弥撒亚主义混为一谈,否则会破坏弥撒亚性的未定性特质,甚至沦为某种原教旨主义。依德里达之见,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都是建立在弥撒亚性这一“没有基础的基础”之上,最终造就了弥撒亚主义(德里达,2006:58),而不是相反的逻辑。
那么这种弥撒亚性是否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呢?德里达的弥撒亚性本质上其实是反乌托邦的,是对形而上学确定性承诺的解构。德里达(2011:505)曾多次解释:“弥撒亚性(我将其视作经验的一种普遍结构,它无法被归结为任何种类的宗教弥撒亚主义)决不是乌托邦性的:它在每一个此地—此时都指向一种不同寻常地真实和具体的时间的到来,也就是说,指向那最不可化约掉的异质的他者。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弥撒亚性的、紧张期待着到来的人/事之事件的忧虑(apprehension)更为‘现实’或‘直接’的了”。弥撒亚性通往的是人类解放的光明之路,如果放弃了对弥撒亚性的追求,也就毫无等待、正义、革命和民主可言了。与此同时,任何民主势必都会有缺陷,因此德里达提醒我们要高度警惕民主是否有“被歪曲为一种威胁的风险”(博拉朵莉,2005:125)。在对民主的无限追求与期许中,“将临的民主”始终是一种充满吊诡的政治构想,将民主的界限和意涵无限延异和拓展,也正因为任何民主都不可能符合民主的概念,民主像幽灵一样游走穿行于未来与当下、不可能与可能之间。
德里达曾在《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ofMarx, 1993)中列举了当今“新世界秩序”的十大祸害:一、失业;二、无家可归的公民被剥夺参与国家民主生活的权利;三、欧洲各国之间无情的经济战争;四、自由市场面对全球市场无力保障国民利益的困境;五、外债和相关机制的恶化;六、军火贸易膨胀;七、核武器扩散;八、种族战争加剧;九、黑手党和贩毒集团势力猖獗;十、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弊端(Derrida,1994:101-105)。由于一种切实有效的民主体制尚未诞生,而现有的“新国际秩序”又弊端尽显,德里达提出了一种颠覆全球资本主义同盟的“新国际”(the New International),这种构想既勾连了无条件好客的世界公民政治学,也为“将临的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践行路径。“新国际”既非“共产国际”,亦非由不同国籍的人联合建立的国际组织,而是一种基于友谊的无组织形式。“新国际”试图克服以主权国家和债务国家为代表的旧世界体制的腐败颓靡,催生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地缘政治的新政治理念。“新国际”所企盼的民主摒弃民族国家的单一框架,从他者伦理学和人类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无条件地尊重、宽容、悦纳各种异质他者,试图在一个更为宏阔异质的开放场域中构筑一种真正的世界主义民主理想。
结 语
德里达(2002:25)曾尖锐地道出今日哲学研究的症结所在:“哲学的任务是不间断地摆脱相对主义的束缚,冲破各种限制,努力跨越民族和地域的限制,以便更广泛地发挥哲学的影响力”。德里达总是激励我们站在哲学的边缘重估一切惯常理念,在质疑与批判中为西方哲学传统与经典注入新鲜血液。他的政治伦理思想不仅是解构哲学的具体实践,也是解构哲学的应有之义,深刻地反映了他针砭社会时弊、反思民主进程的批判视域与人文关怀。好客伦理是对跨国流动背景下外来者接纳问题的积极回应,“避难之城”是对世界主义新政治格局的城市想象,“将临的民主”是对民主弥撒亚性的永恒召唤。诚然,这些充满矛盾辩证的哲学思想在现实施行中困难重重,但是解构哲学对一些问题的剖析也为全球化语境下伦理政治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洞见跌出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德里达提出了“避难之城”的构想,在国际作家协会同仁的努力下,全世界现已成立了三十多个“庇护城市网”(Network of City of Asylum)。解构哲学始终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与希望,其永远在途、绝对敞开的民主本质引导我们希冀一种更加兼容并蓄、自由多元的生存结构。德里达(1997:18)曾反复强调,“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我不知道解构是否是某种东西,但是,如果它是某种东西,那它也是对于存在的一种思考,是对于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因而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权威或本质的权威的讨论,而这样一种讨论或解释不可能简单地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因此,解构哲学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批判的存在哲学,努力消解一切封闭自洽的僵化建构,以流动多元的思考方式观照个体与异质他者的共存空间,从而在不可能的情境中不断寻绎人类社会现实与生存体验的无限可能性。
注释:
①德里达早期虽曾零星论及好客,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才在《友爱的政治学》《别了,列维纳斯》《论好客》和《论世界主义与宽容》等著作中开始密切关注这一议题。
②一九八九年,著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出版了小说《撒旦诗篇》(TheSatanicVerses),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旋即对他下达了追杀令。一九九三年,包括塔哈尔·迪亚乌(Tahar Djaout)在内的多名阿尔及利亚作家遭到恐怖分子暗杀。次年,以拉什迪为代表的三百多名作家联合倡议组建了国际作家协会,从而保障受迫害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
③《另一个航向》《马克思的幽灵》《法的力量》《友爱的政治学》等专著都曾将“将临”与民主、政治等概念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