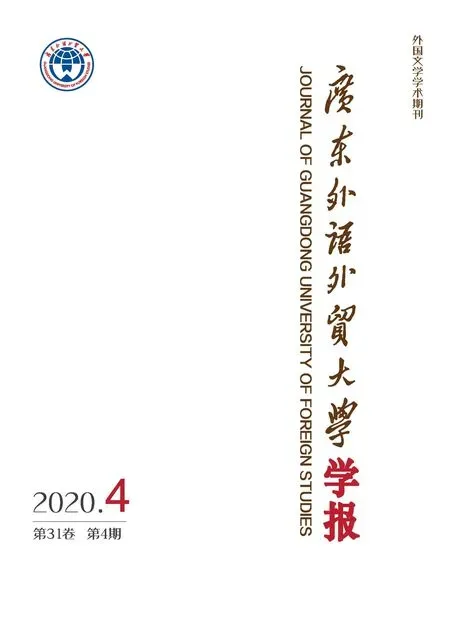远藤周作《沉默》中的耶稣形象塑造与身份认同
2020-03-02兰立亮赵聪
兰立亮 赵聪
引 言
远藤周作(Endo Syusaku,1923-1996)的《沉默》(『沈黙』,1966)讲述了在江户幕府禁止基督教传播并迫害基督教徒这一时代背景下,葡萄牙传教士洛特里哥听到恩师费雷拉在日本变节弃教的消息后,与另外两名葡萄牙传教士潜入日本秘密传教并最终为拯救信徒而放弃信仰的故事。远藤周作通过描写洛特里哥如炼狱般的精神痛苦,立体地展现他个人对基督教的理解,探索基督教在日本的本土化问题。长期以来,关于这部小说的耶稣形象,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国谷纯一郎(1968)探讨了《沉默》中的背叛与救赎的问题以及基督教的本土化问题,认为福音精神与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开山祖师亲鸾法师的“恶人正机说”具有一致性,认为佛的慈悲是拯救恶人的爱,但在基督教中,救赎却是通过耶稣基督自身作为赎罪者承担罪人之罪达成的。在此意义上,“不得不说在形式上弃教的洛特里哥理所当然获得了救赎,甚至连懦弱的叛教者吉次郎也能获得救赎”。玉置邦雄(2002:110)指出,洛特里哥心中的耶稣基督表情的变化暗示着从父性惩戒之神向母性宽容之神的转变,小说“通过流露出无限温柔眼神的母性神的宽容,呈现了日本式感性的克服和基督教本土化的可能性”。笠井秋生(1987:157)分析了基督教的属性,认为小说中耶稣形象的一系列变化,表现了基督形象由“父性宗教的基督”向“母性宗教的基督”的变化过程。江藤淳(2002a:83)考察了远藤周作年幼时由于父母离婚造成的精神创伤与这部小说母性耶稣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指出洛特里哥心中的母性耶稣形象是远藤周作对父性原理支配下的天主教会的反抗。在此意义上,江藤淳将作家所表现的个人思想问题拓展到东洋与西洋或者同日本整个近代相连的问题层面上。兼子盾夫(1996)指出,《沉默》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弱者的义务相矛盾这一框架之中展现了远藤周作对犹大的个人式见解,塑造了连犹大这一叛教者都不会放弃拯救的仁慈的耶稣形象,认为“并不将软弱正当化,而是和信徒一起承受苦难的耶稣才是日本人的耶稣形象”。岩﨑里奈(2014)考察了洛特里哥心目中的耶稣形象变化,指出这一变化源于他在日本传教时亲眼目睹的严酷现实,从这一变化之中,“可以看出欧洲人洛特里哥所持有的基督信仰也因为接触到日本人而不断发生变化”。与以上日本学者研究视点相似,中国学者也将目光投向了《沉默》中的耶稣形象塑造。路邈(2007:44)详细分析了小说中的基督形象描写,指出小说中耶稣形象为“母性基督”,认为“‘母性基督’问题与远藤周作本人的宗教体验及日本人的民族感情倾向有一定联系,主要是民族感情倾向,或者叫做宗教意识”。史军(2013:118)肯定了作者站在日本人立场上理解信仰的态度,认为这一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回归日本本土文化宗教传统”,指出这部小说塑造了站在弱者身边分担痛苦的“母性的耶稣”形象。
不难看出,关于《沉默》的耶稣基督形象研究多集中于母性基督形象以及基督教的日本化等宗教性问题,这些研究对理解小说的思想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大多数研究并未超出将该作视为基督教文学这一框架。《沉默》体现了远藤周作在战后民主主义这一文化语境中对个体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若仅仅停留在宗教问题这一层面,就很容易遮蔽小说本身所呈现的强烈的主体意识。本文尝试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精神分析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分析洛特里哥脑海中的耶稣形象变化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尝试对小说主题进行整体把握,进而将这部小说放在战后民主主义文化语境中进行重新定位。
颠覆与重构:《沉默》对《圣经》耶稣形象的重塑
在小说第一章《薛巴斯强·洛特里哥的书信》中,洛特里哥记述了自己在澳门停留之时对耶稣形象的思考:
他具有怎样一副尊容呢?整本《圣经》都没有记述。您也知道,初期的基督徒们从一个牧羊人的容貌中想到了基督。(中略)随后,东方文化创造出了长着长鼻子、卷头发和黑胡子,带有几分东方色彩的基督形象,进而许多中世纪画家描绘出了充满王者威严的基督容貌①。
可以说,洛特里哥对耶稣基督形象的历史变迁有着明确的认识。他信中提到的背负绵羊的青年神祇形象,是早期基督教艺术中最为广泛采用的牧羊人基督形象,绵羊寓表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主要用来体现耶稣拯救世人的崇高精神。《圣经旧约》对“偶像崇拜”持完全否定态度,因为这关系到何为神圣这一概念,也决定了基督教发展初期耶稣的艺术形象具有高度象征性和实用性,表现了只要信仰耶稣便可得到救赎这一主题。洛特里哥在画作中看到的中世纪画家所描绘的“充满王者威严”的基督形象则是一种庄严的宇宙统治者形象,彰显了中世纪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基督教对基督的信仰体系,正是建立在对异神教偶像崇拜的否定,以及对其崇拜物的毁坏之上;与此同时,基督教在毁坏异神教的偶像崇拜之中,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形象崇拜体系”(汪贤俊,2012)。也就是说,威严的耶稣形象是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根据需要建构的结果。一般说来,耶稣基督的本质特征为“神人二性”,如同福音书所示,既是上帝之子具有完全的神性,也是玛利亚所生之子具有完全的人性,二者共存于一体。不过,中世纪画家擅长对这样的耶稣形象做出为己所用的剪裁,更突出其神性的一面,借此来展现对基督信仰的敬虔之心。但是,在远藤周作笔下的洛特里哥看来,耶稣基督却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如同洛特里哥在圣塞波尔克罗看到的一幅画中圣容。
他的表情英勇而刚劲,(中略)就像男人被恋人的面庞吸引住了一般,我总是被基督的面庞吸引着。(27)
关于洛特里哥在神学院学习时看到的这幅画,我们无法从文本中考证属于何时的作品,但这幅画作的基督表情有别于威严的基督形象,体现了基督之爱这一基督教的精神内核。也就是说,这幅画似乎摒弃了耶稣身上那种神性的超自然元素,进而强调其人性要素,弘扬他传道时的坚定意志以及提比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时嘱托彼得按照神的旨意来牧养信徒的奉献之爱。如果说“英勇而刚劲”代表着耶稣神圣的一面的话,耶稣表情中流露出来的爱则彰显出了人性的一面,从而和传统意义上的神之庄严形象有所不同,体现了对神之绝对权威的解构,在一定意义上似乎更接近福音书对耶稣神人二性的描绘。也就是说,远藤周作用“恋人的面庞”来形容耶稣的容貌,进一步凸显了耶稣基督人性的一面。若按照传统理解进而将“英勇而刚劲”的一面视作父性的一面的话,吸引洛特里哥的那种如同恋人般的爱,毋宁说属于母性的一面。在传统的耶稣形象中,父性和母性这一二元对立的要素不可融合,但在偷渡日本之前的洛特里哥的脑海中,这两种传统意义上不可调和的特征在此得到了统一。
但是,偷渡到日本之后,洛特里哥在传教与寻访的过程中,遭遇了背叛、酷刑以及灵魂的挣扎,开始对基督信仰进行更现实、更深入的思索,最后,他经历了与恩师费雷拉相似的心路历程,在踩踏圣像宣布弃教的同时也拥有自己对信仰的理解和诠释。在劝说洛特里哥为了正在遭受“穴吊”这一酷刑的信徒弃教时,费雷拉告诉洛特里哥自己在传教二十年之后的发现——在日本,我们的神也与挂在蜘蛛网上的蝶并无二致,只有外形和形式看着像神,但已经成了没有实体的尸骸,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向洛特里哥阐明对他人之爱的重要性,认为基督也会为了正遭受酷刑的信徒而弃教。
在教会看来,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弃教始终会成为一个污点。但在费雷拉看来,耶稣走上十字架为世人赎罪,对全人类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爱,这种爱的践行才是最重要的,耶稣也会为了这一目的而弃教。在这一点上,远藤周作通过费雷拉这一人物,表现了超越教会这一共同体的个人宗教理解,这首先表现在他将基督教教义与教会相分离这一认识上。基督教爱的学说在历史上曾是西方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教会却在许多情况下背离了耶稣爱的精神。费雷拉所说的基督教的神在日本已是失去了实体的尸骸,说明耶稣基督已成为一种功能性的关系性存在,也就是说,爱高于一切,基督也会为了爱甚至不惜脱离基督教这一信仰体系。在此意义上,耶稣基督不仅走下了神坛,而且成了与人一起承受苦难的人生的同行者,成了一种实践爱这一美德的功能性存在,其实体被完全消解。小说通过翻译的话阐述了费雷拉的这一认识。
不过,正如刚才忠庵大人所言,编写天文、医术之书,救助病人,也是为他人贡献力量。……在舍己为人这一点上,佛之道、基督教并无二致。重要的是是否行道。泽野大人确实在《显伪录》中也是这么写的。(187-188)
费雷拉改名泽野忠庵,并改信了佛教。在两种信仰体系的碰撞之中,费雷拉认识到爱的践行的重要性,认识到舍弃自我,为他人奉献自己既是耶稣基督牺牲精神的内核,也和佛教普度众生的终极目标高度一致。在费雷拉身上,体现了远藤周作对宗教多元主义的思考,他将耶稣视为关系性的存在,通过对其形象的解构进而凸显了爱的践行这一理念。按照远藤周作这一宗教认识来看,就不难理解他将耶稣形象人格化、结构化本身所具有的世俗性意义。或许可以说,耶稣以自我牺牲成就的至高之爱以及与之相关的人道主义精神对远藤周作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在他笔下,耶稣基督面对世人苦难只是一味地沉默和痛苦,从而将其拯救世人的神性使命悬置了起来,彰显了他为了爱甚至会抛弃一切的精神。这样,《沉默》中的耶稣基督形象显然较少传达出神性的一面,而较多表现出作家对社会、人生和信仰问题的深入思考,具有了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
自我与他者:洛特里哥自我身份认同的确立
小说中,洛特里哥等人要求去日本的动机,是为了调查他们在修道院求学时的恩师费雷拉神父在日本被迫弃教这一传闻的真相。“对佛朗西斯·卡尔倍、赫安提·圣·马太和薛巴斯强·洛特里哥三人来说,若是他们的恩师费雷拉光荣殉教的话倒也罢了,说他像狗一样屈服在异教徒面前这一点,三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10)。也就是说,三人具有坚定的信仰,同时也对自己司祭这一身份充满了焦虑,希望借助到传教条件恶劣的日本传教来实现自我身份认同。“我们司祭就是为人类奉献自己而生的一类人,再没有比无法实现奉献自己的司祭更孤独的人了”(23)。可以说,在洛特里哥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费雷拉的叛教传闻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他心中基督信仰的完美幻像。“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费雷拉在可称得上是世界尽头的一个弹丸小国被迫改信其他宗教这一事实,好像不仅只是一个个体的挫折,还是整个欧洲信仰和思想的屈辱性失败”(9)。在此意义上,费雷拉已经不再是洛特里哥的自我参照的镜子,而是主体被信仰对象异化的开始。另一方面,基督信仰成了洛特里哥反抗日本这一他者场域对其进行规训的精神支柱,信仰所产生的归属感使洛特里哥产生了一种内化式的绝对认同,认为可以从基督信仰之中获得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成功偷渡日本后,洛特里哥脚踏实地开展传教工作,替三十个大人和小孩施洗,听过五十次以上的告解,并在安息日弥撒结束后,第一次用日语在信徒面前祈祷,表现出一副拯救者的姿态,脑海中出现了耶稣基督用仁慈、博爱教化信徒的情景,意识到自己从小时候起就像使恋人的容颜理想化那样无数次地将圣颜紧紧抱在心中。
一般说来,在圣山上传道的耶稣是如同道义一样的理性的象征,这里的耶稣是慰藉者一般的存在,像恋人一样在辗转反侧的深夜中抚慰着洛特里哥的内心。可以说,洛特里哥脑海中的耶稣形象具有圣经依据,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述,在“山上圣训”中,耶稣一方面告知了信徒许多能够安慰人、带给人平安的话语,如“八福”;另一方面,耶稣还讲述了“论发怒”“论奸淫”等关于道德是非问题的严厉而不可妥协的训诫(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6-12)。很明显,洛特里哥此刻脑海中如同恋人般的耶稣形象是经过他主观选择的结果,他将正在传教的自己和人格化的耶稣基督重合在了一起,幻想着自己像耶稣那样在传播福音。对耶稣“美丽的容颜”的迷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本人对自我的迷恋。此时,耶稣作为他者强势占领了主体洛特里哥的位置,使得他无意识地认同于耶稣,并将这个他者当作自我的存在,进而深陷其中而迷失了自我。洛特里哥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可以看作是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所说的婴儿在镜像阶段对自我的误认。拉康将人的心理结构、主体性形成划分为三中毗邻的秩序或领域: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镜像阶段是主体心理发展的最初阶段,处于三种秩序中的想象界。婴儿在六至十八个月时能够利用镜中影像来确认自己的形象,进而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不过,“镜像不过是婴儿在接触社会和进入语言之前的一个‘理想的我’,或者说是虚构的自我”(陆扬,1998:152),从而使婴儿将看见的镜像与自我混同而产生误认。在拉康看来,镜像阶段不仅限于婴儿期,而且贯穿于主体一生,是一个将镜中虚像当作自己,由虚幻而引起迷恋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洛特里哥的自我从一开始就被异化和误认,进而成为一种想象式的镜像存在。从他“像使恋人的容颜理想化那样无数次地将圣颜紧紧抱在心中”这一欲望来看,此时洛特里哥对耶稣的信仰仍然停留在对信仰对象的崇拜狂信和迷恋之中,作为他者的耶稣非但无法帮助他认清自我,完成身份认同,反而成为他主体性形成的巨大威胁。在此,洛特里哥这一主体与耶稣基督这一他者之间为想象界所支配,他将自我异化而与耶稣基督等同,这是他自我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他朝向主体形成迈出了第一步。
为躲避官府追捕在山上躲藏期间,洛特里哥亲眼目睹了茂吉和一藏为了掩护自己而遭受残酷的“水磔”之刑以身殉教,感受到神对人们的悲叹之声置之不理,一直沉默着,透过水洼的倒影,他再次看到了耶稣的脸。与登山施训时高高在上、需仰视才见的耶稣基督不同,这一情形下洛特里哥俯视看到的却是一张“疲惫而眼窝深陷的脸”。他由此联想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美丽而圣洁的面孔,开始摆脱对耶稣基督的迷恋而客观地审视基督形象,进而意识到耶稣那至圣至美的容貌是画家怀着人类一切祈祷和梦想艺术性建构的结果,发现“被追得走投无路的男人那张因为泥水和胡须而脏兮兮,因为不安和疲劳而扭曲的脸”(84)就是他自己。在此,洛特里哥的自我因为怀疑基督的沉默而从他者的束缚中分离了出来,以水为镜所做的滑稽表情,无疑是对自我这一身份发现的再次确认,也为他最后的弃教埋下了伏笔。
在拉康看来,这个世界可以看作是由伦理、规则、语言等一系列外在于世界的他者场域建构起来的。洛特里哥的身份建构过程,体现了拉康意义上以语言、文化、法律为标志的象征界对主体的形塑作用。洛特里哥与当时日本严酷的社会政治环境格格不入,对耶稣基督的沉默产生了怀疑,从而从对信仰对象的迷恋中脱离出来,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如果说洛特里哥刚到日本传教时在想象界通过镜像误认、虚假自恋建立起了拉康意义上的小写的他者——理想自我,那么,此时洛特里哥所发现的自我,就是由象征界和语言所决定的分裂的主体——大写的他者。
被捕后的洛特里哥脑海中的耶稣形象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耶稣基督不再是一副抗拒诱惑、坚定有力的表情,不再是充满威严和荣耀的表情,也不是十字架上忍受痛苦的美丽而圣洁的容颜,而开始用温柔而又看透人之内心的清澈的眼睛一直凝视着这边。在他践踏圣像时,看到那双眼睛痛苦地仰望着自己,诉说着:你最好踩我,最好踩我。我就是为了让你们践踏而存在的。在这种充满爱的目光凝视下,洛特里哥开始能动地思考软弱之人、背叛之人的救赎问题,面对犹大在血田吊死之际,基督尽管祈祷了,但怎么可能会为犹大祈祷呢?这一《圣经》上没有记载,自己也表示怀疑的事件,他最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宽恕了吉次郎的背叛并为之做了真诚的祈祷。
或许神职人员会强烈地指责我这种亵渎的行为吧。但是,我即便背叛了他们,但绝没有背叛那个人,我以与过去不同的形式爱着那个人。我为了理解他的爱,迄今为止所经受的一切都是必要的。现在,我是这个国家最后的天主教司祭。而且,那个人并不是一直沉默着。即便那个人沉默着,我过去的人生也在讲述着那个人。(241)
在此,洛特里哥因为弃教反而坚定了自己的信仰,认识到对耶稣基督的爱可以不必拘泥于某种形式,爱的践行才是基督教这一信仰的本质。在此,耶稣成为具有悲悯情怀的人类的同伴者,成了爱之化身的“那个人”。“为了理解他的爱,迄今为止所经受的一切都是必要的”这句话,就是洛特里哥对自己所遭受的苦难的价值进行重新确认,是对自己信仰道路的肯定。可以说,洛特里哥成功地在象征界中通过与日本当时的社会文化体系建立了联系,通过弃教而获得了客观审视信仰问题的契机,进而可以能动地建构出属于他自己的耶稣形象。与此同时,他也在身份危机中找到了自我理想,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在此意义上,洛特里哥脑海中的耶稣形象变化,成了远藤周作展现小说主人公自我发现的手段。通过描写主人公在异文化背景下为追寻主体性所做出的努力,远藤周作也表达了自己对个体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入思考。
结 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洛特里哥脑海中的耶稣基督形象变化与他对基督教的认识以及他对身份认同的苦苦追寻密不可分。虽然远藤周作将《沉默》的时代背景定位在德川幕府时期,将主人公设置为一名葡萄牙传教士,但他借助这一历史题材,表现了现代人对信仰的思考和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执着追问。江藤淳认为,主人公洛特里哥虽然表达了一些西洋人的看法,但丝毫没有超越日本式的情感结构。“在这一点上,他是与现代日本知识分子完全相像的人物,因此与像是自己不祥的影子那样的吉次郎未必是对立的”(江藤淳,2002b:28)。的确,洛特里哥那充满精神创伤的身份认同之旅与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在主体性追寻过程中产生的挫折感具有一致性。随着二战的结束,被称作“现人神”的昭和天皇通过“玉音放送”发出了人之声,从而走下了神坛,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战后民主主义因打破了那种纵式的权力秩序而成为主流,思想的解放使真正具有主体性的人得以诞生。在远藤周作笔下,高高在上、受人崇拜的耶稣走下了神坛,成了人类的同伴者,成为一种爱的化身的关系性存在。“这部作品并非描述过去的殉教史,实际上展示了以人为中心的近代信仰”(尾西康允,2012)。可以说,作为战后第三新人代表作家的远藤周作明显受到了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影响,因而能够将目光投向历史长河中那些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被边缘化的背叛者,站在具有主体性的个人这一高度上来客观地思考个人的信仰问题,创作出《沉默》这部蕴含着强烈个体意识的小说,将洛特里哥这样一个摆脱了宗教盲信、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现代人形象,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或许在远藤周作看来,宗教问题并非是这部小说要最终表现的主题,而只是一种他表达个体主体性叩问的手段。一般认为,作为一个作家群体,“第三新人作家有意识地将目光从第一次、第二次战后派作家思想政治性上移开,一味地注视着日常世界,通过感性地描绘个人的体验,创造出了独特的文学世界”(万田務,1982:323),但至少从《沉默》这部作品来看,文学史上关于第三新人的这一普遍认识并非完全能够契合远藤周作所有的创作。《沉默》对人主体性的彰显呈现出与战后派作家相似的思想政治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远藤周作对战后派文学的继承。
注释:
①本文《沉默》的引文皆来自远藤周作.1981.《沉默》[M].东京:新潮社.以下此书的引文只标注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