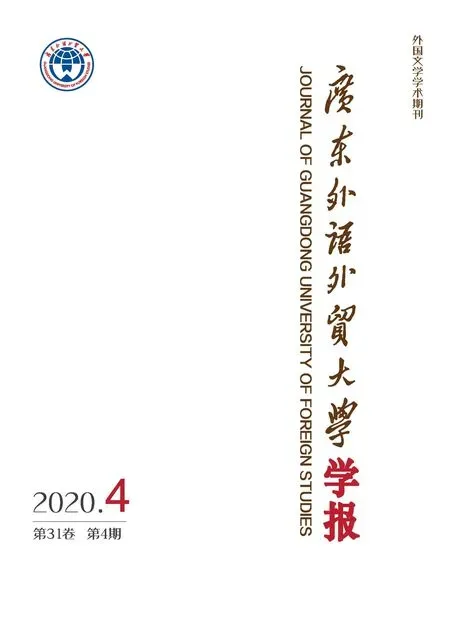渡边淳一《失乐园》的“物哀”绝唱
2020-03-02雷晓敏
雷晓敏
引 言
渡边淳一(Watanabe Junichi,1933-2014)的《失乐园》描写的是一对中年人的情感问题。他们的“不伦之恋”凄美而悲壮。令人感慨的是这样一个悖论,主人公的爱分明是不为世人所接受、也得不到祝福的婚外情,然而其中款曲却让读者过目难忘,以至于无法轻易地说“不”。这个故事里既有真切的现实性,也有人到中年的爱情困惑,故而能够引发万千读者内心的共鸣。有学者从日本的死亡哲学角度解读,也有学者从婚外情的角度分析,还有学者从现代性批判思想的角度,提出反自然倾向以及工具理性倾向的批判。本文尝试以“失”解“失”的方法,即透过弥漫全文的婚外情愫,品味其中 “物哀”的审美观,从而把握作者赋予《失乐园》中的价值取向。
寻觅乐园:婚姻“围城”悖论的文学探求
《失乐园》是一部围绕中年人的婚姻、爱情与婚外情为主题的作品。故事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真实地呈现出来。面对婚姻、家庭与情欲等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与观点。《失乐园》就是渡边淳一的选择,它表达了一种人生的态度,引发了人们对婚姻与爱情的深度思考。作品问世以来,相关评论纷至沓来。截止二○二○年一月,据中国知网数据,已有七十余篇文章见载。这些文章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从日本的死亡哲学角度解读,以杨君的《渡边淳一的异文化——兼论日本文学中的死亡美学》为代表;第二类是从婚外情的角度分析,金蔚的《歧途与拯救——电影〈失乐园〉中婚外情引发的思索》,属于婚恋伦理的评说;第三类是从现代性批判思想的角度切入,侧重对于反自然倾向的关注和工具理性倾向的解析,王思齐的《渡边淳一〈失乐园〉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即这一方面的文章;第四类是关联西方罪感文化的思考,有裘梦楚的《从西方罪感文化的视角看〈失乐园〉中的罪与罚》等等。
中国先秦的礼仪选集《礼记》中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东汉班固等编撰的《白虎通》说:“婚者谓昏时行礼,故曰婚,姻者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现当代,婚姻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元素,它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风俗等众多领域。绝大多数成年人都需要面对婚姻问题。婚姻问题的复杂性与不可预知性,令深陷其中的人备受困扰,因此才有钱钟书的“围城”说。婚姻不仅仅是男女两个人的生理或生活上的结合,它涉及两个家族的联姻。尤其是中年人在婚后会遇到抚养子女的责任与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些都是人到中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人人都期望家庭和谐与事业顺利。然而,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一地鸡毛的琐碎与不堪。在婚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依然有着类型众多的、这样或那样的婚外情。
《失乐园》中男主人公久木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他拥有一份四平八稳的工作、一位温柔贤惠的妻子和在医学院工作的女儿。看似幸福的家庭里暗藏着男主人公对家庭和伴侣的倦怠或失望。女主人公凛子是一位气质优雅的书法教师,她的丈夫是一位医学教授,他们没有儿女。久木与凛子的婚外情,开始于一次偶然的邂逅,他们都是有婚姻的中年人,却如干柴遇上烈火,彼此陷入婚外的感情,沦陷其中无法自拔。他们的“不伦之恋”在精神共鸣和肉体的欢愉中不断升温,但他们不得不面临彼此家庭的束缚和道德的拷问,或曰在情欲与道德的两难中痛苦挣扎。秘密幽会的次数增多,不稳定和不安全感让他们更加渴望光明正大的爱情。
渡边淳一在《失乐园》中展示的是传统道德伦理和人性中情欲之间的矛盾关系。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写作态度也处于矛盾之中,渡边淳一很明显地同情和理解主人公,他认为,肉体交往在人与人之间影响最大。人生无常,因而应该充分享受人生,为了至深的爱不惧违背道德,即便被千夫所指也在所不辞。渡边淳一这个观点可以说继承了本居宣长(Motoori Norinaga, 1731-1801)的“物哀”论。本居宣长在《紫文要领》中认为:“在所有的人情中,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就是男女恋情。在恋情中,最能使人‘物哀’和‘知物哀’的就是悖德的‘不伦之恋’,亦即‘好色’。”他还说:“最能体现人情的,莫过于‘好色’。因而‘好色’者最感人心,也最‘物哀’”(本居宣长,2013:109)。显而易见,《失乐园》的婚外恋在本居宣长的 “物哀”说中见得出理论支点,甚至可以说,“物哀”论本身就是渡边淳一的“乐园”的精神内核。
如果将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仅仅视作唯情论者,也失之简单。作家有其被人物、故事、情节所牵制的真实性涌动的方面,欲望、感情的水深火热推动作家将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诉诸笔墨。变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变。感情的变化才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人是会变的,爱情也是会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关系中的男女,他们之间的爱情与激情被生活琐碎消磨和日常俗事褪色,具体表现就是对于自己的伴侣由厌倦而失去爱意,守住底线者或许能维持“家人”之间的亲情。在婚姻外,若遇到与自己在精神和肉体上都能共鸣的人,“移情别恋”便宛如易燃的电光火石一发而不可收。面对婚外情,人们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来判断。这就是渡边淳一的文学观,或者说是渡边淳一的一种超越伦理的爱情观。这种爱情观通过作者的“乐园”故事,传递给读者,自然毁誉参半。赞同者视之为“一种纯洁的爱情”,反对者则坚持“对爱专有的守护”。
渡边淳一在《失乐园》中,既有继承本居宣长所倡导的“物哀”思想,也有他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具体而言,渡边淳一并非纯粹去宣扬情欲至上。他花费大量笔墨描写已婚男女的婚外情,客观上也唤起人们对现代都市男女、特别是中年男女的生活压力以及婚姻状况的关注。渡边淳一呼吁人们重新审视爱情和婚姻的本质,注重个体生命的精神诉求和人类的本能欲望。如果,我们把渡边淳一的爱情观上升到文学理论的高度,就会发现它确实契合了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其突出的表现是对“性”情节的描写大胆直接,几无遮拦。这也是日本文学自古以来的真实状态。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日本汉学从中国引进的“以理节情”观弃之如敝屣;另一是把欲海浪情推向极端。西学东渐之际,日本文化传统中大尺度的性爱描写,推动了“性解放”的运动,在政治经济等复杂背景下,本居宣长的“物哀”论不但一枝独秀,而且成了日本国学的基调,甚至成了日本彪炳于世界的文学名片。
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描写无疑被“物哀”染色。男女主人公在追求个性解放和性爱自由的过程中,让人看到了当事者受婚姻伦理束缚的悲哀,也披露出了他们内心的虚无和任由欲望横流的“物哀”。前者说明渡边淳一的同情感或曰思想倾向,后者则被包装成了现代的情爱术语。渡边淳一是这样表达的:“在现实生活中,男女恋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而结婚后,共同生活则会使男女双方暴露了彼此的本性。原本相爱的两个人一旦结婚,成为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合法夫妻。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人恋爱时的热情就会逐渐消失,人类原始的欲望会逐渐地荡然无存。社会道德规范的是整个婚姻模式,完全忽略了在这个模式下生活的个人感受,忽略了个体在其中能否得到满足与发展(渡边淳一, 2012:3)。在这里,“物哀”美学的悖论,因婚姻枷锁的束缚而似乎有了新的支点,即婚外情的存在。这确实是现实世界中无法忽视的社会问题。毫无疑问,执于情、困于情者面临着重大考验。选择什么?如何选择?堪称终身大事,一招不慎,甚至会成为生死抉择。正是在婚外情这个节点上,《失乐园》勾起了读者对性欲自由的向往或思考。渡边淳一也正是通过对主人公爱欲形象的塑造和生死关头的去留取舍,再度为“物哀”论的“纵情任欲”观点安放了一子。
选择殉情:逃脱婚姻枷锁的极端了断
每一段凄美的爱情,大致都有如许经历:初始相识时爱欲萌动之甜蜜欣悦;达致高潮时如醉如痴之奋不顾身;结婚数年后爱情钝化之由痒而痛,于是怨偶夫妻要么劳燕分飞,要么形同兄妹,即走向了亲情。这是爱情婚姻关系中司空见惯的三个步骤。那些个悲怆的爱情和婚姻,其发起之时如樱花般绚丽,其枯萎之际则像残雪一样零落成泥。对哲理而言,思想的生活之树与日顽强,即便遭扭曲而依然常青。但是对于爱情和婚姻,世俗的生活之树则随时因剥蚀而叶落凋零,凄然老去。爱情如火之时,往往在创造奇迹;激情燃尽后,终究是要归于平淡,甚至回落到艰苦的日常生活当中。悲怆的爱情与婚姻变数横生,正应了哲学家和宗教观念所说的“此爱无常”。也许只有死亡是个例外,它可以突破无常的铁律……可以让激情在到达顶峰时戛然而止,进入无常之有常,即获得永恒。
叔本华(1986:118)曾说:“对死亡的思考是每一种哲学的源头”。从古到今,中外哲学家都没有停止过对死亡的追问。在西方传统死亡观中,将生与死对立起来,把死看作对个体存在的一种否定。在海德格尔眼中,“死亡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不得不承担起‘去存在’的方式” (马丁·海德格尔, 1987:331) 。 正是由于有死,生命才有了意义——即死亡是一个不断显现自身存在的过程。此在的存在,这个“向终结存在”的过程,不断发现、实现自身存在的意义。
叔本华与海德格尔的这种向死而生的哲学观与渡边淳一对于死亡的态度殊途同归。杨本娟(2011)在《生命诚可贵,死亡亦美丽——论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观》一文中转述,渡边淳一曾说:“一般情况下,人都会认为死是一种悲观的、令人伤感的、消极的事。但是我认为,死是一种强烈的自我表现,是一个人为了能够强烈留下一种印象的方法……”。《失乐园》的男女主人公,他们的爱情轰轰烈烈,因此也期望自己的死也荡气回肠。所以,他们拒绝平庸痛苦的死,而选择了让青春和爱情可以达到永恒的死法。
渡边淳一的这一价值取向,立刻让读者想起本居宣长淡化死亡和凸显爱欲的审美思想。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将色欲和性欲视为无节制涌流的放任之情河。他没有把死亡与“物哀”的深层意蕴开掘出来,而是用泛化爱欲消弭了其中的道德精神,同时也过滤掉死亡对于爱欲乃至淫欲的警示。通读本居宣长的著作,就会明白其“物欲”与“情欲”无度,本质上意味“物哀”无哀。本居宣长援引汉语的“哀”(“安波礼”)字,实际上只给该字一个感叹词的意蕴。在其散文式的行文当中,“物哀”二字组词合用,实际上强调的主要是人的动物性的一面。换个说法,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充斥的是色情物欲,而汉语“哀”字的伦理内涵和情理价值则付之阙如。
平心而论,《失乐园》在这个方面并不完全是“唯欲”论。日本作家的写作,大部分喜欢将故事情节的推演与四季的更替结合起来。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也不例外。渡边淳一从自然之景切入,在爱与婚姻关系的痛苦撕扯中,将人物命运一步步推向绝境。春夏秋冬不再是线性的逻辑,而是被打乱了节奏。故事从秋季开始,从秋到冬,本该是万物衰败的季节,但主人公的感情却是正在浓烈之时;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作者却偏偏安排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危机四伏;到了炎炎盛夏,他们的爱情如同汩汩热浪让人窒息。
小说《失乐园》各章节的题目以“落日”“冬瀑”“落花”等等命名,隐喻久木和凛子的婚外情是一场不被祝福、不被世俗所接受的爱情。尤其是“至福”一章,时值秋天,他们的爱情也如同四季的轮回一样回到了原点,在丰收、欢喜的季节里,两位主人公在轻井泽共赴黄泉。自古以来,爱情臻达婚姻,好的运程和归宿,应是有情人的“有始有终”,即相爱之人的白头到老,忠贞不渝。然而,现实生活里,当爱情如潮水一般褪去之后,婚姻中的男女面临的却是严峻考验,窘境和困境尤其是多数中年夫妻的婚姻状态。若干年的婚姻之痒,由痒而痛,消弭了爱的激情,积累了怨偶的戾气,即便在表面上相敬如宾,内心深处实际上发酵着烦恼和增加着疲惫,好的过渡也许会让双方转入亲情,即俗语所谓“多年的夫妻成兄妹”,司空见惯的常态则是夫妻相互厌倦,于情事麻木不仁。多数中年夫妻大都会“认命”,接受现实,安分守己。《失乐园》中男女主人公却不甘心俗常生活的惯性,他们选择了再爱一次。这种“不伦之恋”让他们陷入疯狂,也陷入了严峻的人生危机:亲人的指责、朋友的疏远、同事的白眼、邻里的讥议,当然还有社会法律的“围栏”和“堤坝”,简言之,男女主人公被周遭的环境所孤立。他们为了彼此间的“物哀”,放弃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来源,抛却了原本颇为稳定的家庭,飞蛾扑火般地投入了爱欲的烈焰,直至走向不归之路。
《失乐园》叙述的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婚外情故事。一般而言,此类作品不会引起许多学者的长久关注与深入地研究。然而,文化界的反应却颇为热烈,这个现象值得思索。《失乐园》引发读者思考的原因是什么?以下三个原因可资关注:一是这部小说具有现实的关怀,它讨论的是人到中年,大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二是它切中人性中“情与理”在婚姻临界状态的两难选择,这也是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纠葛;三是在于作品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即故事不是日本常见爱情文学的温暾泛情,更不是本居宣长“物哀”之“物”而不哀,而是有那么一种剀切的决绝之情爱,虽说“不伦”,但却有一点悲情,物且哀,哀而悲,悲而怆,对于世人而言,多少有一种警示作用。
《失乐园》中男女主人公的经历,可称引人深思的生死恋。渡边淳一是在传达一种人生思考题,或者说他通过这个故事告知世人,男女主人公以肉体的快乐来逃避现实,在感受快感巅峰和爱情幸福时,也要付出道德在肉体中陷落的代价。让巅峰状态的爱情定格,等于打破了爱情向婚姻或者说向稳固家庭运行的定律,促使读者重新审视婚姻人生。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像大多数中年人那样,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婚外情之后,最终回归家庭,这是遗憾;也有人会期望男女主人公在经历婚外激情后,各自归位,重新担负起自己的伦理责任,使踏入歧途的主人公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渡边淳一对故事的处理颇有其不甘平庸的用意。悲剧比喜剧更有震撼力。矛盾交织,情节跌宕,这样的伦理性结果,要比本居宣长的任情纵欲,另有一种心灵反响,至少让人体会到作者写“物哀”之情,而又不局限于“物哀”之物与色的尝试。
《失乐园》之殉情情节,也牵涉到了日本文化中的死亡意识。日本文化深受其地理环境的影响,具有与生俱来的危机感和无常感。“花数樱花,人惟武士”。这则日本谚语集中体现了日本人的樱花情结与武士道精神。樱花盛开时,绚丽多姿,但是花期很短暂。花开时节,日本人举家赏花成为传统盛事,也是日本民族的集体行为之一。同时,日本武士道精神也是日本人的精神底色。日本人“崇尚忠诚死亡”的独特生死观。在日本,剖腹、殉情的古典传统一直是民族精神里的重要内容。杨君(2018)在《渡边淳一的异文化——兼论日本文学中的死亡美学》中转述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观点:“像樱花一样,短暂地盛开又急遽的飘零,似乎象征着这种死亡(自杀)行动是美的、日本式的审美心理。”
再往深远处追溯,日本人的死亡意识也与其民族的亡灵意识有关。根据日本《古事记》记载,人死后埋葬在地下,会通往一个叫“黄泉”的国度,这就是日本的地下世界“黄泉之国”。在日本人眼里,死亡有一种特别的美感。人对于死亡,与其说是害怕,倒不如说带有一种向往。如果做到了“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死就不可怕。用佛教“六世轮回”的教义解释,死是生的另一种形式。也可以说,死是生的延续,从生到死没有绝对的距离,死亡更像是一个温暖的归宿。所以日本文化传统对于死并不畏惧和回避,不仅不避讳,甚至将死看成神圣的事。日本文化的死亡哲学认为死是一种永恒的境界。
渡边淳一的文学创作深受日本文化中生死观的影响。他行医多年,对生老病死见多了,也会增加其对文学人物“死法”的思考。他在小说中流露出的“消极美学”和不甘无常的生死观,成为其作品的一个特色,甚至也可以说,死亡是他的创作母题之一,如《樱花树下》《魂断阿寒》《花逝》《爱的流放地》《泡沫》《无影灯》等。这些作品中,或多或少地都写了一个个凄美而壮烈的死,男女主人公选择了在他们最美好而幸福的巅峰时刻,主动地、有尊严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锐欣(2014:1)在《渡边淳一小说的死亡美学》一文中转述了渡边淳一的一个观点:“一般情况下,人会把死亡看作是疯狂的,或者是悲惨的结局。这是因为人只看到了死得外在,其实,死去的人却是在无比幸福的彼岸世界。无论活着的人如何评判,死去的人皈依了爱的圣殿,在幸福的极致中,走向了永恒的安息”。渡边淳一的小说几乎都以死亡作为结局。死亡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已经达到生命的极致,生命没有上升了,再往下走只有衰落。这种故事情节的设定是渡边淳一死亡美学的特点。“为情而死”,爱情得以升华和永恒;“顶点的死”,是最幸福的境界。这也是作者给此类情爱衰落病症和家庭临界危机所开出的极端处方。在这一点上,渡边淳一清醒地意识到“知物哀”的结局,也可以说是对本居宣长“物哀”的再续。
放纵与节制:《失乐园》的“性爱”启示
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是分割不开的。渡边淳一在《失乐园》中刻画了日本现代社会中的生活百态,从这个角度讲,其作品有现实生活的折光。凛子丈夫的性格,读者可以从凛子的口中得知,他不关心妻子的生活,也不主动与妻子交流,家中宠物猫的生死都激不起他的丝毫关注。这样一个冷漠而清高的人就像是现代社会的一架机器,可有可无。
作者在小说中还描写了一系列为了职位、金钱而压抑自我欲望的各色人等。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心灵空虚而苦闷的人,他们羡慕久木的婚外情,自己又缺乏抗争的勇气,只能每天浑浑噩噩地打发时光,如同行尸走肉,没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与意义。现当代社会的婚姻制度是社会文明的产物。婚姻法既保护了人,也约束着人。在婚姻制度的约束之下,一切出轨的举止,都被视为有悖社会道德伦理的行为。在现代生活当中,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迁导致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人的焦虑与不安全感是人们的婚姻危机的一个社会因素。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对于由此引发的问题格外敏锐。
深入解析,可以体会到《失乐园》正是通过小说人物的婚变,对现当代日本人的性生活有着细致的精神思考。作者更多的是在释放饱受社会现实压抑的性欲戾气和纾解“性变态”心理,可以说,他是在性与死亡之间搭建一座“无常的奈何桥”。做过医生的渡边淳一,在文学中也在诊断世情人性。他以“死”解“性”,以“欲”叩“德”,说到底也是对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宣长“物哀”论的继承和再放飞。
本居宣长(2013:45)在《紫文要领》中认为:“物语的写作就是知物哀,而不是劝善惩恶。”在这一点上,《失乐园》充分发挥了本居宣长的审美追求。作品中的人物失去了道德伦理的自制与监控,读者可从其中辨别出作者对“性”自由所采取的放纵的与美化的笔触,感受得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同情甚至赞赏婚外恋的态度。《失乐园》中女主人公凛子是一位气质优雅、性格倔强的书法教师。她的丈夫是医学教授,他们两个人身份地位对等,在外人眼中,应该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但是“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其实他们的夫妻关系一直很冷漠,甚至可以说是无爱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关系是难以抵抗婚外情感诱惑的。从感情的角度讲,久木和凛子的婚外情是一种追求幸福的表现。但是,如果站在婚姻藩篱和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背叛了彼此间原有的约定俗成,也背离了情理法规给定的既成约束,直接的损害则是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责任。
渡边淳一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婚外恋,也没有把更多一点的同情心倾注于婚外情的直接受害者方面。由此可以说他忽略了倡导节制放纵的文学伦理观,丢失了一个作家应该主动自觉地在情爱与理智、良知道德以及所谓“唯爱唯情”的“超道德”之间发出必不可少的警示信号。在这一点上,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本居宣长“唯情”和任意的“物哀”论。如果说本居宣长的“物哀”论是抛弃了人类基本道德对情欲和性爱的节制,那么渡边淳一笔下的婚外恋形象则更多地让人感受到的是纵爱任欲的“唯情”论倾向。本居宣长在批判汉学道德僵化论的同时,把应该恪守的以理节情的汉学良知完全否定,这就像倾空洗澡水时把澡盆里的婴儿一起倒掉。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也有令人遗憾之处,其笔调向“任性自由”和“爱欲脱缰”的方面飘洒之际,良知婚恋伦理也被淡化,本应给予婚姻人弱者的同情之泪付之阙如。他通过一层层所谓“真爱的”铺排,在爱与死的顶峰处展示幻灭的高度统一之时,留给世人的无非是“超道德”的形象投影。
当然,我们要把思想家、学问家与作家区别对待。本居宣长是前者,是日本非道德唯情说的理论先驱;而渡边淳一是作家,他写的是文学故事,塑造的是艺术形象。他的文学作品虽说让读者感受到其创作倾向流露出的偏颇,但是形象大于思想。换言之,渡边纯一本人也很难给读者划定某种“纯一”。正如栾栋(2017:112)在《文学通化论》中所言,“文学是多面神,是九头怪,是互根草,是星云曲”。作者笔下的文学形象,在读者那里往往会别有意象和另有意味。客观上讲,《失乐园》所述的婚外情,对于读者的启发也是多元的效应。就拿“乐园”意象而言,究竟是指恋爱,抑或婚姻;是婚外恋的赞歌,还是玩火者的自焚,结论恐怕仍然莫衷一是。至少不会是作品主线条画出的一个矢量。纵爱任欲的“唯情”论故事,由婚外恋到以死殉情,完全可能产生多种启发。这部作品不也告诉人们,《失乐园》之所失,毕竟是弃置各方前情的无情,是撕碎两个家庭的无义,是扯裂长久稳定的变异?这一连串的悲怆事件,不仅仅是作家头脑中的风暴,而且也是现实社会中会有的真实。就此而论,《失乐园》不也隐约传达着一个声音:为性爱所驱使,被恋情所困扰的人们啊,要慎重!而这也是这部作品的积极意义之一。渡边淳一是写婚外恋、多边恋和生死恋的老手,他深谙本居宣长的“物哀”唯情唯欲理论。《失乐园》之失,在于作者把“物哀”论的任情观运抵放任自流之极致,也在于作者把“物哀”论的弊端推到了山穷水尽之末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失乐园》称作渡边淳一婚恋小说之浓墨重彩,“物哀”情思之悬崖绝唱。
换个角度看,仅仅用道德去衡量婚外恋是容易流于简单化的判断。一味援引法律维护婚姻的合理性也很难说就一定公正。《失乐园》也给予读者一个很平实的人生教益,那就是要珍惜构成家庭之初爱,呵护激情消退之婚姻。在婚姻生活里的夫妻感情是需要精心培养的,而不是等到出现婚外情,才做诸如放弃、逃避、漠视,甚至出轨之类的举动。对于夫妻来说,学会经营婚姻是会否把婚外情降到最低可能的基本保证。两个人从相识、相恋,到走入婚姻的殿堂是千年的缘分。许多出了问题的婚姻,自然有社会的复杂原因,但是从当事人的方面看,大都有当事人他们不懂得去把夫妻关系作为家去经营的缺憾。结婚并不意味夫妻二人走进了家庭保险箱,爱情加亲情以至融为共同体的那种情分,才是真正的乐园,而且是不易消失的乐园。
结 语
人类需要自由,可也需要自律。男女都有爱欲,而社会少不了约束。文学如何表现这些问题,著名学者聂珍钊(2014: 1)有一个切中肯綮的论断,即“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 这个观点对于思索此类复杂问题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婚姻是社会历史赋予恋情世界的现实规范。在文明演进的正常情况下,婚姻制度是现实生活中最不坏的性爱伦理框架。婚姻是一个悖论,其存在有其合理性,也有其不合理性。伦理选择是调谐这个悖论的社会道德约定。有婚姻存在,就不可避免地有婚外情的出现。在婚姻生活里夫妻双方都需要用心地培养相互之间的那份家的感情。在婚姻外,有社会深水的警戒线和情感烈火的消防器,相关的约束也是不可或缺的情理调谐举措。任性与纵情以至任凭欲望横流,是个体悲剧和社会危机的病灶。婚外恋不但不是解决婚姻“围城”困境的出路,而且是产生悲剧以至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悬崖危象。《失乐园》没有下伦理结论,也没有道德判识,但是其中生动的情节和细腻的描写,客观上展示了一个令读者触目惊心的殉情场景。就这部作品而言,“乐园”之得失映射于婚姻内外,渡边的思绪游移于“物哀”界边。这不仅是作家的笔触在摇曳,而且是日本精神文化在情与理之间躁动,同时也是本居宣长以来“物哀”诗学在这部小说中的深度反响。如何经营婚姻家庭,《失乐园》“以死殉情”的故事发人深思。从这种意义上讲,这部作品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