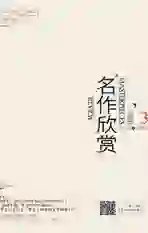战争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分析
2020-03-01汪红
摘 要:《一个人的遭遇》 和《百合花》 分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中“解冻” 和“百家争鸣、百家齐放” 时期的作品。作者不正面描写战争或突出刻画英雄人物,却通过对战争中普通人性人情的美好展示,深切反思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和痛苦,充分展示了苏中战争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关键词:《一個人的遭遇》 《百合花》 战争 人道主义
“文学一产生,人就是文学的主体,文学是人学,人道主义的精神永远闪耀在文学的殿堂上”a。人道主义并不停留在人的外在世界的表象反映,而要深入人的内心,通过人的生存环境、人的灵魂、价值追求等外宇宙和内宇宙的展示,表达出“人间关怀”精神。在战争文学中体现这种关怀精神弥足珍贵。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和茹志鹃的《百合花》这两部作品都没有从血与火的洗礼的角度去描写战争,没有写英雄的运筹帷幄和视死如归,而是将英雄主义的激情转向对于战争本身的冷峻思考。
一、战争文学与人道主义
战争是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最为暴烈的斗争形式。战争文学也多注重描写少数英雄的行为和壮烈、辉煌、鼓舞人心的宏大场面。例如《荷马史诗》中赫克托尔等英雄气吞万里如虎,但荷马却没有将笔触深入到一个普通士兵的悲剧命运和复杂的内心世界。特洛伊战争中无数人的生命如草芥,离开家乡在战场上瞬间灰飞烟灭,普通人不具有个人的自由选择和追求个性、幸福的权利,而仅仅变成了战争中英雄实现其壮志的一个忽略不计的工具。
这种战争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作品中具有普遍性。例如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1943—1944)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也都过分注重描写战争事件本身而没能挖掘战争中人的意义。而在中国,英雄人物多是古代“圣贤人格”的延续,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战争文学多采用“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突出敌我矛盾,塑造鲜明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抽象革命观念的宣泄在一定程度上也远离了艺术与生活的真实。
横跨整个20世纪的极权灾难使千百万人在战争中送命,两次世界大战束后人们开始在强权中喘息。随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和赫鲁晓夫当政,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掀起了人道主义浪潮。1955年苏联文学界有人撰文:“人道主义作为过去时代伟大活动家传给苏联艺术家的接力棒,现在仍然是文学的主要内涵,它获得了原则上区别于过去的新特点。”b在19世纪俄国作家中,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都在呼唤“人类的尊严”“博爱的世界”,但在“解冻”时期人道主义具体地宣扬“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关心人”“相信人”“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等精神,要求各种题材的文学体现“个人的自我价值”“尊重人、爱护人”等人道主义成分。例如巴兰克诺夫的《永远十九岁》《一寸土》、西蒙洛夫的《生者与死者》、贝科夫的《第三颗信号弹》等作品通过“小人物”在战争中的遭遇和命运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要求。
由于政治图式的相似,中共中央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巴人在《论人情》中指出:“文学创作必须有人人相通的东西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情,也就是出于人类共同本性的人道主义。”c由此出现了一大批描写人情、体现人道主义的作品,如《青春之歌》《红岩》《万水千山》《铁道游击队》《苦菜花》《上甘岭》《三千里江山》等,有描写解放前的地下斗争和农村暴动,有描写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描写抗美援朝战争,但作品的主角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真正个性的人。
由此看来,关注普通人、贴近生活真实、“文学干预生活”就成了苏中战争文学中人道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和茹志鹃的《百合花》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从英雄主义和建树功勋的激情转移到平凡世界。《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于1957年,又译为《人的命运》,以苏联卫国战争为背景,主人公索科洛夫出身贫寒, 受尽生活的熬煎,好不容易建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法西斯侵略战争爆发后他上前线保卫祖国;之后他受伤被俘,受尽种种磨难;最终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回祖国。可是战争使他家破人亡,后收养了一个战争孤儿彼此相依为命, 索科洛夫坚强地开始了新的生活。短篇小说就写了一个普通公民在卫国战争中极其悲惨的遭遇, 从“苦难—幸福—战争—苦难—希望”中真实地再现了千百万人的战争经历以及他们在平凡中的伟大精神。《百合花》发表于1958年,以解放战争为背景,与《一个人的遭遇》一样不再突出黑色夜幕,而是以夜幕上的一颗并不耀眼的星星为描写对象。作者笔下的小通讯员不是一个坚忍不拔、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形象,而是走下神坛的一个高大英俊、招人喜欢的小伙子。综观全文,这是一个对革命忠诚但又具有丰富生活情感、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正如评论者所说: 《一个人的遭遇》“既是最早地、深刻全面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大力推崇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又是以一个新的角度来反映战争,从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d。如茅盾评《百合花》:“一如静夜的箫声,初读似觉平凡,再读则从平凡处显不平凡了,三读以后则觉得深刻”e。两部作品都从普通人的角度对战争题材进行注解与阐释,是“一切为了人”的人道主义的反映。
二、凡人的美好性情
肖洛霍夫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不遗余力的人性跟踪对整个俄罗斯文学中人道主义的提升具有前所未有的开创性意义”f。茹志鹃继承并发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是人学”的传统。两部作品饱蘸深情地挖掘普通人的美好性情,为“人的回归”提供了理论与创作的渊源及素养。
《一个人的遭遇》以故事套故事的方式,以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直接引语中主人公的声音道出了索科洛夫真挚感人的内心世界。“对我来说,天下没有比她更好更漂亮更称心的人了,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孩子们也叫人高兴:三个人学习成绩都是‘优,儿子阿纳托利对数学特别有才能,连中央报纸都提到过他”。g几句简单的语言却写尽了一个从无亲无故、孤苦伶仃中走出来的青年男子对幸福的感受和满足。而战争爆发他积极参军表现了他高尚的精神,被俘后在难堪的重负下不仅保持了俄罗斯人的人格,而且以大无畏的勇气为苏军的战略推进提供了重要情报;当自己一无所有,他仍然饱含着爱与希望收养孤儿继续向生活和命运挑战。小通讯员与索科洛夫一样热爱自己原本贫寒的生活,但当祖国需要他时义无反顾在战争中献出生命。两位主人公都是平凡、质朴、勇敢而坚毅的人。《百合花》以叙述者“我”展示了小通讯员的个性,“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有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h描写了他的憨厚平凡、羞涩、腼腆。小通讯员枪筒上插着树枝和菊花,通过武器和树枝、菊花的组合又写出他热爱生活和青春的朝气;通过借被子展示了他“执拗”“任性”与活泼,而最后小通讯员勇救担架员则完成了对一个平凡而崇高人物的建构。
两部作品通过主人公自己的语言和行动,通过叙述者的口吻真切地向读者展示了这些普通人的性情,他们眷恋着自己的幸福,有着大无畏的精神。他们并不是生下来就是战争的工具,这些平凡人有着不平凡的精神,他们更爱平凡的生活。肖洛霍夫和茹志鹃撷取战争河流的一朵浪花,印证了“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一个普通卑微之人的生命得到体现,并在文学作品中发出璀璨的光芒,这是苏中“一切人都是兄弟”“泛爱众而亲仁”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进步的体现。
三、战争的深切反思
作为人道主义精神,不仅要体现人,将大众作为聚焦对象,肯定人的生命世界,而且在肯定的同时需要反思造成人灾难和死亡的战争。《一个人的遭遇》和《百合花》通过反思战争表达作者对战争的感受和对历史的深沉思考。
《一个人的遭遇》中以苦难写痛恨,主人公丢下幸福投入到战争中,而战争后这个满腹酸楚、度日艰难、无家可归的“英雄公民”除了命运相近的战友和相濡以沫的孤儿外,国家和人民没有给他幸福。他无意中撞倒一头牛,交通警便没收了他的驾驶证,夺取了他唯一的生存之本,对他的苦苦哀求也并没有给予任何同情、怜悯。这不是一个国家、民族、阶级甚至集体的遭遇,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俄罗斯人在卫国战争中的悲惨遭遇。他永远失去了妻子和孩子,勇敢的气质和爱国心却换来凄惨的流浪生活。《百合花》中以美反衬恨,作品中出现一幕幕在战场形态下富有生活气息的感人画面:地里的庄稼、中秋的月饼……一切流露出作者内心深处对田园牧歌似的和平生活的记忆与向往。作者也没有正面写残酷的战争场面,却通过人物之间内心情感的交流与碰撞,塑造了几位纯真质朴、优美动人的人物形象。小通讯员年轻又热爱生活,新媳妇漂亮善良,结局确是年轻生命的死亡。“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i。这几个动作的描写恰如其分地写出了新媳妇的哀痛,眼看着一个纯朴可爱、对一切充满激情的年轻生命的消逝,在沉痛而残酷的事实面前,读者连同新媳妇的感情在瞬间得到深化——哪怕是带着革命神圣光环的战争,都必然导致成千上万鲜活生命的牺牲。
两个主人公都是为国家和人民而战,从整个国家体系来说,注重个人对国家的贡献,“个人不过是一部巨大生产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个人完全被视为随时可以更换的零件。人性的因素只有在有利于集體的情况下才被照顾和考虑”j。个人幸福相对于国家来说轻如鸿毛,然而两位作者却没有一味突出人民对战争的积极、勇敢、无私,把人写成是“历史的燃料”“螺丝钉”,却让读者看到人在战争中的苦难和死亡。从索科洛夫这个普通士兵在战前、战中、战后的痛苦经历,从“我”眼中小通讯员美好生命的死亡和新媳妇的悲哀,传达了作者的思考,即任何战争的胜利和失败都是灾难和死亡的集中表现。
战国时期的墨子有言:“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天下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古老的声音表达了世间人的渴望。索科洛夫收养了孤儿,新媳妇为通讯员盖上百合花被子,这一切构成了两部并不相连的作品的共同旋律——爱的颂歌,表达了两位作者面对战争寄托了墨子一样反对战争和“相爱”的希望。
两部作品不以高姿态来俯视战争,而是贴近人情、人性来投射战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没有超群的战功,没有豪言壮语,但其行为却显露出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体现出两位作者对战争中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对特殊状态下人性的理解。通过爱与恨的流露,两部作品真正实践着“文学是人学”的艺术主张,在苏中文学史上架起了一座五彩斑斓的彩虹之桥,使文学的优良传统得以源远流长。
a 李炎:《多棱镜下的文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b 钱善行:《当代苏联小说的嬗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c 转引自邵伯周:《人道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d 谭得伶、吴泽霖:《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ehi许道明、朱华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序选》(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第220页,第226页。
f 王丽丹:《乍暖还寒时——“解冻”时期苏联小说的核心主题和文体特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g 〔苏〕 米·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草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j 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1页。
作 者: 汪红,普洱学院政法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