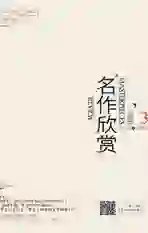论布莱希特《三毛钱小说》
2020-03-01何玉蔚
摘 要: 撒旦(恶)本应潜藏于黑暗中,停留在人的无意识领域,但它却走到了阳光下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令人陌生而又熟悉的事物令人感到恐惧。恐惧是对某种本应隐蔽起来却显露出来的东西的心理反应,从创作理念上说,这正是布莱希特倡导的“陌生化效果”。他把《三毛钱小说》写成一部散文形式的《恶之花》,因为布莱希特意识到,比起善来说,破坏性的恶更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
关键词:撒旦 本我 恐惧 陌生化
作为20世纪德国最具震撼力的剧作家、诗人、导演和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创立和发展的“史诗戏剧”以及“陌生化效果”,不仅给现代剧坛注入了蓬勃生机,也是对西方传统戏剧的一次颠覆性突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布莱希特置小说创作于次要地位。
早在 20世纪 20年代,布莱希特就考虑过创作长篇小说,1920年7月1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有很多想法……还有很多关于如何写小说的认识,这些认识之所以引人入胜,因为它足以置因为(所有其他)小说而早已存在的传统以死地。”a应该说《三毛钱小说》 就是一部充分体现布莱希特对小说想法的作品,同时也是布莱希特计划创作的数部长篇小说中唯一完成的一部,在世界文坛上有“德国最重要的流亡作品”和“德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渊博的讽刺小说” 之称。
《三毛钱小说》 是布莱希特在1933年至1934年流亡丹麦期间完成的,这是一部 “反向改编” 的作品。b1928年,布莱希特把英国剧作家约翰·盖伊的《乞丐歌剧》改编成《三毛钱歌剧》,这个剧作给他带来国际声誉,也是他史诗戏剧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而《三毛钱小说》又改编自《三毛钱歌剧》,这样说来, 《三毛钱小说》不仅是一次“反向改编”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双重改编”之作。
《三毛钱小说》虽然改编自《三毛钱歌剧》,借用了后者的主要人物与情节,与后者存在着一种坚定的互文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读《三毛钱小说》之前读者要先去剧院看《三毛钱歌剧》,或者要先去读《三毛钱歌剧》的剧本。实际上《三毛钱小说》就是一部地地道道、如假包换的小说,它与其他小说并无二致,如果说有的话,那是因为布莱希特是一位善于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加上他对小说的独到思考,使《三毛钱小说》展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奇妙恶世界,让人感到既惊心动魄却又魅力无穷。
布莱希特把《三毛钱小说》的背景放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国伦敦,主人公皮丘姆表面上是一家出售旧乐器的商店老板,实则是伦敦丐帮的帮主。他像任何一位资本家一样进行剥削,只不过他剥削的对象是乞丐,他是伦敦行乞行业的垄断资本家;与他产生交集的是一位绰号“尖刀” 的麦奇思先生,他是一系列廉价品商店的老板,这种商店以大甩卖的价格抛售商品,商品价格十分低廉,因为它们全部都是偷来的,麦奇思可以说是盗窃行业的垄断者,他把伦敦的全部盗贼都变成了他手下的雇员。麦奇思偷娶皮丘姆的女儿波莉,婚宴上警察总督布朗竟然前来道喜,原来麦奇思和布朗是铁哥们,强盗和警察是一家。丐帮和强盗本来就不和,于是皮丘姆去告发麦奇思,紧要关头警察头目布朗帮助麦奇思,使他摇身一变成为“银行家”,随后麦奇思又同皮丘姆沆瀣一气,合伙对伦敦民众为非作歹。小说的结尾是受剥削压迫最重的退伍伤残士兵费康比被判处死刑并被绞死。行刑时,一大堆小业主、缝纫女工、伤兵和乞丐在场,大家无不拍手称快。读者读到这里不禁毛骨悚然,正如评论家所言:“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更凄惨、更无指望的结局了。”c
德国文艺理论家施勒格尔认为:“如果在一部长篇小说里,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塑造并阐明了一个全新的性格,那么即便依照最寻常的看法,也足以使这部小说出名。”d应该说,布莱希特在《三毛钱小说》中就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性格——撒旦式性格,而这种撒旦式性格却又散发着奇妙的恶的魅力。比如丐帮帮主皮丘姆,他不应被看成是通常模式的吝啬鬼,他是个恶棍,这毫无疑问,他的罪行在于他的世界观;“变坏是根本没有止境的。这是皮丘姆深信不疑的,也是他唯一的信念”e。既然他有这样的信念,他做起事情来完全没有底线,为所欲为。他把自己的女儿波莉当作资本,把她推到一个令人作呕的色鬼的床上,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女儿也如同《圣经》一样,只不过是给他提供帮助的渠道罢了;他在把女婿麦奇思送上绞刑架之前,把他当作空气,从不看他一眼,因为皮丘姆想象不出有任何一种个人的价值能吸引他对这个夺走他女儿的人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尖刀”麦奇思及其罪行之所以使他感兴趣,是因为他可以假借这些罪行杀人。而书中另一位撒旦式人物威廉·科克斯,他作为一名经纪人,却勾结政府要员弄虚作假,绞尽脑汁地把货真价实的“水上棺材” 伪装成舒适豪华的游艇,把几艘破烂不堪的旧船卖给国家充当运兵船,结果使满船官兵全都命丧海底,因为作为把赚钱当作自己生活内容的科克斯与其商业伙伴都深深意识到:“这种盯人的竞争真可怕!不管什么卑鄙的生意,只要你不干,马上就会有其他人来干。一个人不得不忍受很多事。你如果感情冲动,即使只有一秒钟,那你就全完了。只有铁的纪律和自我克制才能成功。”f《三毛钱小说》中充斥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撒旦式人物,充满着畸形、暴戾、黑暗,令人触目惊心、脊背发凉,读者读后“与其说感到厌恶,还不如说感到悚惧”g。
但这又有什么新奇之处呢?在此之前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就充满着长长的一大串穷凶極恶、光怪陆离、满身血污的大资产阶级身影,把人吓得胆战心惊,《人间喜剧》的主导方面不是肯定与颂扬,而是批判与否定,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丑恶得到了痛快淋漓的表现。马克思就曾经说巴尔扎克写的是“杀人、通奸、诈骗和侵占遗产”的人的历史,尽管如此,巴尔扎克毕竟还对《人间喜剧》中的贵族寄予深深的同情,为他们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这一方面说明了巴尔扎克头脑中残留着贵族观念;另一方面,从深层象征意义上看,巴尔扎克笔下的贵族形象,又是人欲横流时代人的理性与善的象征,寄予了巴尔扎克对人性复归的希望。布莱希特与巴尔扎克的不同在于《三毛钱小说》中没有正面人物形象,当然更谈不上通过正面人物形象寄托作家对人性复归的希望。布莱希特笔下的世界是鬼魅的世界;在这里,人脱去了虚假的道德外衣,赤裸裸地走向读者,他们不再高贵,不再优雅,而变得自私、凶残、专横,一切人性之恶都表现出来,就是人们最心仪的男欢女爱,也变成了金钱魔鬼式的爱情;爱情不再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而是暴露他们身上的恶的化学试剂。 “尖刀” 麦奇思认为“女人委身于一个男人,责任自负,风险自负。他完全反对给女人规定条条框框。爱情不是养老保险”h。他在心里是这样反思自己对波莉的感情的:“同一个姑娘结婚,是看中她的钱还是看中她的人,这样自问是完全错误的。两者常常兼而有之。一个姑娘家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像一笔财产那样激发一个男人的热情。她没有财产,我当然也会想要得到她,但是或许不会这样热烈。”i而当波莉奉父亲之命来诱惑科克斯,在科克斯的写字桌上看到一枚她估价大约为二十英镑的胸针时,在她的想象中这枚胸针便与科克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内心进行着对各种亲密接触行为的价格计算:“超过接吻是完全不可能的,至多他可以搂抱我。这对那枚胸针来说并不多。”j
在《三毛钱小说》中,不仅爱情丧失了使人们的生活充满温柔和芳香的能力,就连悬壶济世的医生也道貌岸然起来,暗地里“大刀阔斧”地为人非法堕胎,表面上却冠冕堂皇地大谈宗教和道德的神圣、官方禁令、职业良心等,他对前来找他做堕胎的波莉这样说道:“您向我提出的是何种非分要求?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且不说这方面有公安条例。医生要是做您想的那种事,就会失去自己的诊所,而且还要进班房……这毕竟是非法手术,即使为了患者的利益而不用麻醉药,也得要十五英镑,而且要先付,免得事后翻脸不认人……亲爱的小姐,腹中的胎儿就像其他生命一样神圣……星期六下午我有门诊……还有,您把钱带来,不然您就根本不必再来了……”k正如评论家所言:“对混乱不堪的世界中那种混乱不堪的人际关系进行如此冷酷刻画的,除了布莱希特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人了。”l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18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自传》被誉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经典文学作品,他用自己的经历回答“人如何生活”这个大难题,自传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他为自己制定的达到完美品德的十三种德行计划。可以说,道德的自我完善是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孜孜以求的人生境界。布莱希特在《三毛钱小说》中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人如何生活”这个天字号第一大难题,书中这样写道:“人究竟靠什么活?靠每时每刻折磨、掠夺、袭击、扼杀、吞噬人!只有完全忘掉自己是人,人才能活。先生们,休要自作聪明,人只有靠作恶才能活!”m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和动物一样,人类主要的和根本的推动力是自私的,也就是对自己生存和舒适的追求。但不要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人类同所有其他动物有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人类建立了道德的体系,试图以此约束其自私的天性,因此,如果以盗窃、抢劫或杀人来作为获得资源的手段就会受到道德规则的约束,他能够凭良心觉得自己所做的违背道德的事很不好,产生负疚感。吃掉了羚羊以后,狮子就已经满足了,事情仅止于此。人也需要美餐,但对人来说仅有美餐是远远不够的。毕竟,人类生活中确实存在一种无论如何也要捍卫的超越一切的价值,虽然,一旦涉及细节问题,涉及具体的情况,人们的思想和道德情感就开始发生分裂。但是另一方面,恶也与我们息息相关,恶与我们如影随形,魔鬼、女巫、吸血鬼,等等,等等,他们虽是文化虚构出来的产物,但人們正是用它们形象地对恶进行描绘,这一类恶形恶状的事物教育我应该感到害怕,同时也召唤我们与之交锋。
从某种角度上说,基督教完全清楚来自恶的这一方面的长期诱惑,甚至耶稣都受到过魔鬼的诱惑,魔鬼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并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具体参见《马太福音》第4章第8节)。耶稣拒绝了,但诱惑始终都非常巨大,毕竟,大多数人都不像耶稣那样坚若磐石,毫不动摇。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借助恶魔来对恶进行具体的想象,因为,“恶真实地存在着,它就存在于人类的形象之中,潜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n。格奥尔格·西美尔在他的《社会学》一书中是这样说的:“恶与秘密有一种直接的内在联系。”o是的,按照现代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观点,撒旦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它来自于人类的潜意识,是本我,是受到压抑、排斥的欲望,是本能的形象化表达。本我“没有价值观念,没有伦理和道德准则。它只受一种考虑的驱使,即根据唯乐原则去满足本能的需要”p。撒旦对上帝的反叛,正是欲望、本能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对道德律令的挑战与挞伐。毕竟,道德是建筑在群体的彼此约束上的,而本能是活生生的生命之根,具有冒险精神和反抗性,使生命呈现出丰富性与生动性。从某种角度上说,对于本能的扼杀就是文明对生命的禁锢,就是上帝对撒旦的惩罚,就是超我对本我的压抑。人不能长久地囿于知觉状态,他必须重新闯入无意识存在中,因为那里存在着他的根。
歌德的《浮士德》就是这种“根”的产物,是歌德摆脱自我知觉状态而进入无意识存在的本我产物。如果说生命之花的开放需要根的话,那么这花一定是艳丽诱人而又邪恶的“恶之花”,是那心理潜意识哺育了它。所以荣格说:“《浮士德》并非是歌德创作的,而是《浮士德》创作了歌德。”q
应该说,布莱希特的《三毛钱小说》就是一部散文体的“恶之花”,给读者带来一种惊惧的恐怖美,而恐怖又是与人类自我保护的机能相联系,所以恐怖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审美效果。弗洛伊德认为,在常人的理解中,害怕的东西之所以吓人那是因为它不为人所熟悉或了解,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恐惧是对“某种本应隐蔽起来却显露出来的东西”的心理反应,因为“令人害怕” 的事物是脑子里早就有的,只是由于约束的作用,它才被人从脑子里离间开来。“这种同约束因素的联系使我们进一步懂得谢林对‘令人害怕的所下的定义,某种本应隐蔽起却显露出来的东西”! 8。在弗洛伊德看来,害怕的感受来自于本应受到约束的熟悉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本能,人类的本能应该深藏于潜意识领域,如果它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就会遭到道德的惩罚。这种对道德戒律的畏惧就是恐怖。撒旦(恶)本应潜藏于黑暗中,停留在人的无意识领域,但它却走到了阳光下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令人陌生而又熟悉的东西又怎能不令人感到恐怖?从创作理念上说,这也正是布莱希特倡导的“陌生化效果”。他认为“陌生化的反映是这样一种反映:对象是众所周知的,但同时又把它表现为陌生的……毫无疑问,这种陌生化效果会阻止发生共鸣”s。共鸣诉诸人的情感,造成丧失主观能动性的负面效应,会让人丧失改造现实世界的冲动,“每一种旨在完全共鸣的技巧,都会阻碍观众的批判能力。只有不发生共鸣或放弃共鸣的时候,才会出现批判”t。毕竟“艺术之成为艺术,是因为它具有使人精神获得解放、震动、奋起及其他种种力量。倘使艺术无能力为此,它就不是艺术了”@ 1。这样看来,布莱希特把《三毛钱小说》 写成一部散文形式的《恶之花》,是因为他意识到,比起善来说,破坏性的恶更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它表现为一种原始的力量,表现为对一个旧时代的否定,还表现为对某种既定价值的颠覆,因为布莱希特坚信:“这个可怕而又伟大的世纪的人是可以改变的,他也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2
a 〔德〕布莱希特:《三毛钱小说》,高年生、黄明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译本序,第1页。
b 关于布莱希特把《三毛钱歌剧》改编成《三毛钱小说》的问题,本人已有专文论述,具体参见:《论布莱希特的反向改编——从〈三毛钱歌剧〉到〈三毛钱小说〉》,《戏剧文学》2012年第7期。
cl〔德〕玛丽安娜·凯斯廷:《布莱希特》,罗悌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第112页。
d 〔德〕施勒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李伯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5页。
efhijkm〔德〕布莱希特:《三毛錢小说》,高年生 黄明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第35页,第122页,第24页,第101页,第58页,第40页。
g 〔德〕沃尔夫冈·耶斯克:《三毛钱小说的影响》,转引自布莱希特:《三毛钱小说》,高年生、黄明嘉译,附录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69页。
n 〔奥〕弗朗茨·M·乌克提茨: 《恶为什么这么吸引我们?》万怡 王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
o 转引自〔德〕彼得-安德雷·阿尔特: 《恶的美学历程——一种浪漫主义解读》,宁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页。
p 〔美〕卡尔文·斯·霍尔等: 《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包华富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q 〔瑞士〕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黄奇铭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页。
q 〔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孙恺祥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st@ 1 @ 2〔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第240页,第6页,第66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拔尖研究项目“布莱希特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 者: 何玉蔚,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学与文化。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