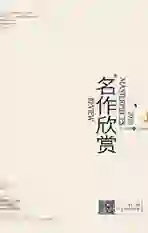湖湘抗战文化视阈下吴奔星诗歌创作研究
2020-03-01范果
范果
摘 要:本文從湖湘文化的精神印记、生命意识与诗化人生、情意蕴藉与慷慨开阔之美三个方面探索了湖湘抗战文化视阈下的吴奔星诗歌创作。
关键词:吴奔星 抗战文化 诗歌创作
吴奔星(1913—2004),湖南安化县人,我国著名诗人、评论家、学者,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美学研究上造诣深厚。“抗战”期间,吴奔星先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以诗歌为武器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的诗作激励了抗日斗志,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湖湘文化的精神印记
吴奔星先生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东坪镇吴家湾。东平镇是一个山区古镇,群山南北环抱、资水东流,始建于宋代,吴家湾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这里是荆楚文化重要支流——梅山文化发源地。晚唐时期,梅山土著民族反统治攻州县,到光启年间梅山一带不听从朝廷命令,不服从州府县辖管制,这种情况历经五代直到北宋中期。在这种独特的环境下,形成和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默默流传千年,直到宋熙宁五年(1072)归皇后才汇入中国文化的江河。随着历史变迁发展,尤其是经历宋、元、明代几次移民,湖湘士民的风俗习惯、人口构成、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逐渐形成新的地域文化形态——湖湘文化。历经荆楚文化孕育和宋明中原文化洗礼后,湖湘文化逐步形成自己稳定的文化特质,归纳起来体现在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和自强不息四个方面。敦厚雄浑刚烈正义的个性、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重实践重履约的务实精神,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是湘人骨子里流淌的基因。湖南文学在精神文化气质上也往往表现为一种放眼天下的浓厚政治情怀,强烈的爱国主义,强健不屈的人格魅力和勇于开拓的学者化倾向这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这些都与湖湘文化精神的哲学传统、文化意识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吴奔星于1928年至1932年就读于湖南长沙的修业农校,1932年秋赴北平发展,1933年至1937年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吴奔星正值大学毕业,于“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回到长沙。作为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深受湖湘文化浸润,十五岁时在家乡安化东坪镇读高小的吴奔星就追随进步教师,参加共青团,投身于湖南农民运动;在北平期间,他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和诗人李章伯创办当时的华北五省唯一的诗刊《小雅》诗刊,处在日本侵略前哨地区,较早地提出了“国防诗歌”口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奔星返回长沙担任教职,曾应担任浙赣铁路理事会秘书长的邀请,担任浙赣铁路职工巡回教育队队长,积极宣传“抗战”,“抗战”期间以诗歌为武器在《火线下三日刊》《广西日报》《扫荡报》等报刊发表诗歌作品。尤其是发表于湖南长沙抗战文艺重要战线之一的《火线下三日刊》上的《湖南人进行曲》《保卫南京》等诗作,不仅推动民众去了解当时的战局,也深深鼓舞了人民“抗战”的热情。吴奔星在成长历程和诗歌创作上都有着湖湘文化的精神印记,他“重经世致用”,同现实社会紧密连接在一起,以宽阔的视野,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将知识分子的抗争和解放,汇入民族和社会历史的洪流之中,以诗歌为武器投身于抗战,演绎出时代的最强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和深远影响。
二、生命意识与诗化人生
吴奔星主张诗歌表现诗人个体生命的真情实感,在创作上他的作品表现出对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探索与思考,他的“抗战”时期的诗歌作品集中展示了战争年代的生存体验和生存远景,展示出对祖国的浓厚感情,以及社会大背景下人民生活、生存、抗战、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广阔的社会历史风貌。“抗战”初期,吴奔星诗作主要抒发生命体验,描摹主体的审美感知,在这种自然抒发中又饱含生活经验、世间百态的积淀。如他的《示丐女》:“行乞的女孩,别盯住我吧,/挂着两行清泪走来;/我,虽对你怜爱,/奈何,也早被驱逐在人生的华宴之外!”当时年轻的诗人在北平发展前途充满着未知,却处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的困境之中,在面对毫不相识的女乞丐的苦难时,他感同身受,思考着她们以及自身的命运,对底层小人物怀着强烈的同情心并满怀对黑暗现实的控诉。但是,社会环境给年轻人带来的阴暗面并没有阻断诗人对未来的希望,这段时期也有“我为着寻求一线希望,年年在天涯海角飘荡”“我要挣扎,到青天里拍拍尘土”“初夏的季候/心之旷野也是葱绿的呢”这样的对自然界景物的欣赏描摹、对未来充满期望的诗句。困境之中,吴奔星有着诗人的热忱热血,始终以一颗入世之心追逐探寻着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奔星离开北平回到长沙。这一时期诗人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充满了历史的忧患感,风雨飘摇的祖国,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感,百姓的苦难,青年人的忧郁、愁恨与悲愤展现于诗行之中。1937年,发表于湖南长沙抗战文艺重要战线之一的《火线下三日刊》上的《赠给洞庭湖》《湖南人进行曲》《保卫南京》等诗作是诗人“抗战”时期诗歌的代表性作品,这些诗作中表现出沉郁顿挫的忧患情怀,具有阔大的史诗气质。1939年,吴奔星到达桂林,之后诗人辗转于桂林、贵阳、重庆等地。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自身前途的探索,怀抱不可知的命运,流亡大西南。这一时期诗人创作了《过桂林》《涧之歌》《流浪人的日子》《都市是死海》等境界开阔的作品。这一时期的诗歌思考了复杂深邃的人性和生命意识,对意象的捕捉、意境的营造、情绪的烘托,都是诗人以内心为出发点,探寻生命中更幽深的层面,在一个非常时期的年代更切实地把握了生命存在。
现实的生活、现时的奋斗都是对生命的珍视。吴奔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的广阔洪流之中去,人文精神始终是其创作的一条主线,其以“抗战”为题材的诗歌中体现的生命意识与诗化人生,忧国忧民的时代放歌,追求人格的独立尊严,追寻生命中的真善美,既具备思想价值也呈现出独特的美学特征。
三、情意蕴藉与慷慨开阔之美
吴奔星在其著作《诗美鉴赏学》中提出“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的论断。正是基于这一诗歌理论出发,他的诗歌创作中追求诗美,呈现出情意蕴藉之美。“抗战”初期的诗歌中虽未有铿锵有力的呐喊,但是触及广阔的社会视野,即使是写爱情、友情、乡情也反映出时代所造成的心境,呼应了历史所震响的声音。如《我沿山涧以彳亍》:“我沿山涧以彳亍,/倒影启示了我的伶仃;/而风尘的脚步,/更启示我不该慕此清高!/遂将污浊之心/濯清流而伴以痛哭。……”孤独的意象中折射出现实的黑暗处境以及漂泊异乡的孤独忧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吴奔星辗转于北京、长沙、桂林、重庆等地,目睹和体验了这块广袤土地上的人们苦难深重的生活,深刻领略了战乱年代的沧桑沉重,他的诗歌创作由个人的抒情和感触,转向更为广阔的描写和更深邃的诗歌空间,从而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现实主义诗歌作品。如写于湖南衡阳的《战区春晚》《水天一色》,写于湖南新宁的《梦着的地带》《衡桂车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