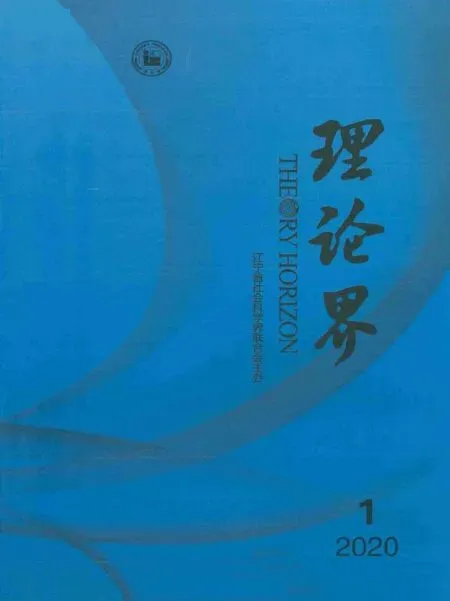论朱熹与阳明对孟子尽心章理解之异同
2020-03-01徐会利
徐会利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1〕在孟子看来,人尽到自己本有的善心,就意味着觉悟到了自己固有的善性。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于是就理解了天命。保存自己的善心而不丢失,养护自己的本性而不被外物改变,以此来对待天之所命。无论自己是长寿或是短命都不改变这种态度,只是修身养性等待天命。尽心、知性、知天在孟子看来是一贯的过程,是为了保持内心固有的善性而不丢失,培养人固有的四端之心。
研究朱熹与阳明对孟子尽心章的理解,除了看到朱熹与阳明对此章理解的不同思路之外,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研究者还应该看到儒家思想从先秦到宋明时代一以贯之的相同之处。关于朱熹和阳明的分歧,学者多就孟子尽心章研究孟子本意,或者从宏观上研究朱熹与阳明之别,但将前后两者联系起来从微观上——针对孟子尽心章来看朱王之异同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旨在探析朱熹与阳明对孟子此章不同的解释思路并分析其得失,以便清晰地观察宋明时代儒者对孟子理论的新发展。
一、朱熹与阳明对尽心章理解的相同之处
孟子尽心章涉及的核心概念便是心与性、命,到宋明时代,朱熹与阳明二人或明或隐都对此章阐发了各自的理解,虽然二人有很大分歧,但其共同之处在于,在心与性、命的基础上,增加了“理”这一最高范畴,从而使心、性、命与最高的天理相联系。此外,朱熹与阳明都重视心的主宰作用,这一主宰有两方面的内涵:形体肉身之主宰与义理之主宰。
1.心之主宰功能
孟子尤其重视心的作用,“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所谓“大体”便是心,跟随心而动,不是跟随耳目之官,这样才能不被外物遮蔽心的本来状态,成为具有崇高德性的“大人”。孟子对心的看重这一思路被朱熹、阳明所继承,到了宋明仍旧继续发挥心的主宰作用,对心的重视和探讨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朱熹这里,“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2〕可见,心具众理,理存于心,天理落于人成为人之性,性在心中。“心者,一身之主宰也。”〔3〕由此来看,心是人的主宰,不仅主宰人的形体四肢的运动,而且主宰着人的是非等义理判断。心的特点是虚灵知觉,正因心之虚才可容纳性的存在,心有知觉外物的作用,才能对外物产生情感并作出各种判断,对外物及时作出反应,比如饥饿的时候想吃食物、口渴便想要喝水、寒冷的时候想要保暖。若无心之主宰,人之行为会失去准则,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只剩个肉体罢了。正因为心的主宰作用使得人与其他外物区别开来,人心所秉受的天理之生生不息的善性成为人之特质。
在阳明这里,“若为着耳、目、口、鼻、四肢时,便须思量耳如何听,目如何视,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动……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4〕心同样主宰着耳、目、口、鼻、四肢,心要视、听、言、动,才有了人的各种器官的功能。至于如何视、听、言、动才合乎天理,则应听从内心的准则。阳明不把心当作那个生理器官意义上的心,若心仅指器官之心,已经死去的人为何有心却不能正常运用?阳明将心提高到天理的地位,人之为人、心之为心在于此心通达天理,心中有性,此性才是导致人能视、听、言、动的原因。至于如何视、听、言、动才合乎天理,阳明认为要抛弃美色、美味、美声等向外驰求之物,回归本心、减去外在束缚才是符合天理的行为。阳明和朱熹一样,二人都充分肯定心的主宰功能:不仅体现在心对人的形体肉身的主宰,更包含义理的判断的主宰。心不能沉溺于外物的享乐,否则就会违背天理,心对是非善恶等义理的判断是二人共同关注的问题。
总之,从对心的重视和心的主宰功能方面看,朱熹与阳明乃至孟子都是一致的,心主宰着人的四肢等器官的运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心对义理判断的主宰,后者是儒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2.天理与本性之纯善
“性即理也,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5〕陈淳作为朱熹的弟子,其思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朱熹的认识。天理下贯于人成为人之性,性存于心中。从更广意义上看,理是为各种事物和人所共有的,而性是理下贯于人而为人所特有之理。无论是理还是性,都是人与生俱来的。这是朱熹与阳明的共识。
天地化育万物、生生不息体现了天地的德性,“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因此,天理是纯善的,而人秉承天理为人性,因此,人性本来也是纯善无恶的。无论是朱熹还是阳明,在承认人性的原初状态是纯善无恶这一方面与孟子是一致的,人都有为善的可能,之所以产生恶要归因于后天。
天理的生生不已的特点正体现了其仁德之性,人与天同构,人秉承了天理之德性,因此,人性也本应该是纯善无恶的。朱熹与阳明各自从天理生生不已以及天人同构、天理之纯善无恶的角度推出人性本来是善的这一结论,虽然二人代表不同的理学观点并有很大分歧,但是就其得出的对人性的本来状态的结论来看,孟子与朱熹、阳明三人是一致的,这也构成朱熹与阳明理解此章的共同的出发点。
二、朱熹与阳明解尽心章的不同思路
朱熹从格物致知角度解知性与尽心的关系,从知与行的角度解“尽心知性知天”与“存心养性事天”二句,朱熹与阳明的分歧便主要聚焦于此二句。研究朱熹与阳明对孟子尽心章的理解,首先要明确孟子所讲心、性、命、天与此二人所理解的不同,宋明儒者所理解的心、性、命、天是对以往认识的丰富,并且在这几个范畴之上立了一个更高的范畴——“理”,天理的预设构成了宋明儒者讨论心性问题的前提。宋明儒者所讲之心是容纳性的存在,而心或者性都来源于天理,因此,宋明儒者所讲之心不单单是孟子所理解的道德本心,更是被置于一个与天理一样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宋明儒者所讲之性更是天理下贯于人的善性,不单单是孟子所理解的人异于禽兽之处。宋明儒者所理解的命也是天理落于人身之命,总之,相较于孟子,朱熹、阳明所讲之心、性、命都赋予了天理的含义,代表了儒学发展到宋明时代,儒者对概念范畴赋予新的解释思路。
1.朱熹解尽心章
(1)先知性而后尽心
“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6〕在朱熹看来,孟子所谓的“知性”相当于格物,“尽心”相当于知至,格物而后知至,知性而后尽心。“知性,然后能尽心,先知然后能尽,未有先尽而后方能知者。盖先知得,然后见得尽”〔7〕心具众理,只有先知性最后才能尽其心。这是朱熹对孟子此章的解释思路。
孟子原文中是按照“尽心知性而后知天”的次序,因此,一般人总是认为先尽其心而后知其性,朱熹认为这就把前后次序颠倒了,他认为心性本不可分,“心只是包着这道理,尽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尽其心”。〔8〕朱熹从天理的角度解释知性、尽心、知天,认定知性在前,尽心在后。“知性者,物格也;尽心者,知至也。”要理解此句,不得不先理解朱熹对心与性关系的界定,“盖郛郭者,心也。郛郭中许多人烟,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9〕“心只是包着这道理,尽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尽其心。”〔10〕在朱熹看来,尽心是指要尽见得、尽知得此心所包之理,要达到尽心就不得不先知心所具的众理——性。因此,他认为知性与尽心是一个一贯的过程,知性与尽心有一个逻辑上的先后关系。
性所具有的道理都存于人心之中,穷尽性之理就是尽心的过程。因此,知性就是尽心,二者并无严格的界限和时间上的先后次序,但就实现目标而言,先知性而后才可能尽心,尽心是知性自然而然的结果。若只追求尽心,却不知先体悟本心所具之天理,便不能实现尽心。“所以能尽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知性则知天矣。知性知天,则能尽其心矣。”〔11〕在朱熹看来,要先知得性之理,然后才能见得此心之尽。性只是此心所具之理,性之理存在于心中,尽知其性之道理便是尽心。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12〕程子认为,心、性、天,其实是一个理,只不过从不同的角度去言说罢了,从理的来源角度讲叫做天,天是理所由以产生的存在;从人秉受天理角度讲叫做性,性是心所具有的理;从存在于人身上的角度讲叫做心,心是具有一切理并可应一切事的存在。知性尽心然后知天,最终追求的是认知最高的天理,而存心养性以事天,是为了具体实践这一最高的天理。朱熹认为,仅仅认知天理、人性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行动,认知此天理并能付诸实践才是最高的智和仁。
朱熹从知而非行的角度理解尽心,“‘尽心、尽性’之‘尽’,不是做功夫之谓。盖言上面功夫已至,至此方尽得耳”。〔13〕尽心不是实践等外在工夫,而是知晓心内所具天理。尽心不仅是个过程也是追求的目标——心内所包含的众理无所不知,存心是从践行上符合理之要求。心内本来具备众理,如今为何有能尽者、有不能尽者?朱熹从气禀角度解释这一差异,“尽心如明镜,无些子蔽翳。只看镜子若有些少照不见处,便是本身有些尘污”。〔14〕尽心便如同擦拭镜子,这镜子本来无所不照,本来是明镜,但如今有照不清的地方,一定是镜子沾染了污物,所以需要擦拭。今人本来具备天理,但在一定程度上受物欲所蒙蔽,所以不能尽其心,处于昏乱的状态。因此,需要去除物欲,尽其心——尽知天理,能“尽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无有不合道理”。〔15〕能够尽其心之人,行走坐卧无不符合天理。
(2)存心养性事天——知行相须
“存,谓操而不舍;养,谓顺而不害。事,则奉承而不违也。夭寿,命之短长也。贰,疑也。不贰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则事天以终身也。立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16〕朱熹不仅看重知,同样看重行,有了天理还不够,还要练习存养工夫,不因长寿或夭折而怀疑内在具有的天理和善性。存养天理要保持诚意和正心,不因人生境遇的好坏而产生邪念,从“尽心知性”到“存心养性”,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愚谓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养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17〕知其理并能行其事,人存养本来具有的天理和善性,不因夭寿乱其心,修身俟死,由此达到最高的智和最高的仁。若仅仅知却不行,便等同于无知,更谈不上“智”和“仁”。朱熹从知行相须的角度解释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18〕知和行的关系如同眼睛和脚一样,两者不能相离,但相较于知,朱熹更看重行。尽心知性知天属于知的范畴,存心养性事天属于行的范畴,朱熹更看重存心养性事天的行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行动所秉持的专一的态度,体现了“智”和“仁”的统一。
朱熹以“操而不舍”来解释“存”,这和孟子所讲“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万物皆备于我矣”,“操则存,舍则亡”,“求其放心”具有一致性。孟子主张操存心中的四端之心,扩充善端成为仁义之人,朱熹所操存的对象是天理,而天理被视为纯善无恶的存在、是仁义的象征,从此意义上看,朱熹对“存心养性事天”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孟子思想契合的。
在教导人存养本来固有的善性方面,朱熹和孟子是一致的,都认为仅仅有善性或善端是远远不够的,修身养性、存养内在固有的善性才能实现仁义。仅仅有善性却不加存养,就有流于恶的可能。因此,孟子认为学问之道不过“求其放心”罢了,朱熹则教导弟子以尽心知性为知,以存心养性为行,以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智之尽、仁之至,以此操存天理成为圣贤。
(3)朱熹解此章之得失
朱熹对孟子此章的理解,其得在于把握了孟子从性善之开端到培养、扩充善端的这一路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19〕人人生而具有四端之心,这可以以突然看见小孩子有入井的危险,而自然生出“不忍人之心”为证,这四端之心正是人性善的根据,但这并不能排除现实之恶的可能。因为四端之心虽然是人生而具有的,但若不精心培养,同样有丢失善端流于恶的可能,“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20〕求学问道不过是培养善端、求其本心,恢复善性的过程,丢了鸡犬尚且要找回来,更何况丢失了人之本心呢?朱熹正是看到了孟子所主张的扩充善端的重要性,因此,认为仅仅尽心——熟知内心所具众理是不够的,更强调“存心养性事天”的实践活动,此二人都从人性善这一端点出发,走向扩充、培养、践行善的道路。
“孟子所谓尽心者,须是尽得个极大无穷之量,无一理一物之或遗。”〔21〕陈淳认为,尽心就是把心内所具众理一一穷尽,所采取的方法就是格物,通过日积月累的格物工夫最终穷尽天理。这为学者提供了清晰的修行方向。陈淳作为朱熹的弟子,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朱熹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朱熹还是陈淳,都和孟子本意所讲有些许偏离。
朱熹解此章时,其关键概念“性”、“尽心”与孟子原意有很大差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22〕孟子认为,人和禽兽的差别很少,但正是因为这些许的差别才将人与其他禽兽区别开来,这细微的差别便是人之性,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构成人的善端,但是仅仅有善端是不够的,只有细心呵护才能使善端得以扩充,最终顺应本性成为善良之人。这种扩充善端的过程就是尽心,只有使善端真正得以扩充、培育才会实现人性之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性”,顺应本性而为,从而与天相合。但朱熹将“知性”理解为“格物”,将“尽心”理解为“知至”,无疑将知性看作通往尽心的手段和方法,这和孟子的思路是相反的。
此外,朱熹所谓“尽心”,是尽知心内所具众理,至于认知到何种程度才算“尽”,以及个人有限的经验是否能完全实现“尽”其心,这都是现实的问题。朱熹所阐述的理论上虽然比较完备,但在现实修行中仍然存在诸多疑问。
2.阳明解尽心章
阳明通过对朱熹的批评阐发自己对孟子此章的理解,他反对朱熹从格物知至角度讲知性尽心,没有区分普通人和圣人的资质禀赋和功夫次第;此外,阳明批评朱熹将“尽心知性知天”理解为知,将“存心养性事天”理解为行,认为这有把知行割裂开的思想倾向。阳明将圣人、贤人和学者分开,认为不能笼统地要求不同资质的人都尽心知性知天,贤人和学者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圣人的境界,因此,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功夫次第;阳明用知行合一观批评朱熹的知行相须、以行为重的说法,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1)工夫次第——“三知三行”
阳明是用《中庸》为孟子此章作解,将此章与“生知安行”的圣人工夫、“学知利行”的贤人工夫以及“困知勉行”的学者工夫相联系,对朱熹的次序做了纠正。“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23〕生而知之者是最具智慧的人,学而知之者是极具有仁义之人,困勉而行之人是最勇敢的人,虽然人性无有不善,但这三种人闻道有先后,行道难易程度不同,等到各自按自己的道路通达目标后,这三种人也没什么不同了。如果没有生而知之的天赋,又轻视困勉而行的办法,就很难达道了。虽然每个人资质禀赋不同,但达道的目标是一致的,闻道有先后,行道有难易,因此,每个人达道的方式可能不同,但一旦达道之后,无论生知安行还是学知利行,或是困勉而行,都没有什么差别了。好学虽非智,却足以破除愚昧,力行虽非仁,却足以使人忘却私欲,知耻虽非勇,却足以使懦弱者振奋。
阳明看到了每个人生来具有不同的资质禀赋,正因为有资质的差异,所以不能对所有人都要求达到圣人的境界。“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24〕在阳明看来,成为圣人不在于知识上多么渊博,成圣的标准只有一个:心纯乎天理。因此,成圣功夫不在于追求知识、增长才干以达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在于反观本心,使心纯乎天理,不掺杂丝毫外在之物。
阳明依据此章将人分为三种:圣人、贤人、初学者,并以《中庸》中的思想作为根据,认为只有“天下至诚者”才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若将之要求到普通人身上,便不能实现。故阳明将“尽心知性”归诸生知安行的圣人。只有圣人能做到尽心知性知天,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并且能自然而然地践行,而贤人所禀赋的资质不如圣人,不能生而知之,是通过学习而后才去践行,才去存心养性事天,对于初学者不能直接要求其做“尽心知性知天”的圣人工夫,初学者在困顿中不因夭寿动摇自己的意念,能勉励而行,修养身心就已经难得了。
阳明区分了“存心”与“尽心”,“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与天为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25〕存心不同于尽心,存心是尚未尽心的状态,事天仍是把自己和天对待来看,如子事父,臣事君,人与天仍是两个物,恭敬事天,不失善性,这是贤人的状态。而圣人却能与天为一,实现人与天的高度契合,因此,比贤人修养程度更高。不因夭寿而怀疑人之本性天理,修身以俟天命,这是对初学者的最基础的要求。从初学者到贤人、圣人,其要求越来越高,夭寿不贰是初学者的行为,存心养性事天是贤人的行为,尽心知性知天是圣人的行为。
圣人生而知之,能尽心知性知天,与天实现高度契合,与天为一;贤人则是存心(未尽心)事天,人与天犹为二物。因此,要求贤人存养本心,“存之而不敢失,养之而不敢害”,等存养功夫日益成熟,才可能达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圣人境界。因此,阳明将“存心事天”归于“学知利行”的贤人。而“夭寿不贰”又是比“存心事天”低一层次的工夫。“存心事天”虽然人与天为二物,但已见得有个天在前,知天命之所在,故能一心为善以“事天”;而“夭寿不贰”乃是教导初学者“不以夭寿贰其心”,不能因个人的人生境遇或夭寿等怀疑人的本心之善,修身以俟,虽然不曾见得天理所在,却能修身俟命,安然自若,因此,阳明将“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归于“困知勉行”的学者。
“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26〕在他看来,朱子所解是将为学工夫倒做了,“知性”不是格外在事物之理,而是反观内心,若一味要求初学者向外寻求事物之理,甚至让初学者做至诚之圣人才能实现的“尽心”功夫,将使初学者徒费心力而一无所得。阳明不赞同朱熹将“知性”理解为格物,将“尽心”理解为知至,不赞同朱熹将孟子尽心章理解为知和行的结合,知行本来就是合一不可分的,不能将尽心知性知天理解为知,将存心养性事天理解为行,认为“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分为不同修养层次的人,将圣人、贤人和学者分开,对初学者不能一下子就要求其“尽心知性知天”,而要循序渐进,从不以“夭寿贰其心”,逐渐“存心养性事天”最后才能达到“尽心知性知天”。阳明认为,朱熹没有区分不同修养程度和不同资质的人,直接要求初学者就做生知安行的圣人工夫,这是难以实现的。
“譬之行路,尽心、知天者,如年力壮健之人,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百里之间者也……既已能奔走往来数千里之间者,则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间而学步趋,而步趋于庭除之间,自无弗能矣;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无弗能矣。”〔27〕
阳明认为,能够达到尽心、知性、知天的人,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或“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因为前者已经包含并实现了后者,这如同身体健壮之人可以走数千百里的路程,一定是经历过了孩童之年在庭院学步这一阶段,因此,不必要求尽心、知性、知天的人还去修行存心、养性、事天的功夫,因为前者本来就已经实现了后者。同理,已经能够做到存心、养性、事天的人,必定已经实现了“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因此,不必要求存心、养性、事天的人还去学习“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前者是建立在后者基础上的。阳明批评朱熹“倒看了此意”,批评朱熹让初学者就去做圣人的工夫,初学者是很难做到的。
(2)知行合一
朱熹认为,尽心知性知天是讲知的层面,存心养性事天是讲行的层面,虽然知行相须,但若要分个轻重,则行为重。此一区分,在阳明看来就有割裂知行的嫌疑。阳明把知行看作合一的,在他看来,关于知行只存在两种可能的状态:“不曾知”与“知行合一”的状态,不包含“知而不行”这种可能,“知而不行”在阳明看来只是“不曾知”,阳明所认同之“知”,必定是与行合一的,知中含行,无行便不为知。
在阳明这里,“知”是一个主观性的范畴,“行”不仅指人的实践活动,还包含人的心理行为。明好色、明恶臭属于知,好好色、恶恶臭这种心理活动阳明将之归于行,是否真知晓孝悌之理,不是看其说了多少关于孝悌的道理,而是看其是否行孝悌之事。
之所以讲知与行,不过是为了纠正那些懵懂而做不知其原因、凭空思索而不践行之人,对于那些懵懂而做不知其原因之人,圣人教其知,即知晓这样做的原因;对于凭空思索而不践行之人圣人才讲行,旨在教其实践已知之理,无论是讲知或讲行,都是为了纠正古人的不当认识和行动,都是为了实现知行合一。阳明所讲知行合一,强调个人体悟,由别人言传得到的认识不够真切,须得自己亲身体悟方能得真知。
朱熹将“尽心知性知天”理解为知,“存心养性事天”理解为行,在阳明看来是将知与行割裂开来,没有离开行的知,也没有离开知的行,阳明采用知行互训的方式界定知与行。阳明强调知与行的合一主旨是强调德行的培养和成圣的目标,“阳明以念为行,无疑有其道德涵养上的考虑:把观念上的恶等同于实践上的恶,旨在根绝观念层面的不良动机,这也是阳明在以知为行意义上讲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28〕由此看来,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具有防范恶念的意义,教人修身向善,同时也有教导人把善念转化成善行的内涵。
三、结语
在对孟子尽心章的理解上,阳明与朱熹有很大的不同,朱熹是从格物致知角度解释知性与尽心,认为“尽心知性知天”是从知的角度而言,“尽心知性知天”是从行的角度而言,“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从态度上而言,知性如同格物,尽心如同知至,知性而后才能尽其心。阳明则将孟子尽心章比配三种不同根器之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尽心知性知天”是生而知之的圣人才能实现的,“尽心知性知天”是学而知之的贤人才能实现的,“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困而知之的学者能够做到的。阳明以三种不同根器的人来反对朱熹以格物致知注解此章,用知行合一反驳朱熹从前知后行的角度注解此章。
朱熹所理解之“尽”是穷尽、尽知的意思,“尽心”就是尽知心内所含众理,这不免让人疑惑:至于认知到何种程度才算“尽”,以及个人有限的经验是否能完全实现“尽”其心,针对这一问题,朱熹为孟子此章所做的注解引起了后世不少学者的批评,比如牟宗三。此外,阳明对孟子此章的分析与他对三种人格以及成圣工夫的理解相关,但阳明对此章的延伸发挥并不具有很高的说服力。
总之,朱熹与阳明分别从理学和心学角度分析此章,虽然和孟子原意不完全一致,但各有所长,二人对此章的理解体现了后代儒者对孟子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创新,借孟子此章不断阐发并完善各自的理论体系。除了看到朱熹与阳明为此章注解的特色和发挥之外,也要关注从孟子到宋明时代儒者朱熹、阳明,不同时期的儒者关注的重点以及思想传承的内在脉络——对心性问题的重视,同时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与时俱进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