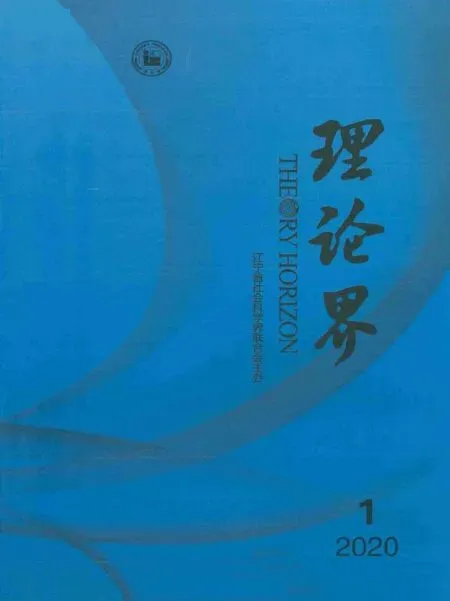精神空间与自我探求:中国古代女性文人室名堂号解析
2020-03-01朱路遥雷环捷
朱路遥 雷环捷
历代文人往往有使用室名堂号的传统。室名堂号可归为自号的一类,一部分与使用者所实际居住的处所有实际关联,另一部分则与名或字互相渗透,界限较为模糊。室名堂号多由使用者自行命名,被应用于非正式或者与文学关系较为密切的场合,例如为个人诗文集命名。室名堂号的结构形式较为自由,发挥空间大,自我阐述的目的性强,凝练性高,往往能够以小见大地反映出使用者的个人志趣。
女性文人使用室名堂号可追溯至唐宋时期。如唐代薛涛晚年建楼名为“吟诗”;又如宋代何师韫因居室外有“懒愚树”而“榜其室曰懒愚”;〔1〕宋代黄由之妻胡氏自号“惠斋居士”,〔2〕均已见雏形。至明清时期,随着女性创作和商品印刷的发展,女性文人对室名堂号的使用进入高峰阶段,尤以清代为最。其原因之一是室名堂号的使用日趋普遍,之二是相关史料和典籍保存较多,之三是女性创作被社会接受程度有所提升。目前可见的较多以女性文人作品集名的形式保留,其中大部分为女性为自号,小部分为刊刻者在出版时所取。整体而言,女性文人在使用室名堂号时,与以男性审美为主流的文坛风尚有所区别,呈现出较显著的群体性别特征。
一方面,以往的研究已对中国古代女性的被命名与自命名行为有所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当时女性的生活和创作情况,但往往仅将女性视为被压迫者进行考察。另一方面,高彦颐 (Dorothy Ko)、白馥兰 (Francesca Bray)、〔3〕伊沛霞 (Patricia Ebrey)、曼素恩(Susan Mann)等学者通过对宋代及以后的妇女史研究普遍认为应采取女性中心和动态演变的视角。得益于前人的基础和启发,对女性文人室名堂号的研究可循着整体性的路径,综合且全面地梳理室名堂号的基本内容与重要主题,深入分析在其背后产生影响的代表性观念,并进行审视与反思。
一、自然意象与“香草美人”
借助自然意象营造意境是室名堂号的主要命名方式。使用者以短短数字勾勒出文学性意境,彰显个人的审美情趣与文学意趣。最常被使用的意象或为云、霞、月、山等自然景物,或为兰、梅、竹、松、桂等植物,都是文学传统中受文人青睐的物象。虽然文学传统中对风云月露之风的批判已是长久共识,但部分文人在室名堂号命名时却未刻意对此规避,依然选用此类意象。文人们择一物而尽发其意趣,取其闲适自然风雅之意,亦不流于绮丽浮靡。有些文人取与居室或书房有关的实物实景入其室名堂号,以纪实性加强室名堂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联,突出其独属特性。
社会容纳女性文学创作活动,但同时也存在成见和限制。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创作在风格和层次上做了区分,并将对女性贞静娴美的规范扩大到文学中,树立了风格的理想模范,许多女性文人在创作诗文和拟定室名堂号时因此趋近婉约清丽的风格。家庭对于女性的命名带有惯性,淑、贞、婉、娴等闺范标准,兰、蘩、芝、莲等植物意象,以及珠、翠、玉、琴等闺阁物象都是十分普遍的女性命名常用字。这一惯性也可能由女性带入到对自我的再命名过程,出现于室名堂号与文集名称中。
在女性室名堂号中被使用最多的自然意象与楚辞“香草美人”意象体系有关,同时也有所改造。检阅《历代妇女著作考》可知,以室名堂号作为作品集名的女性文人共有2357位,其中以“香”为构成部分者即达263位。以“兰”为名者有108位,为字号者有69位,为室名堂号构成部分者有76位,可见“兰”称得上是女性名、字号、室名堂号中最常见的意象。元代薛兰英、薛蕙英姐妹所居楼为“兰蕙联芳之楼”,合著诗集名为《联芳集》,她们对兰、蕙、芳的强调具有一定代表性。此外,其他女性文人所用“艺兰室”“友兰阁”“猗兰室”等名,也直接指向“兰”意象。楚辞“香草美人”之典原本虚指君臣之义,在女性文人室名堂号使用中产生了寓意的迁移,转为实指女性之美及高洁情操,体现了历代女性文人群体中具有延续性的精神追求。
清代毛国姬自号素兰女史,其所编《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弁言云:“诗三百篇,大抵妇人之作,自楚风不录于经,而湖外歌谣传自闺闼者,益不少概见,将澧兰沅芷之馨香,分得于翡翠笔床者,固独寥寥与?抑奇葩异藻吐秀于南国美人者,随序荣落,既无人焉为之采撷,以相饷遗,斯通都大邑儒林词伯,莫由一颂其芳烈耳。”〔4〕所谓“澧兰沅芷之馨香”成为女性文学创作的代名词,其中虽有毛氏本人的湖湘籍贯之影响,但更多的是对女性文学创作特征的描摹——兰心蕙质、馨香芳烈,从而对创作者及其作品都进行定义。从男性文人视角来看,他们亦重视女性文学作品中的性别特质,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审美切入点。男性对女性文人的评价亦常见“蕙心纨质”“澹秀天然”〔5〕等语,“香草美人”的搭配在女性创作评价体系中已基本形成共识。除兰以外,竹、梅、松、桂等植物也被赋予类似内涵,共同构成一个更为广泛的“美人香草”意象体系。
室名堂号是女性文人自我形象的勾勒,是其创作行为的缩影。以“香草美人”为代表、使用自然意象构成的女性室名堂号多表现出幽闲贞静的特点,并与其自身创作风格相呼应。其中表现出女性在文学创作行为中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认知,即她们没有刻意抹去性别特征以趋同于文学主流,而是将之保留下来成为特色。一部分女性作者囿于家庭环境和所受教育的限制,只能在社会对闺阁文学早已框定的风格空间内进行创作。但她们仍能够在有限空间内竭尽所能地锤炼作品,真实地抒发内心情感。另一部分创作水平和自由度较高的女性则对闺阁之学有所反思,她们或突破社会刻板印象限制,豪言壮语不逊须眉;或发挥女性细腻敏锐的长处,将性别特征转化为创作优势,在男性主导的文坛中独树一帜。
二、家庭生活与亲缘关系
家庭生活与亲缘关系亦是女性文人室名堂号的主题之一,按照所面向的不同对象可分为同辈、配偶、父母辈和祖辈等四类。
其一是与姐妹、兄弟等同辈亲属间的联系。除前文提及薛氏姐妹的“兰蕙联芳之楼”外,明清两代亦有许多事例。一类是姐妹间室名堂号互相呼应,如清代王迺德“竹净轩”,其妹王迺容室名“浣桐阁”。〔6〕另一类是汇编家族中同辈女性诗文时取一概括性的室名为作品集冠名,该行为可能出自作者本身,也可能是汇编者或刊刻者所为。浙江海宁朱淑均、朱淑仪姐妹“幼相倡和,比长,同归查氏为妯娌。刻有《分绣联吟阁稿》。妾织霞女史鬘云之诗附焉”。〔7〕阁名记录三人各自独立的家庭生活以及联合性的文学创作活动。安徽桐城张瑞芝、张玉芝、张爱芝姐妹“皆能诗。卒后其弟鹄哀三人之作,名曰《三芝轩诗存》,并为作序”。〔8〕“三芝轩”之名将三位姐妹的诗文囊括起来,在她们身后依然维持其社会性联系,加上其弟张鹄发挥作用,使同一个家庭中姐妹、姐弟间的亲情联系凝聚在“三芝轩”室名中。浙江海盐吴慎室名“琴媵轩”,《国朝杭郡诗三辑》记载:“所居曰‘琴媵轩’,意取于归时,其兄榕园取琴以赠,且戏之曰‘以是为媵’,故名。”〔9〕这是居室主人以室名记录婚前与婚后生活间的交汇点,可忆往昔在室趣事,同时明确当下已为人妇的婚姻状态。
其二是与配偶间的情感状态。清代穆竹村妻金云裳室名“倚竹楼”;〔10〕姚畹真字“芙初”,其夫张蓉静字“芙川”,“故称双芙以名其阁”;〔11〕萧恒贞字“月楼”,其《月楼琴语》附于其夫周天麟《倚月楼词》后。〔12〕夫妇间在室名堂号的运用中进行情感的互动和交流,情侣之间亦是如此。明代旧院妓杨琰与闽县林景清交好,“后林归闽,杨洁身以待,题‘一清’自名其轩”。〔13〕室名堂号成为含蓄又坚定地表明心志的载体。在丈夫去世后,妻子们也通过室名堂号追怀故人。明代顾若璞自题其集为《卧月轩稿》,并在自序中言:“卧月轩者,夫子所尝憩息志思也。”〔14〕以“卧月轩”之名表达对亡夫的思念。清代杭温如室名“息存室”,李元春在其《息存室吟正续集》序中解读:“室名息存,取朱子一息尚存之语,即未亡人之义也。”〔15〕亦是通过室名标注其未亡人的身份,表达不渝之志。
其三是与父母亲间的联系。一类是表达思亲之情。明代仲云鸾借《诗经》中《蓼莪》之典,取名“匪莪堂”,以示追思。〔16〕郭芬“取狄梁公望云思亲之义,名所居曰望云阁”。〔17〕另一类是表示对父母亲文学成就的继承。清代王玉芬之父王凤生有“江声帆影阁”,故王玉芬自号“江声帆影阁主人”,为自己的诗集取名为《江声帆影阁诗》;〔18〕傅范淑“小红余籀室”源自其母李端临“红余籀室”;〔19〕陈芸《小黛轩论诗诗》附于其母《黛韵楼诗词集》后,并有自序云:“少时得承母教,微闻声韵之学”;〔20〕简贞女有《嗣得到梅花馆诗》,原因是“父松培有得到梅花馆诗钞,故云嗣也”。〔21〕
其四是与祖辈之间的联系。清代李杜有《墨颠闺咏》,“曾大父廉访王 额所居曰墨颠,因以自号”。〔22〕钱与龄“少承曾祖母南楼老人家学,尝署所居曰仰南楼”。〔23〕室名使用者追忆童年时在长辈膝下所受的教育,表达对长辈的怀念,并显示家学的传承。
虽然不少男性文人也使用与家庭亲属有关的室名堂号,但此种情形对于女性文人而言意义更为特殊。男性可以在家庭和公共场所间自由穿梭,大部分女性的生活空间则被局限在家庭中。家庭、亲属是女性日常生活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女性情感丰富且细腻的特质也使其更容易珍视亲情。出嫁后离开原生家庭进入男方家庭,归属集体和身份的转换也常能激发女性对于旧日闺中生活及其亲属的回忆,将对原生家庭的思念注入到室名堂号中,作为自己的符号和标志,使内心有所依靠。通过室名与丈夫互动则是女性融入新家庭的表现,她们以此表明自己和丈夫感情融洽,并将丈夫视作可以文学唱和的精神伴侣。女性文学多以家庭、家族为单位,不论是生在这个家庭中,还是以婚姻的方式加入新家庭,家族内的女性间由此形成纽带,往来唱和使家庭内形成一个文学创作的小集体,并激发小集体内部各成员的创作活力。
三、闺阁中的顺从与反叛
室名堂号记录着闺阁女性生活的一角,也寄托着她们在闺阁之中的顺从与反叛,各自构建闺阁文人的鲜明形象。在女性室名堂号中,展现出社会主流观念对女性的认知和期望。她们修习琴艺,并将房屋命名为“颂琴楼”“停琴伫月楼”“友琴斋”等;同时也精研女红,“绣香阁”“绣垂馆”“学绣楼”等室名堂号具有强烈的闺阁特色;宗教信仰也是闺阁生活中的重要方面,明清时期女性群体中佛教流行,于是出现了“羼提阁”“绣佛斋”“双修慧业楼”“芬陀利居”等与佛教有关的室名;妇德也在室名中体现,明代朱有燉室夏云英“尝取女诫端操清净之义以名其居曰‘端清阁’”。〔24〕“静怡山房”“静好楼”“静婉斋”等室名也被广泛使用,是女德在女性群体中的被接受和投射。她们以此自勉,同时也希望藉此证明自身已符合社会所要求的淑女标准。
“弄文舞字,非妇人所便”的观念由来已久,〔25〕虽然朝代更迭,女性作家频出,但传统社会中无论男女的主流观念都认为文学非妇人应为之事。这使进行文学创作的女性要么从正面回应,尝试建构女性文学活动的合理性,要么从反面挣脱,直接选择反叛社会主流观念。当然,前者比后者更为常见,且实际情形往往并非仅属一端,而是更为复杂。清代查昌鹓《学绣楼名媛诗选》序:“余自垂髫,承母氏命,从伯兄介庵先生受业。初授《毛诗》 《女孝经》及《内则》 《女训》,讫于小学四子书,略皆成诵;复授唐诗数百篇,徒伸呫哔,未遑讲解。甫及笄,遂辍诵读,从事女红。刺绣余闲,取向所成诵者,私自研求,略晓大义。时就岩门诸兄质其所疑。至声韵之学,往往见猎心喜。然不敏未尝能作,且以非女子事,辄不敢为。偶有小咏,即焚弃之,不复存稿。”〔26〕她在序中记录,婚后与丈夫一起赏奇析疑,重拾诗文。但后来丈夫去世,米盐琐碎,不复吟咏,直到含饴弄孙时才稍有闲暇编诗选。从童年到婚后,再到弄孙之时,查昌鹓记录了自己学习与创作的波折历程,其中有多次中断和接续。这也是古代女性文人受业修习情况的普遍写照。她们早年间女德与诗文同修,在具有一定文化基础之后则终止诗文的学习,专攻妇德妇功。家庭让她们学习诗文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让她们获得粗浅的知识储备,避免目不识丁的情况。能够真正将女性纳入家学传承体系,与男性成员一视同仁地进行教育的家族少之又少。在这种普遍背景下,女性作者要想出类拔萃、比肩男性文人创作水平的难度也因此倍增。清代沈善宝《名媛诗话》自序:“盖文士自由即肄习经史旁及诗赋,有父兄教诲,师友讨论;闺秀则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27〕她陈述男女自小所受教育内容和环境的显著区别,也阐明女性文人进行创作的艰难程度。
女性只能在社会观念夹缝中的狭小空间内进行活动,寻求传统与创新、顺从与反叛之间的平衡,同时也是对自身声名、品格与文学作品的保护。清代恽珠《闺秀正始集》序:“昔孔子删诗,不废闺房之作。后世乡先生每谓妇人女子职司酒浆缝纫而已,不知《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妇德之下,继以妇言,言固非辞章之谓,要不离乎辞章者近是,则女子学诗,庸何伤乎?”〔28〕尝试发出迥异于传统观念的声音,为女子学诗争取合理性。但她又言“是集所选,以性情贞淑、音律和雅为最,风格之高尚其余事”,〔29〕依然对传统有所妥协,显示出折中态度。陈芸《小黛轩论诗诗》序云:“方今世异,有识者咸言兴女学。夫女学之尚,蚕绩针黹,井臼烹饪诸艺,是为妇功。皆为妇女应有之事。”〔30〕对女性的教育日益获得重视,但教育内容与目的依然未能突破既有范畴。室名常用“琴余”“绣余”“绣墨”之语,并为作品集冠名,表明虽从事采藻但未忘本分。当然其中也有先后轻重之分,文学终究只是女红琴艺之余的消遣。部分女性使用“吟秋阁”“藕香吟馆”等将诗文创作活动嵌入其中的室名堂号,表明文学活动与个人生活之密切联系,但同时也用具有女性用语色彩的词语进行修饰,以求中和。清代左淑芬“度金针室”、徐蕙贞“度针楼”则有双关之义,既可指女红活动,亦可解读为用元好问《论诗》中“度金针”之典指代文学创作活动。虽然多种室名表达方式不一,但其共同点在于女性通过室名堂号表明自身的价值观念,试图达成顺从与反叛之间的平衡。
另外一小部分女性选择直接反叛。如明代邹赛贞号“士斋”,《名媛诗归》记载云:“博雅好吟,每有奇句,见者以为无愧能言之士,因号曰士斋。”〔31〕“士斋”一名突破了女性室名堂号应有之意和应有之貌的限制,但同时也表明文坛仍存在严格区分性别的文学评价体系,即以男性评价体系评价女性作者,暴露出时代观念的局限。王诗龄的“谷应山房”、李端临的“红余籀室”则走得更远,虽是女性室名堂号,却也在它们的主人从事印刷出版行业时作为书坊的名称。〔32〕闺阁名号突破了围墙的限制,成为市场流通中的商业符号。女性文人既有对传统观念的反叛、对文学事业和自由的争取,也有对时代和观念的无奈受限。总之仍值得肯定,她们对于女性文学地位的提升和女性文学创作自由空间的扩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语
本质上,室名堂号所搭建的虚拟空间是在实体建筑之上主体意志的增添,是一种以想象方式所描绘的建筑景观。虚拟空间与实体建筑间的关系既可能是实指,即为主人居住的实体房屋;也可能是虚指,是主人基于自身需求而重构的精神空间;还有可能是虚与实的相互交错,是主人对实体房屋的部分修饰。男性可自由穿梭于家庭与社会之间,女性则居处于内,个体与房屋空间的结合更为紧密,并呈现出更为生活化、非事务性的联系。与此同时,社会对女性的隔离禁闭并非与外界的绝对隔绝,其界限并非固定,亦非不可渗透,女性仍能通过某些方式穿过隔离进入社会,但大部分时间里,女性都居于家中。“等级秩序试图用禁闭来控制妇女,却在这个过程中制造出了抵制这一控制的私人空间。”〔33〕书房代表教养和优雅男性气质,女性则更多地归属于卧室,她们处于公共领域之外,但又通过婚姻合法地成为家中权威。女性对这片私人空间拥有充分权力,包括为其命名的自由及承载其上的情志和喜好。同时,这片空间又成为她们的一方天地,在实体或虚拟空间中,她们皆享有较充分的创作自由。由室名堂号划出的精神空间实际上是对女性文学创作行为的承认和庇护。
女性同男性一样进入文学创作领域,亦使用室名堂号为作品集命名,社会性别的界限在这一行为上有所模糊,但她们所使用的室名堂号内容往往又带有强烈的女性特征。与印刷业发展和女性文学创作增长同时的是女性名字注定被父系和夫系姓氏掩盖的时代背景。女性作者通过室名堂号达成的对自我的认知、彰显和再命名,是她们对自身话语权的强调,是女性生存状态的侧面之一。明清时期,“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步苏醒,滋生较为强烈的才名焦虑,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独特的价值判断体系和自我评价”。〔34〕女性带着她们自己的话语内容及其评判标准主动进行社会意识的建构,可见中国古代女性并非完全遮蔽于父权和夫权之下,而是文化形态与社会秩序的积极参与者。“虽然无可否认妇女才华没有被儒家传统正式认可,但我认为,用‘压迫’和‘受害’去形容她们的处境是不恰当的。因为无论‘压迫’或‘受害’这种被动式,只能通用于身处儒家文化之外的异类。但无论是闺秀也好,名妓也罢,她们本身就是儒家社会的一份子,也是儒家文化的产物。她们是在体制之内,灵活运用既有的资源,去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35〕女性文人以“香草美人”的室名建构自我形象,以将家庭和亲缘关系加工为室名的方式标注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以室名堂号表明对社会观念的认同或反抗,其要旨都在于女性如何在受限制的生活空间中对自我的探求和落定,即明确自我的取向与抒发自我的情志。她们不仅以清晰的自我定位获得内心安定,而且构建出一个面向女性群体、面向文坛乃至整个社会的主体形象,创造出象征其丰富精神世界的文化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