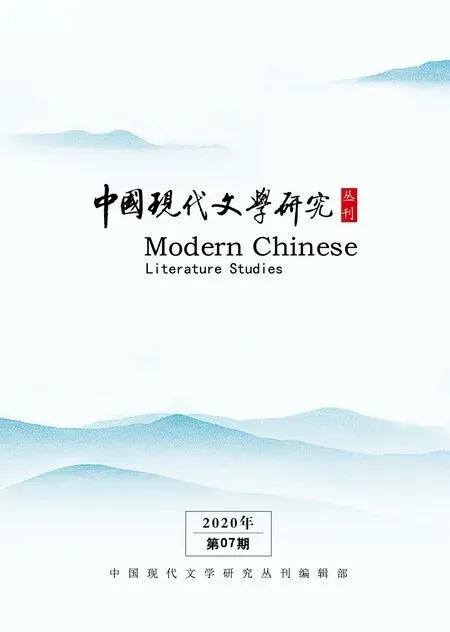附:新文学之过去现在与未来
2020-02-27
新文化运动之一种是文学革命。目的在解放文体,使与语言接近。且用此种文字辟谬理惑,扫除思想界杂乱腐化积习,与旧社会作战,改造社会,虽理想幼稚,却健康坚扑,不可轻视。运动勃兴,因之为新书业开辟一条道路。但当时个人作品虽能影响其人社会地位,与商业却不发生多大关系。写作者即十分认真,依然近于“玩票”。作者求感情出路,人道主义支配了一切作者的感情。
文学被肯定成为商品之一种,在市场中普遍流行,作品且从花样翻新上吸引读者,约在民国十三年左右。因其可以为商品,从业者便较多。新闻政策或变相新闻政策(批评)盛起,作家鱼龙百状,新文学作者于是在社会上成一专业。从前玩票者多收手歇业,无业者又从此得一生活出路。文学思想也因之解放,浪漫派大有势力。新文学读者则各以因缘而有爱憎:此或以为前途光明,彼对之十分悲观。或反对,或拥护,两者皆刺激了出版者,膨胀了一时新书业。
新文学运动原与革命思想不可分开。文学成为商品后,虽略有变动,然“反抗当前一切,倾心未来”这种情形到某一时自然会调协一致,因之十五六年有“革命文学”发生。它的目的是对现实世界正眼的看,大胆的否认,破坏一切,在瓦砾堆上,重新建设一切,革命文学促进了中国革命,革命完成,却结果了革命文学的生命。若就现在成绩言来,事亦明显易见。它虽有个健康理想,可以使人忘掉“过去”,倾心未来;它虽使新文学从“游戏”地位转变成为“工作”,但活动时间究竟太短,世人对它希望又太大,时间短无从产生好作品,希望大商人与作家即不免利用时机通力合作将一切货色标明“伟大作品”发卖。加之“革命文学”与“革命政府”目的分歧,难与并存。在上既禁止,在下则厌弃,作家入狱,商店改图,革命文学,不得不关门歇业矣。
文学如“扫帚”观念受环境限制后,于是避重就轻,有人将文学当成“陀螺”,来玩陀螺。因之到廿年前后,有幽默问世。幽默者笑中有刺。作者思想感情既动辄有干宪令,加以拘束,作者从事幽默正如玩陀螺认为可以健身,无可奈何,聊以解嘲而已。惟作者即甘心作东方朔,今之汉武帝实无需此弄臣。长此幽默下去,非事势所许可。且玩陀螺之事,于作者诚能心灵健康,然其艺易学难精。刊物既定期出版,庸手伴奏,事必不免。虽有人大言不惭,以为杂文时代即伟大时代,观众非傻子,终有厌倦之时。于是聪明人“性灵”独举,使明人小品文集在廿四年成为市场上唯一点缀物。此事说来亦可怜,亦滑稽。惟在目前,当事者固亦俨然以一战士模样,留印象于多数人脑海也。
幽默需有对象,对象即不过问,观众略感厌倦,即难再从事幽默。性灵惟有自己,无当前忌讳,无历史缠缚。作者置身租界,倾心大明,故文章亦从容潇洒,自得其乐。与流行读经风气且俨然对□,具有革命意味。一时热闹,意中事也。惟“杂耍”终为杂耍,明眼人多知之。杂耍容易热闹,亦不过一场热闹而已。
东方朔,陶潜,生于汉晋,其行其言,□可同情□。□在一九三五年间,中国文坛,尚只□□名士,海上文豪,慕东方朔之谐趣,仿陶渊明之高雅,用出版物散播此种不三不四思想态度于大学生中学生间,同大多数中国与水战与饥饿战,与社会理想战群众相对照,未免令人寂寞。人有自甘作陀螺,于己,意谓玩物即足以见志,于人,复谓玩物不足以丧志者。见其志“与人无争”,所以事上,为生存计耳。认玩物不足以丧其志,所谓“诱之使来”告其不必害怕是也。与人无争,所以事上,不必论。诱之使来,所以谎下,实大可畏。点缀此末世,名士文豪已不少。中国目前所需要者,乃有感觉有血气对一切事肯认真之“人”,不是个人主义遇事得过且过白日做梦之“文人”。
中国新文学之“未来”实有待于中国青年取舍抉择。为陀螺?为扫帚?玩隐士?做活人?皆决定于青年人之理性健康与不健康。
廿四年双十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