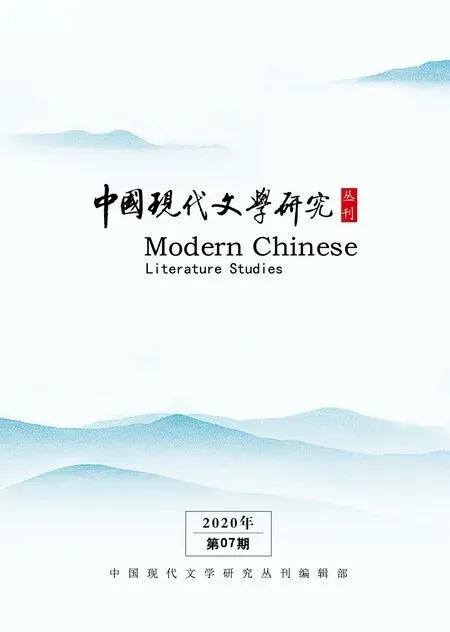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观看之道”
——评唐小兵《流动的图像: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再解读》
2020-02-27
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主义视觉文化不仅在西方的主流话语中,而且在当今中国的后革命式话语中,或被妖魔化为冷战时期“红色中国”的专制性产物,或被简化为“需要否定或者遗忘的东西”①。而以往的西方视觉文化研究理论,在本身存在诸多局限②的同时,又难以对那一时期中国的视觉秩序与多质结构进行在地化与历史化的合理阐释。出于对现有的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研究范式的质疑与反思,唐小兵的《流动的图像: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再解读》(以下简称为《流动的图像》)在延续与完善其1990年代开创的“再解读”思路的基础上③,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视觉艺术发展状况的梳理,以一种“考古学式的眼光”来解读“不同时刻的社会文化所面临和力图解决的问题”④,从而借助“文化生产方式”的框架来廓清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观看之道。这样的尝试与解读,无疑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视觉文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研究启示。
一 木刻艺术的危机及其克服
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于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研究,更多地偏向于对电影、杂志封面以及宣传画的解读,而唐小兵的《流动的图像》除了借助电影这一媒介之外,还选择从鲜有人触及的木刻等视觉艺术形式来切入。之所以会选择木刻,则与其之前关于1930年代的木刻研究息息相关,在十年前所著的《现代木刻艺术:中国先锋艺术的缘起》(以下简称为《现代木刻艺术》)一书中,唐小兵以历史化的方法梳理了左翼时期木刻运动的发展轨迹,围绕着艺术理论、艺术运动与民族—国家危机之间的层层关联,他试图探究木刻是如何成为先锋性的革命艺术的。而在该书的引言部分,他对于版画艺术在1950年代之后的角色转变,只是做了简单的提及,因此在《流动的图像》中,他选择延续《现代木刻艺术》的历史脉络,对这一部分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探讨。“革命之后”的新中国,不仅是在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方面⑤,而且在革命艺术的创造与实践领域,都面临着向社会主义转型,而后者又隐性地内在于前者之中。在1930年代的左翼以及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中,木刻曾发挥出了其他艺术形式所望尘莫及的先锋推动力与革命动员力,“成为现代中国成果最为丰富的艺术运动”⑥。然而,正如老一代版画家力群所指出的,这一革命艺术在解放之后仍然是在“用旧的心情歌颂新的生活……以旧的方法来描写新的内容”⑦,既无法实现从乡村到城市基座上的顺利转换,以便切实地展现新时代城市工人的生活风貌,也无法从一个颇具反抗性姿态的艺术运动,转型为一种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保持一致的、具有积极意义与教育功能的创作实践。因此,这不仅表现了木刻工作者对于艺术发展滞后于时代形势的普遍性焦虑,而且也“反映了隐含在新的文化生产方式之下的结构性紧张”⑧。如何使木刻在新中国时期重新焕发出曾有的先锋性与革命性光芒,成为这群艺术家努力去克服的危机。
一方面,通过1955年围绕梁永泰的《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所引发的争论,以及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版画运动等实例,唐小兵指出,包括木刻在内的社会主义视觉艺术,并非是肤浅的装饰性艺术,也并非是现实实录的自然主义艺术,而是体现着新中国的革命传统、国家身份与民族想象的新型艺术,这样的视觉艺术所反映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不是一套被敬奉为不可逾越的价值和规矩,也不应该是一道用来抵挡新旧替换和社会变革的屏障,更不能被用来掩盖对新的社会秩序的挑战和攻讦”⑨,而是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同步的集体性事业;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视觉艺术不仅仅是描写人民现实生活及精神风貌的艺术,而且是可以成为由劳动群众自主创作的人民性艺术,从而“克服艺术与生活之间的那根深蒂固的隔阂……消灭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等级藩篱”⑩,使人民群众也能亲身参与到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改造与创建中来。
另一方面,通过对王式廓《血衣》的探讨,唐小兵指出了木刻艺术危机的克服,不仅仅是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版画事业,更是需要在打通视觉艺术门类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木刻艺术的革命传统:作为“新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美术的成功典范”,王式廓1959年的素描作品《血衣》并非凭空出现,对于土改诉苦这一革命场景的再现,既来源于其自身在延安土改运动中的采风经验与创作实践⑪,也包含了他对以古元、江丰为代表的延安木刻艺术的借鉴与传承⑫,但他又对既有的延安木刻艺术传统进行了一次调整与超越,使《血衣》成为一幅具有穿透性视野和改造性力量的全景式历史画,它以形象化的“概括”来展现整体、营造观感,更以感官性的思辨来捕捉发展趋势、指向潜在行动,从而使社会主义视觉文化不仅成为“更系统、也更有纪念碑效果”的“新人民文艺”,也获得了全局而有效地深入生活与干预生活的“新的直接感”。就如唐小兵所指出的,这种具有跨媒体性质的社会主义视觉文化改编策略,“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不断协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富于革命意义的观念和传统的方法习俗相碰撞,耳熟能详的文化形式被吸收调整,为新的、突破旧有框架的内容提供表现空间”⑬。
借由木刻艺术危机及其克服,唐小兵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主义视觉文化对革命视觉艺术的重塑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人民对文化危机状态的强势反应,既离不开国家的协调组织,也离不开艺术家自主介入生活的配套性试验,更离不开将其发展为人民性艺术与革命性实践的诸种努力。由此,一个新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艺术范式与视觉秩序得以生成,并处于不断地更新与完善之中,这样的社会主义视觉文化既是一种艺术创作,更是一种社会实践,“不仅仅是怎样看,同时也是看什么,这也就使得创造社会主义视觉文化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弹性的过程,有着不断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与反思”⑭。
二 “山水画”改造与“观看”的限度
正如唐小兵在《流动的图像》的结语中所说,他的这番研究旨在让“从远处看中国”的西方世界,能够摆脱狭隘偏执的政见预设、克服寓言式思维的局限,能够站在“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的位置上……把中国看作一个活的文化生态,而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铁板一块”⑮,从而在这样一种范式转换下获得对当代中国的“多重印象”。毋庸置疑,唐小兵的研究的确在批判性地反思西方文化偏见的同时,确立了一种历史化地、历时性地解读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观看之道。不过,唐的观看之道显然是针对西方而言的,对于其中的暧昧性与共时性问题却并未留意,而这既揭示出了其研究的限度,也彰显出了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难解议题与全球语境。
比如解放初期的国画改革。作为传统的视觉艺术,国画并未像木刻那样经过左翼文艺乃至延安文艺运动的洗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艺术的“前哨阵地”,它即使到了解放初期也未改之前的临摹性习气与臆造式想象,仍然是含有文人趣味的“八股”艺术,既不能与新中国改天换地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也不能“给人以革命、进取、振奋、向上的启发”⑯。在《流动的图像》中,唐小兵关于这一部分的探讨只是借此指出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视觉文化,并非是简单地把政治权威或艺术规范强加于艺术家身上,这之中艺术与政治的有效融合与激烈冲突,体现出的是艺术家对新身份的认同与不适,他们不仅需要在自我改造的过程中培养出社会主义的眼光,更需要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具有生产性与影响力的新型视觉艺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推进的话,就会发现对这一话题的阐释不限于此。
在《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以下简称为《社会主义与“自然”》)一书中,朱羽试图通过毛泽东时代的山水画改造来说明,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传统视觉艺术的再造是试图以革命的“自觉”态度来遏制异己的“自发”力量,使社会主义视觉文化在“去自然化”与“再自然化”这一辩证性的改造中实现良性的循环与惯性的运转:一方面,“新旧转型意味着‘旧’始终没有完全缺席”⑰,传统山水画中的山水表象并非是完全处于批判位置上的旧范畴,其中民族国家和隐逸话语的政治象征性,联结着反抗殖民统治、创建平等家国的共同体问题,蕴含着新政治体生成之意味的传统山水画与新中国的成立乃至愿景,产生了一种超越历史具体情境的同构性和共通感,可以说,对山水画此一传统的重新承继与赋义,能够“使高度风格化的自然形象摆脱特殊利益和趣味的束缚,使之同普遍的历史主体产生联系……使山水画从虚无的艺术市场中解放出来,使之服务于新的集体认同的塑造”⑱;另一方面,新山水画在发现“社会主义山水风景”与展现文艺民主化方面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它能够将集体劳动整合进山水表象之中,而这一特殊的创作构造既突出了劳动者前所未有的崇高的主体形象,也彰显着社会主义新中国未有先例的宏伟的建设事业,使山水画既不再是民族国家的神话性展示,也不再使其具有与普通人民相疏离的精英味与权威感,这样的改造始终与人民群众的政治主体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从而给集体性实践留下了巨大的想象与激励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朱羽的分析为我们指出了这一对传统视觉艺术的再造过程又不得不时刻面临着革命与自然之巨轮那无法严合的缝隙,这既联结着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发展主义三元构造中的动态矛盾,也指向了“无名”性自然向“共名”性革命的艰难转化。其中对国画“意境”的“招魂”行动揭示出了山水画那不只限于视觉的特点,就是那多一点的剩余物,既能使山水表象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赋魅,也能对其造成袪魅化的威胁,从而使新山水画永远在对革命进行建构与解构的两极空间中滑动。除此之外,不能根除的知识与教养、小众化等问题都使得新山水画具有矛盾的特质与不稳定的结构,最终指向的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视觉文化那些尚未解决的难题与难以平衡的困境。
总而言之,朱羽以山水画改造为中心的展开式分析,突破了唐小兵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观看之道,使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传统视觉艺术的再造是一种辩证性的认识与改造过程,它既并非采取着完全否定的粗暴姿态,也并非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完美效果,而是成为一种具有层次性、创造性乃至暧昧性的文化实践。然而,如果我们再将山水画放置于共和国七十年的时段中做一次历时性的考察,就会发现这一视觉艺术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后,并非像版画一样走向被边缘化的衰落窘境,而是伴随着西方艺术的冲击、商品市场的促进与现代都市的兴建,在继承文人山水与红色山水两大传统的基础上迎来了革新的生机,“这种在多元文化中反思百年得失中呈现的开拓与复归并行的又一变”⑲不但破解了图像时代的迷思,而且获得了东西方观者的认同与青睐,这样一种蓬勃发展的趋势似乎离唐小兵预设的观看之道渐行渐远,由此也给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研究留下了更多的疑问与思考。
再比如毛泽东时代的展览文化。据笔者了解,近十年来,除了唐小兵的《流动的图像》之外,国外学者对于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研究还延伸到了立体视觉艺术的领域。如洪长泰的《毛泽东的新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政治文化》一书,他通过考察中国革命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这样的革命性建筑物来探索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⑳,虽然这一借鉴自法国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国内学界仍然属于前沿性的,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相比较而言,何若书的《策展革命: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陈列》一书则在对毛泽东时代的展览文化㉑进行历史化论证的过程中排除了两种叙事模式的干扰,透过中共一大会址、工人新村“蕃瓜弄”、阶级教育展览会等具体的展览案例,她触碰到了社会主义展览文化的人民性、实践性与在地化的特质:这一沉浸式的视觉艺术,一方面通过将具体的真人实物组成一套系统化的革命道理,来激发参观者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认同感,并使其以新的眼光重回至日常生活当中,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上来,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作为教育群众和动员群众的展览,成为回响着民族—国家斗争与解放之歌的“记忆之场”,但它“不仅是革命的教科书,也是革命的指导手册”㉒,有着揭示过去、指导现在、形塑未来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具有广泛参与性的视觉艺术,也“会根据当地的情况进行调整,并呈现出个人故事,而无论怎样引用,参观者都可以将这些经验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事物上”㉓,这就有助于使展览始终切合于当地群众的实际情况,从而使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精神能够在基层当中得到真正的彰显与贯彻。
可以说,何若书这番选题新颖、论证客观的探究,既能够使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展览文化有改观性的认识,又能够便于我们将这一文化遗产应用到当代博物馆策展的运作机制中,从而使当代中国的策展“在与观者的持续互动中传达共识的价值和理念,影响观众的认识方式,达到学习和教育的效果”㉔,使革命的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并加以创新,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具生命力、吸引力、感染力与凝聚力,最终实现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实际上,若我们将毛泽东时代的展览文化与同时期美国的展览文化进行共时性比较的话,就会在全球冷战的格局中凸显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不同之处。与毛泽东时代的展览文化不同,同时期的美国试图以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形式与机械复制的工业设计,创造出象征着美国精神的消费文化,并通过展览的方式向全球推崇所谓的“美国之路”与“美国的生活方式”,而这样的展览文化在为大众制造日常生活之共同理想的同时,也刻上了冷战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迹,它将“自由对暴政”的冷战意识“包装在现代经典文化的外衣下”㉕,并且使美国毫无疑问地“成为‘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峙则给予了其进一步深化自由主义传统的机遇”㉖。相对于美国个人化与消费性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展览文化,毛泽东时代的展览文化则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其鲜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虽然二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但是后者意在强调文化实践的集体性与基层人民的参与性,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文化品质使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视觉文化“呈现出整全性的形象”㉗。因此,透过两大主义视觉文化的对比,能够为我们展现出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另一种观看之道,从而也为该领域的研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与空间。
三 转型困境、“活的传统”与现实之用
在《流动的图像》第二章的尾声,唐小兵提及了当代画家曹勇2007年对《血衣》所做的一次戏拟式重画,正是这含有巨大差异的转型,不仅使得社会主义视觉文化得以显现,而且也揭示出了当下中国视觉艺术所面临的后现代困境:要么它是一种迎合市场的、具有消费性质的大众化商品,要么它成为拒斥市场与政治的、具有冷眼旁观性质的个人化创作。那种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视觉文化所带有的“积极主动地把艺术与生活、自我与他人结合在一起的愿望”㉘,在21世纪中国的视觉艺术中仿佛丧失了某种共鸣的可能,甚至以冷嘲热讽、口诛笔伐的架势来对其加以否定、漠视与遗忘。
就如唐小兵所说,以视觉化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建构中国文化、传承中国精神,“不完全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而是和深层次的文化形态和社会心理有关”㉙,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家国意识、革命传统与人民属性,并非是远离大众日常生活的抽象概念与宏大叙事,而是渗入其中的贯通的精神血脉与细腻的情感结构。只不过个人的这份对中华民族的担当感,在当下的中国,只有在其遭遇整体性危机的时候才能够更为强烈地凸显出来。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借助艺术文化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激发大众的主体性意识与实践性能量,从而使“劳动创造世界”“人民创造历史”不光成为“一种史诗般的表达”㉚,而且可以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精神语汇以及影响其行为抉择的正面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与人民之间建立有效的互动与勾连,才能发挥文化紧密联系现实和保持世俗关怀的深刻意义,而不至于沦为象牙塔中的无用之物。
然而,这样的探索与创造,并非是无本无源的先例,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视觉文化还是一个不可遗忘、尚可承继的“活的传统”,如果能够对其加以适当地借鉴并有效地运用,那么也许我们就能在克服当代中国视觉艺术现有危机的过程中、在建构真正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上向前迈进一大步。因此,围绕着唐小兵的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研究所做这番的考察,其意义就在于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规避本质主义与僵化思维的戕害,能够以历史化的研究方式摸索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观看之道,并且有力地阐释它们与特定历史语境的相互关系,深入地开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繁复图景与变动态势,从而可以为现有的中国文学/文化研究指出进一步思考的方向,开拓出可以深入探索的空间,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持久发展提供一份参考与借鉴。
注释:
①④⑧⑨⑩⑬⑭⑮㉘[美]唐小兵:《流动的图像: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再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48、50、76、36、31、367、138页。
②比如图像研究与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分离,图像的生产性与消费性的本末倒置,以及参观者批判性的观察与内在参与的可能被置于历史叙事之外等。
③1990年代的“再解读”思路更多的是借用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等后现代理论来“另写”以延安文艺为核心的大众文艺,相对于当时的文学研究范式,其突破点在于:一方面,它将延安文艺从狭窄的而又纯粹的政治运动框架中释放了出来,赋予其“意识形态症结”与“乌托邦想象”的双重含义,肯定其作为文化革命所具有的深刻的现代意义,即“反现代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它“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后面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解读的过程便是暴露出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被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和暴力”,从文学/文化生产机制的层面对历史元叙述和“奠基性话语”(foundational discourse)进行挑战与超越。当然,“再解读”思路在做出研究范式转向方面的重大贡献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关史料的支撑,加之沉重的后现代理论枷锁,使其在论证上出现了历史疏离化的倾向,在这种冷眼旁观下,“‘十七年’于是再次经历了‘非历史化’过程而变成后现代理论的文学殖民地……所有曾经具有‘历史丰碑意义’的革命文学都失去了丰碑的地位”(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2页)。尽管唐小兵自己认为当年的《再解读》并不缺乏历史感(李凤亮、唐小兵:《“再解读”的再解读——唐小兵教授访谈录》,《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但是我们在与《流动的图像》对比中可以发现,后者将深刻同情的“历史的眼光”放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上进行强调,并且以一种更为“沉着地进入历史”的研究姿态来解读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
⑤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69页。
⑥[美]唐小兵:《现代木刻运动:中国先锋艺术的缘起》,孟磊等编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⑦力群:《论当前木刻创作诸问题》,《人民美术》1950年第6期,第25~27页。
⑪指王式廓1947年的套色木刻《改造二流子》。
⑫指古元1943年的木刻《减租会》和江丰1944年的木刻《清算斗争》。
⑯杨竹民:《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和成就——与徐悲鸿先生讨论中国美术遗产问题》,《新建设》1950年第6期,第55~57页。
⑰⑱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36页。
⑲薛永年:《百年山水画之变》,《艺术研究》2007年第1期。
⑳在洪长泰看来,政治文化“指的并非政治体制和官方架构,而是指由最高权力机关创造出来的一些大众的共同价值观、愿景、态度和期望。这些集体价值观强调了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影响,而且它们是透过符号、仪式、语言和图像表达出来……但创造的过程却绝非单向的、自上而下的压制,决策者必须不停地调整策略,以应付来自下层的回响,甚至抵制。因此这是经过协商的过程,而且不断改变”(洪长泰:《毛泽东的新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政治文化》,麦惠娴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
㉑在何若书的理解中,展览不仅仅指代展览会、社区展示这样的短期性展览,也包括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这样的永久性机构。
㉒㉓Denise Y. Ho,Curating Revolution:Politics on Display in Mao’s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p.4,17.
㉔隋文馨、肖薇:《中国当代博物馆策展运作中的文化机制研究》,《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3期。
㉕赵容浩:《美国文化冷战中的MoMA设计展——以“美国艺术50年”展览为例》,《装饰》2016年第7期。
㉖金衡山、廖炜春、孙璐等:《印迹深深: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和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㉗罗岗:《联通“媒介革命”与“社会革命”——社会主义文艺转向对“视觉文化”研究范式的挑战》,《东方学刊》2019年第2期。
㉙[美]唐小兵、罗岗:《当代中国艺术背后的“故事”——唐小兵教授访谈录》,《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㉚张炼红:《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