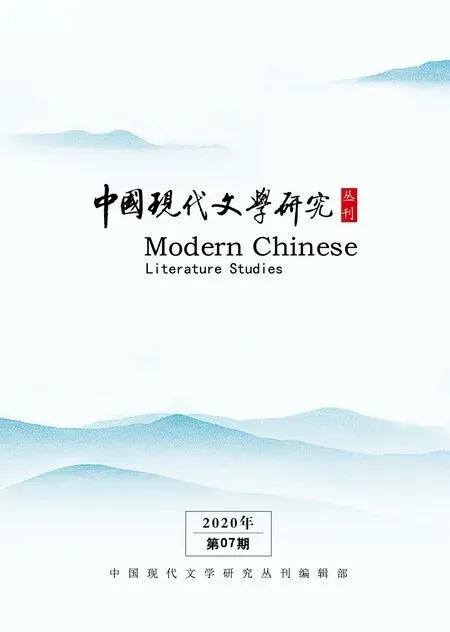文化取向与“五四”新文学译者“直译”主张的形成
2020-02-27
内容提要:晚清至“五四”时期经历了中国翻译史上的文学翻译高潮,翻译手法大体经历了意译为主到直译为主的变化。以思想史的视角观察,这一变化主要由两方面促成:首先,新文学译者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判断,形成了一套西优中劣、二元对立的论述模式。其次,新文学译者显示出一种“文化整体意识”,即认为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两种对立的文化无法兼容。基于“西”优“中”劣和文化整体不可拆分的判断,新文学译者显示出全面西化的文化取向;反映到翻译上,就是注重与原文对等的“直译”。将“直译”树立为翻译基本规范的同时,新文学译者还使用“意译”来指称严复、林纾等晚清译者调和中西的翻译,并在“直译”和“意译”之间也建构了具有伦理色彩的价值对立。
一 引 言
晚清到“五四”前后,是中国翻译史上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翻译高潮时期。相较于晚清普遍不忠于原著的译法,“五四”时期的翻译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直译”的推崇,即注重译出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的严格对等。茅盾就说过:“‘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①关于晚清的所谓“意译”风尚,以往已有不少讨论②;但直译何以从“五四”开始成为主流,却很少引起关注。笔者认为,这种现象背后包含了一种认知上的预设:忠实是翻译的“常态”,只有晚清那种擅改原著的译法才是值得研究的“反常”现象。有论者说,“新文化运动”所崇尚的“现代理性和科学精神”将晚清以来的翻译规范“推上了审判台”③,使“‘信’的本质逐渐得到确认”④。这其实就是把忠于原著(“信”)视作翻译的天然属性,将“五四”确立的翻译规范看成对晚清“意译”之风理所当然的纠正。假如抛开这种“原著中心”的翻译观念⑤,将“五四”新文学译者直译主张的产生置于思想史的脉络中审视,我们不难发现这和晚清的“意译”风尚一样是很值得仔细考察的课题。
晚近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一种文化转换⑥。译者的文化取向——即看待译出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态度——势必影响其对翻译的理解和翻译活动的开展。“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⑦,新文学译者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看法较之晚清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翻译思想必然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本文以“五四”译者的文化取向为观察视角,试析“直译”主张形成的思想根源。
二 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和作为“西化”(进化)方法的翻译
直到1850年代,中国的一般知识阶层都习惯用“夷”来指称西方事物(如“夷技”“夷语”“夷务”等),其思维模式仍不出“夷夏之辨”,轻蔑意味是显而易见的⑧。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刺激了国人的神经,随着一批有识之士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夷务”改头换面成了“洋务”;“西学”这一用来描述西方知识的地域性指称也逐渐普及⑨。“洋务”和“西学”这两个称谓都没有明显的褒贬色彩。甲午一役后,西学的地位空前提升,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⑩的景象。这一时期开始有人用“新学”概称西方知识,最著名的莫如张之洞在《劝学篇》里的表述:“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⑪张之洞所称的“新学”和“旧学”当然没有扬西抑中的意思,只是因为中学传世在前而西学输入在后。但中西文化的地域性指称一旦变成时间性指称,就为“五四”时期以社会进化论为逻辑起点的价值阐释提供了可能。从这个角度看,由“西/中”到“新/旧”的术语变换已经埋下了中西文化价值对立的种子。
“五四”时期,留学归来高张“革命”大旗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论述,形成了一套二元对立的模式。《青年杂志》1卷1号头条刊载的《敬告青年》便奠定了这一基调:该文开篇即强调中国赞赏“少年老成”,西人主张“年老而勿衰”,其本质乃是观念上的“陈朽腐败”与“新鲜活泼”之别⑫。——“新”和“旧”经过“新鲜活泼”和“陈朽腐败”的修辞性发挥,已不仅仅是表示时间先后的中性词。作者陈独秀继而开列了六组对立,分属“新鲜活泼”和“陈朽腐败”的具体表现:
新鲜活泼: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
陈朽腐败: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想像的⑬
通过这六组对立,陈独秀对“新”和“旧”作了诠释和价值上的判断。他极力推崇“新陈代谢”,强调“新鲜活泼”者“适于今世之争存”,“陈朽腐败”者“不容留置于脑里”⑭。虽然行文中没有把这些对立直接同“中”“西”对接起来,但整篇文章关于“陈朽腐败”与“新鲜活泼”的讨论正是由中西方的观念差异引出的;而且就其举例来看,“陈朽腐败”的部分都以中国的传统思想为例,如“忠孝节义”“罢黜百家”“五行生克”等;而“新鲜活泼”的部分尽属西方,如“人权平等”“进化论”“实验哲学”等。
如果说《敬告青年》表达的中西对立还不那么直白,陈独秀在紧随其后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便作了明确表态。他指出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就是“古代文明”和“近世文明”的差异: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洋文明”“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而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⑮。同期登出的《新旧问题》更是直接把“西/中”同“新/旧”对应起来:
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⑯
“新”“旧”文化分别被等同于“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中西文化的冲突被视同新旧文化的冲突。原本表示时间顺序的“新(学)”和“旧(学)”在《新青年》的叙述策略中被赋予了价值判断;“外来之西洋文化”和“中国固有之文化”又通过与“新文化”和“旧文化”的代换,形成了好和坏的对立。
晚清以来,文学被认为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从一开始就被视作“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⑰,托付了重大的社会意义和政治功能。作为这场运动的核心议程,“文学革命”理所当然地将中西方文学也树立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继《敬告青年》和《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之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主义”承续了二元对立的论述模式: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⑱
在这篇著名的“檄文”中,陈独秀对中国历代文学进行逐一批判,他认为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应该“推翻”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⑲。虽然没有说明应该建设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是指什么,但文章最后希望文学界的有识之士能“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向造成“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的文学复古势力宣战。很显然,“虞哥”(雨果)、“左喇”(左拉)等人在作者眼中便是“国民文学”“写实文学”与“社会文学”的榜样。——这一判断是否合乎文学史的事实姑且不论⑳,需要指出的是:在“贵族文学/国民文学”“古典文学/写实文学”和“山林文学/社会文学”以及那一连串褒贬分明的修饰词背后,正是中西文学的二元对立。
罗家伦在《新潮》杂志发表的《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1919)一文中对中西方文学的概括,更是“棱角分明”的二元对立结构:
西洋文学是切于人生的,中国文学是见人生而远避的;西洋文学是为唤起人类同情的,而中国文学是为个人私自说法的;西洋文学是求真像的,而中国文学是说假话的;西洋文学是平民的天然的,中国文学是贵族的矫揉的;西洋文学是要发展个性的,中国文学是要同古人一个鼻子眼出气的。㉑
在“新文化运动”发难者的论述中,中西文化的差异经过选择性的夸大和演绎,被塑造成壁垒分明、优劣判然的对立结构㉒。既然西方文化“美隆如彼”而中国文化“枯槁如此”㉓,改变的方法是什么呢?
将文化的地域差异理解为时代差异,实际上是将世界文明的发展视为同一的、无差别的线性过程。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㉔。我们知道,这种观念背后的学理依据是进化论思想——更确切地说,是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将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这一学说正是“严复版”进化论——《天演论》所宣扬的㉕。中西文化对立的进化论本质,深刻地影响“新文化”建设者们为消除这些对立而设计的方法。
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发表《译书感言》,开篇即说:
现在中国学问界的情形,很像西洋中世过去以后的“文艺再生”时代,所以去西洋人现在的地步,差不多有四百年上下的距离。但是我们赶上他不必用几百年的功夫;若真能加紧的追,只须几十年的光阴,就可同在一个文化的海里洗澡了。他们失败的地方不必学,只学他成功了的。他们一层一层进行的次序不必全抄,只抄他最后一层的效果。他们发明,我们摹仿。他们“众里寻他千百度”,我们“俯拾即是”。所以我们虽然处处落人后,却反而得了个省事的路程,可以免去些可怕的试验。至于我们赶他的办法——省事的路程——总不外乎学习外国文,因而求得现代有益的知识,再翻译外国文的书籍,因而供给大家现代有益的知识。照这看来翻译一种事业的需要不必多说了。㉖
面对“先进”的西方世界,“落后”的中国“只抄他最后一层的效果”,便可以把“四百年上下的距离”缩短为“几十年的光阴”㉗;而“省事的路程”就是翻译。
相应地,中西方文学被各自推向价值判断的正负极之后,对西方文学的效仿理所当然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出路。西方文学被树立为权威和仿效的模板,而翻译便是“复制”西方文学范式的有效途径。因此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最后呼吁:“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㉘周作人也认为,要建设“人的文学”,只有“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㉙。《小说月报》的一位读者说得更加形象:
中国文学害了隔食病同肺病,除了用猛烈的消化药,和换新鲜空气外没有办法。消化药是什么?就是打破一切死章句、腐思想;新鲜空气是什么?就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㉚
这一论断显然是对陈独秀“新陈代谢”说的呼应。
社会进化论将文化的发展视为无差别的单一过程,中西文化的共时性对立便转换成了历时性差异,因此翻译就不仅是“西化”的手段,更是“进化”的手段。
三 “文化整体意识”、全面西化㉛和“直译”的价值翻转
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鸦片战争后举凡提倡学习西方文化的创议,都无例外地必须回答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㉜“中体西用”说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虽然“中体西用”的正式提出是在清末,但西学东渐以来,以“中体”和“西用”相互调和的方式进行文化配置的基本思路始终未变;而两者涵盖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展,呈现出此(“中”)消彼(“西”)长的态势。直到甲午前夕,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提出在科技、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全面采用“西法”,涉及中学的只有一句空洞的“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㉝。戊戌时期,康有为所谓“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㉞,貌似兼容并包,实则因中学本已无“用”,淡化中西界限的言下之意只能是连“体”也一并西化㉟。“中体西用”论——或者说中西调和式的文化配置——已越来越无法满足改革的现实需要。
实际上,对中学和西学进行机械的拆解和拼接的文化配置方式在晚清已受到诟病。其中最著名的是严复以“牛马各有其体用”为喻,指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㊱。其实早在严复以前,仕于道咸年间的吴廷栋(1793—1873)就曾说过:
尝谓世无无体之用,亦无无用之体。有用而无体,其用只是诈伪;有体而无用,其体必多缺陷。㊲
类似的批评还来自拥护变法的海外华人思想家胡礼垣(1847—1916):
体用者,身之全量也,指一身之完者而言。谓其有是体,因而有是用也。非指二物之异者而言,谓其体各为体、用各为用也。体用有内外而无不同也。㊳
他们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体”“用”不能分离,有什么“体”就有什么“用”。
严、吴、胡三人对“中体西用”说的批判皆透露出一种“文化整体意识”,亦即将文化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此前的中国知识阶层并没有这种观念——恰恰相反,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来,无论是将文化分为“体用”“本末”“道器”还是“形上形下”,都是基于文化可分的预设。主张文化可分,就意味着可以拆解组合,可以互相调和;不可分,便只能全盘拒绝或全盘接受。“体用不二”的“文化整体意识”决定了文化抉择必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这种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普遍响应。陈独秀便一再申说:
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㊴
新旧两种法子,好象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㊵
这俨然是对严复的回应。鲁迅的这段话也颇有代表性:
因为“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
所以他的结论是:“All or Nothing!”㊶
文学上也表现出同样的观念。《新青年》第6卷第4号刊文《非“折中派的文学”》,指出:
文学只有新的、旧的两派,无所谓折中派。新文学有新文学的思想系统,旧文学有旧文学的思想系统,断断调和不来。㊷
一旦非此即彼的“文化整体意识”同中西文化的价值对立相结合,最终选择的方案只能是对中国传统的整体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1916年,当陈独秀喊出:“其足使吾人生活状态变迁而日趋觉悟之途者,其欧化之输入乎!”㊸这时的“输入欧化”必定不会再是那个移花接木、中西合璧的模式。诚如钱玄同所说:
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中华民国的一切政治、教育、文艺、科学,都该完全学人家的好样子。㊹
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两种对立的文化无法兼容,因此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该完全学人家的好样子”;而“先进”的西方文化和“落后”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巨大差距要靠翻译来弥补,那么翻译的方法也必须与这种“文化整体意识”相适应,以保证西化的彻底性。“直译”主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直译”㊺一词在清末就有人使用,但在当时是饱受诟病的做法。1902年,张之洞在提议翻译西书作为新式课堂的教材时明确反对“直译”,因为这样的译本“多诘曲支冗之词”㊻。他主张对译文进行润色,“使明白条畅,合于中国古今文法语气”㊼。1907年,有官员建议清廷翻译一些西方宗教书籍颁行各省,让民众了解西教,从而避免教案的发生。在翻译方法上,直译同样在批判之列,其理由有二:第一,“一直译之,便不成文,言之不文,士大夫均不欲观”㊽。这和张之洞的看法一样,仍是在指摘“直译”造成的语法失当。第二,“东西风俗各殊,学问好尚辄为内地人民所不经见,于是因种种之猜疑而目为邪教者有之”㊾。该官员认为,“直译”无法有效实现东西方文化的转换,导致人们对西教产生种种误解,甚至视其为邪教,最终酿成教案。这已是从语言层面深入到文化层面,指出直译在“文化转换”方面的缺陷。也有其他论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月月小说》1907年第7号刊登的《〈解颐语〉叙言》指出的是直译在传达幽默时的无力:
良以他国极可笑之事,苟直译而置诸吾国人之前,窃恐未必尽解,遑论其笑矣。㊿
不过,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在译出语文化中稀松平常的文字,经过不恰当的直译反而引人发笑。1913年5月《庸言》杂志发表的《中国人之弱点》一文中,作者指出“犬马之劳”“泥首叩谢”“亵渎清听”等汉语书面语中的谦辞“设直译为西文,见者必皆大笑”[51]。其立意固在批判中国人的“虚浮”,但也点出直译会暴露中西方文化的隔阂。同样地,曾长期担任晚清史官的恽毓鼎在日记里记录了他和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谈论《庄子》的过程,他也强调“其中寓言十九,恐非直译所能尽其旨也”[52]。对直译的排斥在文学界尤为突出,周桂笙的这段批评堪为代表:
今之所谓译书者,大抵皆率尔操觚,惯事直译而已;其不然者,则剿袭剽窃,敷衍满纸,译自和文者,则惟新名词是尚,译自西文者,则不免诘屈聱牙之病,而令人难解则一也。[53]
“率尔操觚”“诘屈聱牙”云云,几乎就是晚清文学翻译家和批评家眼中“直译”的代名词,可见“直译”在当时确实是个“名声很坏的术语”[54]。
因直译而受挫的最著名的例子,当属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在当下的文学史叙述中,周氏兄弟因为一反潮流地选择当代欧洲(特别是斯拉夫系统)的严肃文学作品而备受好评;但在当时,《域外小说集》却因为“词致朴讷”“迻译亦期弗失文情”[55]的文言直译导致“句子生硬,诘屈聱牙”[56],两册合计只卖出41本[57]。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翻译不单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互动。前文所举清廷官员以“东西风俗各殊”为由建议翻译宗教书籍避免直译、《〈解颐语〉叙言》指出外国笑话一经直译恐难引人发笑等,都是在指摘“直译”无法实现西方文化的有效转换;但到了“五四”时期,直译的上述缺陷反而成了优势:对于新文学译者而言,最理想的翻译正是能最大限度地将西方文化忠实、完整地“移植”过来的直译。直译迎合了新文学译者的文化取向,因而被树立为必须遵守的翻译规范。1919年,傅斯年在《新潮》撰文,开列翻译的“公同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用直译的笔法”[58]。他盛赞周作人“那宗直译的笔法,不特是译书的正道,并且是我们自己做文的榜样”[59]。
除了“文化转换”的失当,直译在晚清受排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直译的文本往往文不从字不顺,所谓“一直译之,便不成文”。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外语法不同,逐词逐句翻译而不加调整,势必会把外语的语法结构带到汉语中来,导致译文语句不通顺、文字不洗练,读起来“诘屈聱牙”。这个缺点到“五四”时期同样出现了戏剧性的翻转,成为新文学译者青睐直译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恰恰希望在翻译西方文学的时候,能把西语中语言形式层面的元素移植到汉语中来。沈泽民便说:
我们介绍西洋文学,一面固然是要把西洋的文艺思想来影响本国,一面却也负有把西洋的文字风体来变化本国文体的使命。那么,直译的文艺似乎在这一方面比意译的文艺多尽一种义务。[60]
傅斯年则强调在直译的过程中“径自用它的字调、句调,务必使它原来的旨趣,一点不失”[61]。这里的“文字风体”“字调、句调”显然属于语言的范畴。
究其原因,新文学译者对原作语言形式的看重,同他们所理解的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密切相关。正如傅斯年所说:
作者的思想,必不能脱离作者的语言而独立。我们想存留作者的思想,必须存留作者的语法;若果另换一副腔调,定不是作者的思想。[62]
在傅斯年看来,作者的思想和语言是二位一体、不可分离的(由此也可以看到“文化整体意识”的投射)。这也是新文学译者的普遍认识。“直译”由此被认为“是‘存真’的必由之径”[63],亦即忠实地译入原著的思想,必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其语言形式为前提。
另外,对语言形式的“直译”还可以把西语的语法“移植”到汉语中来,进而重塑汉语。“新文化运动”中,汉语常常被描述为一种陈旧的语言,无法指称新事物、表达新概念,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64];必须用精密的西语语法对汉语进行改造,形成一种欧化汉语[65]——而直译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便称赞周作人“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方法与口气”,并表示“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欧化的一个起点”[66]。周作人自己对于“直译”有这样的描述:
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67]
严格的直译,造成“中不像中,西不像西”的欧化汉语,为晚清译者所极力反对,而主张全面西化的新文学译者却可以接受,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是为改造汉语不得不做的牺牲。周作人甚至希望在译文中“杂入原文,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68],这已是从移植原文语法发展到直接挪用原文——索性不“译”了。
更进一步看,通过直译西语语言形式来改造汉语还有更深一层目的:改造中国人的思维。鲁迅的这段话常为论者所征引: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说,就是脑筋有些糊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69]
这是1931年鲁迅和瞿秋白讨论翻译问题时的表态,但此种观念早在“五四”时就已显出端倪。当时周作人就说过:
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是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70]
通过汉语的欧化来实现思维方式的欧化——这可以说是要把“西化”(进化)推进到文化的根本源头上去,以期彻底改变中国文化的“落后”局面。
四 “直译”“意译”伦理对立的建构
新文学译者一方面鼓吹以全面西化为最终目标的“直译”,同时猛烈抨击流行于晚清的中西调和式的翻译。钱玄同以其一贯的激烈口吻斥责“近来之贱丈夫动辄以新名词附会野蛮之古义”,“必不能得正确之知识”,“绝不能代表Lamark、Darwin以来之新世界文明”[71]。宗白华说得更形象:
中文名词所代表的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旧思想、旧观念和西洋近代由科学上产生的新思想、新观念,更是丝毫不相仿佛。我们若把这种旧名词来翻译一个西洋学说上的新思想,简直就好像拿一件中国古代的衣冠,套在一个簇新式的欧洲人身上,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现象。这种现象最容易引起人观念上的紊乱和误会。[72]
显然他们都把矛头指向了“用汉以前字法句法”[73]从事西学翻译的严复,尽管他们所服膺的社会进化论正是拜严复所赐。
和严复同列“并世译才”的林纾自然也在批判之列。罗家伦指责他“译外国小说常常替外国人改思想,而且加入‘某也不孝’‘某也无良’‘某事契合中国先王之道’的评语”,“巴不得将西洋的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一律变成中国式,方才快意”。[74]郑振铎认为“旧的文艺观念”“对于新的文学必定要持反对的态度,或是竟把新文学误解了”[75]。这里的“新文学”就是西方文学;所谓“旧的文艺观念”对“新文学”的“误解”,就是“先存一个凡新出之物古代都已有之的意见”,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念来翻译和接受西方文学,结果“把《魔侠传》当作《笑林广记》看了,把莫泊桑之性欲描写的作品当作《金瓶梅》等类的书看了”[76]。因此,只有与“旧的文艺观念”彻底决裂,才能避免对“新文学”的误读。换言之,就是要求译者面对西方文学时,认清它和中国文学截然对立的本质,拒绝调和中西的翻译。周作人也发表过类似言论:
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扛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了一点,便古今中外扯作一团,来作他传奇主义的《聊斋》、自然主义的《子不语》。这是不肯模仿、不会模仿的必然的结果了。……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同汉文一般样式,那就是我随意乱改的糊涂文,算不了真翻译。[77]
简言之,“译书的文笔”“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78]。在新文学译者的心目中,“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绝不“同汉文一般样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译只能是一种“硬改”和“凑就”,甚至是“随意乱改的糊涂文,算不了真翻译”。
作为“直译”的对立面,严复和林纾的翻译被冠以“意译”的名号。1919年3月傅斯年在《新潮》发表《译书感言》,对“意译”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
我们纵然不能做作者的功臣,又何必定要做作者的罪人呢?作者说东,译者说西,固然是要不得了;就是作者说两分,我们说一分,我们依然是作者的罪人。作者的理由很充足,我们弄得他似是而非,作者的文章很明白,我们弄得他半不可解,原书的身分便登时坠落——这便是不对于作者负责任的结果。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假使赫胥黎和孟德斯鸠晚死几年,学会了中文,看看他原书的译文,定要在法庭起诉,不然,也要登报辩明。这都因为严先生不曾对于作者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的声名地位负责任。他要求名,然后译书,只要他求名的目的达到了,牺牲了原作者也没不可以。我并不是说译书定不为求名,这是不近人情的说话。但是断断乎不可牺牲了作者,求自己的声名。这是道德上所不许。[79]
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了二元对立的论述模式,“直译”和“意译”构成了气势逼人的排比:
直译没有分毫藏掖,意译却容易随便伸缩,把难的地方混过!所以既用直译的法子,虽要不对于作者负责任而不能。既用意译的法子,虽要对于作者负责任而不能。直译便真,意译便伪;直译便是诚实的人,意译便是虚诈的人。直译看来好像很笨的法子,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有时作藏拙的用,但是确不若意译专作作伪的用。[80]
“真/伪”“诚实/虚诈”“负责任/不负责任”……傅斯年对“直译”和“意译”的价值判断提升到了道德伦理的高度,越发溢出翻译批评的范畴,而成为捍卫全面西化之文化取向的强硬话语策略的一部分。
五 结论
甲午以后,空间意义上的“西”和“中”逐渐被代换为超越地域界限的“新”和“旧”。“五四”新文学译者立足于社会进化论,在文化和文学“革命”(革故鼎新)的语境中,将“新”和“旧”推向“先进”和“落后”;更通过语词操纵塑造出“(西)优”和“(中)劣”的尖锐对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移植”西方文化,迅速实现社会“进步”的捷径——翻译。
除了价值判断的对立,新文学译者还显示出一种“文化整体意识”,即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他们严厉批评晚清流行的“体”“用”二分的文化配置模式,强调两种对立的文化不可兼容;又基于“西”优而“中”劣的判断,提出全面西化主张。他们倡导在翻译西方文学时,注重对译出语文本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两方面的忠实——即所谓“直译”。“直译”的手法在晚清本被视为文不从字不顺的代名词,却因为保证了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两方面对译出语文本最大限度的“忠实”,迎合了新文学译者的文化取向,其价值得以在“五四”时期彻底翻转,被奉为必须遵守的翻译规范;作为“直译”的对立面,“意译”被用来指称严复、林纾等晚清译者迁就译入语文化而不“忠”于译出语文化的翻译手法,凸显出鲜明的负面价值。在新文学译者基于全面西化取向的论述中,“直译”和“意译”也被赋予了道德化的二元对立。
注释:
①茅盾:《直译·顺译·歪译》,《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②较早的有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二章第二节“意译为主的时代风尚”以及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3期)。
③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五四前后文学翻译规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④同上,第141页。类似的说法还有:“因为近代翻译史上有过任意增删、曲解原义的教训,所以,五四时期直译的呼声很高。”秦弓:《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⑤关于翻译研究中的“原著中心论”,参见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页。
⑥比如,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就明确反对将翻译简单地理解为“把一种语言符号里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符号”,她认为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行为。Susan Bassnett,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22。
⑦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以及在此期间发生的“文化取向危机”,参见张灏《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25页。
⑧熊月之就用“夷学”来概括时人对西学的认识。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0页。关于“夷”这一称谓的详细讨论,参见王宏志《说“夷”: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话语》,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6年春夏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307页。
⑨如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就有《采西学议》。
⑩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页。
⑪(清)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⑫⑬⑭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
⑮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
⑯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
⑰陈独秀:《〈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记者识》,《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3号。
⑱⑲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
⑳其中最具争议的当属王尔德。夏志清就曾批评陈独秀:“在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的当儿,竟把王尔德拉了进去奉为经典,岂不滑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不过,陈独秀确实是把王尔德当成“自然派”作家的。他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3号)中称王尔德和易卜生、屠格涅夫、梅特尔林克是受自然主义影响的“近代四大代表作家”;《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开始连载王尔德的剧本《意中人》(An Ideal Husband)时,陈独秀认为该剧表现了“英人政治上及社会上之生活与特性”,并称作者为“晚近欧洲著名之自然派文学大家”。
㉑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新潮》1919年第1卷第2号。
㉒中西对比式的论述手法在晚清已有,最著名的莫如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名文《论世变之亟》:“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严复列举了12组中西对立,涉及伦理、政治、民俗、经济、学术等多个方面。王人博指出:“严复和后来的五四新文化健将们一样,并不是严守文化中立的立场,对中西文化作‘文化学’上的辨识,而是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即以‘求变’为纲,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丁伟志也认为,陈独秀式的中西对比论述“沿袭并大大发挥了严复在戊戌时期崇西抑中的比较中西文化的论证方式”(丁伟志:《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下卷):裂变与新生——民国文化思潮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但这些说法颇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严复在枚举上述中西对立之后,紧接着就说:“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3页)在严复看来,中西文化虽然存在种种对立,但就整体而言并没有好坏之分,根本谈不上“崇西抑中”。“五四”时期塑造的中西文化对立只是在论述形式上继承了严复,而这一时期跟严复的手法相近的是杜亚泉(伧夫),如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发表的《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
㉓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1919年第1卷第1号。
㉔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㉕关于严复在《天演论》中对赫胥黎和斯宾塞思想的取舍,参见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天演论〉》,《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严复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76~83页。
㉖傅斯年:《译书感言》,《新潮》1919年第1卷第3号。
㉗陈独秀也作过类似表述,只是没有明确点出翻译:“今之欧罗巴,学术之隆,远迈往古;吾人直径取用,较之取法二千年前学术初兴之晚周希腊,诚劳少而获多。”陈独秀:《随感录(一)》,《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
㉘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号。他和陈独秀讨论译书问题时也曾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胡适:《论译书寄陈独秀》,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4页。
㉙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
㉚朱湘、陈静观、沈雁冰:《通信·英文译的俄文学书》,《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1号。
㉛“全盘西化”的口号要到1930年代才由陈序经明确提出,但笔者认为“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所提出的文化主张实际上已经达到全盘西化的程度。为避免混淆,本文用“全面西化”来描述“五四”时期的这一文化取向。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时许多过激的“西化”言论带有论战性质,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策略性。一贯激进的陈独秀在反对“新旧调和”时说:“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所以调和论只能看做客观的自然现象,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张。”陈独秀:《随感录(七一):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1919年第7卷第1号。沿着这样的逻辑,陈独秀只能选择以“过正”的方式来“矫枉”,最后在“客观”上达到“调和”的结果。查良镛的伯父查钊忠在写给钱玄同的信里,更以新旧文体的代换为例,坦承“‘矫枉过正’四个字实在是救久病的良药;中国万事万物都该用这四个字切实做去,才有复活的希望咧”。查钊忠、钱玄同:《通信·新文体》,《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1号。
㉜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㉝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3页。
㉞康有为:《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代宋伯鲁拟)》,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5页。
㉟参见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嬗变》,《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㊱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59页。
㊲(清)吴廷栋:《拙修集》卷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3册,上海古籍出版2010年版,第452页下。
㊳(清)胡礼垣:《新政真诠·新政安行》,(清)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书总税务司赫德筹款节略后》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8页。《新政真诠》系由何启(1859—1914)、胡礼垣二人在1880年代至1890年代发表的九篇政论文集结而成。以往多认为该书大都是何启先以英文写成,胡配合译为中文并加阐发(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编序”第2页),故以上引文也多归于何启名下。但据李金强考证,《新政真诠》一书中包括《新政安行》在内的七篇文章主要为胡自撰,而冠以何启之名。李金强:《书生报国中国近代变革思想之源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62页。
㊴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4号。
㊵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1号。类似的表述亦见于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以及陈独秀与钱玄同、蔡元培的通信(《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1号)。
㊶唐俟(鲁迅):《随感录》(四八),《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2号。
㊷朱希祖:《非“折中派的文学”》,《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4号。
㊸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第1卷第6号。
㊹钱玄同:《随感录》(三十),《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3号。
㊺“直译”这个术语虽然出现较晚,但对应的翻译方法在汉唐佛经翻译中就已使用。参见陶磊《佛经译论中的“取意译”与“敌对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佛经汉译理论中的“正翻”和“义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㊻(清)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1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984页。
㊼㊽㊾程淯:《分省补用道程淯条陈开民智兴实业裕财政等项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9、289、289页。
㊿采庵:《〈解颐语〉叙言》,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276页。
[51]叶景莘:《中国人之弱点》,《庸言》1913年第1卷第11号。
[52]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75页。
[53]周桂笙:《〈译书交通公会试办简章〉序》,《月月小说》1906年第1卷第1号。
[5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第45页。
[55]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初版),《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8页。
[56]鲁迅:《〈域外小说集〉序》(新版),同上,第177页。
[57]鲁迅:《〈域外小说集〉序》(新版),同上,第176页。这时的二周还没有“五四”时期那样强烈的西化倾向,所以他们在翻译方法上虽然选择了直译,语言却用的是文言,在翻译语言从文言逐渐向白话过渡的清末译界反倒显得“落伍”,较之鲁迅早年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时用旧白话夹杂文言的做法,更是“退后”了一步。木山英雄认为,这呼应了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立场,甚至“可以说是把后来在‘五四’时代相互冲突的国粹与欧化沟通起来的一大试验”。[日]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242页。
[58][59][62][63][79][80]傅斯年:《译书感言》,《新潮》1919年第1卷第3号。
[60]沈泽民:《译文学书三问题的讨论》,《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5号。
[61]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1919年第1卷第2号。
[64]其中以陈独秀和钱玄同的批评最为激进,《新青年》曾以通信的方式刊载两人的议论。钱玄同、陈独秀:《通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与《新青年》同一阵营的《新潮》杂志,也登过主编傅斯年的文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称:“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的,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新潮》1919年第1卷第3号。
[65]《小说月报》“文艺丛谈”栏目刊载过茅盾和郑振铎关于“语体文欧化”的讨论。沈雁冰:《语体文欧化之我观(一)》,郑振铎:《语体文欧化之我观(二)》,《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6号。
[66]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257页。
[67][68]张寿朋、周作人、陈独秀:《通信·文学改良与孔教》,《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
[69]鲁迅、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
[70]仲密(周作人):《思想革命》,《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4号。
[71]钱玄同、陈独秀:《通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
[72]宗白华:《讨论译名的提倡》,《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4月12日。
[73]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322页。
[74]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1919年第1卷第1号。
[75][76]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1号。
[77]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1号。
[78]王敬轩(钱玄同)、刘半农:《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