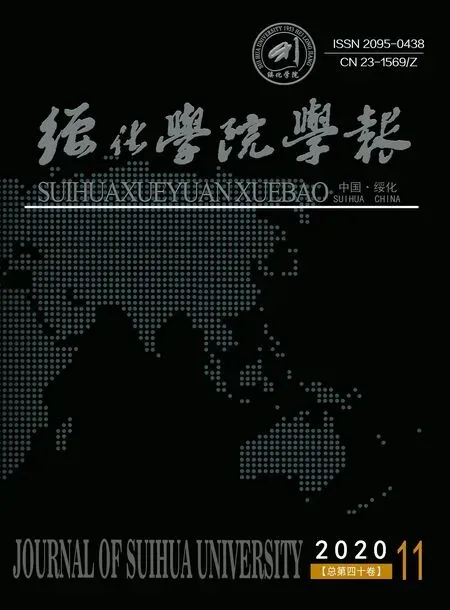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出让主体多元化法律问题研究
2020-02-26仙玉莉詹王镇
仙玉莉 詹王镇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将改变长期以来由地方政府运用土地征收垄断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土地供给模式,集体经营新建设用地入市主体成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首要问题。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的实践来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呈多元化,是由《物权法》《土地管理法》规定代表“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多元(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农民集体);申请主体和审批主体的多元化不利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各项法律关系的明确化,容易引起多种法律纠纷。
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出让主体多元化
(一)法人化主体作为集体经营权建设用地入市主体。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作为入市主体,具体操作中:第一类是农民集体参照公司形式把集体经济组织改造成具有法人资格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由土地股份合作社负责集体土地入市或土地合作社作为出资人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如广州天河、北京大兴区[1];第二类是农民集体把入市的土地委托授权具有法人资格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如安徽省、深州市、山东省、重庆市、四川成都郫都区、陕西西安高陵区。[2]由具有法人民事主体资格主体作为集体土地入市申请主体,农民集体、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合作社及其与合作社成员之间的产权、财产关系、运行规则都按照市场化的方向进行了界定,不会因负责人的变更而影响其独立的市场主体资格,保障了交易的稳定性,但是由于土地合作社制度的设立成本高,取得成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
(二)非法人化主体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由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集体经济组织等非法人化主体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在实践中的表现主要有:吉林长春九台区以村民委员会作为入市主体;河南长垣县以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入市主体;辽宁海城市、江苏常州武进区以村(镇)农民集体作为入市主体[3];上海、重庆大足以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作为入市主体[4]。此类模式突显的特征表现为:由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由“镇”、“村”“村民小组”三级所有,导致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申请的主体也呈三级化。如:长春九台区以“村”作为入市主体;上海松江由“镇”和“村”两级联合作为入市主体;辽宁海城以“村”和“村民小组”作为入市主体;河南长垣县建立多层级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乡集体土地,由乡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入市主体;村集体所有土地,由村委会作为入市主体;村民小组所有土地,由村民小组委托村委会作为入市主体。”[5]非法人化经营模式中,经营者因主体的多元化而产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不安全、不稳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需求方更倾向于从非法人化主体中通过“租赁”的方式取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而不是出让。
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出让主体多元化引起的法律问题
(一)没有明确区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与集体所有权实施主体。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法人化不确定,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与实施主体合一与分离不统一,在以土地合作社法人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形式中,土地合作社特别法人法律地位不明,缺乏法定的经营土地的具体权利,土地合作社的种类繁多,有农民股份合作社、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民股份合作社法人,不同合作社的运作机制不同,农民集体成员加入、推出土地合作社的标准模糊,土地合作社法人的管理人员往往与村民委员的管理人员相混同,易造成矛盾纠纷的产生。在非法人化模式中,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申请主体的多元化增加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基础的复杂化,降低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非法人化主体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未区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与集体所有权实施主体。集体土地有有权主体与集体所有权实施主体合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未从土地所有权中剥离。尽管《民法典》草案赋予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主体“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法律地位,但是特别法人的内容、形式等仍在探索研究中,当土地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最重要的财产时,土地利益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核心利益,加之成员权制度的缺乏,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村民小组”、“村”“镇”三级所有的现状,造成从集体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主体层级性,农民、“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模糊。
(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没分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申请主体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的一项经济活动,履行的是一项经济职能。”[6]其应享有市场主体地位的法人或特别法人,而不应该是履行基层民主管理职能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造成村委会行使经济职能的原因是集体经济组织的缺位或错位。在农村集体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化程度较高,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市场化的能力强,经济组织与村委会之间的职能边界越明晰。依据法律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是抽象的“农民集体”具体化的代表,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是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人、发包人、投资人,其主要履行经营集体土地或向家庭承包经营的户“发包”土地和职能。按照物权法第60条,乡镇政府不能成为农民集体代表,其行使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申请主体缺乏法律依据。实践中,对家庭承包以外的其他方式承包经营土地,有的地方由镇政府组织实施。在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村委会在事实体制上成为农地所有权的代表者,名义上的农民集体所有,变为实际上村干部或村委会享有的决定权。村委会的意志取得了集体成员的意志。[7]有些地区没有集体经济,也就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有些地区有集体经济组织,但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人员和村委会主要成员是一套人马,两套班子,本质上未区分村民委员会的政治职能与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村委会代集体经济组织实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经济职能。
(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法律属性不明确。《土地管理法》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可以推导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用益物权的属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的客体“不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而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8]法律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出让前,应取得“依法登记”确权证明,但是现行法律并没有单独设置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登记,集体建设用地登记被包含在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中,影响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一项独立用益物权的判断,经营性建设用地到期后建筑物与附着物的归属判断也缺乏基础性权利指引,只能依靠合同约定,如果合同约定不明,则易发生矛盾纠纷。
(四)“自治权”的行使易侵犯农民集体、集体成员的土地权益。
1.群众自治权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中的边界不明晰。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均属于自治的社群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形式、土地入市收益分配、集体成员的认定标准都属于农民集体自治的范围。在集体土地收益成为集体成员的重要财产时,成员权成为调整集体组织和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依据,“自治权”的形式离不开“成员权”的认定,但是,成员权的法律属性不统一,成员权是身份权还是财产权亦或是“身份与财产”的双重属性不明确;成员权的认定标准不统一,如户籍、土地权利和生产保障,致使自治权的形式可能会与当地不符合法律制度的习俗、传统观念交织在一起,侵犯集体成员的土地权益。
2.集体成员的民主决策权行使受到限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初始需要抽象化的 “农民集体”拟定出让方案,需要以“全体集体成员”的方式对出让方案行使民主决策权。出让方应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成员代表会议2/3以上同意,在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由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进行入市的模式在一定时间内将仍然存在,如果集体成员的民主决策机制不完善,集体成员的民主决策权就没有充分实现,集体土地入市决策的民主化基础缺陷,增加了集体与集体成员之间、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矛盾纠纷的产生。
3.集体土地出让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出让主体多元导致出让收益归属、管理、分配标准的不统一,易导致集体土地出让收益分配矛盾纠纷的产生,有的地方是所有权人自己管理,设立出让收益资金专户,与集体其他账户分开,如珠海;有的地方不建立土地收益专户,纳入集体所有权主体的集体资产统一管理;有的地方有镇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如上海、苏州。
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多元化法律问题的解决
(一)理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制度中的权利逻辑关系。
1.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申请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法人是市场的重要组织,在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要促进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有法人化的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主体;在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还没有培育成型的地方,由村小组、村委会、乡政府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申请主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是一个过渡性选择,但政府不能依靠行政强制力单方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根据村民自治组织有关规定,以尊重农民集体的自愿为前提,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推进,在这些地方,一方面要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另一方面,要培养集体经济或由政府组织成立的集体联营公司负责全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实现由“农民集体”到“集体经济组织”再到“法人化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转变。
2.集体经济组织应成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申请主体。区分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两个不同主体,集体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上的村社共同体,作为集合概念的集体本身并不能成为民法主体,由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承担包括土地经营在内的经济职能,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实现形式,确定集体经济组织。
(二)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1.赋予集体建设使用权的用益物权属性。法律上明确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用益物权的性质,集体土地使用权入市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为他人创设原始的土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行为属于物权行为,其上的建筑物与附着物所有权属于无期限的物权,集体土地受让人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具有用益物权的性质。
2.明确“集体成员权”的认定标准,重塑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成员关系。目前,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方式和路径是推行股份合作制法人,农民基于“集体成员权”成为“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集体成员权”以“户”的形式存在,“户”按照股份制原则,以土地量化入股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股东和法人的关系,由合作制法人将土地进行承包、租赁、或者开办企业等,成员权和股权得以区分,集体成员对进行股份合作制的集体经营性财产享有股东权利。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集体经营建设用地者之间形成承包、租赁等合同关系,受合同法进行调整;农民个体在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者开办的企业内工作,形成劳动、雇佣关系,受劳动法的调整;但是否入市流转则须履行民主议定决策程序,通过完善村民自治健全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机制,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与保障集体成员的权利相一致,实现集体所有权向个体权利的重新界定。集体经济组织需要根据一定的标准界定是否为集体成员,成员是否参与收入分配,“重庆大足创制了‘三分两不分’分配机制”较好的解决了该问题。①[9]
3.明确农民集体、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土地入市代理机构之间的区别。“集体土地使用权入市的核心问题是集体土地的开发权,允许集体向集体外成员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就意味着承认了农民对集体土地享有开发权。”[10]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为公共权力,退出流通领域,对那些尚未发包或者划拨给农民的集体土地,享有名义上的所有权,也保留着作为财产权的使用权,未从所有权分离时由集体享有开发权。农民集体所有权人“农民集体”通过民主表决程序享有是否决定入市的决定权;“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通过法定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来实现。”[11]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自行,也可以委托集体土地入市代理机构行使申请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权利,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土地入市代理机构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
(三)促进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发展。
1.法人化主体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的必要性。法人化主体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区分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与集体所有权实施主体。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集体土地所有权实施主体与集体土地使用权主体的区,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股份量化的基础上成立法人化的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联社、公司)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从土地所有权中剥离,将使用权出让给受让人,由集体所有权主体经过民主决策程序行使权力决定是否入市,由集体土地所有权实施主体负责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具体实施,如编制入市方案等,取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受让方成为集体土地使用权主体。
2.创设集体经济组织法。《民法典》草案第四节第九十六条已经明确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列入特别法人,承担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第九十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单独立法预留了空间。特别法已经超出了传统法人分类框架,目前,理论界围绕集体经济组织性质、资格认定、功能的实现、立法路径与方案设计,已经取得了比较深入的全面的研究成果,为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设立理论基础。
3.鼓励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形式多样化发展。依据股份制原则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是相对比较成功的方式。实践中,安徽宿州、广州、深圳、上海、安徽等地采用的最多,但是各地的股份制事项不同,有的是农地合作制,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折股给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将土地的使用权自行经营或转租给农业企业,实现经营权的集中流转创新;有的是土地股份合作制,集体所有制性质,家庭承包关系不变,将集体资产、农户的经营权股份化后分配给合作社社员,不是将土地以“收租金”式方法转租,而是由合作社发挥成员和集体共同的力量,自行负责土地用于农业生产经营,发展农业规模经济。
注释:
①“三分”指拥有该集体经济组织农业户籍的人员分三分之一,拥有该集体经济组织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地的人员分三分之一,长期生活在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的人员分三分之一,占两项的分三分之二,三项都占全额分配。“两不分”是指,已征地农转非购买社保的人员不参加分配、空挂户人员不参加分配。从制度建设入手,建立了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收益分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