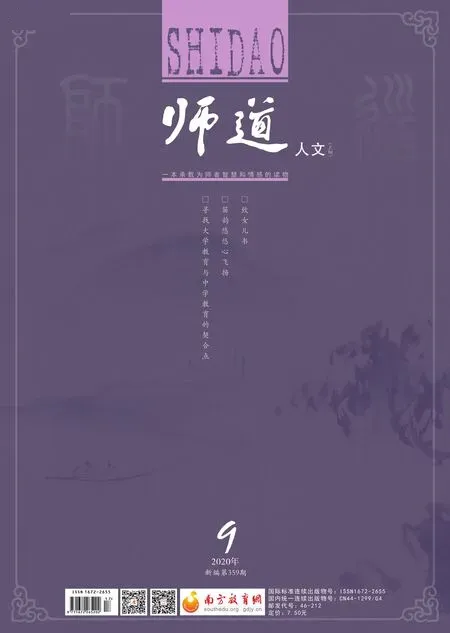流行语镜像中的文化面相 (十八)
——说“投喂”
2020-02-25古北
古 北
“投喂”, 原意为抛撒饵料喂食动物, 本平平无奇, 如今流行起来, 变得生动活泼, 尽显幽默。 一时万物皆可 “投喂”, 即投喂之物不再局限为食物, 投喂之对象亦不局限于动物。 例如, “将成千上万张经过标注的图片组成的数据集‘投喂’ 给机器” ——像这类AI 系统的投喂者, 已经成为新的职业:人工智能训练师。 也就是说, 投喂的语义变得非常丰富, 不仅是食物的喂养, 还可以是对信息、 内容、物资的投递、 输入、 推送、 捐赠等等。 这场缤纷的 “投喂” 秀, 以大数据分析, 敏感捕捉用户喜好, 不停歇的广告推送为最疯狂之 “投喂” 现象。 我们更频繁地接受广告的围剿, 在花样的信息轰炸中, 趣用 “投喂” 一词疏泄了被狩猎的紧张, 同时也渐渐 “撑大” 了 “投喂” 的 “基础量” ——“投喂” 变得隐隐有多余的溢出, 让人感觉已超过被投喂者的需求, 变成一种“填鸭式” 的注入。
不是动物, 而是人接受 “投喂” ——这种主客的错位令人欲罢不能, 其中有被动乏味的不适感(如 “以前总是被老师 ‘投喂’, 现在如何适应大学的自主学习?”),但更多是 “降为动物” 的可爱逗乐(如, “晚餐老板娘 ‘投喂’ 丰盛,太开心了!”)。 也许是某种孱弱自怜, 也许是休憩的需要, 人们在接受 “投喂” 的 “降格” 中感受到滑落的快乐。 这种 “贬低” 是直截了当的, 但接受起来似乎毫不困难,在享受动物式的轻松间, “人格”轻轻被勾销而无侮辱感。 我们溜滑地进入一种由新的语言场景所给予的轻盈里——糊口的不易、 生活的繁琐、 思考的艰难早教人备受压力, 有人 “投喂” 岂不是乐事一桩? 自无须计较是否沦为动物。
而且, 事情还不只是如此这般, 很多东西都在变得亟需 “投喂”。 一切变得嗷嗷待哺, 最好的例子是微信的使用, 就像是领养了一只宠物, 你以语言、 图片或链接“投喂” 它, 它便像狗儿一样跳到最上方; 若久未喂食, 它便沮丧地蜷在窝底, 奄奄一息。 微信的技术设置, 你的 “上线” 必表现为将另一个埋压于下方, 所以若失去互动, 看上去就更像是互相填埋,而非互相发现。 这种填埋, 并没有深挖抛入, 只是表现为堆积, 但又无厚积之感, 倒像是落叶之轻之脆——轻感而无重感, 是一切“微” 媒之特征——哪怕你大量“投喂”, 也避免不了 “速朽”。 观看则可以通过快速划屏来进行, 意味着可以浅尝辄止, 让别人生活的影子快速地从眼前滑过, 从而免去离群索居之孤独想象, 这一点也像是宠物带来的慰藉。
更有家校合作、 工作互联等手机软件, 也一个个张大着嘴, 要求你进行打卡式甚至是多多益善的“投喂”, 至于线下实际完成得如何已经无人问津……这么说, “投喂” 在消磨我们? 别说得那么严重, 但是它确实勾画了新的链条,在那里, 我们的位置已经十分固定, 我们难以根据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无论是从 “投喂” 的哪个方向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