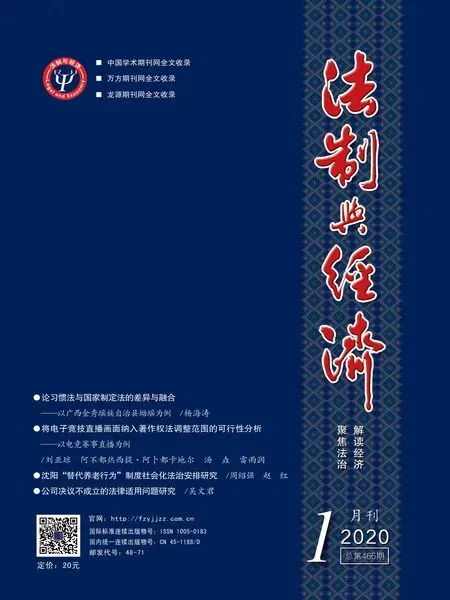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研究
2020-02-25李晓寒
李晓寒
(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中强调了依法保障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①与此同时在2019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提议以修正案的方式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律师调查令制度,为律师调查令制度提供法律依据,此举使得律师调查令制度又一次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明确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含义、实践特点以及运行规律,对在程序上确保当事人取证权利以及保证法院及时有效、公正合理地处理案件有着重大影响。
一、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概述
(一)律师调查令的概念
律师调查令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履行举证责任时,由于客观障碍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形下,而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核同意后签发给当事人,由持令人向被调查人收集证据的一种法律文件存在形式。②这一概念虽然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法律条文中未明确体现,但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纷纷颁布实施了关于推进律师调查令的规定。
(二)律师调查令的特点
第一,在适用阶段有不同规定。之所以存在适用阶段的差异是为了防治诉讼资源的浪费。在诉讼阶段申请律师调查令是司法常态,而诉讼外的证据则作出了否定式的规定。在案件的审理阶段,应在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并且申请调查的证据应当与案件的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在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则应在案件执行终结前提出申请,且申请调查的证据应当囿于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实际履行能力的范围之内。③
第二,权利义务主体明确,且适用条件有严格规定。申请律师调查令的主体应当是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包括原被告双方,申请时应当向法院提供所需要调查的证据与诉讼案件具有关联性证明并且自己确实存在客观障碍举证不能的原由;律师持法院出具的有效律师调查令进行证据收集的过程中,必须经过当事人明确的委托授权且持有律师执业证,在律师事务所的指派下参加该民事诉讼活动;被调查人是除对方当事人以外的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中明确的应当向持令人提供证据的个人和单位。④
第三,申请调查的种类和范围有限。根据各地法院颁布的试行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在当事人无法取得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且该证据关乎案件的判决结果,才可以申请律师调查令。并且规定了持调查令可调查的证据限于档案记录材料、金融机构账户及权利凭证等,而证人证言被排除在外。
第四,严格规定了使用方式和有效期。根据各地法院的实践,律师调查令的有效期一般为15天,期限届满后自动失效;出示律师执业证和法院出具的有效调查令是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的必经环节;该令只可用因诉讼的需要而调查取证,不得滥用,如果违反了该目的,律师便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三)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的优越性
第一,该制度有助于增强提供证据的能力。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从法律层面恰是明确了案件当事人承担获取和提供证据的责任义务,以及当事人收集有利证据进一步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的权利。相反,从现有的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内容以及所传达的意识思想来看,当事人的取证权利并没有得到真真切切的落实,在实际的司法实践运用过程中更是举步维艰,当事人取证权利的行使受到现实阻碍。而且现实情况是当事人所需的一些人身和财产信息大都由政府公共部门所存储,当事人对这些证据的收集很难做到真正的独立,就算律师在获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内部规定”这座高墙的阻碍,但这些证据又是案件审理判决和执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第二,该制度是明确案件事实的必要条件。在诉讼过程中,要想让法官作出有利的判决,就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让法官相信自己的事实主张,从根本上而言充分全面的证据必然是认定案件事实原委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收集证据或者收集的证据不够充分全面,就不能使案件事实明确,从而达到诉讼定纷止争的目的,当事人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第三,该制度不仅仅是法官而且是社会公众期望的能够在审判活动中所追求的司法公正即法官始终处于居中裁判地位的现实体现。《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官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也可以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但是相比较而言该规定与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诉讼与审判相分离的价值追求相悖。建立律师调查取证制度将取证权交由当事人及其律师便很好地缓解了法官的尴尬地位,避免先入为主,从而真正做到中立裁判,司法公正。
第四,合理利用司法资源。在我国案多人少是司法常态,每个法官承担着巨大的办案压力。调查取证是整个诉讼过程中耗时最多也是最繁重的一步,不得有丝毫差错,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可以由专业的律师来完成,使法官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从而有效地缓解法官的压力,做到司法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
二、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域外考察
(一)大陆法系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以德国为例
文书提出命令是奉行大陆法系国家所创立并付诸实施的制度,如德国便是典型体现,此举既保障了当事人能够有效行使取证权,又可以对拒绝提出文书的当事人进行有效的法律威慑,从而进一步减少证明妨碍。
从德国现行的《德国民事诉讼法》中不难发现,一方当事人如果认为确有必要,除了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文书以外,还可以要求与案件存在关联但没有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提出文书,只是在要求该第三人提出文书的程序方面与当事人相比而言更为复杂,即只能通过诉讼方式强制实施。但于2002年开始实行的新法将旧法中的“直接占有”扩展为“占有”,换言之,如果举证人认为文书被第三人占有,那么其可以根据第430条的规定,申请法院命令提交文书。此外《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32条还规定,官署或者公务员依法负有文书提出义务而拒不提交时,适用关于第三人的规定。⑤
(二)英美法系证据开示制度——以美国为例
1993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修正案新设自动开示程序后,请求-回应式的证据开示与自动开示结合使用,用于对自动开示未能涵盖的事项进一步开示。修正后的规制要求所有当事人:首先,在案件的早期阶段,交换有关潜在证人、文件证据、损害赔偿金、保险费的信息;其次,为了找到证据,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确定专业证人,并就特别雇用的专家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提交书面陈述;再次,在接近庭审的日期,确定将在庭审中被提供的特定证据。⑥这种规定强制当事人开示相关信息,不仅符合诉讼经济、免除证据开示过程中所产生的劳费,也可以保障双方当事人对案情具有最基本的认识。自动开示制度使得美国民事诉讼程序更富有完备的证据收集渠道,也有助于强化法院职权参与诉讼管理功能。
三、我国当前律师调查令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一)律师调查令存在的问题
1.没有统一、全面的规则。律师调查令制度并没有在法律条文中被明确规定出来,可见律师调查令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各地方法院根据相关的立法精神所展开的探索实践,尚未有明确的立法规制。2.调查令无强制力保障。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威慑力,拒绝配合的被调查人正是在这种侥幸心理的状态对该制度的践行不以为然。由此可见调查令形同虚设,在实务中常被各种原由规避。3.对律师调查令的使用条件缺乏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法官在适用时存在主观臆断性,拥有较高的自由裁量权。例如无异议和救济等配套机制,使得法院在遇到此类案件时主观性浓厚。
(二)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完善
1.明确律师调查令的法律地位
法律强制力是一项制度有序运行实施的重要依据。虽然我国现行立法确立了关于收集证据的主体和方法的基本规则,但是未能摆脱过于笼统和模糊的困境,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程序的实施仅由法院加以引导,没有单一的法律保障,使得该制度未能达到预期的司法效果。该制度已经是司法实践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并且该制度有效运行的土壤已经孕育成熟。亟需结合域外国家经验在法律层面作出关于律师调查令制度的统一规定。从体系地位这一方面来看,律师调查令制度从属于诉讼制度的统一架构之内,根据我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应当由立法机关以出台相关法律的形式确认其法律地位。
2.提高律师调查令的执行效力
在各地的实践效力中可以看出,调查令制度的效力差强人意,追根溯源是其强制性、拘束性较低,对于拒不配合的被调查者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及惩罚体系。与此同时,该行为日渐盛行,调查令也随之成为一纸空文,与该制度运行的初衷相背离。从根本上而言,建立相应的制裁措施和惩罚体系是该制度运行的有力保障。基于该层面,可以效仿两大法系国家的经验,对不予配合的相关人员付诸相关的惩戒,使得当事人可以有效行使法律规定的取证权。
3.完善相关异议程序及救济措施
辩论原则和救济措施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从各地的司法实践看只是概括地规定了持令人以及被调查人的权利义务,绝大多数未提供相关的异议救济措施,也未给予当事人不予执行该命令的正当事由。正是因为我国相关法律均赋予了当事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相应的救济措施,在律师调查令运行的过程中也有必要将相配套的异议和救济程序衔接在内,在当事人处于不利的情形时,可以提交展开上述程序的申请。即当事人申请律师调查取证被驳回的情形之下,当事人可以进行复议;被调查人不予进行相关配合而怠于提供相关证据时,可以提出异议或对其进行相关的惩戒申请来寻求救济。
四、结语
律师调查令制度在我国各地法院的司法实践当中发挥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但由于存在一些现实的问题,积极探索完善该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一步,统一的律师调查令制度亟待构建,从而在法律层面上赋予其强制保障力,从而提高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促进司法公正。
注释
①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S].2016。
②周赞华.对民事诉讼中适用调查令的法律思考[J].人民司法,1997(5)。
③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关于实施民事诉讼调查令的规定(试行),2015。
④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调查令的实施办法(试行),2014。
⑤包冰峰.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⑥韩波.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