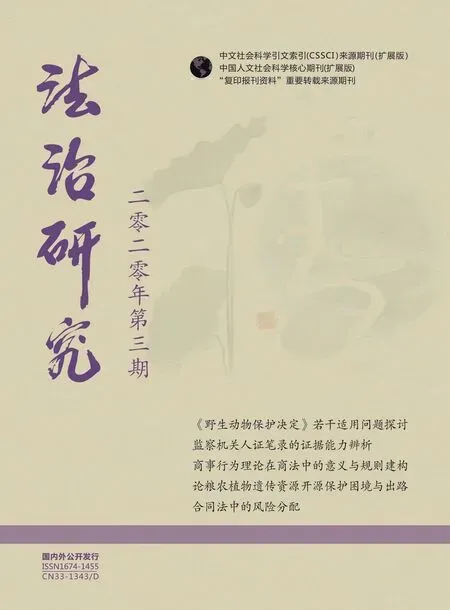合同法中的风险分配*
2020-02-25海因克茨沈小军
[德]海因·克茨 沈小军*译
一、导言
任何交换性合同都与风险的分配有关,并且合同约定的目的通常也只在明确哪些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关情况发生的风险,这些情况使约定的给付交换发生障碍、迟延、困难或者给付不能或者丧失意义。
例如,建筑商(Bauunternehmer)向开发商(Auftraggeber)承诺,为开发商建造特定的房屋,并且将于规定的时间交付,则可能会发生该房屋在规定时间还没有完成的情况,因为供应商没有向建筑商交付工程所需的建筑材料,某个专项承揽人(Spezialunternehmer)没有及时将地基挖好,建筑工程的进展因为罢工或者自然灾害而被延迟了:究竟是建筑商还是其开发商应当承担这些事件发生的风险呢?
虽然在很多合同中都缺乏对风险分配的明确约定,但也可能发生当事人虽然作出了这种约定,但约定有漏洞的情况。在此意义上这些合同是“不完整的”,不过,这并不是因为当事人的懒惰或者无知,而通常是因为产生“完整的”约定并非免费的,而需要支出人们从经济学的角度置于“交易成本”概念之下的花费。
因此,在实践中仅有两种情况这一花费是“合算的”,因此对当事人存在足够大的动机去拟定相对“完整”的合同: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允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给付,费用首先是值得的。此外,如果一方当事人以相同或近似内容订立极大数量的合同,以致对其来说值得,在“一般交易条款”中开发细致的规定并为订入合同而不断重复地向对方当事人提供这些细致的规定。其后果是,对方当事人只需对一般交易条款的适用说 “可以”,一般交易条款即因此成为合同内容,如果对方当事人已经被提示了一般交易条款,并能够知悉其内容。
如果对风险分配缺乏明示的约定或者这些约定不够清晰,有时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提供帮助,通过合同解释来填补约定存在的漏洞或者澄清约定的准确意旨。如果这种方法不奏效,则应适用任意法的规定。因此,适用那些“备用规则(Reserveordnung)”,《民法典》用这些“备用规则”为合同提供一般性并为特定合同类型提供详细的风险分配规则。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了一般交易条款,但这些一般交易条款没有成为合同内容或者无效(第306条第2款),也将适用任意法规。①关于任意法规的定义以及其与补充的合同解释之间的关系,详见Kötz, JuS 2013,289。
二、现行法上的风险分配规则
上述内容完全不是什么新的知识,并且没有人会质疑,由合同当事人所作出的明示或者默示的风险分配约定在所有的交换合同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一方当事人已经承担了特定情况发生的风险,现行法上就已经包括了很多规则,根据这些规则其必须承担这些风险的实现所造成的不利后果。
在一种案例类型中这些不利后果在于,负担风险的当事人必须提供损害赔偿,尽管其对被请求承担责任的合同不履行虽然不应由其“负责”,但可能是因为该当事人已经承担了风险的情况引起。如果一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承担了“担保”或者“购置风险”,依第276条第1款的规定尤其如此。
第二种案例类型的不利后果在于,债权人虽然没有获得(债务人)向其允诺的给付,但仍然需要提供对待给付,因为阻碍债务人提供给付的情况属于债权人的风险领域。分布在《民法典》不同地方的任意性规范都借鉴了这一基本思想。
例如如果存在“寄送买卖”,只要当事人未另有约定,则买受人应依第447条第1款的规定,承担买卖标的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为意外事件灭失或损毁的风险;因此,即便买受人没有获得或者只获得了处于缺陷状态的货物,且其原因在于买受人虽无过错,但因为已经提及的原因而应当归责于其风险领域的情况,买受人也必须支付价款。
如果(当事人)订立的是“寄送承揽合同”(第644条第2款),同样如此。在其他承揽合同中,虽然经营者原则上应当承担由其制作的成果在受领前灭失、毁坏或损坏的风险(第644条第1款)。但依据第645条的规定,如果成果已经灭失或者无法完成,因为定作人提供给承揽人加工的材料有瑕疵或者遵从了定作人作出的指示,则承揽人在受领前即已经可以请求支付报酬。提供的材料有瑕疵或者作出的指示不适合的风险由定作人承担;因此并不取决于定作人的过错。如果定作人的行为具有过错,依第645条第2款的规定,则承揽人因定作人违反合同而依第280条及以下条文的规定或者基于侵权行为而依第823条的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将不受影响。承揽人因这些请求权在结果上经常会被置于比依第645条第1款的规定只请求部分报酬更为有利的位置。
此外,第645条的基本思想还被判例以“类推”方式显著扩大了,将该规定也适用于其他但同样属于应归责于定作人风险领域的情事的案例,这些情况导致尚未完成的成果灭失或者无法使用。②Vgl. zB BGH40, 71 (75f.)=NJW 1963, 1824=JuS 1963, 492 (Gerber);BGHZ 78, 352=NJW 1981,391=JuS 1981, 457 (Emmerich);BGHZ.
第615条的规定也属于这一类型。根据第3句的规定,如果导致劳动者提出其给付的障碍原因属于雇主“经营风险”的范畴,则雇主仍然应当支付约定报酬,也即是说——第3句因此这样表述——雇主应当承担“劳动停顿的风险”。这里也不取决于雇主的过错。也即是说,如果在经营过程中发生停电或者锅炉爆炸,并且这些事件是不可抗力引起的,在劳动者不负担补充提供给付的情况下,雇主必须全额支付报酬。依第615条第1句及第2句的规定,只要雇主因任意原因——即便由于不可抗力——不能受领向其提供的劳务并因此陷于受领迟延的,所有的雇佣合同均是如此。③可能显得有点严厉,雇主——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则为用人单位——也必须支付约定的报酬,即便其对阻碍债务人无法提出允诺的给付的情况不“应当负责”。Vgl. dazu Kötz, VertragsR, 2. Au fl. 2012, Rn. 697-700, 832.
如果上面提到的规定不能适用于该当案例,总是还可以回归第326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债务人不能提供其所允诺的给付,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被免于给付义务(第275条第1至第3款),则债权人虽然原则上也不负担对待给付义务。如果使债务人免于给付义务的情况属于债权人的风险领域,也即是说他——如第326条第2款所表述的那样——对这些情况应当“独自负责或者负主要责任”, 债权人仍然需要提出对待给付。这里也不取决于负担风险的债权人的过错。
比如被告演唱会组织者对原告负有义务,为Tic Tac Toe乐队的特定巡回演出提供灯光设备,即便被告两手空空地站在那里,也即因此没有提出允诺的给付,因为乐队成员关系闹僵,无法修复,巡回演唱会因此泡汤了,则原告也可以向被告请求支付约定的报酬。这里涉及的也是风险分配的问题,也即并非原告或被告对巡回演唱会的取消是否具有过错的问题,而仅涉及何方当事人应当承担演唱会取消的风险的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将这一“风险”分配给了被告演唱会组织者:“只有被告有可能,在巡回演唱会开始之前评估这一风险,因为被告与不同艺术家的经理人保持经常联系。与此相反,原告在这一问题上不具有知悉的可能性。此种障碍并非由合同一方当事人,而是由与被告而非原告存在合同关系的第三人造成的。被告不能将其合同当事人没有按照合同的要求作出行为的风险转移给原告。毋宁说要听其(被告)自便,向其合同当事人请求赔偿损害,并将原告的报酬请求权纳入自己的损害计算中”。④BGH, NJW 2002, 595. 这个案子还是以原第324条为基础解决的,不过,依第326条第2款的规定今天也应如此判决。同样的还有 BGHZ 188, 71 Rn. 16 ff. = NJW 2011, 756 = JuS 2011, 359 (Faust)。对此及其他判决参见Kötz (o. Fn. 3), Rn. 828 ff。这显示,在很多情况下立法者是高度自我的,它将合同当事人明示或者默示希望的风险分配(规则)视为是重要的。在这里并不打算对这些情况进行详细论述。毋宁说旨在强化对以下情况的意义,在其他情况中当事人所选择的风险分配规则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经常会确定任意法规的适用范围,为第276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原则套上缰绳,并能更好地对特定结论进行论证,就好像直接从“诚实信用原则”中得出或是被称之为“有益的”“适当的”“必要的”。
三、错误
如果保证人在订立合同时对主债务人的支付能力发生错误认识,没有人否认,保证人不能基于错误而撤销同债权人订立的保证合同。在这种情况中因错误进行撤销的权利被排除有时是因为,保证人的错误系与不被视为“交往中重要的”——如第119条第2款所要求的那样——主债务人的特性有关。不过,事实上因错误进行撤销的权利也会因此被排除,因为双方当事人知道,保证的目的在于担保主债务,主债务人的真实财产状况因此属于保证人的典型合同风险,保证人不能在事后通过错误撤销而摆脱对这一风险的承担。如果婚礼,在合同订立时即被取消或者此后被取消,而买受人不知情,购买婚礼礼物的人同样不能基于错误撤销买卖合同。虽然这里有时也意味着,买受人处于不重要的“动机错误”中。不过,在这里排除错误撤销的真正原因也在于,买受人应当承担“使用风险(Verwendungsrisiko)”,也即买受人不能像合同订立时想象的那样使用标的物的风险。只要没有约定其他的风险分配规则,出卖人是否也知晓买受人的使用计划并无不同。
承租人也要承担租赁物的“使用风险”。因此,如果被某公务员(承租人)视为万无一失的到租赁房屋所在地的调任没有发生或者其因为其他“自身存在的原因”而不能使用租赁房屋,则该公务员不能基于错误而撤销租赁合同;参见第537条。
如果买受人错误地以为,他可以从其他地方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标的物,或者出卖人错误地以为,他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标的物,基于错误的撤销也将不被考虑。根据一般观点第191条第2款规定的撤销在这里将被排除,因为对买卖物价值的错误判断并非“交往中重要的错误”。不过,这从来不能使理智的人真正理解,为何物的价值不被视为“交往中重要的”物的属性。因此,在这里错误撤销被排除的真正原因也在于,买卖物的真实价值与约定价款之间的差距属于当事人的典型合同风险以及可能会破坏商业交易的安全性,如果出卖人因为“不太满意比其本来可以取得的更低售价,或者作为买受人因为同意了比本可获得货物的更高价款”即可撤销合同。⑤Larenz/Wolf, BGB AT, 8. Aufl. 1997, § 36 Rn.
因此,一般规则应当是这样的,只有当与当事人选择的风险分配规则不冲突时,才能踏上错误撤销的路径。法官必须尊重这样的风险分配规则,他们不得这样使那些风险分配规则落空,即允许某人因根据合同应当承担风险的领域中遇到的错误而撤销合同。⑥Kötz (o. Fn. 3), Rn. 300.
错误撤销与合同约定的风险分配规则之间的界线在其他欧洲法律制度中也是以类似方式划定的。《荷兰民法典》在其第6:228第2款中规定,如果错误“依据合同的性质、交易观念或者案件相关情事应由错误表意人承担”,因错误而发生的撤销即不被考虑。(刚刚新规定的)法国合同法在《法国民法典》第1133条第3款表示,如果“风险(un aléa)”的存在与物的某种特性相关,也即错误的“风险”已由错误表意人承担,对物的特性发生错误即无权撤销。“如果错误与错误风险被承担的情况有关,或者与应由发生错误一方负担的情况有关,”《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3.2.2条第2款b字母项即排除错误撤销。《欧洲合同法原则》第4:103条第2款b字母项亦是如此。在英国法上这一规则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⑦Vgl. zB Associated Japanese Bank (International) Ltd. v. Crédit du Nord S. A. (1988) 3 All England Law Reports 902: “从逻辑上说,在求助像错误这样的规则前……人们必须首先确定合同本身,通过先前的默示条件或其他方式,是否已经提供了相关错误风险应由何人承担的规则。在这一障碍上很多错误的抗辩要么会失败,要么被证明是不必要的。只有当合同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时,才存在诉诸错误规则的空间” (Richter Steyn S. 912). - 比较法上的叙述,参见Kötz, Eur. VertragsR, 2. Au fl. 2015, 225 f., 233 ff., 245 ff。
只要涉及的是第119条第2款规定的撤销,在判例和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支持这一一般规则的论据。在合同表现出风险行为特性时,因为合同明显具有投机或射幸的内容,这种撤销至少是不被考虑的。
例如在跳蚤市场上销售的旧乐谱,如果事后发现该乐谱出自莫扎特,出卖人不能主张撤销,如果乐谱被证明是赝品因而没有价值,买受人亦不能主张撤销。即便被销售的画作在合同中被宣称属于“尼古拉·普桑画派”,上文所述规则也应当适用:出卖人必须预料到,艺术史知识和物质技术能力在不断进步,因此专家鉴定人后来得出结论,该画作并非出自普桑画派,而是出自普桑本人,在这里出卖人也不能撤销合同。该案是法国最高法院2003年9月17日判决的案例(Bull. civ. 2003.I. no. 183):出卖人基于鉴定人于1985年10月25日出具的鉴定书而以160万法郎的价格卖出了该画。9年后出卖人依据错误主张撤销合同,因为在此期间鉴定人根据最新的知识认为该画作是普桑自己画的,其价值约为4500至6000万法郎。不过,法国最高法院认为撤销是允许的,因为出卖人在订立买卖合同时的确定意思是,该画作仅仅来自普桑“画派”,并且没有谈及,她已经承担了画作出自画家自己之手的“风险”(“ aléa ”)。
不过,如果被出售的是当事人认为属于某特定画家的图画,但事后发现,该画的著作权人是另外一位交易价格高得多的画家,人们也必须排除出卖人的错误撤销。虽然判例在此种情况中长期以来赋予出卖人依第119条第2款规定进行错误撤销的权利。⑧Vgl. RGZ 124, 115 - Ming-Vasen; BGH, NJW 1988, 2597 = JuS 1989, 59 (Emmerich) - Duveneck.不过,在文献中可以发现很好的理由来支持以下观点,即事后发现价值增加情事的风险应当由出卖人承担,因此应当拒绝赋予出卖人撤销权。⑨So v. a. Fleischer in Zimmermann, Störungen der Willensbildung bei Vertragsschluss, 2007, 34,附关于德国讨论状态以及比较法的丰富提示。作为艺术品的占有人,出卖人也总是具有检验艺术品属性的好机会,因此,在出卖人未经充分检验而以较少的金钱出卖艺术品时,这一错误评估的风险应由其自己承担。出卖人也知悉且至少应当预料到,买受人自己作为新占有人肯定会请人对画作的著作权情况进行调查。如果买受人在调查后得到的是消极的结果,因为发现画作是赝品或者出自不知名的画家之手,则出卖人可以通过约定排除瑕疵担保责任来防范这一风险。不过,对买受人通过进一步调查得到积极结果的情况,即发现该画作比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设想的价值更高,作出约定也属于出卖人自己的事情。因此,如果出卖人放弃了这样的约定,其也应当承担由此给自己带来的不利益。出卖人也必须预料到,买受人之所以(也)已经为该画作支付了约定的价款,因为买受人认为,在他的调查结论是积极的时,他将会被允许保有该画作。如果出卖人仍然可以撤销合同并请求返还该画作,则买受人可能会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实施出卖人已经同意或者至少没有反对的调查。⑩赞同这一结论的还有,对艺术珍品真实来源的说明存在公共利益且买受人寻找的刺激基于这一原因也不应当被贬低。荷兰著名的Kantharos判决参见Hoge Raad (Nederlandse Jurisprudentie 1960, 59) und dazu Kötz (o. Fn. 7), 229 f。
如果买受人对降低买卖物价值的属性发生了错误认识,并打算基于这一原因依第119条第2款的规定撤销合同及依第812条的规定请求返还价款(同时返还买卖物),则情况会有所不同。这也符合判例一贯的主张,即买受人应该求助第459条及以下条文规定的瑕疵担保请求权,而不能因为对能够产生瑕疵担保请求权的属性认识错误撤销合同。⑪BGHZ 78, 216 (218) = NJW 1981, 224 = JuS 1981, 459 (Karsten Schmidt).即便买受人不享有瑕疵担保请求权,因为它被合同约定排除了,错误撤销也将不被考虑。也即是说,否则会使“以排除瑕疵担保权利追求的风险限制几乎丧失价值”。如果瑕疵担保请求权不成立,因为向买受人提供的货物符合合同要求,则买受人虽然可能会因为对买卖物的其他属性发生错误认识而撤销(合同)。⑫BGHZ 72, 252 = NJW 1979, 160 = JuS 1979, 663 (Karsten Schmidt); BGHZ 78, 216 (218) = NJW 1981, 224 = JuS 1981, 459 (Karsten Schmidt).不过,对该观点可以这样抗辩,买受人已经以提供符合合同要求的货物履行了其债务(Schuldigkeit)。如果提供的货物尽管符合合同要求,也还是不符合买受人的期望,只要买受人没有使自己的期待成为合同约定的标的,则这是买受人自己必须承担的风险。因此,买受人在这种情况中也不能主张交易基础障碍,因为根据“买卖合同中法定的利益评价……通常买受人应当承担风险,其能否像原先打算的那样使用所提供的无物的瑕疵的买卖标的”。⑬BGHZ 74, 370 = NJW 1979, 1818 (1819) = JuS 1979, 902 (Emmerich).
我们不能否认,每个合同都与风险的分配具有一定的关联,因此,只要人们对该合同严加询问,从每一合同中都可以得出关于以下的内容的讯息,由一方当事人促使的不特定的错误想象或期待是否应由其负担,该当事人因此不能因错误而废止合同。如果他方当事人促使其合同相对方发生错误,或者如果他方当事人知悉或应当知悉错误,并违反义务地没有对错误作出说明,前述规则并不适用。不过,如果上述特定要件不存在,只要合同中未另有约定,则对约定给付真实价值的错误认识原则上应当由错误表意人负担。⑭Ebenso MüKoBGB/Armbrüster, 7. Au fl. 2015, § 119 Rn. 102 ff.
紧接着由Kramer就已经开始的对此问题的思考,⑮MüKoBGB/Kramer, 5. Au fl. 2006, § 119 Rn. 113 ff.根据Armbrüster的观点,对于是否存在第119条第2款规定的撤销权的问题,也取决于,“何人应当承担错误的风险。根据这一观点应当询问的是,表意人的错误想象是否应当完全由其负责,也即是说错误想象是否完全属于其风险领域,或者这一风险应由其合同相对人一同负责,合同相对人对交易有效订立的信赖因此显得不具有保护价值”。然而,合同当事人的信赖——正如上文所述——是不值得保护的,如果其自己(即便没有过错地)促使合同相对人发生了错误认识,或者如果其已经知悉或者应当知悉合同相对人的错误,却以不被允许的方式违反了向合同相对人予以说明的义务。即便根据英国法,无论是出卖人还是买受人都不得以错误的提示(“虚假陈述”)促使他方合同当事人发生错误。不过,合同当事人并不负担义务,不经询问、自发地作出这些提示。由此可知,“在不存在积极的误导性陈述时,各合同当事人应当自行承担主观情事被证明比当事人设想的更糟或者更好的风险”。⑯G. H. Treitel, An Outline of the Law of Contract, 5. Aufl. 1995, 160 f.
四、交易基础障碍
只要涉及的是交易基础发生障碍或丧失的情况,一个简单的提示就已经够了。对于这些情况多年来的判例以及自2002年以来新增的第313条也未令人产生怀疑,即关键取决于当事人所选择的风险分配规则。一般规则是这样的,“根据合同目的仅会落入一方合同当事人风险领域的情事,原则上并不适于使主张交易基础障碍成为可能”。⑰BGH, NJW 1978, 2390 (2391) = JuS 1978, 851 (Emmerich). Ebenso zB BGH, NJW 2000, 1714 (1716) = JuS 2000, 918 (Emmerich).
虽然偶尔有人主张,“只要某个难以忍受的、与法律和公平观念总是无法协调的事件不可避免时”,“合同信守原则”在这些情况中才允许退居二线。⑱So zB BGH, NJW 1977, 2263; NJW 1976, 565 (566).不过,这并不符合事物的本质,因为它完全不是对合同信守原则的限制。合同即是当事人据以从事行为的法律。法官应当将合同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因此,刚好是“信守合同(原则)”可以解释,合同中选择的风险分配方案决定着,原告还是被告应当承担案涉未曾预料到的情况或者期望落空的风险。⑲Vgl. dazu auch Kötz (o. Fn. 3), Rn. 1015.在例外情况下允许主张交易基础障碍或者丧失,无疑是正确的,在“未能预见的情事”已经发生,且一方合同当事人提出约定给付因此变得困难、不可能或者变得没有意义时,即是如此。⑳So BGH, NJW 1977, 2262 (2263); NJW 1978, 2390 (2391) = JuS 1978, 851 (Emmerich).不过,这一点也与以约定风险分配规则为基础并无两样,如果它们得到准确、充分的实施,这些风险分配规则完全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特定情事的发生超出了一方当事人承担的风险。如果合同中对此并无明确约定,则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第1款中可以找到值得推荐的限制风险的一般条款。
那里规定的是,如果任意一方能够证明,“不履行是由处于其影响范围之外的障碍原因引起,并且也不能合理期待该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将该障碍原因考虑在内,避免或克服该障碍的原因或其后果”, 该当事人对于其义务的不履行例外地无需承担责任。Ulrich Huber推测,《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与德国现行法虽然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规范技术”,但是,“在供货迟延与支付迟延的情况中,似乎倾向于得到相同的结果”。㉑Ulrich Huber, Leistungsstörungen I, 1999, 678; ebenso Kötz (o. Fn. 7), 373 ff.
即便是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对于交易基础具有共同错误,同样的规则也应当被适用。这一点现在被明确规定在第313条第2款中。这一规定虽然只是错误撤销法的特别法。㉒So mit Recht MüKoBGB/Armbrüster (o. Fn. 14), § 119 Rn. 116.这里也还是取决于“双方风险领域”的正确区分。
这种“双方风险领域”的区分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一则判决中是重要的,在该判决中原告是一家足球俱乐部,其从另外一家社团以4万马克的转会费“购买”了一名球员:原告由于交易基础障碍可以向被告请求返还这一费用,因为该球员在其转会前曾收受金钱而伪造比赛结果,并在合同订立后因为这一原因而被德国足协剥夺参赛资格。在此原告应当承担,球员在转会后不能提供期待的比赛表现或者因为转会前就已经遭受的运动伤害的迟发性后果而不能投入比赛的风险。反之,被告则“更为接近”承担以下风险,其雇佣的某个球员在转会前就已经被贿赂,且由于该球员因此面临被剥夺参赛许可,在转会后不再能够被原告使用。㉓BGH, NJW 1976, 565.——即便当事人遭受的是共同的计算错误,第313条第2款的规定也应当适用。如果计算错误是单方的,则发生错误的人既不能主张错误撤销,也不能因为交易基础丧失主张调整合同,“因为任何人,基于被认为是正确但事实上并不正确的计算基础算出特定的价格,并以该价格作为其要约的基础,也应当承担其计算正确的风险”。㉔BGHZ 139, 177 (181) = NJW 1998, 3192.
五、过错原则与风险分配
尤其在学说中经常有观点主张,德国合同法的重要基础在于过错原则,因此,如果一方合同当事人已经承担了担保(Garantie)或者从其他理由中可知,该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应当承担特定事件发生的风险,即属于与规则不相符的例外。对此Ulrich Huber已经正确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其认为,事实上“完全不是规则与例外的关系,而是一种不同责任原则的结合,它们相互限制与补充:担保责任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㉕Ulrich Huber (o. Fn. 21), 527; 也请参见有关过错责任与担保责任权衡的有说服力的一般思考, 31 ff., 524 ff。
正确的自然是,因债务人违反义务遭受损害的债权人,只有当债务人对义务违反应当负责时,也即债务人负有故意或过失时,才能请求损害赔偿(第280条第1款第2句、第276条)。正确的还有,如果债务人尚未提出已经到期且经催告仍无结果的给付,只有当债务人因迟缓已经陷于“迟延”时,债务人才必须赔偿债权人的迟延损害。不过,也只有当给付因为债务人应当负责的原因没有发生时,“迟延”才会发生(第286条第4款)。以及如果债务人因此没有提出给付,因为某个“在合同订立即已经”存在的障碍已经使其提出给付成为不能,则其在这种情况中也不负担代替给付的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债务人并不知悉该种给付障碍且对不知悉也不应当负责(第311a条)。
然而,在仔细考察时人们可以发现,立法者虽然在显著位置规定了过错原则,但因此也允诺了自己不能遵守的内容。通过课以债务人对过错的举证责任,也即在债务人不能证明自己的行为既无故意也无过失时,就让其承担责任,立法者自己就已经稀释了过错原则。
立法者自己也表明,过失标准应当“客观地”确定,也即是说,只要债务人未与债权人另有约定,其应当承担自己根据其个人关系未能如此谨慎行事的风险,就如同“客观地”对一个处于同等情形中具有平均能力的人所能期待的那样。也即是说,就此而言债务人承担的是一种担保责任,且该担保责任不因被隐藏在过失概念的定义之下而改变。
此外,在不是债务人自身,而是其履行辅助人的行为具有过错时,也被作为自己过错的情形看待。甚至,第278条的起草者就已经以如下理由说明了上述规则,如果债务人已经允诺了给付,“当今的交往从这一允诺中也可以(看出),(债务人)就其明示或默示允许的在给付时提供协助者的行为符合要求承担了担保”。㉖Mugdan, Mat. II, 1899, 16.即便债务人没有钱或贷款,借助这些钱或贷款债务人本可避免义务违反,也不取决于债务人的过错。
也即是说,一个未能妥善保管合同相对人物品的保管企业主,不能通过以下理由摆脱其责任,即证明自己已经无法聘请所需的看管人员,因为为此所需的金钱已经在自己并无过错的情况下花光了,并且他也不能通过银行贷款来获得这些钱。
为说明这一规则,学者们提供了多种理论。㉗Vgl. dazu ausf. Ulrich Huber (o. Fn. 21), § 26.不过,这一规则真实的原因可能也存在于,任何其他的风险分配(规则)都可能导致严重的法律不安定,也即可能会导致,法官在每一个案中都必需审查,债务人如他所主张的那样,因欠缺支付能力而不能履行给付义务——如果这是事实——是否存在一些债务人为维持其支付能力本应采取但因过失而没有采取的措施。㉘对此Ulrich Huber (o. Fn. 21), 629, 提请注意,在《民法典》咨询过程中第一委员会因此说道,对规则的任何偏离可能导致“不可接受的结果”,第二委员会则说道,规则“出于交易利益的考虑必须被肯定”。Vgl. Mugdan (o. Fn. 26), 25, 536 f。换句话说,债务人应当承担其支付能力的风险,对合同法如此重要,就好像疼痛之于人类的身体,丘吉尔曾经对此说过:“它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没有它身体又将会是怎样的呢?”
因此,土地的出卖人不必担心,买受人将来是否有支付能力,或者他是否满足银行愿意为其提供贷款的条件。因此,谋求在未获银行提供贷款的情况中使自己被免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合同约定不是出卖人的事情,而是买受人的事情。
将过错原则举到标签之上的法律规定,是任意性的。在第276条自身中就已经写道,更严格——不以过错为要件——的责任可以从合同“内容”,尤其是从对担保或者购置风险的承担中产生。不过,即便债务人试图通过主张其因某个障碍而依第275条的规定被免于给付义务为其责任辩护,该障碍“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经”存在且其在当时既不知晓也不可能知晓,这种担保通常情况下也应被肯定。第311a条第2款允许债务人提出这种辩护虽然是正确的,不过,从(经过正确解释的)合同中通常情况下也可以得出,债务人应当承担如下风险,合同订立时不存在依第275条的规定使其免于给付义务的障碍。
如果债务人愿意允诺,他作为承包商将在特定时间完成某个特定建筑物的建造,并向委托人交付,则他有所有机会与切实的理由在合同订立前检验,是否拥有足够的能力、人员、建筑设备、运行机构以及有给付能力的供应商和分包商,没有这些他可能无法准时兑现其合同允诺。如果出卖人向买受人允诺提供某物,事后发现,该物在合同订立时即已经被盗、扣押、没收或为第三人利益设定了物权法上的负担,亦是如此。如果出卖人或出租人在订立合同时就知道,买卖物尚不属于自己所有或者租赁物尚处于第三人的手中,同样如此:在这些情况中他们肯定会怀疑,自己可能无法及时取得所有权或者无法及时促使第三人返还租赁物。不过,这些怀疑失败的风险应由出卖人或出租人来承担,而不必还要去检验,曾经像实际发生的那样怀疑过,从他们的角度是否“应当负责”。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合同订立时均存在一定事由,它们让合同的可履行性显得不确定且处于允诺者的影响领域。如果允诺者不知晓这些情况,则他虽然会因以下原因发生费用,必须牢记这些情况并采取预防措施,确保其允诺的履行。不过,与允诺受领人被课以上述义务并负担由此产生的费用相比,这些费用无论如何都要低得多。在第311a条第2款生效之前,判例也以坚定的态度认为,允诺者应当确保其履行合同的能力,也即必须向允诺受领人提供代替给付的损害赔偿(或者依第284条的规定向其补偿产生的费用),而不必还要去检验,债务人对其允诺在将来可履行的信赖或者对此已经产生过怀疑,是否具有过错。㉙Vgl. Ulrich Huber (o. Fn. 21), §§ 22, 23, 附关于先前判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风险分配规则的详细且有说服力的论述。关于现行法,参见BGHZ 174, 61 = NJW 2007, 3777 Rn. 35 ff.; Kötz (o. Fn. 3), Rn. 1106 ff.; Looschelders, SchuldR AT, 15. Au fl. 2017, Rn. 658 f.,1224, m. Hinw. auf das umfangreiche Schrifttum. -也请参见第536a条:如果承租人的损害是因为,租给他的物“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经有瑕疵,则出租人必须提供赔偿,而不能以他认为物没有瑕疵无任何过错为由“免除责任”。这种做法在今天仍然应当坚持。第311a条第2款与此并不冲突,因为该规定是任意性的。
很多理由支持,即便在合同的履行因合同订立后发生的事由而无法实现时,也采取类似的风险分配规则,只要这些事由处于允诺人的影响范围内。然而,从第276条、第280条、第286条中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并且在很多情况中无法对过错原则的适用进行抗辩肯定是对的。比如从合同本身中就已经可以得出,债务人并未承诺特定的结果,而只是特定的努力,过错原则在那里必定是重要的:这里只有当债务人对不履行合同“应当负责”,也即违反其允许而做出不同于谨慎和理性的人在相同情形中可被期待的行为时,债务人才承担责任。即便债务人被请求损害赔偿,同样的原则也必须适用,因为债务人违反了合同上的“保护义务”。
比如,在债务人未对其销售场地的事故风险采取充分的保障措施并对买受人造成不利时,向旅店客人提供了有缺陷的设备,向发货人提供了不够干净因此有危险的运输工具,或者以其他方式未能尽到交往中对他方合同当事人“顾及其权利、法益或利益的”必要注意义务。㉚So § 241 II.
这些“保护义务”与由债务人在合同中允诺的给付没有关联。确切地说,债务人在这些情况中违反了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它们在德国只能称之为合同义务,因为这样可以弥补侵权法的特定不足,尤其是不成功的第831条的规则。㉛Vgl. Kötz/Wagner, DeliktsR, 13. Au fl. 2016, Rn. 321. 此外,根据德国法合同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可以向以下人员提供,完全不是合同当事人但总是为合同牵线搭桥者,或者可以作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的受益人者(参见第311条第2、3款)。对此的比较法介绍,参见Kötz (o. Fn. 7), 154 ff., 478 ff。不过这并不影响,在这些情况中——合同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究竟是装扮成侵权请求权还是合同请求权,是无关紧要的——必须停留在过错原则上。即便债务人允诺了特定的结果且该结果没有发生,根据德国法虽然也适用过错原则。不过,过错原则在这些情况中也只是作为一般规则;更严格的责任可以从合同的“内容”中产生(第276条第1款)。
在实践中,比如在债务人允诺提供种类物,因此在特定范围内承担了“购置风险”时, 这一点(更严格的责任)会发生。如果债务人向债权人“担保”提供符合合同的给付,但却提供了不符合合同的给付,并且也不想或没有能力,在事后通过修理或更换符合合同的货物纠正错误,债务人承担责任同样不需要考虑过错。然而,只有当从合同中可以得出结论,债务人为特定属性的存在承担了保证(Gewähr),并因此让人看出其愿意“为所有后果承担责任,如果这一属性不存在的话”, 根据判例出卖人才需要为其允诺的买卖物的属性负担此种“担保(Garantie)”。㉜BGHZ 59, 158 = NJW 1972, 1706 = JuS 1972, 725 (Emmerich) (stRspr)。 然而,在此不应——至少不是“首先”——取决于出卖人的意思,而应取决于,“在考虑出卖人其他行为以及促使合同订立相关情事的情况下,买受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并顾及交易习惯可得如何理解出卖人的表示”。如果不存在这种“担保(Garantie)”,则在这里仍然是,只有当出卖人或承揽人对提供不符合合同的给付“应当负责”时,也即不能证明他们的行为在这里既无故意,亦无过失时,才承担责任。
然而,在很多情况中实务对待这种过错要求直截了当。如果出卖人或承揽人自己即为给付的生产者,它会以粗暴的基本规则为出发点,谁作为生产者谨慎地工作便不会发生错误,谁生产了有缺陷的物即不够谨慎。
如果出卖人是买卖物的生产者,“在瑕疵出现时,比如因为买卖物不能按照合同预订的使用目的组装,则距离肯定行为有过错也不远了”。㉝BGH, NJW-RR 1989, 559 (560).事实上,在承揽合同法中可以找到不止唯一的判决,法院以各种形式确认了生产者提供的承揽给付具有瑕疵,而不存在过错时其本来可以免除责任的情况。BGHZ 59, 158(参见边码32)号判例就是这样:该案中被告生产者在60年代生产窗户框,窗户框的缺陷“直到1965年后才逐渐在学界及实务界被接受”,因此对于被告来说在给付时“一开始是无法预见的”。尽管如此,被告还是必须提供损害赔偿,因为被告对窗户框没有瑕疵——像人们当时所说的——已经“默示地担保了”,根据今天的表达方式也即:作出了“担保(Garantie)”。
不同的是,如果有缺陷的物是由第三人生产,并且出卖人作为“销售商”将该物未经改变地转售给了买受人,或者承揽人将有瑕疵的物安装进行了自己的工作物中,因此将整个工作物弄坏了,并以这种属性将工作物交付给了定作人。如果在这些情况中出卖人或者承揽人认为由第三人——多数是生产者——提供的物没有缺陷,则违反交往中必要的注意义务最多只能从他们没有事先通过特别的检查来确信没有缺陷就将物转交他人或组装中看出。反之,如果出卖人虽然没有进行这种检验,但他们的行为并未因此即有过错,因为他们在技术上无法进行检验、可能导致物被损毁或无法销售或者可能要负担无法承受的较高费用,因为他们不具有检验必要的知识或设备,他们并不承担责任。如果债务人不是生产者且检验对他们来说不太方便,债务人在这些情况中可以被“原谅”并以这一方式避免其责任,受到很多德国学者的批评。
他们尤其建议,生产者可以视为出卖人的“履行辅助人”,其过错依第278条的规定应如同自己的过错一般归责于出卖人。㉞So Schroeter, Untersuchungspflicht u. Vertretenmüssen d. Händlers bei der Lieferung sachmangelhafter Ware, JZ 2010, 495;Schlechtriem/Schmidt-Kessel, SchuldR AT, 6. Au fl. 2005, Rn. 610; Peters, ZGS 2010, 24; Weller, NJW 2012, 2312; MüKoBGB/Grundmann,7. Au fl. 2016, § 278 Rn.与第278条的规定,“履行辅助人”仅指债务人“为履行其债务”而使用的人,并且出卖人(以及依第651条的规定应根据买卖法承担责任的经营者)的“债务”仅在于使(买受人)取得物,但不在于其有缺陷的生产。然而,这种观点与这一情况有冲突,债法现代化以后出卖人根据第433条第1款的新规则总的来说不仅应当提供物,而且应当提供“没有物的瑕疵和权利瑕疵”的物,并且当出卖人的给付违反合同时,应依第437条第3项的规定提供损害赔偿或者费用补偿。这种观点也与欧洲其他多数法律制度所持的解决方案相冲突。㊱Vgl. dazu ausf. Kötz (o. Fn. 7), 357 ff. 如果合同根据联合国买卖法的规则判决的话,在德国也会作出不同的判决。In BGHZ 141, 129 = NJW 1999, 2440, 因此,出卖人依联合国买卖法第79条的规定必须向买受人提供损害赔偿,尽管出卖人只是作为单纯的“中间商”将由生产者提供的有缺陷的货物以原包装不经改变地转交(买受人)。
在荷兰的一个案子中出卖人向一个玫瑰花种植者提供了有缺陷的除草剂,该除草剂由其直接从生产者(一个化工厂)那里以已经包装好的形式购买,并以这一形式转售给买受人。出卖人应当提供损害赔偿,虽然不是因为过错——并不存在出卖人具有过错的案件事实——不过,可能是,因为出卖人根据“交往中通行的观念”已经承担了除草剂没有缺陷的风险。㊲So die Entsch. des Hoge Raad v. 27.4.2001, Nederlandse Jurisprudentie 2002, 1461。依《荷兰民法典》第 6:75 条的规定,如果债务人对于义务的违反没有过错及义务的违反也不能因此“算在他头上”,因为这是从法律、当事人的约定或者“交往中通行的观点”中产生的,则义务的违反不得归责于债务人。
如果在(经过正确解释的)合同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基础,即便在德国出卖人依第276条第1款的规定也会被课以相应的“担保”。如果出卖人能够知悉,买受人信赖买卖物没有缺陷、自己不具有对(标的物)是否符合合同进行检验的可能性,信赖出卖人基于其专业知识将会选择值得信赖的生产者,并且不愿就其产生的损害在生产商那里寻求补偿,该生产商不是由自己,而是由出卖人选择,因此买受人对生产者的商谈意愿、支付能力以及破产恒定性(Konkursfestigkeit)均不知悉,这一点(默示的担保)即应当肯定。如果出卖人认为这一责任太过严格,则他必须要看,他能否通过合同约定将这一责任完全或者部分地移转到买受人身上。然而,如果合同约定以一般交易条款的形式呈现,则这种合同约定必须考虑第305条及以下条文中就一般交易条款订入合同以及内容有效性所设立的特别标准。
六、合同义务的具体化
在一些义务的确定方面,其履行系基于合同而负担,由当事人所选取的风险分配规则也能够发挥作用。如果债务人在合同中并非允诺特定结果的发生,而只是特定的——有时经常也以结果为导向——费心或努力,就像医生、律师、投资咨询师或者税务咨询师所做的那样,尤其会提出这一问题。如债务人虽然允诺了特定结果,比如提供符合合同要求的买卖物(甚至可能已经提出了),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违反“保护义务”,也即没有以必要方式“顾及另一方的权利、法益以及利益”,给债权人造成了损害。
为阻止其为病人所开药品的副作用对病人造成损害,医生必须做些什么事情呢?如果因为建筑商的施工制造或提高了建筑工地发洪水的危险,并且因此危及委托人的所有权,建筑商应当采取哪些预防措施呢?冰球比赛的组织者应当怎样预防危险,避免已经购买了球票的参观者受到四下乱飞的冰球的伤害?经营者应当采取哪些措施,以便保护顾客交给其维修的机动车免遭第三人偷走的危险?
㉟BGHZ 48, 118 (121 f.) = NJW 1967, 1903 = JuS 1968, 40 (Emmerich); BGH, NJW 1968, 2238 (2239); BGHZ 177, 224 (235) = NJW 2008, 2837 = JuS 2008, 933 (Faust); BGHZ 181, 317 = NJW 2009, 2674 = JuS 2009, 863 (Faust); BGHZ 200, 337 (346 ff.) = NJW 2014, 2183.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关键的问题都在于,债务人根据(经过正确解释的)合同的内容向债权人作出了何种允诺,哪些风险应由他自己承受,哪些风险是由债权人承担。如果基于这些考虑可以确定,债务人已经违反了合同中承担的义务,则其反证自己并非因“过错”造成义务违反就没有存在空间了。㊳
比如可以认为,即便合同对此表示了沉默,二手车经销商负有义务,不经询问地向买受人告知其供出售的机动车的严重瑕疵。判例从以下情况中得出这一点,经销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并兼顾交易习惯”对此负有义务,并且买受人给予其的“信赖”必须兑现。不过,值得优先做的是仔细检验,经销商在合同中到底许诺了什么。如果他违反了这一义务,或自己已经承担了这些瑕疵的风险,在这里——基于马上要说到的理由——人们将得出结论,经销商负有告知严重瑕疵的义务。如果经销商承诺进行告知,但却并没有遵守,人们也不会怀疑,经销商的行为因此具有“过错”。
七、风险分配与合同解释
只要对此不存在明确的约定,在当事人之间应当适用特定的风险分配规则,可以以不同的理由来支撑。债务人必须为其经济上的给付能力承担责任,有时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以“交易利益(Verkehrsinteresse)”或“法律的安定性”作为依据。如果出卖人已经允诺给付种类物,则为何出卖人依第276条第1款的规定应在特定范围内承担“购置风险”,通常也不需要特别的理由。
反之,何时可以认为,出卖人或者承揽人就货物或者成果的属性符合合同要求向其合同当事人提供了“担保”,可能是不确定的。㊴Vgl. dazu den Text zu Fn. 32 ff.一方当事人是否承担了特定的风险,因此无权基于错误撤销合同,不能主张交易基础障碍,或者必须忍受从其所承担风险的实现中产生的其他不利,在其他情况中可能也是有疑问的。
因此,最后应当提出的一般性问题是,是否存在据以决定风险分配的统一的检验方案。由于当事人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约定,因此取决于补充的合同解释,也即——正如判例经常使用的公式——“当事人虽然没有表示出来,但本应当表示出来的内容,如果他们就悬而未决的点在其约定中同样会作出规定,并会同时注意到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习惯的要求”。㊵Vgl. zB BGHZ 16, 71 (76) = NJW 1955, 337.
为查明,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中“本应表达”的内容,人们必须想到,订立也应当包括对风险分配作出约定的“完整”合同,可能会因为较高的交易费用而失败。也即是说,在有漏洞的合同中应当补充的是当事人本可达成的约定,如果他们不必考虑支出的交易成本,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风险分配——原本会进行的磋商。也即是说取决于,当事人会将风险分配给哪一方,如果人们假定,他们在订立合同时掌握所需的全部信息,以便能够评估,各该风险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在这些情况中面临哪些费用或其他不利,以及各方当事人所需的费用,如果其承担了风险,能够采取防御这些风险的措施或者防范这些风险实现的不利后果(比如通过保险)。
这里面存在着判例在必须对此作出决定时需要考虑的核心本质,出卖人或者承揽人是否已经“担保”了货物或成果的属性符合合同。在其他情况中这些考虑也是适合的,因此,应当放手让法官去做,法官在缺乏明确的合同约定时,必须检验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哪些风险,该当事人承担的义务的具体内容为何,以及如果该当事人被一般交易条款课以上述义务,其是否因这一义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不当地”遭受了不利。㊶Vgl. dazu näher Kötz (o. Fn. 3), Rn. 77 ff., 272 ff., 343 ff., 1085 f.;“ 关于“通过法律及判例重建完整合同” 的一般介绍,参见Schäfer/Ott, Lb. der ökonom. Analyse d. ZivR, 5. Au fl. 2012, 433 ff.; Kötz, JuS 2013, 289 (295)。
在这种情况中当事人本可在对双方最为有利的方案上达成一致,在补充合同解释的过程中应当纳入到合同中的内容。虽然反对上述观点的人认为,在具体案件中缺乏用以评估一方当事人或他方当事人因承受风险而产生的费用所需的准确信息。
这里所持的观点,即未能预见到的风险应当像行为理性且合作的当事人在不产生交易成本时希望的那样去分配,也有反对者认为,这种方案虽然是有效率的,并且在将来可能使他方当事人受益,但并非“具体争议案件中的当事人”;这种方案与“第157条中表示有约束力的诚实信用并考虑交易习惯的标准根本不同”。㊷So Ulrich Huber (o. Fn. 21), 58 f.; Eidenmüller, Effizienz als Rechtsprinzip, 4. Aufl. 2015, 402 ff.事实上人们必须要允许法官不去注意这种有效率的方案,如果它与个案中对“诚实信用原则”提出的要求无法协调,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然而,人们还是希望,这一点被法官明确表达出来,并且公开承认其所选择的方案导致了效率的丧失。
在这里经常被忽视的是,这些信息可以由当事人贡献出来,只要它们由法官对其相关性作出了提示,这依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是允许的。即便缺乏这些信息,借助合理的估算以及经验价值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内容,就好像从诚实信用原则中得出的或被称之为“有益的”或者“合适的”未经详细论证而被认为是正确的结论。
无疑人们可以以这些考虑来说明,比如即便没有被问及,为何二手车销售商也应当告知供由其销售的机动车的严重瑕疵。这一结论可以用提出朴实的问题更好地证明,就这一点如果进行深思熟虑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中本可约定,销售商承担这种告知的义务。就其因此产生的费用销售商虽然会请求更高的价款。不过,由于那些销售商必须公开的信息对其来说是现成的(präsent)或容易获得的,其请求的价格补贴比顾客因此可能产生的费用要低,即虽然支付更低的价款,但顾客为此必须自己花(更多的)钱请人对机动车的属性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