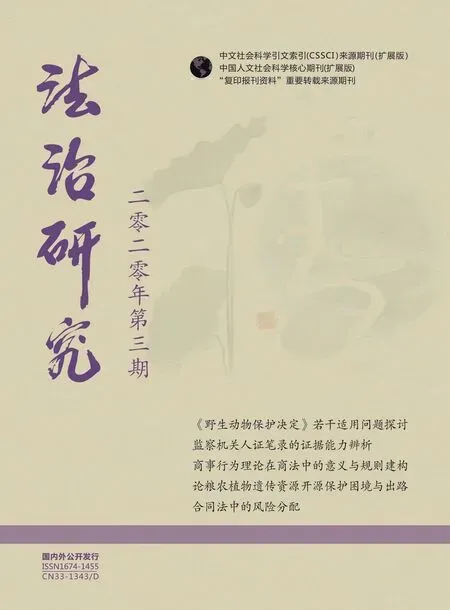行政行为如何说理:事实、规范和决定的法律证成*
2020-06-30刘东亮
刘东亮
学习法律,简单言之,就在培养论证及推理的能力。①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王泽鉴
决定法学方法之科学性的并不是涵摄,而是论证。②[德]考夫曼:《法律获取的程序》,雷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页。——考夫曼(Arthur Kaufman)
20年前,行政行为应当说明理由问题已经引起我国学界的关注。③参见章剑生:《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然而,时至今日,行政行为缺乏说理、说理不足甚或说理拙劣等现象仍然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上至国务院部委、省级政府,下到工商所、派出所等基层执法机构,行政行为的说理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形仍不乏其例。④例如,在日前由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的“郴州饭垄堆矿业有限公司诉国土资源部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被诉复议决定……未履行充分说明理由义务……依法应予纠正。”参见(2018)最高法行再6号判决书,2018年3月7日。在另一引发广泛关注的“杭州方林富炒货店广告违法行政处罚案”中,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山市场监督管理所〕对方林富炒货店使用“杭州最好吃的栗子”等绝对化用语的行为处以罚款人民币20万元,但缺乏充分说理。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维持了原处罚决定。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后,2018年5月21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判决将处罚决定变更为“处以罚款10万元”。2018年9月7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关于该案详细案情,参见(杭西)市管罚处字〔2015〕534号;(杭)市管复决字〔2016〕139号;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浙0106行初240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浙01行终511号。司法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裁判文书缺乏释法说理的情况相当突出,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专门下发指导意见,希望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0号)。另见该司法解释发布时所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文章《新时代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改革的功能定位及重点聚焦》,2018年6月1日。这意味着,研究行政行为如何说理,在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领域都是一个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一、作为法律论证之形式的行政行为说理
行政行为的说理,从程序法的视角看,体现为“说明理由”(reason-giving)这一环节;从更广泛的法的适用过程的角度看,则表现为“法律论证”(legal argumentation)。⑥单从汉语说,论证可视作较为正式的说理。参见陈嘉映:《说理》,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充分的说理,或者说,良好的法律论证,既能避免轻率、鲁莽的执法,有效控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又能使相对人明确知晓其为何承担某种法律后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服相对人接受行政决定,同时也可以为嗣后的司法审查提供基础和便利。⑦See H. W. R. Wade & C.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40~441(2014).
尽管行政行为说理的意义已经被学界充分揭示,但是,行政行为的说理在实践中却常常被忽视。原因何在?除了滥用职权、专断执法的少数情形以外,行政机关对如何说理认识不足甚至认识错误是一个重要因素。以前引“杭州方林富炒货店广告违法行政处罚案”(以下简称“糖炒栗子案”)为例,行政机关作出处罚的理由与逻辑是:
大前提:《广告法》第57条第1项规定,发布有本法第9条第3项所禁止使用的“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绝对化用语的广告的,责令其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小前提:当事人发布了“本店的栗子,不仅是中国最好吃,也是世界上最高端的栗子”“杭州最好吃的栗子”等为《广告法》第9条第3项所禁止的绝对化用语之广告;
结论: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使用违法广告,并处罚款人民币20万元。⑧处罚机关认为,之所以对当事人罚款20万元(而非100万元),是根据《杭州市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定》(杭政函〔2009〕274号)第9条的规定,当事人“未曾发生过相同违法行为的情形,且主动中止违法行为”,因而依法从轻处罚。也就是说,即使是20万元罚款,也已经属于“从轻处罚”。参见(杭西)市管罚处字〔2015〕534号。
上述推理使用了法律人都非常熟悉的三段论法(syllogism)。根据三段论推理,该处罚决定看似非常完美、无懈可击。因为三段论推理是一种必然性推理,其结论是由前提推出的必然结果,三段论推理因而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论证(valid argument)。三段论推理逻辑的有效性保证了从推理的前提到结论的“真值传递”,即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
然而,形式优雅的三段论并不一定属于可靠的论证(sound argument)。因为,从可靠的前提出发,是论证的基本规则之一。⑨[美]韦斯顿:《论证是一门学问》,卿松竹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三段论推理具备可靠性的基础是其前提的真实性。只有前提真实而形式又正确的三段论,才能必然地得出真实的结论。⑩参见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换言之,三段论虽然是一种必然性推理,但其能否得出正确结论取决于大、小前提是否为真,只有大、小前提均为真才能保证结论的“真值传递”。而在“糖炒栗子案”中,大、小两个前提的“真”均未经充分证立,特别是行政机关的“法律获取”犯有严重的过度简化和机械主义错误。简言之,行政机关在本案中并未完成全部法律论证,以证明其处罚决定的正当性(形式合法、实质合理)。或者说,行政机关在该案中有“推理”而无“论证”。⑪在欧美语境中,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一般不作严格区分。不过,在英美传统中更多使用前者,欧陆传统更偏好使用后者。熊明辉教授指出,尽管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非常相似,但它们还是有区别的。法律论证比法律推理更强调整体性。参见熊明辉:《诉讼论证:诉讼博弈的逻辑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71页;雷磊:《规范、逻辑与法律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另外,金岳霖教授等人指出,论证和推理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所不同。推理是为论证服务的,论证必须运用到推理。但推理只是断定前提与结论之间有必然关系或者或然关系。推理并不一定断定前提的真实性。而论证不只是断定论据和论题之间有必然关系或者或然关系,还由断定论据的真实性进而断定论题的真实性。因此,论证比推理要求的条件更多。一个论证必然同时是一个推理,但一个推理不一定同时是一个论证。参见前注⑩,金岳霖书,第287页。从这个意义上说,“糖炒栗子案”虽然经过了三段论推理,但并未完成证明其前提真实性的论证。——事实上,直到“糖炒栗子案”二审终结,甚至直到现在,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仍然不认为其处罚存在问题。这说明行政机关始终没有认识到该案中的说理(法律论证)存在缺陷,杭州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亦未能使其认识到问题之所在。⑫笔者曾和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律顾问及本案被告方委托代理人交流,他们至今认为,原处罚决定合法、合理,不存在任何问题。
长期以来,法律运作过程中相当重要的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理论,一直是我国法学研究的一块短板。虽然法理学界近年来已经尽了很大努力将域外先进法治国家的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理论引介入中国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其影响力尚未渗透到部门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中去。2002年,舒国滢教授将德国法学家阿列克西(Robert Alexy)的著作《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翻译为中文出版。⑬该书原为阿列克西1976年在哥廷根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其德文版1978年出版。参见[德]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以此为标志,域外较为成熟的作为法律论证之核心的“法律证成”(legal justification)理论才经“摆渡”(übersetzen)进入中国。2008年,司法考试大纲首次将“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的区分”列为新增考点,并在当年进行了考查。在此之前,很多法律职业人士根本不知“法律证成”为何物,遑论运用证成理论对法律决定的正当性展开论证。从这个角度而言,行政机关并不十分清楚行政行为如何说理,这个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却真实存在的问题,不过是恰巧借由具有轰动效应的“糖炒栗子案”适时显现出来而已。
二、实践理性主导下的法律逻辑、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
为深入理解法律证成理论,更好地把握行政行为如何说理,我们需要追本溯源,对纯粹理性和形式逻辑的局限性、实践理性主导下的法律推理与论证,以及图尔敏论证模型对传统三段论模式的修正等相关问题先予简要说明。
(一)纯粹〔思辨〕理性和形式逻辑的局限性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一种理性的(rational)动物。”⑭See Stephen Toulmin, Knowing and Acting,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54 (1976).理性作为人类所特有的先天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不仅使科学的发展成为可能,使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而且使得人类在已经到来的第二次认知革命中正在完成从“智人”到“智神”的物种升级。⑮参见[以]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93页;[以]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以下。
在人类依靠理性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过程中,逻辑学——按照康德的说法,理性和自己打交道的逻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认识工具,起到了重要作用。⑯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尤其是由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并构成传统逻辑(形式逻辑)之基础,完美体现人类纯粹理性(reinen Vernunft)之运用的三段论,更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⑰康德认为,纯粹理性是包含有完全先天地认识某物的诸原则的理性,是从理性自身,独立于经验而来,以普遍性和必然性为其特征的先验因素之理性。同注⑯,康德书,第14页。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常常把纯粹理性称为“思辨理性或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对应。在亚氏看来,三段论是一种近乎万能的推理形式。任何事物之间的联系都可借助于这一推理形式来探求,只要前提真实并遵循其推理规则,结论是必然的。⑱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前分析篇》,余纪元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158页。
纯粹理性和形式逻辑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然而,一旦逾越在先验运用方面的界限而闯入经验的领域,纯粹理性就无法站稳脚跟。因为在经验领域,并没有任何类似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公理,也不允许绝对地要求某种先天的原理。力图在经验领域适用纯粹理性,乃是不切实际的“纯粹理性的理想”而已。⑲同注⑯,第347、428页。同样,形式逻辑作为“纯粹的普遍的逻辑”,因抽掉了具体内容而成为单纯的思维形式,单靠形式逻辑无法实现对具体真理的认识。⑳从培根、穆勒、莱布尼茨到康德、胡塞尔和黑格尔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理论(归纳法对演绎逻辑的补充、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等)。在黑格尔看来,形式逻辑是研究科学尤其是经验科学的工具。作为工具来说,它是不可缺少的。但形式逻辑只能在有限关系(事物的简单关系)中作形式推论,仅仅靠形式逻辑不能够把握真理。黑格尔认为,应当运用辩证法对形式逻辑进行改造,也就是以辩证法为根据建立一门新的逻辑学——辩证逻辑。黑格尔关于形式逻辑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以及辩证逻辑的思想,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赞许与肯定,并撷取其“合理内核”,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唯物辩证法。同注⑯,第43页;[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2页、第83~85页;贺麟、张世英:《黑格尔关于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的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另参见张浩军:《胡塞尔的〈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因而,在经验领域,人们必须求助于“实践理性”。特别是在法律领域,人类理性体现出鲜明的“实践理性”(praktischen Vernunft)之特征。㉑“实践理性”,是康德提出的与“思辨理性”相对应的哲学概念,是指离开自然界的必然性而指导人的道德行为的主观思维能力。这一概念后被引入法哲学领域。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4页;徐向东编:《实践理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锐编:《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约瑟夫·拉兹的法哲学思想》,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二)实践理性主导下的法律逻辑、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
虽然形式逻辑尤其是经过数学化的形式逻辑具有跨情境、跨时间的一致性,其有效性不因时移世易而有异,但是,在对以三段论为主体的传统逻辑进行反思时,人们发现——特别是英国哲学家图尔敏(Stephen E. Toulmin)敏锐地观察到,在面对生活中的真实问题时,实际运用的逻辑具有明显的“领域依赖性”(the field-dependence)。换言之,用以证明推论结果合理性的标准或根据因领域的不同而有异。也就是说,在实际的论证过程中,以三段论为基础的论证并不具有代表性,起作用的逻辑并不是那种理想化的逻辑(idealized logic),而是各个领域各有其特色的“工作逻辑”(working logic)。㉒See Stephen E. Toulmin, The Uses of Argu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33, 135-194.后来,人们将图尔敏提出的这种反映实践理性的更加“贴近生活”的工作逻辑称为“实践逻辑”(practical logic)或“应用逻辑”(applied logic)。㉓参见[德]克卢格:《法律逻辑》,雷磊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宋旭光:《理由、推理与合理性:图尔敏的论证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页;同注③。受此影响,英国法哲学家拉兹(Joseph Raz)在1970、1975年先后出版《法律体系的概念》《实践理性与规范》,将法学、法律以及法律制度等概念化为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的内容。㉔See J. Raz, The Concept of a Legal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J. Raz, 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爱丁堡大学法学教授麦考密克(NeilMacCormick)进一步指出:实践推理是在需要作出选择的情况下人们运用理性决定如何采取正当的行动;法律推理是实践推理的一个分支,是法律活动的核心环节。㉕N. 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WORD (1978).
实践哲学在20世纪的复兴,以及实践逻辑、实践推理等概念的提出,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作用。20世纪上半叶,人们从认为法律适用就是三段论推理或者“涵摄”(Subsumption)而一度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否认逻辑的作用。如有德国学者认为,“在法律领域,逻辑毫无用处”(Julius Binder)。㉖同注(23),“译者序”,第8页。在英语世界,大法官霍姆斯(J. Holmes)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一直为人津津乐道。㉗霍姆斯的这句话实际上具有非常复杂的含义,逻辑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指出,逻辑和经验在行使司法职能过程中与其说是敌人,毋宁说是盟友。参见[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497页。比利时法学家佩雷尔曼(Chaim Perelman)评论说,在处理传统上什么是法律逻辑的问题时,有人宁愿在其著作中使用“法律推理”或“法律论证”之类的术语而避免使用“逻辑”一词。㉘参见[荷兰]哈赫:《法律逻辑研究》,谢耘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总序”,第4页。法律与逻辑的关系似乎渐行渐远。
20世纪50年代起,以克卢格(Ulrich Klug)、恩吉斯(Karl Engisch)等为代表的德国学者的开拓性研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逻辑对于法律科学的整体意义,并开始承认“法律逻辑”的存在。按照克卢格的界定,法律逻辑(juristischeLogik),简言之,是指适用于法律科学的逻辑。㉙同注(23),第7页。照此,需要追问的问题是:逻辑在法律运作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逻辑的作用是什么)?法律逻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法律逻辑的本质是什么)?
众所周知,作为认识客观世界的辅助工具,逻辑的作用是对推理和论证进行分析、评价。易言之,逻辑的作用在于,它提供恰当的标准帮助我们判断:假定前提为真时,我们能否合理地接受某一结论。㉚同注(10),第1~2页;[波兰]施特尔马赫、布罗泽克:《法律推理方法》,陈伟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 79 页。See also Frances Howard-Snyder etc., The Power of Logic,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 (2013).应当说,逻辑的这种作用是具有普遍性的,它在不同的领域包括在法律运作过程中都是一样的。当我们说某个法律论证不合逻辑时,意指它是不具有可信性的论证而不能被合理地接受。
然而,在法律领域,逻辑表现出某些独具一格的特点。比如,法律逻辑所使用的概念,其含义与普通〔形式〕逻辑的基本概念的含义存在明显的差异:
(1)逻辑学上使用的前提的“真”(true),尽管在法律逻辑上也使用同一概念,其真实含义却是“证成”(justified),且这种证成具有“可废止性”(defeasibility),当新的信息补充进来后,原来的证成有可能会失去效力。㉛同注(28),施特尔马赫、布罗泽克书,第61页。与之相应,法律逻辑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并非“真值传递”而是“证成传递”。㉜同注(30),施特尔马赫、布罗泽克书,第67页。
(2)逻辑学上的“有效论证”(valid argument)的本质特征是:如果论证的前提为真,其结论也必然为真。易言之,在一个有效论证中,前提和结论之间存在必然的(necessary)联系。但是,在法律领域,这种情况仅在极少数的简单案件中才会出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前提和结论之间无法做到100%确定的必然联系(很多时候也无必要)。从逻辑学角度看,这种论证显然属于“无效论证”(invalid argument)。然而,一个论证不是有效的,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没有逻辑价值。在法律论证中,如果前提仍可对结论提供有意义的支持,或者说,如果前提真,那么结论很可能是真的(但非必然),这种论证就属于“强论证”(strong argument)。在法律实践中,当我们运用法律逻辑评判法律论证时,将前提为结论提供支持的程度达到某一法定标准的强论证称为“有效论证”,意指我们整体上认可这一论证,虽然其属于逻辑学意义上的“无效论证”。㉝在极少数情况下,“弱论证”(weak argument)也是有意义的。比如,在行政法中,适用于即时强制的“有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指向的就是一种“弱论证”。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3)法律论证所追求的并非结论的“可靠性”(soundness)而是其“可信性”(cogency)。如前所述,在逻辑学上,有效性本身并不要求一个论证的前提必须真实,而是假设其前提为真;有效性只是保证前提和结论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当然,我们通常要求我们所进行的论证具有真实的前提,否则论证就会失去意义)。在前提为真并且推理有效的情况下,这种论证就属于“可靠论证”(有效+全部真前提=可靠)。一个可靠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conclusive)论证。相反,至少有一个前提为假的有效论证是不可靠的,所有的无效论证都是不可靠的。但是,如果把这样的标准照搬进法律领域,逻辑体系的大厦就会轰然坍塌。因为,所有的强论证都仅仅是逻辑学意义上的“无效论证”。所幸,法律逻辑所追求的并不是“可靠论证”(sound argument)而是“可信论证”(cogent argument)。可信论证,是指属于强论证并且其前提为“真”(证成)的论证(强+全部真前提=可信)。一个可信论证可能有假结论,因为其前提并不绝对确保结论为真。但是,可信论证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可信论证中,倘若前提真而结论假是不大可能的(强论证),并且由于其前提是“真”的,因此这种论证也是令人信服的。在人类认知能力有限并受到法律程序制约(如时限要求)的情况下,可信论证的结果,虽然不能绝对排除出错,但却是可接受的。㉞关于论证的有效性、可靠性、强度和可信度之含义及其区分,参见Frances Howard-Snyder etc., supra note 30, at 4-50.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法律实践中,论证的目标并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而是提高论证的强度和可信度。这体现出法律逻辑的鲜明特征:它所分析和评价的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是一种为法律决定的正当性提供理性基础的证明活动,而非像常规科学研究那样旨在探索唯一确定的答案。㉟当然,在“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时代,科学也面临着不确定性(uncertainty)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实践中的“工作逻辑”才被称为“法律逻辑”。有人否认“法律逻辑”的存在,认为如果存在特殊的“法律逻辑”就会存在诸如“草莓逻辑”“西瓜逻辑”等等一样荒谬,实则是没有充分注意前述图尔敏所说的实际论证过程中逻辑的“领域依赖性”。㊱例如,比利时学者卡林诺夫斯基早期即不承认存在“法律逻辑”,但后来其态度又发生变化。参见[以]霍尔维茨:《法律与逻辑:法律论证的批判性说明》,陈锐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9、110、138页。
因此,法律逻辑是受实践理性支配的实践逻辑,其分析和评价对象是法律运作过程中的实践推理与论证。这种实践推理与论证和传统的三段论相比有何不同,我们仍借助图尔敏的论证模型予以说明。
(三)图尔敏论证模型对传统三段论模式的修正
从人类一般的思维过程来说,三段论确实是一种经常应用的推理形式。但是,最早系统提出三段论理论的亚里士多德夸大了三段论的作用,他以为三段论就是推理的全部。㊲同注⑩,第152页。
受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影响,长期以来,三段论推理在法学上获得了根深蒂固的地位,几乎成为法律方法论上的“常识”。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现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才得以逐步改变。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英国哲学家图尔敏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图尔敏之前,主张形式逻辑包罗一切的唯理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在欧美思想界长期占据支配地位,其后果之一就是片面理解并夸大三段论的作用。在对人类理性和形式逻辑进行反思的基础上,1958年,图尔敏出版了《论证的运用》(The Uses of Argument)一书。㊳该书2013年修订再版,本文引用皆使用其2013年修订版。图尔敏指出,把论证简单地等同于三段论推理存在过度简化的危险(the perils of over-simplification),而这种严重的过度简化是很多传统逻辑理论的起点。事实上,三段论在各种实际的论证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并且,它简单得常常让人误入歧途,形式逻辑和认识论中的很多悖论都源自这种论证方式的误用。㊴See Stephen E. Toulmin, supra note 22, at 131-135.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论证,特别是对法律实践中推理与论证的细致观察,他提出了被后世称为“图尔敏论证模型”的一般论证方法。
图尔敏指出,在对某个问题进行论证时,我们会确立自己的主张(claim, C)即后来的结论,以及作为我们主张之基础的理据(data, D)。当我们面临对方的质疑时,在事实之外,我们会诉诸某些有助于证明我方主张但不同于理据的依据(warrant,W)。㊵图尔敏认为,理据和依据的区别是:理据的采用是明确的(explicitly),而依据是隐含的(implicitly)。此外,依据是广泛存在的,以证明所有适当类型的论证的可靠性,其产生方式不同于我们从事实中得到的理据。理据和依据的差别有点像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区分。比如,我们可以辩称,某个出生在百慕大的人可以推定为英国人,因为相关法律为这一结论提供了依据。See Stephen E.Toulmin, supra note 22, at 92-93.这样,论证过程可以形象化地表示为:

图1 图尔敏论证模型(基本)
在这一基本的论证框架中,由于理由多种多样,对于其所证实的结论可能产生不同强度的效力(必然、很可能、大概等),因而需要加上限定语(qualifier, Q)对论证效力的强度进行明确提示。对于规则适用可能存在的例外,需要给结论设定条件、提出例外以允许反驳(rebuttal, R)。此外,为了加强论证,应当允许对依据提出佐证(Backing)。这样,把所有这些论证的特征考虑进来,论证过程就可以表示为:

图2 图尔敏论证模型(一般)
必须指出,图尔敏的论证理论绝非一个简单的论证模型所能涵盖,而是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智识背景和宏大理论抱负。㊶同注(23),第52页以下。图尔敏通过观察法律实践概括出的一般论证模型,由于其鲜明的认识论特色(更关注实践中真实的论证)而使《论证的运用》一书成为论证研究的现代经典,并因此成为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诸多学科的重要思想资源。㊷参见阿姆斯特丹大学Frans van Eemeren教授为该书修订版所撰写的说明(该书英文版扉页)。尤其是,图尔敏论证模型揭示出的实践逻辑和实践推理的特征,反过来又对法律论证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20世纪70年代法律论证理论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认识论根基。在简要阐述了图尔敏论证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再“返回法的形而下”,以阿列克西的法律证成理论为线索,深入分析法律论证过程中如何实现事实、规范和决定的证成。
三、法律论证过程中的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
众所周知,由于法律问题往往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作为法律确定主义和〔权威〕决断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法律论证理论应运而生。㊸参见[德]诺伊曼:《法律论证学》,张青波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不难理解,民主和法治国家原则要求,任何法律决定都应当建立在理性论证的基础之上。
1971年,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IVR)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五届大会将“法律论证”作为大会的议题。此后,法律论证理论成为各种国际和国内法哲学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一大批法学家在此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德国学者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在该著作中,阿列克西在道德分析哲学、当代语言哲学、图尔敏的一般论证理论、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论、埃尔朗根学派(Erlangene Schule)的实践商谈理论和佩雷尔曼的论证理论等诸多学说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的法律证成理论。
(一)法律论证理论的集大成者:“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理论
阿列克西认为,法律论证是一种发生在不同场合(如诉讼、法学研讨等)的言语活动。由于这种言语活动有待在进一步精确化的意义上来讨论规范性命题,因而,可以把这种活动称为“论辩”(Diskurs, discourse)。而且,由于牵涉到规范性命题的正当性,可以进一步称之为“实践论辩”。㊹同注⑬,第18页。规范命题亦称“道义命题”,是含有“必须”“允许”“禁止”等规范词语的命题。与传统逻辑的真假不同,规范命题无所谓真假,只存在正当与不正当、合理与不合理的问题。由于法律论证的大前提和结论都属于规范命题,因此,法律逻辑本质上属于“道义逻辑”。而法律论证是普遍实践论辩的一种特殊情形。㊺把法律论辩当作普遍实践论辩的特殊情形的重要意义在于,某个规范或某个具体的命令,一旦其满足了论辩规则确定的标准,就可以被称为是公正的。同注⑬,第22、263、265、272页。
阿列克西指出,法律论证是对规范性命题的特殊情形即法律判断的证立/证成。㊻阿列克西指出,“证成”(Rechtfertigung)和“证立”(Begründung)这两个概念很大程度上可以互换。舒国滢教授也认为,这两个汉语单词,就像其对译的德语单词一样,是可以互换的。同注⑬,第41页,第274页。如果对法律证成的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的证成: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㊼“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之概念最早见于波兰法哲学家弗罗布列夫斯基(JezyWróblewski)1971年提交给布鲁塞尔国际法哲学大会的英文论文“法律决定及其证成”(Legal Decision and its Justification)。该文提出了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的区分,强调内部证成具有演绎的结构,而外部证成是对内部证成所需要的前提的正当性的证立。参见[德]阿列克西:《法·理性·商谈:法哲学研究》,朱光、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同注⑳。
所谓内部证成(interne Rechtfertigung, internal justification),是指法律决定必须按照一定的推理规则从相关前提中逻辑地推导出来。换言之,内部证成所关注的是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推论是否有效,而推论的有效性依赖于其是否符合推理规则。为此,阿列克西从内部证成最简单的形式(法律三段论)出发,推导出一系列内部证成的规则。比如:“欲证立法律判断,必须至少引入一个普遍性的规范”(J.2.1);“法律判断必须至少从一个普遍性的规范连同其他命题逻辑地推导出来”(J.2.2),“需要尽可能多地展开逻辑推导步骤,以使某些表达达到无人再争论的程度,即:它们完全切合有争议的案件”(J.2.4);“应尽最大可能陈述逻辑的展开步骤”(J.2.5),等等。㊽同注⑬,第277~282页。
内部证成的意义在于检验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的有效性,这对于那些非简单案件即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之间缺乏直接联系或者说存在“跨度”的案件而言尤为重要。在内部证成的过程中,愈来愈清楚的是:到底什么样的前提需要通过外部证成(externeRechtfertigung, external justification)加以完善,从而使那些可能隐而不彰的前提条件必须明确地予以表达,并把存在断裂的论证链条补充完整。㊾同注⑬,第284~285页。
所谓外部证成,是对内部证成使用的各个前提的证立。这些前提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1)实在法规则(;2)经验命题;(3)既非经验命题亦非实在法规则的前提。阿列克西认为,与不同的前提相对应的是不同的证立方法。他将外部证成的规则和形式分为六组,分别是(:1)解释的规则和形式(;2)教义学论证的规则和形式;(3)判例适用的规则和形式;(4)普遍实践论证的规则和形式;(5)经验论证的规则和形式;(6)所谓特殊的法律论述形式。㊿既非经验命题亦非实在法规则的前提,大多是法律与事实的混合问题,如“硫酸是否属于武器”。同注⑬,第285页以下。另见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辅导用书编辑委员会编《: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辅导用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2~63页。
应当说,由于内部证成关涉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有效性,属于法律证成的核心问题;外部证成虽然只是对前提真实性的证立,但对于保证法律论证的可信度同样重要。鉴于在当下中国的法律实践中,外部证成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我们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的外部证成,再予分别论述。
(二)法律规范的证成:从一般规范到个案规范的具体化
从法律证成理论的视角来看,每一法律规范的适用同时也是一个规范证成的过程。这一证成过程,是从发现实在法上的一般规范到证成适用于特定案件的个案规范的过程。易言之,寻找“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即法律的获取程序,经历了发现(process of discovery)和证立(process of justification)两个阶段。(51)在英美法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瓦瑟斯特罗姆(Richard A. Wasserstrom)1961年提出了法律规则的“发现过程”和“证立过程”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二阶证成程序”(two-level procedure of justification)理论。麦考密克在1978年提出的“二阶证成”(second-order justification)理论与其非常相似。SeeRichard A. Wasserstrom,The Judicial Decision: Toward a Theory of Legal Justification,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7 (1961); N. MacCormick, supra note 25, at 100.在德国,恩吉施较早提出法的“发现”与“证立”的区分。参见[德]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有关该问题的中文文献,可参见焦宝乾:《法的发现与证立》,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
为什么需要区分法的“发现”和“证立”呢?盖因,从一个抽象的命令(大前提)直接逻辑地推论出具体的命令,基本上是不可能的。(52)[德]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以容易理解的“故意杀人”为例,刑法规定了“杀人者死”,但这一条款不一定能直接适用,因为有时杀人或属于“正当防卫”。这样,应该适用的规范是“杀人者死+正当防卫”。或许,杀人者的“正当防卫”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形,应当适用的规范又变成了“杀人者死+正当防卫+防卫过当”。最终,刑法上的多个条款在对照特定案件的事实以后经整合而形成的具体规范才是应当适用于该案的法律规范,即“个案规范”。
1.“个案规范”的证成:法律规范的具体化
“个案规范”(Fallnormen)是德国法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概念。1975年,慕尼黑大学法学教授菲肯切尔(Wolfgang Fikentscher)指出,大部分法定规则都不能由法官以单纯涵摄方式直接适用,而必须作进一步的具体化,由法官依据法定规则,考量受裁判个案的情况,形成具体的规范。这个真正的裁判规范就是“个案规范”。借此规范,受裁判的案件事实被赋予适合它的法效果,因此,该规范可谓是“技术意义的法条”。(53)参见[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页。——在菲肯切尔提出“个案规范”概念之前,英国法哲学家拉兹在其1970年初版的《法律体系的概念》一书中专章研究了“法律的个别化”(the individuation of laws)问题。根据拉兹的说法,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等方式,有权机关只是创立了规范的一部分,规范所包含的其他部分,通常还需别的机关另行创造。See J. Raz, The Concept of a Legal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0 (1980).
按照个案规范理论,立法者规定的法律条文,并不是一种完全被立法者预先厘定的行为准则,而只是为法官裁决提供证立理由、有待进行检验的“法材料”与“法理由”,是需要进行个案加工的初级产品。英美法系亦有类似的说法,哈特(H.L.A.Hart)称其为规则怀疑论(rule skepticism)〔的温和版本〕。按照这种理论,“在法院适用之前,任何一个法律规则都不是法律,而只是法律的渊源(sources of law)”。(54)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202 页;同注(36),第210页。换言之,脱离了具体案件裁判的规范并非真正的法律规范,只有与个案事实相互映照,得出的适用于当下个案的个别规范,才是真正的裁判标准。外部证成的目标即在于从大量法材料中挑选并证立这样一条个案规范,它才构成了内部证成的大前提。(55)参见雷磊:《规范理论与法律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177页。
个案规范理论的形成源于对法律实证主义和传统涵摄模式的批判。在严格的实证主义者看来,制定法就是理所当然的存在,是不必考量其内容与背景即应适用的权威命令。(56)参见[德]德莱尔:《拉德布鲁赫公式:认知抑或信仰?》,吴香香译,载雷磊编:《拉德布鲁赫公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42页。这种对制定法不加分析地予以适用的实证主义,由于相信“法律就是法律”,使德国法律界在纳粹统治期间毫无自卫能力,来抵抗具有专横的犯罪内容的法律。在此方面,实证主义根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证成法律的效力。相反,它相信自己已经根据法律背后的权力证明了法律的效力。(57)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苏国滢译,同注(56),第9页。二战结束后,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urch)等人提出:当实在法同正义的冲突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以至于作为“不法”(false law, unrightigesRecht)的法必须让位于正义。(58)参见柯岚:《拉德布鲁赫公式的意义及其在二战后德国司法中的运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雷磊:《再访拉德布鲁赫公式》,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1期。
在实证主义的科学理论与法律理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从19世纪到20世纪),人们认为,法律适用的唯一形式是将案件涵摄(Subsumption)于制定法规范之下。涵摄是最简单和最确定的三段论,也就是演绎。这种模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将法律科学(Rechtswissenschaft)证立为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努力。(59)同注②,第1、58~59页。
然而,将法律适用仅仅归结为涵摄是一种无法企及的理想。这种臆想出来的理想不仅认为制定法是一个完美、自洽、封闭的体系,而且将法官降位为自动售货机或者孟德斯鸠所称的制定法的“奴隶”。说得好听些,将法官视为计算机,一种进行“0和1”“非此即彼”二值运算的计算机。这类法官不熟悉“或多或少”“亦此亦彼”,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法律领域普遍存在的”模糊性(ambiguitätstoleranz)这种东西。每个法律适用过程一定能够得出某个必然的结论。(60)同注②,第1、7、59、60页。
如果把法律适用仅仅理解为涵摄,那么,理想的裁判者就是一台没有灵魂的机器。对此,慕尼黑大学法学教授考夫曼(Arthur Kaufman)指出,单纯通过涵摄无法获得司法判决,某种意义上它只是确认了已获得的法律结果。作为演绎的涵摄只是一种事后的正确性控制机制(nachträgl icheRichtigkeitskontrolle),即“波普尔可证伪性”(Popper'sFalsifiability)意义上的机制。准确地说:借助于演绎,人们只能证明某事是错的,而无法用它来证明某事是对的(正面证立)。然而,多数时候,人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因为有经验的法律人在日常生活的常规案件中,没有意识到存在着先于涵摄的程序行为——考夫曼称之为“法律获取”(Rechtsgewinnung)程序——他们看到的只是涵摄。
考夫曼指出,决定性的行为发生于涵摄之前,此即从实在法一般规范到个案规范的证成过程。(61)同注②,第5、6、27页。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这一过程是法律规范“道成肉身”的过程。
依菲肯切尔之见,个案规范的证成可简述如下:法官一方面应考量等待判断的具体案件事实,凭此以具体化及特殊化其由法律或法官法中取得之标准及评价观点;与前述作法同步,法官亦应以其认为适切的法律观点为据,以补充必要的案件事实,使之更趋精确;两者必须一直持续进行,直到不能再为正当的个案裁判寻获任何新观点为止。菲肯切尔将这种规范与案件事实间的相互接近、交互澄清的程序称为“诠释的程序”,中断此程序的时点为“诠释的转折点”。菲肯切尔指出:“以事理及平等的正义为标准,假使进一步的凝聚不能再使规范更特殊化,表达案件事实的概念也不能再细分,我们就达到前述的转折点了。”透过这个程序最后达到的凝聚作用,既提供了个案规范,也确定了待判的个案事实,并因此能对此事实作出评价。(62)同注(53),第22页。这一“诠释的程序”,即法律人耳熟能详的恩吉施的名言“目光在规范与生活事实间的顾盼流转”(Hin-und Herwandern des Blickes)。(63)从一般规范到个案规范还有一个所谓的“约根森困境”(Jørgensen Dilemma)问题,意指从一般规范能否逻辑上推导出个别规范,或者说逻辑是否适用于规范领域。该问题由约根森(JürgenJørgensen)在1938年的一篇论文中最早提出。参见施特尔马赫、布罗泽克,同注㉚,第57页;雷磊:《走出约根森困境:法律规范的逻辑推断难题及其可能出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舒国滢:《逻辑何以解法律论证之困》,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笔者认为,所谓的“约根森困境”是否真实存在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约根森困境”提出的问题“规范不能被赋予真值”在逻辑学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法律论证中,事实和规范的“真”实际上都是“证成”,即一种被认可、被接受的“真”而非必然的“真”,因此,对这一所谓的困境之担心是多余的。
在上述个案规范的证成过程中,有两个重要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个案规范证成中的法律解释及融贯性之要求,二是法律规则与原则的关系之处理。兹分述之。
(1)个案规范证成中的法律解释及融贯性要求。由于法律语言有着所谓的开放性结构(open texture),因此,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64)同注(54),第193~194页;同注①,第166页。不仅疑难案件的处理需要法律解释,即使那些语句平实看似不会产生任何争议的法律条文甚至是数字也需要解释。(65)比如,在1985年的美国诉洛克案(United States v. Locke)中,有联邦法律规定,土地权利人应当进行初始登记并每年进行更新登记。关于年度更新时间,该法规定,权利人应当在每年“12月31日之前”(prior to December 31)向州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交年度更新登记申请,如果权利人未能满足这些要求,其不合要求的行为“应当不容置疑地被认为是权利所有人放弃了采矿权”。洛克家族向土地管理局提交了初始登记,以后也按照要求每年进行更新登记。但是,1980年,他们在12月31日提交了年度更新申请——按照土地管理局的说法,迟了一天。由于登记申请迟延,政府通知洛克家其权利被放弃,并随后宣布矿山被没收。这一案件后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See United States v. Locke, 471 U.S. 84 (1985).
根据萨维尼(F. C. V. Savigny)的解释,解释是“对制定法内在思想的重构”。法律解释需要考虑四种要素:语法要素、逻辑要素、历史要素和体系要素。(66)由萨维尼最先提出的这四种解释要素,成为此后法律诠释学相当固定的组成部分,第87~88页;另同注②,第148页。据此,法律解释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历史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虽然各种解释方法具有不同的功能,在选择具体解释方法时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次序”(gesicherteRangordnung),但是,现今大部分法学家都认可下列位阶:(1)语义学解释;(2)体系解释;(3)立法意图或目的解释;(4)历史解释;(5)比较解释;(6)客观目的解释。(67)同注(51),第95 页。另同注(50),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辅导用书编辑委员会书,第66页。当然,这些解释方法并非在每一个案件都会用得到。事实上,在一个法律体系较为成熟的法治国家,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这两种最重要的解释方法已足以解决大部分案件。
无疑,文义是解释的基石。文义解释是指从法律语言的字面含义说明法律规定的内容。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黄金规则”(Golden Rule),它意味着文本的字面含义起支配作用,除非出现荒谬的情形。(68)See M. Z. Johns & R. R. Perschbacher, The United States Legal System, 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33 (2012); 另同注①,第189页。体系解释也称系统解释,是指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一法律规范都是统一的法律体系整体的一部分,也是某一法律部门的一部分,其功能的发挥或实现是以其与其他规范的相互配合为条件的。诚如古罗马学者塞尔苏斯(Celsus)所说:“若未考量立法之整体,而仅按其中些许片断,即作出裁判或答复,实为不当。”(69)[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德国法哲学家施塔姆勒(R.Statmmler)亦曾言“:一旦有人适用一部法典的一个条文,他就是在适用整个法典”。(70)同注(52),第73页。这种说法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足以说明体系解释的重要性。体系解释是保证法律体系融贯性(Kohärenz, Coherence)的基本要求。融贯性要求法律体系各部分之间相互支持与证立,这既是对法律体系的道德要求,也是法治的目标之一(维护法秩序的统一)。(71)融贯性不仅仅是指逻辑一致性,一致性是融贯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关于融贯性的充分条件(尽可能多的理由,这些理由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且理由之间相互支持和印证),参见[瑞典]佩策尼克:《论法律与理性》,陈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162页。另参见雷磊:《融贯性与法律体系的建构》,载《法学家》2012年第2期;侯学勇:《法律论证的融贯性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以下。
(2)个案规范证成中规则与原则的关系之处理。“个案规范”理论是否有过分轻视实在法本身的规范作用之嫌呢?菲肯切尔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法律固然不能直接适用,但对于如何获得个案规范,它划定了界限并提供指引。(72)同注(53),第23页。易言之,个案规范的证成需要从实在法上的一般规范即立法者确立的法律规则开始。法律规则具有推定的优先适用性。从民主的视角看,经由民主程序与机制产生的代表大多数公众意思的法律规则,作为立法机关的一种权威指令,具有排他性的功能。裁判者应该尊重权威指令的拘束力,也就是说,裁判者首先应当以规则而非以自己的权衡或判断作为裁判的理由。相反,如果在有规则的前提下不首先尊重规则,反而去寻求规则以外的理由,就违反了法治的基本要求。(73)同注(55),第 89~90页。正如肖尔教授(Frederick Schauer)所说,法治的许多美德都在于将规则作为规则来认真对待。(74)[美]肖尔:《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律推理新论》,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不过,在有些案件中,严格适用法律规则会产生异乎寻常的错误或者极端不公正的后果,此时裁判者就需要运用法律原则为规则的适用创造例外。(75)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法律原则不同于法律原理或法理(Doctrines of Law),前者是被确认为法律规范内容的准则,后者是对法律之事理所作的具有说服力的权威性阐述,是法律的公理或法律的教义、信条。适用法理的内容更为复杂,本文不作讨论。易言之,此时就需要特别证立(special justification)。在此情况下,裁判者运用法律原则并未违反“法律规则具有推定的优先适用性”这一预设,因为法律原则同样是有效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法律原则的优先适用只具有个案的效果,而没有普遍的效力,也就是说,在其他案件中法律原则能否优先于法律规则的适用需要再次进行个案论证。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一方面推定规则具有排他性的功能,另一方面需要保持推翻这种推定的可能。规则所具有的是一种弱的、推定的排他性。(76)同注(55),第 90、177~179页。
在依据法律原则提出例外规则时,实际上是根据原则修正、建构新的规则,或者说是将原则转化为规则。德国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法律原则的具体化”(Konkretisierung des Prinzips)。(77)同注(53),第348页;舒国滢:《法律原则适用中的难题何在》,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根据这一理论,规则和原则均为个案规范证立的基础。对此,有学者评价说,法律规则构成法律制度的刚性部分,法律原则构成其柔性部分。理想的法律制度是保持法律制度主体的刚性和硬度,同时也保有一定的柔性和开放度。法律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通过其柔性和开放度来软化过于刚硬的规则体系。(78)同注(55),第59页;舒国滢:《法律原则适用的困境——方法论视角的四个追问》,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糖炒栗子案”中的个案规范证成问题之简评
在(杭西)市管罚处字〔2015〕534号文书中,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对于违法广告,对其适用的法定行政处罚为: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并对广告主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非常明显,处罚机关的法律解释在广告法规定的处罚措施中添加了一个“并”。而对于为什么要在明确的法律条文之中增加这个“并”,处罚机关没有作出说明。
我们知道,《行政处罚法》是规范行政处罚领域的基本法律,行政处罚行为的法律适用不能完全抛开《行政处罚法》。对广告违法行为的处罚既要考虑《广告法》的相关规定,也要考虑《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5条、第4条第2款和第27条分别规定: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
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行政处罚法》第5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第27条)
对于上述《行政处罚法》中如此重要的条款和规定,“糖炒栗子案”的处罚决定书居然毫无反映。可以说,执法机关在该案中存在明显的“怠惰”行为,而未完成个案规范的证成。而当法律推理的任一前提不为“真”时,不能指望其结论的正确性。
众所周知,法律规范纷繁复杂是行政法的一大特点。如何从叠床架屋、多如牛毛的法律规范中找到所有相关法律(规则、原则)并对照特定案件的事实,证成适用于该案件的个案规范,是对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执法能力的挑战与考验。
(三)案件事实的证成:从生活事实到法律事实的建构
在无数的法律争端中,有关事实的评断起着决定性作用。假如人们对有待承认的规范没有异议的话,那么一个裁判(决定)将只取决于其所依据的是什么样的事实。(79)同注⑬,第288~289页。
在事实认定过程中,正如菲肯切尔所言,规范与案件事实是相互接近、交互澄清的。(80)同注(53),第22页。也就是说,个案事实的认定和个案规范的证成是同时进行的。而且,事实认定并不纯粹属于运用证据予以证明的认知过程,它同样也是一个证成的过程,或者说,是从生活事实到法律事实的“建构”(construction)过程。
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细展开案件事实的证成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在从生活事实到法律事实的建构过程中,应当着力避免那些本可以避免的严重扭曲事实的“叙述谬误”(Narrative fallacy)。(81)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事实在本质上信赖于语言”,该命题在法律领域的体现尤为明显。量子力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测不准原理”。在量子尺度的微观世界中,测量结果必然受到测量手段的影响,不存在不受测量者影响的“客观测量”。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对事实的叙述也不存在丝毫不受叙述者影响的“客观叙述”,不同程度的“叙述谬误”无处不在。虽然如此,在证立案件事实时,那些对事实不当取舍、过分剪裁而导致事实严重变形的“叙述谬误”需要努力避免。(82)当然,单靠叙述者本人无法避免“叙述谬误”,而必须借助于论辩和反驳。这正是法律论证(阿列克西所说的“实践论辩”)的意义之所在。
以“糖炒栗子案”为例,处罚机关没有考虑方林富炒货店在其店铺内使用“杭州最优秀的炒货店”和商品包装袋上印有“杭州最好吃的栗子”等用语是否属于“违法行为轻微”,致使其处罚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是不完整的。(83)前注⑦指出,处罚机关之所以对当事人罚款20万元(而非100万元),是根据《杭州市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定》第9条的规定,当事人“未曾发生过相同违法行为的情形,且主动中止违法行为”,因而依法从轻处罚。该从轻处罚并不是根据“违法行为轻微”。参见(杭西)市管罚处字〔2015〕534号。更重要的是,处罚机关对生活事实和法律事实之间的分野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众所周知,生活事实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事实,只有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生活事实才能上升为法律事实。正如一审法院所指出的,方林富炒货店使用上述绝对化用语的行为是否会真正误导消费者,“商品是否真如商家所宣称‘最好’,消费者自有判断”。(84)参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浙0106行初240号。同个案规范的证成问题一样,处罚机关在该案中也未完成其应该完成的法律事实之证成。
如前所述,处罚机关在处罚决定书中承认:“当事人未曾发生过相同违法行为的情形,且主动中止违法行为……。”若照此理解,再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及危害后果,在证成个案规范时需要考虑《行政处罚法》第27条第2款的适用。但由于处罚机关的事实认定不够全面,其法律获取的结果也因而产生错误,并因此导致了错误的处罚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确是“相互接近、交互澄清”的。
四、行政行为如何展开说理:说理的内容和形式
在梳理了法律论证中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的相关理论之后,我们再来探讨本文的核心问题,即行政行为如何展开说理。
(一)说理的内容:说理的“黄金圈规则”(3W规则)
说理的目的是进行说服。行政行为的说理,是为了说服包括作出决定者自己在内的所有与本案有关的当事人,以及可能的复审机关和不在场的社会公众,说服他们相信并接受自己为什么作出如此决定。因而,“为什么”是行政行为说理的核心内容。论证,简单地说,就是讲出为什么、所以然。(85)同注⑥,第193页。
出于掌控外部世界的类本能需要,人们总喜欢寻找事物之间的因果,凡事先问“为什么”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从儿童时代起,追寻“为什么”就成为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信念。当我们不断追问“为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弄清楚事物的性质乃至世界的本原和人生的意义。探索“为什么”的心理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人类决不会善罢甘休。在要求解释行为“包括行政行为”时,最终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追问:“你为什么这样做?”(86)参见[英]布鲁斯:《社会学的意识》,蒋虹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因此,要想最大程度地说服他人,关键不在于传递“是什么”(what)和“如何做”(how)等信息,而在于给出那些深层次的“为什么”(why)的理由。有人说,说服他人的最高境界并不是供需之间的匹配,而是达成信念的契合,即我们都认同应当、必须这么做。(87)参见[美]涅克:《从“为什么”开始:乔布斯让Apple红遍世界的黄金圈法则》,苏西译,海天出版社2011年版。虽然该书探讨的是营销的理念(营销的最高境界不是兜售商品而是营销思想和信念),但其中揭示的心理学法则对行政行为的说理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英国上议院曾经在2004年的一个案件中指出:“行政决定的理由必须明白易懂,并且这些理由必须是充分的理由。它们必须能使读者理解某一事项为什么(why)这样来确定,根据‘最重要的争议问题’得出了什么(what)结论,显示出某些法律或事实问题是如何(how)解决的。理由可以简要叙述,所要求的具体程度取决于有待裁决的问题的性质。……”(88)South Bucks District Council v. Porter (No 2)[ 2004] UKHL 33,[ 2004] 1 WLR 1953, para.26 (Lord Brown), see H. W. R. Wade &Christopher Forsyth, supra note 7, at 443-444.在行政行为的说理内容问题上,英国上议院这一判决的见解非常精辟。它揭示出,在展开说理时,行政机关应当说明其作出了何种行政决定(what)、这一决定是如何作出的(how)以及它为什么(why)作出如此决定。与此相应,在后续的司法审查程序中,法院可以分别运用实体性审查、程序性审查和过程性审查等三种审查方法来复审这三方面的问题。(89)参见刘东亮:《过程性审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方法研究》,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5期。
在我国,当前,行政机关一般都能明确说明作出了什么样的行政决定;随着程序意识的提高,行政机关一般也能交待清楚它是如何作出行政决定的(经过了什么环节、步骤,是否经过听证等)。然而,行政机关对于它为什么作出某种决定,在说明理由时常常存在欠缺。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并便于实践中理解掌握,行政行为的说理内容之要求可简示如下:why-how-what,即为什么,怎么做,是什么。该要求可称为“行政行为说理的黄金圈规则(Golden Circle Rule)”,亦可称为“3W规则”。
(二)说理的形式:对话式说理、反思性说理、商谈和论辩中说理
由于行政行为的说理是一种具有公共话语特征的思维和表达形式,说理是为了提高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说服行政行为相对人、作出决定的机关自身和不在场的社会公众,因而,其说理形式表现出“对话式说理、反思性说理、商谈与论辩中说理”等特征。
1.对话式说理:从对话的视角理解并展开法律论证
有先哲很早就指出,法学的思考方式并非直线式的推演,而是一种对话式讨论。(90)参见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由于行政行为的说理属于公共说理,当然不能自说自话,行政机关在说理时必须要有对方意识(就像我们写论文时要有读者意识一样)。简言之,说理是一种“对话”(dialogue),而非作决定者的“独白”(monologue)。(91)从说理与论证的角度而言,并没有所谓的“单方行政行为”。传统行政法学所认为的“单方行政行为”,是警察国家时期“高权”理论的产物。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不存在所谓的“单方行政行为”。
事实上,行政行为的说理不仅是一种对话,而且还是一场“三人谈”——由作决定者、相对人和不在场的“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参与其中的对话。所谓批判性公民,是指那些立场中立、通情达理并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社会公众,或者说,“批判性公民”就是一个正常的理性人(a reasonable person)。当然,在说理过程中,“批判性公民”始终作为听众而存在,对话的直接参与者——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互为言说者和听众。在行政行为的说理中,“批判性公民”不是可有可无的。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最终要由“批判性公民”来判断。在嗣后的救济程序中,“批判性公民”的角色则由复议机关和复审法院来承担。
如前所述,行政行为说理的核心内容是“为什么”,是对最终决定及其前提的法律证成。基于此,荷兰学者洛德(A.R. Lodder)提出了刻画这一过程的对话模型(dialogical model)并将其称为“对话法律”(Dialaw)。洛德认为,法律证成应当被对话式建模,并在这种对话模型中处理法律的开放性、法律证成的可废止性和所谓的“明希豪森三重困境”。洛德指出,一个法律命题的可接受性依赖于其证成的品质,而证成的品质最好能在一个法律证成的对话模型中来判定。(92)参见[荷]洛德:《对话法律:法律证成和论证的对话模型》,魏斌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以下。由于对话需要借助于语言,而语言的使用方法对说理效果有明显影响,因此,研究说理必须研究语言,这属于论证的修辞学问题。鉴于论证的修辞学进路相当复杂,需另作专门探讨,本文暂不涉及。
2.反思性说理:作出决定者通过自我批判说服自身
行政行为的说理,不仅仅是为了说服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不在场的“批判性公民”,也包括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自身,以克服其固有的诠释学意义上的不当的“前理解”或“成见”(Vorverständnis)以及由此形成的错误认知。这是作为正当程序之本质的“反思理性”(reflexive rationality)的要求和体现。(93)关于“正当程序”与“反思理性”,参见刘东亮:《还原正当程序的本质:“正当过程”的程序观及其方法论意义》,载《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Handelns),行政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交往实践”(kommunikative Praxis)。哈氏指出,交往行为自身当中潜藏着批判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使各方主体在交往与沟通过程中通过反思进行自我控制,即通过反思调整自己的要求、主张与行为,从而为最终达成共识创造条件。不难设想,在交往实践中,我们努力为每一项要求提供充足的理由;理由的质量和分量可能会遭到质疑;我们遇到不同意见,可能会被迫对原初的表达进行修正。从这个意义上说,说理与论证可看作是换了其他手段通过反思对交往行为的一种继续。(94)[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20、25页。
比利时法哲学家佩雷尔曼亦指出,谁要是诉诸“普泛听众”(auditoireuniversel),他也是在诉诸自身,因为其自身也是这种听众中的一员。那些连讲话者自己都不相信的主张和那些连讲话者本人都不接受的建议,均排除在面对普泛听众的论证过程之外。(95)参见注⑬,第212页。
根据前述洛德的对话法律模型,行政机关试图证成某个决定可以被建模为一个两人对话(twoperson)的博弈。证成者交替扮演攻击该决定的角色和为该决定进行辩护的角色。在这种“自我批判”的对话博弈中,当最终实现两方博弈主体与证成者自己相一致的情况时,行政决定才能被证立(justified)。(96)当然,如果最终达不成共识,论证的可接受性由“批判性公民”来判定。同注(92),第31页。
3.商谈和论辩中说理:通过理性的沟通作出行政决定
说理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说理是用语言说服别人而不是用暴力压服别人。在这个意义上,行政行为的说理即哈贝马斯、阿列克西等人所说的“商谈”和“论辩”(Diskurs,discourse):通过理性的沟通、商谈和论辩得出最终的行政决定。
商谈理论属于程序性理论的范畴,其核心问题在于商谈规则体系的设立与证成。为此,在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的基础上,阿列克西提出了商谈程序(理性论辩)应当遵循的五组论证规则和一组论证形式,包括:无矛盾性、语言的清晰性、经验真值性与真诚性、对结果的考量与权衡等等。这些规则共同构成了法律商谈的理性支撑。(97)同注⑬,第234~256页。
民主和法治国家原则为理想的行政行为商谈情境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任何能够言说者都允许参加论辩;任何人均允许对任何主张提出质疑,任何人均允许表达其态度、愿望和要求;任何人均不得受到论辩之内或论辩之外的统治强迫的阻碍而无法行使上述权利。(98)参见阿列克西提出的五组论证规则中的第二组规则。同注⑬,第240~241 页;另同注(43),第88页。可以说,通过商谈、论辩进行说理,是理性的制度化要求,说理也因此成为一种维护民主生活秩序的伦理价值。(99)参见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
五、结语
有先贤曾指出,说理的艺术在民主法治国家非常重要,因为公民是通过正当化的理由被说服的,而不是通过武力被征服的。(100)Thomas Jefferson,参见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每一位执法人员,可以不知道图尔敏、哈贝马斯、阿列克西等法律论证理论家的大名,但不能不知道作出法律决定需要充分的理由,不能不知道说理的基本规则与要求。
事实上,说理不仅是一种话语伦理,更是一种思想能力,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所说的“以言行事”(to do things with words)。(101)参见[英]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特别是行政执法人员,经常地、有意识地做到恰当说理,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判断和说理能力,并能够在此基础上维持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法治秩序。(102)同注(99),,第27页。从这个角度而言,尽管本文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法律论证和说理的所有问题,但仍然希望我们提出的说理的“黄金圈规则”(说理内容的三要素:“what”“how”“why”)和说理形式的三要义(“对话式说理”“反思性说理”“商谈和论辩中说理”)能够对改善我国当下的行政行为说理状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