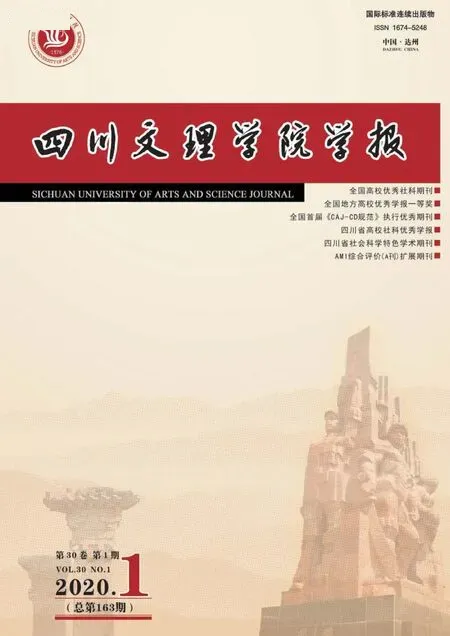飘零何处归:杜诗地方感的历时性考察
2020-02-24魏烈刚
魏烈刚,肖 舒
(1.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苏区研究》编辑部;2.江西省新建一中,江西 南昌 330100)
地方感是一种经过社会和文化特征改造过的特殊人地关系,是人们对于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和认同,并一直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近年来,随着地方感理论逐渐渗入文学研究,文学作品中有关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等的考察也逐步显见。但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解读和研究,对中国古代诗人和诗作的考察较为鲜见,这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空白点。①本文拟结合地方感理论中有关地方体验、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等概念维度,选取了杜甫一生中几个重要的居处空间,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杜诗地方感的生成及演变过程,从而进一步深化杜诗地方感理论研究。
一、长安:忆昔开元全盛日
二十岁始,杜甫先南下吴越,后北上齐赵、河洛,进行了十年的漫游。诗人“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②品味江南景色,“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玩味先秦韵事,这一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漫游生活增加了诗人的阅历,增强了诗人的审美领悟,也培养出诗人积极向上、奋发图强的豪情。不论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望岳》,还是“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的《登兖州城楼》,诗人在对齐赵、吴越和河洛一带的书写中,展示出一种“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的自信,充溢着一股浪漫主义的情调和理想化的色彩。正是带着这种浪漫的地方想象,杜甫踏入长安,开始了十年漫漫求仕生涯。
地方与意义生成。长安居大不易,历经科举、干谒双重失败的杜甫穷愁潦倒,“朝叩富儿们,暮逐肥马尘”,“买药都市,寄食朋友”。对烈风而生百忧,出入富贵门却又处身于社会底层的诗人杜甫更加敏锐地察觉到歌舞升平的唐王朝早已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天宝十一载,杜甫会同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同游慈恩寺,写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诗人笔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的景象,实则是山河破碎、清浊不分,京都朦胧、政治昏暗的现实状况的隐射。在遍游长安曲江、美陂、乐游原、骊山风景名胜,仔细吟咏和细致描绘长安风物的过程中,杜甫逐渐将个人心绪融入对于国家命运的思考,从而赋予了都城长安更为深刻的地方意义。
地方与家国兴衰。杜甫不仅熟知长安风物名胜,而且对长安盛衰与大唐国运之间的关联有着深刻的领会。曲江是长安城最著名的游览胜地。曲江畔修筑有唐玄宗的离宫,玄宗带着杨家兄妹春日游宴于曲江、芙蓉苑,冬日去骊山避寒。这里还是欢宴新中进士的场所,由此演化为功成名就、飞黄腾达的一种地方象征。杜甫的《丽人行》即以此为背景,展示出春日曲江游宴的盛况和玄宗及杨氏兄妹的荒淫无耻,它由此成为了唐王朝繁荣浮华的一个地方注脚。安史之乱后,被迫滞留长安的诗人日日徘徊潜行曲江江头,吞声而哭。曲江见证了唐王朝的繁华,此刻又转化成了“国破山河在”的地方标志。在对曲江的书写过程中,杜甫赋予了曲江较之一般名胜更多的政治象征和文化意蕴,由此也凝聚了诗人于国于家于个人命运更深层次的感悟。
都城与身份体认。“辨华夷是为了定尊卑,明差异,核心在于确立以京师为中心的文化优势,进而树立天子的政治权威。”③虽然仕途不顺、困顿窘迫,偶有“归山买薄田”的念头,但杜甫依旧固守长安,足见诗人对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的执着和对都城长安所代表的政治文化地位的高度趋同。安史之乱后,诗人流落异乡,对于长安的身份体认在远离长安的漫长生涯中得以觉醒和凸显,长安成为兼有故乡、国都和精神家园三重身份的地方空间。这种地方身份认同在其晚年的大型回忆组诗《秋兴》等诗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些融合了诗人崇尚、怀恋、感伤等多重情感的回忆诗作中,诗人主动过滤掉了十年长安求仕中的辛酸与苦楚,掺杂了大量的美好幻想和复杂浓烈的思想意绪。不论是“蓬莱宫阙”“珠帘绣柱”,还是“锦缆牙樯”“武帝旌旗”,都让回忆中的长安散发出绚丽的光彩,这其中灌注了杜甫对长安极度思念的强烈情感,也包蕴了极为复杂的地方象征意义和政治企望。可以说,诗人笔下的长安已经超出了都城的概念范围和地理位置的实指,升华成为诗人体验生命情感和维系人生意义的重要原点。
二、成都:处处无家处处家
杜甫迫于生活所累,自洛阳回华州,又自华州到秦州、同谷,而后“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于乾元二年岁末来到成都,度过了十年巴蜀漂泊生涯。四川相较于中原更为安定,安史之乱爆发后,“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西南重镇、天府之国成都因其经济富庶、文化繁荣,成为杜甫投奔的目标。依靠着亲友的周济和帮扶,杜甫在成都郊外浣花溪畔修筑了草堂,度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草堂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让杜甫短暂地获得了生活上的安定和心理上的慰藉,由此也引发了诗人对于成都草堂的依恋情感。
“恋”的地方书写。“孰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杜甫在草堂度过了一段悠闲愉悦、诗意盎然的田园时光,其诗作中充分流露出对于草堂环境和草堂生活的热爱:“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历尽磨难的老妻画纸下棋,无忧无虑的儿女敲针钓鱼,画面如此优美,令诗人心旷神怡。杜甫避乱梓州期间,对成都草堂流露出深深的情意:“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我有浣花竹,题诗须一行”。当有机会再回草堂时,诗人百感交集,情难自抑,写下“处处青江带白蘋,故园犹得见残春。雪山斥候无兵马,锦里逢迎有主人”的诗句。诗中“故园”“主人”等语词的使用,表明杜甫已经将成都草堂当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回到草堂,但见“入门四松在,步屟万竹疏。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酤酒携胡芦。”诗作中“不忍竟舍此,复来薙榛芜”及“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情感抒发,展现出诗人对草堂深深的依恋和甘愿终老于此的心愿。杜甫入严武幕时,沉闷枯燥的幕府生活令杜甫心情始终不大舒畅,他一再流露出想归返草堂的心情:“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当离去已成事实,卧病云安的杜甫仍作诗《怀锦水居止二首》,细致描绘出“万里桥南宅,百花潭北庄。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的盛景,以此抒发对草堂的深深依恋。
“家”的意义建构。“松菊新沾洗,茅斋慰远游。”历经战乱的杜甫对于“家”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他曾数度拟建草堂——西枝村、成都浣花、夔州瀼西及东屯都曾营建有草堂。初营成都草堂时,“大官遣骑,亲朋展力,客居正复不寂寥也”[1]。杜甫投入巨大心力参与营建:在此寻觅桃秧、绵竹、桤木,栽种松树、果树;在此营草堂、筑水槛、买小舟。在这安静、富饶的四川平原上有了一个安栖的“家”,诗人的心境变得悠闲自在,诗风也一扫前两年的惊惶凄苦,表现出惬意自得、闲散疏放的情趣。杜甫颇有意趣地留意起日常的起居,过起了诗酒为伴、妻儿相依的生涯:“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这些诗句处处流露出一种“在家”时方存的安定感。草堂环境幽僻,诗人甚至懒得梳头:“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懒得穿衣:“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这种“疏懒意何长”的闲散中虽偶尔流露出孤独之感,但其中不乏对当下处境的适意和对草堂生活的喜爱。当然,这种在异乡建构起来的“家”的情感并不稳固,杜甫对于原乡的回归渴望依然在诗作中时隐时现。随着诗人在四川的生存处境恶化,其对于家园的思恋和回归的渴望开始占据上风。林美清曾如此评价《怀锦水居止》:“杜甫豁然劈下的结句‘惜哉形胜地,回首一茫茫’瞬间粉碎了原本清晰的想念,颠覆了精心营建的怀想,在翻覆天地之际,揭露了绝望后的豁达:处处无家,处处为家。”[2]
“栖”的审美追求。“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在对草堂环境的书写中,自然山水的文化功能和审美功能得以充分展现。杜甫将其敏锐的观察力运用于对锦城春夏秋冬四季,尤其是草堂明媚春光特征的把握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裛红蕖冉冉香”,这些诗句令人“每诵数过,可歌可舞,能使老人复少”。草堂满足了诗人对于宁静悠远生活境界的追求,也由此成为其逃避政治生活和功利环境的最佳场所。诗人在诗作中有意强化一种与世隔绝的幽居氛围,用“屏迹”“高卧”来营造一种安隐的心理状态:“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在选址、营建、花木栽培上,处处体现出诗人的精神意趣和生命价值取向:“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在林泉僻地中度过诗酒生涯,成为诗人一度的人生追求:“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事业只浊醪,营葺但草屋。”草堂生涯中,杜甫完成了生活方式世俗化、空间栖居诗意化、日常交往平等化、时间体验持续化的艺术个性创造和人生价值拓展。
三、夔州:万里悲秋常作客
杜甫自幼生长于以中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这里既有家园这一生活据点,也有都城这一政治生活的依托。安史之乱后,诗人被迫脱离北方空间,这种违背自身意愿的强制性空间位移对诗人观察事物的基点、地方身份定位以及文化体认的转变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隔”的空间感受。流落西南后,诗人笔下的空间已不再是一个圆融的整体,而是呈现出分割的态势:杜甫大量使用异方、天畔、天涯、他乡、天边、绝域、天隅、殊方等语词来称呼西南地区,与家园、长安、中原等“中心”意味形成对立。在诗人心目中,西南地区的陌生、冷僻,是被抛弃、被放逐,是远离中心、远离熟悉;而北方空间则是熟悉、亲切,是理想的归属,是充满了意义的家园指代。这种主观上的空间割裂,透露出诗人截然不同的情感倾向和地方意义指代,也展现出诗人对于自身所处空间的定位和人生际遇的深刻理解。杜甫常常在诗作中呈现出一种“北望”抑或是“回首”的身体姿态:“垂白乱南翁,委身希北叟”,“北阙心长恋,西江首独回”,“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寒空见鸳鹭,回首忆朝班”。这种姿态是对客观的空间阻隔的一种无声抗议,展现出诗人“身在此而心在彼”的心里状态,通过“北望”和“回首”,诗人意图在心理上同熟悉的北方取得哪怕一点点的趋近,由此获得一丝丝的心理安慰。夔州时期,诗人将所有情感投注于遥远的北方空间,在回忆和思恋中大幅度提升着固有的地方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诗人对于寓居地地方感的建构。正因如此,诗人始终对于夔州地区缺乏稳固的地方认同。
“客”的身份定位。身份感的建立是人寻得自信的基础。即使在成都草堂最为安闲的时光里,杜甫的客居意识和回归意识仍然执着而强烈。常年客居、漂泊无依是杜甫巴蜀生涯及晚年湖湘生涯最为深切的体悟:在梓州诗人浩叹“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在夔州江岸诗人悲慨“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流落湖湘时诗人自称是“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地方连续性的缺失会引起身份感的缺失,进而引起地方焦虑。相较于成都的繁华富庶,夔州地理位置偏鄙、远离政治中心且风土人情特殊,在诗人眼中不啻为一个陌生的居处空间。因病留滞于此的杜甫在此地停留时间越长,就越发感受到不适和惶恐不安,被放逐的苦闷和边缘化的焦虑始终影响着其地方认同的建立。“老病巫山里,稽留楚客中。”杜甫以“久客”自居,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摆脱客居身份,重新回归故土、寻回主人身份的渴盼和期待。
“异”的文化体验。生长于北方、饱受诗书传家传统熏染的杜甫对以两京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当他被迫居留夔州,其本土意识与巴蜀文化之间的冲突得以凸显,从而令其难以在当地产生新的地方认同。不论是“顿顿食黄鱼”的饮食习惯、“畬田费火声”的刀耕火种,还是“峡人鸟兽居”的巢居方式、“封内必舞雩”信巫好祀习俗,均令诗人难以适应,因而产生“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的主观感受。而“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的生活风俗,以及“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的不事读书、行商重利的社会风俗,与中原的社会分工及儒家轻商传统大相径庭,更令杜甫十分不满,引发了诗人的生存焦虑。夔地民风特异,对外乡来客的情意,似乎不及成都。“形胜有余风土恶”仅仅是从文化风俗层面上提醒着诗人身处异地、远离故土的现实处境,而“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的人情淡薄,则是导致诗人对夔州缺失认同感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远离故园的失落激发了杜甫对北归的长久渴望,而未能融入当地习俗和生活环境,更是加深了诗人与当地文化的隔膜感,从而加剧了其在异域生活的痛苦和长久的地方排斥心理。
四、湖湘:何异漂漂托此身
时常迁徙的人往往无法准确定位自身所处的地方,自然不能对当地产生依恋和认同。大历三年,杜甫乘船出瞿塘峡,东下江陵,晚秋离开江陵,南往公安,又乘船南下到岳阳,再入洞庭,前往衡州,又图北归,遇战乱避难衡州、郴州,终病故于江船。如果说漂泊西南初期诗人曾试图找寻“家园”之感,那么历经晚年漂泊生涯,诗人已经找寻不到与所在地方的关联,进入一种“无地方感”的状态。
方向感的丧失——迷。湖湘时期,杜甫以船为家,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漂泊生涯。在旅途中,杜甫并非没有安居的打算,他曾流连于岳麓山的美景和风土人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但隐居的梦想终于落空。寒食节前,诗人饮酒赋诗:“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云白山青万馀里,愁看直北是长安。”青山白云阻隔了诗人望断长安的愁眼,“天上坐”、“雾中看”不仅描绘出舟中飘荡起伏及眼花昏蒙的情状,更展现出对如隔雾看花般多难时局的忧伤感怀和个人茫茫前路的迷失之感。最终,大大小小的内乱与边患令诗人北归无望,南去渺茫,江陵难留,诗人发出了无家可归的悲鸣:“易下杨朱泪,难招楚客魂。风涛暮不稳,捨棹宿谁门。”“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芜。”颓丧悲观的心态混杂着前路茫茫的无措,这种“失路”的浩叹在其湖湘诗作中喷薄而发,成为诗人自身身份感和地方定位缺失的最佳注脚。
身份感的丢失——弃。远游的目的何在?杜甫应杜观的邀约出峡,将妻儿寄放于当阳三弟家,自己拟前往江陵谋生。他初始寄希望于荆南节度使卫伯玉的赏识,未果;后辗转投靠韦之晋,不意韦忽然病故,诗人再次陷入困境中。为了谋求生计,诗人不得不同官僚们应酬周旋,求人接济,“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这就免不了“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处处被排挤、遭鄙薄无处容身的艰难境遇的现实处境令诗人无法找寻到原有的身份感,因而孤独感倍增。而故园阻隔有家难归的无望混杂着战乱频仍流落逃难的困苦、生活窘迫无以为生的悲凉,令杜甫发出“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的呐喊。《江汉》诗曰:“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一个“一”字,杜甫屡用,用以写其孤苦处境。诸如“乾坤一腐儒”,“天地一沙鸥”,于乾坤、天地之内,下此一字,一个“孤”字充分展现出其微茫的心境。诗人最终丧失了最后的企望,衍生出“百年同弃物,处处是穷途”的弃置感和孤独感。
重量感的失控——飘。杜甫以舟为家,一帆小舟承载了居住与迁徙的双重功用,也给予了诗人最后的一点慰藉。但“风餐江柳下,雨卧驿楼边”的舟中生涯毕竟不同于居处于陆,无法令人获得稳固的安全感、稳定感以及脚踏实地的坚实感、立足感。湖湘时期,杜甫常用“漂泊”“漂漂”“羁旅”“浮萍”“飘蓬”等语词来直抒漂泊之情,体现其无法掌控命运的慨叹以及常年漂浮、居无定所的厌倦之感。常年漂泊的水上生涯以及所见皆为茫茫水域的空间体验,更进一步加重了诗人“失重”的主观感受。“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触目所及的归雁、沙鸥、飘蓬,无一不是寓意着同具失重感的诗人自己。金圣叹评价说:“夫天地大矣,一沙鸥何所当于其间,乃言一沙鸥而必带言天地者?天地自不以沙鸥为意,沙鸥自无日不以天地为意。”[3]杜甫犹如那天空中失群、漂泊无依的飞鸟,产生了一种恒久的失重感。
五、万世漂泊与根植地方:地方感生成及演变的影响因素
李子德曾言:“万里之行役,山川之险夷,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曲尽,真诗史也。”杜甫一生游历了河南、陕西、江苏、浙江、山东、河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湖南等地,他既坚守着以故园、长安和中原为代表的北方地区特有的“根植感”,也在依赖与认同的矛盾中书写了对于巴蜀地区的依恋生成和认同缺失。而在晚年流落湖湘时,他又时时流露出“无归”的独特感受,进入“无地方感”的状态中。这种历时性的演变,不仅受诗人地方体验加深、人生经历变化的影响,也与时空距离改换、在地环境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
地方体验的加深。地方感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定然伴随着地方体验的加深和改换。从类型上说,地方体验由浅至深分为直感型、体验型、依赖型和根植型。杜甫早年漫游时,“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书写了齐鲁大地的雄浑气象,也增强了诗人对于壮美河山的审美领悟。此时杜甫年纪尚轻,对地方的体验和感受还较为浅表,缺乏更为深层的情感融入。胡适评价杜甫早年的诗作:“杜甫这时候经验还不深刻,见解还不曾成熟。……故还时时勉强作豪壮语,又时时勉强作愁苦语。……他们的意境是想象的,说话是做作的。”[4]入蜀后,杜甫在反复的地方实践中开始与成都草堂建立深切的情感连结,甚至于偶尔流露于甘愿终老于此的意愿,将对巴蜀生涯的理解上升为更深一层的生命体验。随着地方体验的深入,巴蜀的山水风物和空间特征投射于诗作中,从而内化为诗人自我与山水相融合的诗歌境界。然而,以对地方环境和人文高度认同为基本特征的根植型体验,始终体现出杜甫对于“家”这一原点的体认和对异域空间文化的排斥。随着活动空间的扩展和地方体验的深化,诗人笔下的“故乡”概念由家扩展到长安再泛化为以中原为代表的北方地区。通过对这一系列富有象征意味的“家”的书写,杜甫展现出浓烈的恋乡情感和深度的空间及文化认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诗人对于寓居地地方感的建构。
人生经历的变化。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对于地方的情感、认知和行为会发生改变,个体对在地情感的改变与地方意义的重构也成为必然。安史之乱是杜甫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乱离和盛唐王朝的落幕,更是诗人常年漂泊的苦难生涯和客死异乡悲惨遭际的开端。战乱导致杜甫常年流落异乡,在空间上切断了与都城长安的联系,由此引发了诗人地方身份感的缺失和随之而来的存在性焦虑。诗人在反复思念和渴望回归的心理过程中,重构了故园、长安、北方等的地方意义,由此凝聚熔炼出郁结于心、持久不化的长安情结。在此意义生成过程中,杜甫短暂的拾遗任职经历和幕府生涯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漂泊西南的人生经历和由此带来的心境改变,也是杜诗中地方感发生演变的重要因素。诗人对成都草堂的筑造过程,展现出诗人意图在异地建设家园,以弱化、消解异乡客生命悲情的努力。但是杜甫对草堂的依恋是并不稳固,随着局势的改换和安定感的破坏,诗人的回归意识时时涌现。随着年岁渐老和多灾多病,加之对于夔州山水风土的不适应,诗人的暮年心态和回归意识更为深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人地方感的建立。
时空距离的改换。人对地方的依恋与认同是建立在对地方高度熟悉的基础之上的。地理空间上的远离中心,容易带来边缘化的地方体验和心理感受。安史之乱后,杜甫流寓西南地区,这种地方位移和改换对其空间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他来说,故土中原是一面,自己所处的西南地区是另外的一个空间领域。边缘化的失落和被排挤、放逐的苦闷一直侵扰着身处异地的诗人,由此也影响了其对于巴蜀地区尤其是夔州地区地方认同的构建。漂泊湖湘时期的居无定所是杜甫晚年陷入“无地方感”状态的直接缘由。以舟为家的现实处境令诗人对于所处空间失去了准确的定位,迷失感、弃置感和失重感相继涌现,导致了诗人后期诗作中大量漂泊意绪的产生。
在地环境的影响。杜甫将大量地方山水、风土人情攫取入诗,其诗歌风格和在地心态也深受当地独特环境的影响。以巴蜀地区为例,蜀中气候异于中原,“江柳非时发,江花冷色频”,由此令诗人生发出“年年小摇落,不与故园同”的观感。而夔州冬日多雷多雨、夏季苦热的特殊气候环境,令诗人深受其苦,由此常常产生焦虑与苦闷的心态,因而对夔州颇有异词。东西两川的地方特性和文化差异深刻影响了杜甫对于成都和夔州两地的地方观感和文化认同,由此造成诗人的心理、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改变。相较而言,成都地区经济繁庶,文化氛围浓厚,与中原差异较小,诗人融入当地环境的过程也较为顺利,云安、夔州地区则不然。夔州的奇风异俗和人情淡薄是杜甫厌恶此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结 语
清代薛福成云:“古之以文章传者,得山川之助而益奇。杜子美崎岖秦蜀,举可喜可愕之境,悉寓之于诗。不获山川之助,亦无以扩其趣而孕其奇也。”[5]杜甫将秦州、同谷、成都、白帝、夔州、荆湘一带山川形胜尽记入诗,山川风貌成为他情感的投射物。从大自然汲取生机,以复苏忧伤心灵,是杜诗独创的体验和意境。地方感与坎坷命运、诗人心境的糅合,共同成就了杜甫丰富深刻的诗歌内涵和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
地方感的演变深刻影响了杜甫诗作中时空意识的表达。成都草堂时期,相对安适的地方环境令杜甫回归了日常,放慢了节奏。杜甫对草堂的依恋之情令其草堂书写充满了诗情画意,其诗作中呈现出一种关注当下、相对静止的时空意识,其名作《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千秋”“万里”的广阔时空被框进草堂内,诗人捕捉到了这一瞬间所触发的内心的激情,将时空停驻在了诗作中。夔州时期,诗人受回归意识和地方认同缺失的影响,在诗作的空间表达上呈现出一种断裂的态势,诗人一直企图用回望、回首的姿态打破时空阻隔。漂泊湖湘时期,杜甫的孤独情绪更加外化,他时常将自身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来突出自身的渺小和孤微。“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乾坤与腐儒、远天与片云、永夜与孤月三组强烈的对比,更加凸显出时空的无涯无涘和个人之飘零孤独。
地方感的演变还深刻影响了诗人的创作心态。纵观杜甫的全部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从其自我表现中反映出来的矛盾。诗人既悲叹于羁旅和离乡之苦,又常常弃官游历四方,处在一种漂移不定的状态之中。恋阙与思家情感相互强化,成为了杜甫思乡之情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他的心灵和意识永远是停留在故园、长安和中原地区,甚至表现出一种百折不回的执着念想。杜甫到夔州后,将自身的身份界定为一个在遥远天边漂泊的乱世中被抛弃而依旧牵念国与君、热爱百姓民生的、衰病穷苦的老人,时常流落出回归意图和边缘焦虑。地方山水和无归的现实激发了诗人漂泊的苦难,诗人只能通过回忆和创作来求取精神寄托和心灵安慰。
【注释】
①《论杜诗中的地方感》一文曾展开对杜诗地方感的考察,其中涉及杜诗地方感的演变过程,但研究不够深入。肖舒:《论杜诗中的地方感》,江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 文中所引杜诗均出自《杜诗详注》(杜甫著,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79年),以下不再另行标注。
③ 转引自周晓琳、刘玉平:《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