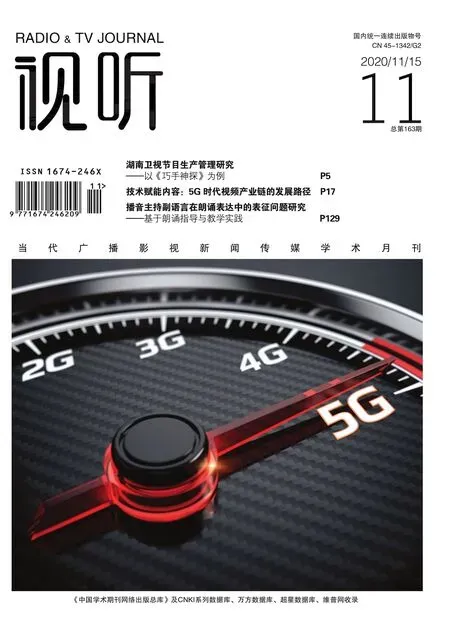台湾新电影“迎来送往”与“去向何方”的母题探究
2020-02-24胡芷语
□ 胡芷语
“来处”与“归处”是台湾新电影时期一以贯之的原始母题。两岸对于这组微妙关系亦存在着差异化解读,且由于历史的混沌与现实的暧昧而显现出或“圆融”或“鲜明”的解读态度。当站在“我们”的角度和立场来探讨“个人”与“在地”时,是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的。然而,当“我们”不得不关照和参考“他者”的历史轨迹与现实叙事时,却又处于“打来处来,到去处去”的失语状态。因此,台湾新电影前承着来自父辈的回忆史诗,后启着通往个人的在地传奇。
从侯孝贤至钟孟宏,台湾电影人对主体意识的定义,从初代的历史认同发展到中段的历史存疑甚至历史虚无,随后又逐渐转化为现在的历史真空。整个过程并非绝对消极,而有效区分阶段性特征的标志则是不同代际电影人对“台湾”这一地缘文化符号的差异化影像表达。
一、代际特征的对比与梳理
初代如侯孝贤《童年往事》里的台湾,融合了“在地性”与“个性化回忆”;中生代如魏德圣在《海角七号》中,将“台湾即在地”化;及至钟孟宏的《阳光普照》,台湾的“本土化”特征已经趋于成熟、稳定。凡提及“在地”,亦需提及“方位”“在地”“本土”,三者亦有不同侧重:“方位”偏重空间地理性质的具体指代;“在地”偏重思想文化层面的抽象指代;“本土”则是包含了前两者指代后的集合。
在钟孟宏的“在地意识”中,家庭即家庭,父子即父子,羁绊即羁绊,不再使用过于明显的关系映射和超范围指代。《阳光普照》上映伊始,就存在着一些将阿豪与阿和的小家庭关系置换到更宏大广阔的政治叙事背景中进行解读的声音。虽然有其合理性,但这种置换并非《阳光普照》的主要叙事目的,因为不同于初代的“侯孝贤们”,当下的台湾电影创作集群更关注台湾本土场域发生的社会问题。
因此,台湾电影关于“来处”的“个性化回忆”,主要集中于初代电影人对父辈与子辈的血缘勾连与历史勾连中。而中生代如张作骥、魏德圣等则通过去父辈化以及父子关系解构,使台湾的前世记忆逐渐模糊、消融。而消融了“个性化回忆”的台湾,如同遗失了台湾的历史族谱,只见今生,不见前世。及至钟孟宏、黄信尧一代则将对“去处”的寻觅延展开来,使影像中的台湾步入相对真空的本地人时间,使“来与去”的母题散发出完成时的气息。
二、侯孝贤与《童年往事》
台湾初代电影人虽然拥有“个性化回忆”,然而将侯孝贤《童年往事》中关于父辈记忆的细节展演开来,不难发现,他对自身的家庭血缘、对在地与原乡之间历史渊源的认同都是作为“在地意识”的前置修饰而存在的。
在《童年往事》的文本结构中,真正的核心主语仍然是阿孝咕的“在地意识”。影片对父辈的情感大部分建立在愧疚—补偿性认同的基础上。“收尸的人狠狠地看了我们一眼,不肖子孙,他心里一定这样在骂我们。”阿孝咕的画外音旁白,外化了其真实的心理活动,也使观众意识到阿孝咕的情感认同是间接性的。他并没有原乡的生活经验,对原乡的好感与认同是通过对父辈的认同进而转化为对父辈所依恋的故土的认同来实现的。“而这种移民表述的方式和特点恰恰折射出台湾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存在的症结之一,即身份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大陆原乡的历史根基。”①这大概就是阿孝咕爱屋及乌。
三、魏德圣与《海角七号》
进入以魏德圣为代表的中生代时期,对台湾本土身份——在地意识的强调变得更加浓重,《海角七号》便是典型案例。
皇民化运动作为日殖民时期典型的文化殖民手段,对台湾本土的社会历史文化认同和民众的集体心理潜意识等方面造成长期的潜在引导和语境暗示,对后来台湾人的自我定位影响深远,亦造成“皇民后”与大陆的疏离、与日本的暧昧这一复杂的双重情结。所以台湾人的精神离乡正是由初代叙述主体中大陆老兵的淡去和二代叙述主体中台日文化姻亲关系共同作用的。老兵的生理衰老加速了原乡人从台湾本土历史舞台中淡去的脚步。皇民化时期的台日姻亲现象则巩固了异邦文化在台湾本土的统治地位。
提及日据时期的台湾,不得不提一部名为《南进台湾》的“宣教”纪录片。与《海角七号》所站的遗民视点不同,《南进台湾》以殖民者的视点对台湾的牵涉性指代进行概念偷换。《南进台湾》的殖民话语权是强势的,与此同时,《海角七号》中的台湾人对日文化的亲近亦是主动性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自觉。在恒春这个影像场域的符号搭建中,台湾的中国身份被无意识地隐略了,取而代之的是台湾人在经历皇民化浸淫后,于血缘(台日家庭结合)、于意识(去汉化禁汉语抹汉史)等多方面的基因重构。
然而魏德圣在《海角七号》中对于台湾人精神归属的诠释与呈现,应属无意识、即非刻意的,因其另一部影片《赛德克巴莱》的主题表达与《海角七号》截然不同。《海角七号》柔淡暧昧,《赛德克巴莱》强烈鲜明,前后两部所表情绪反差巨大,反映出台湾人的反抗精神和恋日情结,具有同质而异向性,两种状态既矛盾又真实地同时存在于当今的台湾社会。
作为电影创作者的魏德圣,并未刻意树立语境暗示,而是出于对现实的坦诚反映。遂此亦需辩证看待。
四、趋势与未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电影人将作品的关注焦点集中于“去向何方”的前景展望中,更加重视台湾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台湾人的精神未来。当今台湾电影,也开始侧重以小成本博取大命题的思路,进行现实主义故事片的类型创作,如2019《阳光普照》、2018《谁先爱上他的》、2017《血观音》《大佛普拉斯》。
就数量、规模而言,尚未达到台湾电影现实主义故事片的类型井喷,但从影片的文本内容、话题普适性、探讨维度等诸多方面来看,质量实属上乘。尤其是对于类型创作中的主题定位、话题择取、人文关怀三大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深度、广度、温度。
特别是《大佛普拉斯》,深入台湾社会的沉疴旧疾,以小人物在悲凉命运中的挣扎沉浮为切口,反映现代台湾在社会发展中的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等现实问题,其中不乏黑色幽默的影像化春秋笔法。如《大佛普拉斯》通过极富讽刺意味的“佛肚藏尸”这一情节设计,将普度众生的佛这一经典的救世主形象进行反转式重构,荒诞而犀利地掀开台湾社会统治阶层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羊皮。而真正的佛却藏在社会最底层的黯淡日常中,如同释迦这类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无声地旁观肚财被殴,又慈悲地送肚财最后一程。在黑白与五彩两重天的人世间,佛法缥缈无言,小人物的善良根本无法改变自我与他人的命运,只能以沉默的姿态为同样卑微的生命超度、送行。
值得注意的是,以2017年《血观音》《大佛普拉斯》两部优秀影片为代表,都不约而同地择取、选用了观音、佛祖等典型宗教文化符号,又通过对传统宗教的影像化解构与重构,创造出超越宗教意味的现实主义“新象征”,使宗教的社会角色从原本的超凡脱俗转变为凡尘俗事的在场见证者,为古典佛教所提倡的慈悲济世增添了更多时代气息与现实内涵。
今天的台湾电影,已然通过早期“从哪里来”的回溯,经历了“送与留”的取舍,迎来了“到哪里去”的本土自省期。历史与现实共同作用在台湾这一巨大的地缘容器中,时而荡气回肠,时而静水流深。相信经过现实的打磨、历史的过滤之后,台湾电影最终会找到通联往今又契合自身的未来航道。
注释:
①李洋,李晓红.新世纪以来台湾电影的移民表述与身份建构[J].当代电影,2018(09):15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