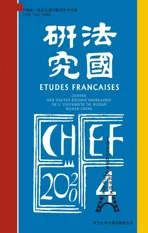象征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历程和策略
2020-02-24李国辉
李国辉
象征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历程和策略
李国辉
台州学院人文学院
象征原为古希腊词语,14世纪随着拉丁语天主教文献传入法国,成为常用的思想和语言术语;19世纪后期它成为法国象征主义的核心美学概念,然后经日本传入中国。五四时期,法国象征主义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黄金时期,但是因为它不合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文学民族化和文学宣传功能的要求,象征主义的译介和创作随后陷入困境。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等批评家、诗人,他们在理论上用中国的比兴、意境理论来解释象征主义,在创作上使用有中国气派的意象,遂使得象征主义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象征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策略,是系统性的、对等性的重构。这种重构寻找与法国象征主义的具体理论有等价性的传统诗学,然后树立这些诗学的中心地位。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并未受到排斥,而是与中国诗学组成一种新的、包容的体系。梁宗岱、戴望舒等人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是法国象征主义的中国化,而且也是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化。
象征主义 本土化 梁宗岱 戴望舒 意境
中国现代文学最具争议性的思潮是象征主义。梁实秋曾这样批评它:“这一种堕落的文学风气,不知怎样的,竟被我们的一些诗人染上了,使得新诗走向一条窘迫的路上去。”[1]尽管象征主义受到很多非难,文学史却有自身的书写规则。站在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再来审视它,会发现它不仅是新诗现代性的主要资源,而且也是国际象征主义思潮的重要构成部分。虽然具有共性的元素,中国的象征主义与其他国家的相比,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移植,而是做到了扎根本土、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国内有学者指出这种诗学已经在中国本土化了。[2]中国象征主义最大的特色,就在它的本土化上。但是这种本土化的历程、策略等问题,目前还未能得到清楚的回答。通过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法国象征主义进入中国的历程,与中国的诗学、政治背景密不可分;象征主义的中国化是一种系统性的、对等性的重构。
一、从“symbole”到象征
在中国诗学中,“象征”一词的源头是《周易》。《系辞》说“圣人立象以尽意”,《泰卦·疏》说:“详谓徵祥”。[3]《周易》中虽然“象”与“征(徵)”都出现了,但没有连用过。在长期的使用中,“象”和“徵”也有合出的情况。例如成玄英的《南华真经》的疏说:“言庄子之书,窈窕深远,芒昧恍忽,视听无辩,若以言象徵求,未穷其趣也。”[4]这里的“象”与“言”是一个词,“徵”与“求”是一个词。“象”“徵”似连实断。晚清以前,未见“象徵”真正作为一个词使用。只是后来,一本叫做《易经证释》的书说:“象徵其物,序徵其数。高下大小,远近来去,莫不可徵。”[5]这里“象”与“徵”仍然是主谓词组,但勉强可以视为一个词。但是《易经证释》是民国时期的书,不足成为象征一词在古代成立的标志。不过,这本用中国易学传统写就的书,对于解释象征(下文出现“象徵”时皆用“象征”)一词还是有一定的参考。结合前面的例子,可以做出如下判断:象征在中国的语境中,合用可视为主谓词组,如果用白话译为“象的征兆”,就成为偏正词组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词。它具有浓郁的占卜学的气息,与文学和语言学上的象征没有关系,倒与天主教神学中的“启示”有些类同。
既然此象征不同于彼象征,为什么国人用象征来译“symbole”呢?这就要从象征主义的译介说起。“象征”在西方,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词语“σύμβολον”。这个词类似于中国的“符节”,双方各执一半,以作验证。到了中世纪,它在拉丁语中写做“symbolum”。因为象征之物往往用来验证身份,所以它的意思就延伸为代表信仰身份的语句,一种“教会概括它的信条的格言”。[6]简化一下,这个词就有了“信条选编”的含义。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大全》()第二集第二部中论信德的部分说:“象征作为信仰的规则而被传递下来(symbolum ad hoc traditur ut sit regula fidei)。”[7]这里的象征,就是“信条选编”的意思,明代来华传教的意大利人利类思将其译作“信经”。中世纪有一部信仰格言选,叫做“Symbolum Apostolorum”,意思是“使徒信经”。
中世纪后期,随着天主教文献传入法国,这个词开始有了法语的对应词“symbole”。该法语词大约在1380年出现,也继承了天主教文献中的意义。(Rey: 3719)例如在1596年,出现过一本书《对信经的布道……》,标题原作“Sermons catholiqves svr le symbole des apostres…”,其中的“symbole”,仍是“信条选编”的意思。到了16世纪中叶,象征在法语中的意义与符号的意义融合了,开始指“通过其形式或本质,与抽象的或者不在场的事物产生思想上的联系的自然现象或者对象”。(Rey: 3719)象征于是成为一种思想方式,也成为一种语言形式。例如在1745年的《新法拉大辞典》中,就同时出现了两个象征的辞条。一种象征是天主教用法上的,另一种则是文学和语言学上的:“符号、类型、标志的种类,或者用自然事物的形象或特性代表道德事物,比如狮子是英勇的象征。(Signe, type, espèce d’emblème, ou représentation de quelque chose morale par les images ou les propriété des choses naturelles, comme le lion est le symbole de la valeur.)”[8]18世纪末期,随着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崛起,象征的意义渐渐从抽象事物的象征,变为心灵的象征。例如斯达尔夫人(Madame Staël)认为要“将整个世界视作心灵感情的象征(considérer l’univers entier comme un symbole des émotions de l’âme)”。[9]这里的象征不再是固定的象征,而是个性的象征。
斯达尔夫人的象征,传到了波德莱尔手里。波德莱尔(C. Baudelaire)是象征主义的先驱。不过,在象征主义使用这个词之前,法国的美学家维隆(Eugène Véron)就在著作《美学》()中使用了它。维隆的书论述象征主要在雕塑这一部分,象征涉及到的是神像的塑造。具体来看,维隆的象征指的是神性的具体化、个性化,这种含意,实际上是从斯达尔夫人退回到《新法拉大辞典》的年代了。《美学》一书出版于1878年,5年后,即明治十一年,日本学者中江兆民,将维隆的书翻成日文,题作《维氏美学》出版。维隆的原书,既出现了“symbole”,也出现了“symbolism”,两个词意义相关,后者指的是象征在艺术中的运用。中江兆民第一次在汉文化圈用“象征”来译“symbolism”,比如这一句话:“一旦诸神的像已经完成,某神因为司某职,一定有甲种象征,某神因为司某职,一定有乙种象征(一旦諸神ノ像已ニ成リ、某神ハ某職ヲ司ルヲ以テ必ズ甲ノ象徵有ラザル可ラズ、某神ハ某職ヲ司ルヲ以テ乙ノ象徵有ラザル可ラズト)”,[10]这句话在维隆的书中找不到,是中江兆民根据自己的理解,增添的句子。它对应的是维隆谈古希腊神像的象征的话。
法国象征主义大约在1886年成立,它将语言和修辞学上的象征,拓展为一种注重暗示和神秘性的写作手法,这就是象征主义最基本的含义。日本的诗人和批评家在明治末期,开始注意这种新的思潮。岩野泡鳴曾在1907年4月的《帝国文学》发表《自然主义的表象诗论》一文,他指出:“法兰西自19世纪后半叶,几乎同时出现种种主义。左拉的自然主义不必说了,诗界中有勒孔特·李斯勒的虚无主义、波德莱尔的恶魔主义、魏尔伦或者马拉美的表象主义(エルレインやマラルメの表象主義)……”[11]这里用“表象主义”来译“symbolisme”,而非使用中江兆民的术语。1907年10月,河井醉茗在《诗人》杂志上发表《解释<薄暮曲>》一文,指出:“原诗的作者波德莱尔,继承法兰西诗坛高蹈派、开辟了象征派的新天地(象徴派の新天地を闢いたである)。”(日本近代诗論研究会:257)这里提出的“象征派”一词,就是后来通行的译法。这个词具有名词的词性,它原本主谓词组的词义被弱化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拐点。明治四十三年到大正三年这几年间,可以看到服部嘉香、三木露風、蒲原有明等诗人、批评家也都接受了“象征”“象征派”“象征主义”的术语,促进了它们的流行。厨川白村是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他1912年出版了《近代文学十讲》。该书提出四种象征的分类法,象征主义的象征属于第四种。厨川白村的这本书,可以看作“象征”成为固定术语的一个标志。
民国初期,由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起步比日本略晚,加上当时有不少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因而日本的象征主义研究就传到中国来。象征主义最早的介绍,是1918年陶履恭发表的《法比二大文豪之片影》。该文提到了梅特林克(M. Maeterlinck)的《抹大拉的玛丽亚》(),这是一部刚刚在伦敦出版的英译剧本。陶履恭还指出梅特林克是“今世文学界表象主义Symbolism之第一人”。[12]陶履恭曾经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过几年书,接触过日本文学的资料,于是他借鉴了日文中的“表象主义”的术语。二年后谢六逸发表《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一文。谢六逸的这篇文章选译了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比如四种象征的分类法。谢六逸对“表象”这个日语词感兴趣,他文中使用的都是该术语。该术语还在当年沈雁冰的《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一文中出现过。
随后“象征主义”这个术语在罗家伦《驳胡先驌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中出现了。[13]这个术语的来源现在还不清楚,不能完全肯定是来自日本。但之后的几个人的情况就比较确定了。1919年11月,朱希祖选译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中的《文艺的进化》一节,发表在《新青年》上。文末有一句话:“未能写实而讲象征主义,其势不陷入于空想不止的。”[14]这里的术语出处是清晰的。几个月后,周作人在《英国诗人勃来克的思想》一文中说:“自然本体也不过是个象征。我们能将一切物质现象作象征观。”[15]周作人的留日学生的身份,能揭示他的术语的渊源。文中涉及到波德莱尔、德拉克洛瓦(E. Delacroix)的思想,因而与西方象征主义思潮有关系。
就五四初期“象征”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判断它基本来自日本。1921年和1922年,是象征这个词在中国确立的年份,这两年,田汉、刘延陵、李璜、滕固等人都采用了“象征”的表述。1922年后,不使用“象征”一语的批评文章就变得极少见了。虽然象征在术语上来自日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象征的概念也完全是外来的。中国晚清之前没有象征一词,但是它的概念在其它的术语中寄寓着。比如比兴、意象等术语,它们同样要求暗示性,在实际运用中,也有一部分与道家的无、佛家的空等形而上学概念有联系,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因而,象征的内涵,在中国诗学的某些术语中是存在的。象征是一个外来词,但并不完全是一个外来的诗学概念。穆木天曾说:“象征主义,是有什么新鲜的流派之可言呢?不错的。杜牧之,是在诗里使用象征的。李后主,也是在诗里使用象征的。”[16]这种说法,既不能算对,又不能算错,需要在术语和概念上综合考虑。
1925年,李金发出版诗集《微雨》,标志着中国新诗新时代的到来。次年,穆木天、王独清等在日本留过学的诗人(王独清后来也在法国留学),热烈讨论象征主义的做法,遂产生了中国现代第一波的象征主义运动。该运动促进了“象征”一词深入人心,不管对象征主义接不接受,“象征”成为稳定的诗学术语。不过,它要真正获得诗学地位,还需要面临时代的选择。
二、被压抑的象征主义
象征有一幅国人熟悉的面孔,法国象征主义就未必如此了。从1919年到1932年,法国象征主义在中国经历了由欢迎到冷落的大转折,这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五四时期的新文学革命,主要的成绩在语言上,它的言文合一的主张,造就了五四时期散文和小说不俗的成绩,但是就诗歌来看,却褒贬不一。梁实秋曾说:“白话为文,顺理成章,白话为诗,则问题甚大。胡先生承认白话文运动为‘工具的革命’,但是工具牵连至内容,尤其是诗。工具一变,一定要牵连至内容。”[17]其实不仅是内容,新诗的风格也有了彻底的变化,当时的风格多为“明白”,喜欢议论。五四新文学是一种“典范的变迁”,[18]它使国人自愿用西方的价值、观念作为标准,对中国文学进行思考和评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可以看到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被搁置了。朱自清在讨论五四白话诗时,曾指责它“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19]这句话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意境美学怀有的乡愁。明白的风格从内部阻止胡适、康白情等诗人重建新诗意蕴的深度,但是唐诗的伟大传统又成为一个潜在的范例,期待诗人在意蕴上有所成就。这种态势在五四之后产生一种巨大的张力,正是这种诗学张力,促进了法国象征主义译介到中国。这说明象征主义最初的译介,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诗人和批评家们想从中得到与中国的意境说类似的理念和做法。
徐志摩虽然被目之为格律诗人,但是他也是象征主义美学的热衷者。他1924年曾翻译波德莱尔的《死尸》。在前言中,徐志摩谈到对音乐的韵味的向往:“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20]这里的音乐精神,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是相通的。徐志摩想通过波德莱尔走入一种特殊的诗境。但是这是一种自我放逐到异国的行为,还是变相的回归,其中界限并非截然分明。徐氏不但在杂志上宣传象征主义,而且在课堂上也布置波德莱尔的翻译任务。一位年轻的大学生邢鹏举受到了徐志摩的影响,开始对法国象征主义产生兴趣,并决心借助英译本翻译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邢鹏举在法国诗人那里找到了当时的新诗没有的东西,他形容自己“整个的心灵都振动了”,他还将象征主义的风格归纳为“舍明显而就冥漠,轻描写而重暗示”。[21]波德莱尔并不是唯一被关注的象征主义诗人。拉弗格、魏尔伦、兰波等诗人也得到了注意。穆木天从拉弗格那里学到了不少象征主义的暗示技巧。
虽然创造社和新月社的一些诗人,开始重视象征主义艺术,但是这种尝试只是昙花一现。在穆木天发表《谭诗》的两个月后,五卅惨案爆发,五年后,九·一八事变发生,这些国难极大地触动了诗人的神经,也改变了文学的风格。穆木天的话有代表性:“在此国难期间,可耻的是玩风弄月的诗人!诗人是应当用他的声音,号召民众,走向民族解放之路。诗人是要用歌谣,用叙事诗,去唤起民众之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的。”[2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使命,使得文学的功能发生了改变,意蕴的营造、象征的探寻都属于诗的内在功能,而宣传革命、号召大众,则属于外在功能。当时诗的功能的变化,就是从内在功能大步地迈向了外在功能。
正是在文学功能转变的大背景中,象征主义开始受到压抑。穆木天并不孤独,人们看到创造社成员几乎集体转向,提倡大众化的诗歌。王独清是其中的一位,他说:“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许多血淋淋的大事件在我们面前滚来滚去,我们要是文艺的作家,我们就应该把这些事件一一地表现出来,至少也应该有一番描写或一番记录。”[23]在此期间,不但象征主义面临困境,有象征主义倾向的新月社诗人也受到批评。后者偏重唯美和暗示的诗风,很多时候被认为是在美化现实。这种批评意见,并不是捕风捉影。为了表现音乐精神,传达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往往吐露的是阴暗、消沉的情绪。比如王独清《失望的哀歌》《我从Café中出来》,穆木天的《乞丐之歌》《落花》《苍白的钟声》,还有冯乃超的《悲哀》《残烛》。这些情绪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作中常见的,但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环境,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环境并不一样。法国象征主义的阴暗情绪,来自于知识分子对法国资产阶级道德的厌恶(比如波德莱尔、兰波),以及对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疏远(比如马拉美)。换句话说,法国象征主义的情感基调,来自于一个被撕裂的社会。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代表了逃避现实的一类人的心理,这种心理在法国有群众基础。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社会的联合而非分裂是当务之急,逃避现实的情绪与主流情感不合。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们的自我世界,如果说有独立性,那么这种独立性往往也属于虚构。
另外,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歌模仿法国的颓废形象,也给上述批评带来口实。李金发诗中生涩的形象,很多是模仿波德莱尔,比如他的“残叶”、“弃妇”。创造社成员的诗人亦然,王独清诗中的“病林”,穆木天诗中的“腐朽的棹杆”、“虚无的家乡”,都有人云亦云之嫌。这些人工的形象,再加上时常欧化的句子,容易让诗作成为众矢之的。李健吾曾这样反思:“李金发却太不能把握中国的语言文字,有时甚至于意象隔着一层,令人感到过分浓厚的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气息,而渐渐为人厌弃。”[24]虽然创造社诗人在语言和形象上得到了一些改进,与李金发早期的诗作已有不同,但是李健吾的批评对他们来说仍然有一定的有效性。
在这种大背景下,诗歌的情感不得不重新定义,它现在的标准是现实的真实。穆木天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感情,情绪,是不能从生活的现实分离开的,那是由客观的现实所唤起的,是对于客观的现实所怀抱出来的,是人间社会的现实生活之反映。”[25]这里可以推出一系列新的观念:真正的诗,就是表现有现实感情的诗;真正的诗人,就是对现实怀有真实感情的诗人。值得注意,这种新的定义,并非完全是意识形态强加的标准,它也是诗人自身的渴望,已经内在化了。对象征主义的疏远也是诗人内在化的要求。
法国象征主义的诗风,有鲜明的颓废倾向。这种颓废并不仅仅是道德上的颓废,它也指美学上的革新精神。颓废在象征主义诗人心中,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眼,它含有对美学新价值的追求。但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下,颓废的意思改变了,它成为远离民众的无病呻吟。蒲风曾这样评价创造社诗人:
穆木天唱出了地主没落的悲哀,颇有音乐的清晰的美;王独清唱出贵族官僚的没落颓废,一种抚今追昔的伤感热情委实动人;冯乃超的诗虽然颇新颖,多用暗喻,有朦胧的美,也脱不了颓废、伤感、恋爱的一套。算起来,三个人都恰好代表了革命潮流激荡澎湃中的另一方面,由他们口里道出的正是那些过时的贵族地主官僚阶级的悲哀,这种悲哀和革命潮流的澎湃是正比例的哩![26]
在蒲风的笔下,颓废的意思与“地主没落的悲哀”同义,这个词义不但不是美学上的,也不完全是道德上的,它主要是政治上的、革命态度上的。其实,这种思想在穆木天那里也存在,穆木天表示“不能作(做)一个颓废的象征主义者”。(穆木天,《我主张多学习》:319)这句话犯了错,象征和颓废本身就是一体。但是穆木天的话又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句话表明,在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那里,象征主义的概念发生了分裂。因为诗的定义和功能的改变,原本属于颓废美学的内容,现在被异化,从诗的领域中被剔除出去。象征主义面临肢解的危险,如果它还想保存它的存在,它就必须调整,也就是说它必须本土化。
三、象征主义的本土化
象征主义本土化的方式是让象征主义与中国诗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能让法国象征主义拥有中国美学特征,而且也能纯化法国的理论。具体来看,这种融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创作上将象征与比兴、意象融合,另一个方面是在理论上用比兴、意境理论来解释象征主义。
就创作上看,虽然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受到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探索过中国风格。李金发和创造社的诗人,有意无意地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李金发的《微雨》集中的《律》一诗,“月儿”、“桐叶”等意象主要来自中国古典诗歌,诗中的情感也与古诗中频繁出现的“伤秋”接近。《食客与凶年》中的《夜雨》,“瘦马”“远寺”等意象,也有边塞诗的风味。不过,这类诗在李金发的作品中数量少,不是主流。穆木天和冯乃超使用的传统意象比较多,比如穆木天《雨后》、冯乃超的《古瓶咏》,这些诗不但使用古典的意象,而且注意营造一种追思的、怀旧的意境。
这些诗作在意境的建造上开启了一条不同于西化诗的新路。戴望舒、何其芳等诗人随后也走上这条路。就20世纪30年代优秀的现代派诗作来说,它们不仅抛弃了法国象征主义阴暗、腐朽的形象和情感,而且在传统形象的使用上,也不同于之前的诗人。在穆木天、冯乃超等诗人那里,传统的形象往往是由某种情调串连起来的,它们就好像一颗颗宝石,但是必须有一个链子串着,否则就散乱不堪了。但在戴望舒和何其芳的一些诗中,形象开始呈现另外一种功能,它不是情感的装饰,而是能生发情感。比如戴氏的《印像》一诗,象征被遗忘的印像(象)的是“铃声”,是“颓唐的残阳”。[27]诗中并没有情感的直接流露,情感是在形象的关系中自己生发出来的。这种寄寓着情感的形象,才是真正的意象。如果形象能渐渐生发情感,那么它其实也是象征。
象征主义中国化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理论上。五四后期出现不少法国象征主义诗学译介的文章,这些文章中少数使用与意象有关的术语来翻译,这是象征主义本土化的最初尝试。李璜编译的《法国文学史》(1922)中,出现了“意味”这个词,比如“象征意味”、“包藏的意味”。[28]明显借鉴了《文心雕龙》等诗学著作。创造社成员也在这方面迈出脚步。穆木天在讨论象征主义的纯诗时,将李白和杜甫作了对比:“读李白的诗,总感觉到处是诗,是诗的世界,有一种纯粹诗歌的感,而读杜诗,则总离不开散文,人的世界。”[29]这里并不仅仅是用李白的诗来附会纯诗,它将象征主义纯诗作了本土的解释。
总体来看,上面这些工作发挥的作用不大,系统地、认真地使用传统诗学理论的情况还没有看到。做出更大成绩的是现代派的诗人和理论家。卞之琳1932年11月发表了《魏尔伦与象征主义》一文。该文译自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出版于1921年的《魏尔伦》一书。卞之琳的译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他底暗示力并不单靠点出无限的境界,并不单靠这么一套本领……”。[30]原文中的“the infinite”,是一个抽象的词,相对的是有限的现象世界。卞之琳用了一个中国化的词“无限的境界”来译它,明显在用中国的意境(境界)理论来解释象征主义。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原文是“to suggest the something beyond”,[31]意思是用一些外在的场景来暗示超越这些场景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是情绪。卞之琳将这句话译作“言外之意”。卞之琳曾说当他在中学时期接触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时,感觉这些诗“与我国传统诗(至少是传统诗中的一种)颇有相通处”。[32]他很早就有会通中国和法国诗学的心愿。
象征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一位理论家是梁宗岱。推动梁氏做这种努力的,一方面是革命时代的时势所迫,另一方面是他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崇敬之心。他曾指出:“因为有悠长的光荣的诗史眼光光望着我们,我们是不能不望它的,我们是不能不和它比短量长的。我们底诗要怎样才能够配得起,且慢说超过它底标准”[33]。对梁氏来说,借鉴法国象征主义,并将它与中国诗歌传统结合起来,这是实现他的诗歌理想的唯一道路。如果两边都是伟大的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就有对话的价值。他把“象征”与中国的“兴”比较,发现它们有很大的相似性。兴即“感发志意”,在《诗经》中常常出现在诗句的开头,引出要吟咏的感情。但“兴”也可以视为一般的做诗法,指情景交融,这样就与意境搭上了关系。梁宗岱将象征解为“情景底配合”,不过,情景的配合有高低之别,较低者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较高者是“景即是情,情即是景”;后者才是象征能够达到的高度,它的表现是“物我或相看既久,或猝然相遇,心凝形释,物我两忘: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梁宗岱:66)梁氏的这句话,明显借鉴了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说。联系上文,则可知一般的“兴”等同于“有我之境”,“象征”等同于“无我之境”。
梁宗岱还将总结了象征的两个特征,一个是情景融洽,一个是含蓄。这两个特点很难看出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子,倒像是宋代诗学的重新解释。这样做不但让法国象征主义去掉了它的颓废美学,而且迎合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风格的要求。中国象征主义现在不仅是一种现代的文学思潮,而且还是一种美学上的复古运动。梁氏后来填出一部词《芦笛风》,这并不奇怪。象征主义的中国化,使梁宗岱发现宋词代表的诗歌才是真正的“纯诗”,于是他选择了一条复古式的现代主义道路。
梁宗岱并非单纯用中国诗学来解释象征,那样会让象征成为一个虚假的幌子,所谓象征主义的中国化就成为空中楼阁了。他造了一个新词“象征意境”,这个中西合璧的词,有他新的思考。表面上看,这个词有点画蛇添足,因为象征就是意境,意境就是象征,两个词原本是一体,硬要相连,岂不是头上安头?梁宗岱其实想让意境与法国象征主义的感应说结合起来。波德莱尔、马拉美的象征,来自一个感应的世界。这种感应的世界,与中国唐宋诗学的境界并不相同。感应需要将人与世界万物看作是一致的,属于相同的实体。而中国佛家的“空”、道家的“无”,都否定这种实体的存在。梁宗岱不但想引入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且想利用感应革新象征的创作方式。他说:“象征之道也可以一以贯之,曰,‘契合’而已。”(梁宗岱:69)这里说的“契合”是感应的另一个译名。理论上看,如果真正可以获得感应的体验,那么诗人的象征就透露超自然的秘密,就与法国象征主义的象征合流了。
20世纪3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一度崛起,但是在全面抗日战争后,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诗人渐渐疏远了象征主义诗风,回到现实主义的潮流中。20世纪40年代,虽然象征主义的一些元素在冯至、穆旦、唐湜等人的诗作中得到延续。这些诗人对于象征主义的中国化也做了工作。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唐湜。唐湜不以象征主义者自居,但是他的诗学理念与象征主义有很多一致性。不同于梁宗岱用“兴”来解释“象征”,唐湜拈出了“意象”。这种意象并不完全是刘勰“窥意象而运斤”的意象。虽然唐湜尽量从中国诗学中寻找根据,但是这种意象与诗意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精神的感应与融合”。[34]这里透露他的意象其实是象征。他想用意象这个本土诗学术语来思考象征的问题。唐湜的意象,到底是象征化的意象,还是意象化的象征呢?可能没必要做严格的区别。这两种倾向有很大的重叠。在《论意象》一文中,唐湜还把波德莱尔的《感应》一诗当作意象的例子,并总结道:“象征的森林正是意象,相互呼唤,相互应和,组成了全体的音响。”(唐湜:10)虽然唐湜没有用“含蓄”“情景交融”等概念,但是他的“意象”本身已经能阐释出象征的特征,这自然产生中国化的象征主义观念。
20世纪40年代后,台湾诗人覃子豪也在象征主义的本土化上做过思考。覃子豪的思路与梁宗岱非常接近,他认为“比兴是象征的另一个名词。而象征无疑的是中国的国粹”。[35]将象征看作是“国粹”,自然不符合事实,但是这里面有一种心理上的真实性,即将象征想象成中国固有的诗学概念。覃子豪也把象征与境界联系起来,但他认为二者还有区别:境界是进入理念世界的状态,而象征则是传达境界的方式。进入新时期,国内已经没有专门的象征主义流派,不过,以梁宗岱等人为代表的象征主义本土化运动,已经让象征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梁宗岱等人是通过什么样的策略做到的呢?
四、象征主义本土化的策略
象征主义本土化只是一种笼统的概括,它并不能说清现代时期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的真实情况。比如为什么能化?怎么化?怎么保留?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下面将象征主义分作四个方面,尝试弄清这个问题。法国象征主义作为特殊的文学思潮,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理论,涉及到主体论、本体论、美学论、艺术论的内容,这四个内容分别对应的是作家、世界、读者、作品四个要素。通过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并以梁宗岱的诗学为主要考察对象,可以对象征主义的本土化作更全面的理解。
首先看主体论。余宝琳(Pauline R. Yu)曾认为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与中国形而上学诗人的共同点是“偏好直觉理解”,[36]这种判断也适用中国象征主义诗人,他们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一样,是直觉而非理性的诗人。这种直觉主要表现在对感受力的强调上。不过,就感受力来看,两边的情况又有很大差别。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感受力具有病态的特征。勒迈特(Jules Lemaitre)曾指出魏尔伦有“病态的感觉”。[37]其他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也大多如此,马拉美得过神经官能症,波德莱尔渴望精神的迷醉,他曾自述自己多次处在超自然的世界中,而兰波倡导的通灵人,本身就有打乱感官的病态体验。为了获得这种病态的精神,波德莱尔和兰波甚至还服用过大麻和鸦片,以达到所谓的“人格解体”的状态。[38]梁宗岱眼中的诗人,则是正常的抒情者,面前的自然与他情感交流,合乎刘勰所说的“人稟七情,应物斯感”。这种心境就是感兴,诗人就是内心发生感兴的人。这种诗人当然有敏锐的感受力,但是他内心得到的触动,并不是人为造就的。梁宗岱自己说得也很清楚:“当一件外物,譬如,一片自然风景映进我们眼帘的时候,我们猛然感到它和我们当时或喜,或忧,或哀伤,或恬适的心情相仿佛,相逼肖,相会合。”(梁宗岱:63)这里的看法与感兴说是吻合的。不过,梁宗岱还提出另一种主体状态,这就是观物:“洞观心体后,万象自然都展示一副充满意义的面孔;对外界的认识愈准确,愈真切,心灵也愈开朗,愈活跃,愈丰富,愈自由。”(梁宗岱:84)宋代大儒邵雍曾提出类似观物的心法,佛家也要求观。梁宗岱这里想沟通过去的圣人,让诗也能体悟大道。这种观物倒是人为的活动,但它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方法仍旧不同。观物并不改变感觉,法国象征主义的人格解体往往带来错觉和幻觉。波德莱尔曾说:“我忘了艾德加·坡在哪里说过,鸦片对感官的效果,是让整个自然具有超自然的意味,每个事物都有了更深刻、更自觉、更专横的意义。不用借助鸦片,谁不了解这种美妙的时刻?那是头脑真正的愉悦,那里更专注的感官感觉到更强烈的感觉,更透明的天空像一个深渊,伸向更无限的空间”。[39]
在主体的精神状态上,可以看出,一边是自然的、正常的,一边是人为的、病态的,这正代表着感兴的诗人与颓废的诗人的分歧。象征主义中国化既然首当其冲的是去除颓废的元素,则法国象征主义的主体特征必然要被替换掉。象征主义诗人一旦变成感兴的诗人,则比兴、意境的观念就能顺利引入,这种诗学就有中国风貌了。
其次看美学论。法国象征主义美学最重要的特征是暗示。它在这一点上与自然主义文学不同。象征主义渴望穿过表面的事物,进入另一个世界。在波德莱尔那里,这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与宗教经验相似;在马拉美那里,这是一种理念的世界,带有虚无主义的精神;在兰波那里,这是一种奇特的幻觉世界。这三位诗人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总的来看,可以将他们的世界称之为梦幻的世界。梦幻的世界也是魏尔伦和拉弗格的追求。梦幻的世界因为是个人性的,所以无法传达,因而法国象征主义采用了暗示的手法。马拉美曾说:“诗歌中应该永远存在着难解之谜,文学的目的是暗示事物,没有其它的目的。”[40]中国象征主义美学主要的特征是含蓄。中国诗人像巴纳斯诗人一样,喜欢表现自然中的事物,但是自然中的事物,往往与诗人的心境存在着交融。这里可以分两层来说。第一层是形象与诗人的情感契合,外在景物的明暗动静,与诗人的悲欢离合有着共鸣。第二层是形象与诗人悟道之心有了联系,形象中好像有天地的精神,正所谓“目击道存”。
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含蓄与法国象征主义的暗示,相同的地方是都反对直接陈述,但又有不同。暗示和象征是一体的,含蓄和意象是一体的。为了说清楚,不妨从象征和意象的区别开始谈。法国象征主义的象征与之前的宗教、文艺上的象征不同,它是梦幻的心境中自发产生的形象。这种形象一来是主观的,不是客观世界现有的,二来是变形的,不是正常的。比如马拉美《海洛狄亚德》()诗中的“紫水晶的花园”。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人们继承的基本是意象的传统。这些诗人喜欢利用客观世界现有的、正常的形象,来抒发感情,传达心境。严格说来,中国象征主义诗人运用的主要是意象,而非象征。其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中国诗人的主体是一个感兴者,而非是一个迷醉的、病态的感受者。
在美学论上可以看出,法国象征主义和中国象征主义依然有很大的区别,以含蓄来解释象征主义,这是对象征主义的重大更改。不过,因为含蓄和暗示在反对直接陈述上、在意蕴的丰富性上拥有相似的倾向,因而这种代替有对等性。
再看本体论。法国象征主义往往表达一个超越的世界,在它那里,“文学的本质也被理解为对另一个理想世界的提示,是对‘天国’的幻象的呈现。”[41]天主教确实有两个世界的观念,不过目前的研究一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要么没有宗教信仰,要么是异教徒。马拉美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兰波在创造个人感觉的宗教,波德莱尔同时信仰基督和撒旦,他曾在日记中说:“即使天主不再存在,宗教仍然会是神圣的、完美的。”[42]这句话一方面表明波德莱尔的宗教情怀,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他的异教徒的身份。整体来看,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眼中的超越世界主要是一个保留感受力的精神世界。在这样一个精神的世界中,诗人并未丧失身体,相反,他们身体的感受力更加敏锐了。他们与人格解体的精神病人接近,不同于陷入迷狂的宗教徒。所以,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超越性是有限的,它表达的主要是一种梦幻的心境。刘若愚认为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用诗来代替宗教”,[43]也表明了梦幻心境并非真正的宗教。中国象征主义诗人由于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的需要,超越性的冲动是缺乏的。尽管梁宗岱强调感应说,也想给中国新诗引进新的内容,但这更多地只是他的理想,而非实效。他的创作和理论出现了不小的断裂。他的世界观融合了道家与法国象征主义的神秘思想:“我们在宇宙里,宇宙也在我们里:宇宙和我们底自我只合成一体,反映着同一的荫影和反应着同一的回声。”(梁宗岱:73)他早期的《晚祷》、《星空》诗中有些基督教的彼岸情感的影子。但《芦笛风》中主要的诗,抒发的是两性之情,情感和形象都更细腻。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梁宗岱的形而上的冲动,但是他的诗作是以人间的感情为主,它不大脱离现实,也不重视寻找梦幻。这种感情还是来源于一个感兴的诗人。
在本体论上,中国现代的象征主义诗人用一种现实的情感来代替法国象征主义梦幻的情感。这种代替因为都弱化形而上的元素,强化个人情感的元素,所以具有相同的倾向,具有对等性。
最后看艺术论。艺术论这里涉及到的技巧和理论很多,无法一一比较。这里以纯诗(Poésie pure)理论为代表,来看双方的不同。纯诗是法国象征主义最重要的技巧理论之一,在波德莱尔、马拉美、吉尔(René Ghil)、瓦莱里(P. Valéry)的理论中都有论述。波德莱尔多次提到纯诗的概念,他没有给纯诗下过定义,只是暗示纯诗具有“异常的和充满幻想的气氛”,有“抚慰人的东西”。(Baudelaire, tome 3: 1226)他的纯诗偏重主题的方面。在马拉美、瓦莱里那里,纯诗成为一种心灵的状态,一种无我的虚无主义。莫索普(D. J. Mossop)将其形容为“一种在另一种状态下理解自己的方式,是把自己当作镜子”。[44]这种纯诗与福楼拜(G. Flaubert)提倡的纯粹的风格还不相同,在马拉美那里,纯粹体现为诗人的退场。即是说诗人似乎放弃他的创造力,让词语和形象本身自己建立联系,诗人就像是一块反射光亮的宝石,他并不改变光亮,也不创造光亮。马拉美曾说:“纯粹的作品意味着诗人演讲技巧的消失,它将主动性交给词语,词语通过它们的差异而被发动起来。它们因为相互的反射而放光,就像火焰隐晦的光亮掠过宝石上面一样”。(Mallarmé:366)马拉美是想在长期体验中等待他想要的形象和语句自发出现。这是一种被动的创作方式,但是需要对词语和形象有更高的体会。这种理论并不是一种设想,而是得到了一些实验。从《海洛狄亚德》来看,它的行间和行际有相同元音和辅音的不断重现,这让诗行内部存在着声音和意义的秘密联系。词语和声音似乎并非是诗人有意控制的,它们有相当大的自主性。
梁宗岱对纯诗的定义,来自瓦莱里,他的理解是到位的:“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藉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像底感应”。(梁宗岱:87)他还说明,纯诗不要说理,不要抒情,并非是没有说理,没有抒情,它们要化在音乐和形象中。日本学者黒木朋興曾指出,不少像马拉美这样的象征主义诗人,“在语言意义的稀薄化中,想看到纯诗的理想”。[45]纯诗确实是以意义的稀薄化为代价的。梁宗岱看到表意与纯诗的对立,这是准确的认识。他还认为意义退场后剩下的音乐要有自身的形式,这也符合纯诗的主张。但梁宗岱的理论具有多面性,他曾指出小令和长调是适合他表现情意的形式,这里也说明梁宗岱的音乐观有自相矛盾之处。其实这里的矛盾也好理解。当梁宗岱在讨论法国的纯诗时,他给出的是马拉美、瓦莱里的解释,但当他讨论中国新诗(或者说他自己的作品)时,他使用的纯诗则是情感纯粹的诗的意思,因为他心仪中国传统文人的感兴状态,自然看重内心与音乐的交流。
法国象征主义的纯诗是一种无我的音乐组织,是反表意抒情的,而中国象征主义的纯诗,是有我的音乐结构,是肯定表意抒情的。象征主义的本土化在音乐方面,表现的是代替。虽然在音乐精神上的理解不同,但是由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也重视韵律的技巧,这就与中国象征主义诗人有了共通性。
法国象征主义和梁宗岱等人的诗学既有相同的倾向,又有不同的理论特质。就相同的倾向来看,双方都肯定直觉,排斥理性,主张暗示或含蓄的美学;反对直接陈述,要求文学表达心境,而非描摹现实;注重音韵效果,而非散文的做法。因为有相同的倾向,就能保留法国象征主义的一些特征。因为理论特质不同,则就可以用中国传统的理论来改造法国颓废的美学,象征主义的本土化就有了可能。中国的象征主义诗人在寻求接近法国象征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保持自身的文学传统,他们用感兴来取代对方的迷醉与病态,用自然的意象来代替人工的象征。因为保留了法国象征主义对内在感受的挖掘,并借用一些对方的技巧,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具有了显著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又不是模仿的现代性,它让传统的许多诗学元素重新复兴了。比如感兴的做法、婉约的意象、伤时的主题、意境的诗学术语。五四时期胡适给旧文学列举的罪状,现在很多都被推翻了,旧文学的艺术、主题重新进入到新诗中,补救了新诗的粗浅与贫乏。总体来看,在20世纪30、40年代,象征主义在中国的确实现了本土化。不管这种本土化得到了多大范围的认可,但一种新的理论、一种新的文学价值已经建立。它在革命文学的时代背景中,给象征主义找到了存在的合法性。
这种融合并不是对抗性的替换。对抗性的替换,是一种理论完全排斥另外一种理论。除了颓废的元素为中国象征主义诗人所拒绝外,感应、纯诗、通感等技巧或者风格,在梁宗岱等人的理论中仍有生存空间。即使在实际的运用中,梁宗岱、戴望舒等人多取法中国传统,但对法国的技巧、风格仍然有包容之意。正是这种包容和接受,中国诗人的创作才有了象征主义的名目。这种融合是系统性的、对等性的重构。首先来看系统性,梁宗岱等人在主体论、本体论、美学论、艺术论上分别用中国的诗学来解释、弱化法国象征主义,他们用自然的、正常的精神状态代替人为的、病态的精神状态,但保留了主观性;用形象的含蓄对应象征的暗示,但保留了形象思维;用现实的情感对应梦幻的情感,但保留了内在性;用情感的音乐对应非情感的音乐,但保留了韵律。这是整体上的融合,不是片面的、局部的借鉴。再看对等性。中国诗学与法国象征主义都具有主观性、体验性、内在性、形象性的特点,这两种诗学虽有不同,但是这些不同在各自的文化里有相近的位置,有等价性。象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在这种等价性的基础上建造的。这种建造是重构,而非完全的替换。说是重构,指的是在美学论、艺术论、世界论方面,树立中国意境(比兴)理论的中心地位,但是并不排斥法国象征主义的论述。因而,神秘性、纯诗、通感等诗学观念,也经常得到中国象征主义诗人的关注。
最后要看到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具有的历史价值。它既表明了中国现代诗人对西方文学思潮勇敢的接受和消化,又显示出中国传统诗学在现代性上的努力。中国象征主义诗歌不仅是象征主义的本土化,它也是意境理论的现代化。象征主义本土化超越了晚清“旧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方式,它摆脱体用的纠缠,直接在对等性的重构中建造适应时代的诗学。
[1]梁实秋:《我也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载《梁实秋文集》编委会《梁实秋文集》,第六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386页。
[2]陈太胜:《象征主义与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
[3] [清]阮元校刻:《周易正义》,载《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页。
[4]曹础基点校:《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18页。
[5]佚名:《易经证译》,上经第2册。天津:天津救世新教会1938年,第22页。
[6]Alain Rey,, tome 3, Paris: Dictionnaires Le Robert, 1998, p. 3719.
[7] Thomas Aquinas,, tome 17, Lander: The Aquinas Institute, 2012, p. 18.
[8]L’Abbé Danet,,, t. 2, Varsovie: L’Imprimerie Royalle de la republique, 1745, p. 524.
[9]Madame la Baronne de Staël,, t. 10, Paris: Treuttel et Würtz, 1820, p. 264.
[10]中江兆民:「中江兆民全集·3」。東京:岩波書店,2000年,第97页。
[11]日本近代诗論研究会:「日本近代詩論の研究」。東京:角川書店,1972年,第250页。
[12]陶履恭:《法比二大文豪之片影》,载《新青年》1918年5月,第430页。
[13]张大明:《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14]厨川白村:《文艺的进化》,朱希祖译,载《新青年》1919年11月,第584页。
[15]周作人:《英国诗人勃来克的思想》,载《少年中国》1920年2月,第44页。
[16]穆木天:《象征主义》,载傅东华编《文学百题》。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44页。
[17]梁实秋:《梁实秋论文学》。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第3页。
[18]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载余英时等著《五四新论》。台北:联经1999年,第17页。
[19]朱自清:《导言》,载朱自清编《中国新大学大系·诗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页。
[20]徐志摩:《死尸》,载《语丝》1924年12月1日,第3号,第6版。
[21]邢鹏举:《波多莱尔散文诗》。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第37页。
[22]穆木天:《我主张多学习》,载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第318页。
[23]王独清:《知道自己》,载王独清《独清自选集》。上海:上海书店2015年,第297页。
[24]李健吾:《新诗的演变》,载郭宏安编《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25]穆木天:《诗歌与现实》,载《现代》1934年6月,第222页。
[26]蒲风:《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载黄安榕、陈松溪编《蒲风选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797-798页。
[27]戴望舒:《诗五首》,载《现代》,1932年5月,第83页。
[28]李璜编:《法国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第244页。
[29]穆木天:《谭诗》,载《创造月刊》1926年3月,第86-87页。
[30]卞之琳:《魏尔伦与象征主义》,载《新月》4卷4期,第17页。
[31]Harold Nicolson,, London: Constable, 1921, p. 248.
[32]卞之琳:《卞之琳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26页。
[33]梁宗岱:《梁宗岱文集》,第2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34]唐湜:《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9页。
[35]覃子豪:《论现代诗》,台中:曾文出版社1982年,第213页。
[36]Pauline R. Yu. “Chinese and Symbolist Poetic Theories.”, 30.4(Fall 1978): 302.
[37]Jules Lemaitre, “M. Paul Verlaine et les poètes‘symbolistes’&‘décadents’,”, 25 (7 janvier 1888): 14.
[38]李国辉:《人格解体与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诗学》,载《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89页。
[39]Charles Baudelaire,, edited by Yves Florenne, Paris :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6, p. 651.
[40]Stéphane Mallarmé,, Paris: Gallimard, 1945, p. 869.
[41]吴晓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42]Charles Baudelaire,, edited by Yves Florenne, Paris :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6, p. 1181.
[43]James J. Y.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 55.
[44]D. J. Mossop,,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142.
[45]黒木朋興:「マラルメと音楽:絶対音楽から象徴主義へ」。東京:水声社2013年,第428页。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5ZDB086;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风行》杂志与象征主义自由诗的发生、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8BWW083。
(责任编辑:许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