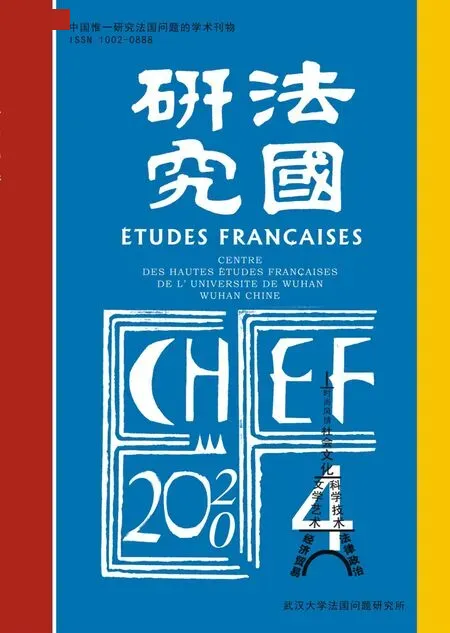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中立远观者纪德
2020-02-24俞楠
俞楠
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中立远观者纪德
俞楠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
初入文坛的安德烈·纪德虽然没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表明立场、扮演重要角色,却在德雷福斯事件的社会语境中展开了对个人和集体、文学和社会关系的思考:他在对巴雷斯民族主义思想的批判中形成了自己对法兰西民族性的定义,通过《扫罗》和《菲洛克但德》两部作品暗示了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错误认知,在《没有缚牢的普罗米修斯》中指出了作家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纪德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观察和反思不仅预示着他对社会事务的进一步介入,也表现并丰富了以文学显示观念的理念。
安德烈·纪德 德雷福斯事件 巴雷斯 作家社会责任
引言
1891年,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出版处女作《安德烈·瓦尔特笔记》(),继而创作了《那喀索斯解说》(, 1891)、《尤利安游记》(1893)、《沼泽》(,1895)、《人间食粮》(,1897)等作品。他的文学才华不仅受到了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等前辈的认同,[1]《修道院》()、《法兰西信使》()等文学杂志也纷纷向这位文学新人抛出橄榄枝[2]。在青年纪德的文学影响逐渐扩大之际,德雷福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在法国酝酿、爆发。
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下,纪德延续了《安德烈·瓦尔特笔记》、《人间食粮》、《那喀索斯解说》等作品中关于个人与集体、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在对巴雷斯民族主义思想的批判中形成了自己对法兰西民族性的定义,并以此出发在《扫罗》(,1903)和《菲洛克但德》(,1898)[3]中暗示了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错误认知及其潜在危机,还在《没有缚牢的普罗米修斯》(, 1899)中展开了对作家介入社会行为的反思。
一 法兰西民族性:多元和谐的整体
纪德在1898-1903年间发表了三篇与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 1862-1923)相关的文章:《论〈离根人〉》(Déracinés, 1898)、《诺曼底和下朗格多克》(, 1902)、《杨树之争》(, 1903),[4]对巴雷斯以“生根”(enracinement)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展开批判。
巴雷斯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小说创作,以“自我崇拜”(Le culte de Moi)为总标题创作三部曲:《在野蛮人的目光下》(, 1888)定义了“我”和不是“我”的野蛮人;《一个自由人》(, 1889)教导踌躇不前的青年如何摆脱野蛮人的目光,创造一个强大的“我”;《贝蕾妮丝的花园》(, 1891)指出要为“我”找到一个和宇宙协调的努力方向,完成“自我崇拜”[5]。巴雷斯对青年心理的关注使其成为一代人的偶像,被冠以“青春王子”的称号。[6]但是,巴雷斯认为“我”与宇宙协调的方向是法兰西的复兴,并在1897年出版《离根人》(),表述其以“生根”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7]。
《离根人》的主人公是七位来自南希的中学生,他们在1879年跟随哲学老师保罗·布代耶(Paul Bouteiller)离开家乡来到巴黎。七位“离根人”在追寻空虚梦想的路上割断了与故乡的联系,失去了传统所能给予他们的力量,其中两位走上犯罪道路,一人被绞死。巴雷斯以此批判代表理性、自由价值的布代耶,认为由他教唆的离乡背井摧毁了传统道德和爱国爱乡之情,导致个人迷失、社会无序、国家羸弱。另外,巴雷斯在1899年发表《土地和亡者》()的演讲,将“土地”作为民族意识的空间维度,“亡者”作为时间纬度,指出“只有在土地的持续作用中,祖先才能将灵魂累积的遗产完整传递给我们”。他认为民族意识的形成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法国民族意识形成的现实基础是要让法国人“生根”,让他们留在出生地,接受地区传统、以尊重地区特性的方式自治,从而形成更强韧的民族意识。[8]
巴雷斯以“生根”为核心的民族复兴思路反映了19世纪以来在欧洲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1784-1791年间,出生在东普鲁士地区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约翰·赫尔德(Johann Herder, 1744-1803)发表了《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将语言作为民族的首要决定要素,“文化民族论”(Kulturnation)渐渐成形。赫尔德赞美所有的民族,指出它们都是平等且独一无二的,没有强弱之分。“文化民族论”影响范围遍及欧洲的各个阶层,为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完成思想铺垫,在提升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却也埋下了沙文主义、民族仇恨的隐患。[9]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第二帝国失利、巴黎被围、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割让给普鲁士,法兰西民族的优越感遭到当头棒喝。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 1828-1893)等人开始反思法兰西的衰退。其中,泰纳从1875年开始出版《当代法兰西的起源》(),直至去世。他目睹了巴黎公社中激情对个体行为的驱使,认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理性,不受理性控制的自由造成了法国的混乱和衰弱,从而批判倡导自由和理性的启蒙思想,希望通过重建一个尊重传统的集权政府来实现法兰西民族的复兴。[10]泰纳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巴雷斯,这不仅表现在《离根人》小说情节、人物命运的安排上,而且泰纳还以本人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道出了个人和法兰西命运一体化的主旨:个人就像梧桐树上的一片叶子,叶子的命运依仗大树的成长[11]。总之,巴雷斯试图从个体心理出发调节个体绝对价值与社会秩序、民族复兴间的冲突,将个人对传统的顺从视为关键,他在《离根人》中将家乡等同于法国以及对个体命运的极端化处理引来了纪德的批判。
纪德在《论〈离根人〉》中以旅行和教育为例质疑生根论的普遍性,认为旅行作为一种生活环境的“离根”,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离根”,都可以带来益处。但同时他也承认教育和旅行的益处因人而异,强者可以从中变得更强,而弱者可能会因为不适应而失去活力,导致《离根人》中的悲剧。[12]
实际上,纪德对“离根”正面意义的维护呼应了《人间食粮》中对个体绝对价值的追寻。在他看来,旅行或流浪可以帮助青年人离开温暖和安逸,摆脱原生社会中宗教、家庭等主流价值观的束缚,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而当你念完时,抛开这本书——去外面!我愿它能给你这欲望:离开任何地点,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你的居室,你的思想。”[13]但值得注意的是,纪德只将流浪作为个体认识自己的一种手段,并非目的:
(……)这只是站在生活前千百种可能的姿态之一。觅取你自己的。另一个人若能和你做得同样好,你就不必做。另一个人若能和你说得同样好,你就不必说;——写得同样好,你就不必写。只致力于你认为除了自身以外任何他处所没有的,急切地或耐心地从你自身创造,唉!人群中最不可替代的那一个。(Gide,1917-1936:163)
这意味着流浪者在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后需要回到人群中,在他所属的集体中更好地塑造和完成自我。实际上,纪德将流浪作为个人反抗社会的一种方式,又以流浪者的回归暗示两者的和解,[14]表现出他对个人和集体关系的思考:集体会束缚、限制个人对自己的认识,个人可以借助流浪突破集体的宏大叙事;但个人和集体最终是相互依存的,个人在认识自我后需要回到集体中实现自我,并让集体更为丰富多元。总之,这个在《人间食粮》中还稍显隐晦的观点在纪德对巴雷斯地区主义倾向的批判中进一步显现。
纪德的父亲来自法国南部下朗格多克地区的于泽斯(Uzès),母亲来自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的鲁昂,纪德在《论〈离根人〉》中就以自身为例质疑了生根说的可行性:“生在巴黎,父亲是于泽斯人,母亲是诺曼底人,请问巴雷斯先生我要在哪里扎根?”(Gide,1933:437)在《诺曼底和下朗格多克》一文中,纪德指出正因为自己不专属于法国的某个地区,才能从诺曼底醇厚的土话和南方悦耳的方言中探寻法语的两大起源,既欣赏茂密的森林又热爱稀疏的灌木丛,同时保有葡萄酒和苹果酒的美好回忆,从而更具有法国特色,并由此形成了对法兰西民族性的构想:法国应当是一个包容并融合了各地区特色的多元、平衡整体,而且这种多元和谐的民族性可以具体表现在每个法国人身上,使个体超越地区间差异、更紧密地与国家结合在一起[15]。
综上所述,纪德对巴雷斯民族主义思想的反驳修正了后者对个人潜能的抹杀和地区主义倾向,却保留了爱国情怀,赞同维护法兰西民族的整体性。相较于巴雷斯彰显的民族主义思想,纪德的爱国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是含蓄的,但也渗透到追求中立的《新法兰西评论》()中(Anglès:184-186)。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演进,纪德渐渐意识到人们以“祖国”的名义把一批批青年送上战场,[16]继而彻底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期与天主教相结合的民族主义变体,[17]提出欧洲前途一体化的意见,[18]逐渐靠近国际共产主义思想。
二 在集体中寻找个人的位置
1894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被诬陷出卖情报、通敌叛国,军事法庭判定其罪名成立;但在德雷福斯被证实无罪后,军事法庭拒绝重审案件,引发抗议。德雷福斯事件引起了法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并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一方面,左拉(Émile Zola, 1840-1902)在1898年1月13日发表《我控诉》(),抨击给德雷福斯定罪的机构和个人,呼吁真理和正义;文艺界和学术界众多人士随即发起一份名为《知识分子宣言》()的请愿书,支持左拉、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另一方面,以巴雷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19]以社会秩序、民族保存和国家最高利益反驳真理和正义,形成反德雷福斯派。([法]米歇尔·维诺克:12-25,30)
在《我控诉》发表后,纪德马上托人寄去自己的签名,成为《知识分子宣言》名单上的一员。可一个月后,当左拉被指控诽谤、知识分子们再次发起请愿时,纪德却拒绝签名。在一些学者看来,纪德的改变源自好友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 1871-1945)的影响,后者是坚定维护军队和国家至高权力的反德雷福斯分子。但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瓦雷里之外,纪德身边不乏支持德雷福斯和左拉的家人和朋友,他的叔叔、著名经济学家夏尔·纪德(Charles Gide, 1847-1932)以及好友兼连襟哲学家马塞尔·德鲁安(Marcel Drouin, 1871-1943)都是热心的德雷福斯分子。[20]因此,判定纪德受瓦雷里单边影响从德雷福斯派转向反德雷福斯派的论断稍显偏颇;而且,纪德虽然没有就他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反复态度作出说明,但承认自己在发表政治意见时容易犹豫,会给左、右派都造成“向前一步是为了后退两步”的错觉[21]。实际上,前进后退的曲折路线反映了纪德对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思考的心路历程,当他的意见超越了“左”“右”的划分而无法做出非黑即白的判断时,就会表现出犹豫、甚至退却。纪德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反复态度恰恰表现了他在听取不同观点后的摇摆不定:他对政府的处理方法感到不满,认为政府为维护权威不及时弥补错误导致了事件的全面爆发,让国家处于危险之中(Conner:65);而德雷福斯事件的持续扩大可能削弱法国的军队力量、让外敌有机可乘,不愿再为被以诽谤罪起诉的左拉请愿(Anglès:29)。总之,他既不能认同为维护权威而无视个体的德雷福斯派,也无法完全融入为追求正义而忽视国家利益的德雷福斯派。在他看来,这两种观点的持有者不仅偏离了对个人和国家关系的正确认知,还可能在两种对立倾向的极端化中导致自我生命意义的消逝。
纪德在1898年创作五幕戏剧《扫罗》。扫罗的故事源自《旧约》:扫罗英俊高大、谦逊得体,是上帝为以色列指定的第一位王;但他在登上王位后,不再听取上帝的旨意,妒忌大卫(David)的功勋,导致国家衰退。纪德保留了《旧约》中的故事框架,淡化了神的作用,却暗示了权威对扫罗的异化:年轻英俊的扫罗在成为国王后变得暮气沉沉,但当他摘下王冠、脱下王袍、剃去胡子却风采依旧[22];扫罗为维护王权想方设法延续自己的王室,排挤大卫,导致外敌入侵。实际上,扫罗将个人权威等同于国家利益,误解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并在这错误认知下无法抵御权威对个人意志的诱惑和消磨,最终成为一个权威符号,造成了自己的死亡和国家的危机。可见,对权威的绝对崇拜和维护不仅消解了个体的绝对价值,也掩盖了国家的本质。
相较于《扫罗》中以权威联系个人与国家的思路,纪德在《菲洛克但德》呈现了为追求无暇美德导致个人与国家分离的故事,暗示了德雷福斯派追求真理、正义的潜在危机。《菲洛克但德》取材于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 495–406 av. J.-C)的同名剧[23]。纪德借用了索福克勒斯的故事框架:在希腊人前往特洛伊的路上,菲洛克但德被毒蛇咬伤,因伤口溃烂腐臭而呻吟不止,被同伴们抛弃在一个荒岛上。在特洛伊战争的僵持中,希腊人被告知只有赫拉克勒斯(Hercule)的神弓箭才能帮助他们取胜,而这副弓箭已被赫拉克勒斯送给了菲洛克但德。曾主张将菲洛克但德遗弃的尤利西斯(Ulysse)带着年轻善良的奈欧浦多伦(Néoptolème)回到荒岛,试图获取弓箭。在索福克勒斯的剧本中,菲洛克但德一开始拒绝合作,在神的干预下才与尤利西斯一同前往特洛伊参战。在纪德笔下,神消失了,尤利西斯预谋让菲洛克但德喝下安眠药取走弓箭,却被奈欧浦多伦暗中告知菲洛克但德;但是菲洛克但德仍旧喝下药水、献出弓箭,独自留在荒岛。
在纪德的《菲洛克但德》中,国家利益不仅高于个人利益,不能“为了救一个人而毁了希腊”;两者还呈现出一种冲突状态:个人需对国家承担义务,并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因为义务是“我们给希腊的献物”[24]。因此菲洛克但德向国家献出弓箭,虽然获得了完成义务后的内心平静,却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全文结尾出现的天堂般场景:“周围的百花破雪而出;空中的群鸟降下来喂他”([法]纪德:73)暗示着主人公生命的结束。不同于索福克勒斯的版本,纪德笔下的菲洛克但德虽然维护了国家利益,获得了道德上的满足,却没有回到集体、在特洛伊战争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综上所述,纪德认为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中,个人不仅需要认识自我、也需要正确认知集体的本质,从而找到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形成个人与集体的融洽状态,批判了德雷福斯事件中左右翼知识分子无法兼容个人与集体的共同思维模式,并意识到在这一思维模式下介入社会的负面影响。但在纪德构想的这对和谐关系中,集体、尤其国家似乎是恒定不变的,个人则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做出调整,既成全个人又维护集体。随着一战后法西斯主义的抬头,纪德在马克思思想理论中发现并认同个人与集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矛盾,开始将这对关系的重点从个人转移到制度,将注意力转向能促成个体价值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社会制度。(Gide,1951:1116-1117,1131)
三 作家的社会责任
德雷福斯事件重新激发了法国作家对自身社会责任的认识,他们通过文学创作、公开演讲、发表评论、请愿等方式介入社会事务、承担社会责任。“知识分子”(intellectuel)的称呼也在德雷福斯事件后开始在法国普及,指向那些凭借在思想领域的声誉和地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士,广义上的政治介入成为定义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25]
1891年,纪德发表《那喀索斯解说》,用临岸自照的那喀索斯来暗喻诗人、讨论艺术家的道德问题,指出艺术家首先是在孤单、静默中观看并获得永恒的人,“遗世独立,避开了事物,避开了时间”;与此同时,他意识到艺术脱离生活的局限性,指出艺术家需要通过观察和沉思发现生活纷乱表象下的“观念”,再用艺术显示它。[26]纪德通过“观念”将艺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指出“观念”可以超越艺术范畴,表现为“一种哲学、一种美学、一种特殊的道德”[27]。但是,以左拉、巴雷斯为代表的作家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介入行为超越了纪德对艺术家中立远观的道德要求,他在《没有缚牢的普罗米修斯》中借由两场演讲暗示了作家介入公共事务、承担社会责任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因窃取火种被宙斯(Zeus)用铁链束缚在高加索山脉的悬崖之上,每日承受恶鹰啄食肝脏的痛苦。在纪德笔下,普罗米修斯挣脱铁链,携鹰来到巴黎,并以鹰隐喻他照顾人类的职责。普罗米修斯“不再满足于给予人类存在的意识,还想要让人类明白存在的意义”,[28]发表关于鹰的演讲,鼓励人们承担责任。但是普罗米修斯不仅需要依靠老鹰和烟花表演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而且他的演讲产生了他没有预料的后果:有人以错误的方法承担责任,还有人因曾经逃避责任而愧疚至死。为此,普罗米修斯取消了之前的言论,并发表第二场演说:蒂提尔(Tityre)将沼泽中的一粒种子培植成参天大树,不仅使沼泽变成了平原,还以树为中心组织人类生活;蒂提尔厌倦了繁重的日常工作,在安热勒(Angèle)的怂恿下一同出走,在路上遇到了赤身裸体的吹笛人莫理贝(Mœlibée)[29];安热勒跟随莫理贝前往罗马,蒂提尔回到故事的起点,再次孤独地被沼泽包围。当听众询问故事意义时,普罗米修斯指出故事只为搏君一笑,意义并不重要,最后他还杀死并与听众分食了象征责任的老鹰,留下羽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全书结束后以第一人称补充道:“这本小书就是我用其中一支羽毛写成的”(Gide,1899 :157)。可见,公共人物的言论并不能完全被人理解,而且可能引发各种意想不到的反应、甚至死亡,与其如此不如专心于艺术创作。对作家介入行为的质疑同样可以解释纪德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态度:德雷福斯事件牵扯到的各方利益和隐含着的种种危机远远超出了一个作家可判断的范围和能够承担的责任。然而,不管是从蒂提尔的故事,还是从老鹰羽毛写作的隐喻,纪德并没有完全否定责任:蒂提尔因离开了责任而失去了一切,“我”试图以更为抽离的态度将责任融入到写作行为中,预示着纪德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1909年,以纪德为中心的《新法兰西评论》创刊。《新法兰西评论》在创刊号的征稿邀约中肯定了文学对社会生活的表现,并细化了表现的途径:
生活中没有什么是可忽视的。艺术家绝不是无辜者或流浪的行吟诗人。组成公共生活的一切都与他们相关,他们的幻想,即使无聊的,也从中而生。但他们难以轻易地从日常琐事中得到收获:坚硬却美味的果实,需要在石磨下碾碎;粗糙的茎杆,只能使用浸渍和捣碎后的纤维部分。[30]
可见,公共事务或政治事件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成为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对象;但是作家必须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提取其中的精华。这不仅进一步拓宽了文学可以显示的领域,也避免了作家对公共生活新闻式的写作。尽管如此,《新法兰西评论》也不得不面对夹带不同政治意见的来稿,努力在编排上维系各种倾向间的平衡,试图保持杂志的中立[31]。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局势的巨变,法国社会自德雷福斯事件后产生的裂痕加深,天主教民族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进一步分化着法国知识分子。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苏醒的作家社会责任感已逐渐演变成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威胁着文学的自主性。1927年,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 1867-1956)在《新法兰西评论》上连载发表《知识分子的背叛》(),指出法国社会、甚至整个欧洲都达到了一个政治激情登峰造极的时代,“已经没有一颗心灵不被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或民族的激情所感染”[32]。班达强调作家或艺术家应秉持中立、理性的态度,将艺术创作和政治激情加以区别,避免将政治激情带进作品,或用作品来表达政治激情。《新法兰西评论》团体在“阿拉贡事件”(l’Affaire Aragon)中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立场,具体划分文学作品与政治激情的界限。
1931年,从苏联回来的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 1897-1982)发表诗歌《红色战线》(),以列宁的名义攻击政见不同者,被以“煽动军人违抗命令和谋杀”的名义起诉。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 1896-1966)认为诗歌源自诗人的无意识创作,因此诗人不用为诗歌内容负责,发起支持阿拉贡的请愿。纪德以及时任《新法兰西评论》主编雅克·波朗(Jacques Paulhan, 1885-1968)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字。[33]因为在他们看来,阿拉贡的目的在于博得苏联的好感,[34]用文学取悦某个对象,即忽视文学本身的价值,将其工具化[35];其次布勒东所提出的文学豁免权不仅与阿拉贡的政治企图相冲突,而且让文学沦为不严肃的玩物。(Sapiro,2007:14)可见,《新法兰西评论》团体试图通过规定作家对作品内容的责任来限定其介入的尺度,从而避免文学的工具化和娱乐化。
可是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纪德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被国际社会事务所吸引。他在1932年公开表达了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同情,不仅认为苏联制度可以促进个人和集体的和谐关系,也相信苏联的五年计划能够拯救世界于危难(Gide,1951:1126)。可是,纪德在1936年访问苏联后,在质疑苏联制度的同时也反思着自己介入社会的行为,提出“不判断”的态度是艺术家面对社会事务应秉持的唯一理性态度,(Gide,1951: 1255)重申了对作家中立远观的要求。
结语
综上所述,纪德在德雷福斯事件的社会语境下展开的观察、批判和反思不仅预示了他进一步介入社会的行为,而且结合了他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对文学本质的探究。他在对巴雷斯的批判中明确了个体绝对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的道德追求,并以此出发批判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两种对立观点,揭示了它们共同的极端化、单一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暗示了作家在该思维模式下介入社会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为此,他逐渐丰富了文学显示观念的理念:“观念”源自生活,却要求对生活素材的反复批判;“显示”要求作家在以艺术表现生活时采取中立客观的立场。总之,他鼓励作家以一种批判、理性的姿态与生活和人群发生联系,呼应着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对作家社会责任的定义:通过将世界公开化、客体化介入到社会事务中,[36]表现了对作家身份认知和对写作行为认知的现代性。
[1]Claude Martin, “ Préface. ”. Paris: Gallimard, 1952 pour, 1986 pour la préface, le journal inédit et le dossier, p. 16.
[2]Auguste Anglès,. Paris: Gallimard, 1978, pp. 19-23.
[3]《扫罗》与《菲洛克但德》都创作于1898年。
[4]纪德将这三篇文章以“巴雷斯相关”()为主题一并收入《假托集》(, 1903)。
[5]Maurice Barrès, “Examen des trois romans idéologiques, le culte du Moi.”. Paris: Flammarion, 1988, p. 171.
[6] J. P. de Beaumarchais et al.. Paris: Bordas, 1987, p.180 (A-D). 值得注意的是,纪德在《安德烈·瓦尔特笔记》中对青年个体的关注让他在文学圈崭露头角时就与巴雷斯联系在一起。
[7]《离根人》与《对军人的号召》(,1900)、《他们的嘴脸》(, 1902)一起构成“民族能量”三部曲(Roman de l’énergie nationale)。
[8] Maurice Barrès,. Paris: Bureau de La Patrie Française, p. 23-25. 实际上,生根说决定了巴雷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反德雷福斯立场:首先,作为犹太人的德雷福斯没有根、没有祖国,不是真正的法国人,无法形成对法国的爱;其次,德雷福斯可能是无辜的,但是那些为正义、真理等抽象概念与国家为敌的知识分子是有罪的。可参考[法]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代》,孙桂荣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年,69-70页。
[9]Guy Hermet,. Paris: Seuil, 1996, pp. 117-129.
[10]Éric Gasparini, “Hippolyte Taine.”. vol. 40, no. 2, 2014, pp. 236-238.
[11]Maurice Barrès,. Paris: Fasquelle, 1898, pp. 202-203.
[12] André Gide, “À propos des.”. Paris: Gallimard, 1933, pp. 440-442(tome II).
[13] André Gide,, suivi de.Paris: Gallimard, 1917-1936, p. 15.译文参考了盛澄华的《地粮》译本。
[14]Pierre Masson, “Politique du voyage chez André Gide.”. automne 1984, p. 85.
[15]André Gide, “La Normandie et le Bas-Languedoc. ”. vol. 2, no. 8, 1902, pp.250- 253. 值得注意的是,纪德认为自己同时继承了父亲家族的新教信仰和母亲家族的天主教信仰,融合了法国的两种主要宗教信仰。实际上,纪德的外祖父一代已经改信新教,他从小接受的是新教教育。
[16] André Gide,. Paris, Gallimard, 1954, p.192.
[17]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天主教右派是法国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的主要思潮之一,一大批作家皈依天主教,包括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1955)、夏尔·迪·博(Charles du bos, 1882-1939)等。Frédéric Gugelot,Paris: C. N. R. S. éditions, 1998, pp. 99-100.
[18]André Gide, “L’avenir de l’Europe.”. Paris: Gallimard, 1936, pp. 124-125 ( tome XI ).
[19]在法国,“知识分子”一词最初指向左翼知识分子,在1930年代方被右翼接受。([法]米歇尔·维诺克:2)
[20]Michel Jarrety, “Valéry et la politique.”. vol. 128, no. 4, 2009, p. 902 ; Thomas Conner, “André Gide et l’Affaire Dreyfus.”. vol. 46, no. 177/178, 2013, pp. 63-66.
[21] André Gide, “Feuillets 1918.”. Paris: Gallimard, 1951, p. 667.
[22] André Gide,.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04, pp. 101-104.
[23]常译作《菲罗克忒忒斯》。另外,迪翁·德普吕什(Dion de Pruse, 40-120)一篇比较埃斯库罗斯(Eschyle, 525-456 av. J.-C)、欧里庇得斯(Euripide, 480-406 av. J.-C)、索福克勒斯三版《菲罗克忒忒斯》的文章也给纪德的创作提供了素材。Susanne Larnaudie, “: Tragédie de Sophocle et drame gidien.”. no. 16, 1969, p. 108.
[24][法]纪德:《菲洛克但德》,载《浪子回家集》,卞之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73页。
[25]Michel Winock, “L’écrivain en tant qu’intellectuel.”. vol. 21, no. 1, 2003, p. 113, 119.
[26][法]纪德:《纳蕤思解说》,载《浪子回家集》,卞之琳译。同上,第10、12-13页。
[27]André Gide, “Réflexions sur quelques points de littérature et de morale.”., p. 425 (tome II).
[28] André Gide,.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899, p. 92.
[29]蒂提尔与莫理贝都是维吉尔(Virgile, 70-19 av. J.-C)《牧歌》里的人物名。
[30]Jean Schlumberger, “Considérations.”. no. 1, 1909, p. 10.
[31]如上文所述,杂志在一战前还是沾染了轻微的民族主义倾向。《新法兰西评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停刊,复刊后由雅克·里维埃(Jacques Rivière, 1886-1925)出任主编,彻底消除杂志的民族主义倾向。(Anglès:184)
[32] [法]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5页。
[33] Gisèle Sapiro, “The Writer's Responsibility in France: From Flaubert To Sartre.”. vol. 25, no. 1, 2007, pp. 13-14 ; Riou Gwenn, “Un rendez-vous raté : communistes et surréalistes dans les années 1930.”. vol. 26, no. 1, 2018, p. 18.
[34] René Crevel,“André Gide nous parle de ‘l’affaire Aragon’. ”
http://melusine-surrealisme.fr/site/EspritRaisonCrevel/Gide.htm#Nte1(site de l’Association pour la Recherche et l’Étude du surréalisme, 2019年4月28日查阅),该文曾收录于André Breton,. Paris: Éditions surréalistes, 1932.
[35]另外在纪德看来,轻视文学本身、迎合大众趣味是阿拉贡的一贯做法,这表现在后者对剧作家亨利·巴塔耶(Henry Bataille, 1872-1922)的推崇上。纪德指出巴塔耶的作品为迎合观众趣味损害了文学价值,给戏剧界带来不利影响。(Gide,1951:922,1073,1275)
[36] Gisèle Sapiro, “De la responsabilité pénale à l’éthique de responsabilité, le cas des écrivains.”. vol. 58, no. 6, 2008, p. 896.
(责任编辑:许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