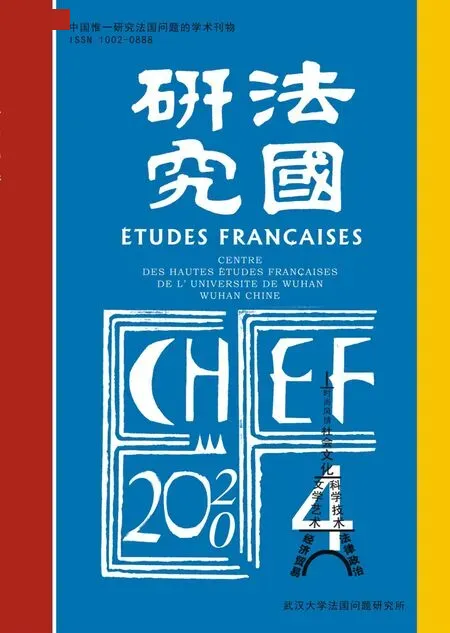多尔诺瓦夫人童话的空间书写及其社会内涵
2020-02-24张东燕
张东燕
多尔诺瓦夫人童话的空间书写及其社会内涵
张东燕
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
玛丽•凯瑟琳•多尔诺瓦夫人(Madame/ Countess Marie Catherine d’Aulnoy)是十七世纪法国童话的开创者和童话体裁的命名者。与男性童话作家注重情节发展、忽略空间细节不同,多尔诺瓦夫人在童话叙事中关注空间环境的刻画,凸显不同空间的流动转换,空间书写可谓其童话叙事的一大特色。童话空间的生动展现不仅增添了童话的文学性,也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一方面表现了波旁王朝鼎盛期的文化繁荣,另一方面揭示了父权文化的道德束缚以及女性对父权统治的抗争,体现了女性童话中的性别政治。
法国童话 多尔诺瓦夫人 空间书写 社会内涵
1697年,法兰西文学院院士、法国古今之争崇今派领军人物夏尔•贝洛(Charles Perrault)收集编写了八个童话故事,以其子之名出版了《鹅妈妈故事集》,成为欧洲文学童话正式出现的标志。[1]不过,在贝洛童话出版前的十七世纪晚期,文学童话已经借由形形色色的沙龙悄然成风,主持沙龙的巴黎仕女根据听到或读到的民间故事书写童话故事,在沙龙聚会中朗读或表演,贝洛童话在她们掀起的童话热潮中应运而生。不可否认,法国女性在民间童话的书面化和文学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玛丽•凯瑟琳•多尔诺瓦夫人(Madame/ Countess Marie Catherine d’Aulnoy)(以下简称多尔诺瓦夫人)是法国童话第一人。在1697年至1698年间,她先后创作了三部童话集,共二十余篇童话[2],对文学童话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她将童话故事定名为“仙子故事”(),使“仙子故事”一词成为专属称谓,英文单词“fairy tale”便由此而来。多尔诺瓦夫人童话与贝洛童话在叙事风格上可谓截然不同。虽然两人都从民间故事或早前的故事文本中攫取素材,但贝洛将编写重点放在精纯语言和道德教化上,在叙事上基本延续了传统故事强化情节、淡化细节、虚化时空的叙述模式,多尔诺瓦夫人则不仅关注道德寓意,也革新了民间故事的叙事形式。她突破民间故事简短的叙事模式,将数个故事加以套叠,并结合传奇小说的叙事手法,使童话情节曲折繁复、细节精微细腻,整体上具有小说化倾向,呈现了与男性童话截然不同的女性叙事特征。空间书写是多尔诺瓦夫人童话的一大特色,她乐于描摹贵族文化空间和女性生活空间,且在情节设置中不断转换空间环境。丰富多元的空间书写不仅烘托了魔幻气氛,为童话故事平添生趣,也折射出她身处时代的社会现实,既生动反映了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贵族风尚与文化繁荣,亦显示了以她为代表的贵族知识女性对父权文化的批判挑战。
一、体现文化繁荣的贵族空间
多尔诺瓦夫人童话出版之际正值波旁王朝的鼎盛期,雄霸一方的法兰西帝国国力强盛,文化艺术繁荣,统治阶级推崇的奢华格调与贵族礼仪成为个人素养和社会文明的评判标志。多尔诺瓦夫人的贵族身份使其对自身阶层的文化诉求谙熟于心,于情节铺陈中细致刻划宫廷、城堡等建筑的内景外观,在童话创作中自觉流露出强烈的贵族意识与文化品味。
《青蛇》是多尔诺瓦夫人童话的童话代表作,讲述的是因女巫下咒相貌丑陋的公主与遭受相同厄运变成青蛇的王子之间婉转曲折的爱情故事。多尔诺瓦夫人不仅着力展现两位主人公多灾多难的命运与一波三折的爱情经历,也悉心描摹人物的生活场景和活动空间,对青蛇王子海上宫殿的描述是其中最精微传神的部分。此间有宏丽的“金色大厅”,“玻璃门”连通着“宽敞的露台”,放眼望去,公主看见了“融自然美与艺术美于一体的人间绝景:开遍鲜花、随处可见喷泉、雕像、和珍奇树木的花园;远方的树林,宝石珍珠砌成,座座堪称建筑杰作的宫殿,更有那百舸争流,帆旗飘扬的宁静海面。”[3]多尔诺瓦夫人另一篇讲述王子与白猫皇后爱情故事的童话《白猫》中也有此类精心描述的宫廷空间。在写到王子无意间闯入白猫皇后统领的森林魔宫时,多尔诺瓦夫人不惜笔墨地描写了宫殿的富丽堂皇:“金色大门”上装饰着绚丽夺目的“红宝石”,墙上铺满晶莹透亮、画满仙子故事的“彩绘瓷砖”,一扇扇房门上镶嵌着“斑岩、青金或珊瑚”,“房间数不胜数”,装饰着高大的“落地镜”、悬垂的“万千烛台”和铺着“蝶翅和鸟羽”的地板。[4]这些巴洛克风格的空间环境本质上都是虚幻不实的魔法空间,但它们却如实呈现了路易十四时期的宫廷建筑格局,其中园林、镜厅、瓷画、露台、众多房间均与凡尔赛宫的建筑式样如出一辙。众所周知,经过长年的扩建和修饬,十七世纪晚期,凡尔赛宫成为路易十四的行宫,气势恢宏,金碧辉煌,显示了法兰西帝国的繁荣昌盛,从多尔诺瓦夫人对魔宫奢华精雅的渲染中不难领略其对盛世王朝的溢美之情。
多尔诺瓦夫人笔下的贵族空间不仅富丽奢华,还充满文化情趣,具有沙龙空间特色。十七世纪晚期法国文学童话的勃兴与法国贵妇主持的沙龙密不可分,童话可谓是书信、人物肖像而外的又一种沙龙文学形式。早在十六世纪,沙龙已在法国宫廷和贵族家宅中出现,十七世纪一、二十年代以后,贵族沙龙的社交作用日益突出,成为法国王公贵族主要的社交场所。举办沙龙的多是巴黎的宫廷贵妇,她们在豪华气派的厅堂里宴请名流贤达,安排各种艺术或游戏活动,使沙龙成为法国当时文学艺术和文化思想的一大策源地。推崇品味、礼仪和才学的沙龙渗透在贵族的日常生活中,推动了法国贵族的文明化进程, 对“整个法兰西民族文化气质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5]
多尔诺瓦夫人描绘的魔宫游乐空间妙趣横生地表现了沙龙文化。《青蛇》里的公主每晚可在王宫中欣赏高乃依和莫里哀的最佳剧目、参加舞会、观看杂技表演、或者阅读各式书籍;一百个长相滑稽的侏儒与她聊天解闷,言谈国家大事、名流逸闻、或是域外奇谭。诸般情景无不是沙龙活动场景的生动写照。《白猫》中的王子同样在魔宫举办的各式游戏中尽情欢乐:晚上,城堡里的白猫乐队用吉他演奏无疑伦比的美妙音乐,十二只猫和十二只猴子跳着芭蕾,前者扮成“摩尔人”,后者扮成“中国人”,一会儿腾跃,一会儿击掌;白天,打猎归来后,他可以参加室内游乐。众所周知,路易十四酷爱艺术,时常在凡尔赛宫举办室内音乐会,本人还擅长芭蕾,跳过“至少35部芭蕾舞剧”。[6]在他的推动下,音乐和舞蹈表演也在贵族沙龙中风靡开来。此外,包括球类、棋类和牌类在内的室内游戏在路四十四时期也得到很大发展,路易十四将原本私人性质的宫廷娱乐发展为君民共乐的大型游乐集会,常在在盛大场合举办数千人规模的游戏沙龙。[7]《白猫》里展现的乐队演奏、芭蕾舞表演和室内游戏场景恰印证了路易十四时代贵族的沙龙文化。
上述两则童话在主题上属于“动物爱侣”,故事原型可追溯到阿普列乌斯(Apuleius)在《金驴记》(又名)中记述的“丘彼得与普绪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乔万尼•斯特拉帕罗拉(Giovanni Straparola)所著《欢乐之夜》里一则“猪王”也属此类故事。多尔诺瓦夫人在情节上明显借鉴了上述文本,但与偏重情节推进,虚化角色活动空间的原有叙事相比,她对空间环境的关注格外突出。有趣的是,这一叙事倾向对其后法国女作家的童话叙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740年维纶纽夫夫人(Madame de Villeneuve)在其创作的《美女与野兽》中对野兽王子的宫殿也不厌其烦地加以描摹,详细叙述美女每日都在不同房间内看到的各色情形与窗外美景。贵妇作家们对魔宫空间的悉心呈现,逼真模拟了波旁王朝时期贵族的起居、游玩与交际环境,为离奇故事注入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现实元素,抒情性描述在客观上使原有故事文本优雅化,使原本情节夸张、细节疏漏的故事显得优雅精致。精雕细琢的贵族空间衬托出故事角色的仪容举止,字里行间无不显明作者的身份自觉与文化自信。
二、蕴藏性别政治的女性空间
如果说多尔诺瓦夫人童话中对贵族文化空间的高调书写体现了她的贵族身份意识,那么她对童话女性角色的一系列空间书写则透露出她的女性身份意识。作为一种女性话语形式,多尔诺瓦夫人童话蕴藏着与父权文化抗争的女性性别政治,故事中不时出现的女性囚禁空间、旅行空间和权力空间生动体现了道德习俗对女性的身心迫害以及女性勇于摆脱束缚、追求个人幸福的主体意识。
十七世纪的法国仍是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作为他者的女性在教育机会、婚姻家庭和经济政治生活方面都未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虽然沙龙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贵族女性地位,但 “沙龙女主人”们仍不能摆脱传统习俗对女性的压制和排斥。她们普遍不能享受良好的现代教育,阅读仅“限于拉伯雷本人那种尖酸的讽刺作品、西班牙田园诗、艳情诗和宗教信奉书籍”。[8]在社交场合和公共领域,女性只能充当被动的参与者,参加沙龙的男性乐意与善谈的女主人交流思想,却不赞成她们进行创作,认为“女人的使命是激发他人的灵感,而不是自己写作”。(梅森:2)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女人被要求深居简出,以维持贞洁。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遭受男性权威的打压,无法支配自己的言行。
多尔诺瓦夫人本人也深受性别之苦。据多尔诺瓦夫人回忆录记载,她十一岁时,母亲为了让初生的儿子获得继承权,强行将她送入修道院。尽管她强烈反抗,却无法令母亲回心转意,直到数年后才在父亲的策划下逃离修道院,与助她出逃的多尔诺瓦公爵结婚。[9]多尔诺瓦少女时代于修道院中度过的“囚禁”岁月是父权体制桎梏女性的一个缩影,个人经历使多尔诺瓦夫人对女性承受的社会禁锢有了深切体验,她将奋力摆脱的“囚徒”体验写进童话,频繁使用“囚禁空间”展现女性的被动处境。在她的故事里,许多公主、王后都在“深宫”、“暗室”或“地牢”中过着囚徒般的生活,直至魔法降临将其拯救:《蛙仙与狮仙》里的皇后新婚后便被前去远征的国王下了禁足令,不可踏出城堡院墙半步,国王数年未归,她百般孤寂下违背禁令,前往树林打猎,转眼被凶恶的狮仙劫持,从此经年幽居在地下魔宫中。《白鹿》中的公主出生后即被邪恶仙子诅咒,不许在十五岁前照见阳光,在父王的严令下,从小居住在没有门窗,烛火照明的暗室里。此外,多尔诺瓦夫人还借囚禁空间的恐怖意像凸显受困女性的内心恐惧。《芭比奥勒》里,公主被邪恶仙子一路追赶,掉进魔宫地窖的酒瓶里,瓶身状如巨塔,由六个巨人和六条恶龙日夜看守,令她无从遁逃;《蛙仙与狮仙》中,禁闭皇后的狮仙地宫建在地心深处,荆棘遍野,花木枯萎,水银湖中怪兽出没,渡鸦横飞,山脚下恋人日日啼哭,泪水成河,一派地狱景象。囚禁空间的描绘中凝结了多尔诺瓦夫人强烈的生命体验,折射出彼时女性的生存困境,她们被完全隔绝在公共领域之外,成为社会中的隐形人。极度封闭的囚禁空间隐含了多尔诺瓦夫人对男性霸权的控诉和批判。
与揭示男性霸权的女性囚禁空间相对,多尔诺瓦夫人童话中还存在一系列表现女性逃亡和冒险的女性旅行空间。她塑造的童话女性角色中不乏反抗命运的自救者甚至男性角色的拯救者,为生存或爱情踏上一波三折的冒险之旅。多尔诺瓦夫人本人出版过三本骑士小说,[10]对冒险叙事十分熟稔。在童话创作中,多尔诺瓦夫人显然吸收了这一叙事模式,并时而以坚强勇敢的女性角色取代骁勇善战的骑士,做出旧瓶装新酒式的改写。多尔诺瓦夫人不仅将以女性角色充当冒险主体,还以互文的手法大大丰富了民间故事中的冒险叙事。因受篇幅短小和重复性情节结构所限,民间故事中的冒险大多在单一空间中进行,而多尔诺瓦夫人童话往往具有中篇小说的篇幅,杂糅不同故事于一体,展现不断转换的旅行空间,从而大大增加了童话角色冒险的复杂程度。在《青蛇》中,公主为寻找失踪的王子,从岛国一路来到高山峡谷、动物王国,最后在爱神的引导下深入冥府救出了被囚禁的王子;《蓝鸟》中的公主为寻找化身蓝鸟的王子,跋山涉水,奋力攀登象牙山,穿越镜子谷;《芭比奥勒》中, 公主为躲避猴王的胁迫与邪恶仙子的追赶,先后沉入河底、穿越沙漠、飘上云端。
毋庸置疑,多尔诺瓦夫人童话中女性角色冒险涉及的多维旅行空间具有女性主义的反叛色彩,凸显了女性自我救赎的主体意识,这一主体意识在她构想的女性权力空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根据法国5至6世纪以来的习惯法《萨利克继承法》, 法国王位只能由长男继承,女性完全无继承王位的权利。14世纪中叶,查理五世正式更颁布法令,明确规定“任何一位女子都不能拥有王权的任何一个部分”,还禁止母亲一方的任何一位男性后裔获得王位继承权。[11]严苛的法令使法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女王,女性在政治上被完全边缘化。
多尔诺瓦夫人在童话中以仙王和女王的形象颠覆了这一传统。首先,多尔诺瓦夫人的故事中尽管不乏男性巫师,但他们的魔法远不及神仙教母或邪恶女巫强大,后者才是真正掌控人类命运的决定力量。法术强大的仙子无疑挑战了男性霸权,仙子故事的异教色彩亦对权威的神圣宗教叙事构成反叛。美国著名童话学者齐普斯说过:“法国女性童话中的仙子形象召示了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相异之处,表明她们对生活处境,尤其是关乎日常行为、言行举止的种种戒律之反抗。”[12]仙子们的反叛形象决定了魔法空间——城堡、丛林、海岛、地府之女性权力空间属性。
此外,多尔诺瓦夫人童话中的公主可继承王位或被拥戴为王:《蓝鸟》和《羊国》中的公主都继承了王位,《芭比奥勒》和《白猫》中的公主也被赋予女王形象。女性统领的王国是与仙子掌控的魔法世界互为映衬的另一女性权力空间,在这一空间,多尔诺瓦夫人淋漓展现了女性的才智和威仪。白猫女王受过良好教育,擅长狩猎,精通音律,通晓治国统军之术,以铁腕手段处置宫廷政变,怀柔之术应对败亡敌军,倍受国人敬仰。《青蛇》中“淑慎女王”统领的动物“共和国”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尔诺瓦夫人进步的民主观念。动物们原本凡人,因种种恶习被仙子变形,“带罪之身”的动物们在山谷中建立了“共和国”,鸟兽之间全无高低贵贱之分,和谐共处。在十七世纪晚期,法国封建王朝内部统治危机日益深化,革新君主制的启蒙思想已在贵族沙龙中酝酿萌生,多尔诺瓦夫人所描绘的这一女王统领下的动物共和国折射出当时先进的民主观念,显示了她具有前瞻性的治国理念。
小结
法国女性童话是沙龙园地中绽放的文学之花,身为十七世纪法国女性童话的领军人物,多尔诺瓦夫人的创作推动了欧洲文学童话的发展和繁荣。对空间的多方呈现是多尔诺瓦夫人童话显著的叙事特色,小说化的叙事倾向使她在情节推进中注重空间细节与空间转换。空间书写不仅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还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一方面,对贵族奢华雅致文化的推崇使她满怀欣喜地描摹充满时代气息的贵族文化空间;另一方面,知识女性的身份自觉又令她不断书写具有反叛意识的女性空间,从而挑战和颠覆男性霸权。
[1]今天的童话研究者将二世纪古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Apuleius)在《金驴记》中记述的“丘彼得与普绪克”视为欧洲第一个童话故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乔万尼•斯特拉帕罗拉(Giovanni Straparola)所著《欢乐之夜》(,1553)中的部分故事和吉姆巴蒂斯达•巴希尔(Giambattista Basil)的《五日谈》(,1643)中的所有故事均是欧洲较早出现的文学童话。
[2]多尔诺瓦夫人的童话集分别是(1697);(1698);(1698?)
[3] D’Aulnoy Marie-Catherine “The Green Serpent” in Jack Zipe(ed.)New York: Viking,1991. p.96.系作者自译。
[4]故事原文见www.surlalunefairytales.com/authors/aulnoy/1892/whitecat.html
[5]赵翠翠:《17世纪法国文化形态和贵族沙龙》,载《传承》2008年第9期,67页。
[6]格蕾尔·伽登:《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早期的法国音乐》,祁宜婷译。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139页。
[7]蒂博•比卢瓦:《从个人娱乐到宫廷仪式:十七至十八世纪法国国王和王后的游戏》,唐运冠译。载《紫禁城》2014年第2期,67页。
[8] [美]艾米里亚•基尔•梅森:《法国沙龙女主人》,郭小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页。
[9]多尔诺瓦夫人此段经历参见维多利亚女作家Anne Thackeray Ritchie在1892年编订的《多尔诺瓦夫人童话》所写的前言中。原文见www.surlalunefairytales.com/authors/aulnoy/1892/introduction.html。
[10]三本小说分别是:(1690);(1692) ;(1703).
[11]韧雾:《太阳王以一己之力遍树典范波旁王朝:文艺与享乐的超强辐射力》,载《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11月,63页。
[12]Jack Zipes, “The Meaning of Fairy Tale withi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2011,25(2). p.224.
(责任编辑:许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