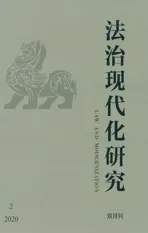英美法系土地发展权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2020-02-24姜楠
姜 楠
一、土地发展权制度的英美法系实践
(一) 英国土地发展权制度
在英国,土地发展权是一种与土地所有权相分离、独立的财产权利。所谓土地发展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土地权利人在土地上建造建筑物、独立的设施、开采矿物及其他利用土地的行为,这一行为被视为增强土地使用强度;其中建造建筑物的行为含义比较广泛,具体包括:(1) 毁损已有建筑物;(2) 重建建筑物;(3) 变更建筑物的内部结构以及对建筑物进行添加;(4) 以商业经营为目的的其他建造行为。(1)See Town and County Planning Act 1900.PartⅢ.Section55.二是土地用途的实质变更。土地所有人或者使用权人实施上述行为,即变更土地实质用途或增强土地使用强度时,必须向政府购买发展权,私自变更土地实质用途或增强土地使用强度的行为将被视为违法。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征收等行为变更私人土地用途或提高土地使用强度时要对土地权利人予以补偿。1947年,英国政府制定《城乡规划法》,土地发展权制度在这部法律中正式确立。但在1947年《城乡规划法》制定之前,英国政府先后成立了多个委员会,就城市规划体系中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周密而详细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的成果以报告的形式提交政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报告为巴罗报告(Barlow Report)、斯科特报告(Scott Report)和厄思沃特报告(Uthwatt Report)。这三个报告对英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的确立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是巴罗报告。该报告是由产业人口分布皇家委员会提供的研究报告。1937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由蒙特古·巴罗(Montague Barlow)为委员会主席的产业人口分布皇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出具的报告因此命名为巴罗报告。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于:(1) 调查城市人口聚集及分布情况;(2) 分析城市人口聚集给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及就业带来的影响;(3) 应对城市人口聚集这一现象政府应当采取的有效策略。基于上述三项职责,巴罗委员会对于英国大城市及中小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住房情况、交通拥挤情况、通勤方式、土地和房产价值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和研究。该委员会在认识和处理土地问题上的独特贡献在于,把国家或地区问题和另一个问题,即大城镇聚集区的物质环境增长联系起来。(2)参见[英]彼得·霍尔、马克·图德-琼斯:《城市和区域规划》,邹德慈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该委员会建议英国政府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城乡规划体制,控制城市和城市聚集区的增长,保护农业用地,设置规划补偿金和改善金制度。(3)参见前引②,霍尔、图德-琼斯书,第68页。这些建议成为英国立法部门确立土地发展权制度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其次是斯科特报告。斯科特报告是由斯科特(Scott)法官任主席的农村地区土地利用委员会于1941年发布的报告,该报告主要关注农村土地破坏性开发问题。当时,英国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海上封锁,食品非常短缺,因此英国十分依赖本国农业生产。所以,政府和公众高度关注农村土地利用问题。斯科特委员会的主要观点是,良好的农业用地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它一旦丧失就很难恢复。因此,国家应建立一个以保护农业用地为首要职责的规划体系;政府部门应控制农村地区的零散建设,引导所有新的定居者都尽量居住于乡镇和村庄中;农地权利人如果要改变现有农地用途,应给出富有说服力的理由,表明建设方案符合公共利益要求。
最后是厄思沃特报告。厄思沃特报告是由厄思沃特(Uthwatt)法官任主席的补偿与改良专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Compensation and Betterment)于194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主要针对土地补偿和改良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该报告对土地的可转移价值(Shifting Value)和浮动价值(Floating Value)两个概念做了区分。所谓可转移价值,是指全部土地的整体价值。该报告指出,政府的土地规划行为不会降低土地整体的转移价值,但是会造成不同土地之间价值分配的不平衡,即某项政府的开发控制决定,往往会让一部分土地权利人受损,而使另一部分土地权利人获益。虽然政府在实施规划控制时应当向受损的土地权利人支付补偿金,向获益的土地权利人收取土地改善金,但是这一政策的执行不能仅仅停留在地方政府层面,而需要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所谓浮动价值,是指一块土地受开发行为影响所具有的潜在的增长价值。这一部分的价值具有天然的投机属性(Nature Speculative),其本身并非现实已经存在的价值,而是要以土地开发已经实际发生为假设前提。举例来说,基于政府的规划行为,假设A、B两块土地只能有一块最终能够获得开发。但是未能实现土地开发的土地所有权人在土地出让过程中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仍然预估其土地可能被开发并将开发后所获得的增值收益部分(政府支付的补偿金)算入土地现实交易价格之中,没有土地出让人会认为自己的土地不会被开发而相邻的土地会被开发。这一心理暗示直接导致了土地所有人在向政府主张土地开发受限补偿金时,往往会过高地估计土地开发利益损失的实际价值。因此,政府支付的土地开发受限赔偿金往往高于土地开发受限的实际损失。(4)See Victor Moore,Michael Purdue,A Practical Approach to Planning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10.基于上述两个概念的分析,该委员会提出的对策为:政府应当将尚未开发的全国农村土地予以国有化,国家应以某一时间点的特定价格为基础,向土地权利人支付补偿金以取得土地。但在进行建设之前,土地权利人还可以对土地进行使用。当国家对土地进行特定建设时,还要向原来的土地权利人支付一笔全部征用的附加补偿金。(5)参见朱芒、陈越峰主编:《现代法中的城市规划:都市法研究初步》(下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594页。补偿金可以由中央政府建立的特定基金会来支付。中央政府负责该基金会的管理,地方政府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关注土地规划的论证与制定工作,而并不用过多考虑规划制定和执行所带来的经济和金融后果。该报告的核心观点在于主张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政府为了公共福利可以行使土地征收权力,任何土地权利人变更土地用途必须获得政府的规划许可。因此,这份报告亦被认为英国土地发展权国有化确立的基础性法律文件。
上述三份报告的核心观点对1947年《城乡规划法》的最终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三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反映在这部法律之中。其主要内容包括:(1) 明确了地方政府土地规划权力。(2) 土地权利人不得随意变更土地用途或增加土地使用强度,土地权利人变更土地用途、提高土地使用强度必须经过土地规划部门审批。对土地开发中有关补偿(Compensation)和赔偿(Betterment)的概念进行了区分,明确了两者的构成要件及适用标准。(3) 明确规划当局对于违反土地规划的土地权利人有采取法定强制措施的权力。(4) 明确土地规划部门为了实现规划目的,可以行使法定的土地征收权力。(5) 明确土地规划部门为了实现控制户外广告、保护森林和历史建筑的目的,可以行使的行政权力。(6)参见胡建淼、何俊明:《英国〈城乡规划法〉百年变迁中的规划行政权》,载《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至此,英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最终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得以确立。
1947年《城乡规划法》的显著特色在于明确了土地发展权归国家所有。这一立法实质上采纳了斯科特报告中农村土地发展权国有化的建议。该法律认为,既然实行土地发展权的国有化,那么政府应当向丧失土地发展权的土地所有权人支付一定的补偿金。该法提出一个规定,即对全英国的土地发展权都要作出评估并将评估价值汇总,汇总价值的数额要按照一定比例缩小。汇总价值之所以要按一定比例缩小,原因在于任何一个时期内城市四周的土地都不能全部开发利用,只有一部分比例的土地能够开发。但是,城市四周所有的土地所有者一般都认为他们的土地会被开发。土地所有者一般在出售其土地时,往往将土地开发后增值部分加入土地出售价格之中。因此,统计部门汇总的土地开发价值必然大于土地开发的实际价值。为了避免土地所有人的不当得利,因而汇总价值要按一定比例缩小。土地权利人在取得补偿金后仍然继续占有土地,但只能按照土地现有用途利用该土地,而国家或其授权的规划当局便取得了变更土地用途的权利。这部分法律规定的内容来源于厄思沃特报告有关处理浮动价值的建议。
由此推论,土地所有者丧失了土地发展权但已经获得相应补偿,因此他们就不再享有土地变更用途后所带来的增值利益。如果土地所有权人在获得土地发展权补偿金的情况下,又获得了规划部门变更土地用途的许可,那么此时土地所有权人即获得双重利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1947年《城乡规划法》规定,凡已经获得补偿金的土地所有者,不再享有土地开发增值利益,这部分利益全部归社会所有。其法律上的形式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向政府缴纳土地开发费(Development Charge)。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发展权补偿金的发放对象为执行政府部门土地规划而使其土地价值减损的土地所有权人,对于拒绝执行政府土地规划的土地所有权人即使其土地发展权受到损害或限制,依然无权获得政府补偿。依据上述规定,从1947年《城乡规划法》开始实施到1954年,英国政府预计要向丧失土地发展权的土地所有权人支付3亿英镑的补偿金。这一巨额数字给英国财政部门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因此,1953年新上台的保守党制定的1953年《城乡规划法》将1947年《城乡规划法》有关政府支付土地发展权费用的相关规定修改为,土地所有者申请开发许可未被批准时,国家才有支付补偿金的义务。(7)参见前引②,霍尔、图德-琼斯书,第80页。
依据1953年《城乡规划法》,土地发展权仍为土地所有人享有的一项权利,土地所有权人因此能够合法获得土地用途变更后的全部增值利益。土地开发者对土地进行开发时只需负担一些外部费用,这些费用往往产生于社区公共目标的需求。这一外部费用的支付视为土地开发者应当承担的规划义务以及新社区基础设施负担。例如,土地开发者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同时负责被开发社区的公共道路、绿化带及幼儿园、学校的施工建设。从性质上来看,政府支付的补偿金不再是国家为购买土地发展权而向土地所有权人支付的购买费用,而是政府限制土地所有权人变更土地使用用途而支付的赔偿费。尽管1967年《土地委员会法案》以及1976年的《土地发展税法案》试图恢复土地发展权的国有化,但是最终没有取得成功。现如今,1947年《城乡规划法》大部分土地金融条款已经废除,土地发展权国有化的做法在英国彻底失败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意图控制土地发展权的地方政府无法承受高额的补偿负担,除非政府允许一部分土地所有权人自己行使土地发展权;另一方面,不想控制本地区土地发展权的地方政府又希望以不付出任何代价并以收取开发费用的形式从土地所有者手中获得大量资金,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8)See Victor Moore,Michael Purdue,A Practical Approach to Planning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09.这种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必然因遭到执行者的抵制而最终消亡。
(二) 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
美国仿照英国于20世纪60年代确立了土地发展权制度。美国法上,土地财产权具有高度的弹力性与可分性。土地财产权被认为是由不同权能内容的子权利所组成的权利束。根据社会发展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不同权能的子权利的地位和重要性会有不同差异,具有普遍认同性且亟须法律加强保护的某项子权利因而可以与所有权相分离,成为具有独立性的权利。
土地发展权原本只是土地所有权中的一项权能,由于变更土地用途权利的行使对于权利人乃至整个社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美国的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人享有的一项私人财产权,取得独立地位的土地发展权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进行合理的转让(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TDR)。(9)有关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的详细介绍,参见刘国臻:《论美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3期;高洁、廖长林:《英、美、法土地发展权制度对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启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4期。规划部门将自然保护区、历史遗迹以及农地等土地发展权受限制的地区作为权利发送区(Sending Zones),而亟须突破法定建筑密度或变更土地法定用途的城镇区域为权利接受区(Receiving Zones)。接受区域的土地权利人如果突破土地、建筑物的使用强度或变更土地、建筑物的法定用途土地,需要向发送区的土地权利人购买土地发展权。发送区的土地、建筑物的权利人出卖其土地发展权后,其土地、建筑物的使用强度不得增加,用途不得变更。
在Suitum v. Tahoe Regional Planning Agency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的合法性给予了认可。(10)See Suitum v. Tahoe Regional Planning Agency, 520 U.S. 725 (1997).随后在各个州法院的判例中,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确认。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为Gardner v. New Jersey Pinelands Com’n案。(11)See Gardner v. New Jersey Pinelands Com’n, 125 N.J. 193 (1991).在该案中,新泽西最高法院认为,松林地农业规划符合宪法规定的原因在于该州土地发展权制度的确立。土地所有权人完全可以通过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获得相应的补偿。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认可了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的合法性。
除判例法外,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在许多州以成文法的形式得以确立。例如,《纽约州一般城市法典》(General City Code of New York)第2章A节《城市权力》第20-f条对该州的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作出详尽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1) 土地发展权的定义;(2) 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设立的模式及条件;(3) 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实施的程序设计。(12)See NY Gen City L§20-f (2015).《亚利桑那州修订条例》第9章《城市和乡镇》第9节《分区管制、听证及定义》第462-1条第12项就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中政府权力、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公告听证程序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13)See AZ Rev Stat§9-462.01 .12(2015).截至2013年,近25个州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了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此外,至少还有8个州虽然在立法中没有规定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得到普遍应用。各个州出台有关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的立法文件的意义在于:一是确立了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的法律正当基础;二是明确了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适用的目的及所要保护的土地类型;三是对自愿及非自愿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做了类型化的进一步区分。(14)See Julian Conrad Juergensmeyer,Thomas E.Roberts,Land Use and Development Regulation Law(The Third Edition),Thomson Reuters Business Press, 2013,p559.
二、土地发展权制度的理念与功能
(一) 土地权利社会化与土地发展权的形成
土地权利社会化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土地利用观念。土地权利社会化思潮催生了土地发展权,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权利社会化的产物,带有土地权利社会化思潮的深刻烙印。土地权利社会化成为土地发展权的确立和发展的核心理念。
近代以来人口数量急速膨胀,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已更为明显。为了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兼顾各方利益,土地权利的绝对化的观念日趋式微,土地权利的社会化思潮为各国所认可。(15)土地权利的绝对化向社会化转变是法律从倾向个人法益保护向倾向社会法益保护的有力回应。这一转变打破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土地利益划分为所有利益与资本利益的二分结构,进而形成所有利益、资本利益与生存利益三足鼎立的局面。法律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三种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具体论述参见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1页。正如法国学者路易·若斯兰所言:“不用精深的研究,我们就可以见到这所谓无限制的财产权,尤其在不动产权方面,有许多的障碍、阻挠、范围在压制它的行动,抗拒它的扩张。”(16)[法]路易·若斯兰:《权利相对论》,王伯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既有土地权利观念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法律以及公共利益的限制,权利人对其权利的行使更加受到法律的关注。土地权利的私有性、绝对性的色彩逐渐退却,公共性、相对性的权利属性逐渐突出。土地权利社会化反应在法律制度层面,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土地权利的行使应当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二是土地权利人负有法律规定的社会义务,如纳税、依照土地规划利用土地;三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发展社会福利的需要,可以行使征收权力,土地权利人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土地权利社会化思潮的核心价值在于强调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土地权利人对土地的利用并非是一种绝对的自由,而是应当符合社会整体秩序和公共福利的要求,这一要求具体表现为土地权利人对其享有权利的土地的利用强度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度,权利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用途利用其土地,不得随意变更土地用途。而对土地用途的变更以及提高土地使用强度正是土地发展权的内容。土地发展权是在土地权利社会化思潮促使下,土地权利绝对化受到法律及公共利益限制的产物。(17)参见黄祖辉、汪晖:《非公共利益性质的征地行为与土地发展权补偿》,载《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土地发展权的观念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前还未为人们所认知。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土地稀缺性日益凸显,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土地用途的决定、变更以及土地使用强度的提高应当受到法律规制,不应当属于土地权利人的一种绝对自由。(18)参见臧俊梅、王万茂:《从土地权利变迁谈我国农地发展权的归属》,载《国土资源》2006年第6期。由此可见,土地发展权在本质上是对“国家和法律只服务于个人主义终极目标的工具”(19)[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页。这一法律理念的回应与反叛,其制度精义则致力于为社会整体福利和秩序服务。
(二) 土地增值利益的平衡与土地发展权的配置
任何权利的设定和运行机制都是以一定法律利益为内在驱动力,土地发展权亦不例外。权利人自主变更土地使用用途要以符合行政部门土地规划并已经获得行政许可为前提条件,行政部门的土地规划实质上决定了土地的用途、容积率等土地利用项目及指标。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块的用途、容积率等土地利用的项目及指标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不同地块的价值产生差异。但土地规划造成不同地块权利人在获得土地价值方面处于不平等地位。此外,现代社会土地价值的增加是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发展政策以及土地周边经济文化状况等多种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土地权利人对土地价值增加的贡献非常有限。因此,土地增值部分完全由土地权利人享有缺乏正当性,土地价值的增加部分应当由其贡献者共同享有。上述利益分配不平衡现象需要一种法律机制予以调节,于是土地发展权制度便应运而生。
变更土地用途以及提高土地使用强度成为土地发展权的应有内容,而土地用途的变更以及土地使用强度的提高必然产生土地增值利益。对于土地用途与土地使用强度受到法律限制的土地权利主体来说,其对土地的利用受到抑制,土地权利人可以依据其享有的土地发展权请求补偿。其获得补偿的资金来源于其他土地变更用途以及土地使用强度提高后产生的土地增值利益收入。对土地增值作出贡献者,可以请求分享土地增值利益,其正当性基础同样在于其享有的土地发展权。如此一来,不同用途及使用强度的土地的价值利益可以达到平衡状态。由此断定,土地增值收益管理,归根到底是一个土地发展权的配置问题。(20)参见惠彦、陈雯:《英国土地增值管理制度的演变及借鉴》,载《中国土地科学》2008年第7期。土地发展权是调整土地增值利益的法律手段,土地增值利益的平衡是土地发展权应有的功能。
三、英美法系土地发展权制度的启示
(一) 土地发展权的本土化
1.土地发展权的界定
在我国,土地发展权又称土地开发权。(21)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开发权事实上并无本质区别。但有学者认为土地开发描述的是土地利用的物质空间形态的变化,是一种行为而并非一种权利。它是土地发展权得以产生的基础,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开发行为的规范和控制。参见张友安、陈莹:《土地发展权的配置与流转》,载《中国土地科学》2005年第5期。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于土地发展权的内涵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用途变更说。该观点认为,土地发展权就是变更土地不同使用用途的权利。(22)参见江平主编:《中国土地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刘俊:《土地权利沉思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二是土地用途变更及使用强度提高说。该说认为,土地发展权的内容不仅仅包括变更土地用途还应当包括土地利用强度的提高。(23)参见陈小君等:《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页;孙弘:《中国土地发展权研究:土地开发与资源保护的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柴强:《各国(地区)土地制度与政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三是农地发展权说。依据我国土地利用的现实状况,农业用地变更为建设用地只能通过行政征收加以实现,土地发展权主要解决的是农业用地变更为建设用地的问题。因此,土地发展权又可以称为“农地发展权”。(24)参见刘国臻:《论我国土地征收收益分配制度改革》,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1期;周建春:《中国耕地产权与价值研究——兼论征地补偿》,载《中国土地科学》2007年第1期。四是综合权利说。该说认为土地发展权的内容不仅包括土地用途及使用强度的变更,还应当包括土地及建筑物空间利用的权利。(25)参见胡兰玲:《土地发展权论》,载《河北法学》2002年第2期;胡兰玲:《房地产法新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110页。四种观点都认为土地用途的变更是土地发展权的应有内容,争议在于土地发展权的客体是否应当包括土地之外的建筑物以及土地使用强度的提高、土地及建筑物的空间拓展是否应当属于土地发展权的内容。
首先,在我国不动产法律规范体系中,土地与房屋是两种相互分离的不动产。房屋作为建造在土地之上的不动产,亦涉及用途变更及使用空间强度增加的现实问题。因此,土地发展权的权利客体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土地,还应当扩张至地上建筑,土地发展权确切的称谓应当为不动产发展权。
其次,关于土地及建筑空间拓展的权利,事实上属于空间权的范畴。为适应不动产利用空间不断扩大的现实需要,我国《物权法》确认了空间权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36条)。所谓空间权,也称为空间利用权,是指权利人基于法律和规划的规定对于地上和地下空间依法利用,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26)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8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458页。虽然我国《物权法》没有将空间权作为独立的权利类型加以规定,而是将其纳入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范畴,但是空间权作为一项独立的用益物权的观点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27)参见前引,王利明书,第463-466页;彭诚信、臧彦:《空间权若干问题在物权立法中的体现》,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3期;马栩生:《论城市地下空间权及其物权法构建》,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3期。因此,土地及建筑物空间拓展权利不在土地发展权概念的涵射范围之内。
再次,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土地利用类型,广义上的土地用途变更不仅包括农地变更为建设用地,还应当包括建设用地变更为农地、农地变更为天然林地、草地等土地用途变更类型。狭义上的土地用途变更仅仅是指农地变更为建设用地。土地发展权概念中的土地用途变更应当是广义上的土地用途变更,农地发展权只是土地发展权内容的一部分,两者不能等同。唯有如此,土地发展权制度的适用才能具有普遍性。
最后,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其重要的使用方式为农业耕种。在农业耕种过程中,农地利用者基于改良土壤、培肥地力而使农地生产能力有所提高,从而使农地价值有所提升,这种情况亦应当属于提高了土地使用强度。因此,土地发展权意义下的提高不动产使用强度不仅仅包括不动产原有空间使用强度的增加,还应当包括通过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等方式使农地生产能力提高的情形。
土地发展权的准确含义应当为权利人变更不动产使用用途或提高使用强度,并从中获得收益或者获得补偿的权利。这里的提高使用强度不仅包括提高不动产利用强度(未变更不动产用途情况下)的情形,还包括通过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等方式使农地生产能力提高的情形。
2.土地发展权的性质
从我国既有土地权利体系以及土地管理实践出发,未来我国土地发展权应具有两面性,即土地发展权既可以是一种公权力,亦可以是一种私权。
一方面,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即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各级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有土地所有权。土地发展权必然以土地所有权的存在为基础。各级政府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其作为土地发展权的主体,行使该权利亦具有正当性。各级政府成为重要的土地权利人和公共管理人。当土地发展权归属于各级政府时,由于各级政府具有公权力主体身份,该土地发展权表现为公共权力。(28)土地发展权国有论的观点,参见陈柏峰:《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彭錞:《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国问题与英国经验》,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另一方面,土地发展权并非初始的、自然状态下的权利,而是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通过强制性手段压缩了土地权利人权利行使的空间而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公权力对土地权利人规划自身土地利用的侵蚀日益加剧。如果土地发展权完全蜕变为一种公权力,土地发展权的更多价值将被掩盖。在我国,国家、集体是土地的所有权人,对土地资源享有绝对的、最终的法律控制权力。将土地发展权作为私权配置给特定的土地权利人,对于维护土地权利人对土地的合理利用,捍卫和保留权利人利用土地的私人空间更加具有必要性。(29)土地发展权私有论的观点,参见程雪阳:《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
3.土地发展权的归属
土地发展权的性质事实上决定了土地发展权的归属。对于具有公权力属性的土地发展权而言,其享有主体为各级政府;对于具有私法属性的土地发展权而言,其享有的主体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建筑物所有权人以及以土地为客体的用益物权的权利人。之所以将以土地为客体的用益物权的权利人作为土地发展权的权利主体,原因在于将所有权与用益物权相分离是我国土地法律规范体系中基本的权利结构。土地所有权不能买卖、抵押,土地所有权不具有市场流通性。以土地为权利客体的用益物权则具备一定的市场流通性。以土地为权利客体的用益物权人自然成为土地权利市场交易的主体,将土地发展权配置给此类主体更能发挥该权利的应有功能。同时,以土地为客体的用益物权一般具有较长的存续期间。在这一期间内,以土地为权利客体的用益物权人对特定土地享有法定的占有、使用权。土地用途的变更以及使用强度的提高对这类权利主体的利益产生实质影响。因此,为了维护其对特定土地的合法利用,法律应当赋予以土地为客体的用益物权的权利人相应的土地发展权。
(二) 土地发展权的应用
随着我国土地法律制度理论建设的不断发展,借鉴英美法系土地发展权先进的制度理念解决我国土地开发利用的现实问题,早已形成理论共识。结合我国实际,土地发展权在我国土地管理以及土地权利制度的完善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土地发展权的应用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土地征收补偿中的应用
长期以来,我国土地所有权形成了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二元所有权模式。城市及其郊区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第1款、第2款)。从土地功能分类的角度来看,由于城市及其郊区的土地绝大多数为建设用地,大部分承载建设职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农村地区的土地主要为农业用地,这部分承载农业用途的土地归集体所有。众所周知,建设用地集中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与农地相比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加之商业开发、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建设用地的价值与仅仅依靠个体劳动力及初级农产品利润增加资本投入的农地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说,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初始的创立阶段就存在先天不足。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3条,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集体土地不能作为建设用地。集体土地只有转变为国有土地才能被赋予作为建设用地的资格。由此决定,国家所有权对集体所有权享有终极控制力,农地向建设用地转化的途径只能为征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集体土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并非单纯的土地用途改变,而是伴随着土地所有权的转变。一方面,集体土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只有通过行政征收才能实现。这便意味着所有权变动的依据是国家公权力的命令与强制。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集体及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人均不享有变更土地用途的权利。另一方面,集体土地变更为建设用地,势必引起土地价值的大幅增加。但由于此时的土地所有权已经归国家所有,该部分土地增值利益归属国家。而集体土地原所有权人、用益物权人,只能获得固定价值的土地补偿,无权参与土地增值利益分配。以土地征收为主要模式的城市化的过程即是“集体、农民交地,政府获利”的过程,进而导致土地增值利益分配不公。(30)参见曲相霏:《消除农民土地开发权宪法障碍的路径选择》,载《法学》2012年第6期。基于这一现实状况,法律赋予集体、农民(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人)以土地发展权,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一方面,法律赋予集体以土地发展权,使其享有特定的变更土地用途的权利,有利于打破国家对建设用地的垄断,进一步缩小征地范围;(3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第10项修订内容为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3条;第16项修订内容为允许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为他人设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这意味着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享有特定的变更土地用途并从中获得收益的权利,集体土地变更为建设用地不再需要通过土地征收手段加以实现。允许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为他人设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享有土地发展权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法律赋予被征收集体土地所有权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人以土地发展权,使其成为集体、农民(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人)请求并获得被征收农地的增值利益的法律依据, 有利于保障集体土地所有权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土地增值利益的公平合理分配。
2.基本农田、历史建筑及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建设用地的需求量逐年增长,大量耕地变更为建设用地,耕地数量日益减少。耕地数量的减少直接威胁到我国粮食生产的安全。针对上述的严峻形势,中央确定了国家耕地面积不能低于18亿亩的红线,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32)参见《国土资源部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8号)。基本农田区域的划定是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具体措施。所谓基本农田是指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基本农田的土地用途被严格限定为农业用途,基本农田权利人变更土地用途的权利受到法律的过分抑制。此时,法律应当赋予基本农田的土地所有权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以土地发展权,以该权利为基础和依据,使其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土地发展权的实现方式由享有变更土地用途的自由转变为获得国家的货币补偿。(33)参见李凤章:《“土地开发权国有”之辩误》,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5期。这一经济补偿金应当来源于邻近地区其他土地用途变更后产生的增值收益。同样,为了实现历史建筑及环境保护的目的,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被划定为环保区域的特定土地权利人必须妥善维护历史建筑,保持特定地区土地的原貌,上述权利人对历史建筑、特定土地的利用受到了法律抑制,法律同样应当赋予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环保区域的特定土地权利人以土地发展权,进而保障上述权利人能够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这一经济补偿金应当来源于邻近地区其他房屋开发以及其他地块土地用途变更后产生的增值收益。
3.土地规划制定及实施中的应用
作为具有权力属性的土地规划权的合理界限在于一般与抽象,其功能仅仅是要为土地权利人利用土地的活动提供一个总体框架。也就是说,土地规划权对于土地利用的干预不能具体到各个细节而应当停留在区域性、宏观用途规制的程度。一旦超越这一界限,土地利用的管制将成为规划行为唯一的目标,其僵化性亦必然显现,土地权利人对其土地的利用必然要受到过度的限制,其追求经济效益和生存价值的动机毫无运作空间。同时,这一过程还意味着规划当局利用权力代替土地权利人作出了土地利用的大胆决定,但是与权利人相比,在一味追求管制秩序的理念支配下,他们并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的情况,并且对如何合理地利用这块具体的土地更是一无所知。事实上,随着统一规划区的扩大,人们对有关地方情况的具体知识的利用必然更为低效。(34)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29页。允许上述土地权利人在符合土地规划的前提下,享有一定的变更土地用途及提高土地使用强度并获得土地增值利益的权利,具有现实意义。
4.农地生产力提升补偿机制中的应用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耕种农地过程中,提高了农地的生产能力,农地的使用强度得以提升,土地的价值得以增加,这部分土地增值利益来源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劳动力及资本的投入,其应当归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法律上,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于这部分土地增值利益有权请求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获得补偿的正当性基础应当为其享有的土地发展权。
综上所述,英美法系土地发展权制度是在土地权利社会化思潮影响下产生的权利制度。在我国,土地发展权的准确含义应当为权利人变更不动产使用用途或提高使用强度,并从中获得收益或获得补偿的权利,其应当具有公权力与私权的双重属性,各级政府、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以及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人应当成为土地发展权(力)的主体。尽管我国既有的土地权利体系中没有土地发展权的概念,但是这一权利对于解决我国土地管理实践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而言,土地发展权在土地征收补偿、基本农田保护、历史建筑保护、自然环境保护、土地规划的制定实施以及确立提高农地生产力请求补偿机制的领域中,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