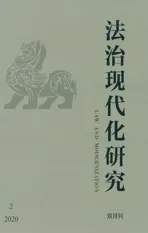《刑统赋》注释本与宋元时期的律学转型
2020-02-24彭巍
彭 巍
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晚年整理所藏孤本旧抄时,检出十二种“世所罕见者”,期待其能“长留于天壤”,其中有四种为《刑统赋》注释本。(1)参见《沈碧楼丛书自序》,载(清)沈家本编:《沈碧楼丛书》,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标点,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遗憾的是,自《沈碧楼丛书》刊印至今百年有余,却罕有对此数十卷旧抄的专门研究,既有研究对这些注释本亦缺乏关注。(2)目前对《刑统赋》的专门研究较少,不过对中国古代律学的部分专门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刑统赋》的地位和价值,如对“例分八字”的研究普遍认为可能是傅霖在《刑统赋》中最早作出了“例分八字”的概括,参见吴欢:《明清律典“例分八字”源流述略——兼及传统律学的知识化转型》,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3期;陈锐:《“例分八字”考释》,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2期。对于《刑统赋》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岳纯之提出《刑统赋疏》具有三项价值:“申述了一些至今仍然值得关注的法律观点,深化了我们对唐宋元三朝刑法制度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唐宋元三朝法典的校勘和复原”。参见岳纯之:《论〈刑统赋疏〉及其法学价值》,载《政法论丛》2014年第2期。沈家本在《宋刑统赋序》中也着重强调《刑统赋》帮助复原、研究宋刑统的价值,这一观点也被当代宋史学者广泛接受。参见《宋刑统赋序》,载(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 附寄簃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12页。这些观点都是从实质上认识《刑统赋》或其注释本的价值,但宋元律学家注释《刑统赋》的行为以及《刑统赋》众多注释本在形式上也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这些尤其为学界所忽视。在修撰《四库全书》毁弃无数刑名之书的背景下,这些成书于宋元时期的注释本能够在七百余年后重现于世,是我们认识其时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的直接素材,无论从其内容、形式,抑或局部、整体的角度,这些注释本都能够为既有研究提供有力的论据。本文试从这些注释本的注释体例和注释内容角度,对律学在宋元时期的转变和发展做一论述。
一、《刑统赋》及其注释本概述
北宋律学博士傅霖所撰《刑统赋》(一说为《刑统赋解》(3)何勤华认为应当作《刑统赋解》,并引沈家本《刑统赋解》跋中所言“似无‘解’字者,脱文也”为据,参见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不过这一观点也主要是猜测,并没有充分证据。现在较普遍的观点,仍是认为傅霖所撰为《刑统赋》。)一书,当时可能并不出名,以致南宋初期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止言:“《刑统赋》二卷,皇朝傅霖撰,或人为之注”,(4)杨一凡编:《中国律学文献》(第一辑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而且傅霖其人在《宋史》无传,生平亦几不可考。(5)刘乃英认为:“傅霖为官当在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以前,并大约在世于此年代前后。”参见刘乃英:《宋代〈刑统赋〉作者与版本考略》,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1年第4期。有观点认为《刑统赋》作者律博士傅霖与张咏同时代的青州傅霖为同一人,参见《中国人名大辞典 历史人物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傅霖”条。何勤华对此作了简要分析,认为青州傅霖和律博士傅霖应当是两个人,参见前引③,何勤华书,第182页脚注。本文认同何勤华此处观点。然而,“在金、元时,颇重其书,故注家甚多”,(6)前引④,杨一凡书,第147页。其中的“赋文”受到极高重视,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注释版本。不过明代以后,此书流传又少。(7)刘乃英研究指出:“《刑统赋》现存最早的传本为元刻本一卷……但此后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刑律变化,流传即渐稀少。书后钤明代嘉靖年间藏书家‘昆陵周氏九松迂叟藏书记’、‘周良金印’两枚朱印……书后钤盖明代藏书家印鉴,可知此书在明代传本已不多见。”参见前引⑤,刘乃英文。傅霖《刑统赋》戏剧性的命运,正是中国古代律学在宋代以后发生巨大转变的真实写照。
关于《刑统赋》及其注释版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有记载,全文如下:“《刑统赋》,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傅霖撰,霖里贯未详,官律学博士。法家书之存于今者,惟唐律最古。周显德中,窦仪等因之作《刑统》。宋建隆四年颁行。霖以其不便记诵,乃韵而赋之,并自为注。晁公武读书志称,或人为之注,盖未审也。其后注者不一家。金泰和中,李佑之有《删要》。元至治中,程仁寿有《直解》《或问》二书。至元中,练进有《四言纂注》,尹忠有《精要》。至正中,张汝辑有《略注》,并见《永乐大典》中。此本则元佑中东原郄氏为韵释(按,赵孟頫原序但称郄君,不着其名),其乡人王亮又为增注,然于霖所自注竟削去之,已非完本。亮注亦类皆剽袭前人,无所发明,且传写伪误,第四韵第七韵内脱简特多,殊不足取。”
《提要》所记注释《刑统赋》者有七家,但正如沈家本在《刑统赋解》跋中所言:“惜当日之宗旨,鄙弃之以为不足道,徒存其名于《提要》之中,而不可复考也。”(8)前引④,杨一凡书,第147页。《提要》中所提到的诸多注释版本,除《提要》本之外,几乎都已亡佚。(9)沈仲纬《刑统赋疏》中有以“直解”为题的注释内容,或许正是程仁寿《直解》,但亦无从考证。此外,《提要》所言李佑之有《删要》,另有记载为《删注刑统赋》,二者应为一书。参见前引②,岳纯之文。经过沈家本多方找寻,方才找到四个注释本,全部收录于其《沈碧楼丛书》中,分别为《提要》所言元人郄氏韵释、王亮增注本《刑统赋解》,(10)郄氏的姓名和生平,甚至所在年代,均有争议,参见前引③,何勤华书,第183-184页。对于郄氏究竟是否为元人,争议各方依据的主要是《刑统赋解》诸序、跋中内容,本文根据《刑统赋解》中郄氏所作“歌曰”内容认定郄氏为元人,详情见后文。元人孟奎注本《粗解刑统赋》(下称《粗解》),佚名注本《别本刑统赋解》(下称《别本》)和元人沈仲纬注本《刑统赋疏》。
以此看来,在宋元时期,为《刑统赋》作注的至少有这十家。不过其中多数注释本都已不可见,今日还能见到的对《刑统赋》的注释,全部来自于沈家本收于《沈碧楼丛书》中的四个注释本。(11)得益于沈家本的搜集和整理,这四个《刑统赋》注释本得以流传至今。该注释本的影印本,参见前引④,杨一凡书。另有整理过标点的版本,参见前引①,沈家本书。此外,沈家本所作“跋”有点校本,参见前引②,沈家本书。为了研究材料的一致性和原始性,本文对《刑统赋》注释本的使用,以杨一凡编影印本为准。
二、现存《刑统赋》注释本内容与结构
尽管现存只有四个注释本,若以注者分而论之,则《刑统赋解》中有三家注,《粗解》与《别本》各一家,《刑统赋疏》中可能有两家。诸家注文详略不一,内容、结构亦有差异,以下分而析之。
(一) 《刑统赋解》的内容与结构
《刑统赋解》正文的内容,从整体上看首先分八韵,从“一韵”到“八韵”依次展开,各韵长短不一,每一韵下又对傅霖所著《刑统赋》赋文逐句作注,包括题为“解曰”的注释、题为“歌曰”的郄氏所作韵释、题为“增注”的王亮所作注释。先举三韵中一段为例。赋文为“罪因搜检而得者许推于状外”,“解曰”:“凡有陈告官司,止凭元词鞫问,不得状外别求他事。按《厩库律》云,若有告人盗杀马牛,搜检得却有私造军器之类,虽是状外亦难推鞫也。”“歌曰”:“官凭状告,不求别词;若因搜检,有犯官司;心怀不臣,岂敢容止;虽是状外,听问余事。”“增注”:“鞠问状外不求余事,若因搜检而得别罪,亦许推之。”(12)前引④,杨一凡书,第54-55页。
其中以“解曰”为题的注释内容,是否出自傅霖,历来说法不一。综合各家观点和现存注本来看,此处“解曰”内容应当不是傅霖所为,但也无从考察究竟为何人所作。(13)沈家本于《刑统赋解》跋中言,“惟原注之为霖所自作抑出自他人,则尚烦考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刑统赋》二卷,皇朝傅霖撰,或人为之注’。《玉海》(六十六)引淳熙中兴馆阁书目之说同。是在宋孝宗时已不能定此注之出于何人。惟沈仲纬《疏》本有俞淖杨维桢二序并言‘傅霖设为问答’。似原赋实有自注之文。《提要》谓霖自为注,而以晁说为非,殆别有所据欤”。参见前引④,杨一凡书,第145页。今人研究中,也有将“解曰”内容视为傅霖自注,如前引②,岳纯之文。然而,《刑统赋解》篇首“律义虽远人情可推”条后“解曰”中有“亡金将十二章类为律义三十卷”语,至少说明“解曰”有部分内容形成于金朝灭亡之后,或可证明“解曰”并不出于傅霖之手。而且沈仲纬《刑统赋疏》二韵中“着而有定者律之文”条下有“律学博士傅霖云:‘见于文者,按文而可知;不见于文者,求意而后得。’”一句,在《刑统赋解》中同一赋文下“解曰”中并未出现,两段注解在文意上也有较大差别。本文以此认定“解曰”非傅霖所作。就内容看,“解曰”注释较为详细,常常引用律文开头,形式为“按《某某律》云”,后接律文,之后再作解释。“解曰”引律文可谓不厌其烦,一条注释中甚至引用多条律文,达二三百字,如六韵“六脏计贯,或终如其始”条就分别引用了《贼盗律》《职制律》《杂律》。除引律外,也有引令,如二韵“余亲余脏,各随文见义”,“子孙非周亲也,或与周亲同”,“高曾同祖父也,或与祖父异”等三条都引《服制令》。(14)前引④,杨一凡书,第39-41页。也有引疏议的,如二韵“窃原著而有定者,律之文;至变而不穷者,法之意”条下,有“议曰若以妻为妾者……”,(15)前引④,杨一凡书,第30页。与现存《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中相关内容文字虽均略有出入,但大意相同。还有引儒家经典的,如二韵“身自伤残者,无避亦等于有避”条下“解曰”中有《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16)前引④,杨一凡书,第44页。
郄氏所为“韵释”,即文中以“歌曰”为题的部分,是《刑统赋解》中非常有特色的内容。傅霖所作《刑统赋》,文字对仗工整,朗朗上口,但文字长短不一,又过于简略。郄氏“韵释”虽在韵律上不甚讲究,文辞上不及傅霖赋文,但其言语通俗,都为四字短句,不仅便于记诵,内容上也较赋文详细许多。“歌曰”部分,对应于各条赋文的大都为八个四字短句,共三十二字,只有个别赋文下,有多达十六句、二十句的情况。对有些赋文内容较简单的,为了凑足八句,也会加上一些套话,如二韵“私贷私借,皆以字为法”条下,“歌曰”部分最后两句是“先王立法,万代为例”。(17)前引④,杨一凡书,第39页。“歌曰”的内容也透露了作者郄氏的生活年代,在二韵“高曾同祖父也,或与祖父异”条下,“歌曰”部分有“若持孝服,止依元制”一句,(18)前引④,杨一凡书,第42页。据此可以认定郄氏为元人。“歌曰”部分不直接引律文或儒家经典,但会将律文、经典甚至历史故事以四字短句的形式简要讲出。“歌曰”在《刑统赋解》中具有独立的地位,不仅在于其歌诀的形式,更在于其内容上有创新,如三韵“配所犯徒杖,不过于二百”条下,“解曰”只讲了“若徒人居役再犯徒者,徒加杖制”及对应杖数,“歌曰”却讲“割鼻刖足,汉文改笞。……景帝减杖,止于二百”,(19)前引④,杨一凡书,第62-63页。从刑种变化和刑罚减轻的历史角度作了额外说明。
王亮所作“增注”在每条赋文后的注释中字数最少,常常只有一句话;内容也相对简单,没有对律文等的引用。大都只是对赋文以较通俗的话简述一遍,《提要》称“亮注亦类皆剽袭前人,无所发明”,并不为过。(20)沈家本于《刑统赋解》跋中,指出三韵“会赦会降有轻于会虑”和六韵“部曲娶优于杂户”条下各有注释内容上的错误,前者在“解曰”中,后者在“增注”中。参见前引④,杨一凡书,第147-149页。“增注”部分经常重复“解曰”和“歌曰”中已经提到的内容,不过偶尔也有新意,如六韵“妻非幼而准于幼”条中就另外提到“在《礼》及《诗》……”;(21)前引④,杨一凡书,第108页。又如六韵“女称子而异于子”条下“增注”简单一句“缘坐不同也”,(22)前引④,杨一凡书,第108-109页。点出了该条赋文的关键。
(二) 《粗解》和《别本》的内容与结构
《粗解》和《别本》都只包含傅霖所作赋文和各自的注解,并且都不分韵。其中,《别本》较之《刑统赋》赋文,则缺一韵、二韵及注释内容。现分别摘取其中“罪因搜检而得者许推于状外”条及其注释为例加以说明。《粗解》中注:“凡人之招,有正招,有又招。正招者,招其状之正犯;又招者,因其搜检而得。此即状外之罪,非状外之余事也。”(23)前引④,杨一凡书,第170页。《别本》中为:“人告某事,止合依某事理论。旧例,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鞫之。若于本状上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其有应掩捕,搜检得余事,必合追究者,即听别推理问,不入本宗之事也。”(24)前引④,杨一凡书,第216页。
沈家本在《别本》跋中言:“(《别本》)其解视孟解为详。”(25)前引④,杨一凡书,第287页。其大致如此。不过,《粗解》作者孟奎在自序中有言:“前辈律士,详论精微,发明蕴奥,或文或歌,无不备具。惜乎泥于傍蹊曲径,巧于赘辞强解,殊使初学之士骤不能知。辗转昏晦难明,而失其本意。愚也孤陋无学,敢误后人,而以俗语粗解,故不揣也。然世之蹈规矩而明刑法者,幸勿以画虎效颦为哂。”(26)前引④,杨一凡书,第155-156页。可见,孟奎之“俗语粗解”乃有意为之,是为避免落入前人窠臼。《粗解》一书,并不像《刑统赋解》一样分韵,又不引律文等规范文字,亦不单独释字、词,而只就赋文内容,以通俗话语重新表达并简单展开解释。《粗解》卷首有“前乡贡进士沈维时”序,中言“邹邑孟氏文卿,略加笺注,然后大义数十,炳如日星,其用心亦勤亦。观者幸勿以为粗解而略之”。(27)前引④,杨一凡书,第156页。此言较为中肯,今日研究也不应以一“粗”字简单否定。
再看《别本》,由于其缺失一韵、二韵两部分内容,加之注释方式和长度与《粗解》相类,附于《粗解》之后,直至晚清才被有心之人看出是两本书。(28)参见前引④,杨一凡书,第287-288页。《别本》亦不分韵,不引律文等,只有对赋文的注释。但注释又较《粗解》略详,方式上也有差异。其中常有对字词的解释,如“诈传制书情类诈为”条下,有“背信藏巧谓之诈,扬递人知谓之传”;(29)前引④,杨一凡书,第228页。“语其常则皆重已然之后”条下,有“常者,事之常行者也;已然者,事之已成者也”。(30)前引④,杨一凡书,第230页。也有引用律文,以引唐律和宋刑统为多,在“女称子而异于子”条下还引有《魏律》。(31)前引④,杨一凡书,第252-253页。此外还有引用儒家经典,如“官物宜吝于给受”条下有“夫子曰:‘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引《论语》;(32)前引④,杨一凡书,第231页。卷末有“书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又曰:‘义刑义杀’”引《尚书》,“妻非幼而准于幼”条下,引用《周礼》《毛诗》。(33)前引④,杨一凡书,第279页。这些在孟奎看来,只怕多是“赘辞”了。
(三) 《刑统赋疏》的内容与结构
《刑统赋疏》从篇幅上看,几乎等于前述三本之和。内容上分为八韵,每一韵下亦对赋文逐句作注,包括赋文后紧接着沈仲纬的释文(无题注,姑且称为“疏文”)、题为“直解”的注释和题为“通例”的案例,其中“疏文”部分远较其他注者为详。仍旧以“罪因搜检而得者许推于状外”条为例。“疏文”为:“断狱律,‘诸鞫狱者皆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余罪者,以故入人罪论’。疏议曰,‘鞫狱者谓推鞫之官,皆须依所告本状推之;若于本状之外傍更推问,求得笞杖徒流及死罪者,同故入人罪之类。若因其告状或应掩捕搜检,因而检得别罪者,亦得推之’。是故《厩库律》云,‘若有告人盗杀马牛,搜检得却有私造军器之类,虽是状外,亦听推鞫’。盖所告之事应掩捕搜检,因其事搜检而得,是以亦得鞫之也。如或监临举劾之欲劾状外他罪者,又必须别举行牒方可施行。”“直解”:“鞫问之法,状外不求余事,若因搜检得罪,虽是状外,亦许推之。”“通例”:“皇元八年九月部检旧例,‘诉讼人皆不得于本争事外别求余事,摭拾见对入及本勘官吏,若实有干,已候本宗事结绝别行陈告状外,不求余事’。大德五年正月,江浙省咨绍兴路金孟二窃盗许尚钱物,内将至元钞二十贯收买私盐一担在家被获,招伏,刺断七十七下。合从私盐为重,取到本路,推官违错招伏。部议,金孟二窃盗钱物、收买私盐,二罪俱发,合从私盐为重科决。计已到断,别无定夺,搜检得罪,合同。”(34)前引④,杨一凡书,第381-383页。
对《刑统赋疏》的结构,沈家本已于跋中概括:“其书于原赋逐句为之疏解,并引《唐律疏议》以证明之。疏之后为‘直解’,语较简质。‘直解’之后为‘通例’,则引元代断例及案牍以相印证。视《韵释》《增注》《粗解》三家为详明矣。”(35)前引④,杨一凡书,第579页。此外,《刑统赋疏》卷首有“会稽杨维桢”序中称赞其“待论厚而诗书者乐闻,演义白而俗吏所共晓,析类例最精而大吏者取信”,对理解“疏文”“直解”“通例”各自内容及相互关系颇有助益。(36)在杨维桢序中,对傅霖所作赋文评价极高,但也指出其存在“诗书者薄之而不读,市井虽读而不能通其意,苛察大吏且或妄引他比以杀人”的问题。参见前引④,杨一凡书,第295-297页。
《刑统赋疏》中的“疏文”部分,主要是对赋文文意的阐明,并根据解释的需要引用律文、律疏等。如前举“罪因搜检而得者许推于状外”条,先引律文和疏议,最后再说明两句。又如五韵“官司捕逐法宽于救助”条,“疏文”先言“官司之事既有缓急,律之议刑岂无轻重”,接着说“故《斗讼律》云”,详述律文规定,最后说:“盖贼盗未散之时救助,则财无伤而人无害;若盗贼既散,虽是捕捉,则财已伤而人已害矣。故不捕逐者,其法宽;不救助者,其法则不得不严也。”(37)前引④,杨一凡书,第442-443页。不难看出,“疏文”与前述《刑统赋解》中“解曰”及《别本》在注释方式上颇有相似处,既如前者广泛征引,又如后者条分缕析;不过“疏文”较此二者更为翔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刑统赋疏》卷首“洛阳令俞淖”序中有言“吾友沈仲纬以儒饰吏,以诗书用律”,(38)前引④,杨一凡书,第299-300页。沈注也的确不时体现出儒家话语,如韵五“替流之役无丁难准徒加杖”条下,最后有“于此可见,先王立法,始恤之以仁,终断之以义也”,(39)前引④,杨一凡书,第471页。这种以儒家仁义道德做评价的话语在元代以后的私家律注中都是十分少见的。
题为“直解”的注释,沈家本在该书跋中说:“元至治中程仁寿有《直解》。此书之《直解》是否采用程书,抑为沈所别撰。程书尚载于《永乐大典》中,《四库》开馆时未经辑出,无从考究矣。”(40)前引④,杨一凡书,第580页。不过,参考前引杨维桢序,“直解”的设置乃是有意为之,针对的是市井百姓和胥吏,若果真如此,则“直解”极有可能为沈仲纬自作。单从内容上看,“直解”大不同于沈仲纬前注,通常只有一句话,多为将赋文以流畅、通俗的语言简单重述一遍,没有任何引用。“直解”较之孟奎《粗解》更为粗简,但其用意可能相近。
相比较于其他诸家,沈注的最大特色在于其中题为“通例”的部分,如沈家本所言,“引元代断例及案牍以相印证”。(41)前引④,杨一凡书,第579页。不过,“通例”中也有引律文的,如“失器物者方辩于官司”条下“通例”中开头就是“至元新格内,仓库局院官物,取贮不如法,防备不尽,曝晒不以时,致有损毁者,各以其事论罪,所坏之物仍勒赔偿”。(42)前引④,杨一凡书,第432页。以成案附于律文和释文之后,要求注者有较高的律学修养和丰富的司法经验,非身为“郡府掾”的沈仲纬不能胜任。这种附成案于律(或律释)之后的注律方法,在宋代及以前几乎不见,而多见于明清。
三、发生于宋元之际的律学转型
沈家本在《法学盛衰说》中提出“迨元废此官(指律博士),而法学自此衰矣”,(43)前引②,沈家本书,第2043页。视元明清三代为法学衰世,(44)这一观点影响久远,如何勤华所著的《中国法学史》第二卷中,就将明清两代一同冠之以“中国古代法学的衰落”。参见前引③,何勤华书。不过许多当代学者从明清私家注律之兴盛对明清律学的发展持肯定态度。(45)如武树臣认为“明清律学便顺着自己本身的规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怀效锋提出“律学在明代复苏,其成果层出不穷,蔚为壮观……清代律学集传统律学之大成,是中国历史上私家注律的鼎盛阶段”;张晋藩认为“清代律学是中国古代传统律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官私并举及一时之盛的发展阶段”等。参见武树臣:《中国古代的法学、律学、吏学和谳学》,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怀效锋:《中国传统律学述要》,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张晋藩:《清代律学兴起缘由探析》,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评判标准各有差异,导致结论不尽相同,但各派观点中存在一个基本共识,即宋代之后,中国古代律学发生了显著的转变。(46)张中秋也提出:“许多事实表明,传统中国律学之衰,应始于宋而不是元。”参见张中秋:《论传统中国的律学——兼论传统中国法学的难生》,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这一转变最直观的呈现就是传世文献的数量。事实上,对中国古代律学的研究,也大致以元代为分界线,对唐宋时期律学的研究与对明清时期律学的研究呈现着截然不同的面貌。研究唐宋律学,用力多集中于《唐律疏议》和《宋刑统》这样的律典,这固然与传世文献稀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唐宋时确实少有注释唐宋律学的作品。(47)对中国古代“律学”的理解,一直有由广而狭的多种定义。张晋藩认为:“律学又称传统律学,是注释国家刑典的一门学问。”参见张晋藩:《中国古代司法文明与当代意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2期。本文认同这一观点,中国古代律学的核心和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注释律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所载唐代法律类著作,尽管已悉数亡佚,但从名称上看,可能主要包含总论法律各方面问题如李博文《治道卷》,以及占多数的各类编定法律规范如刘仁轨《永徽留本司格后本》、王行先《律令手鉴》、卢纾《刑法要录》等,很难再找到对律典进行注释的作品的踪迹。(48)何勤华:《唐代律学的创新及其文化价值》,载何勤华编:《律学考》,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6页。宋代留存至今的法律类作品则数量较多,种类亦丰富,除傅霖《刑统赋》外,还有如孙奭《律音义》、郑克《折狱龟鉴》、“幔亭曾孙”所编《名公书判清明集》等。徐道邻曾指出:“中国过去的朝代,官家所藏前朝及本朝的法典和法律书,要算宋朝为第一。”(49)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中国台湾地区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297页,转引自前引③,何勤华书,第34页。然而,其中仍未出现逐条注释律文的作品。可能与注律相关的,如孙奭所撰《律音义》,其内容只是“正音、正义、正字的资料”;(50)[日]冈野诚:《北京图书馆藏宋刻律十二卷音义一卷的研究》,崔瞳、冷霞译,载前引,何勤华书,第326页。此山贳冶子撰、王元亮重编《唐律释文》也主要是“对《唐律疏议》疏文中的字、词做出的音读和释义”;(51)前引③,何勤华书,第61页。即使是傅霖所撰《刑统赋》,本身也只是将《宋刑统》的一些重要规定以歌、赋的形式予以表达,这都不同于自秦汉以来长期沿用的逐条注律行为。
明清时期情况则大不相同。明代律学作品存世较多,据今人统计有不下百种。(52)《明史艺文志》载“刑法类”只有46种,其中还包括《大明律》和《御制大诰》等官方法令典。何勤华结合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相关藏书记载,统计出明代律学作品101部。参见前引③,何勤华书,第230-235页。其中为注释律学作品的至少有二十余种。(53)以存世作品看,书名提及明律并包含“解”或“注”字的,几乎都是逐条注律的作品。有明代律学为基础,加之清代法制“详译明律”,清代私家注律达到了中国古代私家注律的又一高峰。据今人统计,清代私家注释清律者有百余家,注本一百五十余种,(54)何勤华和何敏的统计相近。参见何敏:《从清代私家注律看传统注释律学的实用价值》,载《法学》1997年第5期;前引③,何勤华书,第241页。并发展出了种类丰富、形态各异的其他种类律学作品。(55)对明清时期律学作品的种类,学界有多种多样的认识。如张晋藩认为有五类,参见张晋藩:《清代私家注律的解析》,载前引何勤华书,第452-477页;何勤华认为有八类,参见前引③,何勤华书,第242-243页;吴建璠认为有七类,参见吴建璠:《清代律学及其终结》,载前引,何勤华书,第398-412页;等等。既有论著分类众多,不一而足,但对律文的注释是核心形式,围绕这一基础才发展出其他种类律学作品。除注释律文的私注作品外,有万维翰《律例图说》、沈辛田《名法指掌》之类图表作品,有黄运昌《大清律例歌括》、程梦元《大清律例歌诀》之类歌诀作品,有王明德《读律佩觿》、吕田芝《律法须知》之类专讲司法活动中的疑难概念和具体问题的作品,以及《大清律例根原》、吴坛《大清律例通考》之类考证律条源流的作品,等等。
因此,比较唐宋律学与明清律学,其间转变最重要的无外两个要点:一是涌现了大量注律作品,二是注律者多为私家。但由于转变之广涉及律学研究的主体、对象、方法、表现形式等多个方面,称其为律学转型亦不为过,即从唐宋时期的官注独秀向明清时期私注勃兴的转型。申言之,纵观中国古代律学发展史,只有两个时间段大量出现私家注律,一为汉代,一为明清。汉代经学家注律,成果为律章句。《晋书·刑法志》载,“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可谓盛世,但终于“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56)《晋书·刑法志》。自此私家注律为官方律注所取代。而唐代官方修撰的《永徽律疏》集前代注律方法和成果之大成,《宋刑统》亦沿用“疏议”内容,其间未有私家注律者。(57)有专文论述中国古代的注释律学中的官注与私注的交替发展。参见彭巍:《传统中国注释律学中的官注与私注》,载吴玉章、高旭晨主编:《中国法律史研究》(201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156页。何以至明清时重又兴起私家注律之风,一般是从明清统治阶级的思想专制、宋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法学教育由公转私的角度加以解释。(58)参见前引③,何勤华书,第201-202页。事实上,明清的私家注律行为,在宋元之际已初现端倪,这就是其时对《刑统赋》的注释。
四、宋元时期律学转型的原因
宋元时期广泛涌现的对《刑统赋》的大量注释及形成的注释本,直观地呈现了唐宋律学向明清律学的转型过程。从注释成果看,《刑统赋》在宋元时期至少有十家注释,形成了十种以上的注释本。从注释方法看,《刑统赋》注释本中的诸家注释包含了对字词句的解释,并广泛引用律文、成案,还编成了歌诀,恰如之后明清律学的大致面貌。从注律主体看,沈仲纬为郡府掾,其余注者是否为官为吏皆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其注释都不是官方行为。《刑统赋》在宋元时期被大量注释,可谓是明清私家注律的发端。但它们之间的区别又是显而易见的,在于后者注的是官方律典,而前者不然。因此,注释《刑统赋》的行为与其形成的注释本,既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官方注律,亦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官私诸家注律,而是宋元律学转型时期特有的产物。
有鉴于此,对宋元律学家注释《刑统赋》行为的理解,应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注释《刑统赋》目的何在,二是为什么会产生对《刑统赋》的注释。前者寻求是内生的动因,后者追问的是外部的改变。
(一) 宋元时期司法实务的现实需求
推动《刑统赋》注释行为的,应当是当时司法实务的强烈需求。《刑统赋》赋文始作于北宋,并非宋元时人所为,专门将一百余年前所作的并不出名的赋文翻检出来进行注释并蔚然成风,究其原因只能是社会实际需要使然。对此徐道邻认为,在宋元统治下,“法官判罪,依然要参考宋律……不过在异族统治之下,汉人怎敢明目张胆的在旧朝代的法典上写作?而恰好有《刑统赋》这篇文章在那里,从名目上看,好像似一篇文艺作品。因而为之作注,不至于犯朝廷之忌。同时传播法律知识,又有很切实的实际作用”。(59)前引,徐道邻书,第284-285页,转引自前引③,何勤华书,第59页。说其似文艺作品,这一理由难以成立,但认可其“切实的实际作用”无疑是正确的。
薛梅卿认为,“《宋刑统》颁行后没有得到较大范围的流传,后曾亡佚一时,从而傅霖的《刑统赋》替代了《宋刑统》的地位”,(60)前引③,何勤华书,第60页。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因为单就《刑统赋》赋文来看,赋文笼统抽象,许多地方高度概括,任举一例如“累脏而不倍者三、与财而有罪者四”,如果没有详细的注释,几乎难以知道所言为何物。(61)在《刑统赋疏》中,沈仲纬已经大体说明傅霖赋文与《宋刑统》的关系:“《刑统》总律有七百一十一条,此赋非其全文,乃宋律学博士傅霖撮取诸条之机要,事有相类者,乃触其类而遍可知矣。”参见前引④,杨一凡书,第308页。《刑统赋》赋文如果脱离了注释和律典,是万难领会其含义的,更不谈实际应用了。尽管傅霖为《刑统赋》所作之注在宋元时仍可能广为流传,但今已难窥其面貌,其注究竟详略程度如何,有无引用律文甚至成案,都不可知。大胆猜测,《刑统赋》在元代,其实是作为基层实际司法活动的原则和准据存在的。从诸家的注释中可以看到,《刑统赋》中抽象的赋文,通过引用《唐律疏议》《宋刑统》以及宋元的法律规范而被具体化、确定化,又通过字词的解析和文意的重述而愈显明晰,更通过与成案的联系而直接指导司法适用。《刑统赋》如桥梁和纽带一般,本身不是法律,却将实际需要与专门法律规定二者联系起来。
同时,元代司法制度尤其是基层司法的实际运行机制催生了这一需求。一方面,在元代的司法实践中,适用“旧例”或“旧律”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包括适用唐律、宋刑统以及金律。(62)参见胡兴东:《元代司法运作机制之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6期。因此,通过《刑统赋》的详细注释以及其中广泛搜罗的唐宋金律,能够为元代基层司法提供更为详尽、更具操作性的法律规范,也能为基层司法官吏提供更详明、通俗的解说,这也是与元代法制不够健全相适应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在元代的司法活动中,在没有成文法等规范时,适用传统“法理”也是较为普遍的情况。(63)参见前引,胡兴东文。而一定程度上,傅霖所撰赋文正是唐宋律学之“法理”的全面深刻的概括。(64)岳纯之认为其“申述了一些至今仍值得关注的法律观点”,参见前引②,岳纯之文。对于《刑统赋》如何阐明法理,亦参见[英]马若斐:《南宋时期的司法推理》,陈煜译,载《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2013年第2期。
这种强烈的司法实务需要是与中国古代的制定法传统紧密相连的。中国古代自春秋子产铸刑书、邓析造竹刑开始,便有制定并公布成文法的传统。对公开的律文加以解释的内在需求,自秦以后一以贯之,直至清末。《商君书》中讲商鞅的理想:“郡县诸侯一受禁室之法令,并学问所谓。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65)《商君书·定分》。商君受《法经》以相秦,其后的秦国《法律答问》,无论是否官方的法律解释,其中对秦法的理解和解释显然都不是可以任意而为的。秦以后,虽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阳儒阴法的实际做法使得对各级官员的规制和管理非常严格,不仅要求官员在司法活动中依照法律断案,更将对法律的不严格遵循和适用入罪。因而,不仅朝廷需要各级官员通晓法律,官员自身也有这一需求。对法律的解释,通过口头传授只能局限于有限范围,而落成文字则不仅能广泛传播,更能使之划一。于是,对律文的解释,以律注作品的方式在古代中国法制发展的早期就已迅速发展起来。但由于历代统治者对注释律文的认识及举措不同,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官方律注只断断续续地出现于西晋至宋。其后出于对官注的补充甚至替代,私注又再度兴起。解释律文的现实需求的长期存在,决定了律文注释无论以官注还是私注的形态都必定存在。
因此,尽管经历宋元时期的转型才广泛兴起私家注律,且《刑统赋》注释本所注并非当时律文,这都不足以切断中国古代注释律文的传统。宋元时期对《刑统赋》的广泛注释承前启后,曲折委婉地延续并发展了注释律文的技艺,也巧妙地填补了战乱时期司法实际的需求。因此宋元时期律学的转型,并非是主旨上、价值上、实质上的转型,而是方法上、结构上、形式上的转型。在前后巨大的变换之中,更应看到其一脉相承之联系。
(二) 法律教育机构和文本的缺失
司法实务的内在需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注律传统,构成了注释《刑统赋》的内生动力,但直接促成这种注释行为的外源性因素,则来自现实世界的制度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作为官方法律教育机构的律学及专职教授法律的律博士在宋以后消失,二是为《宋刑统》所继承的《唐律疏义》中的“疏”部分并未由明清律承袭。
就第一点而言,与今日所称中国古代律学的“律学”二字不同,在唐宋文献中,“律学”一词多用来指代官办的法律教育机构,多与“博士”连用,为“律学博士”,为教授法律的官职。(66)本文作者使用国学网检索工具“国学宝典”(www.gxbd.com),对《新唐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云麓漫钞》《唐六典》《旧唐书》《宋史》《全唐文》《通典》《太平广记》《唐文续拾》《全宋文》《新五代史》《唐会要》《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进行检索,“律学”二字的检索结果共105条,文中判断以此检索内容为据。作为官方法律教育机构的律学,“仅存在于魏晋至宋,期间多有变化”。(67)叶炜:《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徐道邻称:“在南宋的文献里,我们也还没有发现关于‘律学’的记载。可能自南渡起,宋朝就不许置律学了。”(68)前引,徐道邻书,第185页,转引自前引,叶炜文。作为官办教育机构的律学,历史较“律博士”晚,且常有设律博士而不设律学的时期。沈家本在《设律博士议》中考察律博士的历史,言“此历代律博士之官制也。其品秩、人数、多寡、高下虽不尽同,而上自曹魏,下迄赵宋,盖越千余年。”(69)《设律博士议》,载前引②,沈家本书,第2059页。但到了明清时期,都已不再设律学或律博士,尽管明清律中有“讲读律令”条,要求官员学习法律,但已经没有了官办的教育机构和专职的教授人员。(70)明清两代“讲读律令”缺乏成效,有制度和文化两方面原因。参见彭巍、周冰:《讲读律令——中国古代官方法律教育的断点》,载《原道》总第34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律学”一词于宋末元初逐渐突破了“官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含义,自此开始更多的指代一种以讲明律意为出发点,以司法活动的准确适用为导向,以对律文的注释为主要表现形式,以与司法活动相关的官员、幕僚、学生为主要传播群体的专门知识。
就第二点而言,明清律虽承袭唐律,对唐律的继承中与《宋刑统》不同,完全没有保留《唐律疏议》中“疏”的内容。然而《唐律疏议》后以“议曰”“问曰”“答曰”为题的律文注释恰是《唐律疏议》的生命力所在。仅以《刑统赋》注释举例,在《刑统赋疏》中,沈仲纬于“意有未显又详于疏议”条下注道:“律之疏议者,盖诸条所载律,有未明显处,每一条正文之下,各有疏曰议曰谓之疏议。疏者,将正文逐一句一字疏分开。议者,讲正文一字字议论解说,以明其意之微也。”后引用斗讼律中部分内容以说明。最后说,“此其所以作疏议之详,以明律意之微也”。(71)前引④,杨一凡书,第320-322页。而《刑统赋解》该条下有,“解曰:律意千有余条,若有不能解者,再三详审疏文之义,自得其理也”。(72)前引④,杨一凡书,第32页。仅这两条注释,足以表明后人眼中“疏议”对于唐律的价值和意义。
五、律学的转型与法学的衰落
自秦法家倡导并贯彻实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来,对法律文本的教授和学习就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这种注释和解读律文的传统,本质上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及社会文化对成文律法准确性的一致需求的体现,以对律文的官方注解和私家注解此消彼长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法律传统最早期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法律答问》等秦代出土文献,这甚至可以被视为最早的官方律注。其后,汉儒以创作律章句的形式沿袭并发展了这一传统,这是中国古代私家注律的兴起和第一次高峰。再其后,这一传统又经晋朝张斐、杜预注《秦始律》始回归于官方注律,直至发展出中国古代官方注律的最高成就即《唐律疏义》。
但正如本文已经指出的,由于宋代以后,既没有官方的专门教育机构和专职教授人员,又没有官方的详细的律文注释,在司法活动的现实需求下,绵延千年的注律传统以不同以往的面貌重获生机,填补了宋廷南渡后大厦将倾中的制度混乱,也发出了后世明清律学的先声。尽管《刑统赋》不是具有实际效力的律典,对《刑统赋》的注解也不具有规范效力而充其量只能作为基层官员审断案件的参考,但注释《刑统赋》的行为在本质上却与其他朝代注释律典的行为相同。《刑统赋》注释本的大量出现,是宋元时期律学转型的缩影,也是中国古代律学由官学再度转入民间的发端。
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宋元时期的律学转型在中国古代律学发展历程中意义重大,堪称古代律学在注律主体、方法及形式上的全面转型,而且在其后明清时期形成了品类丰富而且体量庞大的著作,这种转型仍是不够深刻不够彻底的,本质上还是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适应和延续,没有触及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文化中的根本性内容,没能为中国古代法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具有变革性的思想力量。《刑统赋》作为北宋律学博士凝炼《宋刑统》精华的抽象文本,后世并没有从抽象原则的层面对其作更进一步的原理性的阐发,而是不约而同地结合自身经历和掌握的素材做着还原抽象原则为具体规范的工作。对于《刑统赋》的注者和读者而言,更为迫切的是司法活动中可供应用的法律规范,或审断工作的技术解说,或至少是辅助记忆的通俗读本,而并不需要学理上的贯通、反思或批判。
因此,从中国古代律学的发展历程看,宋元时期的律学由注释《刑统赋》开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从包含了价值层面和学理层面的中国古代法学的发展角度看,宋元时期的律学转型并没能阻止古代法学进一步走向衰败。(73)从更大层面看,《刑统赋》注释本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宋代司法传统由人伦理性向知识理性转型的深化和延续。参见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的转型及其意义》,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陈景良:《宋代“法官”“司法”和“法理”考略——兼论宋代司法传统及其历史转型》,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但古代律学在知识和技能趋于专精化的同时也走上了去价值化和工具化的道路,这却是需要反思的。中国古代的法学在经历了汉代以来漫长的法律儒家化并在唐宋取得了“得古今之平”的高度法制成就后,逐渐丧失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律学也逐步沦为价值无涉的专业知识,其目光所及仅限于审判工作中的法律适用,而对于律文的修缮甚至法律制度的改革都全然不敢涉及。律学作为一门精研律文的学问,尚且不能从中产生对律文的批判和反思;而古代批评法律者,又多非学律之人,所言亦只能失之泛泛。自始至终以司法实务工作为导向的中国古代律学,在其工具属性不断强化的同时,其学理属性也越来越淡薄,其改革传统法制的能力也因此近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