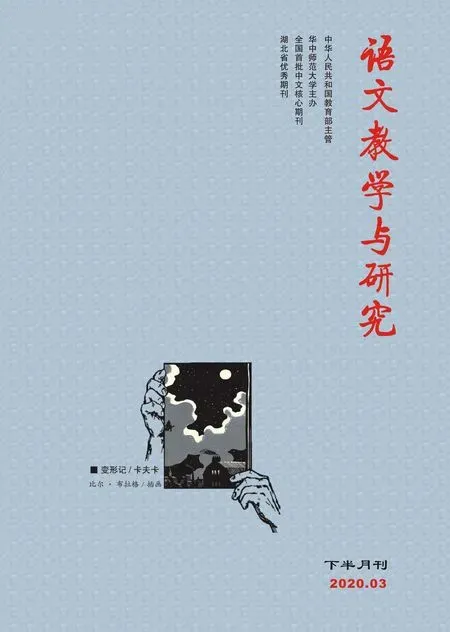语文教学内容的选定策略探析
2020-02-23
王荣生教授说:“我国语文教学的严重问题,是语文教学内容的乱象。教学内容的不正确、不妥当乃至荒唐,在语文教学中大面积地存在着。”而《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要求语文课程以“核心素养为本,推进语文课程深层次的改革”。在语文教学内容的选定既要关注知识技能的外显功能,更要重视课程的隐性价值,还要关注语文课程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新的内涵变化。然而,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语文教学内容选定不确定性的弊病却越来越凸显,很多专家和一线老师逐渐认识到“教什么”远比“怎么教”更重要。为此,研究和探讨语文教学内容选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及策略探析就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一、语文教学内容选定存在的问题
关于语文教学内容的选定问题,语文界对此进行了众多的有益的研究和探讨。但是,目前语文教学内容选定方面依旧有着以下问题:
(一)随意解读
基于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特点,语文教学内容无法具体量化,不像其它课程教学内容那样明确,再者因为教师的个人主观因素,对语文文本的解读和理解也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特性。语文老师对语文内容解读的随意性主要体现在解读历史化、政治化、极端化、分散化等方面。
如部编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第24课,杜甫《春望》,在注释中交代了历史背景:“此诗为杜甫安史之乱时期在长安所作,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八月……途中为叛军所俘,后困居长安,该诗作于次年三月。”若解读中老师一味强调写作背景,本诗会就会被理解为对君主的忠贞和意志的坚定,而爱国之情和对家人的眷恋之情就会被淡化。再如部编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1课,毛泽东《我三十万大军横渡长江》,在较早的文本解读理论书中也有比较强调政治方面问题的痕迹,过重强调政治方面的意义,而忽视了新闻的特点和结构。
(二)以“课文内容”代替“教学内容”
课文内容,是指语文教材中文本所表现的具体内容;而教学内容指依据课程标准、教材体例、文本体式、学生学情等情况,在课堂教学中,对文本内容根据教学需要而选择和确定出来的教学内容。
叶圣陶认为:“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而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然而,目前许多老师仍然是“教教材”而不是“用教材教”,即只停留在“领会教材意图、处理教材内容”的表层上,不能根据“教”和“学”的实际调整教材,简言之就是“活用教材”。
如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1第一单元,主要是现代新诗《沁园春》《雨巷》《再别康桥》《大堰河——我的保姆》,单元目标要求在反复朗读的基础上鉴赏诗歌,着重分析意象,同时品味语言,发挥想象,感受充溢于作品的真情。但是教学过程中,部分老师要么纠缠背景,探讨写作缘由;要么过分强调具体事物的象征意义;要么过分强调朗诵。对语言和写作方法却视而不见,只有文本内容的解读,没有语言品味,没有写法学习,这就是典型的“教教材”,即以“课文内容”代替“教学内容”的学习。
(三)内容解读有“异化”趋势
李海林老师说:“文学教学的目的在于通过文学作品的教学,引导人们超越与现实之间的功利关系而建立起自己与现实之间的自由关系。”但有些老师在教学中却往往忽略这方面的规律,盲目求新、求奇、求异,导致在语文教学内容解读方面出现“异化”。
如部编版初中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第17课,郑振铎《猫》,以某老师的教学设计为例,在教授这篇课文时,老师让重点品读15——34 段,完成下列问题(芙蓉鸟事件)
案发现场
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可能性
(1)案发前的表现
(2)案发后的表现
法官断案过程
第一法官(我)第二法官(妻子)
对犯罪嫌疑人的惩罚方式
事实真相
案件定性
案件反思
在这个冤案中,“我”错在哪里?你从这个事件中,得到什么启示(教训)?
下课后,老师赞扬同学A、同学B、同学C 办案神速准确,有侦破天才,将来可以做一名出色的侦探。该堂课好看,热闹,形式新颖,但语文教学内容的关注已经和语文无关了。
再如部编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13课,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大肆讨论“父亲闯红灯”是不是违反了交通规则;诗经《氓》教育学生如何识别与对待渣男;吴敬梓的《范进中举》,教育学生要学习范进“屡考屡败,仍不坠青云之志”的奋发精神。
陕西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曹公奇先生说:“目前,许多语文教师并没有意识到教学内容选定的重要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着随意性、盲目性,教学没有考虑语文课程的特殊性,没有对整体学段的考虑,没有对年级层次的考虑,没有对单元教学的考虑,没有对文本特殊性的考虑,没有对学情的考虑,想起什么教什么,教到哪里是哪里,特别是语文教学还容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把什么内容都想纳入语文教学的内容,语文赋予了它本身以外的许多内容,结果学生语文素养得不到提升,致使语文教学效率不高,备受社会各界诟病。”
二、语文教学内容选定的策略
语文教学内容选定的策略,是指在进行语文教学内容选定时必须遵循的几个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方法,而不是全部的、特殊的、“投机取巧”的方法。
(一)根据课程特性和《语文课程标准》选定教学内容
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说:“语文作为一门具体的课程,它在中小学设置的目的是什么?它自身的任务是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学生进行本民族语言的教育;具体说些,就是通过读、写、听、说的训练,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
另外,《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语文教学的纲要,是我们一切的教学活动都必须遵循的“标准”。《语文课程标准》关于学习语言文字运用这个核心目标也一直很突出,这是我们选定教学内容的一个策略。
比如部编版初中语文九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第5课,鲁迅《孔乙己》,教学时分析孔乙己的人物形象,只是根据大致的情节,笼统地、概念化的概括人物性格特点,不能抓住人物描写的关键词句(如对孔乙己的四次嘲笑,尤其是对手的动作的刻画)来品析人物形象,也不能抓住人物自身独特的语言、外貌、神态(如孔乙己“你怎么能凭空污人清白”、“脸上黑而且瘦……”)去细细品味琢磨,就不能品味出人物形象的复杂特点,只仅仅介绍了概念化的术语。
再者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3)第四单元的一篇乐普说明文,学习周立明的《动物游戏之谜》,如果一心探讨动物游戏原因的几种假说,并就此展开讨论、争论,完全不顾作为一篇科普文应该引导学生从中学些什么,这就忽略了课标对科普文的教学要求。因此,《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科学与文化论著研习,本任务群研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论文、著作,旨在引导学生体会和把握科学与文化论著表达的特点,提高阅读、理解科学与文化论著的能力,开阔视野,培养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其它文本的教学也是如此。
所以说,根据语文课程的特性和《语文课程标准》立足于语文课程的根本,以品味语言、学习语言为核心,选定语文教学内容,教学就不会出现偏颇,就不会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历史课、生物课等等。
(二)依据文体特征选定教学内容
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宜宣雅,书论宣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对文体发表的最早议论。《人民教育》2013年第6期专设了“关注语文教学文体意识”的话题,“编者按”提出“自觉的文体意识不是单纯的具备某种文体知识,它是一种综合性语文素养。文体意识的培养不仅要清楚某种问题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语文实践中体验、感悟、理解等语文素养相互链接、交叉、渗透,这样形成的文体意识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阅读、写作和表达交际。”这里从语文素养的高度提出了文体应在学生语文素养积累过程中发挥应用的价值。
文体有不同的分类,根据目前中学语文部编版教材和人教版教材中课文的实际情况,对文体进行分类:一是“文学文体”,包括童话、寓言、神话、诗歌(儿童诗、古诗)、文言文、散文、小说等;二是“实用文”文体,包括说明文、记叙文、议论文等。不同的文体特征决定了教学内容选定的不同。
比如学习散文,即使同一种文体的散文也要区别对待,而不是简单的“形散而神不散”。孙绍振先生通过散文发展史的梳理,将散文分成了三类,即:审美的抒情性散文——偏于诗化、美化的审美抒情,遵循的是抒情逻辑;审丑的幽默散文——偏于对并不美好的事情、荒诞情感的抒写,遵循的是幽默逻辑;审智的学者散文——偏于智性观念的表达,遵循的是理性逻辑。教学人教版九年级下册王鼎钧的《那书》,首先要明确《那书》属于审智性散文,明确文体特征后再进行教学内容的选定。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是审美的抒情性散文,就要以通过景物描写来分析文本所表现的情感为主要教学内容;而巴金的《小狗包弟》虽然也是审美的抒情性散文,但教学内容的选定应以文本记叙的事件来理解作者的情感变化为主。
再如学习演讲词,首先要学习演讲词的文体特征,其次是会用这些特征,即会演讲或者写作。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2第四单元主要是演讲词《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在马克思目前的讲话》,学习这类文章,类容的选定应放在注意体会演讲词的情感力量和多样化的表现手法,揣摩其中的感情、语气和表达技巧,再者可以渗透文章的主旨,理清文章的结构等等。
王荣生教授说:“什么是合适的文本解读呢?即符合下面两个要求:一是这种特定体式的文本,阅读取向要‘常态’。二是在特定的文本体式中,要运用符合这种体式的阅读方法。”从小学到高中的教材所选课文众多,而且文体多样,题材广泛。不同文体,不同类别的文章,在组织形式和表达方式上等各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应根据课文的文体、类别选定不同的教学内容,要让文体意识成为一种语文素养在课堂上、在学生中渗透和生成。
(三)根据学生学情选定教学内容
王荣生教授说:“学情的分析,如果不具体到每篇课文学生所具有的学习经验、他们已经懂了什么、已经能读出什么、他们还有哪些不懂、还有哪些读不好、感受不到,实际上等于没有做过。”此处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哪些是学生不喜欢的,是学生读不懂的,是学生读不好的,并据此选定教学内容。
通常情况下,我们探讨的学情是广义的学情,包括学生年龄特点,学生已有知识经验,学习能力和学习风格等等。学生的学情集中暴露在学生原有基础和现有困难所形成的矛盾冲突的问题当中。本文这里所探讨的学情仅针对语文课堂教学方面的学情,是学生在一堂语文课上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学情,不是学生所有的背景状况。因此,学情应该具体化到教学要点,具体化到解读一篇文章的个人化的言说对象、个性化的情感表达、个性化的语句章法表露出来的问题。
例如部编版教材初中语文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第8课,学习《木兰诗》,木兰从军的故事千百年来广为传颂,多次被改编为戏曲、电影等艺术形式。该篇课文的预习提示要求:从木兰的英雄气概和女儿情怀去把握木兰这一人物形象?学生初读课文后,对花木兰最直接的印象是:替父从军的英雄。木兰的“英雄气概”感受到了,那“女儿情怀”呢?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教学时可以提出如下问题:其一,这首诗里面写打仗的一共有几句?(1句“将军百战死”)其二,写女孩为父亲担心,决心出征(16句“唧唧复唧唧……从此替爷征”),备马(4句“东市买骏马……”),对爹娘的思念又是八句(“旦辞爷娘去……”),奏凯归来后,作者写家庭的欢乐,用了6句,写木兰换衣服化妆又是6句(“爷娘闻女来”……)。此时,老师可以蓄势发问:“如果作者的知识写木兰的英雄气概,这样的文章安排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了?再随着发问,一个“女儿情态的木兰”英雄形象就跃然于纸上了。两外“英雄”是一个非常空洞的概念,如何“去弊”呢,去掉一般化的、现成的、“空洞”的英雄概念,像剥笋壳一样,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是花木兰这个女英雄呢?这些问题是文本可能产生的难点、疑点,也是学生的兴趣点,把握住这些,也就掌握了学生的学情。
依据学生的学情选择教学内容才能真正做到将课程专家提供的“一般教什么”转化为“实际需要教什么”。关注与学生实际的契合,这才是语文教学内容的本来含义。
(四)根据助学材料选定教学内容
王荣生教授认为:“助读和练习实际上起着对一项知识,尤其是对一篇文章所要教学内容的固定作用,或者说,它们是对课程内容的具体展示。在具体的教学中,一篇文章教什么乃至怎么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助读和练习的编排。”
“助学材料”又称为助读材料或导读材料。顾之川先生认为助读材料包括“单元提示”、“注释”、“研讨于练习”、“补白”、“教师教学用书”等,是教科书编者为适应实际教学需要而设计的,这也是语文教科书与一般文学作品集不同的地方。这些助学材料已经熔铸了编写者对文本核心价值的认识和教学元素的删选,教材编写者依据《课程标准》,兼顾到教材的整体体例,考虑到文本体式和学情,以此来确定文本应该承载的教学的核心价值,然后把这些价值在教材的助学材料里分别呈现,通俗来讲,就是“为什么要学习这篇文章?为什么要在这个教学位置学习它?要凭借它学习哪些知识技能?甚至于,可以用哪些方式去学习这些技能?学习这篇文章与前后文章有何联系”?所有这些,教材编写者都通过助学材料进行了明确表达。也就是说,作为整套教材中的一片具体课文,教师不能就“文本有什么就教什么”,而是应该研究助学材料,把握编者意图。
如部编版初中语文九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一课,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课,课前预习提示“默读诗歌,了解诗歌的内容,再大声朗读,体会诗歌的韵律和节奏”;课后的思考探究“把握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分析诗人的情感脉络,对重点诗句含义的品析”;课后的积累扩展和读读写写集附录选文。这些助学材料有助于老师把握该篇诗歌教学内容的选定,不至于偏离,重复。再如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2)第三单元第8课,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课后就链接了《晋书·王羲之传》。历来,学生对王羲之了解最多的就是他的书法,那么编者给这个链接是不是有其它的意向?因此,根据此链接,可以要求学有余力的学生把它们译成现代汉语,了解王羲之的奇闻轶事。
语文教学内容的选定在某种意义上比教学方法更重要,语文老师在面对文本进行教学内容的选定时:首先要把握语文课程的特性和《语文课程标准》;其次要有文体意识,了解不同文体阅读与鉴赏的一般规律;再次关注学情,了解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确定教学内容;最后利用好助学材料,在助学材料中具体而精准的确定这一篇的教学内容。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选定准确无误,才能选用适宜的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活动,才能让学生多经历、体验各类启示性、陶冶性的语文学习活动,逐渐实现多方面要素的综合与内化,养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品质、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