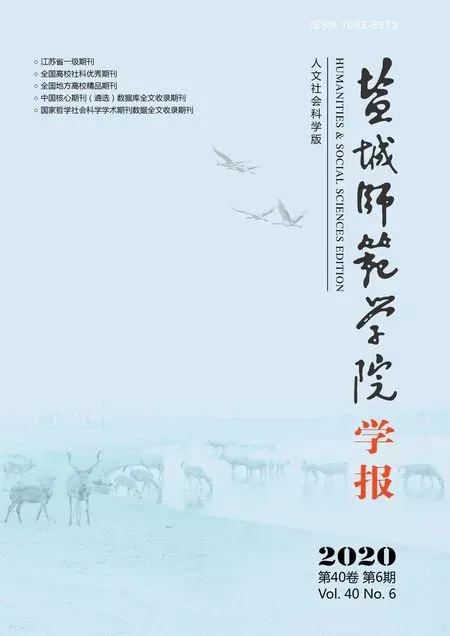《樱桃园》的季节叙事及其美学意蕴
2020-02-22宗世龙蒋小平
宗世龙,蒋小平
(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樱桃园》[1]是俄国剧作家契诃夫剧作风格转型后的重要作品之一,在世界戏剧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书中,俄国社会变革期间的落魄贵族拉涅夫斯卡娅,严重缺失生活能力,终日游手好闲,耗尽家财后又欠下大笔贷款,在儿子溺水后毅然前往法国。拉涅夫斯卡娅在初春从法国回到家中后,面临着樱桃园被拍卖的窘境。但是兄妹二人无法保住樱桃园的所有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祖产被新兴阶级代表——罗伯兴——买下,最终在冬日无奈离开樱桃园。该剧作蕴含着喜剧与悲剧因素,呈现出悲喜交加、以喜衬悲的特点,具有典型的俄国现实主义戏剧风格。在这部作品中,剧作家设置了“春、夏、秋、冬”四季分别与每一幕对应,形成了特定的季节叙事。本文拟从季节叙事这一视角出发,探析契诃夫笔下季节叙事在剧本创作中的独特意义与美学意蕴。
一、戏剧“时间叙事”的内涵
在我国学术界,季节叙事常被用来解读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早在战国时期便有文献记载“以闰月定四时成岁”[2],此句中的“四时”即为“四季”的概念。季节的自然规律为“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四季的更替代表着时间的流转。季节叙事的本质是时间叙事。
戏剧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艺术,其最主要的特点为“在场性”,即演员在剧场中面对面将戏剧故事表演给观众,这就形成了与其他叙事艺术的不同的时间特征,戏剧的时间表现为“故事时间、剧情时间与观演时间”三项:故事时间指的是“隐藏在剧情背后按照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先后顺序所排列出来的时间”[3],即剧作家在文本中设置的具体时间;剧情时间是指在戏剧表演中呈现的时间,由于导演对剧本的二度创作,使得舞台表演中不一定按照故事时间进行;观演时间即为表演和观看的现实时间,也可理解为观众进入剧场欣赏演出的时间。
戏剧作品中“时间”概念,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理论著作《诗学》。亚里士多德在定义悲剧时提到,悲剧是“对一个完整划一,且具一定时间长度的行动的模仿”[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戏剧的本质在于模仿,而模仿的内容则是在呈线性发展的特定时间范围中的人物行动,这一戏剧原则一直影响着戏剧创作。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学批评家卡斯特尔维特罗、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法国戏剧理论家波瓦洛为代表的戏剧家们,也大多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思想,并在其基础上加以强化,提出了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戏剧“三一律”原则。波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有以下论述:
“剧情发生的地点也需要固定、说清。比里牛斯山那边诗匠能随随便便,一天演完的戏里可以包括许多年:在粗糙的戏曲里时常有剧中英雄,开场是黄口小儿终场是白发老翁。但是我们,对理性要服从它的规范,我们要求艺术地布置着剧情发展;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结尾维持着舞台充实。”[5]
即戏剧事件应发生在一个昼夜、一个地点且人物具有贯穿于始末的戏剧行动,这就严格限定了戏剧时间的范围。这一戏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对戏剧创作起到了规范作用,但是由于对规则的过分强调,“三一律”逐渐走向僵硬化与教条化。直到启蒙主义时期与浪漫主义时期,“三一律”原则才有所松动。
法国戏剧家狄德罗认为:“艺术中的美和哲学中的真理有着共同的基础。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判断符合事物的实际。模仿的美是什么?就是形象与实体相吻合。”[6]即要求戏剧作品应该呈现出真实的社会环境,客观地再现现实社会,打破“三一律”严格的枷锁,无论戏剧空间与时间,都可以按照现实发生的原则进行设置,应建立一种自然与真实兼备的“舞台幻觉”,使观众沉浸到剧作家建构的戏剧情境中。至此,戏剧作品中的“时间”设置才脱离了僵化规则的束缚,成为服务于戏剧内容,且与之相辅相成的戏剧元素。
“后戏剧剧场理论”由德国戏剧家汉斯·蒂斯·雷曼在上世纪末提出,是一种对以“文学”为中心的传统戏剧剧场反叛的理论,它在戏剧时间方面进行了大胆的突破。雷曼认为,在后戏剧剧场中“剧场所围绕的不再是一个(阅读)主体的时间,而是很多主体的共同时间(他们集体度过的一段时间)。因此,时间经验变成了一种身体、感官真实,一种精神真实”[7]。这一观点在本质上是消解了“文学”在戏剧中的作用,将戏剧时间中的故事时间与剧情时间的地位降低,让观众走入剧场便进入了一个属于剧场的“梦幻时间”,并与观众的现实时间隔绝,使观众与演员形成一种共时性的舞台行为。
通过梳理西方戏剧史上“时间”概念的理论脉络可看出,“时间”概念呈现出由闭锁至开放、从概念表层到理论深层的转变。在国内戏剧界,以谭霈生等为代表的学者也对戏剧时间叙事做出了理论解读。谭霈生在《论戏剧性》中指出:“自由处理时间、空间,不仅有助于深刻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对于剧本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对于展现复杂的情节线索,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然,剧作家处理时间、空间的自由,总是要以动作的统一性为限度。”[8]谭霈生认可了戏剧时间在戏剧文本的地位,合理化的戏剧时间设置对戏剧人物行动发展戏剧情节的真实性、现实性具有重要影响。胡志毅在《时间和空间:戏剧的原型结构》一文中提出,戏剧的原型结构也体现在时间结构中,“从戏剧本体来说,戏剧不可能完全是在现实时间中进行的,即使是压缩到一昼夜,因为戏剧的演出时间一般都在三个小时左右。因此从时间意义上说,戏剧是浓缩了的人生”[9]。可见“故事时间、剧情时间与观演时间”在戏剧本体意义上的高度融合。
笔者经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对契诃夫戏剧的研究多集中在创作风格、悲喜剧因素的融合以及演剧方面,对契诃夫剧作中的时间叙事,尤其是季节叙事的研究十分缺乏,因此,笔者认为,以这一视角探析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樱桃园》的季节叙事
解读季节叙事手法,实质上是围绕着剧本中的“故事时间”展开。在《樱桃园》这部作品中,“故事时间”为当年的五月至十月,按照四幕划分依次为:第一幕,五月份拉涅夫斯卡娅归来之日;第二幕,介于五月到八月中夏季的某一天;第三幕,樱桃园被拍卖的八月二十二日当天;第四幕,十月份拉涅夫斯卡娅等人再次离开樱桃园之日。根据俄国四季的划分标准与国际惯行标准,可以将四幕的故事时间分别对应为春、夏、秋、冬四季,笔者拟从戏剧文本中的故事时间,即四季的转换展开解读。
(一)春季叙事:新的开始
《樱桃园》第一幕的舞台提示“已是五月,樱桃花开了”,透露出第一幕的故事时间为春季。“春天”是世间万物生长的季节,是一年的开始,是四季的开端,它象征着美好期待的开始,因此契诃夫在这一幕中设置了两处有关“新的开始”的戏剧情节。
第一,拉涅夫斯卡娅在初春重回樱桃园。拉涅夫斯卡娅在法国生活数年后,选择再回到樱桃园,仅出于一个心理动机,这一动机可在拉涅夫斯卡娅的女儿安尼雅与瓦里雅的对话中看出,“妈妈把在法国蒙当的一处别墅卖了。她已经一无所有。我也两手空空,好不容易回到了家”。拉涅夫斯卡娅是由于在法国难以度日,从而选择重回樱桃园。然而阔别六年的樱桃园已经不是以前繁盛的俄国庄园,而是负债累累的破落庄园,但是拉涅夫斯卡娅并不将此放在心上,在她心中只要回到养育自己的庄园,便可以获得心灵上的归属。在契诃夫笔下,拉涅夫斯卡娅重回樱桃园成为解救她自己的必然选择,不论如今的樱桃园是何等破落,但重回樱桃园仍是拉涅夫斯卡娅得以摆脱法国不堪过往的“新春天”。
第二,以罗伯兴为代表的新兴阶级的“春天”。罗伯兴是俄国时代转型期的先行者,他祖辈是樱桃园的底层农民,但是他现在摆脱了世代为农的身份,脱下破旧的衣服,“身穿白色坎肩,脚蹬黄色皮鞋”,如愿成为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拥有先进的资本思想,有着如何赚取更多金钱的奇思妙想,这一人物象征着俄国社会正发生着急剧的变革,落后、腐化的俄国即将迎来“新春天”。虽时隔多年,但罗伯兴并没有忘记自己儿时得到过拉涅夫斯卡娅的帮助,对她有着无限的爱恋与感激,他在此的等待仅有一个目的,即告知拉涅夫斯卡娅可以出租樱桃园的地产,以此获得大量的金钱,摆脱生活的困境。在契诃夫笔下,罗伯兴成为解救拉涅夫斯卡娅于危难的关键人物,也象征着樱桃园可以重获生命的“新春天”。
契诃夫的剧作具有“喜剧与悲剧相融合”的特点,他擅长以充满戏谑的文字书写平凡生活中的悲剧性。在文本中契诃夫奠定了悲剧的伏笔,在第一幕伊始,“虽已五月,花园里还有点冷,是春天早晨的寒意。房间窗子都紧闭着”,交代出这一年的春天不同以往,虽然拉涅夫斯卡娅与罗伯兴即将拥抱各自的“新春天”,但是带有寒意的春天预示着整部作品“悲伤”的情感基调。
(二)夏季叙事:无动于衷
笔者依据三处剧本信息判定第二幕发生于夏季:一是在第二幕中拉涅夫斯卡娅与罗伯兴的对话中的“让我再提醒你们一句,八月二十二,樱桃园可就要拍卖了”,可以判定这一幕的时间在五月到八月二十二号之间;二是第二幕的舞台提示“一边,耸立着一片暗黑的杨树”,通过对杨树描写的形容词“暗黑”,可进一步判断此幕应发生在夏季;三是通过第二幕中女仆雅沙的语言“朝家里那边走,装作刚刚在河里洗完澡的样子”,最终判定这一幕的季节应为夏季。夏天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季节,同时夏季炎热的天气让人难以忍受,影响着人的情绪。在这一幕中,剧作家运用反讽的写作手法,以充满生命气象的夏季,反讽樱桃园中正堕落的生命群像。
拉涅夫斯卡娅与加耶夫兄妹是俄国传统社会的贵族子弟,他们虽然如“野鸭”般深陷泥沼但又毫不自知,同时也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与勇气。在第二幕中剧作家设置了罗伯兴再次建议拉涅夫斯卡娅出租樱桃园地皮的戏剧情节,这一次是樱桃园被拍卖前罗伯兴的最后一次建议。通过罗伯兴的语言即可知晓,“得做出最后的决断了——时间不等人。问题其实很简单。同不同意把土地交出去盖别墅?你们只需要回答一个字:是或否?只需一个字?”可见罗伯兴经历了之前数次建议,得不到任何反馈的焦急、烦闷的心态,但是这一次拉涅夫斯卡娅与加耶夫兄妹装作听不到,自说自话“谁在这里抽讨厌的雪茄烟?”“瞧,铁路建成了,这方便多了。坐火车进城,吃过早饭,黄球打进中间的网兜!我想进屋去玩一局台球。”拉涅夫斯卡娅与加耶夫二人完全将罗伯兴放在一边,不去听、不去回应,只做着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无聊的事,甚至不愿亲身去打一场台球,只在脑子里幻想着打球的场景与球在台面的走向。“贵族”的习性使得拉涅夫斯卡娅兄妹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即使是在罗伯兴的不断催促下,二人仍如同枯木一般活着,不去思考、不去行动,任由时间流逝,任由樱桃园被拍卖。在罗伯兴说到有富翁买下樱桃园时,拉涅夫斯卡娅与加耶夫兄妹才和罗伯兴形成了短暂的交流,但是兄妹二人的反应仍是微弱的,为了维护樱桃园的尊严与自身贵族的脸面,他们不肯听从罗伯兴的建议,而是选择向远方的婶母借钱度日。最终,罗伯兴发出“我要么嚎啕大哭,要么大声嚎叫,要么昏倒在地。我受不了啦!”的呼号。然而,拉涅夫斯卡娅与加耶夫中断了与罗伯兴的交流,再次回到自己无聊的精神世界,开始自说自话与自我感动。
罗伯兴再次建议拉涅夫斯卡娅兄妹出租樱桃园地皮是第二幕的主情境。罗伯兴这一形象象征着似火的夏日,不断催促着拉涅夫斯卡娅兄妹做出决定,但是对已经丧失思考与行动能力的兄妹而言,他们的眼睛看不到活生生的罗伯兴,耳朵听不到任何有用的话。剧作家以反讽的手法描绘着在这旺盛的夏季,罗伯兴点起樱桃园希望的火焰,但是被它的主人无情地扑灭,讽刺着以拉涅夫斯卡娅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的贵族们无力认清转型中的俄国社会,深陷泥沼而不自知,只能一直把头往水里钻,直到失去一切,而俄国的未来只属于罗伯兴们。
(三)秋季叙事:失去庄园
根据《樱桃园》第一幕中罗伯兴的台词“你们已经知道,你们的樱桃园将要抵债出售,拍卖会定在八月二十二日”、第二幕中拉涅夫斯卡娅与罗伯兴的对话中“让我再提醒你们一句,八月二十二,樱桃园可就要拍卖了”,可以推断出第三幕的故事时间为当年的八月二十二日,依据俄国旧历(俄国旧历于1918年废止)与新历的关系,19世纪俄国旧历日期比新历日期早十二天,将樱桃园拍卖时间换算为新历日期应为九月二日,这在现行俄罗斯季节划分中属于秋季。秋季象征着衰败,衰败意味着失去,拉涅夫斯卡娅等人的命运也在萧瑟的秋季发生了转折。
在第三幕中,樱桃园中举办着交际舞会,但是拉涅夫斯卡娅却无心于关注舞会,“列奥尼德怎么还不回来?他在城里干了些什么?”“列奥尼德还没回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在城里耽搁那么久!要么庄园已经卖掉,要么拍卖会没有举行,现在早已有了结果,为什么老让我悬着这颗心!”通过拉涅夫斯卡娅的戏剧语言,可以清晰地看出她在焦急地等待加耶夫拍下樱桃园的消息,内心的不安使得她难以沉下心来,心中担心樱桃园被别人买走,害怕失去祖辈发家的庄园。随着罗伯兴与加耶夫回到樱桃园中,加耶夫将罗伯兴买下樱桃园的消息告知拉涅夫斯卡娅后,剧作家通过两个舞台提示交代出拉涅夫斯卡娅情绪的彻底崩溃,“柳苞芙·安德列耶芙娜(即拉涅夫斯卡娅)十分沮丧;如果她不是背靠桌椅站着,她会跌倒在地上。”“柳苞芙·安德列耶芙娜瘫倒在椅子上,伤心地哭泣。”这时的拉涅夫斯卡娅才意识到是自己将祖产拱手让人,自己与樱桃园的缘分也不得不就此终结。
在文学作品中,凡提到“秋”大多有萧瑟、悲凉之意,中国自古有“伤春悲秋”的说法,在汉代的《古歌》中亦有“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一句,可见“秋”的文学意象多代表烦愁、悲凉、别离。在《樱桃园》中,“秋”是拉涅夫斯卡娅失去樱桃园的季节。在这一幕中,拉涅夫斯卡娅面对着即将失去庄园的关键情境,在前两幕中被拉涅夫斯卡娅忽视、贬低的罗伯兴最终将樱桃园买下,将成为这古老庄园的新主人。这对拉涅夫斯卡娅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她无法想到以前家中的贫贱农民的儿子,现在竟然成为了樱桃园的新主人,而且他扬言将要对樱桃园进行翻天覆地般的整治,在樱桃树的遗迹上兴建一栋栋旅行别墅。所以,在这让人感伤的秋季,拉涅夫斯卡娅失去樱桃园的同时,这座古老的庄园也将失去自身的庄园特色,成为与其他地皮没有区别的赚钱工具。
(四)冬季叙事:被迫离开
第四幕的戏剧情节围绕着拉涅夫斯卡娅再次离开樱桃园展开。根据《樱桃园》第四幕中罗伯兴的语言,可知这一幕的故事时间为十月,是俄国的初冬。在这一幕中“冬”具有两重象征,一是表现拉涅夫斯卡娅的心灰意冷,二是暗示罗伯兴的春天不再遥远。
一方面,“冬季”象征着拉涅夫斯卡娅的心灰意冷。虽然罗伯兴多次建议拉涅夫斯卡娅将樱桃园的地皮出租以此换来金钱,但是拉涅夫斯卡娅选择了与之背离的做法,一再忽视罗伯兴的建议,出于无奈只能试图向姨母借钱买下樱桃园,然而这根本无法与新兴阶级相抗衡,拉涅夫斯卡娅毫无意外地失去了樱桃园的所有权。从第一幕中拉涅夫斯卡娅重回樱桃园,但是仅仅过了五个月她又要面临不得不离开樱桃园的窘境。“再见了,亲爱的房子,年老的爷爷。冬去春来,你就不复存在,他们会把你拆散了架子。这些墙壁见到过多少人世沧桑呵!”“我再坐一分钟。这间屋里的墙壁、天花板,好像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似的,而现在我要带着一份温情如饥似渴地看着他们。”拉涅夫斯卡娅不得不向自幼生长的樱桃园告别,这时的拉涅夫斯卡娅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贵族神气,在屋子里不断回忆、不愿离去。在加耶夫、安尼雅等人的催促下,拉涅夫斯卡娅给这座古老的庄园留下最后一句话:“我们走!”在此,剧作家再次运用了象征的手法,以拉涅夫斯卡娅回答加耶夫等人的催促,暗示这些人再也无法回到樱桃园的悲惨现实。
另一方面,“冬季”暗示着罗伯兴的春天不再遥远。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罗伯兴成为了樱桃园的新主人,内心的雀跃与激动使他感叹“已经是十月份了,太阳还是这样暖和,像夏天一样”、“去年这个时候已经下了雪,如果您还记得的话,而现在呢,太阳静静地照着”。可见客观环境的寒冷敌不过罗伯兴心中燃烧的火焰。作为祖上世代为农的子孙,罗伯兴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这一片樱桃园,成为这一片庄园的新主人,实现了阶层跨越。樱桃园兴建旅游别墅,是俄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这个时代属于罗伯兴这一类人。
契诃夫笔下的“冬季”,蕴含着最深切的悲痛与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剧作家通过对“冬”的叙述,描绘出新旧阶级各自的未来发展方向。以拉涅夫斯卡娅为代表的俄国旧贵族难以意识到自身危险境地,只能在危险爆发后顾影自怜,又无力改变。而以罗伯兴为代表的俄国新兴资产阶级,将跨越令旧地主阶级崩溃的寒冬,迎来属于他们的新时代。
三、季节叙事的美学意蕴
(一)人物情感的外化
契诃夫在创作中“有意淡化作品的故事情节及外部冲突,着力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主观感受,并且大量地使用所谓‘无声的语言’,因而使其剧作显得含蓄、深沉、耐人寻味,具有了诗一般深邃意境”[10]。契诃夫运用季节叙事的手法将人物情感与季节特征结合起来,通过季节的流转揭示戏剧人物的情感脉络走向。
在樱桃花开的初春,拉涅夫斯卡娅回到樱桃园,“我果真坐在家里?我想伸开胳膊跳起来。不会是在做梦!”可以感受她内心的愉悦的情感状态。在万物萧瑟的秋季,当得知樱桃园被罗伯兴买走后,“柳苞芙·安德列耶芙娜十分沮丧;如果她不是背靠桌椅站着,她会跌倒在地上”。“柳苞芙·安德列耶芙娜瘫倒在椅子上,伤心地哭泣。”剧作家通过这两处人物行动的描写,交代出拉涅夫斯卡娅的极度痛苦,她的凄惨与无助得到极致地展现。在这感伤的秋季,拉涅夫斯卡娅失去了她的庄园,不得不面临再次出走法国的现实。剧作家通过对季节的内涵处理,表现出戏剧人物当时当地的心理状态。相似的手法在《樱桃园》中比比皆是。黑格尔认为:“在戏剧里,具体的心情总是发展成为动机与推动力。”[11]在契诃夫笔下,“春、夏、秋、冬”成为戏剧人物情感得以外化呈现的重要象征,戏剧人物情感的丰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戏剧情节的发展。
(二)冷热笔法的运用
季节叙事的本质并非是机械化地遵循固定的四季循环,而是深入把握季节更替的自然规律,将人世冷暖、世事盛衰寄于其间。中国人常将“寒暑易变”隐喻人间的冷暖无常,而将冷热笔法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更是常见的手法,这同样适用于解读契诃夫的戏剧作品。
在《樱桃园》中有着较为明显的冷热隐喻,如春冬隐喻与夏秋隐喻。《樱桃园》中春冬隐喻为第一幕与第四幕的对比,满怀期待的回来与灰头丧气的离开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一次的离开意味着拉涅夫斯卡娅再也无法回到心爱的樱桃园,而樱桃园也将不复存在。剧作中的夏秋隐喻为第二幕与第三幕,第二幕中为夏季,暗黑色的杨树后的樱桃园正经历着最后的搏斗。罗伯兴竭尽全力的劝导与拉涅夫斯卡娅兄妹的无聊生活在第二幕都发展到极致,罗伯兴如火般的热情得不到兄妹二人的回应。直到第三幕,在俄国的早秋,拉涅夫斯卡娅兄妹失去了祖辈生活的樱桃庄园。夏的热烈与秋的萧条同构成一出“先热后冷”的戏剧情境,亦形成热辣的讽刺。
(三)戏剧结构的构建
“明确的时序往往成为建构故事的基础。”[12]契诃夫的创作往往按照明确的“时序”安排每一幕,这一“时序”的原则是通过剧作家的安排进行交代的,使得观众可以清晰地辨明具体的时间及空间转换。戏剧作品创作讲究开端、发展、高潮与结局,契诃夫通过季节的转换交代时序的变化,借助特定的时间构建情节结构,从而推动情节发展。《樱桃园》中,在春季,拉涅夫斯卡娅与加耶夫一行人返回即将拍卖的樱桃园,想要开启一段新生活,罗伯兴首次提醒她为樱桃园的未来做打算;夏季,拉涅夫斯卡娅无意解救樱桃园,忽视罗伯兴的建议,继续过着贵族般的生活;秋季,拉涅夫斯卡娅在焦急的等待中得知樱桃园被罗伯兴买走的消息,这使拉涅夫斯卡娅陷入崩溃;冬季,罗伯兴激动地开展赚钱项目,而拉涅夫斯卡娅不得不离开祖辈居住的樱桃园去往法国。“春、夏、秋、冬”的变化意味着以拉涅夫斯卡娅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悲剧命运,同时蕴含着罗伯兴等新兴阶层的不断前进。在四季的叙事中可以看出契诃夫在戏剧结构上的巧思,即通过季节叙事为整部作品的戏剧情节提供明确的时间线索,进而构建出完整且具戏剧性的戏剧结构。
(四)抒情功能的展现
“季节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刻度,而是既积淀着不同个体的生命感悟,又蕴含着民族精神传统的文化符号。”[13]对生命个体而言,某一季节的记忆往往伴随着特定的事件。对拉涅夫斯卡娅而言,“春季”与“冬季”是她记忆最深刻的季节。在剧本第一幕中,拉涅夫斯卡娅一行人经过半个多月方才抵达家乡——樱桃园,时间为五月份,是俄国的初春。拉涅夫斯卡娅历经辛苦回到樱桃园后,只想忘记不堪的过往,在自己的樱桃园中安享接下来的美好时光。契诃夫通过拉涅夫斯卡娅的台词尽情展现出她回到家乡的激动、愉悦。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第四幕,拉涅夫斯卡娅面对失去樱桃园的事实,坐在屋子里久久不离开。在此处契诃夫运用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技法,将时间的紧迫——离火车发车仅有几十分钟——与拉涅夫斯卡娅一直抒发对樱桃园的不舍结合起来,加耶夫等人的催促与拉涅夫斯卡娅的感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且动人的戏剧效果。最能代表拉涅夫斯卡娅不舍的台词为“我再坐一分钟。这间屋里的墙壁、天花板,好像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似的,而现在我要带着一份温情如饥似渴地看着他们”。拉涅夫斯卡娅在与时间赛跑,以“再看一眼”的方式表达着对樱桃园的爱。拉涅夫斯卡娅从“春天”走来,又从“冬天”离开,从对新生活的美好期待到被现实狠狠地打击,这体现着剧作者对以拉涅夫斯卡娅为代表的俄国旧贵族阶级的冷静审视。春日的归来与冬日的离去两相并置,形成对比,渲染出一种荒芜、萧瑟的悲凉气氛,契诃夫剧作中深邃的诗意风格也由此可见。
(五)舞台美术的设置
戏剧空间与时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即“戏剧所要讲述的故事或者所要表现的某个情节都是通过一定的空间来呈现的”[14]。戏剧作为表演性艺术,剧作家在创作剧本时势必会考虑舞台演出的情况。剧作家在舞台提示中涉及特定的场景与环境,是将剧本搬演于舞台的重要舞台美术提示。在《樱桃园》这部剧作中,剧作家按照“春、夏、秋、冬”四季的顺序进行情节设置,故而舞台美术亦要遵循剧本按照不同季节的特征进行设计。就整部作品而言,最重要的是需要将“樱桃园”的场景呈现出来。我国戏剧理论家刘杏林认为:“‘樱桃园’一直是这一剧作中的关键形象,把它作为大自然景色的一部分呈现出来。”[15]所以,有关樱桃园环境的舞台设置至关重要,不但需要交代清楚樱桃园的关键要素,还要符合契诃夫提出的季节变换的要求。每一幕的舞台提示都交代了在特定季节中舞台美术的主要特征:春季时,“已是五月,樱桃花开了。但花园里还有点冷,是春天早晨的寒意”。夏季时,“耸立着一片暗黑的杨树;后边就是樱桃园”。秋季时,“一间客厅,由拱门与大厅隔开。枝形烛台上的蜡烛燃烧着”。冬季时,“窗上没有了窗帘,墙上没有了画幅,所剩无几的家具堆放在一个角落里”。剧作家在作品中通过“春、夏、秋、冬”的转换,赋予了每一幕独特的舞台美术效果,只有切实按照剧作家文本中的要求设置,舞台才能发挥出切合剧情的艺术效果。由此可以看出,剧作家设置的“季节”元素亦可为舞台美术设置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四、结语
戏剧是一门融文学、表演、导演、舞台美术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在现实主义作品中,戏剧文本是演员表演的蓝本,在戏剧创作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指导着表演、导演、舞台美术等环节,所以深入研究戏剧文本具有重要意义。契诃夫在剧本创作中多注重使用意象,“季节”便是其作品中常用到的意象之一。契诃夫将“季节”意象升华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方法,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与丰富的思想内涵。季节叙事作为时间叙事的一种形式,强调四季流转、自然更替,这无疑将人类生命与自然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透露出契诃夫对四季循环更替、人生却世事无常的无奈,展现出剧作家对世间变换的客观审视,同时这一叙事手法也极大促进了契诃夫剧作深邃诗意风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