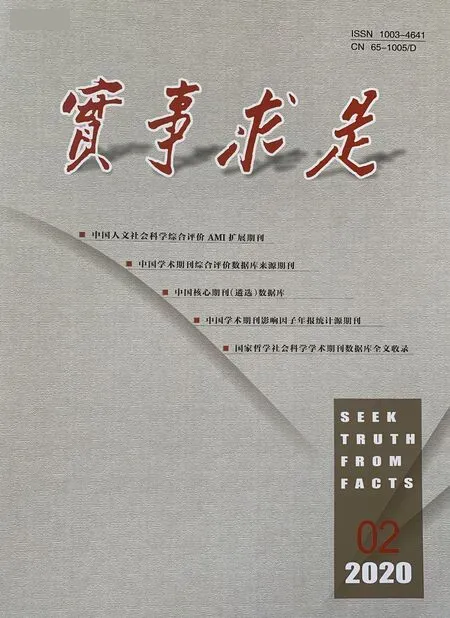康德与马克思道德思想的主体之辨*
2020-02-22刘睿博
刘睿博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110169)
毋庸置疑,无论是先验哲学体系下的道德还是唯物史观视野中的道德,都将其看成是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必要的规范和引导,都将人作为所关注和讨论的对象,都将人作为道德世界的主体。康德公开宣称:“人是道德律的主体”,“这个道德律是建立在他的意志的自由律之上的,而他的意志乃是一个自由意志,它根据自己的普遍法则,必然能够同时与它所应当服从的东西相一致”。[1](P163)换言之,在道德律所规定的目的王国中,人既是手段的一部分又是自在的目的本身,是这个王国真正的成员和主体。在马克思那里,人的主体地位则更加清楚不过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人类精神生产的产物最初无疑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的,是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然而,正如马克思在此后补充道:“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2](PP524~525)虽然康德与马克思都将人视作道德生活中的主体,但实际上在对于人的理解尤其是在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上二者是大相径庭的。也正是这种差异,事实上导致了康德与马克思对于道德的不同观点,或者说马克思道德思想对于康德道德哲学的超越之处根本就在于马克思视野中的现实的实践的人对康德眼中调和而来的人的超越。
一、先验哲学的人何以成为道德主体
在康德先验哲学体系的建构中,道德形而上学的大厦是建立在对人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因此,讨论先验哲学下的人何以成为道德主体实际上就是讨论以先验哲学的人为主体的道德形而上学何以建立的问题。因此,就要对先验哲学的人的出场和这样的人何以进入道德范畴有所把握。
(一)先验哲学的人何以出场
众所周知,康德的先验哲学从建立伊始就带有强烈的调和主义倾向。他总结吸收了笛卡尔、莱布尼茨等独断论者和休谟、巴克莱等怀疑论者的观点,试图通过为人类理性划清界限,探讨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为人类认识视野规定范畴等方式,解决独断论与怀疑论命题之间的二律背反,恢复形而上学“科学女王”的地位。康德的先验哲学区别于独断论在于其对于经验的看重,由此他提出,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而其先验哲学又与怀疑论者有所区别,体现于对人类理性和先天知识的论述之中。由此,他又提出一切知识不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对前一命题作出补充。可见,康德的先验哲学是对独断论和怀疑论的两种观点的一种调和与妥协,是在综合二者观点基础上的一次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彻底性,也导致了在康德先验哲学中的人所具有的分裂、对立和抽象的特征。
休谟的怀疑论将感性的人带入了康德的视野之下,使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促使他将人作为感性存在者来看待,在人是属于感官世界的存在物这一前提下来讨论人的本质。他认为,人首先是作为一个有需求的存在者而属于感官世界的。这种存在方式导致了在实际生活中的人必然受到感性需要的限制,这种限制决定了人的有限性。因此,幸福作为一种人类运用欲求能力使需要得到满足后的快意感觉,出于人类的这种有限性,就成为人所共求的了。这样一来,人的幸福的意图就绝不仅仅是可能的,而是人按照一种必然性所怀有的。如此,对于幸福的追求就成为了人所不可拒绝的感性方面的任务。因此康德指出,在实践理性的评判中,在涉及到人类作为感性存在者的本性时,自身幸福与否是极其重要的评判标准,是人类为自己制定实践准则的根据。在这种意义上,幸福的“意图属于每个人的本质”,[3](P34)但是康德认为,这种幸福是按照经验性的建议来行动的结果,是出于经验性根据的理想,是一个如此不确定的概念。“以至于每个人尽管都期望幸福,却绝不能确定地一以贯之地说出,它所期望和意欲的究竟是什么。”[3](P36)这样一来,人的使命无非就是在想象力中去寻找行为的经验性的根据,而最终只能是在无限的结果序列中白费力气。
但是,为哲学带来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康德绝不仅仅满足和停留于感官世界,而只把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者来规定。而先验哲学则是在承认了人作为感性存在者而存在之后,康德马上就为人的理性树立了权威。他指出:“人毕竟不那么完全是动物,面对理性为自己本身所说的一切无动于衷,并将理性只是用作满足中自己作为感性存在着需要的工具。”[1](P77)人与动物区别之根本就在于理性“将人在价值方面提高到超出单纯动物性之上”,[1](P77)为人类提出了超出感性之上的更高的目的。他试图用理性的原则去规定感性,为先天地、纯粹的善与恶的概念与出自经验的福与苦的概念作出了区分,并将其规定为理性评判行动的至上条件,并提出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的使命就在于意识到自己存在于纯粹的知性世界而对至善不断追求。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所言再清楚不过地表达出了他对人的这种看法:人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具有两个立场,并可以从这两个立场出发来观察自己,认识行为的一切法则。就人属于感官世界而言,他服从于自然法则。就他属于知性世界而言,他独立于自然法则而服从于不依赖于自然的、非经验性的、而是仅仅基于理性的法则。但是,康德又为了避免独断论式的僭妄而为理性套上了界限的枷锁。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理性的理论应用限制在经验的范围内,宣布把知识扩展到感官世界的边界之外在一切思辨中都会是毫无意义,引入“物自体”以避免人去思维先验的东西而得到超验的幻象,将人类的认识能力困于感官世界之中。这样就实际上达到了悬置知识,为信仰留出地盘的目的,从而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立留下的入口。康德正是从这种双重的方式设想人、表现人、理解人,才导致了先验哲学下的人一只脚踩在感官世界,一只脚又踏入了知性世界。尽管康德自己认为“这并不包含任何矛盾”,甚至二者必须同时成立,但是对于人的这种二元的、对立的、抽象的理解使康德不得不求助悬设,不得不借助中介,不得不创造那些神秘的、无法被认识的法则和理念,来为道德的合理性辩护。
(二)先验哲学的人何以进入道德
正如前文所述,康德基于对人的二元的、对立的、抽象的理解,把人当作同时生活在感官世界的知性世界的存在物来对待。但是,单是同时作为有感性存在者和有理性存在者的人还无法被道德所规定,也无法被道德律所统摄。因为在人永远无法脱离感官世界这个前提下,人类的有限性决定着感性需要作为感性自然的第一个原因迫使人永远无法摆脱自然的因果链条,永远处于感性的他律之下。若是人作为处于自然因果性之中的人,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处于他律的支配之下,道德又何以规范人类活动呢?或者说又怎么样能要求人去摆脱感性而做出道德行为呢?正如康德所说,如果“我们的意志不是自由的,而灵魂与物质具有同样的可分性和可朽性,那么就连道德的理念和原理都会丧失一切有效性,而与构成其理论支柱的那些先验的理念一起垮台了”。[4](P298)“如果没有这种唯一是先天实践性的自由,任何道德律、任何根据道德律的责任追究都是不可能的。”[1](P121)因此,自由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不能作任何经验性描述的原因性概念”,[1](P15)是一种自己规定自己的原因性的能力,是人类实践理性能力得以运用的前提性条件。他指出,如果要把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来思考,把人的行动看作意志的结果,就必须预设自由,就必须将“‘按照行动自由的理规定自己’这种属性归于每一个赋有理性和意志的存在者”。[3](P72)为此,康德提出了他的第一个悬设——自由意志来作为人类行为的第一个动机和原因,以此消除自然与道德之间的对立,为建立道德形而上学提供可能。这样一来,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其意志就可以独立于经验,独立于自然了,其行为就可以摆脱自然因果序列的束缚而将自由意志的自律作为根据了。至此,自由就成为了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得以进入道德世界的桥梁,成为了康德开启最崇高的实践原理的钥匙,成为了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结合的拱顶石。
但是,仅以这样的方式,道德律作为一条出于自由的原因性的法则,作为一条拒斥一切爱好的消极的规定何以发生作用是我们无法看出的。为此,康德不得不再次去找寻一个中介来为道德律引路。这次,他将善的意志作为先验的东西预设在了人的意志之中,并赋予它矫正人类行动使之合乎目的的能力,使之成为构成人类配享幸福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康德把这种条件称作德行)本身,成为人类对行动评价的最高标准。如此,道德律就通过善的意志唤起了理性存在者所先天具备的敬重情感(康德认为,敬重意味着我的意志无需对我的感官的其他影响的中介就服从一个法则的意识。也就是说,对道德律的敬重是人先天地善的意志自己造成的情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唤起了理性存在者对于与德行相配的幸福的渴望。这样道德律似乎就作为一条人类出于配享幸福而必须遵守的先天法则而被接受了。但是,这样的动机是康德绝不可以接受的。他认为,如果把“我可以希望什么”作为人类道德行为的动机,那么道德律立刻就沦落为经验性的准则而无法作为法则存在了。这样,康德的道德哲学就不得不再前进一步,去回答“我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了。
为此,康德用至善的概念去表示“意向与道德律的完全适合”[1](P153)这种状态(即德行与幸福之间比例相当,德行配享幸福的状态),但是他又马上指出,在实践原理中这种完全适合的状态只能被想象为可能的。在对至善概念的规定中,“可能”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作为想象,意味着这样而来的至善的概念只能被思维而无法实现。第二则是作为一种假设,意味着至善的概念也许会在无限追求中被实现。而无限追求的必要前提就是康德的第二个悬设:灵魂不朽。康德通过设立一个“同一个有理性存在者的某种无限持续下去的生存和人格性的前提”,将获得配得幸福的德行放到了无限的进程中来思维,也就是将在至善这一概念中与幸福相配的德行作为一种通过“不停息的努力”而可期望的结果保留下来。通过这一悬设,康德就既回答了“我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为出于道德的行为动机的合理性作了辩护,又避免了人类将“自己的期望绷紧到所希望的神圣性的完全获得,而迷失在狂热的、与自我认识完全相矛盾的神智学的梦呓之中”。[1](P153)随后,为了解释“与德性相适合的幸福的可能性”,[1](P155)康德又不得不搬出最高理性存在者——上帝作为裁判,由此引出了上帝存有这一悬设。因为由德性去期望幸福在现世中是一种按照愿望和意志发生的自然。而道德律作为一种自由的法则却是应完全独立于自然的。所以在道德律中没有任何根据来确立人的德性与其应配有的幸福关联,但这样关联却在实践中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应当力图去促进至善”这个命题的合法性,唯有假定自然拥有一个与道德意向(道德品质)相符合的因果性的至上原因,尘世中的至善才是可能的。因此,自然至上原因,作为至善的条件,不是通过理智和意志的作用而使自然与之相符合,这样的能力只有作为创造者的存在者,亦即上帝才能实现。至此,一个以同时作为感性存在者和理性存在者而对立存在的人,作为被束缚了理性能力和认识能力的但拥有自由意志的抽象的人为主体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大厦就真正地建立起来了。
综上所述,在康德那里,人一方面作为一个有感性的存在者,在感官世界中时刻受到自然因果性的制约,显示着作为人所具有的追求幸福、趋利避害的本能,向世界展示着人的有限性一面,而为至善无法实现提供根据。在另一方面,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被先天地赋予了自由意志与实践法则,从而具有了摆脱经验的、纯粹的对行为的评判能力,具有了对道德律的惊奇与敬畏,向世界展示了人无限性的一面,为通往“目的王国”提供了可能。正是由于康德在理解人的活动时所陷入的感性和理性的分裂,理解人的本质时所陷入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对立,理解人的认识能力时的消极与局限,导致康德的道德哲学就只能通过自由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的悬设来进入人类的现实世界了,道德律就只能通过先天的命令式的口气来对人类发号施令了,道德就只能披着神秘的、宗教的外衣(尽管康德想要竭力避免这样的狂热或迷信)来掩盖自己的种种缺陷了。因此,康德的道德哲学在为人提出了实践法则和最高目的后就无法再前进哪怕一步了。因为,康德认识到人永远也无法摆脱自己作为感性存在者的有限本性,但是又不敢越唯物主义雷池半步。于是康德的道德哲学实际上成为了无力的说教,成为了宗教、神学的附庸。
二、唯物史观的人何以成为道德主体
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为人的科学和属人的科学。因此,要说明唯物史观中的人何以成为道德主体这个问题首先就要说明在马克思视野中的人是如何有别于以往哲学家眼中的人而出场的。这将是理解马克思道德思想中的人的关键,也是马克思道德思想成立的基石。
(一)唯物史观的人何以出场
马克思是在扬弃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终结了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越是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越成为非人;越是推崇人的独特个性,人越变得片面;越是努力将人从宗教中解放,人越成为上帝的奴仆的怪圈。把人从“我思”中,从“原子”中,从“先验自我”中,从“绝对同一”中,从“绝对精神”中解放出来,赋予了人以真正的主体地位与人性。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用感性的人代替了概念中的人,用现实的人取代了思维中的人,这正是其哲学的进步之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指出,费尔巴哈哲学的功绩就在于“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5](P314)但是,马克思不满足于费尔巴哈所停留的“抽象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道:“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之外,他(费尔巴哈)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2](P530)为此,马克思摒弃了费尔巴哈所推崇的人与人之间虚幻的爱的关系,阐明了社会关系的现实性,揭示了消融在“实体”和“自我意识”等概念中的人的本质。他明确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综合,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6](P93)换言之,“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P60)这一论断,彻底粉碎了理论家们“神人”“人”的幻象,将人从虚妄的抽象概念和追求与概念相符的陶醉活动中解放出来,为在现实中寻找道德主体设立了前提,为唯物史观大厦的最终建立打下了牢固根基,为人类解放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在对人类感性活动的理解上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他用感性活动着的实践的人取代了在思维中活动着的人、在绝对命令下千人一面的人、在抽象世界中进行精神劳动的人,结束了人的思维与实践被隔绝、被割裂的状态。马克思认为,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PP524~525)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P79)而第二个事实既是在这种需要得到满足后产生了新的需要,创造出了“精神产物”,构造了人类的精神家园。然而费尔巴哈却“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他仅仅将“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6](P60)而把人的实践活动看成了“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看成了直观的反射活动,看成了消极被动地被自然必然性盲目支配的结果。因此,费尔巴哈虽然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使人在上帝那里得救后,又跪倒在了“爱”的脚下。
正是基于对人的这样的理解,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6](P60)“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6](P60)重塑了人类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找到了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为道德确立了真正的主体。
(二)唯物史观的人何以进入道德
纵观马克思道德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会清楚地发现人在马克思道德思想中的主体性地位。马克思道德思想的每一次发展、转变都与马克思怎样看待人、怎样理解人息息相关。马克思对人的理解的变化和发展实际上决定着马克思道德思想的脉络与走势。当马克思带有康德哲学色彩认为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的自由意志、在于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时,他就提出高尚就是神为人指出的共同目标,道德就是宗教对人类的孜孜教诲。当马克思从“自我意识”中走出,从关注抽象的人转向关注“捡枯枝的人”时,他就认为利益是社会中的道德根基,去批判多变的、利己的道德标准;当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和理性,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从而寻求人的复归时,他就力图将道德与宗教区分开来,留下道德的自律而剔除宗教的他律;当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学说的合理内核,将人的自由自觉地劳动当作人的类本质,发现了实践活动的人的异化时,他就批判国民经济学以道德的名义用两种尺度来衡量人,利用道德哄骗工人节制禁欲,为资本家骄奢纵欲打开方便之门;而当马克思进一步用科学的方法观察人,进一步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从前人,将人理解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人,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时,他就将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生产的结果来理解,就从处于社会关系中感性活动着的人出发来阐明道德的本质、功能与特征,真正建立起了属人的道德。
在马克思围绕着现实的感性活动着的人来建构道德时,实际上存在着三条线索。第一,从从事物质活动、进行物质交往的人出发,在人类物质活动中考察道德的起源。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PP524~525)道德是物质行动着的人精神生产的结果。基于这样的理解,马克思指出,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本身没有历史也没有发展,它的一切历史与发展全部都来源于“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PP524~525)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道德并不是先天存在的实践法则,而只不过是人类自己创造像“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那样的人类物质生活的反映。因此,对于道德的考察的出发点只能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样马克思就把道德从某种神秘的“天意”下解脱出来,将道德由不可知变为了可知,从天国带回了尘世,揭示了道德不过是人自己命令自己,自己强迫自己的事物的本质,为此后揭露资产阶级道德伪善的本质做好了准备。
第二,从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出发,在阶级社会中考察道德的实质。在马克思道德思想中,阶级性是道德的重要特征之一,阶级利益是统治阶级评价行为道德与否的重要标准,阶级利益的矛盾是不同阶级在道德评价上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发觉了统治阶级多变的评判立场。他讽刺资产阶级用私人利益的眼睛来观察和判断人的行为,用“两种尺度和两种天平来评价人”,[7](P262)把“细小的”和不变的利己的利益“当作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国民经济学是如何利用道德来为工人带上枷锁而为资产阶级牟利的。他指出国民经济学和道德实际上处于既是对立又不是对立之中,在工人那里国民经济学撇开了一切道德进行欺诈和剥削,然而在资产阶级那里,国民经济学又“以自己的方式表现道德规律”,为资产阶级带来了无数的利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找到了使人们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根源。他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的利益之间的矛盾”,[8](P498)这种矛盾作为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作为这种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体现在了道德理解的偏差之中。因此,马克思说:“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8](P498)一句话,包括道德在内的一切上层建筑无非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无非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资产阶级道德试图通过传统和教育来麻痹工人,让工人以为资产阶级的道德就是他们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使工人成为资产阶级攫取利益的手段和工具,这正是资产阶级道德的伪善之处。
最后,马克思从改造世界的实践的人出发,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展望中描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实现。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破坏了职业的神圣光环,破坏了家庭的温情面纱,破坏了一切封建、宗法关系,而留下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无产者在这种压迫下失去了民族性,因此,无产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法律、道德、宗教在无产阶级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此,必须通过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运动来推翻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道德的工作。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道德将建立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前提之上,建立在私有制和分工被消灭、阶级的差别完全消失的前提之上,将建立在“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的前提之上,建立在社会的每个成员拥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之上,“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P453)
三、结论
道德哲学是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从生活在感官世界和知性世界的人,从认识能力被局限被束缚的人出发来建立道德形而上学的大厦。将知识悬置,为信仰留出地盘,以此为人类理性的实践能力提供根据。他用自由意志、灵魂不朽与上帝存有来解释道德如何发生,企图寄托于“敬重”和人类内心对“至善”的不断追求以规定人类行为,从而通往“目的王国”。但是事实上,康德自己也为这样的道德说教感到无力。他承认,“德行的准则和自身幸福的准则在它们的至上实践原则方面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而且尽管它们都属于一个至善以便使至善成为可能,但它们是远非一致的,在同一个主体中极力相互限制、相互拆台”,[1](P141)因此人类永远无法为“至善何以可能”这样一个命题找到答案,真正完满的道德也无法实现。而马克思则立足于现实的感性活动的人,通过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来揭示道德本质,进行道德建构。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着重强调了人的伟大创造能力和主观能动性。他不仅仅满足于指出人类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更直截了当地宣告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将在康德那里分离的、对立的、抽象的人变为了整体的、统一的、感性的人。正是基于对人这样的理解,马克思剥开了康德为道德所披上的神秘的、宗教的、玄想的外衣(尽管康德自己强调人类要避免这样的狂热),科学地揭示了道德本质上的人为性、属人性和现实性。真正建构起有别于以往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道德学说,真正阐明了人类道德生活的本质,使道德活动摆脱宗教和神学,成为面向现实、面向现实的人的活动,事实上解决了道德何以起源,道德行为何以判断和“至善”何以实现的问题。将在康德那里仿佛是理性存在者怀着敬重情感在某种启示下所做的道德行为,仿佛是来自某种神谕的“最高目的”和只在理念中作为概念出现的至善与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统统带回到现实中来了。以在人的物质生产中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取代了康德的绝对命令,以在人的物质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价值原则取代了康德的实践理性,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取代了感官世界中人的无限差异,以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取代了康德幻想的在上帝统治下的目的王国,为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道德说教的麻痹,展现革命的本质力量,重塑人类社会真正的道德规范提供了理论武器与思想指导,彰显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