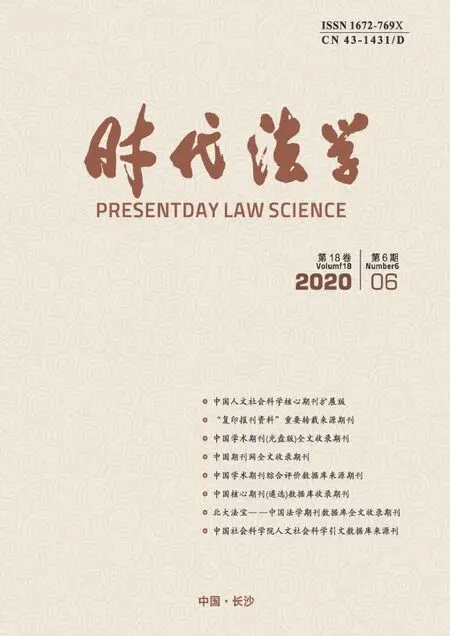科学方法、法令与判例:专家证词可采性规则研究*[1]
2020-02-21EdwardImwinkelried李尧
[美]Edward J.Imwinkelried[著],李尧[译]
(1.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法学院;2.中国政法大学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北京 100088)
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冤错案件不是非常罕见的事情。截至2017年,定罪后的DNA检测已经证实了超过340名被错误定罪者的清白(1)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and Tech., Report to the President—Forensic Science in Criminal Courts: Ensuring Scientific Validity of Feature-Comparison Methods 3(Sept.2016), https://www.innocence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PCAST-2017-update.pdf.。美国国家无罪登记处列出近2000起冤错案件(2)截至2017年2月26日,登记处已列出了1994个无罪判决。Nat’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 Exonerations in 2016, at 3(Mar.7, 2017), https://www.law.umich.edu/special/exoneration/documents/exonerations_in_2016.pdf.。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在许多案例中,有缺陷或至少言过其实的专家证词似乎促成了这些冤错案件(3)See Boaz Sangero, Safety from False Convictions 142(2016); Denise Lavoie, Fallen Forensics: Judges Routinely Allow Disavowed Science, L.A.Daily News(Aug.20, 2017), http://www.dailynews.com/2017/08/20/fallen-forensics-judges-routinely-allow-disavowed-science/(“自1989年起,加州大学欧文校区的美国国家无罪登记处记录了超过2000个无罪判决。‘错误或误导性的法庭科学’是其中近1/4案例的促成因素。”).。在冤错案件研究中,不准确的专家证词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4)Inger H.Chandler, Conviction Integrity Review Units, 31 Crim.Just., no.2, Summer 2016, at 15.。一项对156名经定罪后DNA检测被宣告无罪者的研究显示:在至少60%的案件审判中,“检方委托的法庭科学分析员提供了无效证词……包括对实证人口数据的误用和……关于不被实证数据支持之证据的证明价值的结论”(5)Brandon L.Garrett & Peter J.Neufeld, Invalid Forensic Science Testimony and Wrongful Convictions, 95 Va.L.Rev.1, 3, 9(2009).。研究者业已发现覆盖各个专业领域的错误法庭科学专家意见,“包括血液血清学、毛发证据、土壤比对、早期DNA检测、咬痕分析、犬嗅、声纹鉴定、鞋印和纤维比对。”(6)Donna Lee Elm, Continued Challenges for Forensics, 32 Crim.Just., Summer 2017, at 5.
诚然,在部分案件中,司法不公几乎无法避免。在大多数科学领域,研究是不断发展的。在某个时刻——如被告人最初受到审判时——可用实证数据或许已能够支持某项特定科学理论或技术的正确性了。在此情形下,一位诚实的专家将愿意基于特定技术向法庭作证,而法官也会采纳有关证词,这在审判时是合乎情理的。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演进,后续发现的数据可能会削弱人们对该技术的信心。无论早期研究者如何谨慎小心,他们的研究成果总有可能存在缺陷,因为研究者可能碰巧在有关经验领域中抽取到了不具代表性的样本。除非研究者对整个经验领域做一个彻底普查,否则任何特定“随机”样本都有可能是非典型的。
显微毛发分析是一例明证。数十年来,微量物证专家证明,基于对犯罪现场发现之毛发束的细致显微比对分析,可以确定某被告是否为现场发现毛发的可能来源(7)See 2 Paul C.Giannelli, Edward J.Imwinkelried, Andrea Roth & Jane Campbell Moriarty, Scientific Evidence § 24.02[l](5th ed.2012)[hereinafter Giannelli].。后来,DNA专家研发出毛发线粒体DNA(mtDNA)分析技术(8)Nat’l Res.Council, Strengthening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ath Forward 160(2009).。在FBI的一项研究中,对所选80例毛发比对,均有微量物证分析员告称显微比对结果一致或相关,然而,mtDNA分析却表明其中9例(12.5%)显微比对结果有误(9)Id.at 160-161.。在此类情形下,考虑到实证研究的早期状况,之前基于缺陷证词所作定罪或许情有可原,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被告人是否应该获得定罪后的救济。一些法庭已根据现行规制定罪后救济的法令,给予了被告新的审判(10)See Findings of Fact, Rulings of Law, and Order on Defendant’s Motion for New Trial at 2, Commonwealth v.Perrott, Nos.85-5415, 5416, 5418, 5420, and 5425(Hampden Cty.Super.Ct., Mass.Jan.26, 2016).。在其他司法辖区,如加州和田纳西州,立法机关近期已修订了有关法令,明确为以下情况提供救济:若一项技术或理论在对被告的定罪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该技术或理论在之后的科学研究中被证实是错误的(11)See Cal.Penal Code § 1473(e)(1)(Deering 2017); Tex.Code Crim.Proc.Ann.art.11.073(a)(2)(2017).。
然而在另一些案件中,错误定罪是可以避免的。在此类案件中,就在法庭科学专家基于某项技术或理论出庭作证时,已经有实证数据表明该技术或理论有误,且被告的辩护律师不难获取这些数据。偶尔,当表明技术有误的事实极其充足,可以清楚地显示辩护律师未能对其进行攻击的失职时,法院可基于律师未有效协助被告,侵犯其宪法第六修正案权利,给予相关救济(12)See Hinton v.Alabama, 134 S.Ct.1081, 1088-89(2014)(citing Strickland v.Washington, 466 U.S.668, 690-692(1984)).。但上述问题的最优解是,设计并实施一种能够去伪存真、避免将“垃圾科学”引入法庭的可采性标准。
本文第一部分述评了两种法院以往曾经适用过的可采性标准。第二部分建议采用一种替代性的可采性标准,该标准同时反映出合理的科学方法论,以及规制法令与案例的明智结合。第三部分讨论了建议标准的若干实际应用,旨在为读者提供对建议标准之功效与局限的一些认识。
一、错误的专家证词可采性标准
(一)只要专家意见具备相关性,专家证词就应当是可采的
一种可能的进路是,采纳任何具备相关性的专家意见(13)See Giannelli, supra note 7, § 1.07.。在此进路下,只要专家保证其意见中包含的技术或理论有效,审判法官就会采纳意见(14)See id.。
尽管这一进路会彻底简化法官对专家证词的可采性判断,但是它却同时违悖了科学方法论、规制法令与案例(15)See id.; James W.Hunt, Admissibility of Expert Testimony in State Courts, Fitzpatrick & Hunt, Pagano, Aubert, LLP, at 8, http://www.fitzhunt.com/sites/default/files/news/Admissibility%20of%20Expert%20Testimony%20in%20State%20Courts-Hunt.pdf(last visited Apr.8, 2018).。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译者注: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在其1993年所作影响深远的Daubert案判决中承认的那样,经典牛顿式科学方法论有三步:首先,科学家对某种现象提出假设;而后,科学家以实验室控制实验或系统实地观测的形式,将假设诉诸实证检验;最后,科学家审慎地评价检验结果,以此确定他们证伪或证实了假设(16)See 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 Inc., 509 U.S.579, 593(1993).科学方法是一种认识论技术,亦即生成知识的技术。See Epistemolog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epistemology/(last visited Jan.31, 2018).认识论的观点认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作出一个知识主张,其必须详述主张的基础或依据。See id.。相关性进路体现出与科学方法论的对立。这一进路允许专家基于不科学的“主观信念或未经证实的推测”发表意见(17)Daubert, 509 U.S.at 590.。无论专家如何激昂地声明其对假设真实性的个人信念,这种声明充其量不过是提出假设。如果假设似乎有一定道理,它或许值得被诉诸实证检验。但是,如果仅仅是个假设,那么它既不能代替下一步的实证检验,也更不能代替最后一步对检验结果的评价。无论如何,单纯的假设并未被科学地证实。
在1997年的GeneralElectricv.Joiner案判决中(18)Gen.Elec.v.Joiner, 522 U.S.136(1997).,最高法院明确指出,审判法官可以不采纳单纯基于专家武断宣称其深层技术或理论有效的专家证词(19)Id.at 146.。为了把问题讲清楚,最高法院在1999年KumhoTireCompanyv.Carmichael案中重申了上述观点(20)Kumho Tire Co.v.Carmichael, 526 U.S.137, 157(1999)(quoting Gen.Elec., 522 U.S.at 146(1997)).。毫无疑问,该观点没有被《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译者注:以下简称“《证据规则》”)顾问委员会遗漏。委员会在2000年起草了对《证据规则》第702条的修正案,将Daubert-Joiner-Kumho权威判例“三部曲”的教义部分地法典化(21)See Fed.R.Evid.702 advisory committee’s note to 2000 amend.。按照惯例,委员会准备了官方的“顾问委员会注释”随附修正案(22)See id.。通过援引“三部曲”判例,委员会宣称审判法官不可“轻信专家的话”(23)Id.。
(二)只要专家证词基于在相关科学领域内被普遍接受的技术或理论,它就应当是可采的
在第一条进路中,专家的个人意见是决定性的,如果意见具备相关性且基于专家个人保证有效的技术或理论,那么意见就是可采的(24)See, e.g., 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 Inc., 509 U.S.579, 592(1993)(“不同于外行证人,……专家被允许在更宽广的范围内提出意见,包括那些并非基于第一手知识或观察所得的意见。”).。不过,第二条进路是截然不同的。该进路要求对“技术或理论已被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广泛、普遍接受”进行展示,而非接受个别专家的个人意见(25)Frye v.United States, 293 F.1013(D.C.Cir.1923).。这就是著名的Frye(26)Id.at 1014.规则:
某项科学原理或发现,何时恰好越过实验阶段与可论证阶段之间的界线,是难以界定的。必须在此模糊地带的某处,认可该原理的证据力。尽管法庭将对采纳从某项被广泛认可的科学原理或发现推论出的专家证词起重要作用,但是籍以得出推论的科学原理或发现必须被充分证实,其已在所属特定领域得到普遍接受(27)Id.。
一度,联邦法院和绝大多数州都赞同该规则(28)Giannelli, supra note 7, § 1.06.。
应当肯定的是,与相关性规则相比,Frye规则为专家证词的可靠性提供了更强的保障(29)See, e.g., Adina Schwartz, A “Dogma of Empiricism” Revisited: 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and the Need to Resurrect the Philosophical Insight of Frye v.United States, 10 Harv.J.L.& Tech.149, 156(1997)(“Frye案的哲学核心是……是否被科学家们接受,是决定某一领域是否可算作适格专家能就其作证的真正科学专长领域的唯一标准。”).。单一专家对技术或理论的保证不再足以赋予其证词可采性(30)See Giannelli, supra note 7, § 1.06.。相反,证词的举证方必须证明技术或理论已获得相关领域专家们的广泛接受(31)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 Inc., 509 U.S.579, 594(1993)(quoting United States v.Downing, 753 F.2d 1224, 1238(3d Cir.1985)).。如果技术或理论满足上述情形,则可推知,至少有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已经审查并认可了深层次的实证研究(32)See Daubert, 509 U.S.at 593(仔细研究了科学界对接受同行评议之理论的彻底审查,是如何使“好科学”得以发表的).。然而归根结底,技术的广泛普及,仅仅是技术或理论符合科学方法论要求的间接证据(33)在Daubert案中,最高法院判决,《证据规则》生效之后,Frye规则在联邦法庭中不再是良法。Id.at 588-89(citing Frye, 293 F.at 1013-14).最高法院从对《证据规则》第702条文本“科学的知识”的参考中提炼出一项新的证实/可靠性规则。Daubert, 509 U.S.at 590.最高法院补充道,在新规则的适用中,审判法官应当考虑“普遍接受”的因素。Id.at 594.因此,最高法院仅将“普遍接受”当作技术可靠性的间接证据。See id.at 593-95.。单靠“普遍接受”并不能确定已有实证检验或检验结果证实了假设(34)See id.at 588, 592(以不足以达到《证据规则》第702条对证据可靠性要求之标准为由,最高法院决定拒绝适用Frye案“普遍接受”规则).。“普遍接受”不过是一大批相应领域专家集体的“武断宣称”而已(35)See id.。况且,在为数众多的案例中,诸如显微毛发分析(36)Giannelli, supra note 7, § 24.02[b].、确定子弹来源的弹头成分分析(CABL)(37)Id.at § 14.11.、射击残留物石蜡试验(38)Id.at § 14.13[a].等一度十分盛行的技术,都已被后来的科学研究证明为不可信的(39)Id.at § 24.02[b](显微毛发分析); 14.11(弹头成分分析); 14.13[a](石蜡试验).。简言之,遵循“普遍接受”规则只能为技术或理论的科学合理性提供不充分的保障,它是“对技术或理论科学价值进行直接评估”的粗糙代替品(40)Bert Black et al., Science and the Law in the Wake of Daubert: A New Search for Scientific Knowledge, 72 Tex.L.Rev.715, 725(1994).。
另外,在大部分司法辖区,“普遍接受”规则已被更加现代的法令和判例法推翻。在Daubert案判决中,最高法院认为1975年生效的《证据规则》已经含蓄地取代了Frye规则(41)See 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 Inc., 509 U.S.587, 594(1993).。最高法院强调指出,按照《证据规则》第402条,具备逻辑相关性的证据均为可采的,除非依据宪法、法令、《证据规则》或其他诸如《联邦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规则》等根据立法授权颁布的法庭规则其应当被排除(42)See id.at 587(quoting Beech Aircraft Corp.v.Rainey, 488 U.S.153, 163(1988); then citing Fed.R.Evid.402).。在Daubert案的多数意见中,Blackmun大法官说道,《证据规则》并不包含任何可以被合理解释为将“普遍接受”规则法典化的法条语句(43)See Daubert, 509 U.S.at 588(quoting Beech, 488 U.S.at 169).。因此,《证据规则》第402条废止了Frye规则(44)See Daubert, 509 U.S.at 587, 589(quoting Beech, 488 U.S.at 163; then citing Fed.R.Evid.402).。现在,44个州拥有以《证据规则》为直接蓝本编纂的州证据法典(45)See Jack B.Weinstein & Margaret A.Berger, Weinstein’s Federal Evidence § 6-T(2017).。由于Daubert案判决基于法条解释而非宪法分析,即便是那些模仿《证据规则》编纂证据法典的州,Daubert规则对其亦缺乏约束力(46)See Daubert, 509 U.S.at 587(quoting Beech, 488 U.S.at 163; then citing Fed.R.Evid.402).。然而,目前近3/4的州已经适用了Daubert案可靠性/证实规则的某种变化形式(47)Giannelli, supra note 7, §§ 1.14-15.。
二、专家证词可采性的建议标准
第一部分考虑了两种可能的专家证词可采性规制标准,发现其均在两方面存在缺陷:一是满足这两个标准几乎不能为深层技术、理论已被科学地——实证地——证实提供保障。二是这两个标准与规制法令和案例存在抵牾。一个可接受的标准不应存在上述缺点,而应反映合理的科学方法论,并体现规制法令与案例的结合。本部分建议如下标准(规则):举证方必须收集、安排足够的实证数据与推理论证,以优势证据标准说服法官,通过运用专家意欲依据的具体技术或理论,专家能够准确得出其考虑证明的特定结论类型。
以下按构成要素分别剖析和解释建议标准,更重要的是试图论证,不同于第一部分讨论的标准,新标准反映出合理的科学方法论,并与规制法令和判例法框架一致。
(一)法官
先决性问题是,应当由谁就可采性问题作出真正决定?按照现代普通法与《证据规则》,该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可采性问题的本质(48)See Edward J.Imwinkelried, Trial Judges: Gate Keepers or Usurpers Can the Trial Judge Critically Assess the Admissibility of Expert Testimony without Invading the Jury’s Province to Evaluate the Credibility and Weight of Testimony, 84 Marq.L.Rev.1, 10, 13, 16(2000).。《证据规则》第104条是讨论的关键,其有关部分写道:
(a)总体原则。法庭必须决定任何关于证人是否适格、特免权是否存在或证据是否可采的预备性问题。法庭在此类决定中不受证据规则约束,但有关特免权的规则除外。
(b)取决于事实的相关性。当证据的相关性取决于某一事实是否存在时,必须提出足以支持认定该事实确实存在的证明(49)Fed.R.Evid.104.。
在大多数案件中,《证据规则》第104条(a)款都会发挥效力(50)Edward J.Imwinkelried & Romana Lampley, 1-1 Federal Evidence Tactics §1.04(3)(a)(2017).,此即为人所知的“能力程序”(51)See Imwinkelried, supra note 48, at 17-18.。根据第104条(a)款,法官应发挥真正的事实认定者作用(52)Id.。法官要从双方角度斟酌基础证词(53)当某一事实适用第104条(a)款时,反方同时拥有提出反对和请求预先审查陪审团成员——一种微型的交叉询问——以支持反对意见的权利。Edward J.Imwinkelried, Determining Preliminary Facts under Federal Rule 104, 45 Am.Jur.Trials 1, § 29(1992).,对证词可信性发表意见,并作出最终裁定(54)See Fed.R.Evid.104(a)advisory committee’s note to the proposed rule.。例如,当检察官向出庭被告提出某一问题时,辩护律师以该问题要求被告提供受“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保护的信息为由,反对检方提问。检察官认为,由于问题涉及的对话并非发生在私密状态下,此处并不存在特免权。双方的基础证词中,达成一致的部分是,对话发生在被告与另一位律师之间,地点位于一部电梯内。争议点是,当对话发生时,是否有第三方站在可听见对话的范围之内——若有,则此处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因缺乏必要的机密性而归于无效。根据第104条(a)款,由法官——而非陪审团——对上述争议作出最终裁定(55)See Fed.R.Evid.104(a).。如果法官裁定对话是机密的,则法官支持辩方的反对意见并排除一切有关该对话的证词。将裁定权赋予法官的根本原因是,即使陪审团有意识地认定证词在技术上不可采,陪审团成员也难以在实际上将证词内容抛诸脑后(56)Imwinkelried, supra note 48, at 28.。即便法官指令陪审团无视有关证词,还是存在难以容忍的风险:陪审团成员会在潜意识层面受到“被告作出了确凿坦白”之事实的影响。
对比《证据规则》第104条(b)款——所谓“附条件的相关性程序”(57)Imwinkelried, supra note 53, § 14.。根据第104条(b)款,法官仅起有限的筛选作用,而真正作出决定的是陪审团(58)See Fed.R.Evid.104(b)advisory committee’s note to the proposed rule.。法官只是聆听举证方的证词,以表面价值接受它,并决定举证方基础证词是否拥有支撑一个理性判断的足够证明价值(59)See Imwinkelried, supra note 53, § 31.。如果证词至少拥有上述大小的证明价值,法官会采纳证词(60)See id.。然后,在对陪审团的最终指令中,法官指示陪审团成员,举证方负有以优势证据标准证明事实的举证责任。如果陪审团认定举证方恰当履行了举证责任,他们会在评议阶段斟酌相关证据;但如果举证方无法完成举证责任,他们就必须无视相关证据(61)See id.§ 33.。《证据规则》第602条规定的外行证人个人知识,以及第901条规定的呈堂物证真实性,是两个典型例子(62)See Fed.R.Evid.602; Fed.R.Evid.901.。设想陪审团成员判定证人缺少对案情的第一手知识,或某件呈堂证物系伪造。如果陪审团成员断定证人“并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事情”或某件呈堂物证在真实性上“一文不值”,常识自然会引导他们无视有关证据。个人知识或证据真实性的事实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制约着证据的逻辑相关性,即使对未经任何法律训练的外行陪审团成员而言,这一方式也显而易见。
一项科学技术或理论之正确性的事实,是否受《证据规则》第104条(a)款或第104条(b)款约束?乍一看来,有观点认为第104条(b)款对其具有约束力。《证据规则》第901条(a)款表明,依据该款所作决定受第104条(b)款规制,且第901条(b)款(9)项指涉“描述某一过程或系统,并表明其产生了准确结果的证据”(63)See Fed.R.Evid.901(b)(9).。上述措辞的范围似乎足够宽泛,可以延伸至科学过程或技术。然而在Daubert案中,Blackmun大法官特别指出,由第104条(a)款约束法官的裁定(64)See 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 Inc., 509 U.S.579, 592(1993).。
考虑再三,Blackmun大法官的决定是正确的。在此背景下,存在着一个重大危险:即使陪审团成员断定科学证词在技术上不可采,对证词的接触也会不恰当地影响其后续评议。有若干因素指向上述结论:
首先,有关科学技术和理论正确性的基础证词往往过于冗长。尤其是当双方就基于新理论和技术之证词的可采性进行争讼时,证词通常要耗费几百甚至几千页笔录本。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证据规则》第602条,有关外行证人第一手知识的基础证词或许只需花费一两分钟的审判时间。基础证词愈是量大,对陪审团成员来说将证词完全抛诸脑后就愈困难,即使在他们断定证词不可采时亦是如此。而且,考虑到有关科学技术、理论之证词的专业本质,陪审团成员不得不通过努力学习去理解它们。一个人越努力地审阅或理解某些信息,对其而言,之后无视这些信息就越困难(65)See Ryan J.Winter & Edith Greene, Juror Decision-Making, in Handbook of Applied Cognition 739, 744(Francis Durso, ed., 2006); cf.James S.Schutz, Expert Witness and Jury Comprehension: An Expert’s Perspective, 7 Cornell J.L.& Pub.Pol’y 107, 107(1997)(讨论了专家如何向陪审团表达复杂的信息).。
再次,对陪审团成员来说,判定一位外行证人是否确实目击了其准备作证的交通事故,是一件相对更为简单的事情。
最后,陪审团成员根据第602条和第901条所作抉择通常是直截了当、二选一的决定。证人要么目击了事故,要么没有。一个人要么书写了字迹,要么没写。相比之下,当陪审团成员评价科学证词的可采性时,其决定在本质上往往具有盖然性:研究表明,技术在一定百分比的情况下奏效(66)See Winter & Greene, supra note 65, at 741.。当技术只在49%的情况下有效,但专家证人恰巧是一位魅力非凡的演讲者时,陪审团同样可能会发现,将证词完全抛诸脑后是困难的。
基于以上原因,应当由法官而非陪审团决定科学证词可采性,法官应遵照由《证据规则》第104条(a)款规定之程序作出裁定。
(二)优势证据标准
在适用《证据规则》第104条(a)款时,法官一般会以优势证据标准作出最终裁定(67)See Bourjaily v.United States, 483 U.S.171, 175(1987).。但是,《证据规则》第104条(a)款并未明确规定适用优势标准。有时,会有论者主张法官应当适用某种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甚或是刑案中的排除合理怀疑(68)See Paul C.Giannelli, The Admissibility of Novel Scientific Evidence: Frye v.United States, a Half Century Later, 80 Colum.L.Rev.1197, 1246-48(1980).。这种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刑案牵涉更高的风险,以及对外行陪审团成员倾向于高估专家证词价值的担忧(69)See id.at 1246-47.。
然而,尤其在当务之急是防范错误裁判时,遵循传统的优势标准更为合适。考虑一件谋杀罪起诉和一起类似的民事非正常死亡诉讼。在谋杀案审判中,检方必须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证明被告有罪(70)2 Kenneth S.Broun et al., McCormick on Evidence § 339(K.Broun ed., 7th ed.2013).。在Weinstein法官对其联邦同僚关于排除合理怀疑涵义观点的著名非正式调查中,许多法官暗示,他们相信陪审团成员将此标准与“超过90%概率有罪”等同视之(71)United States v.Fatico, 458 F.Supp.388, 410(E.D.N.Y.1978).。设想在刑事审判中,检方提出一项证据,该证据客观上应当有40%的概率证明辩方实施了谋杀,但外行陪审团成员却错误地认为其有60%的概率证明辩方有罪。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避免冤错案件带来的实体不公,因为在60%至90%之间尚有一块安全的回旋余地。
但是,考虑如果民事原告在涉及同样事实问题的非正常死亡诉讼中提出同样的证据会发生什么:按照一般理解,只要证明概率超过50%,依据优势标准即可作出裁判(72)See Broun, supra note 70, § 339.。然而我们的假设是,尽管该证据只有40%的证明概率,外行陪审团成员却将其错误评价为拥有60%的证明概率。由于60%远超50%的临界门槛,即使陪审团成员未犯其他推理错误,上述错误已足以导致错误裁判。起初的错误是陪审团不当评价了证据的证明价值,但最终却导致错误裁判的实体不公。简言之,民事案件中的科学证据会带来诱发错误裁判的更高风险。如果优势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可以被接受,那么它同样应当在刑事起诉的“能力程序”中被接受(73)Fed.R.Evid.702 app.(2000)(声明优势标准要在遵守《证据规则》第702条的前提下适用).。
(三)实证数据与推理论证
正如佐治亚州最高法院所评论,按照传统“普遍接受”规则,审判法官通过简单的“清点人数”来确定技术或理论是否被普遍接受(74)Harper v.State, 292 S.E.2d 389, 395(Ga.1982).。但是根据Daubert规则,法官必须评估技术或理论受到实证验证的程度与质量(75)Daubert v.Merrell Down Pharm., Inc., 509 U.S.579, 592-93(1993).。具体来说,审判法官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实证研究进行权衡:
第一,法官应当考虑实证数据的体量(76)Edward J.Imwinkelried, The Next Step after Daubert: Developing a Similarly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 to Ensuring the Reliability of Nonscientific Expert Testimony, 15 Cardozo L.Rev.2271, 2281(1994).。数据组是仅包含一到两个传闻,还是十分充实?数据组规模越小,其样本不具代表性的风险就越高,而基于这种样本的统计数据难以准确反映经验领域的参数(77)Giannelli, supra note 7, § 15.04[b].。
第二,法官应当考虑实证数据的质量(78)Imwinkelried, supra note 76, at 2281.。如果样本数据不能代表经验领域,即使一个十分充实的数据组也会产生不准确的观点。单纯依靠样本规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抽取到不具代表性之样本的风险。然而,运用随机选择程序却能增加抽取到支撑关于经验领域参数可靠推论的代表性样本的概率(79)Giannelli, supra note 7, § 15.04[b].。研究者是否只基于方便而选取样本,而没有做到运用随机选择程序科学地选取样本?
第三,法官必须调查实验室实验或实地观测所具备的条件是否近似于当下案件中存在的条件(80)Daubert, 509 U.S.at 591-92.。在Daubert案中,Blackmun大法官强调,专家证据必须“适合”案件事实(81)See id.at 591(quoting 3 J.Weinstein & Berger, Weinstein’s Evidence 702-18(1988)).。更具体地说,最高法院在Joiner案中宣称,从逻辑上讲,审判法官必须断定专家是否可以从实证研究中推断出关于案件的结论(82)See Gen.Elec.v.Joiner, 522 U.S.136, 146(1997)(citing Turpin v.Merrell Dow Pharm., Inc., 959 F.2d 1349, 1360(6th Cir.1992)).。例如,专家提出,要基于气相色谱(GC)分析鉴定一款具体成分未知的致幻剂药物。为支撑其意见,专家援引并依据了一项涉及特定型号气相色谱柱、载气和固定相的致幻剂研究。然而,在当下案件的鉴定中,专家使用了不同种类的色谱柱、载气和固定相,这些条件能够决定样品何时从色谱柱洗脱及其保留时间(83)See Giannelli, supra note 7, § 23.02[d].。在气相色谱分析中,“保留时间”是认定未知药物的最重要提示(84)See id.。审判法官应当裁定专家无权将之前的致幻剂研究作为其意见支撑,因为鉴定意见是基于在完全不同条件下进行的测试。
第四,法官应当要求专家具体说明其打算依据的研究结果(85)See id.§§ 1.08[b], 24.19, 26.07[b].。出现假阴性与假阳性的百分比各是多少?正如法官不应接受专家对技术或理论有效的武断宣称一样(86)See id.,法官亦应拒绝专家对实证研究说明、确立、表明、证实或展示了技术正确性的推断性声明。为使法官明智地决定举证方是否已经以优势证据标准证实了技术或理论的正确性,具体数字与百分比是必不可少的。
(四)专家意欲依据的具体技术或理论
问题并不在于专家领域或学科的总体正确性(87)See D.Michael Risinger, Defining the “Task at Hand”: Non-Science Forensic Science after Kumho Tire Co.v.Carmichael, 57 Wash.& Lee L.Rev.767, 769-70, 772(2000).。在某一科学领域历史上任何给定的时期内,会有一系列理论流动。一些理论或许刚被提出,一些可能有极少的实证支持,一些可能有大量的实证验证,也有一些最终将被证明是不可信的。就科学方法论而言,泛泛地关注某一学科的正确性是没有意义的。学科的普遍正确性是个过于宽泛的命题,以至于无法作为一项可以被检验的假设。因此,我们必须关注那些有关具体技术与理论、可以被检验的假设。
这样做不仅在科学上更有意义,同时也是规制法令与Daubert权威判例的授权。《证据规则》第702条并不要求举证方证实专家的研究领域或学科(88)See Fed.R.Evid.702.。相反,第702条(c)款要求提供“证词是可靠原理及方法之产物”(89)Id.的基础展示。在Daubert案中,Blackmun大法官断言,专家必须展现其执行“手头工作”(90)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 Inc., 509 U.S.579, 597(1993).——而非该领域专家有时会执行的其他工作(91)Id.——的能力。在Joiner案中,最高法院指出,横亘于前的问题是,原告提出证明因果关系的具体专家意见之可采性(92)See Gen.Elec.v.Joiner, 522 U.S.136, 144-45(1997).原告方的专家团队在一定程度上依据了动物研究。Id.at 143.原告在上诉中主张,系争问题在于专家是否可以依据动物研究去推断人类身上的因果关系。Id.最高法院驳回原告主张并判定,决定性的问题是,原告专家援引的特定动物研究是否可以支持其提出的具体意见。Id.最高法院根据以下理由认定,原审法官恰当运用了自由裁量权来断定,原告专家援引的研究无法支持其意见:实验中的老鼠是幼鼠,而当下案件中的人类系成年人;实验中的老鼠接受了巨大的化学物质剂量,而人类仅有中度暴露;实验中的老鼠被直接注射化学物质,而人类仅有皮肤暴露;实验中的老鼠最终患上了与人类不同类型的癌症。Id.at 144-45.。Kumho案的思路与以上两案一模一样(93)Susan Haack, Disentangling Daubert: An Epistemological Stud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xpert Witnessing in Forensic Accounting 167, 177(Walter J.Pagano & Thomas A.Buckoff eds., 2005); Richard Collin Mangrum, Kumho Tire Company: The Expansion of the Court’s Role in Screening Every Aspect of Every Expert’s Testimony at Every Stage of the Proceedings, 33 Creighton L.Rev.525, 538-39(2000).。此案中,最高法院承认,总体上讲,对轮胎专家而言,以视觉和触觉方式检查轮胎残体,在确定事故是否系轮胎设计缺陷导致方面是有用的(94)See Kumho Tire Co.v.Carmichael, 526 U.S.137, 153-54(1999).。但法院补充道,决定性的问题是,原告专家Carlson在构建其“在缺少四个滥用迹象中两个的情况下,轮胎分离很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理论时用到的,更为具体的方法论之正确性(95)Id.at 154.。上述案例中,最高法院的分析全都具体到专家采用的特定方法论;这些判决意见要旨清楚地表明,最高法院不会接受某些关于专家领域笼统而含糊不清的证明。
(五)准确性
案例与评论均使用各式各样的形容词,去描述可能作为法庭证词基础的技术与理论的必要品质。其中,最常用的两个形容词是“有效的”和“可靠的”。从技术层面来说,可靠性涉及方法论的一致性,而有效性可以赋予技术完成举证方声称其可以完成之工作的能力(96)See Giannelli, supra note 68, at 1201 n.20.。一项能够一致地得出相同错误结果的技术,从技术上讲是“可靠的”。但是,基于这种“可靠”技术之证词的可采性,不太可能减少发生冤错案件的风险。然而,Daubert案让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最高法院要求科学证据举证方像证实相关性那样证实证据的可靠性(97)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 Inc., 509 U.S.579, 589(1993).。但最高法院同时补充道,为确定科学技术或理论系“可靠的”,其必须受到“足够证实”的支持(98)Id.at 590.。
已被遵从的是,举证方必须证明,技术或理论在技术层面是有效的,即,它能使运用技术或理论的专家准确地执行“手头工作”。或许,前文提到的《证据规则》第901条(b)款(9)项中的用语,最好地抓住了有关概念:如果举证方提供基于“科学的过程或系统”的证词,那么该方必须“表明其产生了准确结果”(99)Fed.R.Evid.901(b)(9); see Wes E.Henricksen, Peddling Ignorance: A New Falsity Standard for Scientific Knowledge Fraud Cases, 86 UMKC L.Rev.295, 339(2017)。根本问题是,技术或理论能否准确地完成举证方声称其可以完成的任务。如果举证方声称技术能使法庭化学家确定未知样品是否为可卡因,那么该方必须提出技术允许化验员准确地作出判定的实证数据。如果举证方声称技术能使物理学家确定一辆发生迎面相撞的机动车的速度,那么该方应当被要求收集和整理证明技术允许物理学家准确地判定速度的实证数据。简言之,应当以准确性为底线。
(六)专家考虑证明的特定结论类型
建议标准的此项要素带来两大不同之处。
1.结论类型与具体结论
首先,在这一分析阶段,决定技术通常是否能使专家得出一种结论类型,与决定专家在当下案件中的结论是否正确有着根本不同(100)Fed.R.Evid.702(c); Daubert, 509 U.S.at 590, 593, 594; Kumho, 526 U.S.at 149-50(quoting Daubert, 509 U.S.at 592-94); Vern R.Walker, The Structure of Factual Inference in Judicial Settings: Theories of Uncertainty: Explaining the Possible Source of Error in Inferences, 22 Cardozo L.Rev.1523, 1523, 1541(2001).。无论从逻辑还是法律上讲,这一不同都很重要。在大多数案件中,专家会运用三段论推理:
大前提:如果一位病人表现出症状A和症状B,那么其很有可能患上了疾病C。
小前提:该病人的病历中包含症状A和症状B的征象。
结论:因此,该病人很有可能患上了疾病C。(101)Edward J.Imwinkelried, The Bases of Expert Testimony: The Syllogistic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estimony, 67 N.C.L.Rev.1, 2-3(1988).
现在,法官正在评估举证方对专家大前提正确性展示的充分性。不过,即使专家大前提是对的,专家的最终结论仍有可能出错。例如,在对案件事实适用大前提时,专家或许依据了不可靠的关于案件事实的具体信息,即小前提。但在此处,法官裁断的是“专家专长是否能使其准确得出某种结论类型”的问题。专家最终结论的正确性问题会在之后出现,并在分析方法上迥异。
联邦的证据法认识到了这种不同的存在。《证据规则》第702条将“证词是否系可靠原理与方法的产物”问题与“专家是否可靠地将原理与方法适用于案件事实”问题区别开来(102)Fed.R.Evid.702(c),(d).。随附《证据规则》第702条2000年修正案的顾问委员会注释明确指出,审判法官并非要适用判决意见中的“正确性价值标准”(103)Fed.R.Evid.702 advisory committee’s note to 2000 amendment.。如果法官打算采用这一标准,其将篡夺事实审理者作出有关裁断的权力。
2.不同的结论类型
第二处不同在此发挥作用。专家可以尝试得出若干种结论类型。例如,在Daubert案中,Blackmun大法官提到,专家或许试图从月相研究技术收集到的数据中得出两种迥异的结论(104)See Daubert, 509 U.S.at 591-92.。他指出,通过这些数据,专家能够可靠地得出关于“特定地方夜间某一时段有多暗”的结论(105)Id.。但又同时补充道,如果专家从数据中推出“彼地彼时某个人疯了”的结论,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106)Id.。可用实证数据支持第一种结论类型,但不支持第二种。
有两种常见的结论类型,一种是针对系争事实的实体证据,而另一种则揭示证人的可信性。考虑对强奸创伤综合征(RTS)证据的可能使用。在所有使用方式中,专家会从相同的基本理论出发;该理论对报称遭到强奸的妇女进行特征画像,包括特定的恐惧症,以及通常诸如拖延首次报案时间、报称遭受强奸后又否认等行为(107)Giannelli, supra note 7, § 9.04.。正如明尼苏达州法庭认识到的那样,检方可以尝试将此类证词推向两种迥异的使用方向,即,有关案情的结论抑或作为可信性证据(108)See State v.McGee, 324 N.W.2d 227, 230(Minn.1982); see also State v.Saldana, 324 N.W.2d 227, 231(Minn.1982).。
例如,检方提供心理学家的证词,声称强奸报案人的行为表现符合RTS特征画像,因此很有可能遭受了强奸。在此情形下,检方力图将证词作为证明某事发生过的实体证据使用;检方专家打算将RTS特征画像作为历史价值层面的事实发现工具使用。这时,检方将需要某种类型的实证基础。详言之,检方必须展示RTS特征画像系由数据库总结而来,而数据库包含已被证实的强奸报案。并非从表面上接受典型的声称自己是受害者的个人陈述,研究者必须证明:其已联络过医院急诊室,了解到受害人是否表现出遭受暴力性侵的生理症状;已联络过警署,弄清楚犯罪嫌疑人后来是否承认实施了强奸;已联络过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了解到他们是否已经发现了强奸案的独立证据。除非可以保证数据库中的事件确系强奸案,否则专家不得将数据库作为事实发现工具使用。一般来说,法庭拒绝接受某些典型证词作为实体证据(109)See, e.g., Giannelli, supra note 7, §§ 9.03[a], 9.07[a].,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种类实证数据的缺失。
然而,假设检方满足于将证词作有限的、可信性方面的使用。辩方基于被害人延迟报称遭受侵害而质疑其可信性。为恢复被害人可信性,检方意欲援引心理学家之证词,表明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强奸受害者会延迟联系执法机关报案。检察官告诉法官,其同意法官给予陪审团《证据规则》第105条的限制指令,即他们只将证词作为可信性证据使用(110)Fed.R.Evid.105.。简言之,专家意图证明一个迥异的结论类型(111)See Christopher B.Mueller & Laird C.Kirkpatrick, Evidence under the Rules 693(8th ed.2015).。由于检察官不再试图使用RTS证词作为事实发现工具,提出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基础证词就足够了(112)See People v.Taylor, 552 N.E.2d 131, 138(N.Y.1990); see also Helen J.Lauderdale, Comment, The Admissibility of Expert Testimony on Rape Trauma Testimony, 75 J.Crim.L.& Criminology 1366, 1412(1984)(“强奸创伤综合征的研究基础——临床心理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刑事审判中恰当的专家证词学科。”).。设想心理学家为下述情况作证:他已审查了一个包含数千起强奸报案的数据库,在绝大多数案例中,声称自己遭受强奸者都接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治疗,从长期来看,治疗专家在几乎所有案例中发现,声称自己遭受强奸者的心理健康与情感均有显著改善。在这些案例中,确实存在有人虚构受害的可能性。但是,考虑到足够多的成功临床干预,可以得出一个常识性结论:声称自己遭受强奸者至少在主观上相信自己确实被强奸了。概言之,法庭需要的实证验证之本质,取决于专家意图证明的结论之本质。
三、建议标准的实际应用:阐明功效与局限
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个决定专家证词可采性的建议标准。该部分认为,建议标准既反映出合理的科学方法论,又代表了规制法令与判例法的结合。接下来的子部分意图通过阐明此规则的功效与局限,来对其进行精炼完善。
(一)包含优势证据规则的建议标准并非总是要求举证方以超过50%的盖然性证明,专家通过运用技术可以准确得出特定结论类型
在建议标准的适用中,必须密切关注专家意图证明结论的本质。例如,考虑在一起公诉中,检方指控被告医生犯邮件诈骗罪。起诉书写道:被告经营一家癌症诊所,诊所广告宣称诊所使用当前所有可用的诊断测试进行癌症筛查。诊所确实使用了若干质量较差的测试技术,但其从未使用过可用的最佳诊断测试。被告承认其诊所确实没使用过那种测试,但否认那是最佳诊断测试。在审判中,检方从疾病控制中心请来癌症专家,就一项针对所有可用癌症诊断测试的全国性综合研究出庭作证。该研究涵盖10,000名患有涉案疾病的人,样本构成具有代表性,且测试条件真实。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当前共有4种针对涉案疾病的可用诊断测试;第二,第一种测试,即被告诊所没有使用的,具有60%的假阴性概率;第三,然而,其他3种测试具有更高的假阴性概率,分别为70%、80%和90%。
该研究表明,诊所没有使用的测试甚至无法令医生以超过50%的概率判断病人是否患有涉案疾病——相反,该测试有超过五成概率得出假阴性结果。然而,检方已经成功履行了基础证明责任。基于该研究,根据《证据规则》第702条,应当允许专家就“诊所没有使用的测试是可用的最佳诊断测试”发表意见(113)See Fed.R.Evid.702.。检方专家宣称,诊所没有使用的测试是最为专业的测试,而实证数据证实了这一点。
(二)即使专家的技术或理论满足建议标准,专家的最终意见仍有可能不可采
如前所述,在许多案例中,专家的直接询问在结构上是三段论的(114)然而,在许多案件中,专家的证词并不遵循这一模式。相关文献通常涉及专家证人的单独使用,仿佛只有一种方式去使用一个恰好是专家的证人。实际上,使用这种证人有以下四类不同方式。第一,有时,这种证人单纯充当事实证人。设想一位知名毒理学家在驱车上班时目击了一起交通事故。详言之,她看见被告的车闯过红灯并撞上一辆巴士。该证人拥有对上述事实的第一手知识;基于《证据规则》第602条,如同一位外行证人,这位毒理学家可以就上述事实作证。第二,有时,这种证人可以提供外行意见。现在,假设事故之后毒理学家接近被告的车辆。当被告待在车里时,毒理学家注意到他言语混乱、眼睛通红,并散发出强烈酒气。基于上述事实,证人可以就驾驶员醉酒作证发表外行意见。See Fed.R.Evid.701; Broun, supra note 70, § 11.证人的毒理学背景并不会剥夺其作证发表外行意见的资格,另外,依据《证据规则》第701条,该意见也是可采的。第三,有时,专家实际上只是给事实审理者作一个有关某种技术或理论的讲座,而并不试图将技术或理论应用于任何具体案件事实。顾问委员会对《证据规则》第702条的原始注释称,依据该规则,专家“可以就与案件相关的科学或其他原理给出专题论文或进行讲解,而将把这些原理适用于事实的工作留给事实审理者”。Fed.R.Evid.702 advisory committee’s note to proposed rules.该注释说明,起草者通过将《证据规则》第702条措辞表达为涉及“意见或其他形式”来允许这类证词。第四,尽管如此,在专家证实技术或理论的正确性之后,举证方仍可邀请专家通过将技术或理论适用于具体案件事实,来就某些案件事实的重要性发表意见。在此情形中,专家的证词将具备清晰或含蓄的三段论结构。。若是如此,满足《证据规则》第702条(c)款也无法保证专家最终意见的可采性(115)See Fed.R.Evid.702.。除满足第702条(c)款外,举证方必须证明依据第702条(d)款,专家恰当地将技术适用于案件事实(116)Id.at 702(d).。对此,《证据规则》第703条要求证明,专家获得了关于具体案件事实的可靠信息(117)See id.at 703.。
而且,即使举证方一丝不苟地注意到了《证据规则》第7章的每个细节,专家的最终意见仍有可能被证明是不可采的(118)See id.at 702 advisory committee’s note to 2000 amendment.。正如最高法院在Daubert案中提到的,举证方必须同时通过《证据规则》第403条之考验(119)See 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 Inc., 509 U.S.579, 595(1993).。该规则赋予审判法官自由裁量权,允许其在伴随证明危险大大超过证据证明价值时,排除本来可采的证据(120)Fed.R.Evid.403.。该规则明确提及“使议题更加复杂,……浪费时间,或不必要地提交重复证据”(121)Id.等证明危险。
考虑一起假想的毒品公诉案件。检方必须证实,从被告人处扣押的药物系可卡因。法官已裁定检方可以采用气相色谱/质谱(GC/MS)分析。因其具备高度特定性,该技术被普遍认为是毒品鉴定检测的“黄金标准”(122)Giannelli, supra note 7, § 23.03[c].。然而,为使定罪加倍地可信无疑,检方同时提供了有关紫外分光光度法(UV)检测的证词(123)Id.§ 23.02[f].。在就提供UV检测证词召开的审前听证会上,法官断定:UV检测只能以51%的概率支持被扣押药物系可卡因;检方专家关于UV检测的证词包含大量高度专业的技术术语,外行陪审团成员理解起来可能会有困难;在庭上发表证词及辩方对UV检测的反驳可能会耗用4个小时庭审时间。一方面,特别是由于法官准许检方使用GC/MS证词,UV证词就只有极小的“证明价值”。毕竟,审判记录表明,UV证词的准确性也就勉强超过如同“掷硬币”般随机的50%。另一方面,专家使用科学术语可能“使议题更加复杂”,GC/MS证据的使用令UV证词成为“没有必要的重复证据”,而耗用4个小时庭审时间又属“浪费时间”(124)Fed.R.Evid.403.。综上所述,审判法官有理由依据《证据规则》第403条将UV证词排除(125)See id.。
(三)若没有更多补充证词,即使专家的技术或理论满足建议标准,在法律上仍有可能不足以支持定罪
正如(二)子部分指出的那样,最高法院在Daubert案中宣称,即使举证方提供的专家证词满足《证据规则》第7章,审判法官仍可依据《证据规则》第403条排除证词(126)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 Inc.509 U.S.579, 595(1993).。最高法院亦评论道,单独来看,即便是可采的证词,在法律上也可能不足以支持一项判决(127)Id.at 596.。
例如,假设检方以谋杀罪起诉被告。法庭科学探员在犯罪现场发现两处血迹,实验室通过红细胞试验发现其中一处血迹为AB型血,与被害人血型相符。世界人口中仅有3%是AB型血(128)Giannelli, supra note 7, § 17.09.。另一处血迹为O型血,与被告人血型相符。然而在美国,约45%的高加索裔人口、51%的非洲裔人口、57%的拉美裔人口以及40%的亚裔人口是O型血(129)Blood Types, Am.Red Cross, http://www.redcrossblood.org/learn-about-blood/blood-types.html(last visited Feb.2, 2018).。假设在红细胞试验之后,一起实验室事故污染了样品,令其无法接受DNA检测。毋庸置疑,红细胞试验证据是可采的(130)Giannelli, supra note 7, § 17.09.。大量数据显示,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可以精准测定一个人的红细胞血型。证明被告人血型与凶手吻合的证据具备逻辑相关性,间接证据指向被告人可能为行凶者。通过非常微小地增加被告人系凶手的可能性,血型证据缩小了潜在行凶者的可能范围,并满足《证据规则》第401条的要求(131)Fed.R.Evid.401; Broun, supra note 71, §§ 184, 185.。但是,本案中由于实验室事故,检方只能通过提交红细胞试验证据证明被告人系行凶者。在检方主诉案件结尾的一项辩方动议中,审判法官应当不容商量地宣告被告无罪。在1979年的Jacksonv.Virginia案(132)Jackson v.Virginia, 443 U.S.307(1979).中,最高法院宣称,为确保法律上的充分性,公诉案件证据体系必须强大到足以使一位理性的陪审团成员以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确定被告有罪(133)Id.at 323.。而前述假设中,唯一可以证明被告人系行凶者的检方证据,是将被告置于包括世界上数十亿人口之庞大类群中的证词。从法律上讲,可采的红细胞试验证据远不能满足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134)类似问题也有可能出现在民事诉讼中。在民事案件中,法庭通常会采纳关于鉴别诊断(证明患者疾病的本质)或不同病因(证明疾病的起因)的证词。Giannelli, supra note 7, § 20.06[b].在两种技术中,专家运用消去推理的方法,确定最有可能的疾病或病因。然而,分析只能得出最有可能,而非必然的疾病或病因。See Edward J.Imwinkelried, The Admissibility and Legal Sufficiency of Testimony about Differential Diagnosis(Etiology): Of Under—and Over-Estimations, 56 Baylor L.Rev.391, 393-94(2004).即使没有达到50%的盖然性,某种疾病或病因仍然可以是最有可能的。同样,证据是可采的,但不足以在法律上支持一项判决。。检方尽管能够赢得可采性之争,却将输在证据充分性之战中。
(四)即使最初审判时的技术或理论满足建议标准,后续科学研究也可能证明理论或技术谬误到有必要给予定罪后救济的程度
正如Blackmun大法官在Daubert案中评论的那样,法律调查与科学探索的不同之一,就是法庭必须基于彼时可用的数据裁断案件,而科学家可以无限期推迟对某个问题的判断,直到有新补充的实证数据可用(135)See 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 Inc., 509 U.S.579, 596-97(1993).。在审判时,实证记录的情况或许能使法官得出“专家证词举证方已经满足了建议标准”之结论。可用实证数据或许表明,通过运用专家依据的具体技术或理论,专家能够准确得出其打算证明的特定结论类型。
然而,对案件涉及科学问题的研究会继续进展。后续研究削弱人们对之前审判采纳证词之信心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正如引言指出的那样,尽管数十年来法庭一直认可显微毛发分析证据的可采性,后续mtDNA研究却揭示了毛发分析员过去有时作出的夸大宣称。审判法官将其对证据问题的裁定基于作出裁定时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信息,有时还包括法庭依据《证据规则》第706条指定专家的补充内容(136)See Fed.R.Evid.706.。如果科学研究取得了进步,如同在毛发分析案例中那样,后续实证研究可能会证实法官之前的裁定有误。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先前审判中决定证据可采性的标准。相反,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平衡司法裁判终局性与防止司法不公两种互相冲突的利益价值,以确定何时应当启动定罪后的救济程序(137)See Edward J.Imwinkelried, Revising State Post-Conviction Relief Statutes to Cover Convictions Resting on Subsequently Invalidated Expert Testimony, Seton Hall L.Rev.(即将于2018年刊出,在原稿第5页).。
四、结论
我们不能天真地期望,我们采取的任何措施可以完全消除发生冤错案件的风险。包括法官和陪审团在内的人类决策者,被迫在不确定的情况下(138)See Ted Vosk & Ashley F.Emery, Forensic Metrology: Scientific Measurement and Inference for Lawyers, Judges, and Criminalists 129(2015).计量学(测量的科学)在科学证据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计量学的基本原则是,人们不可能确定任何测量是否准确地捕捉到了被测对象的真实数值。Id.at 129.无论测量者的测量技能如何娴熟,抑或测量器具被如何精确地校准,在科学分析的基本层面上,始终存在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以不断变化发展的不完备知识体系作出决策,在需要运用科学知识协助进行审判的案件中尤其如此。如果某一学科被应用于法庭,通常会对该学科中相关假设的进一步实证探究产生强大激励效应。在一些案例中,这种激励是经济上的(139)See George C.Harris, Testimony for Sale: The Law and Ethics of Snitches and Experts, 28 Pepp.L.Rev.1, 3(2001).。潜在侵权责任中的数十亿美元赔偿金可以取决于对“暴露于特定化学物质是否会引起癌症”这一假设的研究结果(140)See, e.g., Bert Black, A Unified Theory of Scientific Evidence, 56 Fordham L.Rev.595, 603 n.29(1988).。在另一些案例中,这种激励与公共安全有关。如果犯罪实验室可以证实低拷贝模板(LCN)DNA检测的有效性(141)Giannelli, supra note 7, § 18.03[d].,执法机关将更加有效地处置和预防犯罪活动。考虑到不断发展的科学研究,曾经被认为是可靠科学的理论,后来却有可能被证明是不可信的;相反地,曾经被当成是异想天开而遭到摒弃的理论,之后却有可能获得可作为法庭证词基础的可靠科学之地位(142)Ronald L.Carlson, Edward J.Imwinkelried, Julie Seaman & Ericka Beecher-Monas, Evidenc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an Age of Science and Statutes 34(7th ed.2012)(“正如现代技术中心主任指出的那样,‘仅靠机械单调的规律性,貌似称职者就武断地宣称什么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什么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这种做法已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有时甚至是在从他们笔里写出来的墨水还没干透的时候’。”)在1878年,当爱迪生即将完善其电灯泡发明的时候,一个特别的英国议会委员会声称,电灯泡的概念“不值得科学人关注”。Arthur C.Clarke, Profiles of the Future: An I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15-16(1984).在苏联发射Sputnik I号人造卫星的前一年,皇家天文学家Richard van der Riet Woolley博士说,太空旅行的建议“完全是胡说八道”。Id.at 15-16, 23.。
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可采性标准,它同时反映出合理的科学方法论,以及相关法令与判例的明智结合。笔者意在构想一个标准,它将提供更强有力的冤错案件预防机制。正如第一部分所表明的,超越“普遍”——无论个人专家的武断宣称抑或科研领域的专断态度——而达于实证论,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如果我们追求科学合理的专家证词,法庭就必须要求实证研究,因为那是科学方法论的根基。第二部分进一步表明,为了对举证方提供的专家证词进行有意义且严格的审查,法官必须采用某种高度具体化的分析。法官必须查明,举证方是否已经收集、安排了足够的实证数据与推理论证,证明通过运用专家依据的具体技术或理论,专家能够准确得出其打算证明的特定结论类型。无可否认,适用此项建议标准并不能确保今后不再出现冤错案件。但是,向具体、实证化的分析迈进,是预防此类司法不公的最佳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