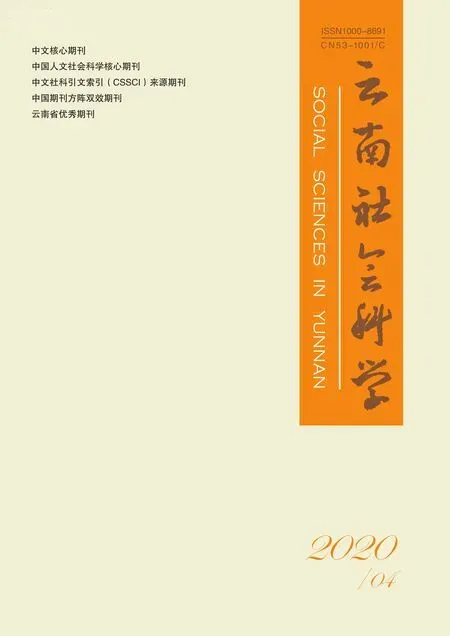与时异趣:唐宋宠物文学中的士人审美与情理对话
2020-02-21王萧依
王萧依
严格来说,中国古代并无“宠物”一词,但确有“宠物”之实。特别是在唐宋时期,人们“养玩鸟兽”①(宋)李觏:《富国策·第四》,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以为美观”“特见贵爱”②(宋)吴自牧:《梦粱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0页。的行为,以及作为这一行为的对象、为主人提供身心愉悦且非功利性的家养动物,确实都存在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因此依然可以使用“宠物”一词来指代这一对象。当时的宠物文学,就是指那些书写有关宠物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哲理思考等内容的文学作品。随着日常生活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热点,文人的宠物养玩风尚及其与文学活动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一个新颖的话题③目前关于唐宋时期宠物养玩与文学创作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着眼于宏观的社会风尚,如纪昌兰《试论宋代社会的宠物现象》(《宋史研究论丛》2015年第1期),对宋代宠物的流行品种、饲养状况、市场行情及时人的审美趣味、休闲生活方式等进行梳理论述;另一类多集中于研究白居易和欧阳修的宠物养玩与书写个案,如坂井多穗子《中国士大夫与作为宠物的鹤》(《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1期)、杨晓山《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论著皆以白居易关于宠物鹤的生活经验及诗文作品为切入点,剖析其玩物观念、生活追求及文学影响,而吕肖奂《宋代唱和诗的深层语境与创变诗思——以北宋两次白兔唱和诗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梁建国《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则都以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围绕白兔、白鹤等宠物的诗歌唱和为研究对象,探讨士大夫群体的审美趣味、文学理念和休闲生活风尚等问题。。唐宋宠物文学最直接的观照对象虽然是宠物,真正决定其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的核心因素还是文人自身的精神世界。欧阳修曾在诗中将自己的宠物之好描述为“与时虽异趣”④(宋)欧阳修:《忆鹤呈公仪》,《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刘德清、顾宝林、欧阳明亮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317页。,含蓄地标榜了自身与社会物质潮流之间的差异。然而,其“异趣”实际上是建立在与整体社会风潮的“同趣”之上的独特士人追求,这是唐宋时期宠物文学审美趣味和情理内涵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结果。本文将以唐宋宠物文学空间与内容的变迁作为切入点,梳理唐宋之际宠物文学日常化、私人化、文人化的演变过程,进而探讨唐宋士人宠物爱好及文学书写真正“与时异趣”的精神内涵。
一、从宫廷、闺阁到文人宅院——唐宋时期宠物文学空间与内容的变迁
中国古代针对各类驯化动物的休闲娱乐方式和观念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汉代宫廷以斗戏表演为目的驯化、饲养大型兽类;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观赏禽鸟受到欢迎;唐宋以降,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人与多种家养动物如狗、猫、兔、鱼等的关系愈发密切,其中,贵族与文士群体饲养这些动物的目的逐渐脱离了传统的劳作或食用,转而用于观赏、逗玩,成为一种新的休闲娱乐风尚。关于宠物的文学创作在唐代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小高潮,这一时期的宠物文学多以聪慧美丽的鹦鹉和西域出产的猧子①参见丛振:《西域“猧子”与唐代社会生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为书写对象,通过它们的活动状态来表现女主人的爱恋悲欢。《太平广记》据《谭宾录》载杨贵妃所养的鹦鹉名“雪衣女”,“颇甚聪慧,洞晓言词”,“性既驯扰”“可讽诵”②(宋)李昉编:《太平广记会校》卷460,张国风会校,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第8232页。,会在玄宗与人弈棋落下风时搅乱棋局助其获胜;《酉阳杂俎》所记杨贵妃的另一宠物“康国猧子”亦有此举。③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姑且不论,它们至少展现出了上流社会的宠物所具备的丰富休闲生活乐趣、增进男女主人感情的功能。而这类宠物所承载的关于爱恋的文学色彩,在诗歌中则主要表现为寂寞和幽怨的情愫,如王涯《宫词》:
白雪猧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其十三)
教来鹦鹉语初成,久闭金笼惯认名。总向春园看花去,独于深院笑人声。(其二十二)④(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增订本)》卷346,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888—3889页。
有趣的是,唐人诗中如果不称“猧”而称“犬”,则大多是在描写乡村田园时将狗作为一个不含个人情感的意象符号,如“篱间犬迎吠,出屋候荆扉”⑤(唐)王维:《赠刘蓝田》,(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增订本)》卷125,第1238页。;“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⑥(唐)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增订本)》卷147,第1481页。;“隔岸鸡鸣春耨去,邻家犬吠夜渔归”⑦(唐)方干:《出山寄苏从事》,(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增订本)》卷651,第7528页。等。唐末五代人卢延让曾有“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饿猫临鼠穴,馋犬䑛鱼砧”“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等诗句,受到文学修养不高的藩镇首领赏识,他对此甚是自得:“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⑧(五代)孙光宪:《北梦预言》,贾二强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4页。在五代诗歌沿袭中晚唐近体诗的入实趣味、平俗意境但格调日卑的情况下,卢延让的“猫儿狗子”诗虽富有浅俗生动的日常生活感,但缺乏诗歌应有的审美内涵与意境,故“人闻而笑之”。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并不把普通猫狗当作应细致观察、描写的对象,更遑论给予其深入参与自身情感体验的地位。在宋诗中,“猧子”一词渐渐不再专指贵族女性钟爱的独特犬种,而是以普通的狗的形象进入诗人日常生活的环境中,成为他们的亲密伙伴,如“尺椽不改结茅初,薄粥犹艰卒岁储。猧子解迎门外客,狸奴知护案间书”⑨(宋)陆游:《书叹二首》其二,《陆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62页。;“闲看猫暖眠毡褥,静听猧寒叫竹篱。寂寞无人同此意,时时惟有睡魔知”⑩(宋)范成大:《习闲》,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227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027页。等。同时,不以美貌著称的一般犬种也能够成为宋代文人的爱宠,如苏轼得于海南并相伴北归的忠犬“乌觜”以及吕本中的爱犬“雪童”,它们虽都因外形而得名,但最得主人喜爱的却是其忠诚机敏的本性。相比昔日在寂静深闺中孤单沉睡的猧子,这些普通的狗因深入文人的日常生活而被频繁书写,它们承载的生活体验与情感内涵要鲜活、真切得多。
鹦鹉诗的创作场合和内涵在唐代就已发生了明显的私人化、文人化的转变。白居易在《双鹦鹉》诗中既夸耀他的宠物“绿衣”“红嘴”的美丽外观,更因“若称白家鹦鹉鸟,笼中兼合解吟诗”①(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朱金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04页。本文所引白居易诗文,文本皆出自此书,不再一一出注。而感到骄傲。鹦鹉仿佛成为了诗人身份、气质和才华的代言,这明显不同于闺中鹦鹉的吟诗,后者不会引起女主人对自身才华的自豪,只会勾起思念和落寞。此外,诗人还会在宠物书写中表达出对动物天性的理性思考,如白居易《鹦鹉》诗云:
陇西鹦鹉到江东,养得经年觜渐红。常恐思归先剪翅,每因喂食暂开笼。人怜巧语情虽重,鸟忆高飞意不同。应似朱门歌舞妓,深藏牢闭后房中。
刘禹锡《和乐天鹦鹉》亦云:“敛毛睡足难销日,亸翅愁时愿见风。谁遣聪明好颜色,事须安置入深笼。”②(唐)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瞿蜕园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53页。他们似乎在惋惜原本聪慧自由的鹦鹉在深笼中被剪掉翅膀无聊度日,实际上也和深锁于朱楼绣户中的人一样在重重束缚中消磨着生命,“人怜”和“鸟忆”的分歧已经越过了单纯的闺情主题。到了宋代,鹦鹉越来越多地作为文人的宠物出现在他们描写个人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的诗歌中。杨亿曾获得一只陇西鹦鹉,“性灵甚慧,触类能言”,出守缙云时也将其携带在身边,“公退玩之,常若不足”③(宋)杨亿:《京师故人有以陇西鹦鹉遗予者因畜养之去年出守缙云提挈而至性灵甚慧触类能言公退玩之常若不足忽遇疾而逝因命瘞于小园作诗一章聊以追悼识者无罪予以贵畜也》,《武夷新集》,徐德明等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页。,这意味着宠物养玩和书写的空间已从假想的闺阁转至士大夫现实生活的宅院中。欧阳修也养有一只鹦鹉,这是他和梅尧臣嘉祐时期诗歌往还的焦点之一,他们深入探讨了人的欲望与鸟的本性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理性思考和讨论成为了宋人宠物书写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
宠物文学的典型语境在中唐以后从宫廷、闺阁逐渐转移到了文人的个人生活中,闺中宠物的意象虽仍时有出现,但宋代文人很快建立起了一套专属于他们自己的宠物书写的话语体系。宠物背后的抒情主人公不再是一个扁平的、假想的女性形象,而是书写者自身;宠物不再仅仅是闺情的传声筒,而成为了文人观照其自身生活经验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媒介,宠物文学的内涵由此得到了重大的开拓。
二、唐代文人宠物养玩、书写的新范式
中唐以后,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热情逐渐让位于个人生活中的现实趣味和闲适态度,宠物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文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因话录》载李约同其所养猿猴“山公”月夜泛舟,琴啸相和④见(唐)赵璘:《因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云仙杂记》载卫济川养六鹤,“日以粥饭啖之,三年识字。济川检书,皆使鹤衔取之无差”⑤(五代)冯贽:《云仙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1页。;《南部新书》载连山大夫张抟为其所养各色宠物猫“自制佳名”,在公务之余与群猫相聚纱帷下嬉戏⑥见(宋)钱易:《南部新书》,黄寿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05页。。不论这些故事的真实程度如何,它们都反映着时人对待宠物的态度,即文人不再仅仅将宠物视为园林的装点或某种象征符号,而是将其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亲密伙伴与情感慰藉,通过宠物养玩来彰显自身的审美格调与人生追求。
与此同时,文人开始切实关注宠物本身的外形、习性、行为以及主宠双方的陪伴关系,并将由此引发的情感体验和哲理思考作为重点书写对象,逐渐确立了一种新的宠物文学范式。前文所引刘、白鹦鹉诗便是此类,而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白居易的双鹤诗,其独特的审美趣味与思理情致在唐代宠物文学中独树一帜,并对后代的宠物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长庆四年(824),53岁的白居易自杭州返洛阳,自求分司,他在杭州任上获得了一块天竺石、一对华亭鹤,将它们视为珍宝随身携带,呵护万分。其《求分司东都寄牛相公十韵》诗云:“万里归何得,三年伴是谁。华亭鹤不去,天竺石相随。”《洛下卜居》诗亦云:“三年典郡归,所得非金帛。天竺石两片,华亭鹤一只。饮啄供稻粱,包裹用茵席。诚知是劳费,其奈心爱惜。……贞姿不可杂,高性宜其适。遂就无尘坊,仍求有水宅。东南得幽境,树老寒泉碧。池畔多竹阴,门前少人迹。未请中庶禄,且脱双骖易。岂独为身谋,安吾鹤与石。”出于按捺不住的“爱惜”之情,他甘愿付出这许多的“劳费”来为它们提供一个适宜的居所,并强调其重要程度甚至不亚于“为身谋”的自我生命之安顿。次年三月,白居易除苏州刺史,一年后他再次带回了一些太湖石、白莲、折腰菱与青板舫,都安置在他的小园林中。随后的两年中他暂居长安任职,于大和三年(829)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这一次,他带回了在长安积攒的粮食、书籍以及精通音乐的歌妓,还有四位友人所赠的酿酒法、琴、《秋思》曲和青石。至此,洛下居所终于布置完毕,白居易开始了闲适自足的晚年生活,他感到十分愉悦,作《池上篇》以歌之:“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吾前。时饮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在白居易看来,鹤与石、莲花、书、酒、琴等都是具有共同性质的玩物,它们被他从各地携带至洛阳的宅院,通过“皆吾所好,尽在吾前”的所有方式为主人提供物质满足和精神愉悦,这些玩物不仅使他的闲居生活充实快乐,还彰显出一种专属于他的风雅格调和诗意情怀。
白居易在诗中常常以“伴”来称呼双鹤,如“白首劳为伴,朱门幸见呼”“秋鹤一双船一只,夜深相伴月明中”“静将鹤为伴,闲与云相似”等。鹤与白居易本人共同栖居的宅院,为他提供了一个相当私人化、日常化的情感体验与文学创作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宠物的养玩与书写同他的生活方式、人生理念融为一体,他将此视为自己独有的精神财富,正如其《郡西亭偶咏》诗云:
常爱西亭面北林,公私尘事不能侵。共闲作伴无如鹤,与老相宜只有琴。莫遣是非分作界,须教吏隐合为心。可怜此道人皆见,但要修行功用深。
大和元年(827),刘禹锡经过白居易在洛阳的居所,因偶遇白居易的另一双苏州白鹤有感而作《鹤叹》二首,其引云:
友人白乐天,去年罢吴郡,挈双鹤雏以归,余相遇于扬子津,阅玩终日,翔舞调态,一符相书,信华亭之尤物也。今年春,乐天为秘书监,不以鹤随,置之洛阳第。一旦,予入门,问讯其家人,鹤轩然来睨,如记相识,徘徊俯仰,似含情顾慕,填膺而不能言者,因作《鹤叹》以赠乐天。①(唐)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第1059页。
白居易答之云:
辞乡远隔华亭水,逐我来栖缑岭云。惭愧稻粱长不饱,未曾回眼向鸡群。荒草院中池水畔,衔恩不去又经春。见君惊喜双回顾,应为吟声似主人。
原本是白居易将双鹤带离故乡又将它们搁置在洛阳后离去的,他却将这一行为描写成双鹤为了他而辞别故乡、千里远行、久候不去,而他也为自己冷落它们感到愧疚,甚是思念。白居易对鹤的喜爱、呵护与眷恋,与鹤对他的依赖、陪伴与安慰,构成了双向的情感互动,这使得双鹤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宠物。
随着宠物养玩与书写同文人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宠物开始成为了文人社交活动中的重要媒介。白居易的双鹤不仅引来了刘禹锡的赠答,还引起了裴度的“觊觎”,促使他作诗向白居易索要双鹤,而刘禹锡也参与其中进行斡旋。杨晓山《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一书曾深入解读过这场纠纷中三人的地位、心理与创作动机,称:“在双鹤转手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不是作为禽鸟栖息地的两座园林之间的优与劣,也不是禽鸟和主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裴度、白居易和刘禹锡之间的社会关系。”②[美]杨晓山:《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第136页。白居易最终不得不将这对鹤转赠于裴度。再度回归洛阳后,他“归来未及问生涯,先问江南物在耶”。同样来自苏州的石笋、莲花、石舫等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尚且都安在园中,真正令他无比惆怅的是“月明双鹤在裴家”。若干年后,一位苏州故吏来访,白居易怅惘道:“不独使君头似雪,华亭鹤死白莲枯。”他曾拥有、珍爱过的这些玩物,终于都随着年华光阴一同逝去了。宠物引起的文人社交在唐代屡见不鲜,但白居易的事例仍然十分特殊,他毫不掩饰自己醉心于玩物且难以释怀的态度。
唐代文人为宠物养玩与相关创作确立了文人化、日常化的新范式,文人对宠物的照料、逗玩与书写无不体现着其对物质、精神追求及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宋人在此基础上逐渐淡化白居易曾标榜的物质满足感,代之以更加细腻平实的日常生活体验与丰富的理趣情思,将宠物文学的精神内涵与品质格调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三、宋代的宠物养玩风尚与文人书写的新经验
宋代笔记、小说中关于都市中繁荣的宠物市场、商业活动和热门品种的记述直观呈现出当时新鲜、热闹、充满商机的宠物潮流。《东京梦华录》记载相国寺每月的民间交易市场,“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养犬则供饧糟,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①(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23页。;《梦粱录》记载了当时最受达官贵人珍爱的宠物猫,“长毛白黄色者,称曰狮猫,不能捕鼠,以为美观,多府第贵官诸司人畜之,特见贵爱”,当时还有专门“以异样龟鱼呈献富豪”的“鱼儿活”②(宋)吴自牧:《梦粱录》,第290—291页。;《西湖老人繁胜录》详细介绍了在集会上参与斗戏养玩的诸多虫鸟品种以及临安诸行市中的“修飞禽笼”“医飞禽”③(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5页。等服务;《武林旧事》记载了杭州市场上特有的“小经济”,包括猫窝、猫鱼、改猫犬、鸡食、鱼食、虫食、诸般虫蚁、鱼儿活、蝌蚪儿、促织儿等,并称“若夫儿戏之物,名什甚多,尤不可悉数”④(宋)周密:《武林旧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52—453页。。宋代都市中的著名寺院常饲养金色的鲫鱼或鲤鱼以供观赏,《梦粱录》《咸淳临安志》中皆有记载。岳珂《桯史》还记载了当时临安人有专门培育金鱼的秘法,“贵游多凿石为池,寘之檐牖间以供玩”,这种喜好“承平时盖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⑤(宋)岳珂:《桯史》,吴启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3页。。这些记述表明观赏、逗玩动物的休闲娱乐方式在两宋都城中持续流行,宋人以称赏的目光将这些“儿戏之物”视为繁华富庶的象征。这种流行风尚源于城市经济发展及坊市隔阂消除,同时还与当时博物知识的广泛流行密切相关。宋初编纂的两部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中都有专门的兽、禽、鳞介、水族等分类,大量收录前代关于猫、犬、兔、鹦鹉、孔雀、白鹇、鹤、龟、鱼等各类动物的饲养、实用历史及相关传奇故事。《孔氏谈苑》《萍洲可谈》《苕溪渔隐丛话》《四朝见闻录》《桂海虞衡志》等两宋笔记中皆可见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驯养、赏玩各类新奇鸟兽的现象。这种文化潮流很容易推动宋代文人将认识、观察动物的兴趣转化为日常生活中亲自饲养并进行相关创作的实践。
宋代流行的宠物不论是大部分常见的种类还是细心呵护的饲养方式都与今人并无太大差异。在宋诗中,普通以猫狗作为生活助手、田园意象和文人爱宠的形象时时交错出现,其原本的实用功能与作为宠物所特有的赏玩娱乐、情感慰藉功能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文雅情趣与平实体验并存其中,催生了一种新的富于感悟思考的日常审美趣味。作为宋代热门宠物的猫逐渐卸下了捕鼠的重任,却并未因此招来太多尸位素餐的批判,反而以其慵懒、娇憨之态赢得了主人的溺爱。胡仲弓《睡猫》云:“瓶中斗粟鼠窃尽,床上狸奴睡不知。无奈家人犹爱护,买鱼和饭养如儿。”⑥《全宋诗》卷3335,第39806页。方岳《猫叹》云:“雪齿霜毛入画图,食无鱼亦饱于菟。床头鼠辈翻盆盎,自向花间捕乳雏。”⑦《全宋诗》卷3197,第38307页。林希逸《麒麟猫》题下小序称:“新得狸奴满口皆黑,人谓含蝉,甚佳。绝不能捕,戏以号之。”⑧《全宋诗》卷3122,第37298页。相比捕鼠之功,他的兴趣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这只猫独特的外貌上。宋代最高产的爱猫诗人当属陆游,猫之于陆游的重要性不亚于鹤之于白居易,他们都反复强调宠物所具备的“伴”这一特别身份,而猫同陆游的亲昵程度比鹤与白居易更深。陆游给他的三只猫取名为“粉鼻”“雪儿”“小于菟”,它们兼具“怒髯噀血护残囷”的精悍和“日饱鱼飱睡锦茵”①(宋)陆游:《赠粉鼻》,《陆游集》,第768页。的慵懒,其“时时醉薄荷,夜夜占氍毹”②(宋)陆游:《赠猫》,《陆游集》,第1087页。的可爱之态令人忍俊不禁。它们是陆游参禅、读书、排遣寂寞时最亲昵的伙伴,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一云:“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氊暖,我与狸奴不出门。”③(宋)陆游:《陆游集》,第710页。可以想象在无数个“夜阑卧听风吹雨”的不眠之夜,乖巧驯顺的猫都为诗人提供了微小而又温暖的慰藉。类似的宋诗还有很多,如“狸奴木上坐,相对成二客。殷勤谢尔曹,伴我此岑寂”④(宋)周孚:《夜坐偶作》,《全宋诗》卷2480,第28739页。,“会当与狸奴,曲肱分坐席。急雪度寒飙,夜窗鸣淅沥”⑤(宋)周紫芝:《砖炉》,《全宋诗》卷1510,第17206页。,“江上孤篷雪压时,每怀寒夜暖相依”⑥(宋)张良臣:《祝猫》,《全宋诗》卷2461,第28459页。等。宋人爱狗与爱猫不分伯仲,而狗原本的忠诚品格和比猫更依赖主人的习性,让它们能更自然地兼具守护保卫和陪伴慰藉两种功能,也更容易获得主人的深情呵护。苏轼的“乌觜”是他在海南的忠实伙伴,“昼驯识宾客,夜悍为门户。知我当北还,掉尾喜欲舞。”苏轼对此非常感激,同它跋山涉水一道北归,饶有趣味地记录它“跳踉趁童仆,吐舌喘汗雨。长桥不肯蹑,径渡清深浦。拍浮似鹅鸭,登岸剧虓虎”的鲜活动态,这一人一犬的组合引得“路人皆惊”⑦(宋)苏轼:《余來儋耳得吠狗曰乌觜甚猛而驯随予迁合浦过澄迈泅而济路人皆惊戏为作此诗》,《苏轼诗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64页。。吕本中的爱犬“雪童”在一个夏日暴毙,他一共写了7首诗来追忆它,充满了挥之不去的内疚和伤怀,其中还有像“客至书来总不知,却缘迩日吠声稀。蛛丝网遍常行处,犹道奔逃未肯归”⑧(宋)吕本中:《又作二绝》,《全宋诗》卷1623,第18216—18217页。这样伤痛至极、难以接受现实的心理描述,而随后的《怀雪童》更表现出“从此穷居添寂寞,夜长谁复绕帘帷”这样几乎逼近了“谁复挑灯夜补衣”的悼亡之痛。可以看出,文人乡居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不仅对猫狗原本的护卫功能仍有需求,还容易对每日陪伴自己的这些小动物产生亲近、爱护之情,久而久之自然会生出双向的情感依靠和慰藉,文人描写这些动物的视角也因此发生了重要转变,“猫儿狗子”获得了远比前代鲜活动人的文学生命。
宋人的宠物书写除了聚焦于自身的日常生活,还常常关注市井民间、权贵豪门乃至皇宫中关于宠物的潮流风尚和传说故事。洪迈曾在《夷坚三志》“乾红猫”一条下记载临安市民孙三将普通白猫染为红色并大肆造势进行商业欺诈的行为。⑨见(宋)洪迈:《夷坚三志》,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73页。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秦桧的孙女极为钟爱的狮猫逃脱,秦桧令临安府限期寻回,“及期,猫不获,府为捕系邻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猫,凡狮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赂入宅老卒,询其状,图百本于茶肆张之。府尹因嬖人祈恳,乃已”⑩(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2页。。事实上,两宋之初的皇帝都曾明确表示过对进贡、采买珍禽异兽的禁止和批评,然而先祖的诏令并不能有效约束后代的每一任君王以及社会各阶层,在《夷坚志》中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前去重金购买红猫的内侍、徽宗奢华园林中的“鹤庄、鹿砦、孔翠诸栅,蹄尾以数千计”11(宋)洪迈:《容斋随笔》,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82页。,以及秦桧全城搜捕狮猫的荒唐事迹,这些真假相掺的笔记小说曲折透露出了文人面对时俗狂欢潮流时所持的冷静、警惕的态度。不过不可否认,正是文人宅院之外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潮流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呼吸的空气,他们从前代继承而来的日常生活与文学书写的兴趣种子,在这种空气中迅速萌发并茁壮成长,使宠物文学的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拓宽。
四、宋代宠物文学情理内涵与审美趣味的开拓
宋代文人对宠物文学的发展除了表现在上述众多新鲜的社会生活体验和文学书写经验之外,还集中于对宠物文学内部的开拓。正如前文所述,许多文人会通过笔记小说对珍稀宠物引发的社会风气与特殊事件进行道德层面的褒贬评判,最极端的做法就是将宠物的问题与民族、王朝的兴亡挂钩。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载泸南有人养秦吉了,因不愿被卖夷中而自戕。①见(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8—189页。传为高宗所作的《祭赤鹦鹉文》②此文《全宋文》据明《文章辨体汇选》及清《宋稗类抄》收之,见第205 册,第172页。,所祭的对象是一只出身于徽宗宫廷、每日提醒他勿忘二圣的神鸟,道德教化的意义在皇帝的宠物身上被提升到了极其崇高的境界。这一新视角体现出了宋代文人在观察记录日常见闻时普遍秉持的理性意识和道德尺度。大部分亲身从事宠物养玩和书写的宋代文人都并不像白居易那样将费心搜罗、占有各种珍贵玩物的过程和满足感付诸文字,反而要通过各种“策略”来淡化宠物的商业价值,如陆游就选择了与他所批评的秦家狮猫具有天壤之别的普通田园猫。还有很多文人虽饲养热门或名贵的宠物,却并不夸耀它们的身价,而是着意于发掘宠物背后的哲思理趣、精神寄托甚至人性与自然的纠葛矛盾。宠物文学因此获得了真正“与时异趣”的内涵特质,具有了超越前代的思想深度。
宋代宠物文学中比较独特的书写对象是观赏鱼、龟等水生或两栖类动物,这或许是最缺乏直观乐趣的一类宠物了。它们无法像猫狗禽鸟一样和主人亲密互动,需要通过相对静态的观赏、观察来获取乐趣和思理,而这种距离恰好提供了理性思考所需的空间。文人关注的对象不仅是宠物本身,还遍及个人生命、社会历史和宇宙自然之道,将闲适愉悦与哲思理趣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实际上是宋代文人对白居易式宠物养玩、书写的改造和发展,如喻良能《绿毛龟》诗云:“白玉盆中浅更清,绿毛浮水斗轻盈。须臾食罢浑无事,自上盆山顶上行。”③《全宋诗》卷2356,第27047页。诗人细致观察并描写宠物的生活动态,甚至揣摩其心理,一种浓厚的格物、观物兴趣渗透在字里行间,观察和思考本身就足够带给诗人丰富的精神乐趣。当这种观赏好尚同已经相当普遍的园林盆池之好结合在一起,本应身处湖沼中的龟、鱼便同其现实所处的盆池一道承载起主人对江湖山林与身心自由的向往或追怀,例如欧阳修于明道元年(1032)在洛阳建非非堂,种竹、设榻、藏书、开池,购买了几十条鱼养于池中,映照自己的“江湖千里之想”④(宋)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洪本健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82页。。但有限的人工营造空间必然会对自然生命造成拘束,曾几在其《白龟》诗中曾对其宠物龟许以“会当放汝江湖去”的承诺,却又因不舍之情令其不得不“小住盆池慰眼前”⑤《全宋诗》卷1659,第18593页。。宠物“多因名色误,不得泳江湖”⑥(宋)释元肇:《金鱼》,《全宋诗》卷3089,第36874页。的命运恰好同庄樗之无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关于圈养与放生的纠结则常常成为文人自身仕与隐、出与处、现实与理想之间矛盾的缩影。
最能体现宋代宠物文学对前人写作经验的深化和超越的,是围绕鹦鹉、白鹤、白兔等宠物的创作。它们或是已被前人反复书写过,又或是本身已成为内涵稳固的文学意象,这些内容在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手中被改造得更加复杂而深刻。欧阳修、梅尧臣、谢绛等人早年在钱维演幕下就其所养的红鹦鹉各自作赋抒发见解。到了嘉祐年间,围绕在欧阳修身边的文人们继承了这一模式并发展成为一场时间持久、规模盛大、兼具文学性和娱乐性的集体活动,其基础依然是继承自白居易式的入实趣味和哲理感怀,但其文学内涵的丰富和理性思考的深度都远远超过了白诗中的现实满足与愉悦。欧阳修的白兔、白鹇、白鹦鹉分别来自滁州乡民、友人梅挚和注辇国使者的馈赠,这些礼物象征着他们对欧阳修的爱戴、欣赏或崇敬之情,其情感纪念意义上的珍贵是市场价格的昂贵无法比拟的。这三种宠物还有着共同的审美特点——“白”,其外观洁白可爱,象征着主人清高无瑕的道德操守和不同流俗的典雅品味。欧阳修对此也有颇多赞美,如“皎洁胜琼瑶”①(宋)欧阳修:《思白兔杂言戏答公仪忆鹤之作》,《欧阳修诗编年笺注》,第1312页。本文所引欧阳修诗,文本皆出自此书,不再一一出注。、“高怀自喜凌云格”等,这足以让他骄傲地把它们展示给众多的友人并邀请他们进行相关的创作。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邀请了梅尧臣、刘攽、刘敞、韩维、苏洵、王安石、裴煜等友人赏兔作诗,其中“诸君所作,皆以常娥、月宫为说”,而梅尧臣的《永叔白兔》《戏作常娥责》《重赋白兔》三篇最具新意,打破嫦娥、月宫旧说,以韩愈《毛颖传》为基础展开想象,“高出群类”②(宋)梅尧臣:《重赋白兔》,《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00页。,深得欧阳修赞赏。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锁院期间和韩绛、王珪、范镇、梅挚、梅尧臣唱和赠答不断,其中就有不少围绕宠物的诗歌。欧阳修和梅挚毫不掩饰自己对家中爱宠的挂心与思念,频繁以“忆鹤”“思白兔”为题进行酬唱,梅尧臣也参与其中,互相调侃戏谑,欧阳修称这些宠物的妙处在于“不惟可醒醉翁醉,能使诗老诗思添清新”。他们不仅赋予了宠物重要的文学“使命”,也令这两场宠物诗唱与当时的文学革新活动相得益彰。③关于这两次唱和活动中诸人的身份、地位、彼此之间的关系、各自的文学创新实践以及活动本身的文学史意义,可参看吕肖奂《宋代唱和诗的深层语境与创变诗思——以北宋两次白兔唱和诗为例》。随后的两年中,欧阳修的友人们还有几次围绕宠物的赏玩唱和活动,虽然规模很小,但也可视为彼时“群诗名貌极豪纵”的延续和尾声。那场盛会直到百年之后都还令人神往,南宋诗人林希逸曾效仿梅尧臣作《戏效梅宛陵赋欧公白兔》,盛赞当年“传夸瑞物遍都邑,倡和千篇模写工”④《全宋诗》卷3120,第37265页。之景况,他大概想象自己也参与其中并共享快乐。欧阳修等人对宠物的赏玩、书写并不止步于获得身心愉悦,而是进一步走向了关于自然天性和士人道德的思考。至和二年(1055)欧阳修初获白兔时就已感慨“天资洁白已为累,物性拘囚尽无益”。一年之后兔子死去,他十分愧疚自责“养违其性夭厥龄”,继而叹息他的白鹦鹉“渴虽有饮饥有啄,羁绁终知非尔乐”。这与当初白、刘二人咏鹦鹉的感慨异曲同工,但其作为主人对自身矛盾心理的剖白令这种感悟更加痛切。欧阳修的思考不仅面向物性,更面向人性。在嘉祐二年的唱和中,梅尧臣曾调侃欧阳修和梅挚挂心于宠物的行为是一种“物惑”,欧阳修对此的解释是“所好虽与时异趣,累心于物岂非情”。他认为作为士大夫应具有独立于时俗好尚之外的审美趣味和精神追求,同时又不否认文人个体对“情”的体验和珍重。类似的还有杨亿悼念鹦鹉之作,他在诗题的末尾特地声明了一句“识者无罪予以贵畜也”。正是因为清楚士人在玩物尺度上应有的自我道德约束,他们才会担忧自己的行为招来非议,才会努力通过强调宠物为他们带来的乐趣与主宠之间的深情来为自己辩护,他们玩物、观物、咏物的活动之中始终交织着情与理的不断冲撞与互相妥协。
综上所述,宠物书写作为唐宋文人士大夫所热爱的相对远离时俗喧嚣、雅致而充满乐趣的休闲娱乐生活的衍生品,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鲜又热门的文学话题,广泛吸收各类社会生活见闻和文化知识,积累了可观的书写素材,在实际创作中又与士人群体逐渐形成的理性精神、道德追求及文学理念紧密结合在一起,最终发展成为“与时异趣”的士人精神载体。士大夫通过私人日常生活中对宠物养玩活动的深入体验,以及对个人生活之外的社会风潮的冷静审视,构建出了宠物文学中真切动人的情感体验和深刻透彻的理性思辨,赋予其独特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