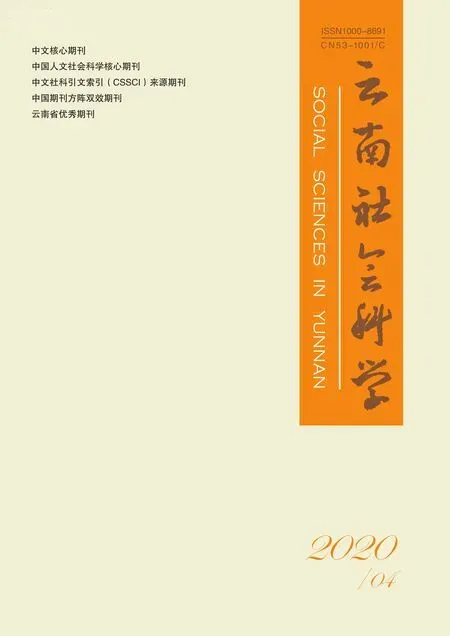通商口岸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以云南为例
2020-02-21肖建乐王明东
肖建乐 王明东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尤其是工业革命的推动,促使世界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区域的乃至世界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则逐渐沦落为外围,形成了“中心—外围”理论;①肖建乐:《云南近代通商口岸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出于全球掠夺原材料和建立产品倾销市场的考虑,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开埠通商,在中国即建立了100多个通商口岸,具体到某一国或者某一区域而言,通商口岸成为了中心,其他区域成为了外围。如何认识这两个层面的“中心”与“外围”关系及作用,就成为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云南边境三个重要城市蒙自、思茅、腾越(腾冲)分别于1889年、1897年、1902年相继被迫开埠通商。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时期,也是自身因素影响和西方力量影响的交汇期。深入探讨云南三城市开埠通商对于近代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助于理解通商口岸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著名学者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以“冲击—回应”为命题线索,揭开了研究口岸城市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自身因素和西方影响这两个因素的作用。②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China Coast,1953.费正清及其之后的“哈佛学派”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变迁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罗兹·墨菲的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提出了在口岸城市中形成的中国本土环境与西方冲击中的互动关系。①[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页。王文成论述了云南在约开商埠后,通过改造传统的边境贸易网络,从而使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部结构也演变为以通商口岸为依托、以全球性、综合性的世界贸易为主体、以边境贸易、边民互市和走私贸易为补充的近代对外经贸关系。②王文成:《约开商埠与清末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的变迁》,《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一、开埠通商后云南商贸的发展
随着近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处于边疆的云南成为列强觊觎的对象,加快了对云南的入侵步伐,1889年蒙自被划为通商口岸,1897年、1902年思茅和腾越被分别强制要求开关通商,随之进出口商品的规模迅速发展,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进出口商品的发展
从进出口商品的价值来看。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历史上形成了经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经越南的海上贸易通道,对外贸易发展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开埠通商以后,进出口贸易数量增加很快。以蒙自口岸为例,“1899年蒙自开关之始,进出口总值仅有14.99万平银两,到1899年即增至547万多关平银两”③云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云南省志》卷16《对外经济贸易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页。。城市经济也发展很快,1889年以前蒙自城区人口只有几千人,到1896年城区人口增加到1.2万人,1904年更是增加到4万多人。蒙自口岸进口商品以棉纱、布匹最为大宗,棉纱约占57%,出口则以大锡为大宗,约占总额的81%。从年均贸易增长率看,蒙自为7.63%,腾越为3.84%。以香烟输入为例,1901年“尚无纸烟入口,及1906年其输入之货值1.0998万两;至上年(1910年)增至2.9914万两;本年(1911年)竟加至4.3329万两”④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2 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30页。。5年间香烟入口货值增加了4倍,其增加速度是惊人的。全省进出口的贸易货值,据李珪和梅丹统计,“蒙自关从1890年的927282海关两增加到1911年的11398300海关两,增加了11倍;思茅关从1897年的185974海关两增加到1911年的235208海关两,增加26%;腾越关从1902年的661695海关两增加到1911年的1684213海关两,增加了一倍半。”⑤李珪、梅丹:《云南近代对外贸易史略》,《云南文史资料》(第42 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页。“从1890年到1931年,云南对外贸易进、出口货值分别从466089海关两和461193海关两增至8498686海关两和7184478海关两,后者分别是前者的18.23和15.58倍,其货值增加之巨不可谓不惊人。”⑥杨伟兵:《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第四卷《西南近代经济地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4页。与全国同期比较,云南1889年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分别为10万美元和7万美元,各占全国出口总值的0.10%和0.05%;1920年上升为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7%和进口总值的1.8%。⑦李珪、梅丹:《云南近代对外贸易史略》,第2页。
从进出口商品的种类看。近代以前,云南进出口贸易商品不足百种,开埠通商后,迅速上升至千余种,传统商品除棉花继续成为大宗进口货物之外,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工业品则居于主导地位,出口则大多为原材料和矿产品。自三关开埠通商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进口年均增长率为3.22%,出口则为9.64%。出口货物分为矿产原料、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三大类。其中,“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发展,对锡的需要大为增加,刺激了锡生产的发展。1917年云南锡出口首次达到11223吨的高点,价值1192.7万美元,占出口总值的79.2%,与1889年相比,出口数量增加42.8倍,价值增加143倍”⑧云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云南省志》卷16《对外经济贸易志》,第47页。。以矿产和农副产品作为交换物的云南对外贸易,既反映了当时生产的落后状况,又说明云南是西方列强的工业品倾销地和原料供给地。
正如袁国友所说:“自光绪十五年蒙自开关至辛亥革命以前……此时的云南对外贸易,已被纳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之中。”⑨袁国友:《论近代前期的滇港经贸关系》,《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开埠之后……仅通过蒙自香港之间的口岸贸易就占到了云南对外贸易总额的60%左右”①郭亚非:《近代云南与周边国家区域性贸易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由此可见开埠通商对云南贸易的推动。由于贸易主导商品的单一性,对外贸易极易受到来自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压低大锡价格和抬高棉纱倾销价格来达到操纵云南对外贸易的目的。从近代国际市场大锡、棉纱交易情况看,大锡价格逐年下降,棉纱价格逐年上扬,两种大宗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差异,成为左右云南对外贸易顺逆的决定因素,每当大锡价格下跌、棉纱价格暴涨,对外贸易必定呈现逆差,反之则为顺差。因此,大锡、棉纱两种大宗商品的多寡,不仅制约着云南全省对外贸易的规模,而且决定着全省贸易顺逆差的程度。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云南对外贸易发展史中,前资本主义时期对外贸易交换物品大都是供生活性消费的产品。明清以前,在云南进口商品中,珠宝、玉石、琥珀、犀角、象牙、海贝所占比例很大,明清以后,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各种奇珍异宝资源日益匮乏,这些珍稀物品的进口日益减少,而满足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各类物品的进出口则显著增加。这充分体现了贸易双方的互补性,这也是早期对外贸易的一大特征。开埠通商以来,平等互利的传统对外贸易格局被打破了。
蒙自口岸在三口岸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进出口商品种类繁多。进口商品尤以棉纱、棉花、纸张、煤油、烟类、海味为大宗,棉纱又居于进口货物之首,经常达到贸易额的一半以上。居于二三位的一般是烟丝和棉花,烟丝和棉花最多的时候也只有棉纱的一半,可见棉纱在蒙自进口商品中的垄断地位。蒙自口岸的出口商品中大锡、铅、锌、猪鬃、茶叶、皮革、火腿、药材为大宗。其中大锡长期居于垄断地位,常年达80%以上,甚至有的年份达95%以上,其余商品的出口值比重极低。可见蒙自的商品出口与进口一样具有单一性特征,大锡的垄断地位远高于棉纱。
思茅口岸主要的进口商品为棉花、缅甸梭罗布、鹿皮、煤油、鹿角、棉纱等,其中棉花进口数量最多,为大宗进口货物,其他商品数量少且变动幅度大。思茅口岸的出口商品中以普洱茶最为大宗,“滇南思普一带恒以花茶为大宗,而坐贾行商无不争利于二物内”②周钟岳、赵式铭等:《新纂云南通志》卷144 《商业考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点校本,第7 册,第111页。。但是思茅产的普洱茶不太适合西方人的口味,因此出口市场受到制约,数量和货值在多数年份都不高,也仅是与其他商品相比较,“惟茶叶尚可称述耳”③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1985年,第575页。。
腾越进口货物主要来自缅甸、印度,以棉纱为最大宗,棉花也是腾越进口之重要商品。腾越口岸出口商品以黄丝、药材、牛羊皮、土布等为主。英国占领缅甸前,缅甸的棉花主要输往云南,在英国占领缅甸之后缅甸的棉花就开始大量输往印度,因为英国为了发展殖民地经济在印度大力发展棉纺业,从而缅甸输往云南的棉花就受到了一定限制。同时,从印度经越南进入云南的棉纱以价廉质优而受到广泛的欢迎,尤其是在开埠以后,更是迅速占领了市场,严重打击了土纱,棉纱成为腾越口岸进口的大宗商品。
(三)不平等贸易的影响
清末到民国时期,世界格局、云南地区社会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外部力量介入,形势变化很快。三口岸城市的进出口贸易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有一种商品占据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商品的贸易数量和贸易额的增减对地区经济有重要影响。如棉花决定思茅贸易额的起伏,黄纱则左右了腾越的兴衰。在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过程中,中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云南以原材料换取西方商品,成为了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主要形式。掠夺原材料资源和倾销工业产品成为西方列强开埠通商的主要目的,严重制约了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为倾销西方的工业品,中国的进口税率不断压低,“一般说来,当时中国进口税率水准只及美国六分之一”④姚贤镐:《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主权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随着贸易的发展,云南大量的原材料被运至西方,西方所产的洋货充斥着云南市场。仅据云南三海关的不完全统计,20世纪20年代,输出的农副产品达90余种,矿产品近20种,其他货物若干;输入品300余种,仅纺织品就有70多种。同期,经思茅口岸输出的有农副产品90余种、矿产品7种,输入品70余种。腾越口岸输出农副产品120多种,内含矿产品8种,输入200余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云南出口的7种大宗产品蚕丝、牛羊皮、茶叶、药材、桐油、大锡均为原材料,其货值累计占全省出口总值的95%以上。其中云南大锡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搜刮的最重要的原材料之—。进口商品中,开埠初期形成的7种大宗商品有6种为工业制造品,仅棉花一项为初级产品。20世纪30年代开始,机器及零部件、交通工具、电力设备、汽油、柴油、电石、搪瓷器皿、水泥建材等工业制品也大量进口。这样,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输入工业制品、云南大量输出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材料的不平等贸易格局。在洋货的充斥下,土货市场日渐萎缩。由于进口商品充斥,土货市场多为洋货所挤占,百姓日益贫苦。
在贸易商品结构变化的同时,商品价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口工业制品价格往往大大高于其价值出售,出口的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材料却常常是被迫以远远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造成进出口贸易商品价格的剪刀差。这种不等价交换,使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在正常贸易中得不到的高额利润,云南却在这种不等价的贸易中损失惨重。以棉纱、大锡为例,在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棉纱价格呈现逐年上涨之势,大锡价格却逐年下跌。进出口市场价格受列强操纵,以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销售。茶叶出口价格逐年下滑,大锡出口价格被不断压低,事实上失去了出口商品的定价决定权,处于完全受制于人的境遇。云南种植业也开始受制于西方,“鸦片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向东南亚出口,成为云南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①[美]戴维·纽金特:《封闭的体系和矛盾:历史记载中和记载外的克钦人》,见云南民族研究所编印:《民族研究译丛》,1983年,第152页。。云南渐渐变为了资本主义的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材料供应地和工业品的倾销市场。
随着云南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漩涡,不平等的对外贸易格局逐渐形成。马克思认为:“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中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②[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8页。近代西方列强对云南的不平等贸易,正代表了这种商业资本的掠夺制度。
二、世界分工体系视域下云南区域经济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社会分工的发展史。分工带来专业化的发展及其对交易的依赖程度加深,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促使交易半径和市场规模扩大,这反过来又促进交易效率改善。
云南近代三通商口岸的开辟是当时经济全球化和帝国主义倾销商品的必然结果,随着形势的发展,云南逐渐融入世界贸易分工体系。③肖建乐:《云南近代通商口岸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由于分工是比较优势和交换的力量促成的,所以分工和贸易必然受到交换能力范围的限制。
通商与开放改变了云南人的生活习惯,如就医观念、就业观念,时空和地理观念,使近代科学、民主的思想渐入人心。口岸通商以后,民众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包括对世界和对自身的认识。相对中国其他地方,云南开放较晚,但是三口岸通商以后,尤其是滇越铁路修通以后,民众的思想观念转变较快,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护国运动的发起上。
开埠通商进一步瓦解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创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催生了近代工业。开埠通商解放了云南的生产力,释放了被抑制的商业资本,增强了要素流动,为云南近代化发展创造了历史机遇。同时,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为近代工业发展提供了文化保障。种植业、手工业、近代工业都面临着东南亚和背后西方列强近代化生产方式的竞争压力,区域间要素流动加大,比如四川的劳动力到云南务工,缅甸和印度的棉纱在云南加工,传统商号积累的商业资本开始投资于矿业、纺织业,等等。通商后大量四川移民同价格低廉的印度棉纱一起进入到云南,催生了云南的织布工业,“从云南南部几乎全民所穿衣物均由印度棉纱制成,可以看出外来棉纱对云南市场的冲击”④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页。。国外商品的倾销促使云南生产改变了自给自足的局面,转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云南在晚清时期就形成了腾越帮、鹤庆帮等大大小小的商帮,与其他省份的交往日益频繁,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传统市场。“云南省际贸易之途径,迤东一带,与川黔交往频繁,而以昭通、曲靖为货物聚散之中心;迤南一带,则与两广、上海交易,以蒙自、个旧为货物聚散之中心,迤西一带与康藏发生交易,以下关、丽江为货物聚散之中心;全省多以昆明为出纳之总枢纽。”①周钟岳、赵式铭等:《新纂云南通志》卷144 《商业考二》,第7 册,第108页。蒙自开关之后,尤其是滇越铁路通车之后,涌入了大量的洋货,这些洋货大多在云南省内被消费,说明云南当时的消费水平已经与商品经济相适应。“随着铁路铺设,外国商品与外国货币涌了过来,洋行的招牌陆续出现在昆明街头,如广聚街的若利玛洋行、徐壁雅洋行、三市街的郭米纳洋行。”②李埏:《滇越铁路半世纪》,《云南日报》1957年4 月14 日。商帮的发展和近代转型,各国洋行在云南纷纷成立并成功运转,一定程度带动了云南工商业的发展。
铁路的修建促进了近代云南经济发展。滇越铁路通车以后,云南到东南亚的交通时间大大缩短,从昆明到蒙自由原来的9天缩短到2天,滇越铁路成为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通向东南亚、走向国际市场最为便捷的通道。除了缩短时间,滇越铁路更为重大的意义是货运能力的大幅提升,1920年全线机车达85台,通车初期,年均货运量在10万吨左右,1925年到1931年的七年间,货物累计运量达222.6万吨,年均31万吨。③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中册,第1013页。滇越铁路对云南对外贸易、居民出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千年的传统交通方式。1911年到1913年的3年里云南省进出口总额达5872.41万关平两,比通车前三年净增长2243.49万关平两,增长了61.8%。在三口岸中,与滇越铁路联系最密切的蒙自增长速度最快,而昆明至广西北海的商路则日渐衰落,“1889年蒙自开关后逐渐衰落……滇越铁路通车后,进出口贸易额又进一步减少”④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 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页。。滇越铁路的修建虽没有能全面提升云南的交通水平,但带来的交通条件改善是极其巨大的,直接导致了云南对外贸易进口由棉纱、烟丝、煤油、纸张等向汽车、机械设备、机械零件、水泥等工业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扩展,出口逐渐从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品向初、精加工产品过渡。滇越铁路推动了云南近代化进程,使得云南进一步融入到早期经济全球化浪潮中。
1889年蒙自开关之后,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主导下,云南传统经济逐步瓦解,这一时期云南对外贸易成为了区域要素流动的桥梁和内外因素交织和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实即经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过程”⑤吴承明:《中国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6页。。蒙自开关,尤其是滇越铁路开通以后,大锡出口更加方便,销往东南亚就成为了主要的途径,此后大锡一直是云南主要的出口商品。大锡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料,成为西方列强谋求的云南财富之一。尽管大锡作为原材料其价格被西方列强大大压低,但是大锡贸易对云南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拉动作用,促使云南从传统经济走向近代经济。
云南近代工业的开端一般认为是1884年由云贵总督岑毓英开办的云南机械局。三口岸通商到辛亥革命前后,受到革命活动与发展工商业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舆论氛围。云南一些商号、地主、作坊主、官僚,感受到国家衰落与国外近代工业生产力的强烈对比,掀起了一股投资办厂的热潮,民办工业一时间风生水起。从通商后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云南轻工业包括了火柴、卷烟、纺织、印刷、制革、食品加工、机械、造纸等部门。虽然规模有限,“所设各工厂中机械,多者十余架,少者数架,强半助以手工。至市内工厂,合计约50余所,职工不过二三千人”⑥张维翰、童振藻等:《昆明市志》,昆明:昆明市政公所总务课排印,1924年,第100页。。由于投入相对低,加上省内市场对轻工业品需求旺盛,因而吸引了很多传统商号投资于轻工业中。如1908年永昌祥在下关开办茶厂,各商号开始纷纷效仿,下关涌现出了10多家茶厂,旺季雇佣工人达五六千。⑦梁冠凡等:《下关工商业调查报告》,《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37—138页。1917年商人王怀庭于下关创办济兴火柴厂,生产玉龙牌火柴,1921年商人张南溟在腾越创立腾越火柴厂,资本4万余,销路较好。①张绍良、李典章:《滇西火柴工业简史》,《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 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0页。这样,蕴藏在民间的商业资本力量也得以释放,促进云南走上了近代工业发展道路。
随着开埠通商的发展,云南口岸城市逐渐纳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体系,地域分工成为口岸城市发展重要推动力。所以,从社会分工的发展来看,不仅云南口岸城市,甚至云南的相当一部分地区都卷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体系,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社会发展规律性。
三、推动三通商口岸发展的中西力量对比
云南口岸城市发展过程中,外部因素和中国内部因素都在起作用。
(一)外部因素
近代化与经济全球化核心的推动力来自西欧,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需要在世界范围寻找原材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客观上需要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他国经济资源,形成统一的全球市场。发达国家处于劳尔·普雷维什“中心—外围”理论中的中心位置,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处于外围位置。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西方因素对云南口岸城市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外来商品充斥市场,云南传统经济体系被打破,新的经济体系难以建立。从西方列强打开云南大门的根本目的来看,其并不希望口岸城市真正完成近代化,而是永久性地充当中心与外围的缓冲地带,为其进一步扩大对内地的资源掠夺和商品倾销而服务。
“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②[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9—370页。对云南影响较大的外国资本是英、法资本,其特点是既追求利益最大化又服务于列强的侵略活动。因此其对三通商口岸的作用是一方面促进了新产业的兴起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列强的介入也严重阻碍了三口岸城市完整系统经济体系的建立,导致了云南经济的畸形发展。滇越铁路通车之后的10年里,法、英、美、日、德等国先后在昆明开设了34家洋行,其中法国洋行最多。③云南省经济研究所:《云南近代经济史文集》,昆明:经济问题探索杂志社,1988年,第109—112页。列强商品的输出和洋行的建立,加速了传统经济的瓦解速度,刺激了云南对近代工业的需求,促进了经济外向型发展。外国资本进入云南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开拓云南甚至整个西南市场。各国列强通过直接资本输出和对滇越铁路的控制来操纵近代云南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布局,使云南轻工业众多、重工业稀少,机械化程度低,大量人力劳动代替机械生产,难以实现传统向近代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列强资本进入云南的另一重要形式是金融资本输出,英法等国纷纷在云南设立洋行,进而控制了云南的金融命脉。1914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于蒙自设立支行,此后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法国金融资本建立了以东方汇理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东方汇理银行依仗背后的法国和自身强大的资金实力,在云南发行纸币、控制外汇,进一步操纵云南外贸,控制云南财政,服务于其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其影响力遍及云南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严重扰乱了云南金融秩序,阻碍了云南金融业的发展。
外国资本还大举进军云南的工矿业,力图操控云南工业命脉。“偌大一个省城,竟无一家从事生产经营的外资企业,那么商业不振,交通不便的外县,就更难想象了。”④汪戎:《近代云南对外经济关系》,《思想战线》1987年第4期。西方列强资本集中于商贸、金融和交通,缺少生产领域的投资,从而导致云南经济体系的不完整。西方列强出于服务其侵略与掠夺的目的,不希望云南发展自己的近代工业。外国资本虽促动了云南某些产业的发展,但其核心目的仍旧是资本积累。滇越铁路通车后,“据云每年收入约6270余万法郎,可得纯利1000万法郎”,而“此或系法公司一面报告,精确与否,不得而知”。⑤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续云南通志长编》(中册),第1000页。
外国资本在自身逐利的同时虽然一定程度促进了云南的发展,但推广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宗教思想也是为了使云南人民迎合其商品,开拓云南市场,都服务于其侵略目的。故此,如果单纯依靠外部力量,是难以实现云南产业结构合理、经济均衡发展的。外部力量可以打破传统经济,但是要实现真正发展仍需依靠自身力量。
(二)内部因素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后发国家卷入早期经济全球化大多是被动的,但是自身如何应对这一过程,如何学习西方技术与制度,并同时努力构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才是决定后发国家近代化命运的最终力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技,富国强兵,抵御外敌。与全国其他通商地区一样,云南在通商开放之后,原有传统经济和封建制度瓦解加速。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外来思想引入、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云南民族资本得以发展,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发展。
随着开埠通商,云南原有的商业资本积累更加迅速,其中滇西民族商业资本总额就达1亿至1.2亿半开银元以上,是云南民族商业资本中的代表。①杨煜达:《试析近代滇西商业资本的积累》,《史学论丛》(第8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20世纪初,云南逐渐出现一批近代民族企业,主要集中于腾越、蒙自、思茅、昆明等商业发达的城镇。通商开放以后,有一些开明人士认识到了近代工业、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如腾冲名士、曾任国会议员的刘楚湘先生就在《腾冲县志稿》中说:“如仅贩运舶来品,倾销内地吸人民之脂膏以富列强,纵土地人民依然如故,而中国亦成一干血痨之病夫”,因此他极力呼吁兴办民族工业。一些较有实力的商号开始投资于近代轻工业,如腾越、蒙自、思茅、昆明、大理、下关等地开始出现肥皂厂、火柴厂、制革厂、茶厂等,甚至还有人在四川投资设立生丝厂,其规模很大,产品主要出口国外。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纺织厂、碾米厂、电厂等机器化程度更高的工业开始出现,其中大部分仍旧是由原先的商业资本转变而来。云南各商号也随之在滇西等地建立丝厂,甚至后来福春恒还到山东博山设厂,用机器解丝,销往缅甸。②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起、发展及其末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8页。
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云南地方政府,积极回收关税、盐税、邮政等所得款项的存汇权力,削弱东方汇理银行在云南金融中的负面作用,稳定云南金融领域,并努力构建完整的近代经济体系。地方政府完成了一系列保护民族资本、完善近代经济体系的举措,一定程度促进口岸城市和云南经济的发展。
四、“中心—外围”理论下近代云南经济发展分析
普雷维什较早提出 “中心”与“外围”之空间关系理论,该理论一经提出立马受到热捧并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普遍理论。依据该理论,“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外围”支援“中心”的阶段,即大量生产要素流向“中心”,“外围”日益沦落为“中心”的附属,导致了“中心”日益发展、“外围”逐渐衰落之态势,就世界范围来看,这一阶段大致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二个阶段,是“中心”反哺“外围”的阶段,即随着“中心”生产成本的上升,相关产业逐渐向“外围”转移,从而带来生产要素的反向流动,这一阶段大致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现在。
毫无疑问,云南近代三个通商口岸设立时期属于该理论的第一阶段时期,通商口岸的设立加剧了贫富分化,促进了世界的两极化发展。这个可以从两个层面来予以解释:
第一个层面,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设立的通商口岸与宗主国的关系上,宗主国属于“中心”,他们所设立通商口岸属于“外围”,所以通商口岸是完全服务于宗主国掠夺原材料和倾销商品所需,一定程度而言,宗主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分布在世界各地无数个通商口岸发展基础之上的。第二个层面,在通商口岸与其周边地区的关系上,通商口岸属于“中心”,其周边地区属于“外围”,周边地区的资源像血液一样源源不断地供向通商口岸,无数个乡村与城市牺牲“大我”换来了通商口岸繁荣的“小我”。云南民间向来以纺纱织布作为农村家庭主要经济收入,随着开埠通商,大量来自海外的棉布对云南农村经济打击很大。因此,通商口岸的一时发展繁荣是建立在广大农村腹地长期贫困基础之上的。
从“中心”与“外围”的第一个层面含义来看,近代化与经济全球化核心的推动力来自西欧(最早来自英国),列强纷纷通过不平等条约来掠夺他国经济资源,进行经济侵略。从1889年蒙自开关到1911年,云南三通商口岸出口总值为6635余万海关两,进口总值9005余万海关两,入超达2370万海关两。①周钟岳、赵式铭等:《新纂云南通志》卷144《商业考二》,(第7 册),第108页。究其原因,即是前文所述西方大量压低云南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抬升进口工业用品价格的结果。就全球范围内来看,三口岸开埠通商以后云南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末端,所生产和出口的商品大都是低附加值的,以服务列强的产业发展需求为目的,“外向性”发展的结果即是本省完整的经济体系难以建立,经济呈较强的依附性。
从“中心”与“外围”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来看,西方列强设置通商口岸并没有带来口岸周边地区的繁荣。此三口岸城市仿佛是西方列强在云南的飞地,与西方列强的联系超过了与周边区域的联系。云南三口岸通商以来,在洋货的冲击下,使得本来就弱小的农村手工业受到沉重的打击,土货逐渐被洋货所排挤,外来商品逐渐充斥云南市场,民生凋敝,并影响到地方财政收入。
所以,依据“中心—外围”理论分析近代云南经济发展,囿于服务于西方列强发展的需要,云南的经济发展是不完全的经济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解释。一是云南经济发展要服务于西方产业链发展需求,即使为了“配合”发达国家产业链的发展需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产业,那也是服从于西方最大限度地从云南获取利益的目的的,不可能实现完全自主发展;二是云南自身产业结构不完善,主要发展的是工矿业,产业结构不完整导致了对世界产业的依赖程度加大,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不足。
五、结语
学界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向来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笔者的观点是当世界经济格局尚未完全确立时,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学习与模仿实现经济赶超,后发优势是成立的;当世界经济格局基本形成,跨国产业链基本形成和全球范围内分工体系基本完成,后发劣势的解释则更具说服力。“后发优势理论”和“后发劣势理论”在解释通商口岸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方面也是适用的。
通商口岸设立使中国经济卷入早期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社会分工发展与生产专业化发展的趋势,有助于后进地区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也有利于后进地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经验,实现经济跨越发展,这是符合“后发优势理论”的。
通商口岸大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设立的,此时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体系已经确立,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已成事实,往往只能生产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阙如,所以经济只能实现有限的发展,这可以用“后发劣势理论”来予以解释。
开埠通商以后,决定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力量依然是内部因素。在外部力量推动有限的情况下,内部的力量尤其是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1912—1919年,中国仅新建的厂矿企业就有470多家,资本增加13000万元,短短7年就超过了过去半个世纪的资本量。一些官僚、商人、地主、华侨开始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企业家热情高涨,众多民营企业家涌现,资产阶级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以“自强、求富”为目标,兴办近代企业,奖励工商。城市工商业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农产品商品化发展并带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些均极大促进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近代化转型。
总之,通商口岸设立使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近代经济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又面临着后天发展环境的限制,使得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始终是有限发展,难以实现近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