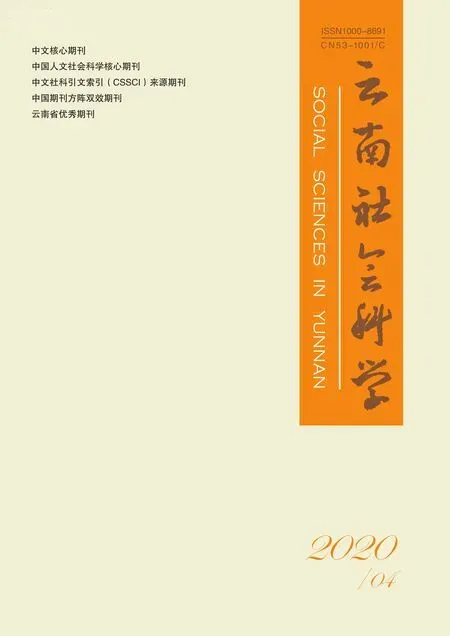论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者的伦理责任
2020-02-21徐大慰
徐大慰
许多人类学者、民族学者从事“他者文化”(Other Cultures)研究,进而反观、诠释和重构本文化。国际惯例是,跨文化研究者必须遵守人类学伦理指南,出版关于土著居民或原住民的研究成果须经过专业委员会严格审查。由于中国尚未制定人类学研究指南,本文借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的土著研究伦理指南和《联合国土著居民权利宣言》等国际法规,结合人类学理论知识和田野工作方法,探讨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者的伦理责任及行动策略。
一、国外土著研究者的伦理责任综述
国外土著民族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来源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医学协会和国际医学组织理事会;国家伦理指南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一般来说,知情同意、协商咨询、参与合作、避免伤害、利益回报等原则是土著研究者的主要伦理责任,文化权是土著民族固有的权利之一。
美国人类学协会(AAA)制定了《美国人类学协会伦理法典》①Code of Ethnic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2009 AAA Code of Ethics,http://s3.amazonaws.com/rdcms—aaa/ files/production/public/FileDownloads/pdfs/issues/policy—advocacy/upload/AAA—Ethics—Code—2009.pdf.,引用时间:2018年12 月10 日。,申明协会研究的立场:通过出版、教学、专业开发、政策咨询等方式恰当使用各民族知识是有价值的;人类学知识的生产是一个动态过程且需要多种方法;知识的生产和运用要符合伦理规范。协会的使命是:推进人类学研究,促进人类学知识传播和运用,重点是帮助协会成员处理各种人类学伦理问题。人类学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资料及同事有首要的伦理义务,如避免伤害、尊重人类福祉、咨询协商和互惠等。人类学研究者在执行和发布研究成果时,要确保受成果影响人员的安全、尊严和隐私。人类学研究须获得研究对象和研究社区的知情同意,要以适当的方式回报,不能拒绝参与者分享成果。
由澳大利亚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研究会颁布的《澳大利亚土著研究伦理指南》分为6 大类,即权利、尊重和认可,协商、咨询、同意和相互理解,参与、合作和伙伴关系,利益、成果和回报,使用、存储和获得,报告和承诺。包括14 条准则:认可土著民族及个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土著民族自决权必须得到认可;土著民族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必须得到认可;土著民族在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达中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保护和保持;土著知识、实践和创新必须得到尊重、保护和保留;咨询、协商、同意是进行土著研究的基础;研究过程中要不断地咨询和协商;咨询和协商应使双方理解研究的目标、方法和结果;协商应该签订正式协议;土著居民有权全程参与;土著民族应该从研究中获益;研究成果要响应土著居民的需要和利益;应为研究成果的管理使用和获得制定双方认可的计划方案;撰写的报告要符合伦理规则。①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tudies.Guidelines for Ethical Research in Australian Indigenous Studies 2012,https://aiatsis.gov.au/sites/default/files/docs/research—and—guides/ethics/gerais.pdf.引用时间:2018年8 月12 日。
《三理事会政策声明:人类研究的伦理行为》由加拿大健康研究所、加拿大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委员会以及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共同颁发。尊重人的尊严(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是该伦理指南的基本价值,它是通过三项核心原则——尊重人、关心福利和正义——来实现的。“尊重人”(Respect for Persons)就是承认人的内在价值,对人的固有价值应当给予的尊重和考虑。尊重对象为直接参与研究的同事和被研究的人,内容包括尊重自治和保护那些在发展中的、受损的或受削弱的人,还包括研究道德方面的问责制和透明度。“关心福利”(Concern for Welfare)要求研究者关注研究对象的身体、精神、隐私、风险和利益等,决定因素包括住房、就业、安全、家庭生活、社区成员和社会参与。“正义”(Justice)是指公平和公平待人,公平意味着平等地尊重和关心所有人;公平待人并不总是要求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人,应优先考虑弱势群体的需要。对正义的一个重要威胁是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权力失衡。这三条核心原则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依存的,它们的适用方式和重视程度取决于研究的性质和背景。②tri—council policy statement:Ethical Conduct for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s,http://www.pre.ethics.gc.ca/pdf/eng/tcps2—2014/TCPS_2_FINAL_Web.pdf.引用时间:2018年7 月15 日。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人类参与者伦理委员会制定《与人类参与者共同研究的指导准则》,这是奥克兰大学开展与人类参与者合作研究时应遵从的最高伦理标准。该指南关于研究的设计、开展和伦理评估的核心准则包括17 条:研究者的责任,研究参与者的招募,诱因、补偿和偿还,知情同意,研究参与者的隐私保护,欺骗的限制,最小化伤害,利益冲突,社会和文化敏感性,弱势参与者和社区,怀唐伊条约(The Treaty of Waitangi),人类遗骸、组织和体液,意外发现和发现违法活动,不良事件,资料的储存、安全、销毁和保留,结果的发表,申诉程序。指南指出,研究的参与者要受到尊重,拥有尊严,他们的隐私、安全、健康以及个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敏感性应受到保护。研究者有责任设计有效的研究和问题,以免浪费研究参与者的时间和投入。研究者也有责任确保研究是有价值的,无论是现实的或潜在的、理论的或应用的、直接的或间接的。③Human Participants Ethics Committee of University of Auckland,Guiding Principles for Conducting Research with Human Participants,https://cdn.auckland.ac.nz/assets/central/documents/2011/Guiding%20Principles%20for%20 Research%2024%20Feb%2010—%20Bookmark.pdf.引用时间:2018年7 月10 日。《毛利人健康研究指南》由新西兰健康研究委员会制定,附录包括《毛利人研究伦理指南:为研究者和伦理委员会成员提供的指导框架》。该指南旨在告知研究者要向毛利人进行咨询,以及开展咨询所需要的过程。咨询的目的是确保研究结果对毛利人的健康发展有利。④Guidelines for Researchers on Health Research Involving Māori.http://www.hrc.govt.nz/sites/default/files/Guidelines%20for%20HR%20on%20Maori—%20Jul10%20revised%20for%20Te%20Ara%20Tika%20v2%20FINAL[1].pdf.引 用 时间:2018年7 月12 日。奥克兰大学副校长(毛利人)在每个学院都任命一名毛利人伦理顾问,并规定从事毛利人研究或与毛利人互动的研究人员都需要毛利人伦理顾问的签署同意。
对土著居民知情同意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评估获得知情同意过程的早期研究项目。在分析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土著居民参与研究过程中的知情同意时,5 个已发表的研究项目评估了土著居民对提供信息的方法或对信息的理解的偏好。①Russell FM,Carapetis JR,Liddle H,Edwards T,Ruff TA,Devitt J.A pilot study of the quality of informes consent materials for Aboriginal participants in clinical trials. J Med Ethics.2005; 31(8):490—4.Bull JR.Research with Aboriginal peoples:authentic relationships as a precuror to ethical research.J Empir Res Hum Res Ethics.2010;5(4):13—22.McCabe M,Morgan F,Curley H,Begay R,Gohdes DM.The informed consent process in a cross—cultural setting:is the process achieving the intended result? Ethn Dis.2005; 15(2):300—4.Fong M,Braun KL,Chang RM.Native Hawaiian preferences for informed consent and disclosure of results from research using stored bioloqical specimens. Pacific Health Dialog.2004; 11(2):154—9.Baydala LT,Worrell S,Fletcher F,Letendre L,Ruttan L.“ Making a place of respect”:lessons learned in carrying out consent protocol with First Nations elders.Prog Community Health Partnersh. 2013; 7(2):135—43.它们都强调土著居民要参与到寻求知情同意的过程,若研究者能与参加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具备文化能力、使用视觉图表和朴实语言则效果更好。二是详细描述获得知情同意过程的文章。一些文章描述了在知情同意过程中协助交流的各种方法,比如使用容易理解的图片②Fitzpatrick JP,Elliott EJ,Latimer J,Carter M,Oscar J,Ferreira M,Olson HC,Lucas B,Doney R,Salter C,et al.The Lililwan Project:study of the prevalence of fetal alcohol spectrum disorders (FASD) in remote Australian Aboriginal communities.Bmj Open. 2012; 2(3):e000968.McDonald MI,Benger N,Brown A,Currie BJ,Carapetis JR.Practical challenges of conducting research into rheumatic fever in remote aboriginal communities.Med J Aust.2006; 184(10):511—3.,翻译用土著语言提供信息③Benitez O,Devauz D,Dausset J.Audiovisual documentation of oral consent:a new method of informed consent for illiterate populations.Lancet.2002; 359(9315):1406—7.Creed—Kanashiro H,Ore B,Scurrah M,Gil A,Penny M.Conducting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xperiences of the informed consent process from communty studies in Peru.J Nutr.2005; 135(4):925—8.,运用土著熟悉的研究范式④Andrews R,Kearns T.Training Community Workers to Deliver Local Informed Consent Materials.The East Arnhem Healthy Skin Project. The Menzies School of Health Research; 2011.www.lowitja.org.au.2012.Wilson S.Research is Ceremony:Indigenous Reseach Methods. Black Point,Nova Scotia:Fernwood Publishing Company; 2008.Smith LT.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London:Zed Books; 1999.。研究者只是寻求土著居民的口头同意,以免签订书面同意时造成研究者和土著社区之间的权力失衡。⑤Mkandawire—Valhmu L,Stevens PE,Applying a feminist approach to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research in Malawi:a study of violence in the lives of female domestic workers.Adv Nurs Sci. 2007; 30(4):278—89.三是伦理指南中的知情同意条款。许多指南都强调土著研究须得到当地社区和居民的同意。大多数指南要求研究者要寻求潜在参与者的“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同意”,同意是自愿的,免于被胁迫;事先通知,使双方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审议和协商;同意是在参与者知道项目的好处和风险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研究的细节须用简单的语言向参与者解释。指南认为土著居民是脆弱的参与者,双方有可能出现权力不平衡,因为很少有指南强调研究者要适应土著社区的口头传统和文化价值观,大多数指南都没有建议用参与者的母语解释研究信息,很少有指南为寻求知情同意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⑥Fitzpatrick et al.Seekingconsent for research with indigenous commuinties:a systematic review.BMC Medical Ethics.2016;17:77—8.
二、尊重民族和文化多样性
研究者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原则。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种族与种族偏见问题宣言》指出,各民族之间的文明成就差异完全是由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因素造成的,此差异不得成为划分民族等级的任何借口。《联合国土著居民权利宣言》指出,任何基于民族、种族、宗教、族裔或文化差异而鼓吹其民族或个人优越的学说、政策和做法,都是种族主义的,这在法律上无效、科学上谬误、道德上应受谴责。“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者总是以自己所属群体的文化价值和传统观念来衡量和评价其他社会文化行为,并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于其他一切文化。如果民族中心主义者再把文化优劣论归因于人种或种族的差异,就成为种族主义(Racism)。①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3页。而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者认为,衡量文化只有相对的标准,没有绝对的或唯一的标准;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性质和充分的价值,不能区分为先进落后、文明野蛮;人类文化在本质上有共同性,它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要尊重所有民族的文化。②吴泽霖、张雪慧:《简论博厄斯与美国历史学派》,参见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 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336页。“对于异民族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好坏来评断他们,我们不能自以为是而强要用之于他人身上,这就是人类学家与异民族相处的基本观念。”③李亦园:《人类学的视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7—18页。
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研究者还须尊重民族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联合国土著居民权利宣言》肯定所有民族都对构成全人类共同遗产的各种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做出贡献。《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人类家庭”概念,将所有人类视为一家,同出一源,后来因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种族,又因创造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形成不同的民族,这才使得人类世界呈现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与之一致的是,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是56 个民族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民族实体,各个民族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联合国土著居民权利宣言》强调所有民族都有权与众不同,有权别于或自认为别于其它民族。族群认同在于自识和他识,族群边界是由族群认同生成和维持的。④徐大慰:《巴特的族群理论述评》,《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土著民族自己确定何为土著人和谁是土著人这一权利必须给予承认”⑤[美]爱德华·劳森:《人权百科全书》,汪渳、董云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67页。,并有权受到尊重。
文化多样性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产物和存在形式。“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最根本的莫过于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⑥林耀华:《民族学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9页。文化权利——特别是那些有关文化传统的保护、特定民族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发展等权利——在特定情况下被认为是“民族”的权利。⑦[挪]艾德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教程》,中国人权研究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页。文化权利的丧失意味着文化的消亡,文化消亡也就没有了民族个性和民族特征。文化权利的目标和归宿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文化是适应不同环境的结果,“一样的人,不同的文化”⑧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文化使人类之间产生区别,对人类来讲文化多样性就像生物多样性那样必不可少。研究者应恪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⑨费孝通:《反思 对话 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的箴言,既能欣赏自己民族的文化之美,又能包容地欣赏其他民族文化之美,诚如《关于文化政策的墨西哥城宣言》所说:“每种文化都代表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价值体系,因为每个民族的传统和表达形式均为展示自己在世界上存在的最为有效的方式。”⑩杨侯第:《世界民族约法总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515页。
保护文化多样性首先要保护好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是在少数民族社区发展、延续和代代相传的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包括民间创作和手工艺、多样化物种和地方性知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可分为语音、动作、物质等方面,体现了少数民族的核心价值和信仰。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文化实践、文化资源和知识体系之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他们表达文化身份的过程中代代相传。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是保持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资源,使人类有了更多的选择。世界上许多农作物的多样性都是根据古老的耕作方法、品种选择和土地利用习惯而保持的。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在解决食品安全、农业发展、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土著居民权利宣言》和《第169 号公约》都强调土著民族享有其文化不被毁灭的权利。《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承认土著传统知识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应该得到充分保护。
研究者应理解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体系、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熟知与其相关的法规和内容。土著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保护涉及10 个方面:神圣遗址保护和利用,祖先和宗教人物遗体的归还和重新安葬,神圣物品和礼仪物品的收回,手工艺品和艺术品的保真,传统图案的集体权利,表演艺术的版权,宗教失密,旅游和隐私,医学研究和生物探索,科学技术。①[希腊]埃丽卡-伊雷娜·泽斯:《关于保护土著人民的文化财产和智力产权问题的研究报告》,参见廖敏文编:《为了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5—430页。研究者要对信息提供者致谢,也可以与研究对象和社区共享知识产权和道德权利。出版物展示或发布内部资料的时候,要征得提供者或负责人的许可,尤其第一次披露和出版的时候,要考虑到披露内容对研究对象和社区的影响。研究者认可少数民族的知识、实践和创新,不仅仅是一种礼节,而是对其权利的认可和保护。
研究者要尊重少数民族社区和成员的“人观”(Personhood)。“人观”是人的“本土观点”(Native’s Point of View),它是人类能力和行动的基础、自我的观念及情感的表达方式。如少数民族把文化遗产、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看作是民族的标识、尊严和价值,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密切的联系;若用现代法律中的文化遗产概念将它们分为文化财产和知识产权是不恰当的,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独特认识,也不利于文化权利的保护。“人观”理论强调对异文化的主位描述和注重当地人的主观表述,重点在于对系统的本土观念的发掘,因为“系统的本土概念既是人观的本质,同时又是一个系统化的经验概念”②[美]马尔库斯、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71页。。“主位”(Emic)是文化持有者的认知,代表着“局内人”(Insider)的世界观。它要求研究者“从本地人的观点出发”,理解少数民族成员的思考和行动方式,遵从少数民族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分类和解释,而不是研究者从自身出发来解释。
跨文化研究者应接受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训练,内容包括:价值观多元化,进行文化自我评估,意识到并且管理文化差异,文化知识的制度化,为所服务社区的文化多样性提供适宜的服务。研究者既要认可各个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也要认可在同一个少数民族社区中个人和群体的多样性,例如,基于性别、年龄、宗教、家庭分组和社区利益的多样性,研究者不能假设一个群体的观点就代表一个社区的集体观点,也不能将对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理解推广到对其他所有社区或民族的理解。研究者不能将文化定势应用于社区和个人,更不要用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评判他者文化。
三、确保伤害最小化和利益回报
少数民族研究成果很容易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成员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这些成果多以民族志形式完成,细致入微的民族志描写很容易伤害到个人。“有些涉及婚姻、身心缺陷以及过去犯罪等,当事人不愿为人所知,对此你有义务为之保密。”③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3页。有些人类学作品被他人不法利用后,可能会对土著居民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法国人类学家孔多米纳斯(Condominas)研究了越南山地的恩龙卡族(Mnong Gar),并于1957年发表民族志作品。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把本书翻译成英文发给美国特种部队,试图强迫越南山地民族参加他们的军事行动。为了获取情报,孔多米纳斯的当地朋友被折磨而死,恩龙卡族人被分散到各个难民营,他们的村庄也被带着人类学著作的军队毁灭。④庄孔韶:《人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这种伤害虽然出乎人类学家的意料,但是客观存在的和毁灭性的。
奥克兰大学的《与人类参与者共同研究的指导准则》指出,研究者有责任保护参与者的隐私,要让参与者明确知道他们的参与会在多大程度上被他人所知,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储存资料和发表成果要符合保护参与者隐私的原则,这也适用于向第三方提供关于潜在参与者的信息。研究者须对每一种需要公开参与者身份的情况做出判断:参与者身份是否足够重要到必须公开的程度;能不能用另外的方法或使用其他来源;如果给参与者带来特别大的伤害,能不能放弃研究成果。化名是隐瞒个人身份、保护参与者免受伤害的一个有效方法。隐瞒村庄的名字可以阻止那些好奇的人进入社区,可以保护社区成员的正常生活。把机密的信息编译成密码,能使其免于落入不法分子之手。而对于影视人类学作品来讲,这种匿名很难做到。最好把人类学影视片先拿到村子里播放,听取当地人关于片子内容的取舍意见。在某些情况下,参与者则要求公开他们的名字,研究者应事先征询他们的意愿。
研究者不能伤害他所研究的人或群体,不能伤害研究对象的感情或亵渎他们的神圣文化。这种对当地人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的尊重,有效地保证了研究对象的权利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完整性。非侵犯性的民族志不仅是好的道德规范,更是好的科学。①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但是,所有研究都有可能带来伤害风险,研究者有责任将这种伤害最小化。研究者应该评估和讨论他的研究项目对个人和社区带来的潜在伤害。一旦有伤害风险,研究者还应该考虑可能的替代程序。研究者应该考虑伤害的严重性和伤害发生的可能性,考虑这些因素之间的平衡。研究者不可能完全保证参与者的安全,必须让参与者在参加研究之前就认识到潜在的风险。此外,研究者也要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在研究活动期间和之后,都要有适当的管理和支持程序。②University of Auckland:Human Participants Ethics Committee,Guiding Principles for Conducting Research with Human Participants,https://cdn.auckland.ac.nz/assets/central/documents/2011/Guiding%20Principles%20for%20 Research%2024%20Feb%2010—%20Bookmark.pdf,发布时间:2013年3 月4 日,引用时间:2018年7 月10 日。
《美国人类学协会伦理指南》指出,人类学家固然可以从其研究中获取个人利益,但千万不能滥用当地的文化及生物资料。研究者应该承认他们的工作对当地社会可能会有所亏欠,因而有义务采用适当的方式回报当地社区和人群。因此,“调查者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当地人民做好事,不能一味从当地人民索取材料而对他们的疾苦漠不关心”③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3页。。对参与项目、可能受到研究影响的人和社区而言,研究者应该意识到研究项目对他们有利。在咨询的早期阶段,研究者就要寻找机会与社区合作,讨论研究结果对社区发展的意义。研究要建立在当地人的具体观点上,将研究成果恰当地具体地融合到参与者和社区的需要上来。考虑到教育背景的差异性和生活经验的不同,研究者应用可以理解的方式撰写研究成果。
参与研究的少数民族应从研究成果中获得利益,这是因为他们为研究贡献了知识、技能、文化产品等,理应得到公平的、同等的收益。这种收益是互惠的,研究者获得研究成果,而少数民族更加熟悉本民族和社区的知识。因此,研究者要与社区公开讨论项目的潜在收益,包括稿酬、雇用和社区发展等;也要将所有不利信息提供给参与者和社区,让他们权衡潜在的收益和可能的风险。参与者的收益要与他们的付出相称,对那些付出重要时间、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或社区尤其如此。研究者应明确有些文化信息属于财产,有所归属,可能需要购买。研究者不能创造或提供条件,对少数民族社区及个人产生经济的、文化的或性的剥削利用。研究者可以考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材料赠送给少数民族社区,比如田野笔记、语言录音、文化实践和民族植物学知识等。奥克兰大学人类参与者伦理委员会认为,对参与者所花费的时间和付出的劳动进行补偿是可以接受的,比如向参与者发放问卷、当导游、给予技术协助。但直接付费会带给人们不良的期望,诱导他们参与,影响他们的回答和建议,最好的互惠方式是在研究结束后兑现。
四、遵守协商、咨询与知情同意的原则
少数民族研究多是跨文化比较研究,关注的是他者的文化和人性。在格尔茨看来,“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④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页。。因此,他提出用“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来“理解他人的理解”,在“比较不可比较的文化”过程中,实现观察者、被研究者和读者的观念世界的沟通。“在研究过程中,观察者应该是土著的一部分,应该以土著的观点来想问题、看问题。”①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第113页。为了能准确地理解和诠释少数民族文化和人性,研究者应与当地人持续不断地协商和咨询。
对一个特定的社区来说,总会有合适的人能提供咨询,研究者可以邀请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持有人参与到项目中来。对于综合性的研究来说,可以向该研究有过重要贡献的个人或社区进行确认和咨询。研究者应确保研究目标、过程和结果有过恰当的协商和咨询,确保研究项目经少数民族同意并有参与者签名的声明。所有参与者在研究过程中都是平等的,他们有权在项目的任何阶段退出。允许少数民族社区有足够的时间对研究项目继续评估、反馈和讨论。当研究者要以数字化形式发布和分享少数民族表演和活动记录时,应与少数民族协商制定协议。
协商和咨询应当促进研究者和少数民族的相互理解。针对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潜在结果,研究者和调查对象诚实地交换信息,而不是研究者单方面地告诉少数民族社区自己想要什么。调查对象适当和完整地获知研究计划的目标、方法、意义和潜在结果,允许他们自由决定是反对还是支持该研究项目。因此,研究者要清楚界定和解释研究的目的和本质、谁在开展研究、谁出钱资助、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和结果。清楚和全面地向调查对象解释信息收集的方法,包括信息保存方式和地方。为了恰当而又带着敏感性地开展研究,双方要讨论相关的文化和政治状况。研究者应诚实地提供一份关于研究可能带来的风险或潜在负面影响的评估,以及环境的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评估。研究者应解释研究在总体上对少数民族的潜在作用,但不能夸大研究的潜在利益。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free,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指研究是在研究对象不受强制或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的,确保研究对象完全明白研究项目的细节和风险。最早的知情同意原则产生于手术治疗和人体实验中。1891年,科赫(Koch)发现了引起肺结核的病原菌,当他对犯人进行实验时,普鲁士当局以文件的形式提到“参照患者意愿”的原则。为了防止德国对二战的囚犯进行未经许可的实验,《纽伦堡法典》制定了人体实验的基本原则,把知情同意原则国际化和法典化。1957年,美国法院在一个案例判决中规定:医生有义务把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各种利弊告诉病人,须征得病人的同意,这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病人权利”。1979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看作为一项基本人权。
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事先知情同意原则,第三方在获取或使用持有人的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之前,须与持有人进行充分协商,并以适当的条件达成协议。②《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zh/tk/933/wipo_pub_933.pdf,引用时间:2018年8 月3 日。可以在合同、许可证或协议中写明商定的使用范围,还可进一步规定所得利益如何分配。《美国人类学协会伦理指南》要求人类学研究者应事先获得被研究者、信息资料提供者及可能被研究结果影响的人的知情同意。研究者应遵守和识别关于知情同意的法律、规范和条例。知情同意需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进行对话和协商,争取知情同意的过程具有动态性和持续性。
当研究者使用具有文化冒犯性和诋毁性的内容时,研究者应事先咨询研究对象,确保得到他们的同意。比如,国内外许多民族都忌讳活人直接提及死者的姓名。为了避免犯忌和招致死者家人的不满,与死者重名的亲戚朋友也往往要重新起名。在西藏僜人中,提到刚逝去者的名字,是对死者家属的莫大侮辱。美洲印第安部落都有禁止提死者名字的习俗。在澳大利亚土著文化中,死者的名字不仅不能提及,连他们的照片或视频也不能发表。在出版这些民族研究成果时,研究者应考虑可能存在的文化敏感因素,选择合适的表达或表现方式。
在民族志研究中,欺骗的技巧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合适的。精心编造的谎言或许对短期交往有作用,但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谎言会破坏研究者和调查对象之间的信任关系。缺少信任关系,资料的可信度存疑,研究就无法进行。因此,研究者不要隐瞒自己的研究意图,或者使用诡计来哄骗人们对一个具体的事物做出回应。这方面与心理学不同,心理学研究常常要求目标群体不知道实验的目的。奥克兰大学人类参与者伦理委员会不同意研究者用欺骗的方法获取信息,即使研究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了欺骗的方法,当资料收集完成后,也要召开一个简介会,向参与者解释清楚欺骗的实际情况。伦理委员会非常谨慎地审查欺骗使用的情况,要求研究者明确论证欺骗的必要性及参与者如何受到保护。
协商、咨询和同意的结果应该签订正式的书面协议,这种协议具有法律意义。良好信任的协商包含全面坦诚地披露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带着诚实的观点达成协议。在设计和项目研究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都应该相互协商并达成协议。协议应该反映双方同意的目标、过程和成果,以及社区参与和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提供详细清楚的关于所有权和知识产权权利许可的叙述;项目成果的分配;少数民族的研究需要和传统文化持有人的利益;认可个人或社区有权退出研究项目;解决冲突的过程;尊重和支持特定的社区条款;提供给当地人的利益安排。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协会在《良好研究实践伦理指南》中进一步指出,当研究者与读写能力有限的土著居民打交道或者在官方程序有漏洞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研究时,获取书面同意并非总是可能得到或有必要性。因此《美国人类学协会伦理指南》建议:当事人知情同意不一定意味着或要求有一份书面或签名形式的协议。关键在于质量,而非形式。
五、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研究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成员的伦理责任,没有论及研究者对同事、学界、公众、资助者的伦理责任。概括地说,研究者必须服从科学或学术行为的伦理准则,就其研究的性质和目的对利益相关者开诚布公,并尽可能地将其发现向科学和学术团体发布。研究者应以恰当方式使研究成果为公众所用,在与政府、资助人打交道时应诚实率直,不得把学科伦理作为妥协条件,不得同意当地人的不合理要求和条件。相比较而言,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和社区的伦理责任是最重要的和基础性的。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者多是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们的行为规范应当遵守人类学会的伦理准则。《美国人类学协会伦理法典》《澳大利亚土著研究伦理指南》《三理事会政策声明:人类研究的伦理行为》《与人类参与者共同研究的指导准则》《联合国土著居民权利宣言》等是本文探讨研究者伦理责任的主要依据。中国的56 个民族都是世居民族,没有土著人问题,但中国政府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社会对土著人权利的保护行动。中国少数民族与美国的印第安族、新西兰的毛利族、澳大利亚托雷斯海峡岛民等类似,都是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地方,分享共同的历史、文化或祖先,其文化对生境有密切的依赖性。这也是本文论述跨文化研究者的伦理责任时参考国外土著研究指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2010年6 月,在“中国人类学的田野作业与学科规范”工作坊上,高丙中教授起草了《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试图建立中国人类学学术伦理规范或“行规”。“基本陈述”的第六条规定:“人类学学者在田野作业中收集资料时,尊重相关人士的人格、隐私;尊重相关人士的知识产权;不以自己工作的所谓积极的价值为借口伤害作为研究对象的个人、社群;不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或社会关系优势损害自己的调查研究所涉及的个人、社群;慎重对待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实物资料;不破坏同行后续调查研究的条件。”①高丙中等:《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第五条强调,人类学者要尊重个体生命和社群文化的尊严,尊重多元文化,反对各种文化的或种族的歧视。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中国人类学伦理指南的研究和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