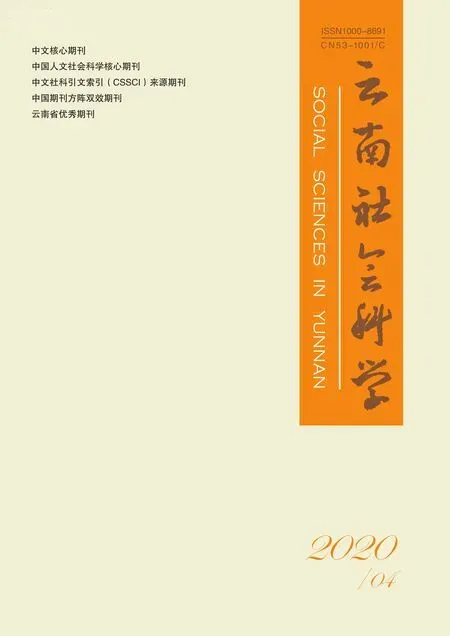变动与坚守:生计方式转型与白族女性日常生活节奏的个案考察
2020-02-21苏醒
苏 醒
一、问题的提出
在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背景下,诸如滞后、延迟、变换节奏等议题都出现在了社会性争议的中心之中。其中关于日常生活节奏的相关考察较早就进入了哲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著名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将身体作为节奏分析理论的核心范畴,认为身体是进行节奏分析的重要工具和节奏分析的对象,并以此为突破口和重要工具分析了资本主义异化问题。他在晚年论述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时将节奏第一次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①参见关巍:《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17年,第18页。,指出节奏是时间、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统一体,各种异质性节奏在时空中不断生成、交织、持存、消失,乃至再生成,如此循环往复,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②吴宁:《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剖析了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的时间意向是如何被“重新部署”的,以此展示时间模式被高度内在化导致行为者的时间意向需要在长时间的并且是剧烈的变革过程中才可能适应新的结构性条件。③[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卡比尔人时间观的考察以及对身体惯习(Body Hexis)的讨论反映出社会秩序、节奏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秩序是通过一定方式调节活动的节奏,并将其深深烙印于身体之上。马塞尔·莫斯(Marcle Maus)则对爱斯基摩社会在年度周期中的节奏变化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爱斯基摩人的社会生活在一个年度周期中会以冬夏两季的规则二分节奏交替进行。①参见[法]马塞尔·莫斯:《社会形态学:试论爱斯基摩社会的四季变化》,[法]马塞尔·莫斯:《人类学与社会学五讲》,林宗锦译,梁永佳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192页。在探讨中国关于“时间”的民俗文化时,周星提出在单位时间内人们某些行为重复出现的频次就可以视为其“生活节奏”。现代社会由于单位时间内人们所做的事情增加、生活节奏变快,于是容易感到疲乏,需要增加往返于“日常”和“非日常”之间的频次来获得休息和放松。并且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具有多样性,比如东部沿海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的增快已经习以为常,而西部地区的居民却还难以适应。②周星:《关于“时间”的民俗与文化》,《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可以将日常生活节奏视作一面能透视文化和社会习俗的镜子,通过它洞悉社区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③张雨男:《鄂伦春族日常生活节奏的变迁与适应》,《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近年来,以“日常生活节奏”作为切入点对特定社区的社会变迁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也已逐渐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新视角。这一研究视角能够较为集中、全面地反映社区居民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文化形式等。④肖红新、王坤:《现代客家村落日常生活节奏的变迁》,《龙岩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总体上,学者们多尝试从“现代性”的动态性和稳定性、内在的张力和发展趋势中,将日常生活节奏同时作为一种结构复杂体和意义复杂体来发现其特性、逻辑和发展。尤其在少数民族社区传统生计方式改变、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这更加成为了一种对社区适应问题的新兴解释框架,典型代表是张雨男从日常生活节奏角度对鄂伦春族社区的讨论。他指出在应对禁猎和农耕的外来冲击时,世代狩猎生活所形成的节奏难以适应农业生活所要求的节奏成为了禁猎转产以来部分鄂伦春族群众陷入生存困境的深层次原因。⑤张雨男:《鄂伦春族日常生活节奏的变迁与适应》。
如前所述,聚焦于社会结构、生计方式等因素的变化对日常生活节奏的影响并从整体性着眼来分析族群、社区对日常生活节奏变迁适应问题的研究为解释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视角和方向,但如果考虑到同一社区内部不同性别的成员在面对变迁时有可能在适应性上存在差异,那么对社区成员内部进行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微观考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有鉴于此,笔者对一个同样正在应对传统生计方式转型的少数民族农村社区——云南大理白族村落N村进行了田野调查。调查发现,该社区在面对由生计方式转变所带来的日常生活节奏变迁时总体较为适应,并未发生因无法适应生计转型而陷入生存困境的情况,但在适应程度上存在一定差别,其中性别差异较为明显。女性社区居民在面对日常生活节奏的变迁呈现出了较高的适应性与积极性——不仅顺利地适应由盐业生产到农耕生产之后生活节奏的改变,从事旅游经营后更是从被动参与转为主动适应旅游业所需的日常生活节奏,进而还引领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在推动乡村振兴以及目的地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N村女性面对生计方式转型、日常生活节奏变迁所表现出的高度适应性是如何产生的呢?基于这一疑问,本文首先勾勒出当地生计方式的转型历程;其次探讨当地女性日常生活节奏是否随之产生变动,如有变动,是本质上的颠覆还是策略性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分析究竟是何种因素在主导着当地女性的日常生活节奏。
二、生计方式转型中的女性日常生活节奏
(一)生计方式的两次重要转型
笔者的田野调查点——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N村其主要生计方式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型,第一次是由盐业生产转为农耕劳作,第二次则由农耕劳作转为旅游经营。N村所在地云龙是云南历史上著名的产盐区之一。唐代樊绰所著《蛮书》中就有“剑川有细诺邓井”的记载。到明清时期,该村已有400多户人家,并根据盐业生产的分工将家户分为灶户、荒户与商贩三个类型。⑥灶户是拥有卤水份额、从事盐业生产的家户;荒户为灶户提供背柴、背水等服务工作;商贩则负责将制作好的井盐运输到外地售卖。盐矿的大力开发使其作为云龙产盐区的重要集镇经济十分发达,作为五井盐课提举司治地,其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也得到了巨大发展。但自清末开始,该社区的盐业经济开始衰落。后经历了1950年7月至1954年2月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1954年3月N村盐井的全部产权收归国有,结束了盐井私有股份制。在此过程中,以盐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灶户”和盐商,以及原本砍卖山柴、为盐业生产提供服务的“荒户”也都转为农业生产。期间虽然也存在县办盐厂、生产队队办盐厂,但生产一直处于半停顿的状态。至1995年,因林木过度砍伐、生态环境遭到破坏,N村盐厂最终停产至今。此后大部分村民都转向农业生产,主要种植玉米等农作物,人口也从明清时期的400多户缩减至现今的200多户。2003年N村被评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村,社区居民的主要生计方式便开始从单一的农业种植转为农业生产与旅游经营并存。2007年N村被命名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这时村中已有两三家以旅游接待为副业的村民家庭。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N村村民抓住党委政府实施旅游产业扶贫的大好机遇,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旅游业成为脱贫致富的主要产业。2019年,N村客栈已达近50家,其中几户村民还在原有客栈基础上扩大经营,开设了咖啡吧、餐吧等。村中以旅游服务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村民家庭已达到30余家。其余村民也都或多或少从事与旅游相关的产业,例如制作售卖火腿等土特产品、餐饮服务等。
(二)不同生计方式影响下的日常生活节奏
1.盐业生产时期:旺平季制盐、淡空季持家
以盐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时期,N村女性日常生活节奏的快慢主要视井盐生产的旺、淡而定。井盐生产与雨量联系密切,雨量少卤水浓度高、井盐产量就高,生产进入高峰期、平稳期;反之,雨量多则卤水浓度低、井盐产量亦随之降低,生产即进入低迷、停滞期。当地传统称之为旺季、平季、淡季和空季。①每年11 月至次年4—5 月为旺季,这一时期雨水最少,卤水浓度最高;9—10 月卤水浓度次之,为平季;5—8 雨水较多、卤水变淡,为淡季;其中6—7 月是一年当中雨水最多、卤水最淡的季节,称为空季。冬、春为旺季与平季,雨水少、卤水浓度较高,是井盐的主体生产期。卤水被从盐井下汲取②卤水由“竜工”从盐井数十米深处汲取。“竜工”由少数有专业技能的男性担任,其余人等,尤其女性不得下井。后,送至轮值灶户家中熬煮,直至干燥成盐。据康熙《云龙州志》记载,熬煮盐“用小灶一为围,铜锅四五口,昼夜煎熬”,期间须时刻注意火势大小、水量多少等,不可离人,因此家中的妇女亦参与生产。由于该时期“昼夜熬煮”所耗甚多,灶户家庭还相应实行一日三餐的餐制③中国自古便有以餐制计时的传统,例如汉代人们就常用“朝食”“昼食”“晡食”“暮食”四次进餐来计时。——除早饭、晚饭外,额外加宵夜一餐以补充体力。熬煮后有散水、归锅、搜盐、滤水、舂盐、捏盐、烧盐等工序。《滇海虞衡记》有载:“白井盐甚白,名人头盐,团盐也。井女手始成”,即在熬煮过程中把锅中结晶的盐粒搜出,滤去汁水,由妇女用手捏成团,同时铲出灶中的热灰,铺在地下,把团好的盐放在灰上,使其渗湿而易烧干;最后用火烘烤,使其干燥坚固。④朱霞:《从(滇南盐法)中看古代云南少数民族的盐井生产》,《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由此可见,在旺、平二季,N村女性在整个井盐制作的全过程中,除参与看顾灶火、熬煮卤水、手捏团盐等直接生产环节外,还要从事煮制夜宵、背卖柴薪等辅助性劳动,几乎昼夜不休、异常紧凑。夏、秋两季是井盐生产的淡季与空季。“淡”指雨量大而致“卤水淡”,“空”指卤水过淡以致无法熬煮成盐,为井盐生产的低迷期与停滞期。此时,N村从事井盐生产销售的男性可稍事休息,而大部分女性则开始将生产重心从井盐生产转向粮食蔬菜种植、家禽家畜饲养、裁衣刺绣等与家庭责任相关的生产劳动并集中参加各类民间信仰活动,如农历六月十三举行的“龙王会”、农历八月二十七举行的“孔子会”等,统称为“做会”。这些活动不仅形成独特的地方生活周期,而且还反映出当地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风貌,例如专门祭祀卤水龙王的“龙王会”就与当地以井盐生产为主要生计方式有关。虽然这些活动的主导者为男性,但女性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参与力量——祭品、茶水等的准备、厨事等大量繁琐劳动均由她们负责。
2.农业生产时期:农忙做活、农闲持家
在漫长的农业时代,民众大多习惯于依靠太阳月亮的升落、星辰位置的变化或者雄鸡鸣叫等自然现象来判断时间,一面又根据日常生活的节奏、对时间进行粗略的把握。伴随盐业生产日渐衰落,N村也转为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方式,主要种植作物为玉米。因此,这一时期当地女性的日常生活节奏也转向以农事节令为划分标准并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同步——在当地体现为以农作物(玉米)生长为主轴,辅之以牲畜、家禽养殖以及农副产品的生产制作(野生菌采集、火腿制作)等。总体可以概括为“顺时而作,农事为先”。首先,女性日常生活节奏反映出围绕农业生产形成地方性知识和生态智慧,并与当地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与各种作物的生长周期同步,这也这构成了当地农时的基本框架。例如根据野生菌的生长特性,她们需要在夏季将起床时间提前至太阳升起之前以便上山采集;种、收玉米的季节则需从日出一直忙碌到日落等。其次,女性日常生活节奏还反映出对劳作时间的依从,即“农事为先”。餐制亦是农业劳作对生活节奏起决定性作用的典型反映:受劳作时间的限制和对农时的争分夺秒,农业生产时期N村普遍实行两餐制,早饭和晚饭。至于进餐的具体时间则视农时的忙闲而定:农闲时多在上午十点和晚上七点左右;农忙季节则可灵活变动。由女性将饭送到田间地头亦是保证农忙期间田间劳作生产的重要措施,携带干粮至田头的场景也很常见。总之,农业生产时期的女性劳作、生活大致上以农时为基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是一年四季的基本状态,晨出夕归为其一日的基本节奏。这也体现出农家劳作生活规律性的一面,当然在这个常态下也可以进行一些个性化的灵活调整,构成了每个女性具体丰富的生产生活状态。①参见邓雅丽:《北宋北方地区的生产和生活节奏——以农时为线索》,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第26页。提姆·英格尔顿(Tim Ingold)认为,文化并不是建构的,而是在人们熟知世界的过程中所不断认识得来的。②参见Tim Ingold,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Londres et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转引自张雨男:《鄂伦春族日常生活节奏的变迁与适应》,《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通过栖居与生活实践,人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来源于整体性生活世界认知的行为方式。③张雨男:《鄂伦春族日常生活节奏的变迁与适应》。N村女性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劳动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符合当地自然发展规律和生态平衡规则的地方性知识不仅影响着她们日常生活节奏的规划,而且使这种规律的日常生活节奏逐渐内化为一种无意识的“惯习”。
3.旅游经营时期:从“农事为先”到“游客第一”
自发展旅游扶贫产业以来,N村开始从单一的农业生产转为农业生产与发展旅游并存,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从事旅游服务。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妇女带来了获取利润的巨大商机,原先的生产生活规律也逐渐转向与旅游淡、旺季同步。旅游经营对时间分配的灵活性要求更多,同时需要对如何实现收益最大化加以认真考量。从事旅游经营后村民转以“游客第一”为原则。当旅游旺季到来,从事旅游经营的女性大都全力投入旅游接待,这同时带来了农事、家事、餐制以及节庆等方面的日常生活节奏的重大改变。
农事方面,旅游旺季与农忙季节如有冲突,那么应行之农事会被暂且搁置。受访者L谈到“原本应该是地里做活的,但算了一下,做了地里的活回来再给客人做饭来不及,而且家里没个人守着,客人也不满意,我想想就把地里活先放一放,要是过几天客人还多,那我就请个人去帮我弄(地里活)。刚开始家里老人说我就是不想做活,后来发现给客人做饭挣的多太多,还喊我不要去地里了,有亲戚来还夸我勤快会挣钱”(受访者P,女,51岁,201808)。家事方面,传统意义中妇女的“持家”行为也根据旅游经营之需求进行了相应改变。如制作火腿、炸制油鸡枞等原属妇女的家庭膳食制作,现已逐渐转变为商业行为;又如N村经营民宿的年轻女性开始雇佣其他妇女为其看护婴儿,以便自己能够有更多时间接待游客,这在该村亦是从未有过的。她告诉笔者:“客人多,我太忙了,所以就雇两个阿姨帮我看孩子。阿姨有钱挣很高兴,把我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我有钱挣也很高兴,把客人当上帝;客人有好的服务也高兴,这就是‘三赢’的事情”(受访者L,女,30岁,201809)。餐制方面则由传统的“两餐制”转变为现代城市社会普遍的“三餐制”,并尽可能地与客源地保持一致,一般在每日早八点、午十二点、晚七点固定提供餐食,部分经营咖啡吧的女性还需要在下午三点左右向客人提供下午茶,这无疑又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女性经营者的工作量,她们需要加快工作节奏以满足游客需求。节庆方面,假日经济驱动当地女性打破其节庆期间习以为常的轻松休闲的生活模式,生活节奏变得快速、紧凑、忙碌。在传统社会,她们认为传统节日的意义主要在于对传统节俗的弘扬,同时也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彰显。但在参与旅游经营后,岁时节令更包含了“假日”的意义,能够为旅游业提供更多文化内涵和发展动力。这种转向自然也伴随着日常生活节奏的变动与调适。以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春节为例,春节在当地被称为“过正月”,即从农历除夕至正月十五都要举行各种庆祝和娱乐活动。除夕日全家吃年夜饭、“守岁”,晚间以红封条“封门”,正月初一早上方揭开封条,以示辞旧迎新;农历正月初四,妇女们忙碌完各种事务后要与家人一起“查运气”①具有博彩性质的游戏在平时被视为赌博,女性参与此类游戏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但春节期间参与这类游戏则被认为是“查运气”,也就是在一年之初来试试自己的运气,与品行无关,因此妇女们在春节期间也都会凑热闹参与此类游戏。正月初五后即止。;之后还有“接姑老太”等专门针对女性的娱乐活动。在从事旅游经营后,传统的生活节奏被打破:受访者L在村中经营一家民宿,她的微信朋友圈信息显示:农历腊月三十(除夕)接待游客14名,L一家人忙着给客人准备餐食,自家的年夜饭吃得简单又匆忙,“封门”和“守岁”的传统习俗也因客人在民宿内外出进玩闹至凌晨而未能进行;农历正月初四本是“查运气”的娱乐时间,但因前来住宿游玩的客人多达12名,L一直忙碌到深夜而未能进行;“接姑老太”的活动由于前来住宿的客人已经预定到正月十六,只能取消。传统意义上农历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期间的“过年”逐渐被旅游参与后的村民们划分为两段:初一至初七强调其“长假”性质,初七之后方转为其传统节日性质,而这种差别被妇女们直观地以“挣钱”和“不挣钱”加以区分。受访者H谈到:“以前不管男女过正月都是不挣钱的。不像现在,春节正是妇女忙着挣钱的时候。一年就靠这几天呢,春节7天赚的比之前几个月的都多。玩也不玩了,也不走亲戚了。玩什么时候不能玩呢,轻重缓急谁会分不清。这几年家家都想着趁春节这几天能好好弄一下,多挣点钱,以后再玩、再休息。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受访者H,女,55岁,201806)。列斐伏尔在其早期日常生活批判概念中曾谈到“日常生活一方面表现为节日与娱乐,另一方面则是非节日的与严肃的生活事务”。②刘怀玉:《论列斐沃尔对现代日常生活的瞬间想象与节奏分析》,《西南大学学校(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从N村的个案来看,从事旅游经营后节日与非节日、娱乐与严肃的生活事务逐渐地重叠、扭结在一起,节庆期间日常生活的节奏也从“缓慢休闲”转为了“忙碌挣钱”。虽然许多传统活动因此而被压缩,甚至被搁置,但这均是源于从事旅游经营后“加速日常生活节奏,最大限度利用假日,以给家庭带来尽可能多的经济收益”这一核心理念。
三、变动与坚守:社会转型背景下女性对日常生活节奏的调适
(一)表层变动:生计方式转型中的日常生活节奏变迁
基于不同生计方式对行动者的要求各异,由此主导的日常生活节奏也在进行相应的改变与调适。盐业生产时期,人们普遍遵循“观雨而作”的原则。妇女在旺季与平季参与井盐制作,淡季与空季则持家、做会,如此往复交替,形成了年度的“环状”时间链。这与何翠萍在对景颇、载瓦人研究中所发现的“干季做人,雨季做活”③参见何翠萍:《生命、季节和不朽社会的建立:论景颇、载瓦时间的建构与价值》,载黄应贵:《时间、历史与记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第158-159页。的时间建构十分类似。尽管传统观念的偏见使得妇女紧凑的日常生活节奏难以在经济价值上得到高度认可④男性辛勤的工作、紧凑的生活节奏以工资或价格形式加以估算,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社会地位与尊严。,但是生产中妇女的各种直接劳动和辅助劳动实际上均在有效地保证井盐获得,她们主要以手工生产能力和家庭管理技能为家庭经济做出大量基础性贡献。农业生产时期,女性的日常生活节奏则仿佛一个围绕着四季自然节令与种植劳作周期而循环往复转动的车轮。当地人认为,即使一年到头辛勤的在田间地头劳作所获取的金钱比外出打工所获的金钱要少,也应勤事生产,因为这是个体、尤其是女性良好德行的外在体现。有村民谈到:“我们这里的女人觉得勤快才是本分,见不惯懒的。种地一年苦到头,虽然挣不了几个钱,但是心里踏实。住在上面那家的男人出去打工了,他家女人觉得反正她男的会挣钱回来,就很不做活,每天闲着,东逛西逛。其他的妇女都很见不惯。虽然她家经济条件好,但是大家都不爱跟她来往”(受访者W,女,50岁,201607)。从这段访谈可发现:当地传统观念认为男性紧凑的日常生活节奏主要意义在于“挣钱”,这是其主要的家庭责任;女性紧凑的日常生活节奏则主要起到维护家庭运转良好的作用,即“持家”。虽然持家并不能带来更多实际收益,女性工作的价值也常常因此以低于男性的形式被感知或者完全被忽略,但紧凑的日常节奏将会转换为社会舆论对她们的正向评价与尊重,而这正是个体追求的荣誉。在由盐业生产转为农耕劳作的过程中,女性日常生活节奏的具体分配规则有所变动,但“守其业、勤劳作”一直是日常生活节奏分配的主导思想,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也是衡量社会秩序稳定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盐业生产与农业生产时期有片面强调勤于劳作的倾向,这一时期女性日常生活节奏的快慢与价值关联度较低,主要是为实现家庭耕读传家、香火延续的传统理想扮演好贤内助的角色,因而缺乏奋斗和进取的意识。
从事旅游经营后,N村女性的日常生活节奏表现出了一些与现代工业社会直指未来的线性时间观相符的特质:由传统“劳作—持家”的二分法转为对时间的更有效利用,追求效率更加受到推崇。在生计方式转型过程中,她们正在经历着段义孚(Yi-Fu Tuan)所提出的那种由“非技术社会”到“技术社会”对其日常生活节奏的改变,不再以“非技术社会”中那种以鸟鸣春、以虫鸣秋的方式来感知时间,技术社会将她们的时间精确地校准到了小时和分钟。①[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4页。相对于盐业生产、农耕劳作时期,旅游经营时期最大的改变在于,测度时间的体验使当地女性逐渐体会到日常生活节奏本身不仅蕴含着“时间资源”,更是一种“时间资本”。正如所罗门箴言所说的那样:“勤劳的双手是通往财富之门。”她们的劳动因为实现了经济价值受到了尊重,而当其意识到旅游业的繁荣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之后,更是希望通过劳动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个体通过日常生活节奏的调节可以获得时间,对时间进行严格控制和积极规划,从而进行更多具有价值的劳动。因此当地人认为,富于美德懿行的女性不仅勤于劳作,还应当懂得合理规划时间、灵活调整节奏,以运用有限时间获得最大的收益。尤其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宿由女性负责,她们可以通过对日常生活节奏的调适将自身所蕴含的劳动力转化成旅游经营场域中经济货币、社会关系网络等资本形式。因此当日常生活节奏松散缓慢、无事可做时便会产生时间被“浪费”的感受,目的意识也变会得空前的强烈,“奋斗”逐渐成为了这一时期当地女性追求荣誉的重要表现。这一点正如康德所言:“我们越忙碌,就越能体验到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意义,也更能感知到生命的存在。在懒惰中我们却只能眼看着生命分秒流逝、擦肩而过,让日子过得死气沉沉,毫无希望。”②张艳芳:《德意志民族市民阶层的“勤劳美德”发展史研究》,《世界民族》2019年第4期。
从N村的田野调查发现,生计方式转型引起了女性日常生活节奏的变动与相应的调适。这种调适通常以时间策略③关于时间策略,布迪厄曾进行了深入的论述(Bourdieu,1997年,第7页)。的形式出现,呈现出暂时性、工具性和灵活性的特质。而事实上无论是从事盐业生产、农业生产还是旅游经营,当地女性日常生活节奏中忙碌、紧凑的核心倾向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笔者认为,表层变动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已被内化的性别观念与道德取向在主导着当地女性的日常生活节奏并在社会转型中被持续坚守。
(二)深层坚守:传统女性文化中“勤”的道德取向
N村女性面对日常生活节奏变迁的高度适应性是具有其内生基础的,即传统性别观念始终要求女性把勤劳作为自己生活的指向标。勤存在于人们内心世界的理性之声对于自身的约束过程之中。在N村,“勤”这一道德指向往往通过性别劳动分工、道德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双向强化等方式得以内化,从而持续、深层地产生影响。
1.性别劳动分工
N村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将男性规范到读书、求取功名、延续家族的角色中,以实现耕读传家的社会理想;女性则被规范到持家相夫的角色中,以保障家庭运转的秩序。日常生活节奏也基于性别角色的不同具有差异。个体从幼年时便开始学习与适应与性别角色相对应的日常生活节奏。当地谚语有云:“女儿像妈,苦不赢。”妇女主持家务,“女儿像妈”意喻着希望女儿像母亲一样勤事生产、操持家务。“苦”指“劳作”,“不赢”意为“没有空闲”,“苦不赢”即深切反映出传统性别角色构建与道德取向对女性的期望——勤劳不怠、片刻不歇的日常生活节奏。当地旅游业主要是为旅游者提供住宿、饮食等旅游服务的以农村家庭为单位的小型村寨民宿,受限于经营理念和资本、技术、人力等条件,通常只有餐饮接待、住宿服务和土特产制作售卖等为数不多的经营项目,而以上项目在N村的传统分工中全部属于女性“持家”的范围,因此女性普遍成为主要从业者,男性则主要作为经营中较大问题的决策者,但较少从事具体劳动。一位男性受访者表示:“现在搞旅游虽然是我拍板决定搞的,但主要还是你阿姨弄。女人家天生就是勤快,眼睛里有活,比如种着菜,就会想着摘个瓜回来。我也承认我们男的是要懒一点,但是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女的就不一样了,女的要勤手快脚嘛”(受访者C,男,52岁,201809)。既然当地人普遍认为旅游经营项目是传统女性家庭劳动的延伸,那么女性的日常生活节奏就与旅游经营的经济收益有着直接关联,用她们自己的话说:“现在搞旅游,基本上还是以前家里那些活,客人要吃要喝要买特产,谁做?还不都是我们女人做。男人家懒,也不会整。女人家不勤快,(旅游)就搞不好。你懒得打理院子,客人看着不顺眼就不来住;懒得种菜,成本就高了;懒得早起去山上采菌子,客人想买土特产你就没得卖给他们的,还怎么挣钱?谁都不眼红我挣钱,我一天从早到晚手脚不闲着”(受访者W,女,51岁,201809)。由此可见,社会性别形塑着日常生活节奏,日常生活节奏也反之对社会性别进行划分并与个体的活动、社会文化融为一体。①纪兰慰:《论岁时节日民俗舞蹈的时空转换特征》,《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9期。男女两性在传统社会文化的持续影响下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从事不同的社会劳动,也保持不同的日常生活节奏。从传统社会“女儿像妈,苦不赢”的谚语,到现代旅游经营中“从早到晚手脚不闲着”的自我表述,N村女性的日常生活节奏始终被“勤”这一道德取向所主导。
2.道德教育
N村一直奉行“笔点文章先点德,斗量阴鸷后量才”的理念,从而将道德教育置于各类教育之首。在女性教育中,勤勉是德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当地女性都有多种途径学习勤勉的道德取向并据此安排日常生活节奏,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宣化等。家庭对女孩“勤勉”品质的教育培养贯穿其成长历程的始终。幼年时,女孩在家长的要求下背诵 “勤则家起,懒则家倾”的家训并从女性长辈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学习各种家务技能;出嫁前,长辈要叮嘱训导新娘在未来的婚姻生活中勤勉持家,以彰显娘家的严格家教;婚礼次日清晨,婆家要求新妇早起打扫卫生,用嫁妆中的铜壶、茶盘、杯子给家人奉茶,然后下厨,以告诫新妇在未来生活中要勤勉持家。这些家教方式与传统习俗至今在N村依然为村民所保留、延续。学校教育也是女孩内化“勤勉”品质的重要途径,无论是N村清代、民国时期的教育,还是今天的小学义务教育中都有关于“勤”的教学内容。清光绪年间,N村办有“内北乡乡立女子初级小学校”,校址在万寿宫,经费由寺庙公款开支,教员由清末贡生一名、廪生一名以及师范生一名组成。除识字、识数等基本教学外,传统道德教育更是首要教学目标。其中教员对女性勤勉品质的强调令村民记忆深刻:“我特别记得,母亲说过,女子小学校里先生教识字的时候说‘婦女的婦字怎么写,左边是女子的女,右边是扫帚的帚’,所以女子天生就是拿着扫帚扫地、做活的人,从此大家就学会要勤快”(受访者G,男,81岁,201809)。时至今日,在2004年修订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三字歌》中也有“个人事,应自理,家务活,要学习;好习惯,早养成,有教养,益终生”的内容。女孩们从小学教育就开始学习、践行并内化着关于“勤”的道德取向。除学校外,社会宣化对女性“勤勉”品质的学习也具有重要影响。清代、民国时期村内设有“圣谕堂”,通过宣读、讲授的方法对民众进行道德品行的宣化教育,称之为“讲圣谕”。所用教材称为“善书”,通常源于儒家经典、佛教典籍、道教典籍、家法家训等。针对女性群体“讲圣谕”时“勤勉”往往是主要教学内容,如“白日种田园,夜晚搓索子,四時播百谷,春来撒秧子,夏天勤栽插,秋天获谷子,金银几柜子”①来自于专门写给妇女的“善书”——《闺阁录》。当地村民杨荣槐家中存有手抄本一部,其余部分村民家中则存有油印版本和复印版本。或“五更鸡唱,起著衣裳,盥洗已了,随意梳妆,捡柴烧火,早下厨房,摩锅洗碗,煮水煎汤”等。社会宣化能够将原本离大众较远的高深的理论礼仪规范加以通俗化大众化改写,以简单明了、朗朗上口的形式使当时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女性群体详熟易懂,为学习和践行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道德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新时代乡村道德也不再囿于传统乡村社会固有的道德规范,但其中勤劳、奋斗、敬业等道德理念始终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而得到传承和发扬。
综上可知,“勤”这一基本道德取向在N村的发展史中不但未被摈弃,而是随着时代变迁在扬弃中被赋予了更丰富的经济内涵和更深刻的社会意义。通过旅游参与的实践,女性村民不但继续将“勤”视为女性应当具备的美德懿行,还深刻意识到“勤”是以积极的方式改善生活条件、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手段,其体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与个人全面发展、家庭富裕和谐、社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都息息相关。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自我意识有一个载体,一方面通过把“勤”这一道德取向写入女教典籍;另一方面,又通过宣化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力来参与女性的生活,如对女性日常生活节奏的快慢进行监督等,这些由勤勉劳动衍生出来的生活方式,在提升了当地女性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使“勤”变成了该社区的一种公共道德。而一个事物一旦具有了价值和道德意义,也就具有了准宗教的性质,其约束力和推动力都会截然不同。②张艳芳:《德意志民族市民阶层的“勤劳美德”发展史研究》,《世界民族》2019年第4期。
3.社会舆论的双向强化
社会舆论的双向强化指的是正强化与负强化的过程。正强化即通过嘉奖、赞许等方式鼓励人们对某一行为持续保持并予以加强,这些行为多是社会和组织需要的行为。负强化则指预先告知人们某种不符合要求的行为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以使人们采取符合要求的行为或回避不符合要求的行为,从而避免或消除不良后果。通过这种强化方式能从反面促使人们重复符合要求的行为,达到与正强化同样的目的。③邵建平、曹凌燕:《威胁激励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管理现代化》2003年第3期。传统上正强化方式有墓志、家训、历代《列女传》等,内容主要是对符合主流价值标准的道德取向和具体行为进行记叙和传颂。众所周知,这些记叙传颂的女性形象都是被高度概括了的、符号化的美德形象。N村《月翁老先生暨孺人徐太君墓志》中就述有“孺人徐氏,出自世族,秉德之厚,所称幽娴贞静,柔惠且直也。年二十适公,优于内助,事阙翁姑,有先意承志之孝,娴于持家,无倦勤诟谇之习。俾公益得以酣畅于学,不必屑屑于家计。及嗣君提名,孺人释然于相夫鞠子,俱能有成,遂先辞世,享年七十一岁,与公伉俪偕老,顾子若孙,将怡然于九京尔”之内容,着重强调的是徐氏生前勤勉持家、使其丈夫得以安心科考的行为。考虑到当时的女教盛行的社会风气以及N村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道德操守和道德理想,墓志上的颂词便是社会舆论对女性“勤”这一道德取向进行正强化的典型。换句话说,为“勤”这一道德取向所主导的日常生活节奏是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要求,社会舆论也会相应对遵从该取向的女性加以肯定和褒奖,并据此对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宣化教育,期望其他女性学习并践行。值得注意的是,女子践行“勤”的道德取向不仅为个人带来社会舆论的肯定,更是其家庭甚至家族的荣誉,杨简《纪先训》有言:“女子事人能敬夫,能奉祀,事舅姑有道,则父母之荣。”④杨简:《慈湖遗书》卷17《纪先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6 册,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894页。普通村民也有“培植一个有德气的,父亲母亲、兄弟姊妹,一家子脸上都有光”一类的表述。
负强化能从反面促使人们重复符合要求的行为,达到与正强化同样的目的。⑤邵建平、曹凌燕:《威胁激励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管理现代化》2003年第3期。N 村谚语有言“一块花帕四只角,花帕上面绣飞蛾。花帕烂了飞蛾在,不看人才看手脚”,这里的“手脚”指的就是姑娘的勤快与否。在当地传统观念中,女性的美好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更多是勤劳与懒惰、能干与不能干、顶事还是不顶事的差别。她们把懒惰视为浪费时间,将勤劳视作人生的意义。在N 村,对女性的负强化普遍表现为舆论压力,例如以议论、批评、指责等对个体施以压力,使其产生羞愧、内疚、害怕等情绪或者以惩罚的方式,对个体的重大活动制造人为障碍,使其遭受挫折,产生沮丧、不安的内心感受,从而达到主动避免或更改不符合要求行为的目的。比较典型的就是婚姻缔结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负强化:择偶过程中勤勉始终是考察女性的一项重要标准。时至今日,该标准依然适用且被看重。同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通过介绍人牵线搭桥仍是目前当地年轻人择偶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与介绍人沟通时“勤快”“能持家”往往是男方对未来配偶的基础性要求。换句话说,年轻女性是否属于优秀婚配对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是否拥有勤劳的品德,而忙碌、紧凑的日常生活节奏又是其具体的表现。如此,婚姻排斥既是一种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也是一种通过社会舆论的负强化使女性内化“勤”这一道德取向的具体形式。
四、结论
既往研究显示,日常生活节奏被打破有可能造成部分人群因难以适应新的生活节奏而陷入贫困。但在笔者的考察中,N 村女性在面对新兴的生计方式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时,非但没有陷入这种困境,相反却表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主导当地妇女日常生活节奏的内生基础的是传统性别文化中“勤”这一积极的道德取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关于如何安排日常生活节奏的思考方式正是源于社会文化所赋予的道德观念。正如巴特勒所说:“性别不应该被用作一个名词,一个本质的存在,或者一个静态的文化标签,而应该被视为不断重复的一种行为。”①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of Identity,2 th ediion,New York and London:R outledge,1999,p43.传统社会中,女性“勤”的道德取向一直为儒家经典所赞颂,生产性的家庭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妻子工作的技能与积极性;现代社会中,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样是女性在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这一道德取向经由社会性别建构、女性教育以及社会舆论的双向强化等方式而得以内化,并相应在外在行为上得以体现。通过女性的代际传承、言传身教,这一道德取向便会深深镌刻进日常的观念与思维里,久之,“社会的建构也被改造成了自然的存在”②魏开琼:《社会性别的建构与形塑——对一个布朗村寨的田野观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2期。。换句话说,基于“勤”这一道德取向而形成的日常生活节奏实际上已成为当地女性的“惯习”——它既是外在的客观结构在个体身上的内化实践,也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实践,其产生及所引发的行动全部基于生活实践,不假思索但符合规范。③张雨男:《鄂伦春族日常生活节奏的变迁与适应》。西方现代哲学认为,理性是工具性的支配意志,包括时间在内的一切事物都被合理化的工具性诉求所支配。④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5页。无论是传统社会中女性通过“勤”来获取美德的赞许,还是现代社会中她们试图通过“勤”来改善生活条件、提升生活品质、获得社会尊重与自我实现,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合理化的工具性诉求。相应地,这些诉求的满足都需要以日常生活节奏的加速为手段。如果我们形象地将生计方式转型视作“万变”,那么“万变不离其宗”——传统女性文化中的“勤”的道德取向正是其中的“宗”。
当社会政策在应对农村地区社会转型问题时,既要正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之处,也应将作为“惯习”的传统性别文化、道德取向对当地人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延续性影响纳入考量。本文个案的分析探讨能够就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道德取向是否能够在新时期的社会转型中继续并持久发挥积极影响、有助应对而成为了一个值得持续关注并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