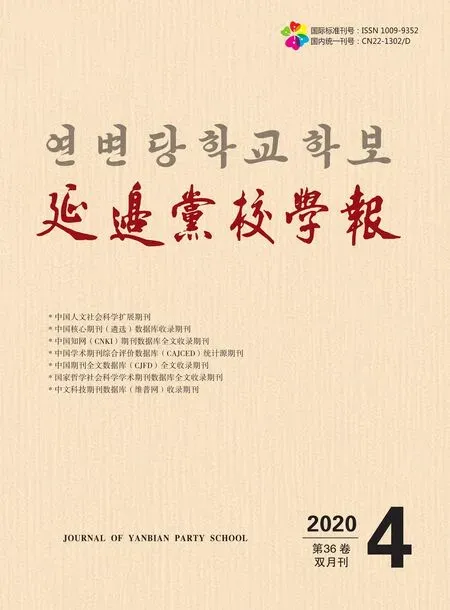1843至1848年间马克思生产力范畴的历史嬗变
2020-02-21杨彩利
杨彩利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 郑州 451000)
1841年马克思提前取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在给莱茵报撰稿期间由于现实事件——例如政府不许砍伐林木——开始关注经济。1843年马克思关注到了生产力范畴。1848年之后直到1883年在英国伦敦去世为止,马克思更多地进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长期研究,专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尖锐批判,进行了包括《资本论》及其三大经济学手稿的理论创作,最终完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因此,1843—1848年间的著作在马克思生产力思想的形成逻辑、历史嬗变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期的经济学手稿及《资本论》没有涉及生产力思想,而且恰恰相反,1848年到1883年的经济学手稿及《资本论》正是马克思的生产力思想从思维抽象到现实具体的再次升华,实现了生产力概念在经济学和历史哲学双重意义上的高度融合。
一、马克思生产力范畴的萌芽阶段——集中于经济学领域
自1843年始,至1845年止,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萌芽与初步探索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经济学。《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三个最为主要的作品是马克思生产力思想的萌芽阶段。马克思这个时期使用生产力概念的角度是经济学。
(一) 《巴黎笔记》:首次使用
马克思于1843年10月至1845年1月间摘录的经济学笔记被MEGA2称之为《巴黎笔记》。马克思在《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摘要》中第一次提到了生产力。“也就是创造不需要增加资本的投入,只是在原来的水平上提高了生产力”[1]。马克思曾经引用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话,即“总产品的构成是一个国家的所有生产力在该年度中创造的所有产品”[2]。
马克思这一时期几乎查阅批判了历史上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文献。在早期的生产力思想中,马克思基本沿用了古典经济学家们对生产力概念所阐述的思想内涵,在经济学领域内使用生产力概念。但随着不断深入的社会问题研究,马克思随之开始了变革生产力概念的理论内涵之路。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理论准备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尝试发掘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特别是马克思试图弄清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规律等相关问题。在该著作中,马克思已经初次认识到了人类社会进步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两次提及生产力这一范畴,提出了分工既能促进生产力的提升还可以赋予劳动无限能力等观点;引用了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力的提法,包括一次引用舒尔茨的“生产力”概念、四次引用亚当·斯密的“劳动生产力”概念。其中,马克思借用亚当·斯密的话:“欲提升劳动生产力,则要具备一定的资本积累。当然,资本积累也会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有效提升”[3]。
在生产力问题的研究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已触及了生产力问题,但由于私有财产是早期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马克思在该《手稿》中研究的重点主要还是分工问题,没有给予生产力过多的关注。
不过,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的使用与古典经济学家已有所不同或有所突破。马克思看重的不是财富的多少,不是交换本身,而是人的劳动。马克思认为资本对劳动的雇佣关系致使劳动本身被异化。此时马克思经由异化劳动范畴开始让生产力表现出从经济学转向历史哲学的迹象。黑格尔认为,人的私利与自我目的中产生的热情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动力。人们在利益、目的所产生的热情的促使下会进一步展开对自己需要的追求。黑格尔的“劳动是人自我本质的确定”思想得到了马克思的承认,在他看来,黑格尔对劳动的本质进行了阐述,“把人和现实的对象性理解为人类为自己劳动成果所付出的努力”[4]。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展现,是马克思对生产力范畴的理解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同时,马克思还未开始从现实的生产方式中理解人、劳动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此时尚在抽象层面上逗留。但是在这种抽象化的理解中,主体意识的高扬、“为我把握”现实世界的超越性,推动着人类历史不断发展和进步。作为内在动力,劳动只有借助生产力才能表现出来。生产力既能反映劳动者的主观要求,又能体现劳动者的客观劳动能力。这种表述虽然明显受黑格尔的影响,但为马克思之后提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思想做好了理论准备。
(三) 《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试图走出经济学视域
该著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完成的。在该著作中,马克思比较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对生产力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不再停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关注的“劳动异化”和“私有财产”,而是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上,从哲学角度分析生产力理论,开始关注人与生产力的关系。
马克思在评论中揭露了李斯特为资产阶级辩护而缺失了主体性的实质,撕下了李斯特的神秘外衣。马克思认为,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只不过是“以理想的词句掩盖坦率的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5],以国家利益的豪华词句来遮掩其荒谬的幻想。从实质上看,李斯特把人当作生产力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马克思批判道:“对当时的德国资本家而言,如果是在工人从事单调职业,精神匮乏、四肢残疾、弯腰驼背的状态下工人可以提供更多生产力,资本家希望所有劳动者都如此”[6]。马克思为此质问道:“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7]反对把人当做增加财富的手段,马克思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表明马克思已开始走出经济学视阈并用历史哲学的视域对生产力范畴进行新的解读。
二、马克思生产力范畴的形成阶段——历史哲学领域的提升
马克思于1845年5月至8月间完成的《曼彻斯特笔记》和《布鲁塞尔笔记》二册笔记,触及到经济学当时的最前沿,为生产力概念从经济学领域转向历史哲学视阈做了铺垫。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形成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柯夫》《哲学的贫困》这三个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他的生产力观。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哲学视阈下生产力范畴的初步形成
如果没有核心概念的“生产力”从经济学层面提升到历史哲学高度,唯物史观就缺失了核心基石。《德意志意识形态》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一方面意味着唯物史观的初步建立,另一方面也标明马克思的生产力范畴具有了唯物史观的哲学意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生产力的提法多达70余处。马克思通过辩证思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意识到了生产力所处的历史地位,第一次从历史哲学意义上对生产力概念进行了界定。
《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技术工具意义、自主活动的能力以及共同活动的方式三个方面对生产力在历史哲学上的内涵进行了阐述。
首先,从工具和技术意义上阐发了“生产力是一种能力”的思想。生产力作为能力的力量表征,是指人们的生产能力或水平,具体表现为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生产力范畴的内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抽象理解的“人们的共同生活方式”包括分工协作以及管理等因素。作为生产力必然要有一定数量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但他们只有在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才能发现生产所具备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社会分工的研究考察了人们的共同活动方式。生产力并非是随着人数的增多而无限扩大,必须考察这些具有一定数量的人是怎样进行共同生产活动。只有通过社会分工、协作和管理,才有合力的意义,这即为生产力的质的方面的规定。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生产力还是物的规定,是异化于人的;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生产力已然是人的能动性活动了。生产力不仅仅是现有财富的机械相加,而且是生产过程中作为人之能力、自主活动以及共同活动形式所产生的力量。在人们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展开共同自主活动就产生了社会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生产力,这是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视阈下对生产力内涵的历史哲学变革。
总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赋予生产力新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对现实的人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从而彻底扭转了他们之前所持的历史观。不过此时,马恩二人还未把经济学批判与哲学建构联系在一起。
(二) 《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回信》:唯物史观的重要阐述
1846年11月1日收到安年科夫的来信,于同年12月28日写下了《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回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对生产力范畴作了重要阐述。
首先,对于任何一代人来说,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先前人们活动的产物。马克思以此为基础,概括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只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历史”[8]的结论。其次,马克思认为,人类获得新的生产力之后,会逐渐改变生产的方式,生产的方式发生变化后,人类便开始改变与之相关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正是借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化时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的推动力量逐步转化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力量的社会历史考察,得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生产到灭亡的整个过程存在着内在的客观必然性这一结论。
三、马克思生产力范畴的全面阐发——历史哲学的具体运用
(一) 《哲学的贫困》:生产力理论的全面阐发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批判的对象是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对生产力的基本概念给予了更加明确的具有历史哲学性的界定,同时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所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一次使生产力这一唯物史观的中心范畴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原理达到了思想上的完全成熟和术语上的准确表达。
生产力概念的完善和生产关系范畴的制定。生产力概念的内涵在《哲学的贫困》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规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从三个方面规定了生产力概念的历史哲学内涵,但并未清楚指出劳动者也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而在《哲学的贫困》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9],这一表述既让生产力概念的内涵更为科学,也为阐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等思想奠定了基础。《哲学的贫困》讨论的重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问题,初步确立了生产力决定交往关系的唯物史观基本理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科学表述。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进行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在生活中一定会出现与之相关的关系;伴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这些关系存在的形式也会有所变化”[10]。生产力的状况表现着该社会形态的性质和水平。生产力的不断革新使它必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产生冲突,为了不让已获得发展的生产力得到破坏,必须粉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些传统生产关系。马克思从全面的角度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关系原理进行了表述。
阶级斗争理论的进一步概括。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因为阶级本身即只跟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层次有关,必定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由于生产方式一直处于动态的变革之中,即使是同一阶级也会分化。生产力的活跃性使得它处于不间断的变动之中,由于这种变动很少会倒退,所以现存的生产关系经常会跟它不适应,当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导致其发展的基础也就是生产关系成了绊脚石时,此时的生产关系就必须粉碎了,那时,原来的革命因素就落后成了保守的一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阐述了这一思想。但是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对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作了比较清晰的表述。人们完全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目的、意愿和愿望改变原来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但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的社会实践导致的社会后果却是不可预测的。
(二) 《共产党宣言》:生产力理论的具体运用
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共产党宣言》中得以具体运用,这其中当然包括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
1.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原理的具体运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结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体现。“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情况,这种关系对于生产无法产生促进作用。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11]。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生产方式没落后,客观意义上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所存在的生产关系,且已经实现了对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替代。资本主义要发展,将不得不完善已有的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情况。“资产阶级只有对生产工具以及社会发展的全部关系进行连续的革命,否则将无法继续存在”[12]。
2.“两个必然”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
《共产党宣言》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说明了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大工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自身将私有制这一基础摒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生产了它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个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和其阶级关系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其进一发展的阻碍,成为它自己已经创造的财富的桎梏。“两个必然”思想既是马恩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也是生产力理论具体运用的结论。
3.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全面地阐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是,资产阶级本身不会自己退出历史潮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具备的生产力条件,为其灭亡准备了掘墓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既发展了使自己灭亡的生产力水平,也培育了掌握这种生产力水平的主人即现代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趋势,无疑将会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运用自身政治优势,集中一切生产工具,并且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优势,又将竭尽所能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1848年欧洲革命的挫折促使马克思反思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唯物史观需要进一步增强自身的说服力。于是马克思号召大家回到书房里去。1848年之后,马克思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研究。1850至1853年摘录的《伦敦笔记》,将生产力范畴限定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进一步深化了生产力范畴的经济学定位;《资本论》第一卷,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率掩盖了生产力的哲学内涵。马克思对生产力范畴的研究随着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分析的精确化而增添了新的内涵。
总之,尽管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没有关于生产力的确切定义。但是,经过对生产力范畴历史嬗变的梳理,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著作里,生产力有时是历史哲学范畴,有时是经济学概念。生产力作为经济学概念,等同于可以量化的生产率。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阈下,马克思强调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是剩余价值的增加。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的目标不是分析作为物的社会关系,不是考察作为生产要素的技术,不是社会契约中普遍的心理认同,不是社会财富分配的规则,而是生成生产力的内在条件,唯有如此,生产力的历史和逻辑矛盾才能被揭示出来,进而,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才能被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