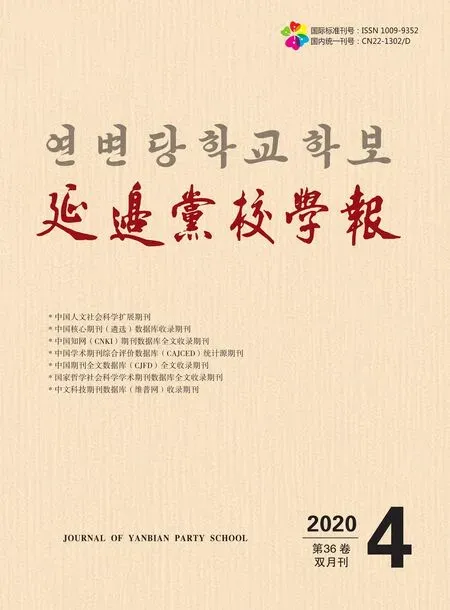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华文化观研究
2020-02-21孔翠萍
孔翠萍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中华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发展主体、具有本民族独特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文化体系,是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和文化精神的三位一体。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深厚文化滋养,具有广泛的思想引导力和社会凝聚力并随时代的演进而呈现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华文化既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和思想内核,也是世界文化版图的重镇,为世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的文化借鉴,呈现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是民族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文化发展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系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系统中综合审视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及时代布展。习近平总书记遵循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发展逻辑、本质和特征科学揭示的理论逻辑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现实价值及发展规律,进行了历史主义的审视和总体性认知,揭示了中华文化的四个维度:“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1],为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时代价值、战略地位及发展愿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遵循。
一、中华文化的历史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历史性的判断来自对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主义审视、思想指引和民族凝聚的历史价值以及中华文化作为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产生的先在意义。
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充分肯定中国人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文化主体地位。中华文化既由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而开创、培育,又反过来强化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基因和文化性格。这是一个社会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华文化的历史延续奠定了其战略地位,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性不断积淀、文化认同不断强化的历史过程。中华文化是保持中华民族独立性的精神命脉。文化提供宝贵指引,提供精神力量,对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民族独立性的保持不可或缺。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文化事业发挥作用的特点、范围及形式,将精神力量视作民族自立自强的关键因素,将文化支撑作为事业持续长久的关键因素。文化不仅是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阐明文化自信与文化繁荣的根本重要性,习近平指出“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富强,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中华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在环境,每一个时代的发展都是以人们所直接遇到的历史条件为前提和基础的,是尊重客观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与发挥治国理政的实践能动性的辩证统一的过程。民族文化的历史形态构成了后世藉以发展的文化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势必遵从这一客观规律与前提条件,既注重中华文化的历史存在而形成的前要性环境,也需要结合新时代的实践需要取得现实的发展进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理论逻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近代中国革命实践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同向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的历史传承,其独特性蕴藏着道路独特性的深刻依据。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方略中,习近平尤其注意到独特的文化传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指出独特历史、文化与国情的三位一体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依据。
二、中华文化的现实维度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国家以及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4]。文化自信既是对自身文化独特质性的坚持与肯定,也是实现文化由历史形态向时代实践融入的必然选择,是继承与发展、信念与理性的有机统一。中华文化不仅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在环境,也产生了核心价值观与历史文化的契合、适应问题。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看待中华文化的时代发展,摘取其中具有精神内核重要地位的价值观,提出了价值观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作用特点。对于以历史形态存在和延续的中华文化,习近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分析其现实价值。中华文化的历史性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历史影响的问题,中华文化的现实性需要说明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的当代融入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借鉴的问题。中华文化既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根基,也面临在新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一步结合及创造新辉煌的问题。习近平意识到中华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作用,也关注中华文化的时代发展问题。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致性,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有机结合的问题。文化自信的战略部署同时彰显了文化软实力的中国维度与社会主义维度,既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文化建设重视的历史发展,又体现了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自觉探索。
中华文化的内在民族精神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神力量。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时空中面对时代问题的文化凝聚、思想积淀、观念体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其时代主题、实践任务、历史问题与当下存在本质的不同。然而这并不妨碍其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有益探索、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思维方法所迸发出的时代价值。中华文化因其植根于中华大地,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凝聚力。中华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文化的语言形式,其为人处世与治国理政的民族内容与历史智慧尤其具有启迪、推动意义。中华文化对客观世界运行发展的内在规律、机制特点、社会优先个人的关系处理原则的教化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具有现实教育意义。在对中华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赏包括政治抱负、报国情怀、浩然正气、献身精神等在内的民族精神,提出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深层次精神内核的时代任务。他用“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说明理想信念的极端重要性,用“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来说明艰苦奋斗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意义,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说明创新的重要意义及其时代要求,勉励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中华文化内在的民族精神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直接的现实价值。
中华文化蕴藏着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与历史教训。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是中华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治理规律的中国探索的有机统一,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实践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及有益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治理有基于国情历史相继发展而形成的延续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中华文化对国家治理及其制衡因素的探讨因其基于中国国情及中国历史现实而具有高度的借鉴意义。中华文化的现实价值不仅是世界观层面的个体意义,也是治国理政历史借鉴的国家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治理文化所蕴含的历史智慧,在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上都可以发挥中华治理智慧的启迪作用和教育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说明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性;用“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说明了对时机的合理掌控与对事物发展的认知、实践方法的设计的协同性,具有辩证思维的基本维度,是对发展规律和条件协同性的有益探索,说明仅有对事物发展认知和对实践方法的抽象设计而缺乏对时势的科学分析与灵活掌控,同样不能导致失败的实践结果。马克思主义强调对时代发展本质特征的整体判断,尤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更加强调对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总书记用“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说明关于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的重大实践意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内在要求,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一致性,为观察和解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和中国式启迪。习近平援引“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来说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用“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也”说明旗帜问题和道路问题作为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和方向性问题的战略性,警醒全党在旗帜和道路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习近平援引“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的历史教训说明缺乏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价值标准、简单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裁剪评判中国现实的严重危害,阐明了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判断标准的根本重要性;用“为将之道,当先治心”说明树立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战略价值,用“秉钢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这一富有中国传统辩证法智慧的治理思想来表明树立理想信念、党性原则等“根本性的东西”的极端重要性;用“令行禁止,王者之师”和“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说明制度刚性运行的重要性;用“为威不强还自亡,立法不明还自伤”来说明党的政治威信受损的严重实践教训;用“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这一富含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智慧的用人之道来表明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深入了解干部实践的重要性;“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以中华文化的形式阐明了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趋势转化及主体应对,习近平援引这句话来说明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底线思维的重要性;“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说明了中国古人在治国理政尤其是立法问题上的思考,给出了有关注重民意基础和具体实际条件的重要性的思考,习近平援引这句话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国基本国情的坚实基础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代表了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作为衡量标准对突破旧体制、旧做法的重要意义,习近平用以说明“于法有据”与“推进改革”的辩证关系,既要改革于法有据,但不能固守“于法有据”的僵死限制,灵活地、辩证地根据有利于群众利益和实践成效的衡量标准做现实的推进。这体现了古代辩证性在当代的运用和发展。
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需要结合实践需要与时代特征增加新的理论质。中华文化在其现代时空中不仅存在对其影响力的历史性和现实价值的延续性问题,也产生其理论逻辑、思想精髓、哲学观念、精神内核与当前时代与实践的适应性问题。因此,在中华文化的问题上,不仅应有历史的观点,也应有实践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需要结合实践需要与时代发展为中华文化增加新的理论质。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统一体,是历史形态与时代成果的有机统一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渊源与发展基础,同时又面临着与时俱进、创造新辉煌的时代任务。中华文化的历史形态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与自近代中国以来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逻辑与价值逻辑相结合。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本质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为主要内容的理论逻辑、价值逻辑为基本内核和发展遵循,对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思想精神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审视,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实践需要,注入新的时代能量、新的时代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固有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增加新的理论质,实现文化吸引力、文化凝聚力在新时代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时代化实现。中华文化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
三、中华文化的民族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以战略思维认识中华文化的战略地位与时代价值的问题上,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主体性,从精神血脉的历史传承角度确立了“文化自信”这一基于历史经验教训总结、极富历史思维的格局部署。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性的坚守并不是基于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而是遵循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统一关系,遵循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而呈现的文化格局,富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底蕴。
文化的民族性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民族文化不仅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外在表现形式,更构成了民族特质的深层次原因。文化自信,最重要的是对民族文化内容及其生命力的自信,是基于深刻理论认知而形成的坚定的思想情感与文化品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在事关民族独立性的理论站位上揭示了文化民族性的重要意义及其独特作用方式。文化认同是最颠扑不破、最具时空穿透力、最能战胜困难的最深层次认同和强大精神动因,具有不可估量的民族凝聚力。论及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基础和影响因素,习近平将中华文化列在首位,指出:“两岸同胞一家亲,植根于我们共同的血脉和精神,扎根于我们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我们大家都认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都传承中华文化。在台湾被侵占的50年间,台湾同胞保持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牢固的中华文化情感,打心眼里认同自己属中华民族。这是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是不可磨灭的”。精神追求、文化秉性是中华文化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深层次文化内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继承中华文化独特传统和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由于对时代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积极回应,而成为中华文化的当代形态,是中华文化这一民族文化整体在社会主义阶段的阶段性质变,是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延长线上鼓舞中国人民砥砺奋进的精神武装。
习近平总书记主张以辩证思维的视角处理“古”“今”“内”“外”“前”“后”的对立统一。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审视中华文化的发展,针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发展、时代环境问题,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需要和实践要求,坚持问题意识和方法创新,科学把握中华文化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提出文化发展的“内”“外”“前”“后”问题,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以及中华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处理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对立统一,用“古”“今”的对子,通过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分析,指出中华文化的时代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时代价值进行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审视,提出了科学处理“古”“今”时空维度的实践要求,他认为“古”“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否定的排斥否定关系。民族性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属性,与世界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四、中华文化的世界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中华文化的世界性问题,这不是一个被迫卷入的被动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借鉴并服务本国实践的能动过程。文化的民族性是决定其能否具有世界性的价值的问题,而“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使中华文化的世界性成为现实必然。由于中华文化的独有特质而造成独特的文化吸引力,以及由于新时代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华文化的世界性问题也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文化观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分析了中华文化所蕴藏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所具有的世界价值,也指出了具有各自不同精神内核的文化间相处之道。
中华文化的世界性问题与中国的世界关注相伴而生。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中华文化载体的文化功能认知,结合中华文化的国际关注需要,提出中华文化的国际化传播问题。中华文化的国际性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问题。中华文化的世界性问题的凸显是与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习近平对中华文化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与全方面的思考,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看待中华文化的历史价值与战略地位,而且关注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与国际化问题,关注中国的时代需要与文化自觉,“要加强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中华文化内在地蕴含着世界范围内异质文明的相处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文明相处之道,既基于对各自文化特质的看重,也超出了对一己文化的固守,因而是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文化相处之道。习近平总书记以“多彩”“平等”“包容”来表明其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相处之道的看法,对不同文明的差异性、独特性表现出充分尊重,“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不仅‘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成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以战略思维审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与国际化问题,倡导开创开放、公平、公正的国际文化新格局。这一思想与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相适应。不是一尊独霸,而是共同发展。与“文明冲突论”的论调不同,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危机,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为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格局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