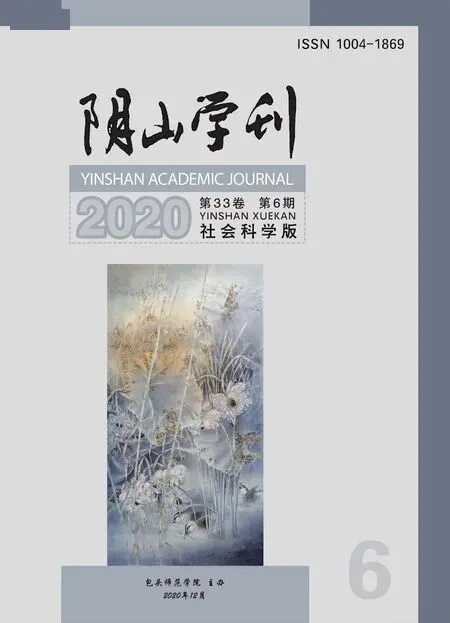唐诗中的“绡”及其审美意味
2020-02-20杨艳如
杨 艳 如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绡是一种生帛,质地薄脆,轻盈挺括。许慎《说文解字》注:“绡,生丝也。从糸,肖声”[1]。《礼记·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绡衣以裼之”[2],郑玄注《礼记》曰:“绡,绮属也”[2],《周礼》郑玄注:“轻绡一曰轻纱,薄而疏”[3],“绡又为生丝,则质坚脆矣,此绡之本质也。”[3]《释缯》则曰:“绡者,竹孚俞也。竹孚俞薄而脆,亦名曰绡,绡为生丝,其脆薄亦也卷绡之绡同”[4]。故而可知,绡与绮等丝织品应属于同类,但以轻薄、疏脆为其主要的特点。曹植以“践远游之文,曳雾绡之轻裾”来形容女子薄雾般的裙裾,左思的“泉室潜织而卷绡”更是引用鲛绡传说赞美绡的丝绸品质。绡不仅是做衣服的材料,很多时候还可以用于货币交换、上缴赋税,尤其在唐代,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可受用绡丝。因此唐人多以绡入诗,反映了唐代兴盛的绡丝生产,其诗意表达形求于趣,流露出唐人的丝绸审美。探讨唐诗中绡的特质、诗歌意象、审美美感及丝绸文化在唐诗中的渗透程度,可为解读唐诗中丝绸文化所承载的独特意蕴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唐代“绡”的种类及其用途
有唐一代,经“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两大盛世,为唐代繁盛的经济奠定了殷实的基础,由此唐代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都显示出雍容大度、兼蓄并包的时代风格。唐代丝绸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各种品类丝绸的产生,据《新唐书·地理志》及《唐六典》的相关资料记载,唐代的丝绸贡品中,品种大类有绢、绫、锦、罗、纱、縠、缎、、丝布、绮、、缯、轻容、光练、双、布、丝葛、缂丝、御服、纶巾、刺绣、丝头红毯、油衣、八蚕丝、染缬等,这些丝绸制作的难易和精致程度各不相同,在中国丝绸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从制作工艺上来看,绡是轻薄型的平纹素丝织物。与绡相似的平纹类素织物是绢,由于经纬丝粗细、捻度、密度的不同,绢还可细分出纱、縠、缣、纨、缟等多种平纹绢类织物。比较而言,纱的经纬线稀疏或有小孔;縠则是在纱的基础上做得有皱纹、有样式;纨的质地较纱更为细腻,细泽有光;而缟是平纹类素织物中未经练染的本色精细的生坯织物,它主要以轻细为特色。绡则著以轻薄透明,在纺织技艺上,更讲究蚕丝的经纬织造比例与数量,才能既薄又不失韧劲。《开元天宝遗事》中载:“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5],用绡裁制成衣,常常在酷夏所用,尽管绡衣已经非常轻薄,但也难挡暑热。刘言史《偶题》中亦曰:“迟日新妆游冶娘,盈盈彩艇白莲塘。掬水远湿岸边郎,红绡缕中玉钏光”(1)本文所引唐诗全部出自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后不再注。,隔着衣衫,犹能看到戴着的玉钏发出的光,可见唐代的绡织的确非常轻薄透亮。除了贵族穿绡衣,在唐代,普通市民阶层也穿绡衣,说明绡织品在唐代并不昂贵,这在唐诗中多有体现。只是,相较于贵族们穿戴的有纹饰且精致的绡衣,普通市民的绡衣偏于简单质朴。欧阳詹《汝川行》写到养蚕采桑女的穿着:“汝坟春女蚕忙月,朝起采桑日西没。轻绡裙露红罗袜,半蹋金梯倚枝歇”。采桑女身穿的“轻绡裙”,轻薄透明,略有花纹。白居易有诗曰:“斜凭绣床愁不动,红绡带缓绿鬟低”(《闺妇》)。该诗写一位深闺女子斜倚绣床,身披绡带,她或许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市民阶层的闺妇,“红绡带缓”,一缕闲愁围绕,红绡轻盈又恰似闲愁。再有韩偓诗曰:“酥凝背胛玉搓肩,轻薄红绡覆白莲。此夜分明来入梦,当时惆怅不成眠”(《偶见背面是夕兼梦》),描写了女子穿戴轻绡,绡长覆盖双足。再如李贺《秦王饮酒》中说:“花楼玉凤声娇狞,海绡红文香浅清,黄鹅跌舞千年觥”,诗中的“绡纱红衣”指的是身穿奢华服饰的歌女们。绡纱轻薄,在舞女的身上随身浮动,既表现出舞女的妩媚之态,也衬托了绡衣的美丽。“绡”织品轻薄和质朴的特点为唐人所喜爱,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能以“绡”裁衣,再加以符合身份的丝绸绣、染工艺,体现不同阶层的物质追求和生活档次。
唐代的绡种类繁多,相传南海鲛人会织绡,鲛人在龙宫所织的绡便被称为龙绡,有关龙绡的唐诗如数家珍,均赞美龙绡珍贵难得,如徐凝诗“披香侍宴插山花,厌著龙绡著越纱”(《宫中曲二首》)、卢纶诗“麟笔删金篆,龙绡荐玉编”(《和常舍人晚秋集贤院即事十二韵寄赠江南徐薛二侍郎》)等,化用龙绡典故,寄情于诗。由生丝织成的轻软有稀孔的薄绸子是为罗绡,徐凝《郑女出参丈人词》曰:“掣曳罗绡跪拜时,柳条无力花枝软”。杜甫笔下有“侍婢艳倾城,绡绮轻雾霏”(《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写的是朱门人家的婢女,身穿“绡绮”。“绡绮”通常是有花纹的丝绸,薄如雾,比白绡、素绡在制作工艺上更为精美。
从绡丝的印染颜色来看,唐代绡的颜色较为明艳,这得益于印染技术的提高。先秦时期便有了印染技术,《周礼》载:“染人掌染丝帛,凡染,春暴练,夏玄,秋染夏,冬献功。”[6]而到唐代,染色工艺大为发展,仅底色就有大红、正黄、叶绿、翠蓝、宝蓝、湖蓝、绛紫,藕荷、古铜等。唐朝还专门设立官营丝绸机构,少府监下的织染署为主要丝绸生产加工场所,据《唐六典》记载,唐代练染颜色有青、绛、黄、白、皂、紫六种,通过印染,唐代的绡在色泽上多元明艳,以唐诗为证。如同为“青”色,白居易《山枇杷花二首》中的“叶如裙色碧绡浅,花似芙蓉红粉轻”,是为碧绡,是青绿色的绡;而杜牧《题池州弄水亭》中的“弄水亭前溪,飐滟翠绡舞”是为翠绡,比青色更为深一点,即为绿色。绛色是贵族身份的象征,殷尧藩《早朝》写到唐代王公大臣早朝时衣着“绛绡”,列队上朝,诗曰:“曙钟催入紫宸朝,列炬流虹映绛绡”。唐代宫廷朝服选取绛色绡绢制成,彰显了王朝的气象。除了绛绡,还有一种红绡,江妃《谢赐珍珠》中的“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是为红绡,红绡多为歌舞女子所穿,因此,透过织染的绡衣,还可窥见唐代织染颜色所对应的人物身份。唐诗中少有出现黄绡、白绡、皂绡和紫绡一类,但王建诗中出现藕绡,实为特别的颜色,诗曰:“藕绡纹缕裁来滑,镜水波涛滤得清”(《上李益庶子》)。藕色是一种浅灰略带红色的颜色,《红楼梦》第四六回写到了这种半新的藕色绫袄,可知这种颜色不太常用,也不显新。另有姚合诗说,唐代“裁绡样岂似,染茜色宁同”(《和王郎中召看牡丹》),这里的茜色也较为少见,但总体而言,唐代的绡织在色彩上是多元且明艳的。
唐代丝绸在社会中的用途是广泛的,除了可以裁制成衣,也有用绡来做帕子、头巾、裹布等。李煜有诗“牙签万轴里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题金楼子后》),这里的“绡”就是一块红丝布,诗中写到梁元帝惜书如命,用红丝布包裹书册珍存,说明古代“绡”是柔软且不易损坏的,可以长时间保存。白居易“泪痕裛损燕支脸,剪刀裁破红绡巾”(《山石榴寄元九》)、“绡巾薄露顶,草屦轻乘足”(《香山寺石楼潭夜浴》)、“竹鞋葵扇白绡巾,林野为家云是身”(《游丰乐招提佛光三寺》)三首诗都提到绡巾,绡巾是由丝织原料做成的薄丝头巾。唐代以前就早有束发的绡头,《后汉书·独行传·向栩》里有记载说:“(向栩)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着绛绡头”[7]。唐代绡巾轻薄能擦拭面汗,既是头巾装饰,也是帕子。元稹的“歌辞妙宛转,舞态能剜刻。筝弦玉指调,粉汗红绡拭。”(《寄吴士矩端公五十韵》)几句诗,写到一位抚琴女用“绡”巾擦拭汗水,可见绡巾在人们的生活中较为常见。
另外,绡是人们进行日常交流与外传的重要物品。唐代随着交通的发达,丝绸的陆路和海陆的畅通,使得丝绸成为一条连接世界各大陆的纽带,它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货物实体,也是唐代与异域文化交融与发展的载体。绡是唐代较为普遍的、原始而素简的丝绸之一,但它的用途依然不可小觑。唐代曾以“绡”为贡品。如《新唐书》记载:“徐州彭城郡,紧。土贡:双丝绫、绡、绵、绸、布、刀错、紫石。”[8]彭城郡在唐代的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徐州市中部、安徽省淮北市东部一带。据此可知,唐代江苏、安徽一带可能产绡。这些地方以绡帛为贡品,可知产量不薄。绡亦可当税来交,张籍的《促促词》中写道:
促促复促促,家贫夫妇欢不足。今年为人送租船,去年捕鱼在江边。家中姑老子复小,自执吴绡输税钱。家家桑麻满地黑,念君一身空努力。愿教牛蹄团团羊角直,君身常在应不得。
这首诗写的是吴地一家贫贱夫妻,因各自忙碌不得见面,所以凄苦万分,诗中提到的“吴绡”,便是吴地产的绡丝。妇人日日辛苦织绡,为的就是为官府补交税钱,最终得以与丈夫团聚。唐代的贡赋制度已经完善,“由于唐代贡赋原则上均是根据当地土产情况而定的,较为可靠地说明了当地丝绸产区的布局”[9]。从9世纪末到11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沿海转移,由于社会经济的需要,唐王朝加大了对东南地区的开发,丝绸产地扩展,产量增加,朝廷命官也常常劝民耕桑,因此东南地区逐渐成为丝绸生产的密集区。与此同时,唐代社会的繁荣带动了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岭南地区后来也成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陆龟蒙“蜀彩驳霞碎,吴绡盘雾匀”(《奉和袭美太湖诗二十首·圣姑庙》)的诗句,写的是蜀地的帛彩和吴地的绡帛。由此来看,绡的产地大抵在南方一带,而且鲛绡出在南海,更有姚系《送周愿判官归岭南》诗“山驿风月榭,海门烟霞城。易绡泉源近,拾翠沙溆明”说明岭南地区也有绡帛,那么就绡的产地而言,唐代吴地和岭南地区是产绡的,从唐人笔下“绡”织品的丰富书写来看,我们可以对南方的丝绸生产、丝绸贡赋以及丝绸之路的发展有一定的了解。
唐代绡丝还有一个用途是货币流通。白居易诗中写道:“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琵琶引》),缠头是古代歌舞艺人表演结束时,听客们赠送给艺人的锦缠头。琵琶女年少时美名远播,一曲弹罢惹得京城子弟争先恐后给她喝彩,弹完一曲收来的红绡不知其数。在这里,绡充当了赏钱的角色。达官子弟不把它作为珍宝来看,更多的是一种赏赐的小钱。唐代皇帝也常以绡作为赏赐,王维诗曰:“薄赋归天府,轻徭赖使臣。欢沾赐帛老,恩及卷绡人。去问珠官俗,来经石砝春。东南御亭上,莫使有风尘”(《送元中丞转运江淮》)。安史之乱前,江淮地区轻徭役,广施恩,州县殷富。皇帝赐老臣丝帛,百姓也得到薄税的好处。唐代的商品交易中,绵帛等丝织品可直接充当货币使用。唐代钱贵绢贱,白居易《卖炭翁》中说:“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半匹红绡和一丈绫,比一车炭的价值相差很远,却就此充当炭的价钱了。白居易诗讽刺了唐德宗时太监专管其事,公开掠夺的恶行,同时也直述了红绡的廉价。
“绡”还被文人墨客当成一种指代性名词,代指人名、书画作品等。白居易“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咏兴五首·小庭亦有月》),干脆以美丽的“绡”作为女性的名字了,这也体现了唐代绡织品的普遍性。很多文人将“绡”用来作画、写书法,如杜甫“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中的“绡”借指书法的神妙;韩愈《桃源图》曰:“生绡数幅垂中堂”代指画卷,古代未漂煮过的丝织品均可作画,李隆基的《题梅妃画像》曰:“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画在绡上的梅妃形象虽然逼真,然而毕竟不能以娇波顾人,少了些许生气。由此可见,“绡”在唐代社会中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
二、唐诗中的“绡”意象
全唐诗中约略有110首诗提及“绡”,唐人吟咏绡丝物事,不仅是因为他们享受了绡的实用价值,而且还赏识绡的审美价值。随着唐人文化自信的不断建立、深入,又逐渐赋予了绡丝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成为唐人文化品格书写的内动力。绡意象既是唐代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又是丝绸文化与中国神话相结合形成的文化意象,具有象征意义。
1.绡帐
帘、帐等是古代常用的遮蔽物品,古代家庭中悬挂帘帐于不同的场所,遮寒保暖,遮蔽视线,或者用来分隔空间。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常出现帘、帐这类遮蔽物品意象,既展示帘幕的细腻做工,又表达诗人隐约幽深的情感。唐代以帘幕为意象的诗歌尤其多,唐人品性细腻,每每通过一帘之阻隔怀想千篇。
绡因其轻盈薄透可制作成帘帐,如李贺诗中“西施晓梦绡帐寒,香鬟堕髻半沉檀”(《美人梳头歌》)的“绡帐”,说的是美人西施躺在薄薄的罗帐里周游梦乡。诗人在此用绡帐,衬托美人的慵懒与富贵之态。冯延巳诗歌则通过对绡帐的拟人化描写诉说愁绪,《如梦令·尘拂玉台鸾镜》中的“绡帐泣流苏,愁掩玉屏人静”一句,以一个“泣”字赋予了绡帐以生命,把一帘阻隔内外的帐子写活了,同时“泣”字也点出了作者“闲愁”的词风,能使读者对所表达事物产生鲜明的印象,产生强烈的感情,引起共鸣。在该部分第二句,作者也巧妙地用“掩”这个字将“愁寂”这种空间之感具体化了,以动写静使人更觉其静。
2.绡幕
唐诗中多以绡幕比喻天地之间的浑然气魄之景,如杜牧“香连日彩浮绡幕,溪逐歌声绕画楼”(《和宣州沈大夫登北楼书怀》),这句诗描写的是诗人站在谢朓楼上,在太阳的光芒下,天地有如绡幕悬浮,景象壮观;任希古《和李公七夕》也以景喻为绡幕:“开轩卷绡幕,延首晞云路”。这是一首写景诗,诗人把雾帘看作是轻薄的帘帐,开窗可见薄纱帘帐,有置身仙境的幻觉;杜甫诗《夜宿西阁,晓呈元二十一曹长》有“城暗更筹急,楼高雨雪微。稍通绡幕霁,远带玉绳稀”的句子,诗中所描绘的是刚刚停了雨雪的西阁外,天亮了起来还未完全放晴,诗人在西阁楼上远眺,天地好似通绡帘幕,这样的胸襟与气魄,唯有唐人才肯锤炼得来。
3.鲛绡
鲛绡是传说中鲛人所织的绡,是一种独特的衣服,也泛指薄纱,或宫中美人跳舞时所穿的衣服。但是唐诗中的鲛绡意象,多赞美鲛女织绡的勤劳品质,咏叹鲛绡的珍贵与美丽。相传鲛人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鱼尾人身的生物,《述异志》说“鲛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博物志》记载:“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10]。《搜神记》记载:“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11],据这些记载可知,鲛人不仅能纺织出五彩的鲛绡,鲛人还可以滴泪化作粒粒美丽的珍珠。古代诗人提及“鲛绡”总要联想鲛女织绡的过程,催生怜悯疼惜鲛女之情。唐代李颀最早所作《鲛人歌》,便摹写了鲛人的生活状态和鲛绡的纺织情状:
鲛人潜织水底居,侧身上下随游鱼。轻绡文彩不可识,夜夜澄波流月色。有时寄宿来城市,海岛青冥无极已。泣珠报恩君莫辞,今年相见明年期。始知万族无不有,百尺深泉架户牖。鸟没空山谁复望,一望云涛堪白首。
这首诗前四句介绍鲛人是何物、鲛人何以织绡。仅仅凭借夜夜波动的水面和流光月色,我们就可知鲛女纺织的勤奋。而那些辛苦织好的绡丝,还需要鲛女上岸卖出去:“有时寄宿来城市,海岛青冥无极已。泣珠报恩君莫辞,今年相见明年期”,鲛人携带织成的绢绡来到城中市坊售卖,寄宿的人家对他很友善,鲛人约定明年还来这家人家中报恩,因此泣下眼泪,化为明珠,赠与人家。“始知万族无不有,百尺深泉架户牖。鸟没空山谁复望,一望云涛堪白首。”诗的末四句是作者对于读罢鲛人故事后的感叹,通过鲛人的故事,作者认识到大千世界物类纷繁;同时作者也意识到,如此多情、勤劳的鲛人哪里寻得,就像飞鸟去往无人的寂静深山一样,无法追随其踪迹;意在说,鲛绡固然精美,但世所罕见,无法获得。
如以上表达的诗句还有杜甫的“箫鼓荡四溟,异香泱漭浮。鲛人献微绡,曾祝沈豪牛”(《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骊山温汤之东有龙湫》)、顾况的“帝女飞衔石,鲛人卖泪绡”(《送从兄使新罗》)、吴融的《鲛绡》题诗“云供片段月供光,贫女寒机枉自忙。莫道不蚕能致此,海边何事有扶桑”等,鲛女的生活清苦,与珍贵的鲛绡和鲛人泣下的珍珠形成了对比,诗人以此“鲛绡”意象,表达对鲛人勤劳、勇敢、守信美德的赞美,也同时突显了唐人的文化品格。
唐人还巧用鲛绡的细腻,来抒发诗人缠绵、细腻、梦幻的情感,达到一种审美追求。鲛绡柔美坚韧,“江烟湿雨鲛绡软,漠漠远山眉黛浅”(罗隐《相和歌辞·江南曲》)把江南的烟雨比作鲛绡,足见江南的温润,也可见绡丝细腻;“龙宫月明光参差,精卫衔石东飞时,鲛人织绡采藕丝”(顾况《琴曲歌辞·龙宫操》)呈现了一幅龙宫织绡采藕图,延续神话笔触;温庭筠《相和歌辞·张静婉采莲曲》有一句“掌中无力舞衣轻,翦断鲛绡破春碧”,展现了如春碧色的鲛绡舞衣。李商隐“鲛绡”诗歌“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卷四《外编》下),亦是表达李商隐的审美情趣。而其诗作《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围绕梦境展开,诗人凭借雨、梦、鲛绡帘幕这类道具来求得飘忽绵邈之趣以及扑朔迷离之美。李商隐另有诗:“弄河移砥柱,吞日倚扶桑。龙竹裁轻策,鲛绡熨下裳”(《玄微先生》)、“河伯轩窗通贝阙,水宫帷箔卷冰绡”(《利州江潭作》)、“五里无因雾,三秋只见河。月中供药剩,海上得绡多。”(《镜槛》)均以鲛绡为意象,营造出一种迷离朦胧,让人难以捉摸的诗歌意境,体现了李商隐崇尚朦胧美的审美心态。
唐人吟咏鲛绡,一方面是诗人承继鲛人织绡神话传说,对其进行新的演绎,另一方面是对丝绸物事的独特感知。“谁遣虞卿裁道帔,轻绡一匹染朝霞”(李贺《南园十三首》),唐人将“绡”与周遭联系起来,借此表明自己的清高志向。唐人赞许鲛人的品质,更赞美鲛绡之美,也抒发诗人细腻温润之情思,为唐诗增添朦胧之美。
三、丝绸文化与唐“绡”的审美意味
丝绸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唐代丝绸沿着陆路和水路两大丝绸之路传向欧洲等国,所带去的不仅仅是一件件华美的服装、饰品,更是中华民族古老灿烂的文明,因此,丝绸在促进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丝绸文化起源于中国古老的蚕桑文明,而蚕桑的起源又充满了神话色彩。上古时期,桑树被认定为“神树”,《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12]扶桑神树是太阳金鸟的栖息地方,它可以连接人、神、魔三界。因此,先民将桑树、桑林封为圣坛,祈雨求子、施行巫术。于物质而言,桑树最早为先民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产原料,但于精神而言,桑树更是满足了先民们的原始心理,构建了人类天地同一的哲学思想。后来各代的典籍有很多记述了桑树神话,同时也记述了以桑为原型的宗教、舞蹈、祭祀活动。随着人们对蚕食桑叶的认识,春蚕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春蚕“食桑而吐丝”“功成而身废”,人们每每通过赞美蚕的温暖、勇敢和奉献精神,来倡导温暖人间、兼济天下的人文精神。当一缕一缕蚕丝,在采桑女手中一茧一丝养成,一针一线绣织后,丝绸便具有了更高一层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
商周时期,人们生产绢、绣等丝绸产品,制成华丽的衣服或是饰品,提高了丝绸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春秋时期丝绸生产数量明显增多,宫廷与民间的丝绸纺织技术各有所能,丝绸工艺融入广大人民的内心情感,使得丝绸更有了人间情味。秦汉以后,有关纺织的提花机、斜织机等陆续发明出来,丝绸生产渐成体系;又有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方贸易往来,其中丝绸成为通往西域主要的商品之一,丝绸对外贸易空前繁荣。不仅如此,汉代丝绸已经印有了中华民族的标签,走出国界,走向世界。
唐代丝绸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唐代以强盛的国力为根据,以泱泱大国的文化自信和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王朝格局,形成一个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这对丝绸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唐代丝绸生产工艺的变革进一步提高了丝绸的纺织效率,丝绸的纹样、印染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再加之唐人尚胡风,唐代的丝绸在艺术上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藉此,唐代的丝绸文化即从一种物化的文化,上升成了一种审美文化。在海、陆丝绸之路的推动下,丝绸还作为一条纽带,把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紧密联系起来,用世界话语升华了丝绸的文化品格。
唐代诗人吟咏丝绸物事,实为对中国丝绸文明及丝绸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基于对丝绸文化的理解,唐代诗人笔下的那些绡诗,或直抒绡丝质朴与柔美,或敬畏裹在绡帕里的珍贵典籍,或叹绡衣与美人同命,或赞天地如绡幕般的壮阔景象,绡丝与人、物、景合为一体,体现了唐代诗人对绡的本质的认识和绡文化内涵的解读。
绡是生丝,因其至纯至真而保持着丝绸朴素自然的气质,绡的质地细腻,具有柔美而高贵的视觉审美印象。唐人以绡入诗,将绡与扇子、风等物象结合起来,如李存勖诗句“纨扇动微凉,轻绡薄,梅雨霁,火云烁”(《歌头》),纨扇微动,便觉凉意,衬托了绡的轻薄。若说绡本是朴素且不乏气质,卢士衡的那首《题牡丹》“万叶红绡剪尽春,丹青任写不如真”,以牡丹比作红绡,借用绡丝的柔美特质,描摹牡丹的美艳与高贵,从视觉上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而对于身穿绡衣的女子来说,“红绡撇水荡舟人,画桡掺掺柔荑白”(李咸用《塘上行》)的画面也给予诗人视觉冲击,诗中红绡画中人,着实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唐诗赋予了绡以艺术生命,这是对丝绸文化内涵多层次理解的一种新的尝试。
丝绸的生产需要付出很多的辛劳和智慧,数千年来,正是一代代华夏儿女勤劳织作,求真务实,才推动了我国丝绸工艺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唐人笔下的鲛绡书写虽说带有浓郁的神话色彩,但是不乏对中国人勤劳质朴、求真务实品质的反复赞美,在这一文化内涵的高度上,唐代绡诗具有了很高的价值。
绡作为丝绸中的一种类型,对唐代的日常生活甚至是风俗教化起到了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唐代,绡主要被裁制成为衣饰。《新唐书·吐蕃上》记载,文成公主下嫁给松赞干布后,不仅将佛教和内地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带到了高原,进一步促进了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还鼓励吐蕃人承袭中原服饰特色,强调“袭纨绡”,学诗文。由此可见,唐代“绡”已经代表中原的丝绸,成为一张文化名片,推动了唐代吐蕃对中原服饰文化的认同。另有陆颙《宣室志》记载南海鲛人捧珠献给胡人,一女“貌极冶,衣雾绡之衣,佩王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盘,中有珠数十,来献胡人”,南越是岭南之地,“货于南越,获金千镒”,岭南鲛绡丰富,鲛人织绡化泪的传说也多半源于此,该文中多次提到鲛人捧珠来献给西域胡人,有将中原文化植根给胡人之意,实为唐绡的有趣之处,印证了唐绡的文化价值。
综上所言,唐诗中所反映的绡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种类和用途是广泛的。唐人的“绡”织书写囊括了唐代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形态、审美追求和精神向往,以绡为意象的唐诗,营造了柔美、朦胧的诗歌意境,传达了唐人对丝绸品质的理解与推崇,推动了中国丝绸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唐代的绡,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给唐人带来无数慰藉,无以计数的绡诗便是唐人对丝绸文明的绚丽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