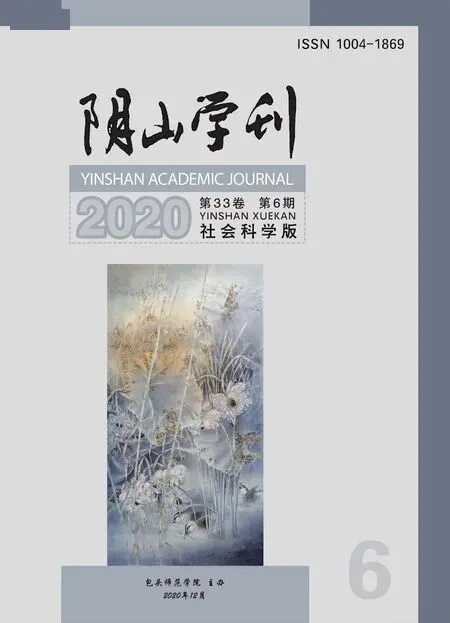权力·话语·身体
——省思《人生海海》的个体生存困境
2020-02-20袁香
袁 香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麦家以“谍战小说之父”的头衔跻身于作家行列,从2002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伊始,相继创作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他善于塑造远离尘世烟火的天才人物及其传奇的一生,在抽丝剥茧的叙述中解密重重的故事疑云,其中深不可测的人性、险象环生的命运始终是其创作的不变母题。“我试图从乡村出发,从一个人的苦难,从一个不可描述的地方描述我们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怀揣这份浩瀚的文学野心,麦家带着八年岁月的凝结之作《人生海海》重归大众视野,不再重复书写凌驾于生活之上的英雄和天才,不再庸于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而是把目光聚焦到一个老式的江南山村,让英雄回归世俗生活当中,以“我”之眼窥探昔日英雄“上校”颠簸起伏的一生,同时“我”作为亲历者,一同承受着乡土社会权力体系的施压,凸显出人与社会环境的紧张对抗关系及其苦难命运,进而达到对乡土社会伦理秩序的批判性审视和个体生命况味的终极关怀。
本文以“上校”的形象建构和身体刻写为中心,影射权力话语对个体所施加的规训和控制,进而探讨个体的生存困境。
一、权力的符号化表征——话语的暴力游戏
麦家在《人物》杂志的采访中谈及童年,特殊的家庭成分带来的不平等待遇促使他倍感人生的孤独和痛苦,另一方面也更能觉察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这些独特的个人经验也构成了他写作的根基,对人性的幽暗和乡土伦理的固化有着更为敏锐的觉察力,表现在新作《人生海海》中复杂暧昧的人物关系和无望的人生境况,究其实质是权力演绎的结果。麦家通过两种异质性的话语模式向我们呈现了权力秩序的运作方式,以不为察觉的个体话语作为符号化表征,来确立中心权威和伦理规范向世人施暴,而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既是权力的施加者也不自觉地承受着权力的规训,沦为丧失自由意志的群体一员。
念过私塾也开过学堂的爷爷,在村中颇有声望,被视作民间思想家、哲学家和评论家,深谙各种人生哲理和世故人情。作为乡土社会中常见的智者形象,爷爷使用的是一种简练、讲究、富有生活哲理和乡土气息的语言,像“天要落雨,娘要嫁人”“世间海大,但都在老天爷眼里,如来佛手里,凡人凡事都逃不出报应的铁链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1]“收音机里看不见人,玻璃柜里藏不了人”……爷爷常引用大道古理和民间俗语,这些涵盖了集体记忆和历史经验的话语在乡土社会中被视作普遍真理,在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关联性和控制力,无形中规范着每个人的行为举止。因而当爷爷以“体面”作为人生信条时,其言语行为也受到了伦理秩序的监督,在儿子陷入“鸡奸犯”的污名化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日益凸显。“准天塌下来,也不准鸡奸犯这污名进我家”,爷爷教育“我”大打出手,并随身带一把白亮的三角锉刀,方便对传谣者一招致命,认为即使偿命也好于顶着污名活着。“污名化”的身份标签刻写了“不具备被社会完整接受之资格的个体的处境”,消弭了个体在社会中的身份认同,暗示爷爷一家人已沦落到被排斥、被边缘化的现实困境。爷爷家从受人尊敬到众人唾弃,这种巨大的身份落差隐射了封建伦理对个体思想的固化,鸡奸这一行为本身背离了传统道德,因违反了乡土社会长期以来遵守的伦理信念而受到惩罚,爷爷由此生出强烈的贱斥感(1)贱斥感指主体身心遭受不洁的危险威胁时所产生的对抗力量。正是伦理秩序作用于个体的产物,促使爷爷不惜轻贱生命来维护传统道德。至此,“污名”构成了一种权力话语凌驾于个体的生命之上,操纵并管控着生命秩序,个体也在不自觉中充当着这种自我监督和约束的对象。
与此形成共谋关系的是爷爷反身成为中心话语的支持者,在摆脱耻辱身份的过程中,逐步走向了自身所信奉的道德良知的背面。爷爷将汉奸身份公之于众作为前提,偷偷向公安举报上校,以此摆脱“我”父亲的鸡奸犯身份,同时也将全村敬重的上校推向了死亡边界。爷爷的行为动机是“我是不想让你背黑锅,叫一家人被当贼看,丢人……”[1]233,不再让全家人蒙受羞辱,维护“家族的体面”作为爷爷违背道德伦常后的一种补偿性的话语修复,体现了个体难再与现实情境对抗的无奈心理。从起初的对抗到无奈的屈从,话语逐步成为一种主宰个体生命的合理秩序,其实质就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外化,作为真理存在的传统道德信念受到了巨大冲击,外化为爷爷的人物形象的崩塌,进而成为全村人心头的畜生、恶棍。这种话语所形成的认知暴力也导向了爷爷的自杀以及“我”一家人的悲剧命运。与此同时,反观“去污名”的整个过程,爷爷与认知暴力的关系又是极其暧昧的,一方面他建构了中心话语,是认知暴力的实施者;另一方面他又是权力话语旋涡下的牺牲者,是集体暴力裁决下的他者,其生的困窘皆源于依附和盲从于伦理信念的权威性。
特定的时代总会生成一套与其相适应的官方话语体系,显示出权力与话语之间紧密的关联性。在“文革”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小瞎子所代表的红卫兵团体一跃成为时代的领导者,其话语宣扬传播文明和现代理性精神,煽动年轻人投身到剔除旧社会思想顽症的斗争当中。以批斗“反革命分子”来确认统治阶级身份的权威性,打砸寺庙和祠堂来摧毁乡土民众的精神信仰。其对“反革命分子”上校的规训和批斗话语,很大程度上可视作对个体的自由意志和异质性思想的抹杀,使红色真理对乡土文化和自我意识的侵蚀合理化、合法化甚至崇高化,进而重构一个集体化、同一性的乡土世界。麦家通过对红卫兵团体的形象及其话语实践的展开,呈现了“文革”的“新思想”是怎样改变了乡土社会的全貌,进一步揭露图示化的权力是怎样隐匿到意涵着“现代意识”的话语之中,取得了充分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促使人无意识地服从并参与到权力秩序的建构当中,自觉地被支配和征服。即使是时隔多年,手脚尽废的小瞎子依然能够相隔万里,借助作为话语载体的科技产品来对“我”进行精神施暴,可见话语在世代更迭下依旧是知识和权力的形象化表征,其破坏程度可见一斑。
“一方面权力建构着话语,掌控着秩序;另一方面话语构建着并争夺着权力,维系或挑战秩序。权力和话语相互渗透、相互建构,人们通过一定权力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与其他话语体系抗衡,通过话语斗争寻找自身在话语秩序中的位置。”[2]简言之,话语既是权力的组成部分,也是权力抗争的结果。与爷爷相比较,老保长的话语截然相反,讲故事时“有两多一少:多的是废话和脏话,少的是具体年份。”[1]154闲聊时“多是下流话,荤故事,男欢女爱,色情淫秽”等较为粗鄙污秽的词语。在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村庄里,老保长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在他的话语表述中,生活的物质性和个体的欲望得到了充分合理化的表达,强调个体感官所获得的愉悦,追求物质享受和身体本能的欲求而非精神意义上的富足,皆与传统的伦理观念背道而驰。在庄严肃穆的批斗大会上,他一身酒气,用散漫毫无逻辑的话语证实了上校的身份谬误,戏谑社会权力体制甚至威胁到当权者的中心地位,使本是政治色彩浓郁的批斗会变成了一场荒诞的闹剧,极具有反讽意味。老保长的话语排斥主流价值体系和伦理观念,其一生不受权力体制的控制和束缚,活得随心所欲。相反,固守伦理道德的爷爷自始至终也不得安耽,二者的命运归宿形成强烈对比,表达了话语兼有的束缚和反叛力量,同时对固化的传统道德观念提出质疑,对加诸人们身上的权力话语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构成挑战,是个体反叛意识的初步觉醒。
二、权力话语对身体规训——自我意识的剥夺
麦家通过两种不同的话语模式,揭示了话语是怎样成为权力的载体,影响并改变着人物的命运。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受制于各种权力关系的锻造,经由话语的形式施加到身体的维度上。“身体不是私人性的表达,而是一个政治器官,是宇宙的和社会的实在之镜像,反映着人的病相、毒害和救治过程。在身体这个位置上,人们可以审美地、社会地、政治地、生态地经验世界。”[4]文中从不同的身体界限上探讨社会权力话语是如何运行并对身体进行“有利”的改造,进一步探询个体生存困境及其背后意涵的时代症候。
上校的前半生走南闯北,既杀敌也行医救人,立功受奖,是人民敬仰的英雄,后来遣返回乡后,就有了“太监”的绰号。传统的伦理观念认为断后的人是前世作孽太多,今世才会受到这种惩罚,身边人也会牵连受难。所以爷爷从来不让上校进家门,调皮捣蛋的小孩敢当面叫喊“太监”,昔日的英雄形象在这样的排斥和调笑中似乎荡然无存。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性”作为身体最基本的本能之一,为人类的一切活动提供了生物性的动力,广为接受的“太监”这一身份标签意味着昔日的革命英雄失去了男性的生理特质,是身体的耻辱。其表层含义是上校失去了追逐世俗幸福的本能冲动,但放在时代背景下思考,被阉割的身体绝不仅限于表征个体的隐疾,它关涉着深层社会政治权力关系的转变。“性是在权力为了控制身体及其质料、力量、能量、感觉和快感而组织的性经验的展布中最思辨的、最理想的和最内在的要素。”[5]性服从于权力话语的支配和操纵,上校性无能的身体在村子里被放大、被渲染,是政治去势的隐喻,在褪去了战争迷雾向现代化行进的社会中,他所代表的革命英雄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时代所抛弃。
“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6]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和权力技术,围绕着身体展开角逐,身体成为社会文化和权力机器合谋建构的场所。“文革”期间,上校因身份不明成为重点改造的对象,捆猪的麻绳绑着上校的身体,在村里大阵仗的游斗,文中麦家用描述性的手法揭示了上校身体的改造过程,“以前在村子里走,一向是腰板笔挺,昂首阔步,神气活现。尤其到大冬天,他总是要穿着那双高帮大靴子,靴子底下掌满铁钉,在鹅卵石上走过,即使是在冰雪上走,照样喀!喀!喀!像一匹战马在行军。而现在,他变得像一只癞皮狗,要人拖着走,架着走,威风扫地,狼狈不堪。”[1]154先是肉体遭受伤害,接着是精神打击“两只手被剪在背后,绑着,头上戴着一顶圆锥形的大高帽子,上面写着“人民公敌”和“十恶不赦”,挂胸前的纸牌子上也写满各种罪名,还打一个红色大叉叉。”[1]63在此,权力隐匿于爱国的话语之中,确立了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对人身体施加的管控也进而成为捍卫家园和正义的合理手段。在一系列的批斗和闹剧中,上校被建构成一个威胁集体化统治的反叛者,其身体被赋予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反动性特质,通过官方话语规训和群众裁决等带有表演性行为的教化和改造,削弱了反叛个体的自我意识,以作为对当权者身份的体认。
在形如“全景敞视式监狱”的批判大会上,上校的身体暴露在公众的集体“注视”中,沦为被观看的“他者”。在严格的监视下,强势的权力由集体注视的目光投射到“他者”身上,发挥着干预作用。当上校的身体被视为“不洁”之物,瞎佬和群众企图揭开其身体私处的耻辱时,“瘦弱的上校刚才似乎连站都站不住,这下却爆出天大的力量,像手榴弹开了爆……他喉咙像安了扩音器,身躯像一匹野马,横冲直撞……他一路嗷嗷叫着,冲着,把人群像浪花一样一层层拨开…”[1]69就这样,带着时代的精神创伤和耻辱印记,上校变成了精神病人,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识。福柯在《权力和惩戒》中阐释了“注视”在社会公共场域中产生的压制和惩戒效果,麦家在文中将这种无形的权力外化为群体的“注视”来运行对上校身体的管控,最终上校成为注视目光下的承受者和受害者,权力对身体的改造是如此具有震慑力,以至于权力的“注视”最终渗透进人的灵魂深处,“他发癫时见人要打,见刀要抢,捅自己小腹”[1]256,主体意识在权力禁锢下也被无限期的延宕了,其生命仅剩肉体意义的存在,精神意志已然消亡。
麦家将上校近似一个世纪的生命长度,具象化为不同形态下的身体呈现出来。固有的伦理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盘踞在乡土社会空间中,羁束着身体的能动和感知,在层层权力关系的规训和约制下,个体丧失了生命活性,外显的身体被削弱为空洞化的生命存在,消解了个体的社会价值和基本意义,这即是当代乡土社会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
三、身心的回归——重构自我认同
文学不是一块遮羞布,其意义不在于编织生活的美梦,而在于揭露不为人察觉的幽暗的现实角落,触发个体反思。麦家从权力、话语和身体三者的关系维度,深刻揭示了权力话语对人施暴的过程及置身其间的人的生存之艰,同时也用个体的时代省思予以回应,阐释了个体的精神与肉体如何挣脱权力支配而重构自我认同。
(一)身体回乡—于时间之流重拾身份认同
故乡对麦家而言并不美好,在过往的写作中他有意回避故乡和童年经验,直至亲人离世后才敞开心扉。“故土就像母亲,母亲即使把你抛弃了,你还是想方设法去寻找她。这中间没有道理和是非,只有“存在”—海枯石烂都改变不了的东西。”[7]故乡作为记忆的载体,构成了人的部分存在,那么,回到故乡在某种程度上就意涵了寻找个体的身份认同,麦家将独特的个人经验熔铸到主人公“我”身上,“我”的归乡之旅就携带了两重含义,不仅是“我”的自我救赎同时也完成了麦家对于自我的身份确认。
“文革”期间,爷爷的不耻行径使“我”受到了基于道德伦理的集体宰制,不得不踏上逃亡的征途,异国的孤独成为权力话语给“我”的永久性惩罚,时过境迁,“我”依然身心煎熬,失去了身体和灵魂栖息的家园。狄尔泰曾说:“若人们把过去置诸脑后,以便重新开始生活,就会完全徒劳无益。他们无法摆脱过去之神,因为这些神已经变成了一群游荡的幽灵。我们生活的音调是取决于伴随着过去的声音的。”[8]也就是说,过去是“我”的一部分,回到故乡,消除童年时期的阴影和困惑,成为“我”多年身心流浪后获得主体意识的主要途径,也是摆脱道德禁锢的一种反叛动力。在两次回乡中,过往的苦痛和凄怆一拥而上,经过内心反复的挣扎,“我”最终捐助了小瞎子,淡化了过往的仇恨。这一举动是“我”从心里原谅了这位暴力的施予者,同时也解救了自身,标志“我”主动接受并涵化了伤痕记忆,由此也解开了精神的禁锢。陪伴上校走完人生的过程中,我印证了父亲不是鸡奸犯的事实,彻底击碎了小瞎子的谎言,心病的逝去伴随着重拾自我认同,“无罪的我”主动建构了自我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同时与自身达成和解。“这是我的胜利,饶过了他,也饶过了自己,我战胜了几十年没战胜的自己,仿佛经历一场激烈的鏖战。敌人都死光了,一个不剩,我感到既光荣又孤独,孤独是我的花园,我开始在花园里散步,享受孤独留给我的安宁”。[1]257主体战胜了自己的心病,获得了久违的归属感,同时也摆脱了身心的负罪感,得到了解脱。这正是麦家所希冀传达的人生海海的真谛,“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在时间之流中,受损害的身体重返故乡—精神的原乡,直面过去的伤痕印记,主体克服并将损害内化为自我主体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重获自身与乡土社会的联系,即是个体身份的寻回。
(二)自我关照——于感激中重构生命价值
多年后“我”再一次见到上校,他的神色全然不同。“面色红润,双眸明亮,白白胖胖的,加上一头晶晶亮的白发,十足像一个鹤发童颜的洋娃娃。他白净饱满的面容,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换过皮肤,白得生机勃勃,富有弹力活性,完全是孩子的风采。”[1]344上校在林阿姨的关怀与照顾下,创伤的身体得到了修复,仿若回到孩童原初状态。对于人的疯癫状态,福柯认为“疯子并没有失去人的本质或基本的人性。他恰恰构成人的基线、人的本真;变成真理、正义、直言和诚实的化身,构成一种对社会现实、伦理道德、科学文化的激烈否定和有利批判。”[9]疯癫后的上校只有七八岁孩子的心智,还未建构与世界的联系,因而他的行为更多出于本能直觉和无意识的冲动,而非权力和理性的操纵。
上校逢人就展示自己的画作,将身体上烙印的耻辱柱以图画形式进行修正,一些侮辱的言辞被改成富有家国主义和爱国热情的“命使我乃鬼杀奸除”“军令如山”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必胜”等字样,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创伤后的话语补偿,作为自我无意识的创伤修复,经过想象性的满足上校完成了自我的疗救,也于想象中重获了个人的社会价值和信仰。“上校”的残年生活归于平淡,即使是养蚕拨丝这种简单的工作,上校也一丝不苟,表现得十分突出。作为一种社会性行为,工作的意义“不仅源于其提供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开销来源,更重要的是,人们所从事的工作界定了他们自身在社会的整体想象中所拥有的身份地位”。[10]上校在孕育蚕蛹的工作中再一次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和钦佩,可视作重获自身的社会位置,其认真热爱的态度彰显了对于生命个体的珍视和积极态度。林阿姨花费余下的一生照顾上校,用爱的雨露呵护上校,用文身技术祛除了上校身上最隐秘的耻辱,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垂有四盏灯笼的大树的画作,隐喻了生命的美好和希望,同时也涵化了个体的受难意义,拯救上校身体的同时也治愈了自身。麦家通过个体的社会性实践去关照身体和灵魂,改变了自我的存在状态,也由此获得了挣脱权力规范追求自身价值的动力,进而在新的价值体系中完成身体与自我的主体重构。
四、结 语
麦家从权力、话语和身体的关系维度,深刻揭示了权力如何内化并作用于话语,实现对人的暴力压制,而无论权力关系怎样重塑社会的肌底和纹理,致使生命个体陷入灵与肉的双重困境,生命的能动和反叛力量也不可小觑。一方面经由个人书写和想象的置换重塑个人经验,另一方面回溯记忆的缝隙和空白寻求个体的身份认同,是麦家对人摆脱权力困顿问题的两种思考路径,实现了普遍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的自我解救。他对现实的回应真挚而诚恳,正如腰封所示:我想写的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从朴质的话语中道出生命的真谛,人生海海,这句闽南方言浸润着麦家对于生命的关怀和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