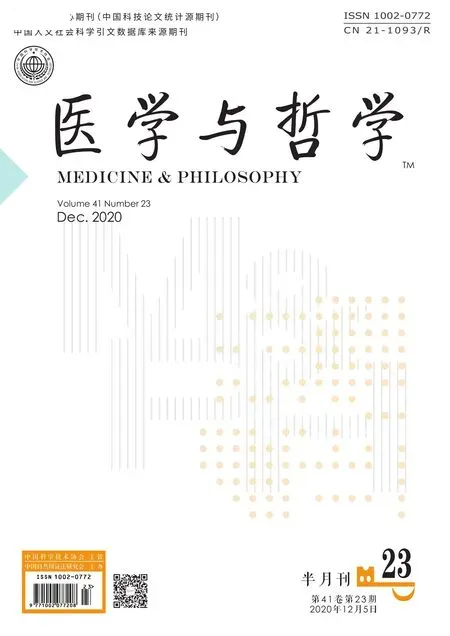产科医护人员在围产期死亡事件中不良体验的应对进展*
2020-02-16宋莉娟胡捷波袁长蓉
宋莉娟 胡捷波 袁长蓉
围产期死亡(perinatal death)是指在孕28周之后或出生不足1个月发生的死亡,是突然的、无法预期的、无法解释的死亡[1]。围产期死亡包括流产、死胎以及新生儿死亡,被认为是最痛的死亡,对一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种“毁灭性事件”,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2]。近年来全球围产期死亡事件的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但其对家庭的影响却很深远[3];且随着全球出生率的下降,每个家庭新生儿出生数量也在下降,每一次围产期死亡事件的发生都对家庭影响巨大;然而,围产期死亡不仅对患儿家庭造成影响,也给产科医护人员带来很多不良体验[1]。
围产期死亡相关研究起源于西方国家,主要关注患儿家庭在围产期死亡事件中的不良经历、需求以及心理精神方面的影响,以帮助支持患儿父母满足需求,顺利度过悲伤期和丧亲期,而忽视了围产期死亡照护对产科医护人员造成的不良体验[4]。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保护母婴围产期安全,消除歧视和虐待,自此,关于围产期死亡的家庭支持和产科医护人员支持性研究逐渐得到关注[5]。国外相关研究较多,我国对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探索期。本文就国外产科医护人员应对围产期死亡事件的不良体验与需求进行总结,以期为我国该领域研究提供借鉴。
1 产科医护人员在围产期死亡照护体验的影响因素
产科被认为是一个偶然或不经常发生死亡的科室,因此,从事产科工作的助产士、医生、护士往往成为“丧亲护理、临终护理”研究忽略的群体[6]。然而正因为围产期死亡发生的突然性和偶然性,从事产科的医护人员面对的压力和挑战也更大,死亡带来的悲伤也更严重和复杂[7]。而影响其体验和感受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因素和文化背景因素。
1.1 个人相关因素
临床工作经验、工作职位、年龄、沟通技巧、专业知识、培训经历、他人的支持,以及个人或职业中曾经历死亡的情况等都是影响产科医护人员应对围产期死亡事件的个人因素[8]。文献显示,应对死亡经验缺乏、医护人员的年龄与分级相对低、缺乏丧亲护理的知识与培训经历、缺乏同事和单位支持、个体信心不足等都是导致负向情绪或严重不良体验的主要因素[9-10]。Bandura自我效能理论提出个体执行任务的经历会增强个体执行任务的自信心[11]。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临床经验丰富、职位高、之前有死亡经历的医护人员在应对围产期死亡事件时的体验或感受会相对好一些。有些有经验的护士会主动将自我与围产期死亡家庭隔离,保持情绪的独立,以避免悲伤情绪的影响,做到自我保护,反而一些年轻的工作人员相对经验较少,经历死亡时间机会较少,自信心不足,因此,负性情绪和体验会更多[12]。
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发生:一些经验越丰富的医护人员在面对围产期死亡事件时,内疚感越强烈,也可能出现一段时间的情绪崩溃,安宁疗护专科护士也有类似问题。而一些高年资医生的内疚感可能源于他们对先进医疗技术的期望和既往经验,因此,会对自己产生内疚和不足的感觉[13-15]。由此可见,影响产科医护人员不良体验的自我效能因素是综合的,而非单方面的。
1.2 文化背景因素
文化对悲伤的表达和态度具有重要影响,文化背景是影响人们对死亡认知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围产期死亡[8]。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是一个禁忌话题,是一个家庭的私密事件;甚至有观点认为围产期死亡是因为母亲未能尽到照护胎儿或孩子的责任,从而受到谴责,因此,医护人员更加无法公开表达他们关于胎儿死亡的感受或态度[16];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日本,医护人员无法表达自己对围产期死亡事件的真实情绪,却必须为丧亲父母的悲伤情绪作出正确合理的回应[17];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医护人员则可以更自由地表达个体情绪、沟通交流,积极发现悲伤的原因,并为丧亲家庭提供适宜的照护措施[11,14]。这与东西方文化背景差异有关。
文化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Leininger[18]在跨文化理论中指出:一个人的经历和随之而来的行为受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影响;应重视不同文化背景对医护人员经历和需求的影响,围产期死亡照护的产科医护人员也不例外。文献显示,影响产科医护人员对围产期丧亲护理积极态度的因素包括所在地区的医院政策制度、医护人员的宗教信仰、接受丧亲护理培训等[16]。Chan等[19]对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济南的医护人员关于围产期丧亲护理态度的调查研究显示,我国济南市护士对丧亲护理的态度最积极正向,其次是新加坡,最后是我国香港地区;分析这三地的文化背景、医院政策、医护人员的宗教信仰、接受的丧亲护理培训等均不同。地域文化也是文化因素之一。
2 产科医护人员在围产期死亡事件中的不良体验
产科医护人员在为围产期死亡家庭提供支持性护理服务过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事件,往往也给自身带来很多不良体验,甚至造成深远影响。文献显示,产科医护人员中,35%的护士报告具有一定的工作压力,33%的助产士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经历,甚至近乎崩溃;75%的医生在照护围产期死亡家庭时有情绪创伤的体验,甚至10%的医生曾考虑放弃从事产科工作[20-22]。这些不良体验也给医护人员造成较大的身心压力,有医生认为死胎带来的创伤低于新生儿死亡的创伤,然而当照护围产期死亡的父母时,很多医生和助产士仍会发生头痛、疲乏、易怒、丧失感以及全身慢性疲劳症等身体不适现象[14];严重者甚至希望轮岗轮班、希望得到休息,甚至希望离开产科工作;更有些人几年之后仍清楚记得那些发生围产期死亡的父母,仍会分享这种经历[20]。这些不良体验严重危害了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也影响了其对职业的积极性和职业态度。若不及时疏导缓解,可能造成更多更严重的后果。
死胎被医护人员认为是最难处理的事件,每个人面对死胎的反应各不相同,提供的照护服务也就不同,且围产期死亡照护被认为是医疗-法律的双重责任,这也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心理负担[23]。Ben-Ezra等[24]对产科护士和助产士的调查显示,围产期死亡暴露的医护人员心理症状发生率明显高于非暴露的医护人员。每个人悲伤的感受不同,应对机制不同,产生的症状也不同。
面对或经历围产期死亡事件,产科医护人员往往会有未做好准备应对、内疚、自责、抑郁,无法面对内心的矛盾和冲突等心理和情绪反应[10,25];Ellis等[22]的研究显示,医护人员对围产期死亡事件的情绪控制、知识和系统化照护服务提供时有困难;很多医护人员往往集中于“任务”本身,将自我与家属“隔离”,以逃避自身压力;也有医护人员有失落感和不知所措、害怕与无助感。Fenwick等[26]研究发现,关于围产期死亡照护服务要求,助产士最满意的是与丧亲家庭保持联系、反映他们的个体化需求并为其提供支持性照护,最不满意的则是被要求为围产期死亡家庭提供丧亲照护,并与丧亲的母亲保持开放的、持续的沟通,这一定程度也反映助产士本身的无助和无力感。更严重者,经历围产期死亡事件后,很多护士呈现高水平的心理症状,如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近乎崩溃,甚至一直难以忘记等;极少数人员希望尽快离开工作岗位[24,27]。这些不良反应不仅严重影响产科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其工作积极性、工作质量以及职业稳定性。
反之,有极少数医护人员在面对围产期死亡照护时会出现积极正向的情绪反应和有意义的体验。他们感受自己能为围产期死亡家庭提供最大的支持和帮助时,会很有成就感[6]。他们感觉自己与患儿家庭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保持自己的积极正向情绪,他们会采取一些方法让患儿家庭专注于未来,以“合理化”自己的想法,让自我舒适,甚至有一定的成就感[22];然而这种“合理化”并不一定会得到患儿家庭认可,有父母认为医护人员忽视了孩子的“存在”和“价值”,未能理解他们的悲伤情绪;因此,医护人员应在帮助丧亲父母保留孩子“存在”记忆的基础上,尽可能帮助父母将注意力集中在未来,这是一种因医患角色不同产生供需矛盾的体现,也成为绝大部分医护人员难以达到的“正性情绪体验”。
3 产科医护人员应对围产期死亡事件的措施
3.1 教育培训
专业的培训和教育课程对提高产科医护人员围产期死亡事件应对能力非常重要,也是医护人员需求较高的应对措施之一。长远来看,医学院校应在护理、助产和临床专业课程设置中增加关于围产期死亡和丧亲护理的课程[13-17,19,22,25-26];在医学生临床实践之前开展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提高学生对围产期死亡事件的认知,树立正确的职业态度,掌握与围产期死亡家庭的沟通技巧,减轻焦虑恐惧情绪,增强自信心,做到前馈控制。短期而言,为缓解临床医护人员的工作困境、提高应对能力,通过开展关于死亡与悲伤主题的继续教育项目,提供必要的知识支持是快速而有效的教育措施,如丧亲教育项目、以丧亲护理为主题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总结分享会等[28-29]。
关于培训课程内容的需求包括围产期的丧亲护理、围产期的丧亲沟通交流技巧、文化照护、自我保护性分享、经验交流与学习等[13-17]。对培训课程形式的需求主要是经验分享法[19-22,25-26],如在培训课程中邀请曾经历丧亲的家庭现场分享需求和体验;或采用多媒体技术邀请丧亲家长和有经验的医护人员以录音、录像的方式分享经验;通过分享发现他们未被满足的需求,有助于解决照护者和被照护者之间的供需矛盾,从而帮助医护人员有针对性地从“患者”立场出发提供帮助和支持,对医患双方都是一种正向改善。另外,也可采用标准化病人情景模拟的教学方法,让学员在课堂中模拟实践,既解决了床边教学带来的伦理困扰,又能让学员在仿真情境中获取学习经验,从而减轻临床直面围产期死亡事件时的紧张焦虑情绪[1]。
3.2 制度保障
通过设立专门的支持性组织或机构,制定相关的政策制度提供支持。文献显示,不同的围产期实践经历对助产士有不同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或体制缺乏,这是增加产科医护人员心灵创伤和人员流失率的主要因素[2,9,23,26,30]。例如,产科医护人员有参与相关专科的课程教育或培训的需求,但可能会因为工作时间、政策制度等问题导致无法保障,从而给其带来很多不良体验,进而影响人员稳定性。另外,制定相关政策制度应充分考虑个人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允许产科工作人员有一定程度、合理化的脆弱情绪,在照顾丧亲家庭时可适当采用轮岗轮班制度,为产科医护人员提供疏解悲伤情绪的时间和空间。或者一些医疗机构在岗位安排中可考虑弹性工作制度,为一些受情绪影响较大的产科医护人员提供换岗机会,也可适当安排经验丰富的产科医护人员承担围产期丧亲照护工作,对照护和被照护双方都有帮助,有助于促进产科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2,9,23]。
3.3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对提高产科医护人员应对围产期死亡事件的能力亦很重要,可以来自多个方面:高年资、经验丰富的人员带教指导低年资人员、与同事分享工作经验、多学科团队合作,以及来自家庭和朋友的支持等都属于社会支持范围[9-10,12,17,26-27];另外,与丧亲事件家长进行非正式的沟通交流,确认需求和服务,从家长的体验和经历中获取工作经验等也是对医护人员的一种社会支持[2,14]。
3.4 其他
临床工作中,护士和助产士陪伴照护围产期丧亲家庭的时间相对医生较多,需要更多关注和支持,但医生也有相似经历和需求,同样需要支持和帮助[14,22]。除教育培训、政策制度保障、社会支持之外,个体应对不同的心理和身体症状,也会采取适合自己的个性化应对方式,如与同事朋友交流、运动、祈祷、旅行、专注于某项照护任务(如为宝宝洗澡、穿衣)等[22];陪伴、倾听、洗礼、提供纪念品、参加葬礼等也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方式;有护士和助产士认为参加宝宝的葬礼是一种经历、一个事件的结束,对自身情绪缓解很有意义[11]。而祈祷、与同事交流是西方国家医护人员应用较多的方法,祈祷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应对技巧之一[8];亚洲护士,尤其是日本,更希望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个体选择的应对方式因人而异、因文化背景而不同[27,30]。
4 结语
围产期死亡事件虽然发生率不高,但对患儿家庭和产科医护人员都造成了身心不良体验,甚至更深远的影响。应对围产期死亡事件,必须引起社会和医疗机构的重视,采取全方位措施满足产科医护人员的需求,提高其应对能力。个体选择不同应对方式与以问题为中心的外部应对思路和以情绪为中心的内部应对思路有关;而要真正提高内外应对能力,改善不良体验,必须将文化因素与教育项目相结合,充分考虑围产期死亡事件的家长和医护人员双方的需求[19],最终解决供需双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