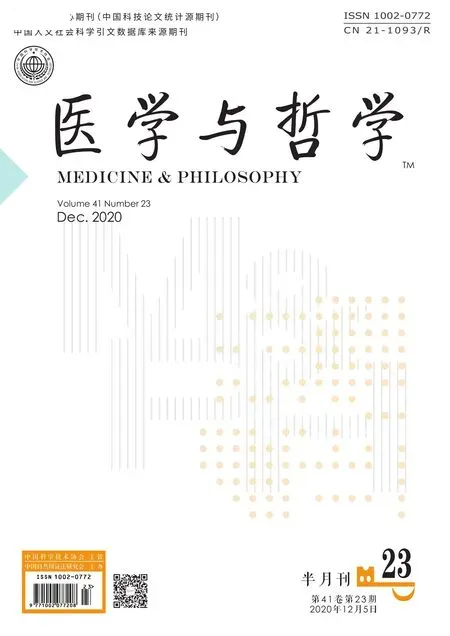感知/亲历医疗暴力医生的内向和外向反应*
——基于浙江调研数据的分析
2020-12-21王淑红孙泽生
王淑红 孙泽生
我国的医疗暴力发生率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1],新近发生的严重伤医案例也表明医疗暴力尚未得到有效遏制[2]。因我国尚未建立全国性的强制性医疗暴力事件报告系统,因此以已有文献或依赖于媒体/法院披露的致医生伤亡案例、判例数据来估计医疗暴力频度和特征[3-4],或借助调查数据分析医疗暴力发生规律[5-6]。在反医疗暴力法律环境和医疗卫生政策情境下,探讨感知/亲历医疗暴力的医生如何做出自身的内在反应并对职业关联的法律环境和政策做出外向反应,是治理医疗暴力的重要实证依据。本文将医疗暴力具体区分为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并借助自行设计问卷来探讨感知和亲历暴力的医生的内向和外向反应特征,以增加学界对医疗暴力影响的理解。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定义的医疗暴力既包括文献强调的以推搡、殴打导致身体伤害为指征的身体暴力行为[3-4],也包括以威胁/辱骂为衡量的语言暴力。因医生的人力资本特定性和职业锁定[7],本文定义的内向反应主要涉及医生自身及其家庭的行为反应,其外向反应则是对诸如政府、立法、执法和医院对医生安全的保护力度以及卫生政策效果等的评价。按照浙江省卫生资源下沉改革中三级医院向二级医院下沉的制度设计,本研究将二级和一级医院归类为基层医院,以与三级医院相对应。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在2018年6月~2019年3月,由经培训的工作人员向杭州、嘉兴、湖州、宁波、丽水和衢州等地共36家医院的医生发放调研问卷。所有医生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最终获得72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671份,有效率为93.19%。利用SPSS 23.0软件和信度检验发现Cronbach's α系数为0.818,表明问卷及调研数据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
1.2 调查方法
1.2.1 问卷设计
基于5点积分法自行设计问卷。问题项包括:(1)医疗暴力,包括感知所在医院暴力频度以及医生亲身经历的暴力频度问题项,“从未”“很少”“偶尔”“经常”“频繁”感知暴力者分别赋分1分~5分;是否亲历医疗暴力的赋值方法为:报告“从未”经历医疗暴力受访者赋值为0分,其余为1分。(2)暴力防控,包括医生对防控流程的认知和所获得的反医疗暴力培训。二者虽有关联,但前者强调医院层面,后者强调医生个体层面且不仅限于医院提供的培训。对前者,“使用过”“培训过”赋1分,“听说过”“不清楚”“不存在”则赋0分;对后者,曾在“学校”“医院”获得培训赋1分,否则为0分。(3)法律环境评价,分别纳入政府、立法、执法和所在医院4个层面对医生保护力度的评价。其中,政府保护用以评估公权力对医生安全的总体保护,立法和执法则分别评估成文法和司法机构对医生的保护力度。赋1分~5分分别对应评价“很低”“较低”“尚可”“较高”和“很高”。(4)卫生政策评价,结合调研地浙江正在实施的分级诊疗和卫生资源下沉改革,考虑与医生工作相关且医生均有所了解的7个方面医疗卫生政策[8]: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政策、职称评审、医学生基层工作激励、定向生、考核评价以及下沉津补贴政策,赋分标准与法律环境问题项相同。(5)医生内向反应,包括工作积极性、高风险患者识别意愿以及对子女学医支持度。其中,工作积极性赋1分~5分表示“无影响”“较小”“中等”“较大”“很大”;1分~5分分别对应患者识别意愿“很低”“较低”“尚可”“较高”和“很高”;对子女学医支持度赋1分~5分分别对应“上升”“不变”“略有下降”“明显下降”和“大幅下降”。
1.2.2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3.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方差分析方法比较不同组别医生间的医疗暴力认知和反应差异。差异显著性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受访者基本信息
三级医院和基层医院医生所占比重分别为71.39%和28.61%。31岁~40岁年龄段占比43.52%,41岁~50岁和30岁及以下占比分别为29.51%和22.65%。本科学历医生占61.25%,硕士学历医生占24.89%。中级职称者占34.43%,副高和正高职称比例分别为26.23%和9.69%。3年~5年工龄医生占比最高(41.58%),随后是新入职2年以内医生(21.61%)以及工龄6年~10年医生(20.86%)。
2.2 不同等级医院医生的认知和反应
区分医生对所就职医院医疗暴力的“感知”和“亲历”,可发现感知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频度均值介于2(“很少”)和3(“偶尔”)发生之间[(2.61±0.81)和(2.93±0.91)]。其中,回答所就职医院身体和语言暴力“从未”发生的比重分别为8.49%和4.92%,回答“偶尔”“经常”“频繁”的比重合计为59.32%和69.45%。受访医生亲历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的比重分别为45.74%和39.04%,但回答身体暴力“经常”“频繁”发生的受访医生比重达到27.75%。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级医院医生认知的身体和语言暴力发生频度之均值[(2.78±0.75)和(3.12±0.86)]均大于基层医院[(2.19±0.80)和(2.46±0.84)],且这一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级医院医生子女学医支持度(2.78±1.05)和工作积极性(3.07±1.01)均低于基层医院[(2.88±0.87)和(4.43±1.06)],但高风险患者识别意愿(2.84±1.06)却高于基层医院医生(4.43±1.06),以上结果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亲历/非亲历医疗暴力的医生认知和反应
亲历身体或语言暴力医生认知的所在医院医疗暴力频度之均值高于未亲历暴力所认知的医疗暴力频度,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亲历身体暴力和亲历语言暴力两个变量间显示有统计学意义的同向变动关系,即亲历语言暴力的医生所亲历的身体暴力频度(2.15±0.90)高于未亲历语言暴力医生(1.14±0.43),同样,亲历身体暴力医生所亲历的语言暴力频度(2.69±0.82)亦高于未亲历者(1.56±0.75)。见表1。
亲历医疗暴力的影响还反映在医生的外向反应和内向反应上。首先,亲历语言暴力医生对政府、立法、执法和医院保护4个指标的评分均值都低于未亲历语言暴力医生,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相对照,亲历身体暴力医生对除立法保护之外的3个法律环境变量的评分显著低于未亲历者。其次,亲历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医生对卫生政策的评价都要较未亲历者负面(P<0.05)。最后,对医生内向反应,亲历语言暴力或者身体暴力者均具有显著较低的子女学医支持度和工作积极性,但高风险患者识别意愿却显著较低。
2.4 医院暴力防控的组间比较结果
由调研结果可知,对医院暴力防控流程“使用过”“培训过”的医生占比为53.20%(357/671);分别有0.3%(2/671)和48.29%(324/671)的受访医生报告其在医学教育和所在医院获得反医疗暴力知识和技能。无论医生认知医院暴力防控流程和接受反暴力培训与否,其医疗暴力频度认知都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但认知流程和接受培训者对法律环境和卫生政策评分的均值都较高(P<0.05)。在医生的内向反应中,认知医院暴力防控流程和接受反暴力培训医生的高风险患者识别意愿显著较高,但其子女学医支持度和工作积极性均值也较高(P<0.05)。见表2。

表1 亲历和非亲历医疗暴力医生认知及反应的比较

表2 医院防控认知和反暴力培训对医生内外向反应的影响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三级医院医生亲历身体/语言暴力的比重显著高于基层医院医生。先前的聚焦于三级(甲等)医院医生的文献报道了60%左右的医疗暴力发生率[5-6],比本研究的所有医院暴力发生率高;研究中基层医院医疗暴力发生率低于三级医院的结论与文献报道医疗暴力主要发生在三级医院结果一致[9]。除亲历之外,医生群体还基于自身可得信息评估所就职医院的医疗暴力状况。方差分析发现,三级医院医生感知的医疗暴力发生率与基层医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因三级医院有更高的诊疗能力但却面临与基层医院相似的医疗服务价格管制,导致患者倾向于优先选择三级医院,使三级医院拥堵程度更高、诊疗等待时间更长,患者就诊体验弱于基层医院,发生医疗暴力的概率亦高于基层医院。基于媒体报道和法院判例的统计数据支持这一结论[3-4]。
与以上医疗暴力发生率情境相对应,三级医院医生的内向反应特征是更低的工作积极性和子女学医支持度,以及更强的高风险患者识别意愿。其解释在于,从医所面临的要素特定性和职业锁定使医生的内向反应空间较窄。首先,为降低医疗暴力风险,需在接诊时通过“小心诊疗”“多做检查”和“劝说转院”等识别和应对高风险患者,由此降低了医疗服务可及性、增加了医疗成本[7]。其次,因医疗暴力带来的从医效用下降,内向反应还延伸至医生的家庭成员,使其对子女学医支持度明显降低,以实现跨代的职业再选择,与已有调查结论相符[10-11]。相比较而言,医生外向反应被证明在不同等级医院医生间少有显著差异,仅在医疗服务价格和(差异化)医保政策上,基层医院医生评分较高,与这两项政策偏向基层医院有关。
基于是否亲历暴力进行分组发现,亲历暴力医生所感知的就职医院暴力发生率显著高于未亲历暴力医生的认知。医学文献所称的应激反应刻画了亲历医疗暴力后对暴力的过度敏感和信息放大特性[12],以此加总至群体行为后,亲历暴力医生也放大了所感知的医疗暴力发生率,其与无亲历暴力医生的差异在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情境下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方差分析还表明,在内向反应上,亲历暴力医生具有更低的工作积极性和子女学医支持度,这与前面的讨论相似;但有所区别的是,亲历医疗暴力医生有更低的高风险患者识别意愿,且对身体/语言暴力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其解释是,已发生的暴力反而降低了医生面临的不确定性并消极作用于其对患者的选择行为,但这是以降低工作积极性为代价得到的结果。在外向反应上,亲历语言暴力医生对包括政府、立法部门、执法部门和医院在内的反医疗暴力法律环境均给予了显著更低的评分;亲历身体暴力医生除在立法保护上与未亲历者无差异外,对其余3个方面法律环境之评分也显著较低。这表明,已有之遭际说明了法律环境在保护其安全方面的不足,未亲历者则并不知悉这一点。同时,亲历医疗暴力者在几乎所有医疗卫生改革政策上均给予了有统计学意义的较低评分,说明他们同样因其遭际而负向评价改革和相关政策。
按照《劳动法》,作为雇主的医院有法定义务保护作为雇员的医生的安全。其主要举措包括医院暴力防控及对医生的反医疗暴力培训。本文发现,获得反暴力培训并知悉医院暴力防控流程的医生均对反医疗暴力法律环境和卫生政策有更高的评价。因此,医院方的暴力防控流程构建、落实及对医生的信息传递,以及医院组织的反医疗暴力培训具有重要作用。其效果延伸到医生内向反应的两个方面:首先,它提高了医生的工作积极性和子女学医支持度,接受反医疗暴力教育、了解医院防控流程医生的这两项反应均值显著高于未了解防控流程和未受培训医生的均值。其次,接受反医疗暴力教育、了解医院防控流程医生的高风险患者识别意愿虽较高,但它是以工作积极性改善和反医疗暴力技能的提升为支撑,有利于其将风险进行再配置,起到帕累托改善的效果。不过,问卷调研也说明,尚有46.80%的医生报告医院暴力防控流程“不存在”“不了解”或者仅“听说过”,有51.71%的医生反映其未在医院接受过反医疗暴力培训,加之99.70%的受访医生未从入职前的医学高等教育中获得此类知识/技能,均使得医生对反医疗暴力法律环境的评分下降。
需说明的是,医生职业承担保护公共安全的职责但却高度暴露于风险中,承受极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但却面临要素锁定,导致医疗暴力会产生远较普通工作场所暴力更高的社会成本[9,13]。已有医疗暴力案例表明[14],于社会而言医疗暴力会导致严重的医疗人力资本损失,于受害医生而言则带给他们职业锁定但又发展受限的心理创伤。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创伤和负面影响还会传递给医生群体,产生更大的社会成本。要治理医疗暴力,作为雇主的医院方的作用可能只是边际意义上的、有限的,更根本的举措既依赖于医疗资源的平衡配置和患者在不同等级医院间的理性就医选择,以大幅降低医疗市场尤其是高等级医院的拥堵、改善就诊体验、降低暴力发生率[15],也在于考虑医疗暴力之高社会成本后实现优化的刑罚设计和更强的执法力度,使得处于高风险暴露中的医生群体能匹配于更强有力的法律保护[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