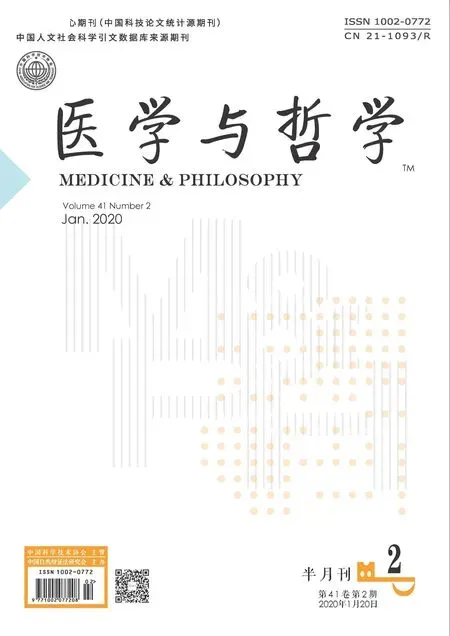欧美生命伦理委员会的机构建设与咨询服务*
2020-02-16张肖阳
张肖阳 肖 巍
在当今国际世界,生命伦理学已从20世纪60年代问世的新学科发展成一种国际性的“社会运动”,成为学术界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领域。在欧美社会,生命伦理学不仅作为学科蓬勃发展,而且在生命伦理委员会机制建设和社会咨询服务等实践方面也取得许多成果,这些成果以体制和文化背景为保障有力地推动了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发展和临床应用。本文将从机构建设、咨询服务和哲学思维嵌入三个方面探讨欧美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建设的经验,以期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学科发展及生命伦理委员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1 机构建设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出台了《建设生命伦理委员会指南》,把各种类型的与医学、生物学和健康保健相关的伦理委员会统称为“生命伦理委员会”,较为恰当地包括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实践。这一文献首先强调各国建设“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随着生命和健康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物技术的不断创新,个人和社会都愈发地难以作出与生命相关的道德抉择,必须以正规的组织形式来解决与日常健康及政策相关的伦理问题。“生命伦理委员会是一个有组织地、连续性地强调:(1)健康科学;(2)生命科学;(3)创新性健康政策的伦理维度的委员会。一个典型的生命伦理委员会应当由一定范围的专家组成,它通常是多学科性的,其成员以不同视角探讨解决生命伦理学问题和难题,尤其是道德困境的方案。而且,这些委员会的成员不仅要对伦理困境保持敏感,而且要及时把握更有效的应对这些困境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生命伦理委员会“强调的不仅是事实,也是深远的规范性问题,其决定不仅关乎与某一案例相关的利益纷争,也超出经验证据的事实层面,不仅要求回答‘我应当如何决定和行为’的问题,也要求回答‘我们应当如何决定和行为’的问题,这将把我们从作为哲学传统分支的伦理学引入到政治学,回答‘政府应当如何行为’的问题”[1]。
目前欧美各国的生命伦理学机构主要包括:(1)临床伦理委员会(Clinical Ethics Committees,CECs)。它的宗旨在于为本机构的健康保健实践提供伦理服务,为寻求咨询的个人(患者、家庭和在这一机构任职的健康保健人士)提供价值观方面的帮助。在欧美国家,这一委员会具有不同的名称,例如机构伦理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以及生命伦理委员会等。(2)医疗保健伦理委员会(Health Care Ethics Committees,HECs)。它的含义更为广泛,可以为特定健康保健制度中的所有机构提供伦理服务。与临床生命伦理委员会相同,其宗旨也在于为患者、家庭、代理人、健康保健人士,或者其他相关人员分析和解决价值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和冲突,为之提供咨询服务。(3)研究伦理委员会(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s,RECs)。(4)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IRBs)。与(1)、(2)不同,(3)、(4)的主要任务是对于所提出的关于临床药物或者治疗研究,研究机构所进行的包括人体受试者的研究等进行伦理审查。
美国生命伦理委员会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开始普遍使用肾脏透析机,但透析机资源远远不能满足肾脏衰竭患者的需求,所以医院便成立委员会配置透析机资源,例如1962年,西雅图建立了“透析委员会”(Dialysis-Committee)。然而,由于其成员多半是白人中产阶级男性,所作出的决定总是偏袒自身阶层,便引发全国性的强烈抗议。1973年,政府开始为使用透析机付费,这些透析委员会便终止了功能。然而,这一事件却引发了公众关注“医院伦理委员会”问题。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便举行了首个强调临床实践技术发展复杂性的伦理学论坛(Ethics Forums),70年代又建立“流产委员会”(Abortion Committee),8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受理的几宗案件导致“健康保健伦理委员会”的建立。有统计数据表明,1981年,美国大约有1%的医院成立了医院伦理委员会。1983年,美国“总统委员会关于医学、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研究报告”(President’s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Ethical Problems in Medicine and Biomedical and Behavioural Research)对于“医疗保健伦理委员会”的职能作出政治陈述。此后“医疗保健伦理委员会”和“临床伦理委员会”在美国各个医院得到迅速发展。1984年,“美国医院联合会”(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也强调在机构层面探讨生命医学伦理问题的意义。1998年,“美国生命伦理和人文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Bioethics and Humanities,ASBH)成立[2]。
相比之下,生命伦理委员会在欧洲社会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而且在不同国家发展过程和模式各不相同。有的国家采取行政命令方式促进“医疗伦理委员会”建设,例如2000年挪威议会便要求所有医院都应当成立HECs,并要求在5年后基本达成这一目标。根据德国卫生机构2006年的估算,在德国每2 000家医院里,只有200家成立了“医疗保健伦理委员会”。在欧洲其他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也陆续得以建立,例如意大利帕多瓦大学专门成立了“儿科伦理委员会”等[3]。1997年4月4日,“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在西班牙的奥维耶多市缔结了《人权与生物医学公约》,这成为欧洲国家在生物医学发展中所奉行的尊重人权原则的纲领性文献。尽管这一公约分别对临床医学和研究伦理学实践作出详细规定,但却未提出建立“生命伦理委员会”的要求。
在欧美生命伦理委员会机构建设过程中,也不断地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引发许多学者思考这一机构的能力和限度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例如美国道德神学家理查德·A.麦考密克(Richard A.McCormick)等[4]的“伦理委员会:承诺还是危险?”,R.韦尔(Robert Weir)[5]的“儿科伦理委员会:伦理咨询者还是法律的看门狗?”,J. 弗利特伍德(Janet Fleetwood)等[6]的 “给出答案还是提出问题:机构伦理委员会有争议的角色”,D.卡拉汉(Daniel Callahan)[7]的“伦理委员会及社会问题:潜能和陷阱”,D.布莱克(David Blake)[8]的“医院伦理委员会:医疗保健机构的良心还是白象?”。这些争论主要缘于第一代医院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局限性,它们最初仅是一个维护个体患者权利和解决棘手案例的咨询机构。然而,如今这种模式已不足以满足欧美国家在医疗保健方面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要求。这些争论也导致一些学者对生命伦理委员会存在的意义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在官僚机构盛行的背景下,生命伦理委员会似乎成为一种管理机构,而且在医学决定过程中,这种机构可能使问题更为复杂。如果把问题都公开出来,专家意见可能不再起作用,同时它的伦理规范也只是偶尔地产生作用[9]。甚至一些美国医生开始抵制生命伦理委员会,认为这种机构干预了医患关系,不仅没有存在的意义,反而具有破坏性和煽动性。尽管如此,美国社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推动下,生命伦理委员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因为这场运动不仅对政府机构、同时也对社会机构(如医院和学校),以及人际关系(如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和医患关系)提出挑战。美国黑人、妇女、同性恋者、囚犯、学生和消费者、病人都参加进来,目的在于追求个体自主性以及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生命、自由和幸福权”,例如住房、受教育和工作权,以及掌握自己健康与生命信息的权利和决定权。一些患者和家庭也开始要求拒绝使用维持生命系统的“死亡权利”[10]93-94,在这种背景下,生命伦理委员会便更多地承担起协调医患冲突,规范医生行为和减少法律诉讼的任务。
21世纪以来,欧美学者也在不断探索生命伦理委员会的新模式,例如N.温格(N.Wenger) 认为这种新模式必须具备四个特点:(1)它应当是前瞻性的,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医院把各种困境呈现出来;(2)它在组织上是紧密结合的;(3)需要通过结果,而非良好动机来衡量其功能;(4)它应当受机构价值观的支配,而不仅仅由患者的合法权利来引导[9]。目前欧美各国生命伦理委员会也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功能和手段,以期适应生命伦理学本身发展和实践产生的新要求。
2 咨询服务
临床伦理咨询是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一种重要服务方式。在“美国生命伦理和人文学会”的一份报告中,临床伦理咨询被定义为“一种由个人或群体提供的服务,帮助患者、家庭、代理人、医疗保健提供者,或其他相关方分析在医疗保健中出现的与价值相关的不确定性或冲突。”这主要集中在两个伦理领域:(1)针对特有患者案例的临床伦理学;(2)针对健康保健组织与企业实践的组织伦理学[10] 91。在一些欧美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都具有这一临床伦理咨询功能。然而,学术界对这一功能也有不同的看法。赞成者认为,临床伦理咨询是一种轻便灵活的结构,能够随时启动,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其功能直接与医疗决定相关,这就要求对咨询员进行伦理学等学科的培训。反对者则认为,如果鼓励医生成为伦理咨询专家,他们便可能不再培养自身的伦理意识,不必自己作出伦理选择,这势必导致医生行为和医疗实践与伦理的分离,同时也会削弱医生作出医疗决定的权力。还有人认为,伦理选择关乎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和期望,它应当属于私人性的,不需要伦理专家来指导[3]。
尽管存在上述争论,但欧美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所做的临床伦理咨询工作仍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其一,在解决每一种冲突时,咨询人员要基于一种道德判断来确定自身的角色,并在咨询过程中向各方呈现这种角色。咨询伦理要求解释案例,与相关者进行交流,预测解决这一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质影响。然而咨询者并不是道德真理或者法律的化身,也不需要扮演哲学家和牧师的角色,而只是一个伦理促进者和服务者。他们首先应当明确在道德上可/不可接受的行为界限,负责提醒和帮助人们意识到这些界限。还应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使之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而且,他们不能仅仅是患者权利的代言人,把临床生命伦理委员会变成患者的维权机构,而是需要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权利语言方面的冲突,及时向各方呈现这些冲突,并提出解决冲突的建议,而非代表某一方争取权利。其二,案例研究是临床伦理咨询的基本方法。针对具体情境,临床伦理咨询者应当意识到自己是案例的作者、行为者和评论者,应当从不同案例中总结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意识到有时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要胜于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采用案例方法需要完成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把现成的案例应用于具体的道德困境,解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二是根据临床实践自己编辑案例以备日后使用。其三,目前欧美国家的临床伦理咨询主要采取三种模式:伦理委员会咨询、个体咨询和小组咨询。这三种模式各有利弊:(1)伦理委员会咨询模式。伦理委员会传统上包括在医疗保健部门工作的各种职业代表,如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医院的律师、牧师,通常还有一名至两名行业外的公众代表。它的功能类似于一个管理机构,仅仅通过一次例会,听取临床主治医生说明情况和数据,经过讨论,给出建议。尽管这种形式会让患者本人或者家属参与意见,但却无法让他们充分表达看法。此外,它的决定大都根据二手或三手资料,其成员也有一种从众心理,以便形成大家共同承担责任的局面。(2)个体咨询模式。这一模式让咨询者感觉到友好氛围,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马上与相关患者和家属直接对话。在美国的一些医院里,个体咨询要求成倍地增长。然而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咨询专家很容易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并有可能造成一种幻觉,即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机构能够既有知识,又负责任地作出最佳的伦理决定。(3)小组咨询模式。这种模式能迅速作出反应,收集数据,并能清楚地作出决定,因而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或许是临床生命伦理委员会的最佳咨询模式[3]。
3 嵌入哲学思维模式
在欧美国家,生命伦理学家一直自觉地借鉴和应用当代哲学理论资源来建构生命伦理学理论,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也会对生命伦理学实践直接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后半叶以来,欧美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建设主要嵌入三种哲学思维模式——身体现象学模式、“对话伦理”模式和“问题”模式。
3.1 身体现象学模式
当代哲学现象学发展重塑了生命伦理学家的角色,例如美国学者德鲁·莱德(Drew Leder)试图通过现象学阐释人们对于健康与疾病的身体体验,以及医学干预对于人体的改变。他对基于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形成的现代医学科学主义提出批评,倡导一种整体主义理论。在《缺席的身体》一书中,莱德阐明了自己的“身体现象学”理论,认为西方文明一直贬低身体,使之总处于缺席和隐蔽状态之中,例如身体在表达某种功能时本身就是缺席的——在看的眼睛不会看到自己在看,睡眠状态中的身体也无法体验到自己在睡眠。这种身体存在样态和功能方式导致它本身的自我遮蔽,而人们却尚未意识到身体的这种缺席及其影响,反而由于这种忽视贬低身体的存在。莱德着重研究身体现象而不是关于它的理论,试图探讨身体的来源,以及身体如何成为人们自我意识的组成部分,它如何进行表达,以及人们如何通过身体体验到健康与疾病、痛苦与疼痛等等。可以说,以莱德等人为代表的“身体现象学”理论对于欧美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建设带来三点重要启示:其一,这一理论强调身体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一种自我表达和存在方式,以及一个人的身份。疾病不仅改变了人的躯体,也改变人的存在方式和身份。因此,人类社会一直以来围绕着健康与疾病以及身体所建构的哲学认识论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都应当重新审视身体的意义和价值。相应地,生命伦理委员会在提供临床咨询服务时必须意识到身体的整体性,重视患者的身体体验以及围绕身体、疾病和健康所建构的社会文化和体制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其二,这一理论看到传统生命伦理学教科书总是把生命伦理困境描述成“赞成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战争,而“身体现象学”则始于公开的对话,相信每个人在这一建设性对话过程中都能不断地超越、推翻或者修正自己的看法[11]。其三,这一理论呼唤一种“谦虚”(humility)美德。这一美德亦可被称为“叙事性谦虚”(narrative humility),它要求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专家和医生认真倾听患者的叙事,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打断患者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因为即便他们已经知道疾病故事的始末,也不可能把握这位患者完整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叙事性谦虚便涉及“如何对待我们不知道的他者之面容——我们无法知道这幅面容——但我们有责任作出反应。”这也需要医生具有一种想象力,进入到并非属于自身的痛苦中去想象患者的痛苦体验,并依据这种想象进行诊治,把握生命事件中尚未发现的意义[12]。
3.2 “对话伦理”模式
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理论也为欧美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建设引入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哈贝马斯认为,对话伦理的惟一途径就是在生活世界和公共生活中实现符合交往理性“话语意志”的平等与自由:不论话语活动参与者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如何,每一个人都应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不允许有任何来自权力和暴力的威胁。对话原则相信“每一准则的有效性都在于它是一个如果所有相关方参与到实践对话中来,都能够同意的准则。”[13]哈贝马斯的这种对话伦理也在倡导一种“审慎”(deliberation)美德,他借用当代政治哲学家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的观点阐释这种美德,强调它具有三个主要特点:它以争论形式出现,通过信息交流对所提出的方案进行批评审查;它是包容的和开放的,让受到这一决定影响的所有人都平等地参与进来;它是自由的,没有任何外在的强制力。参与者依据准则和交流实现自己的权利,它对于任何参与者来说都不具有使其偏离平等轨道的内在强制力。每一方都有权利平等地倾听、提出问题和作出贡献[14]。西班牙医学史教授、生命伦理学家迭戈·加西亚(Diego Gracia)也要求把这种“审慎”应用到生命伦理委员会的日常实践中,认为审慎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个过程,它要求完成下列步骤:(1)由决策人提供案例;(2)针对临床病例进行全方位讨论;(3)识别出伦理问题;(4)为患者选择出他/她所关心和希望分析的道德问题;(5)确定价值观上的冲突;(6)提供行为路线图;(7)分析最佳行为过程;(8)最终决策。“对话伦理”模式要求生命伦理委员会在决策时充分考虑各方观点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让所有参与案例讨论者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体验;各方要相互理解和尊重; 作为解释者,每一位参与讨论者都应当清楚他人对事物理解上的偏差,反思那些制约对话的历史、政治和形而上学结构。正如加西亚所言,每一个最终决策都要被置于三个范围内进行检验:置于法律范围内检验其是否合法?置于公众关注范围内检验“你是否准备为这一决策进行公开辩护?”置于时间范围内检验“如果再多给你一些时间,你是否还会作出相同的决策?”[15]
3.3 “问题”模式
“问题”一词来自希腊语problema,是从proballo演变而来,其含义是“向前抛”,意味着问题被摆在或抛到我们面前以求得到答案和解决。然而,“人类思维更倾向于‘非此即彼’的思考而不是同时处理两个或者更多选择的复杂思考,而且这通常是人们在无意中犯下的错误”。以往生命伦理委员会习惯于这种“非此即彼”思维模式,易于把问题推至极端,陷入一种道德困境,而没有意识到完全可以通过改变思维方式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方案。加西亚建议生命伦理委员会应当以“问题”模式来代替“困境”模式提供生命伦理决策和服务,因为问题本身是开放的,并不要求从两种或更多的可能性中作出选择,而是要求创造或者生产出正确答案,只有这种思维模式才符合伦理学的“本性”,这首先因为道德推理不应当依据“科学”方式来理解,即相信可以获得一种具有确定性的普遍知识,而应当以“观念”的方式来理解,即使观念本身是不确定的,但也不是非理性的。其次由于道德问题并不是数学演绎,而是与人们的观念相关,不同的人对于现实的感知不同,因而会产生不同意见。人们需要作出一个不确定的、但合乎情理的道德决定,这就是以“问题”思维作出道德决定的根据[10]225-226。
4 结语
建设“生命伦理委员会”是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及其实践的重要举措,它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可以减少和避免许多医患关系及临床医疗实践冲突,而且长远地看来,亦可以通过社会制度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医疗保健领域来促进社会的民主建设,体现出对人的生命权和自主权的尊重,达到医疗保健资源的公平配置,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的目标。欧美国家建设生命伦理委员会的经验和哲学理论思维方式可以为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从机构建设来说,尽管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启动“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建设过程,并于1988年成立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在90年代的综合医院等级评审工作中,卫生部和各省陆续颁布《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把医疗机构设立医学伦理委员会列为一个评审条件,并由此促进了全国三级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和发展。然而在实际作用中,各地各医院的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发展并不平衡,总体上尚处于摸索整合阶段,相关理论研究也较为薄弱。此外,尽管中国的生命伦理委员会在临床医疗实践中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功能较为集中在医学伦理和研究伦理审查方面,缺乏欧美国家的咨询服务,尤其是服务于个体患者的功能。而且,中国缺乏对于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作用、工作质量与效果的审查和监督机制,致使这些机构更多地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鉴于上述局面,中国生命伦理委员会在建设中应当关注四个重要问题:(1)基于文化基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委员会。生命伦理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体现出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委员会建设需要服务于“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找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模式和途径,例如在理论上需要汲取五千年优秀传统伦理文化,尤其是中医药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构建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因,基于这些文化基因培养民众的生命伦理意识,使其能够自觉参与生命伦理选择、决策与评价,共同建构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文化和有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委员会。(2)加强生命伦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生命伦理学也是一门理论学科,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建设、作用与完善仰仗于生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这里的学科体系主要指以知识结构和科学分工为基础的学科设置,专业划分和学术机构。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委员会建设要从根本上解决生命伦理学的学科体系设置问题,借以带动生命伦理委员会有分有合地协调统一发展。学术体系主要指学科内部分析研究问题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学术标准和评价体系。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与生命伦理委员会建设既需要借鉴欧美国家的相关理论并进行双向的文化汲取和改造,也需要发展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原则。话语体系主要指一个学科的标识性概念、新概念和表述方式,例如欧美生命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有自主性、权利、尊严、公正等,这些概念主要基于欧美国家的伦理价值观形成。相应地,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和生命伦理委员会建设需要打造出自己的标识性概念、新范畴和表述方式,即便使用与欧美国家相同的术语,也需要赋予它们不同的文化内涵,以便使生命伦理委员会能在中国文化中落地生根,临床生命伦理咨询话语更符合中国文化语境,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并能以这些自身特色走上国际交流舞台。(3)生命伦理委员有必要提供临床伦理咨询服务。培养临床伦理咨询人员的专业素质,以及建构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中国生命伦理委员会建设的必要环节。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作用是否能够发挥,以及是否能够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临床伦理咨询服务的水平,因而临床伦理咨询工作者十分有必要接受哲学和伦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培训。(4)生命伦理委员会专家要善于在生命伦理分析中培养和转变哲学思维模式,与时俱进跟踪和学习当代哲学和伦理学学科新发展。在这方面,欧美国家生命伦理学家善于把哲学新思维融入生命伦理学实践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对于身体、精神以及身心关系的现象学理解,对“叙事性谦虚”美德的强调,以及哲学思维方式从“非此即彼”到“创造性”生产答案的转变等都可以为中国的相关实践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