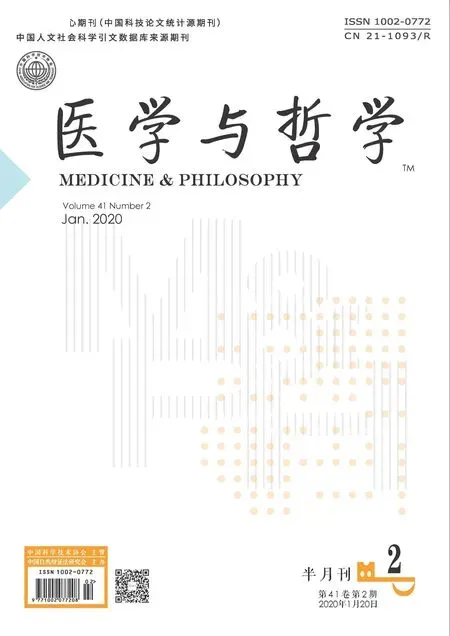基因组学研究免除具体知情同意的伦理挑战与审查实践*
2020-02-16周伟莉
康 辉 周伟莉 熊 茜 李 杏 万 仟 侯 勇
随着分析工具和方法的飞速进步,基因组测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急剧下降[1],基因组学研究与临床的结合愈加紧密,研究规模和范围也大大扩展。这些研究推动了精准医学时代医学的进步,在科研伦理审查中的分量日渐增加。
基因组学研究所需的组织、细胞等遗传材料采集方式一般较便捷,少量材料即可产生大量数据。常用研究材料和数据既可源于临床诊疗活动废弃的生物材料(血液、组织液、活检组织、手术切除组织),也可来自唾液(含口腔上皮脱落细胞)、毛囊细胞甚至粪便(含肠道上皮脱落细胞)等资源提供者易于自行留样的材料[2]。少数需特殊手段如切除手术、胚胎植入前筛查、羊水穿刺、肿瘤组织活检才能获得的,其采集一般与诊疗活动伴随进行,且无需显著多于诊疗所需。因此,资源提供者(受试者,含其监护人)留样的顺从性往往较高。但这种“顺从留样”实质未必等于“同意提供”。所获取的同意形式上常体现为“入院告知书”或“诊疗告知书”的概括性条款,如“我院可能会使用少许标本进行医学科学研究”或“我授权医师对手术切除的组织进行处置”。这种告知难以使资源提供者充分知情,也未明示其应享有的选择权和退出权。这样的“同意”是否能被视为合格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值得商榷。研究者使用这样采集留存的材料开展基因组学研究,需要伦理委员会逐项审慎考量,并共同承担保护资源提供者权益的责任。
研究者如果不是计划以具体知情同意(specific consent)方式收集和分析遗传材料,而是使用以广泛同意(broad consent)或一揽子同意(blanket consent)方式收集材料,伦理审查就涉及是否同意研究者免除再次知情同意的问题。
原国家卫计委2016年以第11号委主任令形式发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以下简称“11号令”)第三十八条规定,需要再次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情形包括:“(二)利用过去用于诊断、治疗的有身份标识的样本进行研究的;(三)生物样本数据库中有身份标识的人体生物学样本或者相关临床病史资料,再次使用进行研究的。”第三十九条规定伦理委员会可以免除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条件是:“(一)利用可识别身份信息的人体材料或者数据进行研究,已无法找到该受试者,且研究项目不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利益的;(二)生物样本捐献者已经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同意所捐献样本及相关信息可用于所有医学研究的。”[3]可见,11号令规定的适用“已无法找到受试者”,或仅免除资源提供者再次具体的知情同意。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CIOMS)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16年共同修订的《涉及人的健康相关研究国际伦理准则》第4版(以下简称“CIMOS 2016”)准则11对“研究者试图使用过去收集和储存的材料同时又没有获得捐赠者对数据未来研究的知情同意”提出免除知情同意的指导原则是:“(1)不免除知情同意,研究不可能或不可行;(2)研究具有重要社会价值;(3)研究对参与者或所在群体的风险不超过最小风险。”[4]与11号令的规定相比,CIOMS 2016免除知情同意的范围似乎更广。
审查实践中,11号令和CIOMS 2016相关准则的适用应结合研究的具体情境进行。
1 基因组学研究申请免除知情同意的典型案例
对于基因组学研究,CIOMS 2016规定的条件(1)“不免除知情同意,研究不可能或不可行”实质为寻回资源提供者并获取知情同意“不可能或不可行”,亦即11号令“无法找到该受试者”。如留存材料的身份标识不明,资源提供者自然难以通过常规途径寻回。如果身份标识明确,则有可能有以下情况。
1.1 研究材料或信息具有身份标识但知情同意范围未覆盖研究范围
案例1:某研究者欲以合作单位近年开展细胞保存服务时处理样品所产生的弃置血浆(约40ml/人·份)为基底液,与肿瘤细胞系批量混合后研发肿瘤DNA液体活检的标准品。然而细胞保存的知情同意书和服务协议,未考虑和提及医疗废弃物的研究用途。研究者希望变“废”为“宝”,申请免除知情同意匿名使用。伦理委员会认为细胞保存服务仍在有效期,要求研究者通过合作单位联系服务对象征集知情同意。首轮征询以电子邮件进行,回复率23%,已回复邮件中同意率达97%。研究者称服务对象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可充分理解科研活动,已回复的同意率极高,未回复的视作默认同意或已“无法找到”,申请推进科研活动。伦理委员会认为已回复人群的高同意率不代表未回复人群的意愿,77%的未回复率不能忽视,服务有效期内“无法找到受试者”不成立。后伦理委员会委托合作单位随机抽取部分对象电话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在完全了解研究内容后有相当比例明确表示不同意,之前不回复是对研究内容不了解或不愿被打扰。因此,伦理委员会的判断得以证实,未通过免除知情同意申请。
“无法找到受试者”具有一定表面性。研究者往往以获得的研究材料已编码化为由声称“无法联系”受试者。实际上,编码记录可以通过资源采集方回溯。伦理审查应深入剖析“无法联系”的真实原因。“无法找到”的标准应设定为该材料初始采集机构所保留的联系方式均告失效或研究时点明显超出资源提供者期望生存期。
1.2 研究材料或信息已具有广泛知情同意
包括CIOMS 2016在内的诸多指南和研究性文章认可,由于研究的确切内容往往未知,所以在样本采集时不可能获得具体的知情同意,采用广泛的知情同意“可以接受”[3,5]。使用这些样本应通过伦理审查机制对申请逐项把关,保护资源提供者。
案例2:2018年Cell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2011年~2014年间产生的141 431例基因组大数据,产生大量科学发现。在该研究设计和伦理审查阶段,伦理委员会检视到知情同意书模板已注明“我同意在去掉个人信息后,检测数据可供(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的)研究参考”,即具有广泛知情同意;由于NIPT数据测序深度(sequencing depth)平均不足0.1x(即个体基因组测序量不到全基因组的1/10),远小于常规意义的全基因组测序(个人基因组测序深度已普遍达到30x~100x),该项申请定位为群体分析,不对个体特征进行深度挖掘,大数据分析的预期结果降低特定群体社会评价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同意研究者使用未声明退出(opt-out)的数据,免除再次获得知情同意。此外,因为国家规定检测剩余标本、信息和资料的保存期限应不少于3年以备追溯复核,故研究者申请对随机筛选的40例过期剩余复核样本进行15x测序,验证0.1x低深度数据分析方法有效性,且15x测序数据也不进行个体特征分析或公开发表。伦理委员会也予批准。该研究结果连同其研究范式在同行评议中得到广泛认可[6-7]。
2 免除个人具体知情同意审查的伦理考量
CIOMS 2016免除个人具体知情同意审查的条件(2)“社会价值”的判定与其他研究的伦理审查程序无异,在此不予赘述。另一关键依据是条件(3),即研究对参与者或所在群体的风险不超过最小风险。
审查实践中发现,某些知情同意书对研究风险的描述往往只详细描述采样风险,而对数据分析利用风险一笔带过或者忽视,客观上使受试者(资源提供者)未充分知情。伦理审查应把这两种风险区分评估。如前文论证,如采样风险被视作不超过最小风险[8],则数据分析利用风险应侧重于分析结果潜在受益、隐私保护和意外发现等方面。
2.1 再次获取知情同意对资源提供者的风险受益
案例3:某研究者与某市妇幼保健院合作,利用该院积存的400例0岁~5岁死亡儿童出生体检干血片从基因组层面分析早夭因素。研究者以该研究对社会群体有利、对个体无害、再次知情同意操作困难为由申请直接开展研究。伦理委员会认为干血片作为死亡儿童留存的唯一遗传材料,携带的遗传学信息可被适龄父母(即理论上还拥有生育力的父母)用作二胎生育指导,一旦消耗不可再生,具有个体“稀缺性”,不应完全被视为废弃物。虽然再次联系有一定难度,但增加了资源提供者(适龄父母)的选择机会,使其潜在受益大于风险。基于“有利”最大化原则,伦理委员会不同意研究者在不联系父母(监护人)的情况下直接使用样本,要求通过医院尝试再次获取具体知情同意。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再次征求父母知情同意其实也平衡了研究者和合作医院的责任风险。
2.2 遗传信息隐私保护
生物医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编码化或匿名化是公认的可保护受试者隐私的有效方法。但与其他个体识别性较弱的材料和信息不同,遗传资源所携带的数据和公开数据库比对后更易还原资源提供者的身份信息,甚至追踪到其亲属。“千人基因组计划”3名匿名志愿者的身份就曾由此被识别[9]。在我国已经出现遗传歧视案例、“反遗传歧视”立法还不健全的情形下,涉及基因组学研究的隐私保护应格外审慎,特别避免研究结果可能降低个体的社会评价[10]。
2.3 意外发现
案例4:某研究者推测NIPT检测如果数据出现异常,部分原因可能是受检者自身疾病(如肿瘤)的干扰,申请直接调取原始数据分析。该NIPT检测剩余样本和信息的科研用途也已获得广泛知情同意,但知情同意中并未预见和提及肿瘤。考虑到研究的预期发现明显超出原检测范围,对资源提供者有重大影响,伦理委员会依据知情同意书中提及受检者应接受必要的回访,不同意研究者免除知情同意,要求研究者修改方案,与资源采集方合作借助医学随访取得拟入组研究对象的再次具体知情同意。该研究后续确实揭示了孕期肿瘤与NIPT检测数据异常的强关联性,为孕期肿瘤的发现提供新的精准手段,也使得部分接受随访和再次知情同意征集的研究对象直接受益[11]。
如果伦理审查不考虑意外发现,轻易免除具体知情同意,都有可能减损资源提供者的权益:假如意外发现完全不反馈,那么资源提供者就丧失了相关的医疗机会;假如直接告知,那么资源提供者可能因为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会受到巨大的身心冲击。这会将研究者和伦理审查机构都陷入尴尬甚至纠纷中。意外发现的结果是否反馈,基本原则是结果是否可靠、是否具有干预措施。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s,ACMG)的指南具体描述了遗传咨询需要告知资源提供者(受试者)的若干种意外发现,伦理审查可以参考[12]。
3 讨论
世界医学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WMA)2019年10月修订的大会声明(EthicalConsiderationsRegardingtheUseofGeneticsinHealthCare)指出,以基因组数据为核心的基因信息具有以下特点:(1)基因信息可以用于识别个体;(2)基因分析能够大量产出个体的详细信息;(3)基因分析可能产生额外发现(additional findings);(4)基因分析所得信息的充分含义尚不明确;(5)个体基因信息不可能完全匿名化,去身份识别的基因信息仍然可能被重识别;(6)基因数据蕴含的信息不仅牵涉受检者,也影响与其有遗传关系的个体;(7)个体基因检测势必需要医生使用受检者或与其有遗传关系个体的医疗信息。因此,基因组学研究的伦理审查应有别于其他生物医学观察性研究的审查[13]。遗传信息的个体特异性、终身伴随性和族群相关性应成为影响伦理考量的核心要素[14-15]。
2019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规定获得人类遗传资源应尊重资源提供者的隐私,取得其事先知情同意,保护其合法权益。伦理委员会今后原则上不应受理和批准新采集遗传资源完全免除知情同意的研究申请。使用过往留存样本开展研究申请免除个人具体知情同意的,伦理审查应严格把握相关法规和指南设定的条件。
CIOMS 2016同时推荐了具体知情同意和广泛知情同意都可用于生物材料及相关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使用[4]。后者在综合型生物样本库中的应用正逐渐扩大[16]。CIOMS 2016还指明,“广泛知情同意的伦理可接受性有赖于适当的管理”。伦理审查并不能因为已有广泛知情同意而削减研究者的责任义务,反而应强化对资源提供者权益的保护,增进和维护社会信任。
就基因组学研究而言,如果研究方案使用的测序数据量不大(深度较低或覆盖度较小),仅涉及相关突变位点、突变频率,可以酌情免除具体的知情同意。如果使用个体全基因组高深度数据,或深度分析个人特征,不建议免除。此外,审查还应考量遗传材料的稀缺性、隐私保护和意外发现。一旦批准免除,需要定期跟踪,不能“一免了之”。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公众隐私意识的广泛增强,有条件地获取再次知情同意是一种与广泛知情同意相配套、增进资源提供者(受试者)对研究内容充分知情、强化资源提供者对个人遗传信息进行有效控制的手段,应该越来越多被鼓励使用。